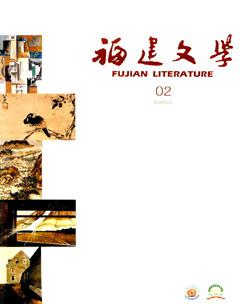马铺的金水桥
何葆国
北京有金水桥,我们马铺也有个金水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马铺的金水桥是1999年12月31日正式剪彩通行的,所谓千禧盛典,跨入新世纪,马铺人民只闻其名未见其面的许多大人物纷纷从北京从省城从其他城市回到这个南方小城,场面蔚为壮观。金水桥是一座悬索桥,横卧在兰水公园和江滨公园之间的内河上,全长380米,宽6米,为步行桥。索塔上“金水桥”三个题字,没有落款,一看就是老干部体,后来才知道就出自捐建者的手笔。
其实在我们马铺民间,早就有“金水桥”的说法,官方也视为荣耀,它指的是圩尾街刘家三兄弟,名字分别是建金、建水、建桥,合称金水桥,这是一种口碑,更是一种传奇,老大建金曾任本省副省长,后调至北京任某部副部长,老二建水曾任马铺县长、书记,后升任副市长,老三建桥曾在马铺经济局任副局长,后下海从商,收购多家国企,组建了金水桥集团公司,成为马铺最大的民营企业,他也一跃而为马铺首富。“金水桥”由马铺官方的荣耀和民间的传说演变成一座实体的建筑,正是刘建桥出的钱,刘建金题的字,剪彩那天,三兄弟一人一把金剪刀,金晃晃晃花了马铺人民的眼睛。那天我们在乔三皮的鸭面店里相聚小饮,也算是迎接新世纪吧,电视上正直播金水桥落成通行的盛大仪式,我看到电视镜头笨拙地从金剪刀摇到金水桥三兄弟的脸上,那三张写着马铺传奇的大饼脸啊,我立即跳起来,指着正默默吮吸可乐的刘良海说,刘浪刘良海,这不是你老爸三兄弟吗?刘良海头也没抬一下,说别跟我说这个,无聊。胡汉三手持酒杯,满脸绷得非常有正义感地说,刘良海刘浪,亲爸都不认啦?刘良海生气地站起身,把可乐瓶子掼在地上,又说了声无聊,就往外走。在灶前忙活的乔三皮转过身来,正挡在他的面前,他头一偏就走了出去。乔三皮连忙问我们怎么回事,我们也不知说什么,就指着电视机说,快看快看,金水桥落成了。
刘良海笔名刘浪,他一直不愿意在我们面前提及他的家庭背景,他说我们都是诗人,可以不那么无聊啊。无聊是他最常用的词。我们知道刘良海看重的是“诗人”的身份,以及诗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我们都是诗人,这句话在上个世纪末说起来,已经显得底气不足,如今更像是一句梦呓。然而正是因为“我们都是诗人”,我们四个人十多年来一直维持着一个相对稳定的小圈子关系,如果不是因为“我们都是诗人”,我们无论如何不会有任何交集。四个人中胡汉三年纪最大,乔三皮次之,我第三,刘良海最小。胡汉三是我们圈子里的叫法,他原名胡汉军,据说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跟诗人舒婷、顾城通过信,在一些地下油印刊物发表过不少诗作,还曾经跑到厦门鼓浪屿找过舒婷,结果失望而归,他大学学的是工科,毕业后分回马铺工作,因为写诗,跟领导和同事的关系一直非常紧张,后来不再写诗了,当了文化局副局长,不幸因为万把块红包的事被当作腐败的典型抓了起来,幸运的是判了缓刑,那时政策规定判了缓刑还可保留公职,所以他就一直在文化局当着普通科员,并恢复了写诗的习惯。乔三皮原名乔波,乔三皮也是我们圈子里的叫法,他原来是马铺糖厂的宣传干部,据说他的一首8行诗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在《诗刊》发表过,在马铺轰动一时,后来糖厂倒闭了,他自谋出路就开了一间鸭面店,生意不好不坏,店面几度搬迁,始终是我们四人小聚的固定场所之一。我在马铺读高中的时候突然热爱上诗歌,自然而然就认识了马铺最有名的诗人胡汉军和乔波,但是大学毕业后回到马铺,我当上了一名律师,所谓吃了原告吃被告,几乎就没空写诗了,正是在一次原告宴请的酒席上,刘良海第一次出现在我的生活里,他看起来年纪不大,却被放在比我重要的主宾位置,然而他一直显得不识抬举,不仅不喝酒,也几乎不动筷,神色凝重,对满桌美味佳肴没兴趣,对在座的主人客人也没兴趣,他就这样公然地不愿意表示哪怕一点点虚伪的礼貌。那原告和他熟络,就问他是不是又在构思新诗了,我就顺口说起我也喜欢诗,他的眼光唰地一亮,立即就盯着我看了好久,看得我好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一样。但是对他来说,却是在茫茫人海中找到知音似的,那天宴席散时,他非用他的太子摩托把我送回家不可,我们就这样相识成了诗友,他虽然身世显赫,但他从不以为然,甚至刻意回避,不久我又介绍他认识胡汉军和乔波,一个四人帮的格局就形成了,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至今,十多年来,风风雨雨,时紧时疏,不离不弃,差不多也是马铺男人友谊的典范了。
时下是2013年的盛夏,马铺热浪滚滚,但是马铺午间新闻告诉大家,马铺人民都挺好的,马铺的各项建设事业热火朝天蒸蒸日上。胡汉三来电约我在金水桥头的凉亭纳凉,我关掉电视,走出空调冷气充足的房间,迎面扑来的热气像是打了我一巴掌,好在金水桥离我办公室不远,胡汉三穿着一条大裤衩,腆着肚子站在亭子里,远远就对我说:“游西水,这边是自然风,别让空调把你吹得基因变异了。”
顺便说一下,我原名游东水,但是在我们圈子里,他们都叫我游西水。我走到亭子里,摸了一下胡汉三的肚子,表扬他说:“不错,相当于副处级了。”
胡汉三掀起一截汗衫,露出瓷实的肚皮,说:“要是刘浪在,肯定要批评你无聊了,诗人是不需要级别的,无冕之王。”
刘浪就是刘良海,这是他的笔名。这里必须介绍一下,刘浪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写诗,他已经出版了22本诗集,早年他买香港书号自费出版,后来听说这样不正规,省市作协评奖都是不认帐的,于是委托书商买大陆的书号重新出版了一遍。这没什么,他有的是钱,因为他的父亲是马铺金水桥的老三刘建桥。因为胡汉三说到刘浪,我就想起至少有半个月没见到刘浪了,不知道他在做什么,胡汉三说北京有几个教授正在把刘浪的一百首诗分别翻译成英文、法文、瑞典文和西班牙文,他准备先行推出中英、中法、中瑞、中西对照诗集四册,计划中还要出版中德、中日、中韩对照诗集,据说这都是北京一家图书公司帮他策划的,目的是走向世界,争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刘浪为此交了38万元。我听了不由很感叹,有钱真是好啊,胡汉三拍着肚皮,模仿刘浪的语气说,无聊。
亭子里有河面上吹来的风,吹到身上还是湿润的,让人感觉舒服。胡汉三说这些天的下午他基本上都是在亭子里渡过的,他的班可上可不上,因为就要退休了,没人管他,他说:“我就坐在这里,吹吹风,发发呆,有时望着金水桥,有时望着流水流向远方。”
我说:“我没你这么好命,我还要接案子,不然就没饭吃了。乔三皮也没这么好命,他要做鸭面,一碗才能赚一块钱,你是仅次于刘浪的好命人了。”
胡汉三满脸菩萨般的笑容,笑而不语。
有个男人从金水桥上走过,又有个女人走过,然后有两个相熟的男人在金水桥上相遇,停下来说话,日头白花花一片,晒得金水桥的钢索都在冒着热汽。我们坐在亭子里吹着河风,胡汉三突然用朗诵的语气说道:“即使不写诗,即使一贫如洗,坐在这里吹吹风,也是凉快的,金水桥的下午,像一根冰琪琳,生活其实就是缓刑,安逸不安逸,一切都在执行中。”
我说:“你这是梨花体呀。”
胡汉三说:“不,胡汉三体。”
胡汉三说他女儿在成都读的大学,毕业后在成都找了个男朋友,准备明年结婚了,胡汉三说那地方不错,他也喜欢,以后他就两头跑,马铺住腻了就到成都呆一段,呆腻了再回来。我说最近接了个案子,有点意思,有个男的喝酒醉了回家,走到楼下,居然门没关,就进了房间,床上的女人以为老公回来了,就和他发生了关系,现在这女的告男的强奸,男的被抓了放,放了抓,如今三进宫,我准备为他做无罪辩护。闲扯之际,乔三皮来电话,说中午有两个染头发的小年轻在他店里吃鸭面,声称在面汤里发现了一只苍蝇,用手机拍下了相片,乔三皮只好不收他们的钱,但他们一定要五百块钱作为赔偿,不然就要把相片放到网上,乔三皮为了息事宁人,把早上收的钱全都给了他们,也就三百多块,这两个小泼皮扬言晚上要来取那欠下的一百多块,乔三皮说我都一把年纪了,开店也开了十多年,没想到第一次遭到小泼皮的敲诈。胡汉三说,不怕,我们晚上到你那坐堂,给你壮胆。我说我们四比二,生擒小毛贼,扭送派出所。
又闲扯一阵,我跟胡汉三告别,相约六点左右到乔三皮的鸭面店见面。我们四个人的见面一般就意味着一起用餐(一人一碗鸭面,不够可以两碗),然后一边啃着鸭脖子一边喝酒(当然酒精严重过敏的刘浪是以饮料代酒),然后一边喝酒一边正儿八经地讨论问题或者漫无边际地闲扯八卦。回到办公室处理了一些文件,我六点整准时来到乔三皮的鸭面店,胡汉三说他已经在这坐了一个多小时了,两碗鸭面下肚,就等我来喝几杯。我连忙让乔三皮给我来碗鸭面,胡汉三说他给刘浪打了三个电话,他都没接。刘浪的手机时常放在他自己也记不得的地方,我们都是知道的,他一旦看到我们的未接电话,不管什么时候都会打过来,现在只有等他的回电了。
我吃过一碗鸭面,乔三皮端来几根鸭脖子,胡汉三开了三罐喜力啤酒,一人一罐对着嘴喝起来,也不用杯子。顺便说一下,这喜力啤酒是刘浪整件整件买过来放在鸭面店的。
胡汉三咕咚咕咚灌了一口长气,抹着嘴说:“刘浪没来,那两个小泼皮也没来。”
我看到店外面的天都黑了,掏出手机说:“我再给他打一下。”从电话簿里拨出刘浪的号码,是一首很恶俗的彩铃,唱过一遍无人接听,重播的时候才被接听起来:“嗯。”这也是刘浪接电话十几年不变的第一个声音。
“你在哪里呀?怎么不接电话,也不过来?”我大声地咋呼。
“我在北京。”刘浪说。
“怎么了,你怎么突然跑北京去了,也没吭一声?”
“我本来也不想去,可是……”刘浪在电话里顿了一下,“我、我大伯突然不行了,今天中午过世,我们家一大帮人都来了……”
我们三人几乎同时哦了一声,原来是“金水桥”塌了一角。这时,电话断了,再拨过去,对方已关机,我们估计刘浪的手机是没电了,他那苹果手机很不经打,我们甚至猜测他不会记得带充电器到北京的。话说金水桥一直是我们马铺长盛不衰的话题,前几年刘建金退休享受正部级待遇,依然有专车、秘书和保姆,去年回马铺探亲,那前呼后拥的场面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了,他在电视上用马铺土话说他很喜欢家乡的生活环境,准备过几年回来养老。谁知道呢,突然病故于千里之外的京城。因为电话联系不上,我们无法向我们的朋友表示一下节哀顺变的慰问。其实在我们长达十多年的交往中,刘浪从来不说起他家这位贵为京官要员的大伯,对我们的议论也一向嗤之以鼻。但毕竟那是一道耀眼的光环,照亮了刘氏家族的人生,刘浪不愿意沾光,事实上也被罩在了里面。
这个晚上,那两个小泼皮最后也没来,乔三皮关上了店门,我们多少都有一点失落。
第二天从中午开始,我连续被请了三摊酒,最后一摊还在酣战中,我偷偷溜出了酒店,已是晚上十点多了,我发现这一天除了啤酒、葡萄酒和一种本地米酒,还有一些荤料,我没吃过一粒米,也没吃过一口面,肚子突然饿得难受,便叫了一辆人力三轮车,直奔乔三皮的鸭面店。
我刚下车就看到刘浪坐在店里埋头吃着鸭面,他那微秃的脑门上闪着灯光和汗光,嘴里发出嘶嘶的响声。我放轻脚步走过去,准备吓他一下,没想到还没走到他面前,他就抬起头,鼻子抽了两下,说:“酒气这么重。”
“刘浪,你怎么不在北京给你大伯守灵呢?”我呼着酒气说。
“我刚回来,我肚子饿坏了,飞机上什么都没吃。”刘浪说。
这时鸭面店里的电视正在播放马铺新闻:马铺县委书记、县长等主要领导满怀悲痛,代表全县58万人民,前往北京悼念不幸病逝的马铺乡贤刘建金同志。电视上播出从北京现场传回来的镜头,刘家灵堂,刘建金遗像,书记、县长的脸一晃而过,然后定格在刘建水、刘建桥等一干亲人的脸上,又闪回书记、县长的脸,哀乐声声……刘浪从桌上拿起遥控器,一下把电视关掉。
“干吗关掉?我看看嘛。追悼会还没开,你怎么就回来了?”我说。
“人太多了……没什么好看。”刘浪说。
“刘浪,对你大伯的不幸逝世,我向你表示沉痛的慰问。”我说。
刘浪站起身,冷冷地说:“无聊。”
尽管我知道“无聊”是刘浪最常用的口头禅,在不同的语境有不同的意思,但此时他使用这个词的用意以及他脸上毫无表情的冷漠,让我感到不可理喻的同时怒不可遏,我不由吼了一声:“你大伯死了,金水桥塌了一角,你怎么无动于哀?有你这么冷酷这么不近人情的诗人吗?”
刘浪嘴角扯了一下,说:“这关你什么事?”
我说:“这是不关我的事,可它跟你息息相关呀,你大伯过世了,你作为他的亲侄儿,应该在北京参加他的葬礼。”
刘浪瞪眼看着我说:“无聊,你也教训我来了?告诉你,我是诗人,我不喜欢什么金水桥……”
我哈哈大笑,笑声像一群炸飞的麻雀满屋子乱窜,我指着刘浪说:“你敢否认吗?刘浪,要不是金水桥罩着你,你能这么舒服地当着你的诗人?”我咽了口水,继续说:“要不是有你大伯,你二伯能当书记县长副市长?要不是你大伯二伯,你老爸能收购那么多国企,摇身变成马铺首富?要不是你老爸是马铺首富,你一本诗集也出版不了。”这时,乔三皮好像从外面回来,惊讶地问我是不是要开批斗会?我有了听众,便借着酒劲更加猛烈地数落起刘浪,我说:“刘浪刘良海,你一方面享受着金水桥给你带来的无穷无尽的好处,一方面又不屑提起金水桥,追求什么人格独立,狗屁,你要独立就别要你老爸的钱,你的诗能当饭吃吗?能赚得来一分一厘的稿费吗?我觉得你太虚伪了,太造作了,你想从精神层面切断跟金水桥的关系,你首先就不要它的物质利益,你做得到吗?你做不到,所以说,你一直戴着沉重的矛盾的皑甲面具,你不觉得你活着太累吗?”
刘浪定定看着我,说:“游西水,你说得好,我们都是诗人,也是十多年的老朋友了,你说得好。”
我接着说:“我说错了吗?我没说错吧,你可以清高,可以特立独行,可以蔑视权贵,可是凡事有个度,过了就不好了,事实上,你的清高也罢,特立独行也罢,都只不过是你造作的假像,你要是真的清高,你就靠你的工资来养家糊口,然后节衣缩食来自费出版你的诗集,你有种就不要到你父亲的户头上取钱……”
乔三皮上前拉住我说:“游西水,你说这些干吗?你今天真是喝多了呀,大家都是老朋友,说这些干吗?真是的,无聊!”
我说:“有感而发嘛,刘浪说过我们都是诗人,诗人就是想说就说嘛。”
乔三皮对刘浪笑笑说:“刘浪,他说他的,你别往心上去。”
在我们这四个人的圈子里,乔三皮一向是和事佬。不过回想起来,我也是很久不曾这么壮怀激烈,慷慨陈词了,这几年来随着年岁渐长,大家一直很和气,最多调侃几下,挖苦一回,已经不再这么赤裸裸的直捣内心。
刘浪又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转身走了。
乔三皮责怪我说:“你这是何必呢,每个人都有他的难处……”
我手一挥说:“不废话了,快给我来碗鸭面。”
吃过鸭面,我搭了辆人力三轮车回家。一身酒气的,老婆难免唠叨几句,我也懒得理她,进了自己的书房,关上门,把沉重的躯体卸在电脑前的转椅里,思绪飘飘荡荡的又飘向了“金水桥”。马铺民间认为,“金水桥”是马铺几百年风水所致,我也是认同的,一个地方总是注定要出现一个强势的家族,据马铺民间不完全统计,金水桥家族单单在马铺县就有副科级、正科级、副处级领导将近30人,分插在各个重要的部门,不从政的,就经商,房地产、矿产、水电、通讯、物流、酒店娱乐等等热门行业,他们都占据了相当的份额,唯独刘良海刘浪是个异数,中专毕业分配在马铺县总工会,一直就没挪窝,既不从政也不经商,只是写诗,写写写,然后自费出版。是的,刘浪写诗,以此显示和他们的不同,可是他拿了老爸的钱,虽说老爸的钱不拿白不拿,但是他的清高就因此大打折扣了。我想起那金水桥落成不久,也就是2000年春节期间,刘浪的母亲不幸病故,据说他母亲病故前把10间旺铺全部转到他名下(现在一间旺铺的年租金就有8万元),同时要求他父亲给他一张VIP消费卡,透支额度50万元,因为他母亲早已知道他父亲后面有人,果然在她病逝半年后,刘浪的父亲光明正大地迎娶了一个比刘浪大不了几岁的新妻,现在生育了一男一女,马铺民间传说他另外在外地还养了小三小四,也各自生了一个男孩,因为这样的缘故,刘浪自然无法跟父亲亲近,形同路人,所以他写诗,在诗中寻找情感的慰藉——其实刘浪是从中学阶段开始迷恋上写诗的,也正因为诗,他和父亲的关系一向格格不入,父子间的裂痕不断扩大。也许不写诗的话,刘浪就不会跟父亲弄僵了,他就有可能成为父亲所期望的人,按父亲设计好的路子走下去,谁知道呢,诗这玩意儿,是他的食粮又是他的毒药,是救了他呢还是害了他,到底是害了他呢还是救了他,真是说不清。
这晚上迷迷糊糊没睡好,第二天醒来,已是九点多了,手机上有几个未接电话,其中一个是胡汉三的,我首先回拨过去。
“听说你昨晚在鸭面店把刘浪狠狠说了一顿,他半夜三点多就打电话给我,说他一夜无法入眠,我本来睡得正香,结果惨死了。”胡汉三说。
“哦,这个……”我猛地坐起身,酒是全醒来了,“昨晚喝了点酒嘛,其实也没说得多狠吧,平时我们含沙射影的也跟他说过,只不过昨天直截了当而已。”
“刘浪跟我说,你的话让他很震撼,他要开始反思自省……”
“反思自省,这不是也很累吗?”
“人活着哪个不累,诗人就更不用说了,他虽说衣食无忧,锦衣玉食,可他的心比谁都累,你要多理解嘛,我们都是十多年的老朋友了。”
“嗯,嗯,理解,理解。我等会给他打个电话道个歉吧。”
“道歉?倒也不必,你也没什么错,我的意思是提醒你一下,以后多注意,大家不要伤和气。”
挂断胡汉三的电话,我正寻思着怎么给刘浪打个电话,他却先打电话来了,我连忙接起来,说:“刘浪,昨晚我说话比较冲,你别在意……”
“不,我很感激你,你说了真话,我想了一晚上,”刘浪说,“确实如你所说的,我一方面享受着金水桥的好处,一方面又不认同它,这显示了我的人格分裂,说明我作为一个诗人是不够真诚的,你的话犹如醍醐灌顶,我真的应该醒过来了,这样我的诗才会有长进,越写越好……”
“不,不,不,”我紧张地叫起来,我想刘浪所谓清醒之后,是不是就要切割“金水桥”的经济来源,开始自食其力?那他一千多块的工资真的只能让他作一个穷困潦倒的诗人了。我说:“刘浪,其实,我昨晚也是瞎说的,每个人生活方式不同,文学艺术嘛,本来就是有钱有闲的事业,你不用多想,上辈给你的钱财,其实是你的福气……”
“我想明白了,谢谢你,游西水。”
刘浪把电话挂断了,我不由长吁一口气,心想刘浪到底想通了什么,他到底想怎么样呢?这个物质的时代,他如何从容地写诗?尽管他的诗……说实在的,作为一个富二代,他不抽烟不喝酒不泡妞不飚车,就兴趣一个写诗、出版诗集,尽管他的诗……这是一个多么难得的人啊,这么多年来我们能在一起,不正因为诗吗?尽管他的诗……
下午三点多,胡汉三突然跑到我办公室,向我报告了刘浪刚刚作出的四个决定:退还父亲给他的那张可以透支的消费卡,把10间旺铺捐献给马铺慈善总会,把锦江花园的复式房留给老婆孩子,他独自搬回圩尾街的老宅去住。胡汉三站在空调冷气下面,依旧满头冒汗,他说:“这个刘良海刘浪,看来神经线有点故障了。”
“他要真的这么干,他老婆会同意吗?”
“肯定不同意呀,他们就吵起来了,这也是小唐打电话告诉我的。”
小唐就是刘浪的老婆,我们都是认识的,但是不大熟悉,她看起来跟刘浪就是不同类的人,开跑车、挎名包、披金戴银,比较张扬,她对刘浪写诗以及跟我们的交往,基本态度还是支持的。我知道她一个小妇人的心思,只要老公在外面不学坏,不招惹女人,脾气古怪一点,花些钱出些诗集,这又有什么要紧呢?
胡汉三说:“小唐让我们去给刘浪做做思想工作。”
我说:“昨晚上我的话真的刺激他了,上午他给我打电话说他想通了,我就猜测他可能会走极端。”
“游西水,你老实说,你是不是嫉妒刘浪的身世和财富?”
“是的,你不嫉妒吗?人家是含着金汤匙出世的,父亲资产几个亿,大伯二伯都是高官……”
“可他还是有精神追求的,不同于其他的纨绔子弟。”
“是呀,说起来我们也是诗人,写了十多年前的诗,一本诗集也没出过,单是一个书号就一二万块,下不了手,可人家眼也不眨一下,就一本接一本地出。”
“我觉得刘浪还是不容易,他本来可以选择别样的人生,可他偏偏喜欢诗。”
“胡汉三,现在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一定要说真话。”我认真地看着胡汉三说。
胡汉三拍拍肚子,走到沙发上坐下来,说:“我什么时候没说真话了?”
“好吧,那我问你,你觉得刘浪的诗怎么样?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准?他有写诗的基本素质吗?”
“靠,你这三个问题了。”胡汉三笑了一下。
刘浪的诗,我、胡汉三、乔三皮都是认真读过的,他所出版的诗集,每一本都签名送给了我们,我们一般以“这首总体还不错”、“这首比前面那首好一些”、“这几句意境不错”这样比较笼统的话对他进行表扬和肯定,我们没有详细解读过他的诗,我感觉以我们三个人的审美能力是可以作出一个比较中肯的判断的,但是我们心知肚明,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公开地坦诚地把这个问题摆到桌面上来,只是各自在心里嘀咕几声便作罢,因为此时我们更看重的是朋友而不是诗,虽然因诗而成为朋友,但朋友肯定比诗更重要吧。
在我目光的逼视之下,胡汉三突然有点不自在,说:“告诉你,乔三皮也曾经问过我这个问题,跟你说实话吧,我觉得刘浪的诗陈腐不堪,最多只达到市级晚报副刊发表的水平,他应该没有写诗的天份和素质,只是靠着执着和勤奋,把若干文字分成行而已。”
“我同意你这一评价。”我说。
“可是,在他面前,我们能如实告诉他吗?这年头,爱诗的人越来越少,难得他一个富二代还如此痴迷诗歌,鼓励为主,不算是谎言吧?我没有违心吹捧过他的诗,他有时花钱从北京买一些什么‘新世纪新诗经典大奖、什么‘中国风大奖回来,我们明白他的虚荣心,虽不说破,但总是要讽刺他几句的,这回北京书商要给他策划几种外文对照的诗集,还要向什么诺贝尔冲刺,我本想告诉他人要有自知之明,感觉这句话太重了,最终还是没说出口,不管怎么样,刘浪还是一个不错的朋友吧。”
“是呀是呀,我们四人吃饭他买单最多,他还说过要赞助我们三个人一人出版一本诗集,只是我们自己不想出。”
“如果他是一个天才,就让他去经受苦难好了,那会有结果的,可他不是,他能有金水桥的福荫,也是他的造化,哪能轻易放弃?所以,我们要好好劝他一下,我看就这样,我打电话叫他来鸭面店,我们三个一起劝他。”
我点点头。胡汉三掏出手机打刘浪的电话,已关机,再打他一个同事的电话,被告知刘浪下午没来上班。我说你打小唐问问吧。胡汉三便打小唐的电话,小唐说刘浪带着自己的铺盖回圩尾街老宅去了。
“走,到圩尾街去。”胡汉三说。
我开车载着胡汉三往圩尾街跑。圩尾街是一条老街道,车开不进去,只能停在街头的观音庙前。我们刚下车,只见乔三皮开着电动车直往我们奔来,我从没见过他神色这般慌张,嘴里念叨着死了死了,这语境里马铺话死了就是糟了。他慌乱中似乎刹不住车,我和胡汉三一人一手按住他的车头,他的电动车才驯服地停住。
“怎么啦,看你这样子?”我说。
“死了死了,我刺激到刘浪了,比游西水昨晚还严重,我越想越不妥……”乔三皮说。
原来乔三皮刚才在鸭面店门口遇到刘浪,刘浪用自行车载着铺盖要往圩尾街,他告诉乔三皮四个重大决定,乔三皮一听就急了,大声地嚷道,你傻呀,你简直全马铺最没脑子的人,你以为这样就能写出好诗来呀?我们起早摸黑的为了吃饭,你不用干活就有饭吃,那是你命好,命好才有闲有钱写诗,你以为你是曹雪芹呀,生活一困顿就能写出《红楼梦》?告诉你,你没写诗的天才,受苦也是白受,还是好好享你的清福吧。
“刘浪当时脸就黑了,眼睛长刺一样盯我一眼,踩着自行车就跑了,那时刚好有两个客人来吃鸭面,我越想越觉得不妥,我真是言重了,他心里肯定受不了,客人一吃完面,我就关了店跑过来……”乔三皮喘了一口气说。
我和胡汉三听了,默不作声,我们实在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
“我一急话就说重了,我不应该对他说这么重的话……”乔三皮带着愧疚的语气说。
我们抬脚往刘浪的老宅走去,记得有一年的一个假期的傍晚,刘浪曾经带我们到过他家的老宅,那已经空置多年的老宅,弥漫着一股阴冷的气息。凭记忆找到刘浪家的老宅,那紧闭的门上锁着一把铁锁,还加了一条锁链。刘浪用自行车载着铺盖过来,早就应该到了,可是这紧锁的木门看样子都好久未曾打开了,刘浪不可能有缩身术钻到里面。
我们猜测刘浪可能半路上先拐到哪里去办事,比如到小超市添置一点什么,我们就在门口等待他的到来,边等边聊,这其间乔三皮和胡汉三分别给他拨了几次电话,均是关机状态,我们等啊等,等到天黑了,刘浪也没有来……
最后简单一点说吧,刘浪一直没有来,他失踪了。我们知道他的失踪跟我和乔三皮的话语是有关的,这让我们倍感愧疚,赎罪般地积极配合亲友、单位和警察多方寻找,现在一个多月过去了,刘浪还是没有一丝音讯,而这期间,马铺发生了许多事情,其中和他最有关联的就是他的二伯,也就是金水桥的老二刘建水由副市长改任政协副主席,又干了一届五年,在卸任前几天被双规了,而他的父亲,也就是金水桥的老三刘建桥也因为偷税漏税,被有关部门查处。马铺民间传说,因为金水桥最有含金量的金缺失了,水就枯了,桥也将塌陷。也正因为金水桥的这两件大事,对刘浪的寻找暂告一段落。我们三人时常在鸭面店碰头,每次都必定说起刘浪,我们更愿意他还在人世,只是不知道他躲藏在哪个角落,当他知道金水桥发生了这么重大的变故,他是窃喜呢,还是无动于衷?按照他失踪前的思想变化,他应该正中下怀的窃喜一场——可是,你这家伙,怎么就不露个脸呢?
责任编辑:练建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