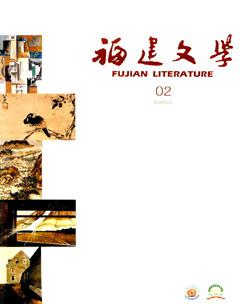走失在莲花湖边
一
我清楚地记得,那头黑驴来到我家是一个黄昏,它被拽在父亲手里,畏怯地扫视着陌生的环境,不停地打着响鼻。后来,父亲把病床上的母亲背出来,驮到了驴背上,在最后的一抹夕阳里庄严地对母亲说,有了驴,我得出去“拉脚”了。
拉脚是出去挣钱的意思。
父亲第一次出去是一个雾天,雾气水一样流淌,很快把父亲和驴车裹住了,从雾气里传回的只有嗒嗒的蹄声,直到走到县城雾才小了起来。父亲站在县城的大街有些茫然,父亲是来县城的屠宰场收骨头的,像村里几个做收骨头生意的人一样,把收来的骨头再卖到一个城市的骨胶厂。可父亲是第一次,不知道屠宰场在什么地方。父亲牵着驴走到了马市街,不断出现的小胡同让他眼花缭乱。穿过人流,他揣摩着到底该去的方向。云开雾散,阳光穿过县城的楼巷。他最后按照一个清洁工的指引,终于找到了一家屠宰场,怯懦地敲开屠宰场的大门,父亲手上出现了一层发粘的东西,然后闻见了浓重的粪尿味儿,看见一股血水正汩汩地往一口大池子里流,屠宰场里的几十棵椿树上粘着厚厚的油腻,浓重的腥气扑面而来使他想呕。他牵着驴,使劲地鼽鼽鼻子,驴打了几个响鼻,大概排斥强烈的腥味。忽然,驴狂叫起来,父亲心疼地捂着胸口,大院里响起一片牛驴的叫声……
父亲收来的骨头垛在厕所外边的一个角落,用一个大塑料布盖着,等到一定的数量再送到焦城的骨胶厂。每天的傍晚,父亲回来后,我和妹妹跑出去帮父亲先把黑驴卸了,牲口槽里有我早已拌好的青草,青草散发着来自土地的香气。在等待父亲回来的傍晚,我常常坐在驴屋的门槛上,听着嗒嗒的驴蹄声,或者从村口传来的那一阵艮呱艮呱的驴叫。
父亲的“拉脚”逐渐正常,每天晚上他在母亲和驴屋之间穿梭,和母亲算着收来的骨头,对母亲说,我得把驴喂好,它是来帮咱的是咱家的贵人,你好好养病,有这头驴帮咱今后的日子就好多了。
半月后的一个雪天,父亲没有回来,我和妹妹在路口的雪地里冻僵了,成了雪人。雪无声无息地越下越大,世界很快蒙上了一层皑皑白雪,看不见大地,看不见沟壑,树顽强地顶着纷纷扬扬的大雪。这个夜晚我们偎在母亲的床前,握着母亲的手,母亲的消瘦加上对父亲的担心让我们害怕,母亲的指甲陷得越来越深,我给母亲做的汤面,她倚着床头吃了几口再也吃不下去。我踩着雪去村外,积雪深了,雪钻进鞋筒里冰凉,踏出的雪窝又被卷过来的雪弥住。母亲说去槐屯的桥上看看吧,我走了几步又被娘叫住,母亲艰难地挥着手,说,离桥栏远些。我踩着雪往槐屯去,我看见的只是大雪,雪铺展而成的雪原,雪晃得眼都花了。
风起来了,把一层一层的雪往沟里刮。
第二天,父亲还没有回来。
我们沿着雪地走,一直走,走很远很远,却总看不到驴车的影子,我们又回到桥头等,我们等成了雪人了还不见父亲的影子,听不到驴的叫声,世界很静,这种天,路上没有车辆。妹妹在雪地里喊,爹,爹……问着,咱爹咋还不回来?我拉着小妹的手,冰凉冰凉的小手,踩着雪往家里回,雪在脚下咯吱咯吱地响,两个小脚印被一阵风吹乱了。我们得回家看母亲,母亲还躺在床上。
第三天,我们全家都出动了,我去求了老塘南街做同样生意的人:老连叔、张山……他们散开,在周围的屠宰场里都没有见到父亲。母亲从床上挺起来,扒着窗口朝窗外看看,对围在我们家里的人说,这老二,难道要走在我的前头?
可是,父亲回来了,而且拉回来了半车骨头。父亲的落拓让我们心疼,他的半个脸肿着,一条腿翘着,走路一瘸一瘸,穿在身上的皮袄划出几个洞,露出了里面的棉絮,架子车歪歪裂裂,狼狈不堪。父亲像一个挂彩的伤兵,只是背上缺少一杆破枪。雪后的冷月破云而出,黑驴和父亲站在一起像一对残兵败将。
父亲说,那天,他实在是回不来了。
第一天,父亲一连跑了几个地方都没有收获,在他从第三个地方出来时雪飘老毛子一样下来了,纷纷扬扬。他不想空手而回,他挥了一下鞭,黑驴拉着他往县城的另一个方向,后来父亲才知道驴把他拉到了牧城的北站区,里我们的县城很远很远了。父亲终于找到了一家屠宰场,门终于开了,首先卷进门的是一场厚雪。屠宰场因为下雪停工,骨头倒有,堆在房后的一个角落,蒙着一层雪,地面结了冰渣,老板说,你怎么选了这么一个好天?
他说,摸这儿了,大雪天我都不知道走到了哪儿。你不卖给我,我只有拉一车雪走。老板指指骨头,说只有雪天你可能有这好的运气,不怕冷你自个儿装去。骨头装好天暗下来,哪里还看得见路,雪明得连灯光连树都是模糊的。父亲有些怵,路上是少得可怜的比驴爬不了多快的汽车。黑驴拉着父亲小心翼翼,车轱辘在雪地上往歪处扯,蹄子踩上去一声声闷响,踩下去的不是路是雪。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上了一条岔道,父亲说迷茫中他看见了一座桥,桥西边是看不见流水的白沟,几根芦苇从沟边刺出来,父亲心里就犯了怵。眼看着上了桥,父亲下意识地往车下跳,谁知道桥上有个窟窿正好踩了进去,呼哧一声一条腿下去了一半儿,身子趔下去,脸生疼地扎在雪凌上,他使劲地用胳膊往外架,叫了一声娘啊,掉下去可是一条深水沟啊。黑驴这才看见了,咴咴地喷着响鼻,哽哽地发出无可奈可地嘶鸣,低着头,蹶着蹄子。他觉得自己不行了,要是掉下去大雪天连个尸首也不好找,好婆躺在床上没人照顾,两个孩子别想再上学。他闭上眼,架着胳膊努力地往上挣扎,他睁开眼,有些乞求地看着黑驴。
父亲说,其实,驴儿是我们的恩人啊。父亲开始叫黑驴驴儿。驴竟然叼住了他的前衣襟,蹄子咚咚地扣地,身往后坐着,拼命地往外叼他,呼呼地喘着粗气,喉眼里哽哽地叫,他伸手拽住驴的笼头,驴低低头,猛力地往上挣,低低头又猛力地往上挣;有几次驴滑倒了,再起来挣,挣了几次,终于将他扯出来了。他躺在雪地上不想动,浑身疼,想自己没有掉下去说不清又要冻死了。他躺着,听见黑驴把车往前拉,小心地错过他的身体,在车身挨着他的身体时它停下来。他终看出了它的意思,使出浑身地力气扒住了车杆,翘了几次腿扒到了车厢里。黑驴把他拉到了一个大路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停在了一个小车马店前,他昏迷着。黑驴可怜地瞅着车马店的老板,不停地挠着蹄子,老板被驴感动,把他送到了一家小医院,又给他买了碗热汤面。雪停了,他从医院顺着已经辗化的路回来了。
二
父亲赢得了同情,每天晚上总有人打听父亲的消息,甚至去街头翘望父亲的身影。有人拉我的手,拍我的膀子,安慰我说,别急,孩子,你爹马上就会回来。有人对我说,孩子,争口气吧,好好学,混出个人模狗样的让你爹享享晚福。多少年过去,当我伏在一座城市的案边来写这段生活时,我感谢父亲当年智慧地选择了一头毛驴和一个“拉脚”的门路,使一个家在困境中往前走,母亲能在床上多躺了两年,我们又多了两年有母亲的幸福。
父亲救了一头驴。父亲去了乌城,他又看见了马市街的清洁工,他站在大街,想起他第一次来乌城,乌城的大街飘满落叶,弥漫着雾气,他茫然地问清洁工屠宰场在什么方向,清洁工指给他一条叫夏街的胡同。
父亲回忆那头驴好像认准了他可以救它。那是一头青驴,青色的驴身滚着汗水,已经被绑在桩子上,屠夫把大锤掂在手里,锤上沾着血,锤把变成了血色。驴捣动着蹄子,咴咴地喷着响鼻,响鼻里喷出的是一种绝望,一绺粘稠从鼻腔里流出来,尾巴宛如一根钢筋猛然直挺,腿根暴出粗大的青筋。父亲紧张地站着,仿佛自己受到了威胁,他更紧地攥着黑驴,生怕大锤砍到它的头上。父亲的腿开始颤抖,牙颌嗒嗒地打着梆子。父亲说,就是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中他看到了青驴的眼睛,乞求哀怜的眼神让他的心滴血。驴的眼泪一颗颗渗过眼角,像一条河长流不止。有一刻,青驴忽然把一双眼可怜地朝向它,朝它乞求,咧着嘴,似乎认定了父亲就是救它的贵人。
父亲抓住了那把大锤。
那是父亲回来最早的一次,父亲的车上没有骨头,跟在车后的是那头青驴。两匹牲口后是溅起的烟尘,村里人都奇怪地看着父亲和父亲带回来的青驴。父亲坐在地上,给村里人讲着经过,母亲被我背出来坐在父亲的身后。我看见村里人坐着、蹲着都直直地看着父亲,听父亲讲。
可是,我们家养不起两头牲口,那天晚上父亲把两头驴喂到了一个槽上,拌了草料,使劲地拍拍青驴。驴仰着头没有贪吃,扑闪着眼看父亲,那神情像一个懂事的孩子。几天后父亲去找了田交易,然后有一天我们家来了几个人。青驴恢复了常态,咴咴的响鼻里充满了温柔。我看见这头青驴,如果父亲出现在它的身边,它总会歪过头看着父亲,在青驴心里,父亲已经成为它的亲人。父亲对田交易说,老田,这驴善,你找个好人家,要养着,不能送屠宰场,你比我懂,还是好牙口,我实在养不起才找你的!青驴是五天后被牵走的,那人看着像个善人。那一天傍晚,青驴被牵在新主人手里出了我家栅门。突然,我们又听见急骤的蹄子声,青驴抖开缰绳跑回了院子,久久地站着,看着父亲,咧着嘴,又咴咴地打着响鼻,神色庄重。父亲不知所以,搂住了青驴,捋着它的鬃毛,低着头说,对不起,我实在养不起你,我还会再去看你的!青驴点点头,突然跪下了双腿!父亲早已经泣不成声。
三
母亲还是走了。下了一场春雨,春寒料峭,雨凝成雪粒,又变成米粒样的细雪。殡母亲那天雨雪还一直在下,我们踩在泥泞里向坟地走,黑驴驮着来吊孝的亲戚,耷拉着头,耳朵下垂,尾巴拖地,淋得浑身湿透。按照风俗,父亲没去坟地,在门口无声地掉泪,后来,他倚着墙坐到了泥地上。一路的白衣拥着棺木,母亲的一生就这样结束。
父亲把更多的时间用来侍候我们家的黑驴,我们家的驴倒在这种环境中膘肥体壮起来。几天后,父亲又赶着驴上路了,在乡间的道路上父亲任驴车不紧不慢地走着。那几天父亲一直都是这种不紧不慢的状态。
我的眼前经常出现我们家黑驴的一次逃逸,多年以后,我的本家叔回忆起来还禁不住捧腹大笑,嘎嘎嘎,你们家的黑驴。那年的春天,沧河清淤,毛驴被牵到清淤工地上。黑驴被牵到河上后,父亲天天坐在门口等它完成任务后回来。
黑驴逃逸的壮举是在一天傍晚,在又拉上一车淤泥后它挣脱了缰绳,蔚蓝的天空里飘满了蒲公英的翅膀,小麦地里飞旋着麻雀和一排彩色的蝴蝶。它忽然有了逃逸的念头,我想那一刻它可能想我的父亲了,它突然撂起蹄子开始狂奔,那些开放的迎春,穿过麦地的米蒿,路边的狗尾巴草和车前草都被它抛到身后。它狂奔的四蹄让人望而却步,套在它脖子上灰白的护脖像一个神秘的怪物在夕阳下晃动。黑驴的后头是我的本家哥哥和一个远房叔叔,然后是整个队里的年轻人。它狂奔着,飞一样掠过河堤,身后是蹄子溅起的一路尘土,整个大堤上的驴都狂风暴雨般地叫起来,震耳欲聋,在对我家的驴呐喊助威。黑驴逃进了乌城,跨过乌城的几条街道,迅速地把乌城跑了一遍。最初它在北城门停下过脚步,越过北城门就是它来过多次的城区,它熟悉的街道。它回过头,我的哥哥和远房叔叔被它远远地抛在千米之外。溅起的烟尘还在弥漫,一绺绺往空中漫延,纷乱的草屑在风中舞蹈。哥哥和远房叔叔气喘吁吁,东倒西歪,奔跑的能力根本就不是一头驴的对手,如果和一头驴赛跑胜出的无疑是驴。
这是黑驴第二次逃离工地。第一次离开工地是在一个夜晚,守在家里的父亲忽然坐卧不宁,心里又堵又乱,他踱着步,觉得会有一年大事发生。他想看到母亲或者母亲的遗像,可是没有,每一次抬头后的失望,他就惭愧没有留下母亲的遗像是一个巨大的失误,后悔自己没有画像的技术。他曾经在我和妹妹之间巡视,说你们两个能不能选一个去学画画,把你妈画出来,你们谁有这样的能耐再刮我一层皮我都高兴。我们大眼瞪小眼瞅着父亲,心里酝酿着当不当画家,直到今天我还在后悔当初没有听父亲的话去学画画当一个画家,哪怕学到能把母亲画出来的水平。没有母亲的遗像,父亲只有朝着母亲经常倚卧的床头用劲地捂着胸口,等待将要出现的大事临头。后来,老实巴交的父亲走出房间,仰头看着星星一颗一颗地发白,像正在成熟的杏儿。父亲看一眼闲下来的架子车,他喜欢赶着毛驴外出的日子,在家的日子让他发闷。父亲倚着栅栏门,胸口还在咚咚地跳,这样老的心脏这样跳一定会有事情发生!一定会有事情发生!要不就是会有亲人回到他的身边,要不就是谁有什么灾痛。父亲每一次都相信他的预感。父亲在迷蒙之中终于听到了踢踢踏踏驴的蹄声,由远及近,像敲响的大鼓,父亲的心呼啦松了。父亲和黑驴相对着脸,驴静静地站着,像一个孩子,后来父亲抱住了黑驴。
我们家的黑驴在乌城狂奔,奔过北城门后看见的是一条传统的大街,这是乌城的老北街,路两旁的店铺冷冷清清,瓦房上结着苔藓,从院落里穿出来几棵桐树,桐树叶像乡村的大锣。黑驴往南看到了热闹的马市街,大街上人影晃动,叫卖声刺耳,它最后选择了往东;往东的路叫做夏街,它和父亲第一次来乌城收骨头进的就是胡同里的屠宰场。
我们家的黑驴看见了父亲,父亲正自己架着车,弓着腰,满头大汗,车上装满了骨头,一头苍白的头发在夕阳中干燥而且凌乱。父亲抬起头,看见了驴,他仰起头叫了一声,驴儿。撵过来的人都愣在那儿。
四
父亲的凳下长满了荒草,荒草在秋风中摇曳,栅栏门外是两棵椿树,零落的椿牌儿吊在树上。父亲倚着西侧的椿树说,你们都不要管我,如果驴儿回来了我能听见。父亲每天都等到半夜,露水把胡子打湿,头上冒出了一层霜气。半夜里我悄悄地出来,默默地坐在父亲身边或者给他披件衣裳。父亲不说话,似睡非睡地面向大街,老塘南街静得能听见鸟儿的呼吸。一只狗在大街上遛食儿,看到我们默然无声地离开,院子里传来一只鸡的呓语,咕咕几声又沉入了梦乡。父亲攥攥我的手,仰着头,很小的声音,儿啊,睡吧!大约过了十几分钟,又说,你去睡吧!又过了一个时辰,父亲说,儿,还没去睡,你还要上学。你放心,咱家驴儿会回来,不用找它,它很懂事,比你们还有智慧,它能在雪坑里救我,你说它多有智慧的一个孩子,对吧?
我不想让父亲丢开我的手。
父亲说,它在我们家太辛苦了,天天拉着我东奔西跑,它腿上的毛都磨得没有几根了。父亲不说了,父亲听到了一种声音,过了一会儿滑过去的是一辆摩托。
现在,我告诉你们这是我们家的驴儿的又一次失踪,我们家的黑驴每年都会有一次失踪。它的第一次失踪是来我家的第二年秋天,我们不知道它是怎样挣脱缰绳的,又是怎样拱掉了那扇门,至今对我们是一个谜。父亲凌晨起来喂它的时候不见了黑驴,那几天父亲说的最多话的就是,它要不回来真是畜生,它真没良心。幸亏后来的一天深夜它真的自己回来了,又回到我们家,安然无恙地和我们相处。好像它只是去旅游了几天。
父亲坐在椿树下等,像第一次等驴一样坐在门口的椿树下。我们瓦塘南街的很多人都劝我父亲,说,你要好好休息,回屋吧,你在屋里也能听到驴的消息。父亲说,你们不懂我的心情,我的心其实像刀绞一样。大家说,你的心像刀绞一样我们清楚,可这秋风刮起来也像刀子一样,你不要被刀子样的风攘出病来。有人劝父亲报案,说丢一头驴在老塘南街也算件大事,报了案说不定抓住了偷犯,谁家丢过的东西也能带出来。父亲摇头,咱家还没有报过案,报案挺麻烦的,我哪里有钱请破案人吃饭啊,说不清把一头驴吃进去了驴还没有找到。有人接过父亲的话,再不报案限定的时间就要过了。
父亲说你们不要打乱我,我有主见,我相信我的驴儿。
父亲挤住眼,细心听着路上的声音。
那时候,我的本家哥哥和我本家叔走在寻找黑驴的路上,他们先去了驴的“娘家”,根本没有驴的行踪。当初主家说你们来我们家找错了,驴不会再回到它原来的地方,这是驴的脾性,它怨主家把它卖了。本家哥和本家叔去了常屯,驴是父亲在常屯的庙会上买的,当时父亲在驴腿间穿棱,最后才看中的这头黑驴。他们正好逢到了常屯的又一个庙会,两个人去了驴市,和父亲两年前买驴一样在驴腿间奔走,最后他们还是失望地离开常屯。
不断听到送来的消息,乡村不缺这样的探子,传话比捎东西要快得多。说黑驴在一片稻田里走,有人看见它走在千亩稻田的一条沟边,像一个种田人在田里散步,待走过去想看个究竟,又不见了它的影子。那一天,常屯的一个亲戚过来,是我的一个本家姐,她告诉父亲,庙会那一天深夜,有人看见一头驴在拴牲口那片地方,孤自地来回游荡,天快亮的时候又跑得没了影踪。
父亲说,好,这说明驴要回来,它离家越来越近了。
果然在第三天的黄昏,父亲从椿树下站起来。父亲去了九湾河,父亲站在桥上,一阵风掠过河床,传来一阵河水的翻滚声,父亲就是这时候清楚地听见了蹄声,伴着河边的草地,河水一涡一涡从蹄子下掠过,一波一波朝远处流远。父亲睁开眼,父亲看见一个黑影,在河边站着,父亲沧桑地叫了一声,驴儿——驴儿响亮地打过来几个响鼻,接着听见了它哒哒地奔跑声,河水哗哗地流动。
黑驴的失踪一直是一个谜,它每次安然无恙地回来更让我不解,也许是父亲后来的悟道:它是要让父亲休息几天!也许吧,我宁愿相信这样的理由。
五
我看见了一池莲花。应了父亲的话,我接过了父亲的鞭杆,我赶着毛驴去送骨头,开始加入收骨头拉脚的行列。我跟着老连叔、瘸子张山往焦城的骨胶厂送,夜晚睡在路边的麦场里,驴也睡着了,只是偶尔喷几声鼻子。那一年我毕业了,考大学几分之差名落孙山,我沮丧极了。我先是天天坐在房顶,望着村外的庄稼,看着风一缕缕打着旋儿绕过来绕过去,把鸟儿绕到了天上,白云绕成了带颜色的云。雨下来了,我和雨斗着气还在房顶上坐着,我觉得这样才能发泄我的心情。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我想复读,或者在冬天的时候报名参军,可我不敢对父亲说。就是这时候父亲把我从房上叫下来,说,你坐得再高也坐不出个名堂,坐树梢上也没用,你看得再多也是空的,天上不会往你怀里掉宝贝,最多掉几片树叶,或者鸟儿会尿到你的身上。我不想说话,我知道我的挣扎和奋斗还没有结束,我不服气,我咬住嘴唇。父亲说,不服气也不行,嘴唇咬破也不顶事,干什么都要实打实,孩子,原谅你爹。在父亲和我谈话对我教训时,妹妹躲在门口隔一会儿伸过头看我一眼,扑闪着大眼。父亲说,我说过了,给你鞭杆。
我仰起头,搂着膝盖,摇摇头,咬着掉到嘴角的泪。
我看见了鞭,看见小鞭上的红缨子在微风中飘悠。
父亲低下声音,我去收,你跟着你老连叔,替我去送。
我答应了。这合我的心意,我一直想替替父亲,想去看看通向焦城的路,父亲和我们家的驴儿已经走了几年的路,我无数次在等待父亲回来中想像的路。父亲说,别怨爹,路只好一点点地走了,你比我强,还有人交给你一头驴,你爷什么也没有给我留下。
就这样,我赶上了驴。
我看到了一湖莲花。我走迷了,和老连叔、瘸子张山分开走到了另一条路上。是我们家的黑驴拉着我走到这路上的,后来,我想到了这是驴儿的预谋。我被大片的莲花迷住了,青翠欲滴的莲叶,亭亭玉立的莲花,把一个湖或者一个野坑撑得像一个仙境,太好了。在镀金的夕阳中,那一抹夕阳恰好反衬在莲叶和莲花之间,湖水中泛起耀眼的黄金色,风掠过莲湖,在湖面上蹁跹,听到鸟儿在莲叶间唱歌。驴儿停下来,惊呆地看着莲花,梦一样的莲花,我记得莲花湖边开满了野菊、水仙,蓊郁的草地似一片地毯,像一处宫殿,让我陶醉,我想不到驴儿也会那样忘情地凝望莲花。我忘情地走向莲花湖,我脑子里迸出的不仅是周敦颐的《爱莲说》,还有一个叫莲的同学。后来我还一直爱她,一直把那场最初的萌动看成我的初恋,我给她写信,收到她委婉的拒绝。我把她的拒绝归同于我的高考失利,如果我再次考试成功,我会再给她写信或者直接找她。我在走向莲花湖时浮想联翩,美好的事物让人展开的想象像孔雀开屏,我又默默地背了几首关于莲花的诗,我坐在莲花湖边,我把什么都忘了,甚至驴儿。
我把黑驴丢了,就是那天。或者说我们家的黑驴又一次失踪。在月光下,我看见它留下的蹄印,蹄印是它写下的几行给我的留言,我当时没有读懂。奇怪,我们家黑驴那天催我的叫声我根本没有听见。祸不单行,我高考失种,我听了父亲的话,赶驴往焦城的骨胶厂送骨头,我看到了堆积如山的骨头,在我赶着毛驴的路上,那些骨头的腥甜一阵阵钻入肺腑。回家的路上,我被莲花迷住,我家的黑驴再一次失踪。
我跑回家,看见老连叔、瘸子张山和我们老塘南街的邻居都已坐在我们家等我。看见我回来都吃惊地站起来,他们以为我和驴一块儿丢了。我在父亲面前痛哭失声,黑驴没有回家,我以为它想念父亲抛下我自己回来了,驴却真的丢了。
在第二天的月光夜我又回到了莲花湖边,我又一次打坐,期待着莲花湖边的蹄声,我相信它会回来找我,它不会那样没有良心,走得那样决绝。
可是没有。此后的很长时间我一直都活动在那一带的乡村,我提着浆糊,不断地贴“寻驴启示”。我翻印了黑驴的照片,整天穿棱于乡村,打听着黑驴,我们始终没有得到消息。那一年,再一次坐在椿树下的父亲彻底地失望了,凳下的荒草串出了凳缝,结了草籽。
我回到家,父亲还坐在椿树下,看见妹妹守在父亲的身边。我狼狈不堪地站在父亲面前,等夜越来越深时,我庄严、惭愧地对父亲说,黑驴可能真的丢了。我说,有一天晚上我跟踪黑驴,它竟然把我带到了我刚离开的学校,那是一天的黎明,等我再四处找时,怎么也见不到它了。我在学校周围找了3天,等了3天3夜,它再也没有出现,从此就再也没有见到它。
父亲像恍然从梦中醒来,他踢翻了凳子,拽起凳下的一把荒草。忽然大喊,孩子,准备你的书包吧!这是驴儿要成全你啊——
我回到学校复读。第二年,我拿到一张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接到通知书的那天晚上父亲在门口的椿树下站了很久。我又去了莲花湖,而后,我独自走在去焦城的路上,我要亲自量量去焦城的距离……
还有,黑驴,你该回来了吧!我们一直都还在等你。
责任编辑 林东涵
安庆,本名司玉亮,中国作协会员,河南文学院签约作家。已在多家期刊发表中短篇小说多篇,小说多次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等转载,收入多种选本。获第三届“河南省文学奖”、冰心儿童图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