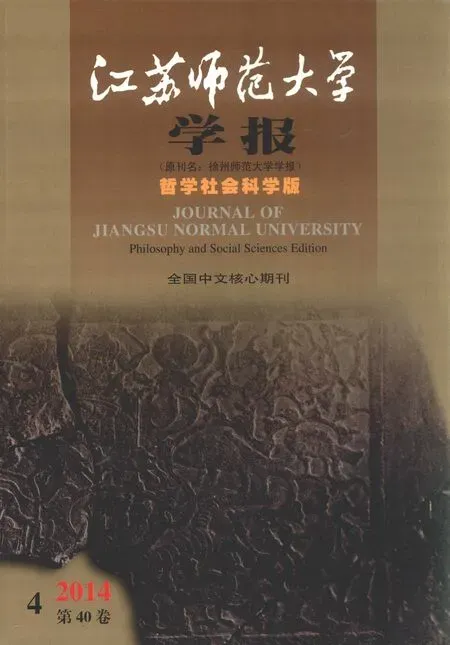孔子“为仁由己”道德主体学说及其启示
陈二林
(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合肥 230009)
孔子“为仁由己”道德主体学说及其启示
陈二林
(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合肥 230009)
孔子;“为仁由己”;道德主体
中国传统文化十分重德,德之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在此过程中,孔子作出了重要而独特的贡献。秉承西周以来“惟德是辅”的德政思想,孔子强调“为政以德”的政治制度之德;更为重要的是,他还提出“为仁由己”,重视个体内在德性的激发与道德主体意识的培育,这对以重德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型塑具有关键作用。而孔子具有创新意义的德性论,也是他对殷周之际及春秋时期社会变革与哲学突破进行深入反思与认真总结的产物。它给我们的启示是,当今社会进行思想道德建设,既要重视制度性之公德建构,也要重视个体性之私德涵养,并努力促进二者的良性互动。
中华文化具有重德传统。而“德”观念本身又经历了一个演化发展的过程。诚如晁福林所指出:“大体说来,先秦时期的‘德’观念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天德、祖宗之德;二是制度之德;三是精神品行之德。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德观念都没有能够摆脱天道观念的影响。‘德’观念走出天命神意的迷雾是西周时代的事情,然而将它深入到人的心灵的层面则是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们的贡献。”[1]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在“德”观念的演化进程中,孔子既继承前贤又进行重大创新,在注重“为政以德”的政治制度之德的同时,更强调“为仁由己”的个体内在之德,从而为完善道德理论与推动道德践履作出了独特而重要的贡献。其理论创造与社会实践的意蕴积极而深远,尤其对当代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一
有感于春秋时代礼崩乐坏之乱势,孔子对“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后引《论语》只注篇名)的周代文化与制礼作乐的周公表达了由衷的仰慕与慨叹,对当政者提出“为政以德”(《为政》)之要求,对君子与民众提出“克己复礼”(《颜渊》)之期求,并由此抒发了“吾从周”(《八佾》)之宏愿。而在知礼与行礼上,孔子也总是率先垂范,一丝不苟,“入太庙,每事问”(《八佾》),十分注意在不同场合下礼仪礼节的恰当表现。然而,令孔子深感忧愤的是,“八佾舞于庭”(《八佾》),整个社会对礼仪礼节的遵从状况很不理想,人们对礼仪礼节缺少发自内心的认同与敬重,缺乏行礼的内在动力,这样,也就谈不上“立于礼”(《泰伯》)了。也就是说,在“复礼”过程中,孔子敏锐地察觉到,并不是礼本身有什么不好,也不是人们真的不知礼为何物,而是缺乏行礼的内心基础与动力之源,明明知道礼却不愿意遵行。鉴于此,孔子进行了深入的思索与积极的身体力行,特别是认真探寻了礼的根基问题,并最终“借鉴历史上有关的说法,将这个内心的基础叫做仁,从而创造了仁的学说,以仁作为复周礼的内在根据和支撑”[2]。
可见,孔子是在认真思考如何使德政礼治深入人心,即在追寻德政礼治的心性根源及礼乐实践的精神基础的过程中,提出和强调“仁”的理念的。其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很显然,孔子已非常清醒地认识到,“礼”与“仁”是表里关系,“仁”是一个人修德行礼的心性依据与动力源泉,脱离仁,舍弃仁,也就无所谓修德行礼,德与礼只会变成枯燥烦琐而难以遵从的形式[3]。
不过,从理论上找到“仁”这一行礼复礼的内在动力之源,却并不意味着人们不“崇德”、“尚德”、“怀德”而“知德者鲜”(《卫灵公》)的现实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要想让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发现和感悟到这一潜在动力,从而“志于仁”和“据于德”,尚有较大困难。孔子坦承,其“未见蹈仁而死者也”(《卫灵公》),甚至“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宪问》);孔子也清醒地意识到,人们远未做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季氏》),更不用说达到“好德如好色”(《子罕》)的境界,“仁”对于人们的感召力并未如想象中表现得那么强大。因而,他明确地表示:“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述而》)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差距,着实使孔子大为忧虑。
而要化解这一忧虑与困惑,在孔子看来,就必须首先让人们明白:到底什么是仁?怎样做才算是仁?修德践仁的困难究竟有多大?然而,孔子并未给仁下一个标准定义,而是根据不同情况,因材施教,对仁给出了“爱人”、“立人”、“达人”、“忠恕”、“孝悌”等多样化的解释。不过,仔细品味则不难发现,孔子所谓的仁的精髓,主要是指每个人本有而无需外求的内在德性,相当于孟子所说的“良知良能”、王阳明所说的“良心本体”、熊十力所说的“当下呈现”,类似于康德所言“人的本性中的向善的原初禀赋”[4],而并非什么高不可攀的神秘物。孔子所期许的仁人君子,也是普通人经由修德讲学而可企及的理想人格,并不限定于贵族人物,更非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恰如有学者指出:“孔子所谓‘君子’并非一种身份,他对君子、小人的判分依据是德性而非身份地位”,“君子人格则是他对每一个进德修业者的期许。”[5]正因为如此,所以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对此,朱熹注曰:“仁者,心之德也,非在外也。”(《四书章句集注》)正是这种人人本有而“非在外”的内在德性,才构成了人们修德行礼的不竭动力之源。因而,从根本上讲,人人具有修德行礼的“资本”与条件,由此而成为君子贤圣也并非至难之事。
依孔子所论,“仁”是内在于人、潜在于“心”的道德自主性。对人之向上的内在道德心之肯定,提示人们要多从外部索求转向内心省悟,从而做到由内而外、推己及人,这应是孔子论“德”释“仁”之初衷。恰如方颖娴所说:“‘仁’的实践,乃反求诸人的内在的道德心,凭藉人自己内在的道德主体性;‘仁’的成就,归根到底,需在人的‘心’上求,故‘仁心’的确立——人的内在道德主体的确立,与由此而来的道德意志的坚持,才是行‘仁’的保证,而且是个体自己可以绝对把握的保证。”[6]所以,孔子特别就“心”上说“仁”(谓颜渊“其心三月不违仁”,要求对他者行为“察其所安”),这意味着“仁”生发于内“心”,根源于内“心”。
然而,生发于、根源于内“心”的仁德又并非什么神秘玄虚的东西。其培育与养成,须通过学与思结合、内省与外行结合,尤其须通过广泛深入的学习践行,“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为成就仁德,君子也需要不断努力习行,“好学”而“博学”,“学而不厌”(《述而》),“学而知之”(《季氏》),并“学而时习之”(《学而》)。正因为仁德重在自省而贵在行动,所以才有“仁者先难而后获”(《雍也》),才有“仁者必有勇”(《宪问》),才有“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甚而“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卫灵公》)即是说,仁德不仅表现为“由己”的内心意志活动,而且表现于“躬行”、“亲为”的实际行动上,体现在主体“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子路》)的行为方式中,“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的言行举止上。而对广大民众来说,要成就仁德,也不能仅靠“政”与“刑”的外在作用,因为“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仅起到“民免而无耻”的消极效果;而要使民众产生“有耻且格”的道德心理与自觉行动,则必须“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为政》),使民众在德礼规范下的人伦日用中“发现”和践行发自内心的良善德性,从而达到“无讼”(《颜渊》)之境界。
当然,孔子在强调“仁”的“操持在我性”的同时,也强调人的“天命在身性”[7],并认为人通过主观努力而可“知天命”。这就表明,自律自省之仁德又须在人人互动中即在人伦网络中生成,在天人合一的过程中生成,由此指明人道与天道可以实现贯通。不同于“仁”之“为仁由己”的自觉自主性,“天命”多少表现为一种个人难以把握从而心生敬畏的外在的客观力量。那么,作为个体的人怎样才能知晓和通达这种外在的客观力量呢?依据孔子所说,唯有“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方可做到“无忧”乐天而知命。诚如有论者所指出的:“在周初‘以德配天’、‘保民而王’的观念下,天对‘德’的鉴察重点指向王者的功业而非个体的德性,这使当时的天命观呈现为一种政治化的贵族式天人关系,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孔子的仁学立足于个体的安身立命,将周初的天命问题由外在的承领转作内在的证悟,提出了对人的道德意识的普遍性的思考。”[8]如此说来,通过体验仁德与践行仁德,纵然是外在威严的天命,也会变得可知可亲了。
诚然,孔子对仁德的个体性重视有加,但作为践行礼乐内在动力之仁德,作为须“以友辅仁”(《颜渊》)之仁德,注定其不能用来孤芳自赏,其要求君子“不器”(《为政》),“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打破自我的封闭与狭隘,由内而外、推己及人、成己成物。由此,孔子注重私德与公德的关联互动,特别主张通过修养和践行私德,以影响和促成公德。对于为政者来说,更应如此。孔子要求当政者正人先正己,认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主张通过“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宪问》),强调“上好礼”、“上好义”、“上好信”(《子路》)的示范效应。而君子也要从身边做起、从细微处着手,“迩之事父,远之事君”(《阳货》),“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子罕》),“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泰伯》),“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遵守“恭宽信敏惠”(《阳货》)等为人之道与处世原则,坚守“三戒”、“三畏”(《季氏》)等行为界限。
总之,孔子之所以重视仁、提倡仁,融仁入德,以仁摄礼,其目的无非是要唤醒人们潜在的道德主体意识,确立人的道德主体地位,在道德修养、道德行为、道德意志、道德境界方面体现出人的自觉自主性[9],使人们能够自觉地讲德修身,心悦诚服地遵从礼乐,表里如一地践行道德,实现真正的道德自由,并使那些修德不力者找不到借口托词(《里仁》:“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吾未见力不足者”)。诚如牟宗三所言:“孔子讲仁是敞开了每一人光明其自己之门,是使每一人精进其德性生命为可能,是决定了人之精神生命之基本方向,是开辟了理想、价值之源。”[10]这就突破了西周时期“德”主要表现为天德、君德、政德、制度之德的形上抽象性与外在局限性,而展示出“德”的内在性、普遍性与理想性,进一步将人从神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否定摒弃了人性的无根状态,体现了人的尊严,提高了人的地位。正如杨向奎所言:“周公逐渐脱离了‘天人之际’而倡德;孔子转向‘人人之际’故倡仁。”[11]这一转向,“表明了人对自身力量的进一步觉醒”[12]。因而,应该说,孔子将“仁”作为讲德复礼的内心基础与精神支撑,实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次重要转折与重大创新,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母型”。
二
前文有述,孔子在强调“为政以德”政治制度之德的同时,特别提出“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表征了德的内在性与自主性,凸显了道德主体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彰显了人禽之别与人之为人的尊严与价值。由此,儒学推己及人、内圣外王的立德治学之方也初步确立起来。
不过,“为仁由己”的思想主张,虽对人之普遍性的道德自主具有开创意义,但孔子对其终极根源语焉未详(这一问题在当时也确实不是很紧迫),这一探究任务自然要留待后世。对此,恰如有学者明言:“孔子的主要成就,乃在为中国传统的政教与礼文的外化制约提出一内在理性根据,为人揭示一内在自主的道德潜能以凸显人的存在价值与意义。”[13]而对于此道德潜能是否为人人先天俱有的问题,孔子尚未深入解决。
于是乎,孔子之后、思孟学派之前的有识之士[14],开启了这一为人之仁德之性寻找终极根源的工作,进一步明确了仁德的内在性。如郭店楚简《六德》篇云:“仁,内也。义,外也”,《语丛三》也说:“仁生于人,义生于道。或生于内,或生于外。”而君子通过“敦於反己”(《郭店楚简·穷达以时》)、“闻道反己”的“修身”活动,就可“近至仁”(《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以此为前提,可以推己及人,由知而行。“知己而后知人,知人而后知礼,知礼而后知行”(《郭店楚简·语丛一》),“察者出,所以知己,知己所以知人,知人所以知命,知命而后知道,知道而后知行”(《郭店楚简·尊德义》)。尤其是对仁德的内生性作了非常明确的阐发,指出“仁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行于内谓之行。”(《郭店楚简·五行》)显然,将知己作为知人、知礼、知命、知道与知行的前提条件,从伦理社会关系方面强调道德主体意识的重要意义,以道德主体的行为是否“形于内”即是否发自内心作为判别与界定德行的根本标准,这些都是对孔子仁学思想的深化。不过,此派学者,一方面强调仁德重在自觉内省,另一方面对于仁德贵在行动、私德尤其是当政者的私德(政德官德)对民德民风的影响也多有强调。其借引孔子“上好仁,则下之为仁也争先”之语而加以阐发:“故长民者,章志以昭百姓,则民致行己以悦上。”(《郭店楚简·缁衣》)又曰:“君子之莅民也,身服善以先之,敬慎以守之,其所在者入矣,民孰弗从?形于中,发于色,其诚也固矣,民孰弗信?是以上之恒务,在信于众。”“上不以其道,民之从之也难。”(《郭店楚简·成之闻之》)“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命,而从其所行。上好是物也,下必有甚焉者。”“先之以德,则民进善焉。”“德之流,速乎置邮而传命。”(《郭店楚简·尊德义》)这些论述,引经据典,正反对比,以此表明,仁德善念只有在行动中体现才能产生良好的影响与示范效应,颇有说服力。
沿着同一方向,子思与孟子都强调“诚”,由此进一步突出了仁德的内在特质,特别是孟子,提出仁、义、礼、智“非由外铄”而为我本具内备之“四心”说,为孔子所揭示的道德主体提供了内在支撑。传为子思所作之《中庸》,强调“君子不可以不修身”,而“修身”是指通过“自诚”、“自明”的“事亲”、“知人”、“知天”而进行的自我修养,是“正己而不求于人”的“自得”,“修身”“成己”也正是“仁”的表现。孟子也强调“反身而诚”(《孟子·尽心上》),“反求诸己”(《孟子·离娄上》),从而“尽心”“知性”以“知天”(《孟子·尽心上》)。他还针对告子等人虽承认“仁”为“内”而将“义”视为外在规范的思想倾向,提出了严厉批评,倡言人们要从行仁义转为由仁义行,并径直指出:“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上》),进而提出了著名的“四心”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这就将仁、义、礼、智都与人心明确关联起来,与作为道德主体的“我”联系起来,以此劝导人们要自觉自愿地存心养性。因为,在孟子看来,毕竟“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所以,每个人对自己仅有的那一点良知良能不可不时刻加以存养呵护。以此而论,孟子也是在为礼进一步寻找“内在心理依据”[15]的过程中提出“四心说”,从而对人人通过修德讲学而成为圣人君子的可能性加以推定的,这就将孔子之仁的内在性与普遍性的本质特征完全彰显出来,将孔子仁学发扬光大了。经孟子发挥,仁德的内在特征虽得到了强化,但实践性则明显减弱了。
而主张性恶论从而隆礼重法的荀子,也强调君子圣人应注重“诚”以“养心”和“度己”。荀子曰:“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惟仁为之守,惟义为之行。”(《荀子·不苟》)他还说:“圣人者,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荀子·非相》)在荀子看来,圣人之所以为圣人,恰恰在于其能由“度己”而“度人”。并且,“君子之度己则以绳,接人则用抴”,“度己以绳,故足以为天下法则矣;接人用抴,故能宽容。”(《荀子·非相》)这就是说,君子要以道德原则严格要求自己,而待人接物时则要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而不应苛求于人,应充分考虑人情因素。同样,荀子仍是把道德修为的基点与重点置于道德主体自己身上,惟其如此,其“化性起伪”才有可能。相比于孟子,荀子更加强调仁德的修为习行过程,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仁德过分内敛而流于玄虚的倾向。
总之,孔子提出“为仁由己”,唤醒了人们潜在的道德主体意识,为后人确立了成己成物、推己及人、内圣外王的“反躬”与“絜矩之道”[16],树立起“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涂之人可以为禹”(《荀子·性恶》)的道德信心,从而主动加强道德修养,奠定了坚实的学理基础,其后,思孟学派及荀子等人进一步强固了这一学理支撑。而后宋明时期,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虽彼此存有差异,但无论是主张理本体还是主张心本体,都十分看重道德主体自身的体悟与修为,都看重道德主体内在德性的启蒙与激发,以此为立足点而践行伦理道德,这都是孔子仁学思想合乎逻辑的发展。
三
如上所论,孔子强调“为仁由己”,唤醒了人们潜在的道德主体意识,有助于人们自觉自愿地修德讲学,立身做人。后世儒家深化和阐扬了孔子的理论建树。而追根溯源,孔子具有独创性的“为仁由己”理念的提出,也是他对殷周之际与春秋时期社会变革与哲学突破进行深刻反思与总结的结果。
众所周知,古老的中华文明肇始于夏商周三代。三代文化一脉相承,都相信天命。殷代统治者对天命尤其笃信不疑,将“帝”视为至上神而顶礼膜拜。以天命自负的殷代后期统治者,暴虐无度,以致“受(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尚书·泰誓上》),社会矛盾空前激化。乘此时机,卧薪尝胆而深孚众望的“小邦周”,经牧野决战,终于取代了“秽德彰闻”(《尚书·泰誓中》)的“大邑商”,实现了巨大的社会变革。
然而,周初政局还很不稳定,特别是武庚叛乱的发生及管蔡流言的传播,对周代政权构成了极大威胁。以周公旦为代表的周初统治者,在积极进行平定叛乱与安抚殷民活动的同时,竭力为周代政权的合法性寻找理据,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与敏锐的政治觉悟。在稳固政权及寻找政权合法性理据的过程中,周人逐渐对殷商天命不改的观念产生了怀疑,进而认为“天不可信”(《尚书·召獎》),“天命靡常”(《诗经·大雅·文王》),“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这表明,随着时势的演进,周代统治者渐渐洞察到,在殷人看来不可更改的永恒天命实际上是可以移易的,移易的关键就在于当政者本身是否有“德”和是否实施德政,而德政的必然要求和具体表现则是保民、安民、和民、惠民。
迨至春秋时期,诸侯纷争,周文疲敝,生灵涂炭。在此情势下,疑天思潮进一步高涨起来。人们开始有意识地甄别天道与人道,并认为天道体现于人道之中,这就为进一步注重人事活动与人为因素奠定了基础。由此,人们渐渐认识到吉凶祸福实乃人为造成,非天命鬼神所能主宰。而有感于社会的动荡不安与人生世事的复杂多变,贤能之士普遍觉察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诗经·小雅·十月之交》)式的社会政治剧变难以避免,而只有“唯变所适”(《易传·系辞下》),顺应潮流,更切实地重人修德,推行德政礼治,保民、利民而非暴民、陵民,才能更好地治国安民。
从上可知,与夏商对天命神权的痴迷执信有所不同,西周时期已然意识到人本身的重要作用与人为因素的积极意义,显示出巨大的历史进步性,这就为春秋时期人们更加怀疑天命神权,而相信和依凭人本身的力量与作用,奠定了基调。西周时期以《易经》为代表的着眼于人事与人为因素以趋利避害、逢凶化吉的变易观,也为春秋时期在更大范围内因应变化思想的展开作了铺垫。而正是以西周时期具有一定工具手段性与政治实用性的德政礼治思想为前提,春秋时期才可能将德政礼治提升到治国理政之纲领与原则的高度来加以强调。也正是以西周时期的保民思想为起点,春秋时期的民本思潮才得以喷涌[17]。
可见,恰是在对殷周之际与春秋时期的社会变革与思想更新进行深刻反思与总结的基础上,孔子才有可能提出“为政以德”及“为仁由己”的理念,在重视建构政治制度之德的同时,强调个体内在德性的涵养。
四
综上,孔子“为仁由己”的道德主体学说,是在礼崩乐坏的社会背景下为寻求“复礼”的内在动力与心性依据的基础上而提出来的,是在重视政德公德的同时对私德民德的强调,是对殷周之际与春秋时期社会变革与哲学突破进行深刻反思与总结的结果。这一道德主体学说,至少能给我们如下几点启示:
首先,与康德刚性的绝对律令相比,孔子以仁摄礼的思想主张表现出由内而外的柔性特征。的确,道德重在自省、自觉与自愿,而自省、自觉与自愿,则须通过唤醒道德良知、激发道德意志、培育道德情感而实现。今天的思想道德建设,也应致力于运用多样化手段促使道德主体实现自省、自觉与自愿,催生其道德意识,净化其道德动机,提升其道德觉悟,做到知、情、意合一,从而臻于更大的道德自由与更高的道德文明。
其次,孔子强调“为仁由己”,还表明践仁复礼关键在于道德主体的躬行亲为,而非玄虚的形上建构。故而,不同于西方哲学重“说法”,中国哲学更重“做法”与“活法”,重视道德践履,强调知之而行,知之必行,知行合一、表里如一、言行一致。道德贵在行动,而非说教。再好的道德理想与道德愿景,若缺乏道德主体的真诚认同与相应行动,也是没有意义的。若长此以往,还会造成人格分裂与道德伪善。当下,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己任的思想道德建设,也要在落实、落小、落细上下工夫。对社会个体及全体而言,思想道德建设也的确是“说一尺不如干一寸”。
再次,孔子将“为政以德”与“为仁由己”相提并论,意味着政德、公德与民德、私德不可偏废,而是相须为用、相辅相成的。同样,当前的思想道德建设,也应既重视制度性、公益性之公德建设,又重视个体性、自洽性之私德涵养,要努力促进在个人品德、家庭道德、职业道德与社会公德之间实现良性的关联互动,尤其要重视政风官德对民风民德的示范效应与引导作用。
[1]晁福林:《先秦时期“德”观念的起源及其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2]杨泽波:《中国“哲学突破”中的问题意识》,《云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3]关于“仁”与“礼”在孔子思想中的地位与关系问题,学界大致有三种意见:其一是认为孔子思想中以“仁”为主,“礼”只是“仁”的外在表达;其二是认为孔子思想的中心是“礼”,“仁”附庸于“礼”;其三是认为孔子思想中的“仁”与“礼”同等重要,并无主次之分。笔者认为,这几种观点皆有可取之处,但也有一定的偏差。其实,孔子是在为礼寻找内心基础的过程中发现并提倡“仁”的,因而其在保留“仁”之古义的前提下,又进行了可贵的创新,赋予其个体内在德性的意涵。实际上,“仁”这一概念早在孔子之前就出现了,其除了具有一些政治方面的含义外,主要还是作为一个赞美嘉许之词来使用的。这从孔子称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管仲“如其仁,如其仁”,但又批评其“不知礼”中可以显见。也就是说,孔子主要是从“仁”之政治古义及出于赞美而称许管仲为“仁”的,但从其某些“僭越”行为来看,确实又是有违于“礼”的。孔子对管仲的评价看似矛盾,其实不然,而是体现出孔子实事求是的务实态度。
[4][德]康德:《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12页。
[5][8]崔涛:《孔子对天人关系的本体论诉求》,《孔子研究》,2010年第5期。
[6][13]方颖娴:《先秦之仁、义、礼说》,台北文津出版社,1996年版,第145-146、123页。
[7][12]唐文明:《与命与仁:原始儒家伦理精神与现代性问题》,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2、57页。
[9]叶飞:《先秦儒家人格教育思想的主体性意蕴》,《道德与文明》,2011年第1期。
[10]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11页。
[11]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59-360页。
[14]目前,学界普遍认定,郭店楚简属于公元前300年左右介于孔孟之间的文献。
[15]刘丰:《先秦礼学思想与社会的整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2-127页。
[16]参见龚建平、宁新昌:《儒家哲学中“知己”与“絜矩之道”的方法论意义》,《孔子研究》,2010年第2期。
[17]参见陈二林、陈绪新:《中国先秦时期的“哲学突破”及其文化精神》,《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Confucius's Moral Subject Doctrine and It's Enlitenment
CHEN Er-lin
(School of Marxism,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Hefei 230009,China)
Confucius;"to be benevolent by one's own";morality subjec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emphasizes morality,while the concept has experienced an evolution process.In the process,Confucius makes important and unique contribution.Adhering to the thought"God helping who could possess morality"since Xizhou dynasty,Confucius emphasizes the political morality of"governing with morality,and more importantly,he also proposes"to be benevolent by one's own",emphasizing individual internal moral stimulation and cultivation of moral subject consciousness,which is crucial for the shaping of traditional characterized by emphasizing morality.And Confucius's innovative theory of virtue is the product of in-depth reflection and earnest summary of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philosophical breakthrough from Yin Zhou to the Spring Period.Confucius's moral theory enlightens us that we should not only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institutional ethics but also attach importance to personal moral cultivation,and try our best to connect them,in the process of ideological and moral construction.
B222.2
A
2095-5170(2014)04-0097-06
[责任编辑:李文亚]
2014-03-26
本文系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创新社会管理视域中群众工作的价值意蕴”(项目编号:SK2012B542)、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风险社会’视域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生成研究”(项目编号:AHSK11-12D252)、江苏省2013年度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当代中国公民教育实践研究:来自亚里斯多德的启示”(项目编号:cxlx13_330)之阶段性研究成果。
陈二林,男,安徽望江人,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