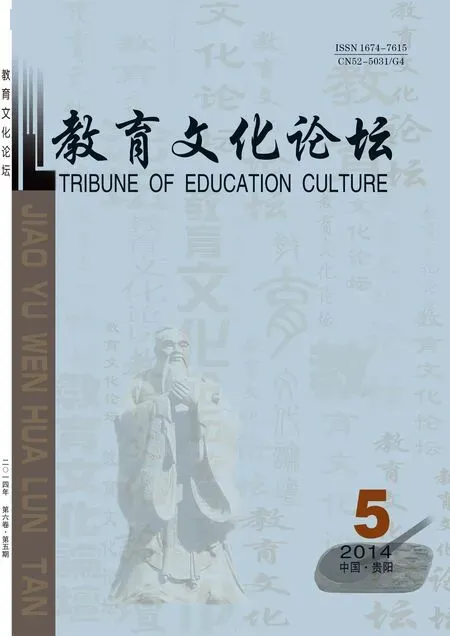廿年九宿试官槐
——郑子尹的科举之路
张嘉林
(遵义师范学院 人文与传媒学院,贵州 遵义 563002)
隋唐以降,科举取士即成为选拔人才的制度,这为中下层知识分子进入仕途提供了方便。由秀才而举人,由举人而进士,是历代知识分子向往之路。生活在晚清时期的郑子尹,当然也不能避免这一进身的路径。子尹一生,“廿年九宿试官槐”,二十年间参加了三次在北京举行的会试,每次都以失败告终。在这一次次的考试中,子尹经历了怎样的情感体验?而被后人誉为“西南巨儒”的子尹,为何屡试不售?本文旨在对这些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一
子尹17岁童试得中秀才,20岁即得选拔贡,在遵义之应乡荐的学子中,是年龄最小的一位。次年(1826),即以“拔贡”(选拔推荐的秀才)身份进京参加廷试。清代士子会试,每三年在北京举行一次。遵义士子到北京应试,要途经80驿站,行程5000余里。那时交通不便,道路难走,中途有一段水路可以乘船,其余皆旱路,完全靠步行。这是他第一次进京应试,内心深处充满了对前程的希望与期待。在《巢经巢诗》中,未见有关这次考试的描述,不过从子尹后来的一首诗中所述,可以感受到他当时的心情:“忆我丙戌年,春风三月时。驻马樊仲国,渡江恣盘嬉。背载双葫芦,笑杀襄阳儿。兴到即野炊,菜花迷大堤。寻碑万山顶,访古习郁池。晓探鹿门去,晚度檀溪归。落日三板船,快泻青琉璃。苍苍渔梁渡,馀映依山陂。”(《樊城感旧》)[1]没有旅途艰难的描述,只有驻马樊城、泛舟江上、野炊山间、寻访名胜的惬意与欢快。子尹怀揣希望参加这一次考试,却以失望告终。子尹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挫折。
12年后,子尹(已过而立之年)的功名之心已然淡漠,但他还是又一次踏上了进京应试之路。其实子尹是不想去参加考试的:“十年不作科名想,一堕仍为牛马身。”(《夜趣安肃》)十来年了,本想把它丢开的,可到头来还是要为它做牛做马。“无名亲戚悲,名得又反累。得失俱可怜,伤哉功名事。”(《度岁澧州,寄山中四首》)没有功名,亲戚看不起你;有了功名,反而会被它所累。对子尹而言,功名的有和无、得与失,都是悲哀。对功名的追求,在子尹看来,实在是无奈之举。“聊谋三径资,倾身已违己。”(《和渊明饮酒二十首其十九》)所以这次出行,已经没有了12年前那样的心境,“寒风峭白日,萧条异山川。”(《黔阳郭外三首》)在子尹那里,所见的景物都是那样荒凉萧瑟,没有一点生气。子尹甚至对自己的行为产生了怀疑:“我本窗下人,胡为异方客。”(《出门十五日初作诗黔阳郭外三首其二》)一个读书人,如此奔走、作客异乡,到底是为什么呢?“读书究何用,只觉伤人情。不学耕亦得,看我黔阳城。”(《其三》)读书到底有什么用啊?到头来还不是一事无成,戕害人性罢了。还不如回家种地,归隐田园。子尹喜欢读书,怎么会怀疑读书的意义呢?中国古代的文人,无不以读书为务。读书是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基础。对于子尹来说,怀疑读书的意义,这可是一个严重的精神事件。
这次科考之路的艰难痛苦,在子尹诗中有很多的抒写。从遵义到北京,如果顺利的话,按每天走60里计,也要两个多月的时间才能到达。山路崎岖,就像李白笔下的蚕丛蜀道。山巅挤压着云团,如同头上悬挂着巨石。那山野的狂风,似要把木屋吹破。(《安化道中》)《自沾益出宣威入东川》更是把沿途苦况描写得动人心魄:“出衙更似居衙苦,愁事堪当异事征。逢树便停村便宿,与牛同寝豕同兴。作宵蚤会今宵蚤,前路蝇逢后路蝇。任诩东坡渡东海,东川若到看公能。”此中苦况,非亲历者不能道。
除了路途遥远难走,子尹还要忍受因离别而产生的对亲人的思念之苦。只要出门,这种痛苦就相伴而行:“梦醒觅娇儿,触手乃船壁”(《出门十五曰初作诗黔阳郭外三首其二》)梦中到处找孩子,醒来摸到的是冰冷的船壁。子尹有多少次的离家,母亲就有多少次的送别。每一次的送别,是母亲对儿子的牵挂,也是儿子对母亲的不舍。“一回别母一回送,桂之树下坐石弦。渡溪越陌两不见,母归入竹儿登箯。”(《桂之树》)母亲坐在门前的石头上,看着儿子远去的身影,直到看不见了,才回屋。二十多年的宦游,子尹的好多生日都是在异乡过的,而每一次的生日,他都会想起母亲,这天是母亲的受难日,使他百感交集。想着渐渐年迈的母亲那期待的眼光,子尹在心里表示,即使这路再艰难,也要走下去。
子尹旅途之痛,还在于沿途所见的民生疾苦。到湖北公安,子尹看到因长江缺口过后的哀鸿遍野,写下七古《江边老叟诗》,希望有人能出来治理水患,诗中回荡悲天悯人的情怀。在《网篱行》一诗礼,还描写了百姓用渔网做篱笆的情形:“公安民田入水底,不生五谷生鱼子。居人结网做耒耜,耕水得鱼如得米。高田鱼落田反芫,生鱼之地变生蔬。网亦从之变其用,环葱绕芥如围鱼……”
老天真是弄人。这一次考试,尽管子尹文才出众,文章做得再好,也入不了试官之眼——子尹败北而归。
但是,科考还是子尹挥之不去的梦魇。“六年不试北风寒,又历人间行路难。”(《贵阳寄内四首其一》)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的岁暮,子尹已近39岁,又不得不与友芝结伴去京师参加会试。距上一次进京,已经过了六年。这次离家才不到十天,子尹就已经厌倦。想起为了赶考,妻子到处筹措衣食费用,觉得自己就像孟子说的那个在坟地里乞讨祭祀残余的齐人,也像庄子笔下那个大而无用的葫芦瓢。
这一次考试,子尹经历了一生最艰难痛苦的磨难。子尹从小营养不良,身体孱弱,不到四十岁身子就日见枯萎,而且还患上了奇怪的眼病,视力每况愈下。让子尹最害怕的就是眼瞎,有的著述还没有完成,自己的心愿就成泡影了。更让子尹难受的是,一到京师就受了风寒,转成疟疾。第二天就要考试,病情越发严重,在床上昏厥过去。醒来后在朋友的帮扶下硬撑着进入考场,在地铺上趟了两天两夜,散考时交了白卷出来。
一次又一次的科考,一次又一次的落第,而每一次的落第,子尹都要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世人的嘲讽,对家人的歉疚,对死亡的恐惧……诸般痛苦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在势利社会里,如果一个身份低贱的人所遭受的痛苦,在物质层面表现为贫困的话,那么被人忽略、受人白眼则是这些缺乏重要身份标志的人们在精神层面上所遭受的痛苦。”[2]像子尹这样一个来自黔北乡村的士子,在那个由权势与金钱织成的人际关系网中,想要进士及第,比登天还难。经历了九死一生之后,子尹写下《六绝句》,表达了自己对浮名的厌倦和对科举考试的决绝。如其三云:“钓骥苍凉断鹤哀,廿年九宿试官槐。掷将空卷出门去,王式从今不再来!”
古代的士子,大都将个体的生命价值完全寄托在功名的成功与否上,在科场失利后,他们甚至怀疑自身存在的价值,往往自怨自艾。如唐人顾非熊所表现的“客中下第逢今日,愁里看花厌此生。”(《长安清明言怀》)子尹没有像有的士子那样,沉入虚无,而是将有限的时间用之于教书育人和学术研究,证明了自己存在的价值,终成一代巨儒。
二
子尹多次参加科考,既有传统的“修齐治平”的功名之念,也有家庭生计的考虑。既有秉承家风的的自觉担当,也有异于世俗的价值取向。
子尹从小接受的是儒家传统思想的教育,同样有着强烈的功名观念。“男儿生世间,当以功业显。”(《樾峰次前韵见赠,兼商辑郡志奉答》)“少志横四海,夜梦负飞天。”(《和渊明饮酒二十首其四》)舅父黎恂最了解这个外甥,说他有不羁之才,书读得多,文章做得好,随口成珠。(《郑子尹珍婿生日作长句示之》)所以黎恂深感欣慰:“昔欧阳文忠刮目苏子瞻,有‘当让此人出一头地’之许,吾于甥亦谓然。”[3]黎恂以苏子瞻期许,足见其对子尹的认可与期待。子尹曾游幕湖湘,得恩师程春海之器重,赐字“子尹”,以乡先贤尹珍期许。当子尹离开时,恩师有“吾道南矣”之喟叹。子尹对自己的才学十分自信:“我年十七八,逸气摩空盤。读书扫俗学,下笔如奔川。谓当立通籍,一块所欲宣。……腾身九霄上,袍笏光且鲜。”(《阿卯晬日作》)“通籍”,即做官。这种对自己才学的自信,转化为对科考的自信。因此,由参加科考而进入仕途,以实现自己的飞天之梦,是子尹的必然选择。
除了传统士子价值观的追求,子尹科考,还有生计的考虑以及亲人的期望。子尹家贫。祖父学山,乾隆诸生,精于医道,在当地颇有名望,也算得上小康之家。然祖父为人慷慨,乐善好施,而自己却十分节俭。郑父文清,秉承祖父遗业,也承继了祖父率直洒脱的基因,凡来求医的人,无论贫贱富贵,都必定赴医,至于医疗费,只要能够买一壶酒就行。手里多少有点钱,只要有人告急,就会给对方。“常济急者以为快,以故坐贫困,然亦不以为戚。”(《续遵义府志·郑文清传》)子尹弟兄三人,还有一姊一妹,家庭人口多,祖父去世后,家境越来越差,渐渐败落。
一部《巢经巢诗》,随处可见穷愁生活的描写。如《饭麦》一诗所记:入夏了,没有米吃,家里八口人等着下锅,市场上米价贵得吓人,家里还有两瓮麦子,只能靠它度日了。“有蔬苦无盐,有水复无米。”(《题新昌俞秋浓汝本先生〈书声刀尺图〉》)子尹38岁时,去仁怀厅(今赤水市)拜访平翰(字樾峰,原遵义知府),谁知到了那里即染上重病,子尹有诗四首寄樾峰,其中云“少小苦长饥,读书牧豕暇。渊明拙乞食,孙楚每遭骂。”(《至仁怀厅五日即病……》)说自己像渊明那样,拙于求饭碗;像孙楚那样,多傲骨而少人缘。又“贫薄多艰虞,肌肤就销竭。”因为生计艰难,饿肚子是常事,身体不好,又常常生病。
就在子尹20岁被选拔推荐为秀才时,母亲说:“所望汝得名者,冀不坠先声,为科目儿,侍裙牏尔。宦路险,一行作,即我生死不见知。春秋榜,可命并取,可勿图仕。即艰食,可授学,给我破衣粗韮,杭织海错无取也。”(《郑母黎孺人墓志铭》)[3]母亲的庭训概有如下要点:第一,为了“不坠先声”。“先声”是家族的一种精神财富,包括功业盛德、伦理祈向、文章盛名等,子尹先祖为江西吉水人,七世祖郑益显为游击将军,随刘綎入播平乱,后居遵义城西之水烟田。对祖上的功业,子尹常常引以为荣:“维昔别子公,锋冠刘綎军。”(《阿卯晬日作》)郑氏祖上,出了两位进士,一是康熙时期的郑之桥,授翰林院编修,是子尹祖父的族祖父;二是乾隆时期的郑琯,官黄平州学正,是郑珍的伯曾祖父。子尹祖上,多有诗歌传世,如郑东里、郑琯、郑学山、郑文清等。他所辑的诗集《播雅》、所录母亲平时家教言行的《母教录》,是对祖上文学和文品的礼赞,对于家族后人来说,是家族传统的不朽典范,是教育子孙的示范读本。第二,功名可取但不必为官。古代的士人读书科考,大都奔着做官去的,母亲之所以这样嘱托儿子,是因为“宦路险”——官场险恶。母亲太了解儿子了,在母亲看来,儿子生性淡泊,不知官场应对,一旦做官,恐多不测。第三,为了生计可求教职。子尹至孝,谨遵母亲庭训,后来得了“大挑”二等,也只是做过学正、教谕之类的学官。他接受主讲启秀书院的教职,为的就是就近可以奉养母亲。后来已曾赴镇远任训导,赴荔波任教谕,都是生计所迫。51岁时,贵阳知府刘书年聘请他到省城担任书院监院,被他拒绝了。
子尹参加过三次乡试,第三次是在32岁(1837)那年秋天,终于得中举人。据凌惕安《郑子尹年谱》载:子尹作文喜用古字僻典,譽写人不识,错写的较多,考官俞汝本细心,调子尹的原卷来对读,果然不错,这才取了。这次能中举,也属侥幸。当时子尹做完试卷,时间还早,觉得无聊,就在考场里做了一首长诗。其中一段可见其应试之目的:“所以来试者,亦复有至惰:父母两忠厚,辛苦自夙婴,一编持授我,望我有所成。未尽无所成,而世以此轻。因之忘颜厚,自量非不明。贵从老亲眼,见此娇子荣。痴心有弋获,焉知非我丁。”(《完末场卷,矮屋无聊,成诗数十韵,揭晓后因续成之》)十多年的的游宦生涯,子尹早年的锐气渐渐磨灭,其实子尹是不想来应试的。试与不试,常常成了他内心的纠结。为了能让父母高兴,也为了一大家人的生活,所以这才厚着脸来应考。
三
子尹之所以屡试不售,与他不喜时文、淡泊名利、向往林泉、侍亲至孝的个性有关,亦有科场腐败的因素。
不喜时文。子尹所处的时代,朝廷以八股文取士,读书人要想步入“正途”,必须做好八股文,舍此无他。八股取士发展到晚清,已经完全程式化、形式化、僵死化。富商巨贾们为了应对考试,延请名士,馆于家塾,将所拟数十题,参照成稿各撰一篇,计篇筹价,令其弟子记诵熟习,以备考场之用。对大多数具有真才实学的士人来说,八股文实在是扼杀才学的魔刀。子尹平时着力于六经训诂,在朋辈中已有名气,说他文笔精到。子尹为文,“纯白古健,变化曲折,不豫设局度,任其机轴,操纵自如。”[4]而做这种八股文,子尹是无奈之至,说自己做这种文章,就像搾油饼,加紧楔子,用力压搾,油也就出来了。这样的文章像什么呀,就像庄子说的对着夏虫讲冰雪。子尹第二次参加乡试,还是没考上,但他并不在意,决心把精力放在学术研究上,他尽其可能地购置儒学典籍,把自己的书斋也命名为“巢经巢”,潜心于汉学研究。
生性淡泊,无与世争,不知官场应对。“我生骨少媚,所如辄坎坷。”(《游石鼓书院……》)大概具有真才实学的人都不会趋炎附势,逢迎拍马,却多了几分铮铮傲骨,这样的人是很难适应官场的。子尹爱梅,《巢经巢诗》中有近十首咏梅的作品。子尹还在子午山上栽种一片梅树,写下《梅垓记》以叙其情。梅之傲雪凌霜的品质,为子尹所亲近与仿效。他说自己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一路坎坷。道光十八年(1838),子尹与子偲(莫友芝)同赴京师应试,二人“逆旅对床,闭门赏析,鲜与世接,未及两月,外议沸起,厌物之号,遍于京师。识与不识,指目而唾。计吾两人,初未尝敢忤一人,惟是语言拙讷,应对疏野,其于伺候权贵,奔走要津,为性所不近,不能效时贤之所为耳!”[5]科场有科场的潜规则,郑、莫不知进退,不能像那些士子那样“伺候权贵,奔走要津”,自然会被目为“厌物”。这样的个性,即使你文章做的再好,也不会被录取。子尹曾随舅父黎恂往云南平夷做幕宾,尽管是舅甥加岳婿的关系,子尹还是感到很厌烦:“出衙更似居衙苦,愁事堪当异事征。”(《自沾益出宣威入东川》)说自己就像嵇康那样,虽未长虱子,却同样“把骚”不已,浑身不自在。子尹在平夷只待了一年的时间,就回到他的巢经巢去了。
性至孝。子尹受母亲影响,从小喜欢劳动,凡打柴、生火、甚至纺织等家务活,都争着去做。25岁那年,母亲生了一场大病,四处寻医问药,医生也束手无策。子尹刺破指头,给文昌帝君(读书人的保护神)写了一封血书,愿自己减寿十岁,也要治好母亲的病。在焚化血书、香烛默祷之后,母亲的病逐渐好了起来。在子尹看来,侍奉母亲比什么都重要。不得已出门谋生计,只要撰够了一个月家用,子尹就赶回来见母亲。离家宦游,他无时不在思念母亲,“自腊初之俶驾,倐榆火之已新。高堂老泪日不知其几落,鲜衣游子尚自得乎京尘。”(《思亲操》)是说自己腊月初一就离家启程,一转眼又见点新火迎新春了。不知母亲为儿子掉了多少次眼泪,做儿子的却衣着光鲜地在京城里徜徉自得。子尹心中所牵挂的,只有母亲。“万事无心早闭关,慈云依映懒云闲。梦中悔送朝晖过,守着夕阳尚满山。”(《山中杂诗四首其二》)对于子尹来说,乡居奉母的祈愿远远超过获取功名。后来母亲去世,子尹悲痛欲绝,在子午山筑舍守墓,其间回忆母亲生前的点点滴滴,写下《母教录》一书。儿子对母亲的那份深挚感情,于此书可见一斑。
向往林泉,耕读传家。子尹一生,酷爱自然,只有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他才能忘记世俗的烦恼,所以写下不少山水田园诗。游黔灵山,饮圣泉水,他会感于造化之神奇。到云南,往紫云庵看梅,那满树的梅花,仿佛一下洗去所有的郁闷忧伤。山居,可以尽情享受亲情之乐。“晚饭依花聚,林风入酒醒。闲情更无暇,儿女上池亭。”(《山居夏晚》)原来的子午山荒芜贫瘠,子尹用了几年时间,培植成了一处清幽雅静的园林。其中佳景无数,子尹作《子午山杂咏十八首》。如《果园》:“山妻识方法,栽接罗高卑。小女时偷果,持竿叶底窥。”小女持竿窥果的神情宛若画中。又如《藻米溪》:“溪翁相识尽,遇饷即牵留。下来还上去,得得复悠悠。”与溪上老人和谐融洽的的关系如在目前。子尹自号“子午山孩”,足见其对山居生活的挚爱。在子午山,子尹永远都是一个孩子。葆有的,就是一个孩子的纯真。
子尹在山居中还能享受人生之另一种乐趣——读书。世人读书,惟做官为目的,子尹读书,是一种生存方式。“窗外落光翠,庭气霭凉阴。静数门前树,归来沙际禽。仕途殊冷暖,人事信升沉。清净西林月,明明照此心。”(《尧湾夏暝》)在屋里读书,不觉也是黄昏来临,看着远处的山峦树木,归来的白鹭,只觉得仕途冷暖、人事浮沉都算不上什么,此时自己心地澄澈,就像西林上那皎洁的月亮。这时的子尹,心情变得单纯了,享受着陶潜“即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的人生况味。
科场的腐败,是子尹落第的外在因素。科举制运行到晚清,已有千年时间,其弊窦丛生,积重难返。咸丰八年(1858),发生了一场重大的科场舞弊案,被人们称为晚清科场第一案,这个故事说明,人们对科场舞弊已经见怪不怪,习以为常。贿赂考官,是士子获取功名的有效途径。有人凭借这样的手段飞黄腾达,有一幅对联,可以窥见科场当时之黑暗:
公刘好货,菩萨低眉,六万两特放优差,广东被害。
少许胜人,空谭无补,八十名循行故事,赴北为高。[6]
说的是光绪年间广东的一次乡试,刘(富姚)、萨(廉)、许(振祎)三人分别担任此次考试主考官、监考官,与广东总督谭钟麟沆瀣一气,营私舞弊,公然索贿,录取的八十名举人,以贿银的多少而定,让广东的众多士子深受其害。不独广东,全国上下皆如是。
科场腐败令当时的有识之士深恶痛绝,龚自珍的七绝“九州生气侍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就表现了对于科举制的切肤之痛,也传递出改革科举制的急切愿望。
如此腐败的科场,子尹数次败北就不难理解了。
[1] 郑珍.巢经巢诗钞注释[M].龙先绪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162.
[2] [英]阿兰·德波顿身份的焦虑[M].陈广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53.
[3] 莫友芝.莫友芝诗文集·郘亭杂文燹余录卷一[M].张剑等点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689.
[4] 郑知同.子尹府君行述[M]//郑珍家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151.
[5] 莫友芝.莫友芝诗文集·郘亭遗文卷五[M].张剑等点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620.
[6] 晚清科场故事.http://bbs.tianya.cn/post-no05-105682-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