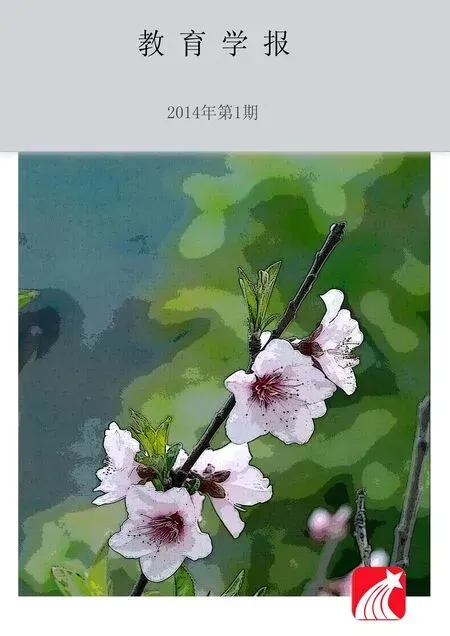教育何以关涉权力
徐 巍
(华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广州 510631;河北师范大学 民族学院,石家庄 050091)
一、权力
美国政治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在其逝世前完成的巨著《权力与繁荣》一书中针对其长久思考的“为什么有些国家是富裕的,而有些国家是贫穷的?”[1]这一问题提出:导致一个国家富有或贫穷的根本性因素并不是资源、人力资本或技术上的差异,而是由于“制度与经济政策,也就是界定国家属性的那些东西”[2]9。奥尔森认为,一个社会中经济的繁荣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财产所有者对财产清晰稳定的财产所有权以及相关权利,二是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强取豪夺。”[2]3而这两个条件实际上也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那就是合理的权力分配和约束机制。奥尔森认为,虽然满足这两个条件并不能确保完美的市场运行机制,但已经具备了足以使得社会经济繁荣的最基本条件,而这两个条件的实现与社会运行的制度设计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这种社会制度要能够有效地防止政府或者其他团体对私人产权的掠夺,通过保护生产者从事经济活动的利益而激发人们从事生产与商业活动的热情,并因此而导致经济的繁荣,正因为如此,奥尔森将其著作命名为《权力与繁荣》。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在其《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也提出:政治自由、经济竞争、社会机会、透明性担保、防护性保障等条件共同构成了社会经济繁荣的基本保障和动力。森的观点恰似对奥尔森所阐述的“权力观”从不同角度所做的阐释,二者相互呼应,在某种意义上共同解答了同样的问题,那就是一个社会的经济繁荣与权力机制的关系。“权力”何以成为解释经济繁荣的关键因素,“权力”与教育是否又有某种“神秘”的关系呢?
传统上,权力既非经济学考察的基本问题,亦非教育学关注的理论视角,而是政治学研究领域的“圣杯(the Holy Grail)”[2]2。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对权力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古希腊时代,柏拉图在其《理想国》《政治家》《法律篇》等著作中对国家政治体制进行了讨论,他从“什么是最好的国家政治制度”这个问题出发,讨论了城邦应该由什么人来统治,统治者应该拥有何种政治权力,在何种程度上拥有,行使最高权力的人是否应受到约束等问题。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继续对当时希腊城邦国家的各种政治制度进行比较研究,试图发现最理想的国家制度,之后历代西方政治思想家无不对权力在人类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加以论述,权力也因此而成为政治学所研究的核心范畴之一。
然而,随着人类对自身及社会理解的不断深入,学术研究的边界和视域也在不断变化,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分别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发现了“权力”的在场,并沿着各自的研究路径顺藤摸瓜地捕捉到“权力”这一重要因素发挥作用的隐秘方式,经济学在社会经济繁荣的表象下发现了权力机制的决定性影响,社会学在社会诸现象的幽暗背景中发现权力的关键作用,文学在对其合法性的历史考察中也发现了权力之手的影子,权力这一传统政治学殿堂中“圣杯”的光芒似乎照亮了更多学术领域晦暗难解的谜团,“权力”也不再是政治学研究的专属领地,而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公共问题。伯兰特·罗素(Bertrand Russell)认为:“权力是社会科学的基本概念,犹如能是物理学的基本概念一样。……社会动力学的诸规律也只能以各种形式的权力来阐明。”[3]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提出:“在社会科学中,不能把对权力的研究当成是次要的问题。可以说,我们不能等到社会科学中比较基本的观念都一一阐述清楚之后,再来探讨权力。没有比权力更基本的概念了。”[4]米歇尔·福柯(Michael Foucault)认为,权力像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一种不断流动的能量,在日常生活最细微之处都能发现权力的影子,权力可以说是“无处不在,不仅因为它拥抱一切,而且因为它来自一切。”[5]
权力何以成为影响社会生活诸领域的基本因素?人类作为社会性动物需要通过一定的组织方式生活在一起并构成社会系统,除了维持种群生存与繁衍之必要活动,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便是通过何种方式组成社会。社会构成方式意味着某一个体或阶级、集团在社会群体中所处的位置以及拥有的权力,而在社会群体中的位置以及权力则决定着不同个体的生存方式和生存机会,这对于每个个体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这种群居生活所要求的社会关系体系不仅仅存在于人类的社会生活中,也存在于动物的社会生活中。美国动物行为学家弗朗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通过多年研究发现在黑猩猩的社会中也同样存在着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对权力的斗争,成年雄性黑猩猩通过武力、联合或斗争的策略获得在群体中的支配性地位,成年雌性黑猩猩也通过微妙的联合、支持或反对的方式左右着群体中的权力结构,这种斗争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一般对动物情感、智力以及社会关系复杂程度的认识,德瓦尔认为就此意义而言,“政治的起源比人类还要古老”[6]。
权力不仅仅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而且是理解人类社会生活方式的一个关键要素。人类社会生活有一种基本的机制,那就是人与人之间以何种关系从事社会生活,这种基本的机制控制着社会公共生活的运作,这种机制——用罗伯特·H.威布(Robert H.Wiebe)的话来说——就是“规矩”,而“规矩这个词的含义就是权力”[7]。在社会生活中,权力掌控者决定着社会生活的组织结构、利益分配方式、游戏规则、话语权,这种控制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系统和角落,“从家庭到兄弟会、专业协会、地方政治组织,以至国家,处处如此。在家庭一级,岳母与女婿,婆母与儿媳间的冲突具有典型意义,其实质也是一种权力斗争,即保护一种已经建立的权力地位,反对建立新的权力地位。……工商业之间的竞争、业主与雇工之间的纠纷,往往不是为了经济利益,有时甚至主要不是为了经济利益,而是为了互相控制或控制他人,也就是说,为了权力。最后,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民主国家,从地方到中央,其整个政治生活就是持续的权力斗争。”[8]
权力结构也决定着社会关系中个体的行为限度与权利,经济学因此而发现在经济生活中这种结构所导致的对经济行为的打击与激励,社会学因此而发现这种结构对阶级构成与生活方式的影响,在任何一项由人参与和组成的社会活动中都存在着这样一些基本的问题:谁拥有权力?谁可以发言?为了谁的利益?实现谁的意志?因此,权力在人类社会生活中体现的是关系的存在方式,这种关系的存在方式在由人所组成并从事的社会政治、经济、教育等所有社会事业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为了“揭示构成社会宇宙(social universe)的各种不同的社会世界(social worlds)中那些掩藏最深的结构,同时揭示那些确保这些结构得以再生产或转化的‘机制’”[9]7,提出“场域”概念并把“场域”作为其研究社会问题的基本构型。布迪厄把人类社会比做一个巨大的“场域”,其中除了利益、策略、斗争等基本元素之外,还有一个更基本、更重要的元素,那就是权力,在一定意义上讲,正是权力这个因素决定着整个场域的结构和其他因素的形态,为此,布迪厄还特意提出了不甚完美的“权力场域”概念,一个社会中的政治、经济、教育都是彼此关联的“子场域”,而“权力场域”则处于一个相对特殊的位置,权力的分布形态影响甚至决定着各“子场域”的存在状态,因此对任何一个特定“子场域”的研究,都“必须分析与权力场域相对的场域位置”[9]104。
二、教育
权力以何种方式影响着教育,在作为社会场域子系统的教育体系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而一个社会、国家中的教育又以何种方式与权力发生着关联的呢?
教育作为一种塑造人的活动与政治有着近乎“天然”的关系,古代东西方的政治思想家在研思统治之术时都不约而同地论述了教育的功能,也因此而被教育史家冠以“教育家”的美名。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构思有哲王统治的“理想国”,并把教育作为巩固其统治的必要手段。柏拉图为了培养出符合“理想国”需要的护国者,提出教育应该被置于城邦的强制性管理之下,并煞费苦心地提出可以在教育中使用其所谓“高贵的”谎言[10]。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进而指出教育与政体之关系:“邦国如果忽视教育,其政制必将损毁。一个城邦应常常教导公民们使能适应本邦的政治体系(及其生活方式)”,因为“平民主义的性格创立了平民政体并维护着平民政体;寡头主义的性格创立了寡头政体并维护着寡头政体”。[11]在中国,教化作为统治术的一部分早已不是秘密,儒家提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12],其对教育与政治关系的重视程度由此可见,对于孔子而言,从事教育本身也就是在进行政治活动,因此当有人问孔子为何不去从政的时候,孔子回答:“《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13]
国家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组织形态与机构,将教育与统治权力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学校作为一种社会组织也具有了维护政治统治的功能,在统治阶级权力掌控之下的教育机构以培养统治阶级所需要的人——具有符合统治者利益的性格与观念的人——为目的,要在被教育者的头脑中建立对统治阶级的文化、观念、道德与价值体系的认同感。在统治权力的控制和谋划下,“正确”的知识与“高尚”的道德被制造出来并作为教育的内容写入教科书中,而种种教育目标的实现,无不体现着权力之手的意志和精细入微的安排。在中国,儒家思想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在国家强权力的保护下,通过其几乎无所不在的教化形塑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与伦理观;在西欧,当基督教会在西罗马帝国的废墟上成为统治性力量,并拥有了控制教育的权力时,基督的信仰与观念经历千年浸染被融入西欧诸民族的血液之中;近代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也通过教育把 “爱国主义”的观念牢固树立在国民的价值观与情感中;而当1939年一代德国青年以崇高的使命感和满腔的热情投入到纳粹发动的战争时,不能不说纳粹的教育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认为,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因此在现代社会政治生活中,阶级与阶级斗争仍然存在,国家权力维护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作为国家机制中一部分的制度化教育系统也必然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服务。一个社会、国家、政府中统治权力的所有者会精心地构建其教育系统,这个系统的目标指向统治阶级的利益,统治者的意志将最大限度地得到贯彻,这个系统要既能够满足既定目的的需要,同时又能够防范可能出现的偏离,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中存在着多元的力量纷争,权力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正如尼古拉斯·马斯特斯(NicholasA.Masters)曾言:“显然,任何起如此重大作用的社会事业是不会被允许在某一政体下任意游荡的。拥有权力和影响的团体与个人在必要时刻,将会尽最大努力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塑造一个体系,并使课程设置得在技术与科学上符合自己特殊的需求。”[14]
三、权力与教育研究
传统教育学关注的是如何把更多的知识传授给更多的人,如何让人更加自然的或全面的成长以及教育方法与教育的理想类型,教育学家更乐于阐述的是他们对于教育的美好期望。传统教育学往往把被教育者设想为温室中的花朵,而教育者则是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设置温度和土壤的园丁,但这种教育学有着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忽略了掌控着教育的无形或有形的社会权力之手,也因此而丧失了对教育作为社会现实的解释力。学者董标认为:“教育理论偏爱人是人的命题的崇高意义,在漠视人的具体利益的前提下,谋求人的发展的最大化。但是,不为社群一员的个人,作为生物学和生理学的确凿事实,不是教育理论的立足点。”[15]
教育与政治、权力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一个国家的教育形态往往与其社会、国家的权力形态同构同形,中国古代东周时期,天子式微、诸侯争霸,诸子百家争鸣,权力呈分散与多元之势,教育也相应地呈现多元蓬勃发展的态势,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教育权力完全为中央政府所掌控,焚书坑儒,万马齐喑,教育的繁荣不见,只剩统治权力宣扬的一家之言。美国建国后采用联邦制以及中央政府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州享有较高程度的自治权,教育的权力也相应地在宪法修正案中规定属于各州及人民所有,时至今日,教育仍然是美国联邦政府不能以行政强权涉足之领域。19世纪法国的政治体制是高度中央集权,学校教育也完全处于教育部的控制之下,法国的教育部长只要看一看表就可以知道“整个帝国的学生这个时刻在学习维吉尔诗篇的第几页”[16]。一个社会或国家中的制度化教育体系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更大社会整体的一部分,教育作为一个子系统,既在其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又受到更大系统运行机制的制约,同时也与其他子系统发生着复杂密切的影响。因此教育的研究不可以就教育而论教育,就教育问题而论教育问题,探究教育的现象不能脱离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的因素而孤立分析,单纯地把教育的现象或问题在学校或课堂的范围内讨论的做法既无法真正理解教育问题的成因,也因此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教育问题。比较教育学家迈克尔·萨德勒(M. Sadler)曾说:“在研究外国教育制度时,我们不应忘记,发生在学校外部的所有事情比发生在学校内部的事情更为重要,它们制约着并可用来解释校内的那些事情。……一个国家的教育制度……隐含着某种左右民族生活的潜在力量。”[17]38弗雷德里克·施奈德(Friedrich Schneider)认为,对于教育学的研究“视线不能局限于教育领域,而是要研究各种形成性因素,熟悉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以及一般文化”[17]49。教育研究不能忽视权力的在场,忽视了权力就无法正确地理解和解释教育现象,现实中的种种社会问题往往仅是冰山的一角,在表象之下是盘根错节的利益纠结与权力角斗。教育并非独立的社会事业,作为社会系统中的制度化教育,它的目的、它的机制、它的手段都要受到权力的规范,教育目的不是教育本身所决定的,而是决定了教育所在的社会形态的权力所决定的。随着教育学术领域研究的不断深入,权力与教育的关系也引起了更多研究者的重视,那么,权力是通过何种方式实现其对教育的影响的呢?
(一)权力对教育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对合法性知识的界定
对于任何一种统治权力而言,知识——尤其是文学、历史、宗教、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知识——都不是完全中立的,它以自己的方式对美与丑、善与恶、是与非、高尚与卑劣提出道德与价值判断,要么为既有统治提供理论与舆论的合法性支持从而构成统治力量的一部分,要么对现实进行批判或否定而成为推进社会前进的力量。统治权力会通过对知识的甄别、筛选、鉴定而宣扬、创造符合其统治利益的知识,而批判、否定、修改或者隐去不符合其意识形态的知识。在学校教育中,知识的合法性主要体现在课程的设置与内容的选择,阿普尔(Michael W.Apple)说:“课程从来都不仅仅是知识的不偏不倚的汇集,正如一个国家教科书里以及课堂中所显现的情形。它总是一种选择性传统的一部分,是某人选择的结果,是某个集团对合法性知识的见解。……当某个集团的知识被定义为最合法的、官方的知识,而其他集团的知识则几乎被视而不见时,这种决策本身就说明了关于谁在社会中拥有权力的重要事实。”[18]
课程与书本知识的合法性选择只是全部知识甄别的一部分,一个社会可以通过学校之外的诸多复杂方式成功地实现对其成员的教育,这种知识弥散在文化、宣传、法律、规则、娱乐、社会生活方式、习俗的每个角落,权力之眼在所有场域的最高处注视着这一切并以无所不在的力量渗透进这一切之中,文学是被允许发表的文字,历史是被胜利者书写的历史,歌曲是被歌唱的文学,仪式是给粗人看的书,知识是喂哺思想的乳食,也是权力之手的延伸。
(二)权力对教育的影响同时体现在制度化教育系统的权力分配与运行机制中
以法律或制度的方式所规定的谁拥有对教育的管理权以及实现管理的方式是一种基于暴力基础的强制性权力,是教育权力分配与归属的坚硬结构。在一个国家的教育制度中,它确定着谁有权力干预教育行政事务,决定一个学校能否创建以及必须接受什么人或机构的管理,学校行为的限度、以及谁拥有接受教育的权利等。权力对教育机构的掌控最显而易见的体现就是对学校系统的掌控,权力掌控者建立或通过其他方式控制学校系统,决定学校系统的教育目的,制订学校系统的规则,教师的资格、教科书的内容、考试的方式、并通过人员的任免来实现对学校教育的掌握。这种权力往往被称为行政权力,以区别于学术权力或基于其他资本的权力,但二者并没有截然分明的界限,权力的面孔是多样的,但它所体现的永远是权力拥有者的意志与斗争。
(三)权力对教育的影响还体现在教育的方式与手段中
与目的相比,手段有时候被认为是相对次要的,但手段本身也是一种技术,这种技术本身就是一种博大精深的知识体系,它既体现于物理,也体现于规则;它既通过肉体,也关注精神。
教育的方法与手段与教育目的有着密切的因果关联,具体方法虽然不胜枚举,但就其目的指向而言,可分两类:控制的方法与解放的方法。前者以控制为目的,视教育与被教育者为指向某种目的的工具或手段,以机械记忆、服从权威、扼杀思考力为特征;后者以解放为目的,是教育为实现“人的解放”的手段,主张“教育之外无目的”,以鼓励思考,不服从权威、培养思考力为特征;前者如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权力技术学”中所揭示的“规训”手段,从背手挺胸的身体姿势到教育生活空间的设计,从精心构思的奖惩制度到特定思维习惯的培养,从全景敞视的监视技术到作用于肉体的规训细节,这种技术无处不体现着权力的影子。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指出,在教学方法中,“灌输式的方法”能够把学生的创造力降到最低并使学生“轻信”,而“提问式的方法”则能够使学生批判性地思考现实,前者符合压迫者的利益,而后者则符合人民的利益。一定的教育目的必定与一定的教育技术相匹配,它是实现目的的工具,没有适切的工具,目的也无法实现。
教育是培养人的行动,作为一项有组织的社会事业,教育指向特定的理想、目的和利益,虽然不同的言说者以各自的观点阐发着对于教育的理想、构思、观点,但在纷繁复杂的教育表象之后,却有一个简单的事实——同时也是一个基本的教育原理:掌握教育权力者实施教育。理查德·肖尔(Richard. Schauer)讲:“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中立的教育过程。教育要么充当使年轻一代融入现行制度的必然结果并使他们与之不相背离的手段,要么就变成‘自由的实践’,也即人借以批判性地和创造性地对待现实并发现如何参与改造世界的途径。”[19]权力直接决定着合法性知识的界定、制度化教育系统的掌控与教育的手段,不理解教育背后的权力之手就无法真正理解教育,对教育中权力机制的研究有助于认识教育的现实,发现社会现实中教育问题根结之所在。教育学研究的规范与实证范式分别指向教育的理想阐扬与现实批判,二者互相配合可以共同构筑更科学、更有力量的教育学。
参考文献:
[1] Mancur Olson, Mancur, Distinguished Lecture on Economics in Government-Big Bills left on the Sidewalk: Why Some Nations Are Rich, and Others Poor[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0(2):3-24(Spring 1996).
[2] 曼瑟·奥尔森. 权力与繁荣[M]. 苏长和,嵇飞,译.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5.
[3] Bertrand Russell, Power: A new social analysis[M]. George Allen &Unwin Ltd, London,1938:4-6.
[4] 安东尼·吉登斯. 社会的构成[M]. 李康,李猛,等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410.
[5] Micha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I: An Introdution[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0:93,94.
[6] Frans De Waal, Chimpanzee Politics[M].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7:207.
[7] 罗伯特·H.威布.自治——美国民主的文化史 [M].李振广,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52.
[8]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M].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Beijing, 2005:39.
[9] Bourdieu.Pierre & Wacquant.Loic.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M].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
[10] 柏拉图. 理想国[M]. 郭斌和,张竹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6:127.
[11]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5:406.
[12] 《礼记·学记》
[13] 《论语·为政》
[14] 理查德·D·范斯科德,理查德·J·克拉夫特,约翰·D·哈斯. 美国教育基础——社会展望[M].北京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所,译.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69.原文出自:尼古拉斯·马斯特斯. 公共教育政治学[M].
[15] 董标.教育与国家.未刊文.
[16] 詹姆斯·C.斯科特.国家的视角[M].王晓毅,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293.
[17] 何塞·加里多. 比较教育概论[M]. 万秀兰,译.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18] 迈克尔·W.阿普尔. 文化政治与教育[M]. 曲囡囡,刘明堂,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4.
[19] 保罗·弗莱雷.被压迫者教育学[M]. 顾建新,赵友华,何曙荣,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前言: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