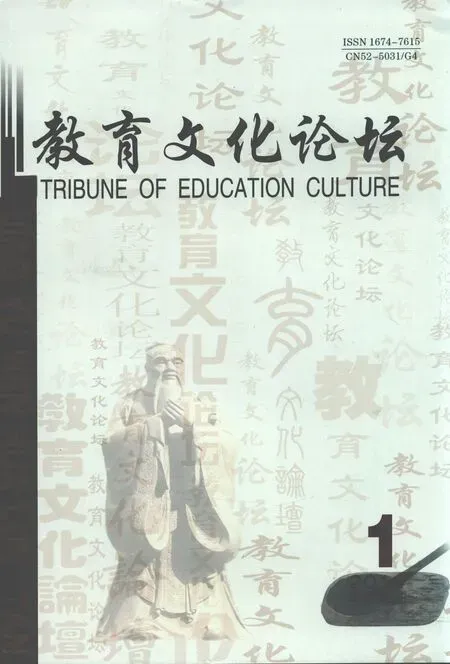论“撮泰吉”的戏剧艺术性
吴电雷
(贵州民族大学 西南傩文化研究院,贵州 贵阳 550025)
论“撮泰吉”的戏剧艺术性
吴电雷
(贵州民族大学 西南傩文化研究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撮泰吉”从四个方面充分体现出它的戏剧艺术性:一是演员扮演角色,当众表演一个含有矛盾冲突的故事;二是具备演员、角色、观众三位一体的戏剧特质;三是其语言唱腔、服饰道具、舞蹈乐器等方面的艺术性;四是具备戏剧的表演虚拟性(象征性)、程式性和综合性。所以说,“撮泰吉”是彝族一出古戏,是一出仪式程式和戏剧因素兼备的傩戏。既不能凭其民俗事项的内容,来否定其戏剧性形式。同时,说其是“一种健全的戏剧形态”,亦过之。
撮泰吉;仪式;戏剧;艺术性
贵州彝族“撮泰吉”*彝语音译,又称“撮衬姐”、“撮泰几”、“曹腾紧”、“撮屯基”、“撮寸己”、“撮特几”、“撮特坚”、“撮特基”、“撮登几”、“搓特基”等。,又称“变人戏”、“彝族古戏”、“彝族戏剧”、“彝族原始戏剧”、“彝族古傩戏”、“彝族创世纪戏剧”。种种称谓总离不开“戏”,可见“撮泰吉”是“戏”似乎是确定无疑了。但是,与事实相反,过去学者们对其讨论过多的是它的文化意蕴、民俗、舞蹈等内容,只有安天荣、庹修明、顾朴光、皇甫重庆等为数不多的学者宏观论证了它的“戏剧形态”身份*安天荣《〈撮衬姐〉戏剧形态及译名浅析》,《文史资料》第四辑“撮衬姐具备了戏剧的各种基因,戏剧形态占着主导地位”,参见陆刚主编《撮泰吉调查研究文集》,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36页;庹修明“威宁彝族傩戏‘撮泰吉’完成了傩祭向傩戏艺术的初步过渡,是傩戏的低级层次”,参见庹修明《原始粗犷的彝族傩戏“撮泰吉”》,《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顾朴光“(撮泰吉)不仅有对话和动作,而且有简单的故事情节和矛盾冲突,已经具备了戏剧的基本要素”,参见顾朴光《彝族古戏撮泰吉浅探》,《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4期;皇甫重庆“从内容到形式都闪烁着戏剧美的健全的戏剧形态”,参见皇甫重庆《彝族戏剧〈撮特几〉初探》,《贵州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但没有进一步解读它的“戏剧”内涵。笔者认为:从“撮泰吉”的表演内容上看是一种民俗事象,从其形式上看是一项演剧活动。下面将独辟专文,从“撮泰吉”的戏剧本质,表演因素和审美特征等方面对其“戏剧艺术”性质进行微观解读。
一
戏剧是什么?戏剧的本质就是角色扮[1],是当众表演一个含有矛盾冲突的故事。“撮泰吉”具备了戏剧角色扮演的性质,其中有五个主要角色:惹戞阿布、阿布摩、阿达姆、麻洪摩、嘿布,与宋“爨弄”之“五花”——引戏、副净、副末、末泥、装孤,京剧之生、旦、净、末、丑相对应。脚色职能上也基本一致,表演过程中惹戞阿布担当两种职能:一是“引戏”,串联剧情,交代每个排场演出的主要内容,引导其他角色表演;二是唱念祭辞,祭词内容是驱邪、讲史、祝福,由惹戛阿布领诵,与撮泰们的跟唱形成“一唱众和”的地方戏演剧形态。阿布摩、阿达姆一生一旦,为夫妻神,阿达姆这个角色由男性反串饰演。麻洪摩为净角,是一名将军。嘿布,彝语为“愚蠢者”,兔唇嘴,戴铁嘴面具,为丑角。其他表演角色还有阿安、牛和狮子。阿安是阿达姆和阿布摩的孩子,没有“戏份”,实际上起到道具的作用。两人扮演耕牛,三人扮演狮子。加上乐队两人,举灯笼者四人。这样,全场演出需扮演八个角色,十位演员,十六个人左右出场。
再者,这些表演者装扮成角色,当众表演一个含有矛盾冲突的故事。这里特别强调了“撮泰吉”演出的故事性。
“撮泰吉”故事性强,具有曲折的故事情节。第一幕“祭祀”开场时在场地四角点燃灯笼,由惹戛阿布扮山神宣读文疏,部分“龙套”演员走台步状绕场一周,然后分站于场地四角。伴着锣鼓,阿布摩领着几个撮泰老人,手拄木棍,下肢呈半蹲状,步子踉踉跄跄,同时,从喉咙深处发出阵阵后嗓音。来到场地,他们在惹戞阿布的带领下以酒向祖先、山神、谷神、火塘等各方神灵祭拜。之后,他们把马脖子上的铃铛套在手上,不停地摇晃着,同时踏着深浅急缓错落有致的舞步。第二幕“耕作”部分,演述先民在此地定居以后,如何烧火开荒、刀耕火种、驯牛养马、撒灰种荞、收荞晒场,喜获丰收的过程。期间,以粗犷夸张的肢体动作模拟先民买牛、驯牛、犁地、撒灰、播种、薅刨、收割、脱粒、翻晒、贮藏等系列情景,演述劳作间隙的歇息、喂牛、吸烟、交媾、喂奶等嬉闹情节。第三幕“喜庆”,主要戏份是舞狮子。惹戞阿布带领撮泰老人围着荞堆唱祝词,起舞欢庆丰收,随后,狮子舞蹈入场,把热闹场面推向高潮。第四幕“扫寨”,紧随“喜庆”一幕,在庆丰收的欢乐气氛中,惹戞阿布带着众位撮泰老人进村扫寨,为每家每户驱疫禳灾、祈福纳祥。他们进家入户后,要把木棒插在炕上摇来晃去,同时,说一些吉利的话,“一切天灾人祸、邪恶灾难随着老人去;一切吉利留下来,六畜兴旺,四季发财,五谷丰登,儿孙满堂”。此刻,主人要出门迎接,并备酒肉当以酬谢。
“撮泰吉”完整的故事,曲折的情节,经过长期传演,已经有了成熟的演出台本。“撮泰吉”演出活动由来已久,最初仅有彝语演出记录底本。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今,较为完整的记录文本有四个:1.杨光勋、段洪翔整理的《彝族古戏——“撮衬姐”》(1987);2.由文道华、文富强口述,罗德显、杨全忠整理《撮泰吉》(1987);3.由李永才、罗德显、马昌达口译,皇甫重庆记录整理的《撮太吉》(1988);4.由罗德显以威宁县板底乡裸戛村民组“撮泰吉”记录的彝文底本重新考订翻译出的《撮泰吉──古代彝语民间戏剧演出记录本重译》(1999)。其中,第四本对于演出时间、地点、角色、唱词、对白等表演事项分列清晰,已呈现出较为成熟的戏剧文本体制,起到演出文本的作用。
戏剧表演特别强调“当众”表演故事,既强调演剧场所因素,又突出观众因素。“撮泰吉”依据趣味性的故事和关乎生命的祭祀性有着稳定的观众群,这些观众不时与演员对话交流,使表演场上场下交融为一体。况且,“撮泰吉”的演出场所是几个空间的转换,或在平地广场、田间地头,或在寨中的街头巷陌。“祭祀”、“耕作”、“喜庆”三出一般在寨子西方的空地上表演,“扫寨”一出则转到村寨中演出。从戏剧发生学的观点考察,村外旷野,街头巷陌正是戏剧最初的表演场所。*例如:在日本,“戏剧”一词被写作“芝居”,“芝”是草地,“居”是存在,说明最初的日本戏剧是在草地上演出。中国戏剧也是从“沿门逐疫”的傩戏形态发展演化而来。
二
“撮泰吉”在服饰道具、音乐舞蹈、演剧语言等方面具备较为全面的戏剧特质。
服饰是构成戏剧的要素之一,它包括头饰、服装、面妆等方面。撮泰们头饰装扮独特,六个角色均有帽子装饰。帽子色彩、造型简单朴素,惹戞阿布用黑色或青色棉布缠头,阿达姆戴黑筒尖帽,其他角色用黑布或白布把头顶缠成尖锥状。服装则统一着青色或黑色长袍,穿蓝色或黑色短衣长裤,并用白布交叉缠于腰间。面妆,早期演出“撮泰吉”时,惹戞阿布不戴面具,随着经济和文化交流,他和其他撮泰一样也被戴上面具,形色与阿布摩相仿,戴白须面具。阿达姆为女性戴无须面具,麻洪摩戴黑胡子面具,嘿布戴竖状纹路的兔唇形面具,阿安为幼儿角色,戴无须面具。所有面具皆要全面戴。舞狮人头戴戎子帽子,身着披风长靠。
演出“撮泰吉”,道具主要有拐杖、牛头牛尾、狮子、火镰、瓦片、鸡蛋壳、竹编锥形帽、白布条、草鞋、牛角、五倍子木棍等。瓦片在买牛情节中当作银子,作为交易商品的货币,鸡蛋壳作族长惹戞阿布的眼睛,牛角则在祭祀时用作盛酒的器皿。五倍子木棍,一物多用,在撮泰老人行走时用作拄杖,劳作间歇抽烟时用作烟杆,当作耙土、收割、打场等农用工具,还可作为逐疫驱邪的神圣法器,等等。其他道具的演出用场通俗易晓,毋庸赘述。
舞蹈方面。“撮泰吉”演出以肢体模拟动作的“演”为主,唱为辅,因此,解析其动作舞蹈甚为重要。“撮泰吉”的舞蹈由表演示意性动作和原始舞蹈两部分组成。前者如“祭祀”一出的步形为例,采用罗圈脚蹒跚前行,上身僵硬,双膝微微弯曲,两脚外撇成八字,行动迟缓,略显艰难,行走时脚与肩同边,跨步幅度大,着力体现拓荒者的步履艰辛或者年高体弱。再者,“耕作”一出中的劳动、耕作、喂奶、交媾、买牛、给牛喂盐水等都是采用对人们生产生活动作的模仿。不过,对比实际生活,表演时动作有所放大。
表演过程中还穿插表演“铃铛舞”、“狮子舞”等原始舞蹈。在“祭祀”一出,表演“铃铛舞”*铃铛舞,彝语又称“肯毫崩”,又叫“跳脚”。,有几个青年人手持小马铃摇响拍节,撮泰老人们随节拍扭动腰肢挪动脚步,表演翻山越岭、披荆斩棘、互相背驮等系列动作。表演者一边跳舞,一边唱“啃嗬”,歌词有赞颂逝者功德、悼念亡灵和述古训世的内容。在“喜庆”、“扫火星”两出,为节日吉庆,喜获丰收,要耍狮子,表演狮子舞。狮子舞表演有三个基本动作:狮子笑天,狮子扑地,狮子滚绣球,舞狮人在惹戞阿布的指挥下舞动,念咒语。
“撮泰吉”的演剧语言腔调特点鲜明。演唱全用彝语,对白和诵词亦用彝语讲述,时而夹杂少量汉语。担当“引戏”的惹戞阿布一人用端公调主唱,其他角色如阿布摩、阿达姆、麻洪摩、嘿布等“撮泰”老人用吸气冲击声带发音重唱或接唱,音调低沉沙哑。唱时乐器不伴奏,表演时边舞边响锣、鼓、钹等乐器。“撮泰吉”表演在时而激昂时而低沉的声乐伴奏下,尽显历史的厚重和岁月的沧桑。
三
虚拟性、程式性和综合性是戏剧最重要的三个特征。关于“撮泰吉”的虚拟性,中间形形色色示意性动作即为戏剧“虚拟性”的原生形态。由于它在特定的时间,有限的空间内向观众展演彝族原始族群生存繁衍的发展历程,具有丰富虚拟场景和象征意义,充分体现了戏剧的这一特性。
首先,虚拟性体现在人物形象的象征性。撮泰老人们用白布条缠身象征裸体的衣服,表示人类还处在蛮荒时期无衣可穿。走路时腿脚呈罗圈脚,蹒跚前行,似从遥远的原始森林或穴居的岩洞中走来,象征原始时代彝族先人跋山涉水、迁徙繁衍的艰辛历程。说唱是从喉咙深处挤压出嘶哑的声音,象征拓荒创业时期先人的苍老形态。惹戞阿布包头的青巾,拖地青衫衣襟,象征智慧与老练,因为他被看作是自然神和智慧神的化身,是当地人幻想世界、精神领域的统治者。他的麻丝和麦草制成白胡须,象征长寿,眼罩用两个生鸡蛋壳制成,生鸡蛋代表天地未分时的混沌状态,眼罩象征透过混沌与朦胧,看清事物发展变化。阿布摩面具上的横式波浪状纹饰,黑帕缠圆锥状的头饰,阿达姆圆盘脸面具顶端螺旋形的白色纹饰,脸庞部位的下斜波浪状白色纹饰,黑帕圆锥状头饰等,寓意他们苍老、年事高。在表演过程中阿达姆不时轻拍背上的小孩,揉揉胸部,撮撮裆部示意自己的雌性性别,要担负着彝族社会生息繁衍的重任。麻洪摩是保家卫国、领军作战的军人,肩负彝族社会和平、安全的重任,所以戴的面具上画黑胡子,象征年轻、刚强和威武。嘿布,戴兔唇面具,表示口无遮拦,滑稽可笑,面具上的竖状纹路以示年轻。
整个故事情节象征性。“撮泰吉”用粗犷地象征性动作演出人类繁衍,在与自然灾害斗争中生息、发展,从刀耕火种走向驯服牲畜和使用工具而迎来丰收喜庆的欢乐。“撮泰吉”用“祭祀”、“耕作”、“喜庆”、“扫火星”四幕剧象征人类生产劳作春播、夏养、秋收、冬藏一年四季为周期的轮回过程。演出开始前,在场地的四隅有四个悬挂在木杆上的“朵鲁”(灯笼),意指把撮泰老人从祖先灵魂寄居的岩洞引送到表演场地。最后“扫火星”(亦称“扫寨”),借助“扫”之动作的象征意义,为整个族类禳灾祈福,扫进威荣丰年、福禄吉祥,扫除瘟疫病灾、口舌伤风、苦难纠纷等不吉祥之物。
其次,“撮泰吉”表演具有固定的程式性。年复一年,“撮泰吉”演出就重复祭祀、耕作、喜庆、扫寨四个叙事单位。其中,“祭祀”算是正戏之前的例戏,“艳段”。主要内容是布置戏场,举行祭祀祖先仪式,由惹戞阿布带领主要角色出场表演。“耕作”一折是正戏,演示先民春种秋收、夏育冬藏的生产过程。“喜庆”是正戏的第二出,展现丰收带来的喜悦之情,利用且歌且舞,舞蹈为主的演出形式。“扫寨”一出即为“撮泰吉”的尾戏。承接“喜庆”纳吉之后“驱邪”过程,撮泰们到寨中挨家挨户为乡民扫尽种种秽物,并为来年送上吉言良愿。整出戏开合有度,“开”部分蕴含着对先人的感恩与现实的满足,“合”部分寄寓着对未来一年的美好设想。
程式性在“撮泰吉”表演中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民间宗教的仪式性。从表演程式上看,四部分起、承、转、合各环节紧密衔接,呈现先祖开荒辟壤、刀耕火种、欢庆丰收的演剧过程,其实也是祭祀——感恩天降福祉——驱秽禳疫——祈求神佑的仪式过程,程式性是“撮泰吉”演出的基线。仪式性的内涵与其戏剧艺术形式并不相悖,因为“戏剧的根源则是宗教仪式,仪式可以看作是戏剧性的、舞台上演出的事件,而且也可以把戏剧看作是一种仪式”[2]。
“撮泰吉”活动集聚了音乐、舞蹈、美术、文学等因素,体现了戏剧的综合性质。从其表演目的看是娱神的仪式,实际演出变成一个娱人的节目,演员在表演过程中载歌载舞,剧中有舞,舞中有戏,戏中的文学成分占较大分量。
结 语
“撮泰吉”从四个方面充分体现出它的戏剧艺术性:一是演员扮演角色,当众表演一个含有矛盾冲突的故事,演述彝族先民迁徙、创业、生产、繁衍的发展历史;二是具备演员、角色、观众三位一体的戏剧特质;三是在语言腔调、服饰道具、舞蹈乐器等方面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四是具备戏剧的表演虚拟性(象征性)、程式性和综合性。所以说,“撮泰吉”是一出彝族古戏,是一出仪式程式和戏剧因素兼而有之的傩戏,只是产生的年代遥远,流播区域环境封闭,至今没形成成熟的戏剧形式。
说其是“一种健全的戏剧形态”[3],则有过之。因为它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冲突、悬念,缺乏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人物性格的刻画还不完整细腻。只能说,“撮泰吉”具备较强的戏剧艺术性,是不完整的原始戏剧[4]或称“亚傩戏”和“前傩戏”[5]。
[1] 康保成.后戏剧时代的中国古代戏剧形态研究[J].文艺研究,2008(1).
[2] 马丁·艾思林.戏剧剖析[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19—20.
[3] 皇甫重庆.彝族戏剧<撮特几>初探[J].贵州民族研究,1988(1).
[4] 杨光勋,段洪翔.彝族古戏“撮衬姐”[J].贵州文史丛刊,1987(1).
[5] 顾朴光.中国面具史[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6:325.
(责任编辑 杨军昌)
On the Dramatic Artistry of “Chuitaiji”
WU Dian-lei
(Southeast China Academe of Nuo Culture, Guizhou Minz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550025)
“Chuitaiji” shows its dramatic artistry in four aspects: 1) Actors and actresses perform a conflict story in front of an audience; 2) It has dramatic character of three in one of actor, role and audience; 3) It has artistry in language aria, clothing props and dance musical instruments; 4) It possesses the virtuality (emblematic), procedure, and comprehensiveness. Therefore, “Chuitaiji” is an ancient drama of the Yi people, a Nuo drama having both ceremonial procedure and dramatic element. Its dramatic form cannot be denied just according to its content of folk custom facts. At the same time, it is overdone to say that it is “a sort of wholesome dramatic form”.
“Chuitaiji”; ceremony; drama; artistry
2014-01-06
2009年教育部重大项目:西南傩戏文本调研与整理(项目编号:2009JJD850005),贵州民族大学引进人才科研基金资助项目(编号:校引才科研2013002号)研究成果之一。
吴电雷(1972-),男,汉族,山东平邑人,贵州民族大学西南傩文化研究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戏曲民俗、少数民族戏曲史研究。
J825
A
1674-7615(2014)01-012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