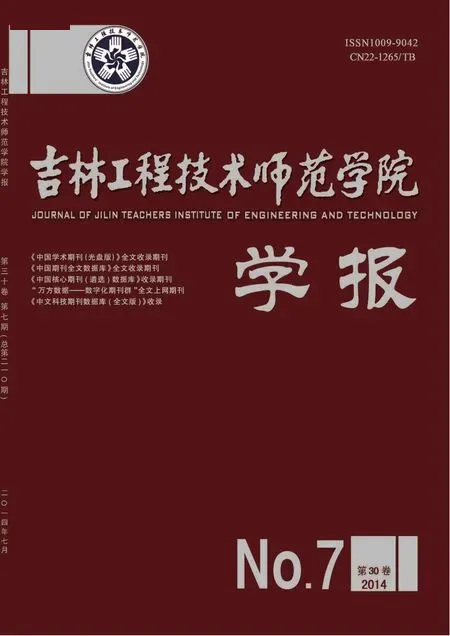国际人权视角下生物遗传资源的法律保护
魏连媛
(福州大学法学院,福建福州350108)
生物遗传资源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在生物技术蓬勃发展的今天,遗传资源中蕴藏的巨大商业利益引起了各国的注意,对生物遗传资源的保护也成了全球关注和讨论的焦点问题。一方面,发达国家试图利用发展中国家遗传资源的做法对发展中国家人民的人权造成侵犯;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对自身发展权的重视也造成了生物遗传资源在保护方面的重重阻碍。因此,从国际人权的视角看待生物遗传资源的保护问题,是国际生物多样性保护立法所要关注的重要内容。
一、人权与生物遗传资源的关系
人权一般是指一个人作为人所享有或应享有的基本权利。人权的内涵随着历史变革而不断变化和发展,为了反映人权的代际演进,著名人权法学者瓦萨克将整个人权体系分为三代权利。第一代人权的概念建立在《国际人权宪章》的基础上,其主要内容是公民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与社会文化权利。第二代人权的内容是民族自决权,此时国家的义务从消极地不作为转变为积极地作为,人权的性质也由关于自由和豁免方面的消极权利进化为积极的权利。第三代人权以发展权以及环境权为核心,它被国际人权文件确认并在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一系列决议中得到了突出体现。
(一)生物遗传资源与人类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密切相关
生物遗传资源是指具有实际或潜在价值的,来自植物、动物、微生物或其他来源的任何含有遗传功能单位的材料,包含物种及物种以下的分类单元(亚种、变种、变型、品种、品系、类型),包括个体、器官、组织、细胞、染色体、DNA片段和基因等多种形态。从这个定义来看,生物遗传资源可以大到一个完整的植物、动物或微生物个体,也可以小到这些个体中的组成基因。因此,从生存权的角度来说,作为个体存在的生物遗传资源可以满足生物遗传资源所在地居民的饮食需求,为其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从发展权的角度来说,作为个体存在的生物遗传资源,能够给当地居民带来生活上的便利,同时还能为国家带来经济上的利益。从科研价值的角度看,对生物遗传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技术成果的推广,都能够解决一国国内的重大难题,如粮食危机、健康问题等,同时技术成果推广所获得的收益也带动了遗传资源国财政收入的增长,满足一国发展权的需要。所以,生物遗传资源与人类的生存权与发展权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生物遗传资源对于实现生存权与发展权至关重要。
(二)生物遗传资源的保护与人权保护的内容存在重叠
由于生物遗传资源与人类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密切相关,因此二者的保护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重叠的范围。首先,保护目的具有一致性,两种保护都以实现人类的生存权与发展权为目的。随着人权内涵的不断演进,受其影响和调整的对象也不断增加。其次,义务主体具有同一性。生物遗传资源保护与人权保护的义务主体都是国家。再次,保护理念的共通性。生物遗传资源保护不仅仅是因为其利用价值,更重要的是基于对每个物种生命延续性的尊重,这种普世性的价值观与人权保护有着共通之处。
二、国际人权视角下生物遗传资源保护存在的问题
(一)生物遗传资源的保护与资源所在地发展权的冲突
利用遗传资源有目的地改良动物、植物的形状和品质,为人类解决粮食、健康和环境等21世纪的重大问题提供了诱人的前景。从地理分布上看,遗传资源较为丰富的地方往往是经济不发达、技术不先进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有着较大的人口密度,出于对生活环境的改善以及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发展中国家往往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谋求发展,此时对遗传资源的保护将不可避免地限制这些国家的发展权。
(二)生物遗传资源的研发过程与人权的冲突
利用遗传资源研发出新的技术或产品往往是为了改善人们的生活条件,或是解决一些医学上、农业上的重大问题,然而其技术和产品研发的过程有时会涉及对人权的侵犯。2012年8月30日,美国一科研机构发布了其对24名中国湖南省儿童进行转基因大米人体试验的结果,这一被称为“黄金大米”的事件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和争议。这一事件说明,生物遗传资源的研发利用并没有得到法律的有效监督和规制,研发过程中的实验对人体造成了损害具有不可测量性和难以预测性,因此难以估算其所造成的危害,同时对研发过程所产生的不利影响也没有相应的赔偿依据。但是,无论这种实验造成的损害如何,其对人权的严重侵犯是无可厚非的。
(三)发达国家“获取”与“垄断”的制度设计
印度的植物姜黄具有治疗伤口的医药作用,是印度本土所有的特有物种,然而这种植物却在美国被授予专利。相同的情况还有印度的楝树,这种在印度土生土长的植物具有驱虫治病的强大功能,却被美国公司申报了杀菌剂的欧洲专利。在我国,“北京烤鸭”虽然声名远扬于海内外,但是烤鸭的原料北京鸭已经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来自英国的“樱桃谷”,而“樱桃谷”正是由“北京鸭”在国外进行杂交后出现的新品种,之后又被被重新引进中国。
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继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资源的争夺后,发展中国家的生物遗传资源已经成为了发达国家觊觎的对象。由于生物遗传资源所带来的巨大的经济效益、发展中国家对本土遗传资源的不重视以及发达国家窃取手段的高明性,使得发展中国家的本土生物遗传资源流失愈发严重。而发达国家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完善的法律体系,当它们从遗传资源中研发出新的技术或产品时,其研究成果就处于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之下,从而形成了一种“产品垄断”或“技术垄断”现象。当发展中国家要引进这些利用本土遗传资源研发出的产品和技术时,仍需支付高额引进费用,这种现象不仅违背国际法的平等互利的原则,同时也侵犯遗传资源本土国的发展权。
(四)发展中国家对“惠益分享”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
惠益分享原则是生物遗传资源保护的原则之一,其目的在于对成员国遗传资源的获取进行规范,以及对利用遗传资源产生的惠益在资源提供国和资源利用国之间作出合理的分享安排,尤其是保障作为遗传资源提供国的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确定生物遗传资源保护和分享的路径十分重要,然而由于惠益分享机制的不健全,发展中国家对于外国利用本土生物遗传资源的所得利益很难得到平等互利的分享。
三、国际人权视角下生物遗传资源的法律保护对策
当前,在国际法体系中,与生物遗传资源保护有关的法律文件主要有《生物多样性公约》、《波恩准则》、《名古屋议定书》以及其他一些专门性法律文件。其中,《生物多样性公约》奠定了生物遗传资源保护的基础,该公约在序言中确认了“各国对它自己的生物资源拥有主权权利”,同时也明确提到“确认保护生物多样性是人类共同关注的问题”。在《生物多样性公约》框架下,《波恩准则》于2002年诞生了,《波恩准则》的宗旨是保护生物多样性,并对其进行可持续性利用,同时强调获取遗传资源的合法手段,确保对生物遗传资源所带来的惠益进行公正和公平地分享。《名古屋议定书》产生于第十届生物多样性条约缔约国会议,会议中,在关于今后十年生态系统保护世界目标和利用生物遗传资源及其利益分配规则的问题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取得了共同意见。
上述法律文件确认了生物遗传资源保护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第一,各国对本土的生物资源拥有主权,发达国家不得以生物资源全人类共享为理由来攫取发展中国家的生物资源。第二,对遗传资源的开发利用应当秉持可持续发展原则。第三,遗传资源的获取应通过合法的途径。第四,惠益分享应公正公平。从国际人权的视角来看,这几个重要问题在人权中映射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各国有利用本土遗传资源以谋求本国发展之权利;第二,发展权是有界限的,它的最大边缘是能够保障遗传资源的延续存在且不损害后代人对其的需求;第三,遗传资源的保护和公正公平的惠益分享对于保护遗传资源国发展权而言至关重要且需求迫切。
可以看出,国际人权与生物遗传资源保护存在矛盾和共进之处,而二者共进的部分却受到了来自发达国家掠夺手段的破坏,国际法作为维护国际社会的工具,在国际人权与生物遗传资源的保护共同受到挫折时,由于生物多样性破坏的不可逆转性,国际社会应当及时作出应有的法律对策。
(一)《生物多样性公约》地位的提升
《生物多样性公约》作为保护生物遗传资源的提纲掣领式的文件,对于遗传资源的保护有着指导意义,但是其在国际诸多公约中的地位并不高。《生物多样性公约》第22条规定:
1.本公约的规定不得影响任何缔约国在任何现在国际协定下的权利和义务,除非行使这些权利和义务将严重破坏或威胁生物多样性。
2.缔约国在海洋环境方面实施本公约不得抵触各国在海洋法下的权利和义务。从该条文可以看出,公约的地位普遍低于其他国际公约,当公约的履行与其他国际协定相违背时,各个国际主体遵循的是其他国际协定。虽然公约中有一项“严重破坏或威胁”的例外条款,但是这一条款在适用上的可操作性不强。此外,该条文的言辞对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表现出的是一种近似被动的先破坏后治理的理念,没有主动保护的意识。
(二)风险预防原则
风险预防原则是国际环境法的基本原则之一。由于现代生物技术尤其是转基因技术对生态系统、人类健康造成了很大的隐患,且这种隐患导致的损害具有范围广、不可预测、不可控制以及不可逆转性,因此需要确立风险预防原则来限制生物技术的使用。从国际人权的角度来说,风险预防原则的适用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此时的“风险”不再局限于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造成的风险,其还包括对人权损害的风险。这种风险主要体现在:首先,遗传资源的过度开采将导致损害当代及后代生存权与发展权的风险。其次,遗传资源的研发技术存在侵犯人类生命健康权以及环境居住权的风险。
因此,对遗传资源的开发利用应当从人类长远利益角度出发,对生物技术和生物产品带来的风险进行合理的分析、判断、预测和评估,预防其对人类生存权和发展权造成的损害,并针对风险的可能性建立相应的预防措施体系,并根据损害评估结果做好相应的损害救济。
(三)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应当有所限制
知识产权制度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而逐渐兴起和完善,使得现代文明在人类发展史上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其在推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随着知识产权制度的不断扩张,其渐渐演变成为发达国家攫取他国资源的工具。在遗传资源的流动过程中,发达国家获取遗传资源的手段常常不具有合法性,而遗传资源一经开发利用就立马得到发达国家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形成一种垄断的产业链,进而对遗传资源国的发展权造成侵犯。因此,在知识产权体系日益扩张和强化以致损害其他权利时,对其进行适当限制是非常必要的。
1.对用于人体的知识产权专利的限制。一些转基因农作物以及医药产品的研发过程以及使用往往具有很大的风险,而这种风险在知识产权的保护下很难得到有效的削弱或消除。一些研发人员在利益的驱使下,甚至不择手段以侵犯人类生命健康的方式进行科学实验,这种侵犯人权的做法却在知识产权的保护下日益猖獗。因此,应当主要从技术层面对这种知识产权进行限制,合理规制遗传资源的开发手段,禁止以人体为实验对象的任何研究。
2.对以不正当手法获取的遗传资源所产生的知识产权应当破除其保护。从国际人权的角度来看,目前生物遗传资源保护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发达国家大肆攫取发展中国家的遗传资源并以知识产权制度体系进行垄断的行为。发达国家以牺牲遗传资源国发展权的方式坐享巨额的利润,长此以往,必将导致发展中国家的不满乃至世界格局的动荡。
3.弱化知识产权的保护,防止知识产权的滥用。知识产权制度与遗传资源的保护始终是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知识产权的过分强化必然导致遗传资源的开采利用因得到法律保障而呈现出无节制、耗竭性的无序开发状态。知识产权同时具有人权和财产权的性质,当知识产权中的个人人权部分与国际人权冲突时,个人人权必将做出让步,而对于知识产权中财产权利方面的弱化,可以通过加强对其他财产权利的保护来平衡协调。
(四)惠益分享制度的建立和推广
遗传资源的开发利用带来了庞大的商业利益,随着技术产业领域的逐渐增多,遗传资源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广,对其商业化利用所产生的惠益形式主要有货币、产品、技术等。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与发达国家利益冲突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对于生物遗传资源所带来的惠益进行公平合理的分配,是平衡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利益冲突的关键所在。
惠益分享原则自从在《生物多样性公约》中得到确定之后,就引起了各国的广泛讨论,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多次谈判,但是,惠益分享制度建立的情形并不乐观。其主要障碍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于实现惠益分享机制的对立态度。发达国家主张采用“合同机制”,这也是当前国际社会上惠益分享机制主要模式。与“合同机制”相对应的惠益分享机制是“立法机制”,主要由发展中国家所倡导。这一对立的局面导致了惠益分享难以在国际社会上得到有效的制度化。
惠益分享原则已在《生物多样性公约》、《波恩准则》等国际性立法文件中确立,其对于保护生物遗传资源的重要性以及参与国的广泛性不容置疑。惠益分享制度的建立应当向“立法机制”的模式发展。原因有三:第一,与“立法机制”相比,“合同机制”具有个案性,这一特点显然不符合国际保护的需求。第二,“立法机制”有助于将谈判成果法定化,从而明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权利义务,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法律保护依据。第三,生物遗传资源大部分分布在发展中国家,且发展中国家的人权问题日益严峻,此时惠益分享的国际走向应当偏重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保护。
惠益分享制度的建立,对于实现国际人权与生物遗传资源的双重保护之共赢至关重要。惠益分享制度建立后,应当在国际范围内推广,鼓励发达国家加入与该制度有关的公约。发展中国家对于惠益分享的需求迫切,发达国家主动分享技术和成果的做法,能够促进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分享,推动生物资源利用的国际合作。
国际人权与生物遗传资源的保护既有互相包容之处,亦有矛盾重重的地方,国际法作为维护国际秩序的重要工具,在平衡与调和冲突时应发挥其调整功能,并针对实际情况做出灵活应对,建立相应的保护和分享机制。生物遗传资源是人类的重要财富,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对其进行合理的开发,看似限制了当代的发展权,实则为后代长远的生存权与发展权作出了正确的衡量。而惠益分享机制的建立,也将实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平等对话与协商,遗传资源给人类带来的财富将得到公平正义的合理分配。
[1]曾令良.国际法学[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史学瀛,仪爱云.遗传资源法律问题初探[J].政法论丛,2005,(5).
[3]周寒立.论《生物多样性公约》中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原则及其实践[D].上海:复旦大学,2009.
[4]孙昊亮.多维视野下遗传资源的法律保护分析[J].西北大学学报,2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