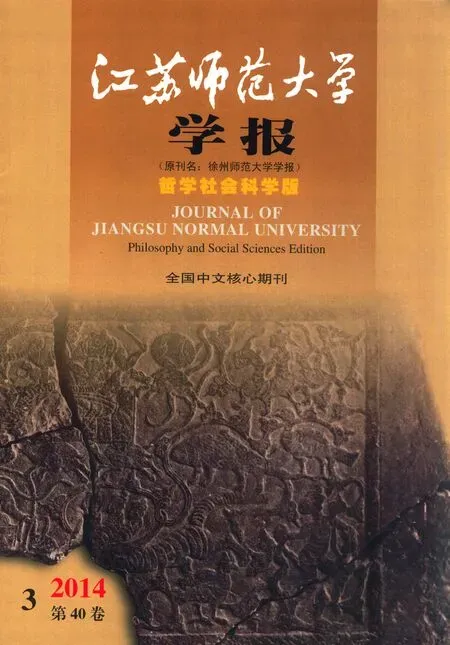权利三论
王炳权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北京 100028)
当代人类社会正处于一个权利彰显的时代,毋庸置疑,当代的权利问题备受关注与尊重。“权利”、“权利意识”、“公民权利”等词语已经成为社会的热点,权利在当代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也越发凸显。在历史上,权利曾是资产阶级追寻民主和自由的武器,以此反抗封建专制的压迫,表达发展商品经济的愿望。如今,权利已经成为现代社会赖以存在的一个实质性要素。如何认识权利、把握权利和发展权利是当代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
一、权利的历史源流
权利作为人类从古至今思想精华的积淀,已经伴随着人类走了很远,这一凝聚人类实践经验、思维成果的范畴,“不能被限定在僵硬的定义中,而是要在它们的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来加以阐明”[1]。“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2]权利作为理论思维的成果和工具,它的形成有一个历史过程,是历史的产物,是思想和文化进程的凝结。
(一)权利的萌芽与孕育
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把儒家的伦理道德作为正当权利和利益的基础,强调对“仁、义、礼”的追求,体现的是一种“义务本位主义”[3]。中国的传统文化因素并没有孕育出现代意义上的权利观念,“中国历史上即便有法律权利的观念存在,也是很‘微弱的’”[4]。现代意义上的“权利”,只有其外壳是中国的,其观念和内核则是西方的,是19世纪末期西学东渐的产物。
西方有学者认为:“直至中世纪结束前夕,任何古代或中世纪的语言里都不曾有过可以准确地译成我们所谓‘权利’的词句。大约在1400年前,这一概念在希伯来语、希腊语、拉丁语、阿拉伯语或中古语里缺乏任何表达方法,更不用说在古英语或晚至19世纪中叶的日语里了。”[5]虽然人们公认在古希腊并没有产生“权利”的概念,“希腊的哲学家不讨论权利问题,他们只关心什么是正当的,什么是正义的,所以希腊人在当时主要考虑从人们相互冲突和重叠的要求之间寻求正当和正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古希腊不仅没有出现权利概念,而且希腊人也没有明显的权利观念”[6]。但古希腊哲学家所讨论的正义问题,却与后来出现的权利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不论是柏拉图“正义的观念建立在城邦的秩序之上”[7],还是亚里士多德“人的最高生活是政治生活,国家的目的就是要创造人的良好生活,实现公共的善”[8],他们关于正当或正义,以及在特定场合可以适用的正义标准或正当行为,“已经触及到了权利问题的症结”[9],对后世权利及其概念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古罗马时期是一个法律技术发达的时代,为后世很多法律模式开创了先河,构成了近现代西方法律体系和法学的历史基础。在罗马法中,没有确定的单独的权利概念和权利分类。“罗马法学家没有表达对特定个人权利的专门词汇,因而也没有表达与这种权利相应的一般义务的恰当词汇。”[10]但罗马人却以法律来支持希腊哲学家所说的凡是正当的事情,“这就在观念上和技术上把问题引到权利概念上来了”[11]。正如马克思所说:“罗马人最先制定了私有财产的权利、抽象权利、私人权利、抽象人格的权利。”[12]在《查士丁尼法典》中,译作“权利”的拉丁字“jus”原来有10种解释,其中有4种接近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权利。这4种最接近的意思是:“一是受法律支持的习惯或道德的权威,例如家长的权威;二是权力,即一种受法律支持的习惯或道德的权力,例如,所有人出卖他所有物的权力;三是自由(权),即一种受法律保护的正当自由,例如一个人在他的土地上建造房屋的自由,即使这座房屋是一种丑陋不堪的小屋并触犯了邻居的审美感;四是法律上的地位,即公民或非公民在法律秩序中的地位与人格。”[13]这4种意思可以说是带有现代意义权利的雏形,为后来权利及其概念的产生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权利的现代生长
现代意义上的权利源于中世纪的“权利之争”[14]。中世纪虽然被很多人认为是“黑暗时代”的代名词,但实际上却孕育着西方的文明和制度。在中世纪,托马斯·阿奎那曾首次解析性地把“jus”理解为“正当要求”,并从自然法理念的角度把人的某些正当要求称之为“天然权利”[15],“低级的人必须按照自然法和神法所建立的秩序,服从地位比他们高的人”,“人与人之间天然不平等,但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16]。他把正义权利观念归结于上帝的意志,所以这样的“天然权利”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权利。
在中世纪中后期,随着城市的发展、商业的复兴和市民阶级的形成,城市居民为保护私有财产、实现城市自治,开始和封建领主进行激烈的斗争[17],人们的个人意识得到了极大成长,他们对于财产权、人身自由等的重大意义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自由和平等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所有权成为集中讨论的话题,“这种讨论直接导致了中世纪晚期权利争论中所出现的主观权利”[18]。这一时期科学技术的发展也起了重要作用。马克思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19]文艺复兴运动,则“促进了对于人的理解和认识,强调了人的尊严和价值,提倡个性的解放和发展,使人们的目光从神转向了人”[20]。宗教改革运动,对人们的思想解放也起到了巨大作用,成为“人类心灵争取自治权的尝试,是对精神领域的绝对权力发起的名副其实的反抗”[21]。
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商品经济的发展,权利观念开始逐渐成为普遍的社会意识。“于是‘jus’作为权利明确地区别于‘jus’作为‘正当’和‘jus’作为‘法律’。”[22]格劳秀斯最先区分了“jus”的三种含义,并把权利看作是人作为理性动物所固有的、即与生俱来的“道德品质”或“资格”[23]。有学者认为,格劳秀斯是现代权利理论的创始人,因为正是从格劳秀斯起,权利开始侵占自然法学说的整个领地[24]。应该说,格劳秀斯论述的自然权利问题已然开始带有一定的现代意义的权利观,但格劳秀斯仍旧没有把权利和诸如正义、道德等因素明确地区分开[25]。与格劳秀斯同时代的霍布斯明确地把权利与法律和义务相区别。霍布斯提出:“自然法的十三条戒律,其中第二条是:当一个人为了和平与自卫的目的认为有必要时,会自愿放弃这种对一切事物的权利,而在对他人的自由权方面满足于相当于自己让他人对自己所具有的自由权利。”[26]“一个人停使对任何事物的权利便是捐弃自己妨碍他人对同一事物享有权益的自由。”[27]霍布斯的权利观以人性论为基础,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他肯定了个人权利先于政治国家而存在,是现代权利传统的奠基人”[28]。
(三)权利的发展
17、18世纪欧洲启蒙时期,“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29]。具有“现代性”特征的权利及其观念是在这个时代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洛克强调:“每一个人对其天然的自由所享有的平等权利,不受制于其他任何人的意志或权威。”[30]在洛克的权利观中,民众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为了捍卫个人权利,民众应该联合起来向侵犯者进行严厉的斗争。正如G·H·萨拜因所指出:“洛克哲学的最大要旨超越了英国同时代的政治解决办法,在美国和法国奠定了政治思想的基础,于18世纪末叶的两次大革命中达到顶点。洛克学说中为了捍卫个人自由、个人同意以及自由获得并享有财产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进行抗争的思想在这两次革命中受到了充分的效益。”[31]卢梭的权利观则强调,自由是绝对的“第一核心要素”,“人类组织文明社会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利。在社会状态中,一切权利都被法律固定下来。”[32]“人民之所以要有首领,乃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自由,而不是为了使自己受奴役,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同时也是全部政治法的基本准则。”[33]
康德把权利和义务划分为道德权利和义务与法律权利和义务,认为“道德权利应属于应然义务,法律权利应属于实然权利”[34]。康德说:“要理解权利的概念,必须要考虑到三个方面的条件,首先,权利只涉及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外在的和实践的关系,因为通过他们的行为,他们可能间接地或直接地彼此影响;其次,权利的概念并不表示一个人的行为对另一个人的愿望或纯粹要求的关系,它只表示他的自由行为与别人行为的自由的关系;最后,在这些有意识行为的相互关系中,权利的概念并不考虑意志行动的内容,不考虑任何人可能决定把此内容作为他的目的。”[35]康德对权利的理解已经明显带有了法律权利的性质,而不再是过去的那种自然权利概念。把法律权利从自然权利中区分出来,对于权利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是权利发展的又一个新的阶段。可以说,“康德才是真正提出现代意义上的权利概念上的人。”[36]
二、唯物史观视野中的权利
马克思主义权利理论实现了从抽象的人到现实的人、从自然人到社会人的转变,对个人权利与社会集体权利的关系作出了科学合理的解答,为我们正确认识权利问题提供了历史唯物主义视角。
(一)权利并非“天赋”
按照“天赋人权”观点,权利是人们与生俱来的,适应任何社会经济结构而不受到限制和制约。这种看似正确的“天赋权利”实际上将客观存在的权利描绘成一种脱离历史的、非社会的东西,实际上,“‘人权’不是天赋的,而是历史地产生的”[37]。
马克思恩格斯对权利的解释,一刻也不能脱离“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38]。整个社会的历史,就是人类自身进行物质资料生产的历史,人的生产活动和社会交往是社会历史发展最深刻的本质。伴随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变强,社会的分工和商品的生产也在不断地扩大,商品交换不断地发展起来,权利及其观念随之产生并发展起来。马克思认为:“平等和自由所要求的生产关系,在古代世界还没有实现,在中世纪也没有实现。古代世界的基础是直接的强制劳动;当时共同体就建立在这种强制劳动的现成基础上;作为中世纪的基础的劳动,本身是一种特权,是尚处在特殊化状态的劳动,而不是生产一般交换价值的劳动。”[39]正是近代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确立了对权利的渴望和追求,促使权利及其观念诞生。现代意义上的权利一旦生成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经济发展的变化不断发生变化的。“无论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还是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出现,本身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一观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而这种历史条件本身又以长期的以往的历史为前提。所以,这样的平等观念说它是什么都行,就不能说它是永恒的真理。”[40]
可见,权利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为一定时期人类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制约,“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41]一旦“所谓的权利只要脱离了作为他们的基础的经验的现实,就可以像翻手套一样地任意翻弄。”[42]
(二)权利具有阶级性
权利反映着一定阶级的利益,是为特定阶级服务的。在阶级社会中,对立的阶级因为所处的经济地位不同,彼此享有的权利也会有实质的不同。人们所享有的权利表面上看似平等,其实是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是生产资料的拥有者,在社会生产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据此就可以无偿占有剩余劳动,而直接从事生产劳动的无产阶级,则由于不占有生产资料从而丧失了支配自己劳动产品的权利。恰如恩格斯所指出:“劳动契约据说是由双方自愿缔结的。而只要法律在字面上规定双方平等,这个契约就算是自愿缔结。至于不同的阶级地位给予一方的权力,以及这一权力加于另一方的压迫,即双方实际的经济地位——这是与法律毫不相干的。”[43]
启蒙时期的权利学说是为新兴资产阶级服务的,在阶级利益的引导下,资产阶级权利学说鼓吹“天赋人权”,倡导对自由平等的追求,个人私有财产、私有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体现了资产阶级要求打破封建专制束缚,发展商品经济的愿望。马克思主义的权利观则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为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服务的。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要实现更广泛的人类的自由权利,必须反对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消灭阶级,不断提高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逐渐摆脱人对物的依赖性,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虽然强调权利的阶级性,但也承认人的权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不同阶级的共同权益,如生存权、和平权、环境保护权等等,承认人类具有共同权利的一面。
(三)权利具有社会性
人的发展离不开社会,人是社会的动物,人的权利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是在人类的社会实践中产生的,同样具有社会性。权利的内容由社会关系规定,不同的社会关系孕育着不同的权利内容。“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44]经济结构是一段时期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决定着一定时期的社会性质、社会关系,“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45]在不同的时期,由于社会关系不同,权利的内容也是不同的。
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是权利实现的社会基础和根源。有怎样的社会条件,就有怎样的权利。“现代国家承认人权和古代国家承认奴隶制具有同样的意义。就是说,正如古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奴隶制一样,现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市民社会以及市民社会中的人,即仅仅通过私人利益和无意识的自然必然性这一纽带同别人发生联系的独立的人,即为挣钱而干活的奴隶,自己的利己需要和别人的利己需要的奴隶。”[46]马克思在这里告诉我们,只要人所生活的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压迫,权利就不可能不带有阶级的烙印。“必须使既得的生产力和现存的社会关系不再能够继续并存”[47],只有彻底改变不平等的制度和生产关系,权利才能得到真正的实现。
(四)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
恩格斯强调:“如果说在野蛮人中间,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不大能够区别权利和义务,那么文明时代却使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和对立连最愚蠢的人都能看得出来,因为它几乎把一切权利赋予一个阶级,另一方面却几乎把一切义务推给另一个阶级。”[48]这种由于阶级压迫和阶级对立产生的不平等性,“对一些人是好事,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49]马克思恩格斯从根本上对权利与义务相分割的思想进行批判,强调“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50]。离开义务的权利,只能是阶级特权,因此,只有权利与义务相统一才能够构建科学的权利理论。恩格斯对《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进行了批评,对资产阶级只讲平等的权利进行了修改,他说:“我建议把‘为了所有人的平等权利’改成‘为了所有人的平等权利和平等义务’等等。平等义务,对我们来说,是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平等权利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补充,而且使平等权利失去道地资产阶级的含义。”[51]
马克思恩格斯权利义务观的真意是,在权利的享有资格和义务承担责任上,每个人的资格应该都是平等的。恩格斯强调:“无产阶级所提出的平等要求有双重意义。或者它是对明显的社会不平等,对富人和穷人之间、主人和奴隶之间、骄奢淫逸者和饥饿者之间的对立的自发反应——特别是在初期,例如在农民战争中,情况就是这样;它作为这种自发反应,只是革命本能的表现,它在这里,而且仅仅在这里找到自己被提出的理由。或者它是从对资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反应中产生的,它从这种平等要求中吸取了或多或少正当的、可以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成了用资本家本身的主张发动工人起来反对资本家的鼓动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它是和资产阶级平等本身共存亡的。在上述两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52]这就是说,实现权利与义务的不可分离,从根本上取决于阶级内容的消灭,而不仅仅要求所谓权利与义务的对等。
(五)民主是实现权利的手段
民主从本质说是一种阶级政治权利,是承认平等权利的统治阶级的共同统治。正如列宁所指出:“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因此,它同任何国家一样,也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53]马克思曾断言:“民主制是一切形式的国家制度的已经解开的谜。”[54]民主制与其他形式的国家制度相比其最大的区别是突出了鲜明的“人民主权”特色。“民主制从人出发,把国家变成客体化的人。”[55]“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56]民主制是对人民意志的发挥和保障,而不是相反。
民主制是无产阶级寻求解放的必然选择,它应成为“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把劳动从垄断着劳动者自己所创造的或是自然所赐予的劳动资料的那批人僭取的权力(奴役)下解放出来的政治形式。”[57]无产阶级“如果不立即利用民主作为手段实行进一步的、直接向私有制发起进攻和保障无产阶级生存的各种措施,那么,这种民主对于无产阶级就毫无用处。”[58]民主制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就是使人民真正成为事实上和法律上的国家与社会的主人。
三、权利的历史价值
“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59]人的解放的目的在于使作为整体的人类和个体的人摆脱一切外在异化关系的束缚,使其成为自身的主宰,成为自由的人。权利的争取、确认和维护就是人类不断解放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下,权利始终拥有巨大的价值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一)解放的号角
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60]“人的依赖关系”是人存在的原初状态,是人与人的初始关系。这种关系尚未孕育出任何“权利”的观念,“氏族制度的伟大,但同时也是它的局限,就在于这里没有统治和奴役存在的余地。在氏族制度内部,还没有权利和义务的分别;参与公共事务,实行血族复仇或为此接受赎罪,究竟是权利还是义务这种问题,对印第安人来说是不存在的;在印第安人看来,这种问题正如吃饭、睡觉、打猎究竟是权利还是义务的问题一样荒谬。”[61]
随着私有制的产生,“物的依赖关系”被逐渐强化。“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对一些人是好事,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62],“奴隶同他的劳动的客观条件没有任何关系;而劳动本身,无论是奴隶形式的,还是农奴形式的,都被作为生产的无机条件与其他自然物列为一类,即与牲畜并列,或者是土地的附属物。”[63]特权始终是奴隶主、地主、贵族的“奢侈品”,以被压迫阶级对全社会义务的担当为前提。人与人不平等关系的发展催生了被压迫阶级对平等权的渴望,权利意识越发浓烈。
权利的萌芽与发展,伴随着人们精神的觉醒,使越来越多的民众不满于特权的压迫。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争取权利、实现人类解放,越来越成为人们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从文艺复兴时期追寻对人的尊重,到启蒙时期宣扬“人权不可侵犯”,人们开始普遍接受“天赋人权”,认为人的权利是先天的、与生俱来的。争取权利斗争的资产阶级革命,首先在英国爆发,继而蔓延到美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宣称“所有的自由臣民都有自由地经营其行业的继承权”[64]。“就人间而言,人民是所有公正权利的来源”[65],“下议院议员是由人民选举出来的,代表人民,拥有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力”[66]。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宣称“个人幸福是政治的最高目的”[67],反对英国人将繁重的税收负担转嫁到美利坚。在法国大革命中,国王、贵族等这些人民的压迫者统统被送上了断头台。正是对权利的追求,唤起了人们精神的觉醒,从而起来反抗封建剥削和压迫,促使了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实现了人类历史的进步。
(二)权益的保障
权利是一种观念,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文化,一种现象[68]。当人们意识到有必要争取自身权益、维护自身利益时,首先吹响的是反抗封建特权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号角。一旦革命取得成功,人们所追求的权利便需要以法的形式确定下来。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成功的重要标志是,权利以制度的形式被规定下来。
1689年英国颁布的《权利法案》以法律的形式限制了王权,扩大了臣民权利,为反对王权对人民权利的侵犯提供了基本的制度保障。被马克思称为“第一个人权宣言”的美国《独立宣言》宣称:“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69]法国的《人权宣言》规定:“人生而平等,享有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的权利。自由包括言论、著述和出版等自由,其行使以保障社会其他成员能享有同样的权利为限度。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非因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并经公共和事先的赔偿不受剥夺。主权属于国民。实行分权原则,任何团体或个人不得行使主权所未明白授予的权力。法律为公共意志的表现,公民均有权亲自通过其代表参与制定。”[70]彰显权利、实现权利、保障权利逐渐成为制度社会的核心要素。
对权利的呼唤逐渐向着制度化方向迈进。从1679年英国的《人身保护法》和1689年的《权利法案》、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1789年法国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等等,都明确提出了“人的权利”,初步建成了一套保障权利的制度。伴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权利的实现也在逐步推广和扩大,保障权利的制度开始得到逐渐完善,其地域亦从欧美走向世界。从18世纪到19世纪的权利运动限于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20世纪后,世界联系的紧密性大大加强,保障权利成为世界性的议题,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摆脱殖民统治而走上国际舞台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开始追寻民族独立与自由。大大小小的法律机构先后成立,一部部法律相继问世,权利保障制度变得越来越完善。
对于权利制度化的作用,英国首相老威廉·皮特在一次演讲中表达得淋漓尽致,他讲道:“即使最穷的人,在他的寒舍中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风可以吹进这间屋子,雨也可以打进这间房子,房子甚至在风雨中飘摇战栗,但是国王不能踏进这间房子,国王的千军万马不能随意踏进这间门槛早已磨损的破房子”[71]。“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通俗表达,形象地说明在权利制度下,民众的基本权利得以维护,权利制度化从而成为维护人类权利的有效手段。
(三)法律的“要义”
梁启超曾说:“国家,譬如树也;权利思想,譬如根也;……为政治家者,以勿摧压权利为第一要义;为教育家者,以养成权利思想为第一要义;为私人者,无论士焉、农焉、商焉、男焉、女焉,各自坚持权利思想为第一要义。”[72]法律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手段。保障权利的实行,不仅是法律的重要原则,也是法律的“第一要义”。
法律从其诞生开始,就并不总是维护和保障人的权利的,“法跋涉的道路上曾几度流血,到处可见惨遭蹂躏的权利”[73]。如何使法律在为政治服务的过程中,体现社会的道德要求呢?只有通过维护和保障权利来实现,只有通过法律对权利的张扬,对权利的维护和实现,才能实现法律的价值。正如美国学者德沃金在《认真对待权利》的中文版序言中指出:“法律和政治道德之间的这种关系的确立和保持的手段是:通过法律来实施基本的和宪法的‘权利’。这些权利使法律本身更为道德,因为它可以防止政府和政府官员将制定、实施和运用法律于自私或不正当的目的。”[74]可以说,“法律制度离开了对权利的维护,就是失去任何存在的根据。”[75]
权利对法律的价值,除了对法律的制约使其不成为“恶法”外,还表现在权利增长了人们的法治观念和法治精神,推动了社会的法治进程。“权利是法的内核,没有对权利的要求,也产生不了对法的需求和对法律的渴望,权利意识与法治观念的形成是密切联系的,权利意识的增强导致法治观念的增长,反之,法治观念的增长,也必将推动人们权利意识的扩张。”[76]“一个社会一旦丧失了权利意识,法治建设就会失去目标和方向。”[77]只有民众树立了权利观念、权利意识,才能够树立起对法律的信仰,才能重视法律,并用法律来为维护自身的权益。
(四)和谐的根基
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调节,是社会和谐的基本体现和根本动力。权利的张扬与制度化保障是社会和谐的重要保障。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们的交往关系尚未充分展开,尚未形成全面的内在利益需求,“劳动生产力处于低级发展阶段,与此相应,人们在物质生活生产过程内部的关系,即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很狭隘的”[78]。这个时期权利可能产生或得到一定发展,但绝不会形成十分强烈的法权要求与感受。“一种真正普遍性的权利要求只有在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才能被深刻体验并明确提出”[79]。只有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超越了“人的依赖关系”这一阶段达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80]这一阶段时,权利才能得以充分实现。
人类社会正处于权利彰显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讲,权利是现代社会和谐的基石。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的出现,社会利益开始分化,出现了依经济地位而划分的不同利益集团,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关系开始显现,这为个体权利意识的产生创造了条件。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造就了个人相对于群体的独立地位以及相应的独立意识,“个体的利益体验与权利观念由此蓬勃而发”[81]。市场经济越发展,形成的社会交往关系也越发达。个体与社会越来越密切的联系使得以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为实质而构成的权利现象势必变得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和经常性。因而,“现代人在这种愈益频繁的交往关系中越来越需要认清自己的位置,明确自己的利益,确立自己的牢固基点,否则将很难开展生活与行为。怎样对自己与他人、自身与社会之间经常性利害关系定位,成为现实个体不得不时时考虑的一个问题。”[82]
在市场经济时代,对“物的依赖性”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资源的稀缺[83]。从这个意义讲,每个人的利益都会客观地与他人利益、社会利益产生不一致性。为了防止人与人之间因不同利益而产生的矛盾和冲突,就必须建立一种权利的协调机制,对人的权利作出正确、合理的规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新的法权权利不断催生,权利文化、权利观念、公民自主平等意识、利益意识不断被强化,权利体系不断向前发展,也不断地推动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得到调整与合理化”[84],进而改善着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公民与公共权力的关系,不断使社会趋向和谐。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页。
[2][40][5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6、113、112 页。
[3][4]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吴玉章译注,上海三联书店,2008 年版,第67、92 页。
[5]米尔恩:《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人权哲学》,夏勇、张志铭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
[6]罗·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沈宗灵、董世忠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4页。
[7]柏拉图:《理想国》,吴献书译,世界图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33页。
[8]亚里士多德:《尼科马亥伦理学》,刘国明译,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年版,第93页。
[9]L·W·萨姆纳:《权利的道德基础》,李茂森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5页。
[10]奥斯丁:《法理学或实在法哲学讲义》,参见夏勇:《人权概念起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6页。
[11]张康之、张乾有:《探寻权利观念发生的历史踪迹》,《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10期。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82页。
[13][22]张文显:《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理论、方法和前沿》,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71、272页。
[14][18]何志鹏:《权利基本理论:反思与构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7、7 页。
[15]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16页。
[16]托马斯·阿奎那:《阿奎那政治著作选》,马清槐译,商务印书馆,1963 年版,第101、146 页。
[17][21][25]基佐:《欧洲文明史》,程洪速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 年版,第116-132、218、219 页。
[19][60][6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338、52、139 页。
[20]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4页。
[23]H·格劳秀斯:《战争与和平法》,引自《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43页。
[24]黄森、沈宗灵:《西方人权学说》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
[26][27]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译,商务印书馆,1985 年版,第98、99 页。
[28][36]公丕祥:《权利现象的逻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8、42 页。
[29][41][45][50][5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523、435、435、227、197 页。
[30]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霍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4页。
[31]G·H·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册,刘山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04页。
[32]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9页。
[33]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常山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32页。
[34][35]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2、39-41页。
[37]《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2页。
[38][46][47][58][5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525、312、655、685、46 页。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0页。
[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页。
[43][48][49][51][61][6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 86、197、197、411、178、196 页。
[44]《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9页。
[53]《列宁专题文集 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0页。
[54][55][5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第39、40、40 页。
[64][67]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7版,吴象婴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24、519页。
[65]齐世荣:《精粹世界史:英美法资产阶级革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49页。
[66][70]杰里·赫伯特:《新全球史》下,魏凤莲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834、835 页。
[68]李海青:《公民、权利与正义:政治哲学基本范畴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版,第66页。
[69]何勤华、贺卫方:《西方法律史》,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43页。
[71]赫·乔·韦尔斯:《世界史纲》第15版,吴文藻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79页。
[72]转引自沈家本:《删除律例内重法析》,载《寄文簃存》上,(台湾)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73]鲁道夫·冯·耶林、梁慧星:《为权利而斗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
[74]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页。
[75][77]郑贤君:《基本权利研究》,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538、299 页。
[76]刘佳:《中国法治化的现实基础》,《中外法学》,1999年第1期。
[7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6页。
[79]高志明:《法律与权利》,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年版,第157页。
[8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页。
[81][84]夏勇:《走向权利时代:中国公民权利发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43、376页。
[82][83]王人博、程燎原:《权利及其救济》,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第93、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