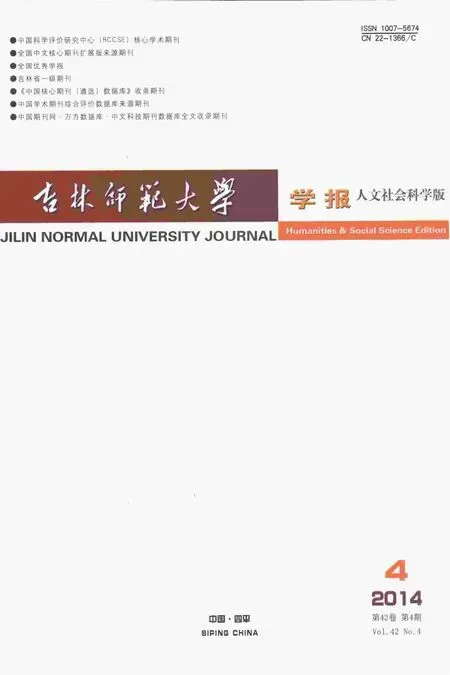经济发展与战国秦汉之际法制建设的互动
朱红林
(吉林大学 古籍研究所,吉林 长春 130012)
经济发展与战国秦汉之际法制建设的互动
朱红林
(吉林大学 古籍研究所,吉林 长春 130012)
战国秦汉之际是中国古代国家结构转型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也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战国时期的列国及秦汉国家在法治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经济方面的立法尤为关键。这方面的成就不仅为传世文献所记载,在出土的秦汉法律文献中也有丰富的史料,农业、手工业、商业以及财政管理方面的法规都有所建树,表现了战国秦汉之际国家较为成熟的经济管理职能。
秦汉律;简牍;经济;管理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过来又影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这条理论在战国秦汉之际的简牍资料中再一次被证明是正确的。战国秦汉之际是中国古代经济政治发展的一个转型期,国家授田制度取代了西周春秋以来的井田制度,并且不断得到巩固和完善,“工商食官”格局彻底被打破,商人阶层开始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阶层登上了历史舞台,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经济上的统一加速了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建设,反过来,政治上中央集权的巩固也加速了经济上的中央集权,具体表现就是一系列经济法规的制定和颁布。
一
农业是古代中国的立国之本,国家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尤为重视,立法方面也加快了步伐。银雀山汉简有《田法》[2],睡虎地秦简有《田律》、《仓律》、《户律》、《傅律》[3],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也有《田律》、《户律》、《傅律》等等[4],这些法律基本上一脉相承,从土地分配、农田管理、农作物的收获与储存,到劳动力管理、租税征收、粮食加工等,进行规范指导。睡虎地秦简及里耶秦简的记载表明,战国末期秦国各级政府直接经营着大量的农田,简牍与玺印中亦称之为“公田”,主管官吏即以此命名,有“左公田”、“右公田”之称,还有大量的“田官”。里耶秦简8-63:“廿六年三月壬午朔癸卯,左公田丁敢言之:佐州里烦故为公田吏,徙属。”陈伟等曰:“左公田,管理公田的官吏。《秦汉魏晋南北朝官印征存》13为‘右公田印’。”[5]在公田上劳作的人群,主要是刑徒和奴隶。法律规定,根据劳作者的劳动量在农作季节适当增加他们的口粮,到农闲季节则取消这一部分口粮。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仓律》:“隶臣田者,以二月月稟二石半石,到九月尽而止其半石。”
劳动者根据身高或年龄分别编入全劳动力和半劳动力簿籍,统计的时间与户籍统计时间相吻合,法律上称之为傅籍制度,国家为此制定了专门的法律——《傅律》来进行规范。睡虎地秦简《秦律杂抄·傅律》曰:“匿敖童,及占(癃)不审,典、老赎耐。百姓不当老,至老时不用请,敢为酢(诈)伪者,赀二甲;典、老弗告,赀各一甲;伍人,户一盾,皆(迁)之。”这夅虎地秦简中仅存的一条《傅律》,它说的主要是关于傅籍制度中弄虚作假的惩罚措施。关于秦代傅籍制度具体操作的记载,可从《秦律十八种·仓律》中得到一些内容。《仓律》说:“小隶臣妾以八月傅为大隶臣妾,以十月益食。”“隶臣、城旦高不盈六尺五寸,隶妾、舂高不盈六尺二寸,皆为小;高五尺二寸,皆作之。”这就是说男刑徒身高在六尺五寸、女刑徒身高在六尺二寸以上,都属于成人,服全役,属于“大”;五尺二寸以下,完全免除徭役,属于“小”;而身高在五尺二寸以上、六尺二寸以下,服半役,称为“小可使者”。秦简整理小组注:“大,成年,如《管子·海王》和居延汉简均称成年男女为大男、大女。”[3]33刑徒的傅籍年龄当与庶人相似,庶人傅籍之后称为“士伍”。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内史杂》:“除佐必当壮以上,毋除士五(伍)新傅。”新傅籍的士伍经验不足,因此选任官吏时这类人被排除在外。简牍中关于汉代傅籍的记载则要丰富得多。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傅律》的记载表明,汉初傅籍制度是有等级性的,不同爵位者的傅籍年龄与免老年龄是不一样的,爵位越高,则傅籍年龄越高,免老年龄越低;爵位越低,则傅籍年龄越低,免老年龄则越高[6]。
国营农业生产严格按照计划进行。国家有专门的农业技术人员,他们负责总结研究各地农业生产发展状况,然后把这些技术以口头或以书面形式传达给基层劳动者。睡虎地秦简《仓律》:“种:稻、麻亩用二斗大半斗,禾、麦亩一斗,黍、荅亩大半斗,叔(菽)亩半斗。利田畴,其有不尽此数者,可殹(也)。其有本者,称议种之。”这是一条关于农田播种量的规定,规定了不同农作物的每亩播种数量。同时,还补充说,可以根据农田的实际情况,适当地调整播种量。这属农业技术法规的范畴。我们相信,秦汉简牍中一定还存在不少类似的律令,只是尚未见到而已。《周礼》中提到一个国家机构叫“司稼”,它的职能就是负责调查研究全国各地农业生产的发展状况,并把成熟的经验推广到各地[7]。尽管《周礼》一书的成书年代存在争议,但司稼的这项职能在战国时期的国家机构中无疑是存在的,不过它的实际存在形式因国家情况不同而名称各异罢了。
传世文献中的《月令》类记载就属于这方面的内容。《吕氏春秋·季冬纪·季冬》说:“天子乃与卿大夫饬国典,论时令,以待来岁之宜。”《孟春》篇又说:“王布农事:命田舍东郊,皆修封疆,审端径术,善相丘陵阪险原隰,土地所宜,五谷所殖,以教道民,必躬亲之。田事既饬,先定准直,农乃不惑。”《孟春》篇王布农事的各项措施,就是《季冬》篇天子与卿大夫所讨论的国典时令的具体内容。国家有关部门在对来年农业生产的安排讨论明白之后,就以法律的形式颁布到地方去。睡虎地秦简《仓律》中关于播种的规定也属于这方面的内容。学者们现有的研究已经表明,《月令》类文献是战国秦汉法律的来源之一[8]。值得注意的是,《周礼》一书中“司稼”的职责就是搜集整理和研究各地的农业生产技术,然后以法令的形式把这些生产技术写在简牍或木方之上,悬挂到乡村的村门,供农民们学习。《周礼·地官·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种,周知其名与其所宜地,以为法而县于邑闾。”从出土简牍的情况来看,《周礼》的这项记载是可信的。由此而言,在中国古代,官方对农业生产技术的研究和传播确实值得研究。
注重农时和保护民力是战国秦汉之际农业生产立法关注的又一主要方面。由于科学技术的局限,农业生产靠天吃饭,所以顺应天时就显得非常必要,《吕氏春秋》因而提出了“得时之稼兴,失时之稼约”的论断。农时的概念范围很广,它既包括顺应农作物生长规律的思想,也包括保护农业劳动力的思想,二者是密不可分的。国家只有拥有充足的农业劳动力,才能真正顺应农作物生长的规律,到什么时候干什么事。战国秦汉之际的国家立法对此非常注意,在有关徭役的专门立法《徭律》中特别强调了这一点。秦法规定,除了按制度正常服役的劳动力之外,国家一般不允许地方官府随意征发百姓兴土动工,特殊情况要按程序向上级请示并得到批准才行。睡虎地秦简《徭律》曰:“县毋敢擅坏更公舍官府及廷,其有欲坏更殹(也),必(谳)之。”遇到紧急情况,不得已而征发百姓,也要严格遵守先富后贫、能省则省的思想,用最少的人最大程度地办事。滥用民力的官员将受到法律的严惩。里耶简[16]5正说“田时殹(也),不欲兴黔首”,又说“[兴黔首]可省少弗省少而多兴者,辄劾移县,[县]亟以律令具论,当坐者言名史泰守府”。岳麓书院藏秦简《徭律》也说:“田时先行富有贤人,以闲时行贫者,皆月券书其行月及所为日数,而署其都发及县请(情)。”[9]即使是由于债务原因而为官府劳动的人,到了农忙季节,官府也会给他放一定时间的假期,以便回家完成必要的农活。睡虎地秦简《司空律》:“居赀赎责(债)者归田农,种时、治苗时各二旬。”传世文献中的记载一向使得我们对于秦法望而生畏,觉得它只能以“严酷”二字来概括,而战国秦汉简牍的记载却令我们耳目一新,感觉到对于秦法和秦朝短时间灭亡的认识有必要重新思考[10]。
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畜牧业发展在战国秦汉之际同样受到法律的关注。农业生产有《田律》,畜牧业管理则有《厩苑律》,与此同时一系列相关的令、课等辅助法律形式也随之出现,如《牛羊课》、《田令》等等。律的基础性、稳定性强,令、课则更强调特定的针对性,是律的有效补充。
简牍的记载表明,战国秦汉之际的畜牧业管理与农业管理机构一样,存在着中央、县道、乡、里四级体制,国家为此制定了严格的考课制度,各级政府都有专门的畜牧业饲养机构,牲畜饲养、繁育和使用受到严格的管理[11]。牲畜数量的增减是定期考核的内容之一。睡虎地秦简《厩苑律》:“今课县、都官公服牛各一课,卒岁,十牛以上而三分一死;不【盈】十牛以下,及受服牛者卒岁死牛三以上,吏主者、徒食牛者及令、丞皆有罪。”《秦律杂抄·牛羊课》:“牛大牝十,其六毋(无)子,赀啬夫、佐各一盾。羊牝十,其四毋(无)子,赀啬夫、佐各一盾。”官营畜牧业饲养着大量的马牛,马牛繁衍数量的增减是考核各级饲养机构的重要指标。一旦考核成绩不理想,不但畜牧业主管官员难逃法律的问责,就是县令、乡长这类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也难辞其咎[11]。
牧场的设置受到保护,马牛饲料的征收也以立法的形式来确保。银雀山汉简《田法》、秦简和汉简的《田律》中都提到“刍稾税”,成为与“谷租”并列的主要农业税收种类之一。银雀山汉简《田法》:“稾,民得用其什一;刍,人一斗;皆藏于民。”这就是说,农民要将十分之九的禾稾交给国家。这是战国时期齐国的情况。睡虎地秦简《田律》:“入刍稾,相输度,可殹(也)。”“相输度”指的就是刍与稾之间可以互相折合[3]21。这是战国末期秦国的制度。这一制度在随后的汉律中得到了继承。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田律》:“县各度一岁用刍稾,足其县用,其余令顷入五十五钱以当刍稾。刍一石当十五钱,稾一石当五钱。”法律中规定,在国库储存的刍稾数量足够一年的用度时,允许以钱折合缴纳,这反映了商品经济得到一定发展时,秦汉政府处理此类问题的灵活性。
二
商品经济在战国秦汉之际得到长足的发展,相应的国家立法也随之建立。文献方面以《周礼》中的记载最为全面。《周礼》中有关市场管理的部门称为司市,下属质人、廛人、胥师、贾师、司虣、司稽、胥、肆长、泉府等机构,职能涉及市场的组织管理、商品质量及价格、商业券书、商业区划、商业税收、商品流通、市场治安诸多方面。
银雀山汉简《市法》反映了战国时期齐国的市场管理制度,睡虎地秦简《关市律》记载了战国末期秦的市场管理制度。其中不但包含有对商人的组织管理,还包含了对货币的管理。张家山汉简《关市律》反映了西汉初期的市场管理制度,与睡虎地秦简《关市律》有明显的前后继承关系。这三种出土文献中的市场法规,虽然没有《周礼》的记载全面,但其中共同点还是很明显的。一是,对于市场中商人的组织管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记载都强调了商人的组织形式与农民组织形式是一样的,都是按照什伍组织来进行管理的[12]。睡虎地秦简《金布律》提到市场管理中有“列伍长”,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的《关市律》也提到有“列长、伍人”,就是一个证据。二是,对商品质量及价格的监督。货真价实是对商品质量价格的基本要求。《周礼·地官·肆长》曰:“陈其货贿,名相近者相远也,实相近者相尔也,而平正之。”郑玄注曰:“俱是物也,使恶者远善,善自相近。”这就是说商品陈列以类相从,以质相聚,体现了官方商业管理指导中的诚信思想。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关市律》则明确打击市场上的商业欺诈行为:“诸(诈)紿人以有取,及有贩卖贸买而(诈)紿人,皆坐臧(赃)与盗同法,罪耐以下有(又)(迁)之。有能捕若诇吏,吏捕得一人,为除戍二岁;欲除它人者,许之。”官府对市场市场商品的价格进行宏观的管理。《周礼》中有“贾师”,职能之一就是负责监督市场上商品的价格波动。睡虎地秦简《金布律》要求商品买卖明码标价:“有买(卖)及买殹(也),各婴其贾(价)。小物不能各一钱者,毋婴。”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金布律》说偿还官府债务,或者官府赏赐,“各以其二千石官治所县十月金平贾(价)予钱”,也说明当时存在着商品价格由官方控制的制度。三是,市场中商业税的征收。从战国以来,商业的迅速发展,使得商业税收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周礼·天官·大宰》所列的国家九大财政收入来源,“七曰关市之赋”。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关市律》提出了明确的征收措施:“市贩匿不自占租,坐所匿租臧(赃)为盗,没入其所贩卖及贾钱县官,夺之列。列长、伍人弗告,罚金各一斤。啬夫、吏主者弗得,罚金各二两。”
战国秦汉之际手工业的立法也发展很快。睡虎地秦简中的《工律》、《工人程》、《均工》等等,都是关于官营手工业的立法。计划经济是官营手工业的标志之一。《礼记·月令》和《吕氏春秋·孟冬纪》都记载了类似的官营手工业基本的管理原则:“是月也,命工师效功,陈祭器,案度程,毋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必功致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睡虎地秦简《秦律杂抄》也说:“非岁红(功)及毋(无)命书,敢为它器,工师及丞赀各二甲。县工新献,殿,赀啬夫一甲、县啬夫、丞、吏、曹长各一盾。城旦为工殿者,治(笞)人百。”“岁功”就是手工业生产部门的年度生产计划,严格控制生产计划之外的产品。
官营手工业的工人要经过一定的技术培训,方能进入生产岗位。睡虎地秦简《均工律》:“新工初工事,一岁半红(功),其后岁赋红(功)与故等。工师善教之,故工一岁而成,新工二岁而成。能先期成学者谒上,上且有以赏之。盈期不成学者,籍书而上内史。”工人工作量的考核是衡量工人业绩及口粮发放的必要依据。秦简《工人程》:“隶臣、下吏、城旦与工从事者冬作,为矢程,赋之三日而当夏二日。”“冗隶妾二人当工一人,更隶妾四人当工【一】人,小隶臣妾可使者五人当工一人。”“隶妾及女子用箴(针)为缗绣它物,女子一人当男子一人。”“矢程”就是工作量的标准。官营手工业队伍中有服役的平民,也有大量的刑徒。
三
战国秦汉之际,金属货币被以立法的形式逐渐确立了它在经济活动中的优势地位。从战国时期开始,不论是传世文献,还是出土简牍,都表明当时的经济活动中货币种类逐渐集中到铜钱和黄金身上。秦律的规定更让我们看到了秦国政府处理经济问题的智慧。
睡虎地秦简《金布律》一方面规定,实物货币“布”可与铜钱、黄金以一定的比率相互兑换,并行流通。另一方面又规定,只有符合质地和尺寸标准的“布”才能被国家认可,而铜钱和黄金则是无条件地流通。这是因为作为实物货币的“布”私人可以制作,而铜钱和黄金,只有国家才享有铸币权。秦简《法律答问》中关于逮捕盗铸者的记载,清楚无误地表明了这一点。这样一来,就出现一个问题,使用布币的风险大大增加,一旦从买方手中接收的布币不被国家所认可,卖方就会损失惨重,而作为铜钱和黄金则不存在这一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还有谁会喜欢布币呢?《韩非子》一书的记载表明,即使是给农户打短工的雇工,如果知道主人要付给他铜钱作为报酬,他就会加倍卖力地工作,而主人为了使雇工尽心竭力给自己干活,也想尽办法“调布而易钱”[13]。由此可见《金布律》的实际社会效果。所以秦始皇统一货币制度的时候,宣布黄金为上币,铜钱为下币,其他龟贝珠玉皆不为币,那已经是水到渠成的事了,劳干先生在他的研究中也已经指出了这一点[14]。马克思说:“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15]秦始皇统一货币,也是按照经济发展规律行事的。
目前的问题是,睡虎地秦简中有《金布律》而没有《钱律》,而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却出现了专门的《钱律》。尽管《二年律令·钱律》中的内容部分地见于睡虎地秦简《金布律》,但我们不能据此断定《钱律》就是直到汉初才出现的。也许在睡虎地秦简《金布律》之后的秦代某个时期,《钱律》就已经出现了,也不是不可能的。一切还有待于新材料的出现和研究的深入。不过《钱律》是从《金布律》中分离出来的。它们之间的衍生关系总是没错的[16]。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钱律》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使我们认识到了原来在睡虎地秦简《金布律》中的“行钱布”是“行钱、行布”的省称,属于专有名词,“行”为法定实施之意。《钱律》把达到一定标准的铜钱和黄金称之为“行钱”、“行金”。而居延汉简中有关“不行钱”的记载,也进一步印证了这一认识。有的学者不同意这一看法,认为“行钱”是指质量不好的钱,并举出走马楼三国吴简中有关“行钱”、“具钱”的区别以为佐证[17]。实际上走马楼吴简中的例子并不足以否定我们的观点。我们说得很明确,“行钱”是达到国家法定流通标准的钱,并不是说“行钱”一定就是质量品相优良的铜钱。也就是说,行钱也可能存在着各种程度的品相和质量问题,但这些问题在法律允许流通的容忍范围之内。而走马楼吴简中“具钱”指的是品相质地优良的足额货币,相比而言,“行钱”只是面值仍在,而实际存在不同程度破损的钱,属于马克思所说的“于是金属重量的货币名称就和金属的一般重量名称在历史过程中脱离了”的那种情况,但这种钱仍然得到国家的认可[18]。
另一方面,战国秦汉之际货币的广泛流通,在司法领域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经济处罚开始大大增加。睡虎地秦简中凡类似于今天行政处罚的判罚,多以“赀甲盾”来处理。学术界曾对秦简中的赀甲盾是缴纳实物还是缴纳铜钱有过争论[19],实际上在赀甲盾这项法律颁布的早期,很可能是缴纳甲盾等实物,但从秦简的其他条文来看,很显然在睡虎地秦简墓主人的时代,这种处罚已经缴纳金属货币铜钱了,只是在法律文字上还没改过来而已。里耶秦简中赀甲盾的记载虽仍有出现,但更多地明确记载了“赀钱”的处罚,应该就是立法者根据现实对法律条文修改之后的结果。
秦汉简的记载表明,铜钱的使用在战国秦汉之际非常广泛,国家收入和支出的相当一部分已经都在使用货币。《田律》有关征收刍稾税的规定中说,在仓库中的刍稾足够政府马牛一年的用度时,后缴纳者就要以铜钱折合缴纳,并且给出了明显有利于官府的价格。县道地方政府库存的金钱数额要定期向上级财政部门汇报。百姓的财富也都喜欢以铜钱的形式来储存。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中记录了多例有关盗窃的案例,案发赃款数额成百上千,乃至有上万者,里耶秦简有关债务文书的记载也是如此。货币经济的迅速发展,也影响到了官吏执法的思想。《法律答问》中提到有一官吏本来应该处罚罪犯缴纳一盾,并附加五千钱的罚款,实际却只罚了五千钱了事,结果他因此而犯了“失刑罪”,即执法不当的罪名[3]104。学者们也因此而联想到一盾与五千钱的关系,有的甚至认为一盾的价格就是五千钱。然而岳麓书院藏秦简的资料表明,一盾的价格仅仅三百八十四钱。这就是说,那位执法官吏的错误是因为主刑的处罚金额相对于附加刑五千钱来说微不足道,因而不屑一顾,忽略不计了[20]。
四
战国秦汉之际经济的迅速发展,国家财政的收入也成倍地增加,与之相应的经济立法也随之产生,一项是《金布律》,一项是《效律》。《金布律》是关于财务收入和支出的法律,《效律》则是经济审计的法律。这两项法律对当时的财政管理影响巨大。
据《晋书·刑法志》的记载,秦汉时期的《金布律》有两项内容,一是“毁伤亡失县官财物”,另一是“罚赎入责以呈黄金为价”,前者是关于公物赔偿的法律,后者是关于货币流通的法律。这两项法律在睡虎地秦简《金布律》和张家山汉简《金布律》中都保留着。由此我们认为,这两项内容可能是《金布律》的主要内容。不同的是,睡虎地秦简《金布律》中有关货币的一部分内容在汉初已经分离出来,变成了《钱律》。
除此而外,睡虎地秦简《金布律》和张家山汉简《金布律》还有一项共同的内容,就是记录了地方政府各级部门每年定期处理公家报废物资的规定。就战国秦汉时期全国范围而言,这可是一笔不小的财政收入。《周礼》有一机构称为“职币(敝)”,其职责就是处理报废物资,所得收入称为“币(敝)余之赋”,被列为国家财政九项收入之一。睡虎地秦简《金布律》详细描述了具体的处理方法,哪些物资需上缴中央部门处理,哪些物资地方政府可以自己处理,哪些物资可以先处理再汇报情况等等。这是研究战国秦汉之际国家财政制度时一个非常有趣且值得关注的地方。
秦汉时期的《效律》,内容可分为三项。一是,官员离任时的财务审核制度。睡虎地秦简《效律》规定“实官佐、史柀免、徙,官啬夫必与去者效代者。节(即)官啬夫免而效,不备,代者【与】居吏坐之。故吏弗效,新吏居之未盈岁,去者与居吏坐之,新吏弗坐;其盈岁,虽弗效,新吏与居吏坐之,去者弗坐,它如律。”官员离任,必须接受继任者的财务审核,审核期为一年,一年之内发现问题,离任者要承担责任。如果继任者不认真检查,一年之后发现财务问题,由继任者负责。这种相互监督的措施,是法家思想的指导下的一贯做法。张家山汉简《效律》:“县道官令长及官无长而有丞者节(即)免、徙,二千石官遣都吏效代者。唯(虽)不免、送(徙),居官盈三岁,亦辄遣都吏案效之。效案官而不备,其故吏不效新吏,新吏罪之,不盈岁,新吏弗坐。”这进一步告诉我们,汉初的官员每三年就要接受一次财务审核,不管离任与否都要进行。秦汉时期的这种官员财务审核制度,也许对今天的官员廉政监督制度也不无借鉴意义[21]。二是,仓库管理制度。《效律》强调财物的出入实行集体监督,参与入库的财务人员最好与支出者是同一批人。三是,严格的会计制度。《效律》的记载表明,秦代的会计制度已经有较为系统的规章可循,会计人员出现财务问题,将视情节轻重给予不同的处罚。郭道扬先生在这方面有深入的论述,值得关注[22]。
战国秦汉之际的经济立法,涉及农工商各个领域,从经济发展到规范监督,可以说基本上形成了体系。这个体系与后世相比也许还不太完备,但规模和框架已经建立起来了,后世朝代的很多制度都渊源于此。
完善的法律需要训练有素的执行者才能达到理想效果,战国秦汉时期国家各级官吏就是这一历史任务的承担者。精通法律成为这一时期为官者的必备素质之一。不论是传世文献,还是出土简牍资料都不乏这方面的记载。《周礼》一书记载官吏考课的六项指标之一就是“廉法”,即通晓法律。睡虎地秦简《语书》说“凡良吏明法律令,事无不能殹(也)”,又说“恶吏不明法律令”。居延汉简中也常说某某官吏“能书会计治官民颇知律令”,等等。官吏学法、懂法,才能依法治民,百姓学法、懂法,才能更好地遵守法律。因此,法律的编纂和传播就显得非常必要了。出土简牍中所见的战国秦汉之际的法律法规正是这些历史的遗迹。
[1]朱红林.论春秋时期的商人[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1):35.
[2]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3]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4]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5]陈伟.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48.
[6]朱红林.汉代“七十赐杖”制度及相关问题考辨[J].东南文化,2006(4):42.
[7]孙诒让.周礼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97:1236.
[8]杨振红.出土简牍与秦汉社会[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09.
[9]陈松长.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徭律例说[G].//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出土文献研究:第十一辑,上海:中西书局,2012.
[10]肖永明.读岳麓书院藏秦简《为吏治官及黔首》札记[J].中国史研究,2009(3):58.
[11]朱红林.战国时期官营畜牧业立法研究[J].古代文明,2010(4):61.
[12]朱红林.周礼中商业管理制度研究[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68.
[13]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684.
[14]劳干.汉代黄金及铜钱的使用问题[J].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71(3):1517.
[1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21.
[16]朱红林.睡虎地秦简和张家山汉简中的《金布律》研究[J].社会科学战线,2008(1):65.
[17]沈刚.走马楼吴简所见“具钱”、“行钱”试解[J].中国历史文物,2008(6):38.
[1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62-63.
[19]朱红林.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205.
[20]朱红林.“当赀盾,没钱五千而失之”新解[J].秦汉史论丛,2008(11):47.
[21]朱红林.睡虎地秦简和张家山汉简《效律》研究[J].社会科学战线,2014(3):85.
[22]郭道扬.中国会计史稿:上[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2:134-170.
[责任编辑 薛柏成]
The Interac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Legal System during Warring States Qin and Han Dynasties
ZHU Hong-lin
(Ancient Books Research Institute,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Jilin 130012,China)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of Qin and Han dynasties is the ancient Chinese state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of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period,also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period of economic development.State the na⁃tions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Qin and Han dynasties made great progress in the rule of law construction.It is im⁃portant to the economic legislation.The achievements not only for the literature handed down from ancient times,unearthed in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in the legal literature also has a rich historical materials,agriculture,hand⁃icraft industry,business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 regulations,performance of the warring states Qin and Han dy⁃nasties as the country's relatively mature economic management function.
the law of Qin and Han dynasties;bamboo slips;economy;management
K23
A
1007-5674(2014)04-0075-06
10.3969/j.issn.1007-5674.2014.04.014
2014-05-3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出土简牍所见战国秦汉之际的经济立法研究”(编号:09CZS009)
朱红林(1972—),男,山西侯马人,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先秦两汉经济史,法制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