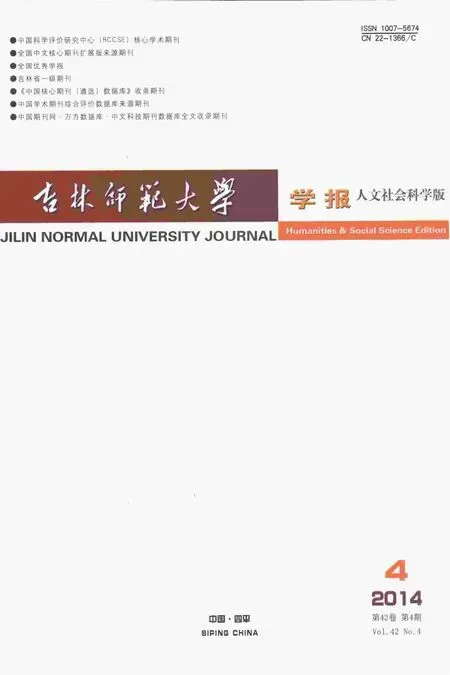论中国诗学道德批评的现代效能
贺根民
(广西师范学院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1)
论中国诗学道德批评的现代效能
贺根民
(广西师范学院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1)
道德批评是中国诗学的一种基本模式,接续古代文学的德本意识,是拯救浮躁凌厉、欲望泛滥的当下文学病症的重要武器。古代文学道德学重新发现文学的道德价值,它是拯救文学话语困境的积极应对,重建了文学价值体系。直面当下的消费主义文化,弘扬时代文化主旋律,有效处理读者的接受期待和积极引导的关系,建构古代文学道德学指明了文学健康发展的绿色通道,也彰显文学批评的人文关怀力度,它有利于重估道德批评的现实价值,从而给当下的传统文化建设与中国文论重构等相关的问题提供有力的理论参照。
文学道德学;现代效能;文学生态
现代学术惯性和操作规范期待新的突破,我国具有悠久灿烂的文化脉络,道德精神是中国文学、文论的一个基本特征,传统文人藉以感受生活、接近自然等实践实现了道德至善的思维认同。道德批评是中国诗学的一种基本模式,笔者在此前发表《道德箴规与中国文学叙事的救赎情结》等系列文章中提出“文学道德学”一词,文学道德学属意文学和道德学的学科交叉,注重文学和伦理学、哲学、社会学等相关知识的综合运用。它以范畴、主题和模式切入道德观念本体,以其来建构一种合适的研究体系。文学范畴展示了文学道德学的文化间性,是其赖以建构的基础;文学主题绘制了文学道德的动态演变空间,演示文学主题的古今演变脉络;文学批评模式构筑一个动态演进机制。
中国诗学的道德批评根基于文化——心理的动态把握,从道德观念角度去展现中国诗学的文化生态,就文化生态去挖掘中国文学道德观念的历史意义,可以透视追求生命之善的道德思维的自律性。从方法论角度看,中国诗学的道德观念建构落脚于传统文化生态,它并非简单地以某种道德标准对文学文本进行褒扬或贬抑,而是对传统的文学现象进行道德的、审美的考察并给以历史的、辩证的阐释。从文化生态视阈来透视中国文学的道德精神,它不仅强化了道德观念建构的纵向脉络,也凸显了道德观念的文化场域,有利于建构中国文学道德的古今演变谱系。有利于重估道德批评的现实价值,从而给当下的传统文化建设与中国文论重构等相关的问题提供一个有力的理论参照。
一、文学的道德价值的重新发现
传统文化是支撑民族、国家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武器,文学的功用价值维度素来是古今文人关注的重要命题,重德是儒家思想体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不可避免地带有浓郁的工具论倾向,汉儒心目中的诗歌是规范君权、教化黎民的施教工具,凸显诗歌外在的价值向度,而并非其诗歌本质,“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1]39。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自觉援引道德尺度,来展示其价值建构层面的约束力,叙事文学层面亦充斥着大量的欲理之辨,“有诗为证”、“有词为证”等叙事干预手段往往不失时机地展示道德话语的惩诫力量。即便是叙事文本的故事结构,也难免浸染一定的道德色彩,文学表现很难离开其所依托的社会伦理。明清小说四大名著,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标领后世历史、英雄传奇、神魔、世情小说创作潮流,可一旦除去其小说类型的外壳,其所呈现的文化内核亦不外乎是忠奸、善恶等礼教、道德层面的问题,文学与道德联姻几乎是古代文学的集体取向。
古代文人的文学话语、文化人格存在明显的同构关系,古代士人心中的理想社会模式是天下一统、君仁臣忠、长幼有序、父慈子孝的局面,儒、道二家深刻影响到古代文人的生存策略,他们在出世与入世的文化生态中展示其生存智慧。特别是儒家人士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试图藉以话语建构来确立社会的道德价值,从而影响到社会政治,显示士人的立法者角色。文学言说,包括某一理论体系的建构,不仅仅是纯粹学理层面的问题,它密切关乎着言说者的身份,文学理论的言说者更应搁置其立法者、布道者的角色,在阐释途中彰显价值评价和道德判断的元素,“在中国,文学理论从来就不是一种纯粹知识意义上的话语系统。从中国古代文论到现当代文学理论都与言说者——古代的士人阶层与近现代的人文知识分子的认同意识直接相关;或者是言说者操控文学并实现身份确证的方式;或者是国家意识形态通向文学领域的桥梁;或者是人文知识分子乌托邦精神的话语显现。”[1]46文学书写承载传统文人的道德责任,不可讳言,中国古代包括文学理论在内的文学书写过多地承载了道德、政治等意识形态的重任,以致忽略了文学自身的本位特征。
晚清民初以来的针对道德的现代反思,展示文化现代性的光彩,道德至上的文化体系受到欧风美雨的洗刷,以德为本的文化观念在西学的冲击下处处告急,道德观念赖以支撑的精神支柱逐渐摇晃。晚清以来文明图像的变迁,给予传统文化改弦更张的时代契机,中华文化在确立世界他者的定位中重新发掘自我,开始了自我认识的过程。中华老大帝国步履蹒跚地进入近代以后,藉以《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等刊物媒介的传播之力,新理念、新方法的输入,加速了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从“铁屋子”里走出的国人,在睁眼看世界的同时,不忘尽情吮吸西方的文化理论,继而引来一个批评传统、再造文明的新时代。
20世纪上半叶流行的文学思维是侧重载道与言志的冲突和起伏来描绘中国文学流变,周作人于1932年曾在辅仁大学以“中国新文学源流”为主题的讲演中,就倡言言志和载道构成文学中相互反对的力量,它们的起伏、消长造成中国的文学史:“中国文学始终是两种互相反对的理论起伏着,过去如此,将来也总如此。”[2]周氏此论,明显将当下文学思潮纳入西方的“为人生而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二元对立的现代框架之中,缘于周作人的新文化运动的突出地位和影响,朱自清《诗言志辨》、朱光潜《谈文学》、吴文琪《近百年来的中国文艺思想》、傅庚生《中国文学批评通论》均有不同程度的学术回应。20世纪初的“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秉持“文学为人生”和“文学为艺术”两种理念,来接续传统的载道与言志之说。以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为例,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唐代部分,对初唐、盛唐和中唐诗论的分析,就将前者归入艺术文学领域,而将后者以人生文学的理论来观照;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在唐代诗论梳理上,认为殷璠、高仲武、司空图属于“为艺术而艺术”一派。而元结、白居易、元稹可算是“为人生而艺术”代表。西学检讨下的民国文学书写,冲击着文以载道的传统观念。
20世纪80年代萌茁的关于文学审美本质的讨论,一度呼唤文本研究的回归,重新将文本置于文学研究的中心位置,这或许是当代学人疲于政治、道德传道之后的抽身换位,谋求文学话语独立的突出标志,并以此来寻觅自我的精神家园。文学理论面临的困境主要是思维方式的问题,不仅仅是文学理论的自身问题,任何理论的言说均不同程度地受人本观念的制约。经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洗礼,传统的理论言说失去面向现实的主导地位,人文精神迫切需要重建,李春青先生云:“为了解决文学拒绝倾听文学理论的问题,文学理论应该调整自己的言说指向,即不再仅仅为文学而言说,而是直接面向社会大众,将自己提升为一种文化批判理论。”[1]260突破传统的理论说教,在多元对话中确立话语方式,展示理论的适用性,文学理论的交叉势在必行。美国文艺理论家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提出“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之说,从作者生平、社会历史维度、文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角度都属于外部研究,外部研究的视角揭示了文学文本背后的文化内涵。知人论世层面的文学道德批评凸显文学批评的价值向度,侧重现代文化语境的文学与道德交叉有利于彰显文学批评的现代效能和拓展其应用空间。
文学演进之河具有相对稳定的途辙,人本和文本构成文学书写的二重性,前者着眼于人物活动,后者落脚于文学作品的演变。西方新批评、结构主义思潮主张将文学研究定格于文本解读,藉以强化文学的自律色彩,而文本作为作者心灵的诗性呈现,作为社会生活的具象反映,很难割舍与社会的联系,即便是文本中价值色彩不鲜明的声韵、结构、布局等元素,亦会潜移默化地受作者主观情感的影响,从而染就人学的烙印,古代文人的山水写意、田园抒怀亦不无道德思维色彩。当今文学、文论的一个缺陷就是忽略了对古代文论的有效吸收和盘活,即便是20世纪50年代钱谷融等先生提出的“文学是人学”之论,也只是援引高尔基等人的前苏联文论而已,援引路径仍根基于西方人道主义,而不是取法于中国传统文论。另如巴人根据19世纪的欧洲的人文主义来诠释中国文艺创作中的人情和人性,亦难避免因为文化生态的差异而带来消化不良的反应。
文学不能承受无根之轻,道德与文学的互动,是提升文学表现人文精神的实践操练,现在诸如“文学终结论”、“为文学减负”的种种说法,提出回归文学本身的主张,张扬了文本的存在效应,却带有某种走极端的趋向。当下文坛的一班“叛逆”由于反感文学的价值向度,主张将文学的道德维度大面积地删除,拒斥除审美、娱乐以外的任何价值考量,以纯粹的审美来实现和超越一切有功利的价值言说。可是,他们因为过于追求文学的自由之境,局限于封闭的世界而遮蔽了文学与外界的联系,忽略了文学必要的社会价值,反价值、欲望化的创作和研究甚嚣尘上,文本成为媚俗、眼球经济的产物。大众文化淡化了经典的文化记忆特质,成为现实社会无规则的行为碎片,它追求感官消费带来了人生境界的负面影响,大众文化的带菌特征,迎合了肤浅的官能刺激,竞相上演的隐私抖露、个体心理秘密的公开叫卖,在所谓“前卫”、“先锋”等标签中不自觉地陷入欲望和生理的裸露之中。享乐主义风行,带来现代性的断裂,他们往往打出反道德或非道德的旗帜,貌似追求身心的全面放松,其实那玩世不恭的姿态、超然中立态度下难掩文学内质的苍白。文学创作一味迎合单纯的感官刺激,变成低俗的替代,美女写作、甚至下半身写作不断充斥文坛,勾起大众的好奇心和窥私欲,社会价值主旋律暂时让位于媚俗的消费潮流,文坛的滔天欲浪遮蔽了其应有的崇高追求。缘于文人担当意识和人文关怀情结淡化,文学逐渐成为一种弱势的存在,文艺作品讳言道德,放弃崇高,在刺激中寻求金钱至上,进而迷失了真善美。文学价值观的缺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文学创作的健康发展。
消费时代的社会指令劫持文学话语,文学创作沦为满载物质欲望和感官享受的过程,文学生产所体现出的种种病症需要我们去积极应对。基于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现状,我们提倡文学道德学,原本扬弃传统道德批判精神,在弘扬社会主旋律的前提下,以包括道德伦理在内的价值坐标来剪裁当下的文学实践,为矫枉过正的欲望书写设置相应的堤坝,使之在合理的区间内,既有效地延续传统,又直面当下活生生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现实。应当承认,传统诗学即便是审美批评,也不能完全脱离道德意识的影响,德本批评一直是具有东方神韵的中国诗学的主要特质。孜孜于德本批评研究的王德清先生认为在文学批评取得独立地位的今天,德本精神依然贯穿于审美批评之中,“由德本精神而生成的德本批评,依然是中国文学批评的主流。”[3]所有创新皆有所本,文学传统是过去的现在,它不只为当下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提供借镜自照的契机,也是拷问历史获取资源的有效途径。在坚持会通意识的前提下,特别是在还没有更好解决方式的现在,我们取法传统,重新呼唤文学道德的回归,就是一种积极面对文学创作误区、剖析文学批评弊端,从而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
二、拯救文学话语困境的积极应对
备受社会转型期的阵痛,以娱乐为目的的消费文化迅猛发展,形形色色的文化产品充斥文化市场,当下的文学话语正陷入困境。“走向市场是90年代文学出版的显性话语”,[4]商业意志、时尚快餐盛行,文学出版的生产本位逐渐向消费本位的市场机制过渡,市场效应改变了文学的操控方式,文学一旦遵循赢利的市场规则,便会丧失文化精神的自律。大量为迎合读者需求的“畅销书”被炮制出来,严肃高雅的文学备受冷落,文学沦为普通的消费文本,批判的功能被悬置起来,凡此种种,消解了高雅的精神追求。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文化研究拓展了文学的研究疆域,但喧嚷的研究话语之中,难免会出现泛化、时尚化的趋势,眼下的泛文化现象渗透了社会的各个角落,却因为人文精神的缺失,浅表、浮躁的文化病态日渐影响国人的精神需求和文化期待。许多研究者总感觉文化研究是一个菜篮,拾到里面的都是菜,边界的无限拓展致使文学纷纷转向大众文化、新兴媒体等研究,出现文化研究热、文学理论研究冷的现象,特别在一些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方面存有过冷的偏失,文学理论的核心问题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文学书写作为文人感受生活、拷问历史、剖析社会的工具理性被弱化,面对日新月异的网络文化和新兴媒体,它越发显得平板和乏力。文学接受时空亦呈现飘渺虚无的特征,文学作品是否为读者接受,往往不取决于作品的品位,而听命于读者的阅读趣味和作品的包装,文学作品的消费符号色彩日趋强化。
文学如同世界其他事物,有其固有的内在规律和文学生态,我国传统文学是东方文化土壤培育的文明之花,文学的政教功利功能一直是文学之脉中的主要价值诉求,它只在少数几个儒学思想相对松弛的时代,如魏晋六朝、明代中后期,才屈居次要地位,直至当下,我们仍不能漠视它的影响。从纷繁复杂的材料中梳理和归纳事物的规律,是事物发展过程不可回避的事情。文学书写和文学批评攸关社会生活与社会批评机制的契合,丹麦的勃兰兑斯说得好:“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5]熟参古人著作,具了解之同情,可以更好地精品细味古人作品。魏晋时代的文化大树陶渊明,其诗歌及其人格往往被视为中国诗学和隐逸人格的突出代表,其田园诗直面躬耕的田园生活,抒写在场生活体验,已包孕对民生和社会问题的深层次思索。现代的陶渊明研究一度纠结于陶渊明思想究竟是属于儒家还是道家的讨论,却相对忽视了陶诗的文学本位,田晓菲的观点具有警醒力:“我们甚至会忘记,陶渊明首先是一个诗人——无论我们多么颂扬他的‘人格’,如果没有他的诗,陶渊明不过是《宋书》、《晋书》和《南史》所记载下来的众多隐士中的一员。”[6]陶渊明人格传响千古,或许基于其文学的巨大成就,易言之,陶渊明的伟岸人格,客观上也成为其诗歌泽被后世的助推器。因此,我们直面当下的文学困境,不必斤斤于某些抽象理论的纠缠,侧重文学文本自身寻觅出路才是务实的办法。
当下文学困境的另一突出表现则为文论的失语。伊格尔顿云:“文学理论就其自身而言,与其说是一种知识探索的对象,不如说是观察我们历史的一种特殊看法……那种‘纯’文学理论不过是学术的神话,因为我们在本书里研究过的某些理论在它们不理睬历史与政治的企图中最清楚地表明了它们是意识形态的东西。对于文学理论,不应责备它有政治性,应责备的是它对政治性的欺骗和无知。”[7]自20世纪90年代发凡起例的文论“失语”讨论,至今仍方兴未艾,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当今文论过于西化,忽视对传统文论的接续。如潮水般涌入的西方文论致使古代文论与当下现实出现了断裂,文论体系现在已成为“一个带有浓厚西式风格的建筑”,但在这一建筑里,“透过西式的概念范畴和思想体系,在这个建筑不易为人们察觉的内部,中国古老的思想传统依然发挥着制约和引导作用”[8],长此以往,瓣香西学,势必会失去文化之根。文论重构必须走出一味取法西方的学科怪圈,正视传统文论中的道德功利因子,展示文论的多元文化特质,盘活古代文论的现代价值。我们不必拘囿于古代文论自身,摆脱当今文论对西方文论的依附状态,秉持会通意识,以更加开放、开阔的视野来彰显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
如前所论,文学研究有人本与文本的纠葛,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传统文学有中华民族的特有轨迹,无论是西方的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弗莱,还是艾布拉姆斯、韦勒克,他们的观点或理论体系均植根于其所属的时代,是西方文化生态的具象反映,单靠舶来的文学理论未必完全适应于当下的文学实践。我们固然提倡文学书写和文学理论研究的多样化,不拒斥西方学说对中国文学现象的参照作用,但是忽略自家文学的传统理路,而套用西方那一套理论体系或者话语言说模式,无异于拿我们的材料去印证西方的理论而已,势必会遮蔽民族文化特质,沦为西方话语的传声筒,以致最终丢失自己的民族本位。西方理论的话语霸权空前挤压我们的生存空间,媚俗的大众消费话语又误导文学指向,文学思想的贫乏,丧失了应有的精神支持。我们提倡立足本土展开多元对话,藉以搜寻中国文学理论的源头活水,以皈依传统文化来救赎当下文论的无根性危机。
文学因革沿袭,自有守成与创新之分野,我们无法彻底返回过去,对待传统文化,不该是秉持一份凭吊古迹的心态,而应视其为有生命的事物并加以冷静和客观的分析。对此,民国文人的做法很值得参考,他们著书立说,登台讲学,往往贯彻知识传授与人格培育并举的原则。钱穆先生认为,只有怀揣一份温情与敬意,才能充分认识传统文化的优异特质。民族文化的复兴,先需了解和体认传统文化的魅力和价值,抗战期间,钱穆的《国史大纲》、冯友兰的《新理学》、金岳霖的《论道》均是在资料极端缺乏的情况下,以传统文化来砥砺气节。波涛汹涌的消费时代如约而至,文学存在方式趋向多样,文学边界扩大,文学的商品化造成文学意义的大面积流失,日常生活审美化趋势加快,我们采取鸵鸟政策不太合乎时宜。照实看来,当前文学还未出现所谓的“终结”征兆,文学的批评精神并非完全丧失,正视社会转型期的各种挑战,文学与道德联姻,刚好找就一个新的定位,既不放弃文学的价值理性,又不忽视文学作品的消费属性,弘扬文学应有的精神品位,引领文学健康的发展。王德清的看法足可参考,他认为中国古代文论不只是定格于过去的历史存在,完全可以盘活于当下,“诗学德本精神以及德本批评研究的理论意义,不只是在于被研究对象内所含蕴的德本特性,阐释这种德本批评的现实效价,把传统批评中具有现代生命力的成分激活,发掘传统的批评理性和文化精髓,并以此为资源,投入新的意义组合之中,重构理想的批评话语,培植新型的批评范式”[3]25。传统诗学的德本意识,指明了文论重构之路,符合疗救当下文论困境的需要。
三、重建文学价值体系的有效尝试
西学烛照下的传统中国,自觉或半自觉地融入万国时代,晚清民国以来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我国固有的文化传统走向解体和重建的过程。社会转型期的学术会在一定程度上伴有分娩的阵痛,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传统文化面临着新文化体系的定位问题,本土经验和外来学术范式艰难磨合,徘徊于新旧学术之中的学人遭遇无数尴尬,传统文化的内在裂痕一时无法满足他们的知识期待,自然去西方文论那里寻求奥援,却不得不再次遭遇文化话语的不适。西方重逻辑的分析思维刷新了世人的认知谱系,西学的纯文学观念输入,为传统提供自我更新的契机。
1980年代以后,国内学术界出现一股解构主义潮流,解构型思维改写了文论的建构方式和研究对象,冲击着昔日文论研究只局限于经典或精英文学范围的研究积习。由此之故,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的边界逐渐模糊,大众文化和大众文学慢慢进入文论的研究视野。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浪潮中,身体的解放被无限制地放大,隐私暴露消解了人文理性,因此一味地效仿或东施效颦,疲惫不说,还形成理论失语,重建追求审美理想、升华人文境界的人文精神是提升社会担当意识的需要。但是,即便在西方,解构主义亦未脱离具体的文化生态,它本身就是一种介入伦理及政治转型的姿态。
陈寅恪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倡导对研究对象“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鉴于西方学说因为文化生态差异而遗留的话语陷阱,我们应该有针对性地回避,尊重古人的文学书写习惯,不直接套用西方术语,开拓视野、更新装备势在必行,一个独立的学科或理论应该有其独特的逻辑体系,否则其存在价值和生存空间都备受怀疑,所谓文学理论的重新建构,意味着开辟新的言说领域、一套新的言说模式。人文性是文学理论的基本价值之一,盛行于欧美的各色文学理论,在不同程度上带有以知识论取代人文性的倾向,譬如那些倡导“到语言为止”的学说,像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结构主义、形式主义、符号学、新批评、后结构主义,遮蔽了作者的存在价值,去崇高化。特别是后现代批评、精神分析法,往往都带有忽视文本道德价值的倾向,致使研究者专注于精神分析、本能的揭示,剥离了理论的价值向度。20世纪以来如潮水般涌来的西方理论,多少存在着切断文学与外部联系的趋势,斤斤于文本自身结构、语词篇章的欣赏,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文学的人本色彩。
缘于中西文化的生态差异,以西律中式的阐释会导致某些自觉或非自觉的误读,却无益于阐释文本的原初意义。诚然,有意误读会创造性地开启思想高峰,但是破坏性的误读只会制造一类所谓的“深刻的片面”,事物的真实意旨仍无法完全浮出水面,祛蔽仍有必要。20世纪80年代文论总体性地向内转,文学回归自身的世界,这客观上提升了文学创作的主体地位。文学创作抽身换位,意在凸显人的意识,赋予人物形象以更多的主体地位。20世纪80年代中期刘再复提出“文学主体性”理论,突出创作主体、对象主体、接受主体的“人”的属性。鲁枢元“文学向内转”之说,进而强化文学研究的心灵和情绪的作用,对接了古代文论的重“人”本色。知人论世,在文论总体性地向内转的潮流中,外部研究非但没有缺席,反而以新的姿态参与了多元文论体系的建设,毕竟文学接受的主客体无法割裂与其周遭世界的联系。
学贯中西的王德威警醒地提起现代话语的视野问题:“在一片后殖民、反帝国主义的批判话语之后,作为中国文学研究者,我们到底要提供什么样的话语资源,引起对话?还是只能继续拾人牙慧,以西方学院所认可的资源,作为批评或参与西方话语的资本?我们对本雅明、德曼这些西方大师的理论朗朗上口,但对和他们同辈的陈寅恪、朱光潜、宗白华、瞿秋白、胡风、钱钟书,甚至胡兰成,有多少理解?我们口口声声强调‘将一切历史化’,但在面对中国历史(尤其是文学史)时,又有多少尊重和认识?”[9]眼前无路想回头,冷静思考过后,向传统取资不失为一种较为理性的选择。尊重传统,便在一定层面上实现文学、文论研究的理性回归。
重建文论的话语体系,必须从无根和失语的状态中突围,注重接续传统,又直面文学的现代价值,加强与世界文论对话力度。刘梦溪先生认为:“传统的重建,有两条途径最重要:一是文本的经典阅读,二是礼仪文化的训练与熏陶。”[10]后者固有文化习惯培养方面的因素,前者强化了经典文本的指引效应,原本是缓解因为西学而导致的消化不良。在一定程度上说,传统文化经典,即为一类鲜活如新的道德文本。钱中文认为:“对传统采取全面颠覆的态度,一脚把它踢开,那实在是一种反理性主义。文化传统是人类几千年间积累起来的精神成果。传统就是过去,然而不是纯粹属于过去的东西,它是通向未来、构成未来的过去。它包括许多旧的东西,然而生根于民族文化深层的东西,即使是旧的东西,也是最具持久力的东西,最具生命力的东西,因此否定它们就是铲除自己的历史立足点。文化传统具有极强的惰性,但完全可以给予改造,使之参与新理论的建设。”[11]建设包括文学价值体系在内的中国文论体系,理应凸显强烈的本土特质,讲究多元文论元素的组合,它既要吸收中国古代与现代文论的优良传统,又要取资西方文论精华,以创造符合社会发展的新型理论体系。
20世纪90年代后,“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西方文论中国化”等问题逐渐引起学人的关注,二者聚焦于建设有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古代文论也好,西方文论也罢,均收拢到当下文论体系的重构实践。它反映了对本土文化的反思力度,虽然学术沉潜期有所缩短,但这种立足国情、正视社会现实的文艺反思潮流,倒也显示了理论的自觉。1999年5月在南京召开的“1999世纪之交:文论、文化与社会”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与会的100多位学者就历史理性和人文精神展开激烈论争,《文艺报》亦于同年6月份特辟“关于文艺精神价值取向的讨论”专栏,深入引领相关问题的探讨。他律和自律相统一的文艺学成为文艺学同仁的共识,文学理论的价值理性重新受到学人的关注。与此旗鼓相应的是1993年《上海文学》发表了王晓明等五人的对话体文章《旷野上的废墟——文学与人文精神危机》,对当时中国文坛和知识分子的精神状况提出质疑,首次亮出了“人文精神危机”的命题。其后,张承志、张炜高举“道德理想主义”与王蒙、王朔展开对阵,对商业化社会下知识分子心态进行了激烈而深度的讨论。也就是在这次“世纪末”的论争中,文学界出现寻找和重建人文精神的强音,针对由于世俗化、市场化而导致的道德沦丧、价值失落进行自我救赎。
文学批评似一把无情的过滤器,只有经得起时光磨练和岁月冲刷,事物方显出其长久的价值。文学与道德同属于社会意识形态,在社会功利和审美追求上具有广泛的共通性。在融合中西、构建本土文论体系的文化实践中,重新关注文学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古代文学道德学体现了由内部研究向外部研究拓展的趋势。文学价值论其实就是一种意识形态,虽然当下各种有关文学定义的言说,大多将其定格为审美意识形态,审美与意识形态联姻,前者似乎绑架了后者,审美纯粹化理念往往会掩盖文学的多重指向。一旦审美成为超越一切的意义指涉,势必会遮蔽文学丰富而深刻外延,易言之,道德价值的缺位,会导致文学创作的缺钙,使之沦为官能的愉悦。德本意识与乐感文化构成中国文人特有的心理结构,疗救文化侏儒症及审美粗俗病,古代文学道德学彰显了基于社会现实、接续传统的有效路径。
古代文学道德学的逻辑建构,拿捏起来并不容易,它不单是方法论的运用,更需要回到历史的道德文化现场,还应积极回应当下的学术思潮。在学术与时代的关系定位上,陈寅恪《陈垣敦煌劫馀录序》之论可资借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12]立足新材料的发现,侧重学术眼光的拓展,不失为一种相对务实而有效的研究路数。文学道德批评既是传统文学道德因素的现实再现,又是盘活古代文论和诊治当下文学病态的有效策略。它并非意味着按照我们当下的道德观念去干预文学创作,只是为当下的文学消费和文学批评领域中的缺陷或误区提供价值层面的参照。尤其在我们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出现道德缺位的情况下,更有必要呼唤道德价值的回归。聂珍钊先生引领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其关注点虽在外国文学领域,却启发我们关于中国古代文学道德学的研究。文学道德学的体系建构是当下文学批评良性发展的明显标志,当下文学书写之于传统文学资源,由最初的揭露和批判过渡到现在的理性传承,对待西方文学、文论思潮,亦从最初简单引进转变为现在的冷静分析、吸收,这种整合视野全面展示了文学价值的现代效能。
在文化生态理论整合视野下,古代文学道德学主要涵盖道德批评范畴、道德批评主题和文学道德批评模式三个主要领域,并藉以建构中国诗学的道德观念大厦。在古代文学道德学的逻辑建构之中,家族伦理、王国精神等宗法元素是中国文学道德学的社会基础,它彰显了道德观念的历史文化语境。道德批评范畴突出表现了古代文学道德学的文化底蕴,传统文人对野、丽和骨等范畴的看法,对放荡、情理等范畴的认知,展示了道德思维的功能取向。建筑于传统家国基础之上的道德批评主题,决定了诗化批评的伦理趋向,促使历代文人就家国关系去体验文本的意义指向、抒写人生感喟。道德批评模式将礼治规范转化为形象的自然物象,展示传统诗教的乐感特色,高扬了自然风物的社会伦理色彩,书写了人类体察自然或社会活动的审美与政教的双重意蕴,从而影响到中国诗学吟哦山水、体验生活的演变脉络。古代文学道德学的逻辑建构,从某种意义上说体现了古今文学、文论的对话和阐释,正是植根当下的古今对话,文学道德批评足以成为文学价值体系重建的思想元点。
四、结语
任何学术研究和理论体系的建构都是现实文化的具象反映,建构理论体系均会以有效介入当下现实为鹄的。古代文学史上的庄子和杜甫,作为奉行道、儒二家思想的代表,后世各据一词,评说纷纭,但魏晋六朝的注《庄》、清代的千家注杜潮流,不无时人追慕二者高尚人格范式的考量。鉴古以知今,返本可开新,传统文化不只停留于遥远的历史空际,还存活于当下的文学实践。我们的工作就是挖掘其中的活性元素,让其焕发富有时代色彩的青春活力,成为当下文学书写和理论建构的崭新驱动力。接续和传承古代文学、文论的德本意识,是拯救当下文学浮躁凌厉、欲望泛滥的重要武器。古代文学道德学重视对文本、作家的研究,有效避免了当下文学批评中那种脱离实际的唯理论倾向。直面当下的消费主义文化,弘扬时代文化主旋律,既贴近现实生活,又不失高尚品位的坚守,有效处理读者接受期待和积极引导的关系。文学道德的审美呈现有利于个体人格完满和培育超迈的精神境界,有益于社会和谐,建构古代文学道德学体系指明了文学健康发展的绿色通道,也彰显文学批评的人文关怀力度。
[1]李春青.在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反思[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39.
[2]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18.
[3]王德清.中国诗学的德本精神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07.
[4]黄发有.文学出版与90年代小说[J].文艺争鸣,2002(4):58-64.
[5]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一分册[M].张道真,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2.
[6]田晓菲.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7:20.
[7]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229.
[8]代迅.中国古代文论:两种言说方式及其现代命运[J].文艺理论研究,2005(3):61-66.
[9]王德威.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课[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64.
[10]刘梦溪.书生留得一分狂[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182-183.
[11]钱中文.文学理论: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57.
[12]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36.
[责任编辑 王金茹]
The Modern Efficiency of the Moral Criticism in Chinese Poetics
HE Gen-min
(College of Literature,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Nanning,Guangxi 530001,China)
Moral criticism was a kind of the basic mode of Chinese poetics,which followed the moral con⁃sciousness of the ancient literature,which was an important weapon that rescued the present condition on impetu⁃ous and desire flood in literature.The criticism on literary and ethics rediscovered the moral value of literature,which saved trouble and rebuilt the system of literary value.Facing to the consumerism culture,carrying forward the era theme,dealing with effective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aders and actively guide,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moral and ancient literature pointed out a green channel,which revealed the humanistic care of literary criticism.It was advantageous to revaluate the real value of moral criticism,so as to provide powerful the⁃oretical reference which relat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urrent cultural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literary theory.
the criticism on literary and ethics;modern efficiency;ecological literature
I02
A
1007-5674(2014)04-0060-07
10.3969/j.issn.1007-5674.2014.04.011
2014-05-20
广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古代文学道德学的逻辑建构”(编号:SK13YB059)
贺根民(1971—),男,湖南邵东人,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古代文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