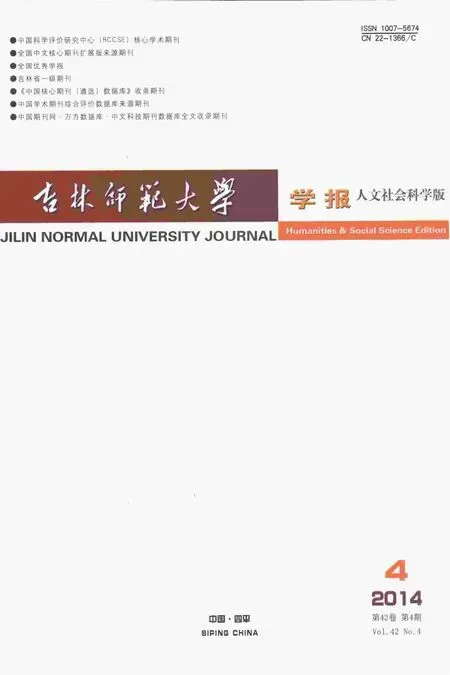唐传奇之“感应母题”与佛经故事
王永丹,谭晓闯
(1.吉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吉林四平136000;2.吉林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唐传奇之“感应母题”与佛经故事
王永丹1,2,谭晓闯1
(1.吉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吉林四平136000;2.吉林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感应母题”是中外文学共有的文化母题。中国古代早期的文史记载中便蕴含了“天人感应”母题。从印度传入的大量佛经及民间故事中也蕴含了这一母题。佛经“感应”故事所具有的印度神话的夸张性、荒诞性、神异性及虚幻性对唐传奇小说母题起到了很大的触媒作用。此外,佛教“感应母题”所宣扬的果报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天人感应”思想的有机融合,亦极大地催化了“感应母题”的风靡。
唐传奇;感应;母题;佛教
在中国文化中,“天人感应”思想存在已久。自先秦以来,人们便有一种共识,那就是人世之外还有一种至高无上的存在,即“天”。天可以主宰人的命运,具有判断是非、赏善罚恶的能力。“天人感应”思想基于原始先民对天体、大地的崇拜及对自然灾害的恐惧心理。由于科技不发达,时人无法解释自然界中诸多奇异现象,于是便把这些变化附会到国家命运抑或个人命运上。汉代以前,“天人感应”思想主要与国运相联系。人们把自然现象、地理变迁等与国家命运结合在一起,认为自然界的某些现象是国运兴旺或不详的预兆。这是中国文化体系初期的一种天人感应思想,认为人的身外有一种神灵(通常称为“天”)在主宰着人间的现实人生。“天”根据君主的行为来决定其国运的兴衰。对于个人而言,往往根据其行为的善恶来决定其吉凶祸福。中国传统的善恶报应思想主要以“天人感应”的形式表现出来。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土以后,它宣扬的果报观与中国的“天人感应”思想杂糅在一起,为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天人感应”思想亦影响并扩展了中国文学中“天人感应”母题的深度与广度。文学中的“感应母题”是指对古代一些中外文史资料或民间故事中的“天人感应”思想及现象的反映。“感应母题”是中外文学共有的文化母题。中国古代早期的文史记载中便蕴含了“天人感应”母题。从印度传入的大量佛教经义及民间故事中也蕴含了该母题。外来物语同浓厚的本土意识的融合,大大催化了中土固有的“天人感应”母题的风靡。佛教“感应”故事所具有的印度神话的夸张性、荒诞性、神异性及虚幻性被喜好“征奇话异”的唐代传奇小说家所汲取,佛教“感应母题”中所蕴含的果报思想也在唐传奇中留有印痕。
一、汉译佛经及民间故事中“感应母题”的先在文本载录
“感应母题”是印度文学中常见的母题之一。譬如冤死导致天灾灵异之事发生,是印度文学中惯常的叙事模式。在著名的印度古代史诗《摩诃婆罗多》中便有多处涉及“天人感应”母题。如诗中描述般度族与俱卢族交战时,黑天使用不正当手段,用暗箭射中毗湿摩。“上天”被黑天阴险卑劣的手段惹怒,顿时日月无光、天昏地暗、地动山摇,以示上天对毗湿摩之死的不平而做出的反应。
印度民间故事集《故事海》中也有一则故事讲国王怀疑大臣湿婆婆尔摩与王妃有染并导致她怀孕,于是便想除掉他。国王派他出使邻国,但同时派密使告诉盟友将湿婆婆尔摩处死。然而在湿婆婆尔摩出行后,王妃与她真正的奸夫私奔被捉到,这时国王才知道冤枉了湿婆婆尔摩。湿婆婆尔摩在邻国请求被处死,并同时说他在哪里被杀,那个地方就将十二年不下雨。于是邻国不但不敢杀他,还要时刻提防他自杀[1]。天灾灵异以示人间冤屈的写法一方面基于古人的认知局限,另一方面也是借助神的权威性与神圣性来宣扬赏善惩恶的道德标准。
这些印度的民间故事、寓言大概都是口头创作,长期在民间广泛流传。“每一个宗教,每一个学派,都想利用老百姓所喜爱的这些故事,来达到宣传自己教义的目的,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2]。佛教徒也看准了这一点,他们把这些民间故事、神话、寓言等附会到菩萨身上,成为释迦牟尼前生的故事,即佛本生经或佛本生故事。
佛教自东汉传入华土,佛经翻译工作也渐次展开。随着僧侣对佛经的宣讲,佛经故事也在中国民间流播开来,并与中国固有的“感应母题”融合为一体。中土汉译佛经中便有多则佛经故事蕴含了“天人感应”母题。如《六度集经》卷四《象王本生》讲述了菩萨成佛之前转世为象王,忍辱负重以成佛的本生故事。该故事写道,象王有两位妻子,第二个妻子因为嫉妒,认为象王对第一个妻子比对自己好,最后愤愤而终。她转世投胎为道陀罗家的女儿,长大后成了王后。为了报前世的仇怨,她决定报复象王。于是对国王说自己梦见一头六牙大象,想要象牙做装饰品。因此,国王召集四方猎人,并按照王后教的方法,射中了大象。象王本可以杀死猎人的,但是它没有。另外,在拔牙过程中,大象一再为猎人考虑,例如它担心其他象听见它的呻吟声,便忍痛一声不吭,并告诉猎人跑时尽量不要留下脚印等,最后象王悲惨地死去。猎人拿到象牙交给国王时,国王一见到象牙,便觉得浑身哆嗦,没有勇气去接。“夫人以牙着手中。适欲视之。雷电霹雳椎之。吐血死入地狱”[3]。凶残的王后终因自己心中的恶念而遭受到报应。
中国民间社会很早就存在善恶报应的心理。《周易》便载有“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之类的名言。在中古时期,这种善恶报应观通常表现为“天人感应”思想。佛教的因果业报观与中国固有的“天人感应”思想殊途同归,因而在佛教传入以后能够很快地融合在一起,共同起到规范人们道德行为的作用。
关于菩萨受难却隐忍不发导致天怒的故事还见于《佛本生故事》之“忍辱法本生”。该故事写菩萨转生在拥有八百万钱财的婆罗门家族。他的父母去世后,菩萨便把所有的钱财都施舍给他人,自己出家了。在一次来到波罗奈乞食时,被统帅邀请,住到了御花园里。一日,羯罗浮王喝醉后在舞伎陪伴下来到御花园,不久便睡着了。看到国王睡着了,舞伎们便停止歌舞,到御花园里欣赏美景。后来她们看到了菩萨,被他所吸引,便围着他,让他给她们说些适合她们听的东西,菩萨便向她们说法。国王醒后不见舞伎,问人才知,舞伎们都在围着一个苦行者听他说法呢。国王大怒,便问菩萨说什么法。菩萨回答,说忍辱法。国王说:“我倒要见识一下你的忍辱法。”于是让刽子手用荆条抽打菩萨两千鞭,又将菩萨的双手、双脚砍掉,割去了菩萨的耳鼻,最后还用脚踹菩萨的心窝才悻悻地离去。国王离去后,统帅帮菩萨包扎好了伤口,并说:“如果你要怨恨,就怨恨残害你的国王,不要怨恨别人。”菩萨却说:“剁我手足,割我耳鼻,愿王长寿,我无恨意。”[4]然而就在国王离开花园,消失在菩萨视线之外时,大地迸裂,阿鼻地狱喷出火焰,将国王吞噬了。面对菩萨的隐忍、宽容,“上天”并没有熟视无睹,而是选择惩戒。但是菩萨的本意却并非如此。面对国王残害自己的暴行,菩萨选择宽恕、忍让,以此消解仇恨。
佛本生故事中讲的是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佛祖在成佛前经历的无数次的轮回转世。他每转生一次,便产生一个“行善积德”、“普度众生”的故事。菩萨经历磨难,最后终成佛。但对于普通民众尤其是下层民众来讲,弘扬佛法,修成正果似乎并不是他们的真正目的。其实,普通民众由于文化层次、认识水平等各方面的限制,他们并不能够按照佛教本身的教义来理解佛教,信奉佛教。与其说他们信奉佛教,不如说他们只是信奉佛教中的某位菩萨或罗汉,他们相信这些神灵可以在其身外明断是非,惩恶扬善,主宰他们的命运。《六度集经》卷五《睒道士本生》故事写迦夷国有一对盲人老夫妇,决心去深山修行,以求得来世的解脱。山中有个修道人担心两位老人在山中生活会有诸多不便,于是便投胎到他们家。老人给他取名为睒子。十年后,一家人进深山修行。由于他们的修行,山中林木茂盛,果实累累,泉水甘甜,猛兽不侵。然而,一日,国王进山打猎,误将箭射入身披鹿皮的睒子。睒子将死,林中百鸟都盘旋而来,声声哀鸣;狮熊走兽,也都大声悲号;山中刮起暴风,暴风刮得天昏地暗、清泉干涸、百花都枯萎凋零了。睒子被误杀后,天地间出现异常的现象,以昭示睒子的冤屈,这种夸张的描写无疑加大了冤情的渲染力度。
印度佛教本强调“出世”,但在传入中土以后,为了不与中国传统的孝道相悖逆,佛教徒们大量翻译佛经来宣扬佛教的孝道,同时又依附中土传统孝道观来宣扬佛教的因果业报观。上述故事中的睒子是个不折不扣的孝子,这样含冤而死的结局显然不能被中土民众所接受。于是,为了弘扬睒子的孝行必受到福报,故事后半部分讲睒子的父母在睒子的尸体前对天盟誓:如果上天知道睒子是个孝子,那就救活他吧。睒子父母的“叫天”行为得到了回应,天神们降到睒子身边,喂他灵丹妙药,于是,睒子死而复生。佛教将其善恶果报观同中土感应思想巧妙地杂糅在一起,既迎合了中土孝悌风气,又宣扬了因果业报观。
无论是菩萨受难还是普通民众蒙冤而死引发天怒,佛经故事都将天灾灵异事件同个人命运联系在一起。该叙述视角的转换对中国汉代以后的叙事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不仅影响了中国的民俗,而且对文人小说的创作也给予了极大的触媒。佛经故事中关于“感应”描写的夸张性与荒诞性吸引、感染了唐代传奇小说家,加之它与中土固有的“天人感应”思想杂糅在一起,极大程度地促进了“天人感应”母题的风靡。
二、佛经故事对唐传奇中“感应母题”的触媒
在中国文学中,“感应母题”多存在于史籍中。汉代以前,主要以关注国运为重心。如《史记·周本纪》写周幽王二年发生地震,河流枯竭,山体崩裂。对此,伯阳甫说道:“周将亡矣。……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国之徵也”。伯阳甫便将山崩川竭这样的自然灾害同周国的存亡联系在一起。但也偶有把天灾灵异事件与个人命运相联系的记载,早在《吕氏春秋》“必几”中便有苌弘被枉杀,三年后,血化作碧玉的记载。汉代以降,该母题的关注点开始向个人命运转移,并逐渐以后者为重心。如东汉刘安《淮南子·览冥训》、刘向《说苑·贵德》、东晋干宝《搜神记·东海孝妇》等都将异常的天象变化同个人命运,尤其是个人冤屈结合在一起,以示上天对人世不公的昭显。
魏晋南北朝时期,民众对佛教表现出极大的宗教狂热。从当时佛教造像的普遍性上便可以看出佛教已经开始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中了。这个时期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因果报应思想开始与中国传统的善恶报应观相结合,佛经故事中蕴含的“天人感应”母题与中古“天人感应”思想及时人的心理诉求相吻合,加剧了“天人感应”母题在其时文学作品中的泛滥。如颜之推所著《还冤记》中便有多条记叙了佛教感应、报应及灵验之事。颜之推本人是佛教徒,又同时兼通儒家思想。他认为,“三世之事,信而有征……内外两教,本为一体”。颜之推是将儒释两家调和为一体的六朝士大夫的典型人物。《还冤记》中蕴含的“感应母题”主要表现在人在冤死、枉死或不当罪而死后会出现的灵异现象上。譬如“徐光”条记载:徐光会法术,“种梨桔枣栗,立得食”[5]。他的预言也很灵验,“凡言水旱甚验”。[5]然而,徐光的一句话,便为他招来了杀身之祸。徐光“常过大将军孙綝门,褰衣而趋,左右唾践。或问其故,答曰:‘流血臭腥不可耐。’綝闻而杀之。斩其首无血”[5]。这则故事揭露了封建社会中封建官吏的残暴与专横,平民的生命没有保障。徐光只说了一句大将军不喜欢听的话,便被有权有势的大将军孙綝杀死,其冤屈天地可鉴。小说中又添加了荒诞离奇的情节,即徐光被斩首后,居然没有血流出。此类“斩首无血流出”情节似源自佛经的叙事模式,汉译佛经中经常用“白血”或“无血”来表示个体的冤屈。如唐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药事》卷十五所载的象王拔牙九群象的故事:“当拔之时,白血流注,拔已欲与猎师,象王身色鲜白,如优昙钵花,血流遍身,如山雪覆,亦如裥(裙幅等折叠)文。”[3]卷二十四71a-72a白血是象王对自己冤屈的控诉。佛经故事中常以此类奇异的现象来宣扬佛教的感应及灵验,引起读者对于残暴官吏的愤懑及对枉死者的同情。作者将现实批判与佛教的“感应母题”及因果业报思想交织在一起,这是佛教观念对中国人思想潜移默化影响的表现。
隋朝的作品中也偶有蕴含“感应母题”的。如《会稽先贤传·陈业》条写陈业兄渡海丧命,同时死了五六十人,骨肉消烂,不可辨别。陈业仰皇天誓后土曰:“闻亲戚者,必有异焉,割臂流血,以洒骨上,应时歃血,余皆流去。”[5]卷161:1158陈业对手足的亲情,感动上天,最后果然找到其兄尸骨。
唐前志怪小说对于佛经故事中“天人感应”母题的采撷,一方面体现出佛教因果业报观与中土善恶报应观杂糅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为唐代传奇小说接受佛经故事的影响奠定了基础。
佛教在唐代发展进入鼎盛时期,民间的佛教活动十分频繁,而且具有相当的规模。唐代的寺院里以讲唱形式开讲的变文,或称俗讲,深受民众的喜爱。此外,唐代很多文人、士子都有在寺院温书的习惯,自然也受到此等佛经俗讲的影响。他们汲取了佛经中的某些故事题材进行加工再创作,使这些口头流传的佛经以书面的形式记录下来,得以更久远地流传,反映因果报应的佛教“天人感应”母题便在这样的背景下得以广泛流播。
唐传奇中的“感应母题”虽然承袭该母题在中古文学中的内容,即通过描述主人公枉死后出现奇异现象的故事来宣扬佛教的善恶果报观,但小说中超现实的、玄虚的情节比例减少,对现实人生的观照比例增加。如《朝野佥载》“江融”条载:唐朝佐史江融性情耿直不阿。杨州徐敬业叛乱后,江融也被编造了一个罪名抓进了监狱,酷吏周兴等人枉奏要杀了他。江融临刑前乞求周兴帮忙引见皇上,但周兴却拒绝了他。江融死前怒斥周兴说,他无罪被枉杀,死后也不会放过周兴的。江融被斩后,“尸乃激扬而起,蹭蹬十余步,行刑者踏倒。还起坐,如此者三,乃绝。”[5]卷121:852江融乃忠臣,却因莫须有的罪名而徒遭斩首。他死后尸体不倒,这是上天对周兴枉杀忠臣行为的控诉,灵异事件的产生可以使行恶者内心受到极大震撼。
爱情是个亘古不变的永恒母题。唐传奇汲取了佛经故事中“天人感应”母题夸张性、虚幻性的精髓,将真爱与“天人感应”融合为一体。如《法苑珠林·河间男子》记述了一个真爱感动上天,女子死而复生的故事:河间有男女相爱,“许相配过”。[5]卷161:1160后来男子从军数年,女子的父母便将她许配他人。没过几年,女子便伤心离世。男子回来后知道女子已死,悲痛不已。他来到塚所,忍不住相思之情,将棺木打开,女子竟然复活了。于是男子将女子背回了家。可是女子的丈夫却过来找她,要求她回家。女子不从。丈夫便将她告到了县衙。郡县难以裁决,便上报给廷尉。廷尉认为,死人复活,此乃精诚所至,感动了天地。于是“断以还开塚者”。[5]卷161:1160男子对女子的真爱感天动地,女子竟死而复生,小说大团圆的结局符合民众的心理诉求。东晋干宝《搜神记》“河间郡男女”条情节与此故事几乎一致,该故事可能是在《搜神记·河间郡男女》基础上所作,与此事类的还可见《搜神记·王道平》。
除“天示冤情”外,唐代传奇小说中也不乏因斋戒奉佛或孝行感动上天而得福报的“感应母题”。
奉佛可息灾免难也是佛教“感应母题”的主要表现。《法苑珠林·岑文本》写文本年少时便开始信佛,经常诵读法华经。一日,遇到船难,船上所有的人都死了。他也没入水中。“闻有人言,但念佛,必不死也,如是三言之,既而随波涌出,已着北岸,遂免死”。[5]卷162:1168《法苑珠林》是唐代僧人道士所作,该书的价值一方面在于弘扬佛教、招徕信徒入教。但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将外来宗教与本土传统相融合,使佛经故事本土化。这些“中国的僧侣文士,曾将佛经消化,转化为本国的、身边的故事,造成一种报应‘近在眼前’的逼真感觉”。[6]“感应母题”在《法苑珠林》篇末、部末多有引用。通过志怪传奇小说形式将佛教的因果报应观与灵验事迹体现出来,使读者相信佛教经典所言非虚,以招徕更多的信徒来抄经诵经。这些感应小说均表现了佛教的效能及灵验,强调了佛教的神通威力。
孝文化一直都是华夏民族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佛教为了避免被排斥在华夏之外,也一直积极采取与儒家融合的态度。一方面,佛教信徒们通过翻译佛经来宣传佛教也是讲孝道的,如姚秦鸠摩罗什翻译了《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大方便佛报恩经》及《孝子经》等。另一方面,佛教依附于中华民族的传统孝道观来宣扬善恶报应及轮回观。佛经中多有关于孝道之故事,其叙述婉转,情节跌宕曲折,这都吸引着唐代传奇作家。在佛经故事的触媒下,他们创作了大量有关孝行的感天动地的传奇小说,譬如《孝子传》中有多条记载孝子们的孝行感动上天,最后或病愈,或遇险境而逢生。如“陈遗”条写陈遗对母亲特别孝顺。后来孙恩作乱,陈遗逃走。陈母因为思念儿子而失明。后来陈遗逃难回到了家,看到母亲为自己哭瞎了双眼,再度拜母悲号。突然,母亲双目竟然复明了。陈遗母亲盲而复明的情节很可能是受到《六度集经》卷五《睒道士本生》故事的触媒,类似传奇可见同卷“王虚之”条。
三、结语
在佛教东传并渐次兴盛的过程中,佛教信徒为了自神其术,弘扬佛法,将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与中土固有的“天人感应”思想相融合,以“天人感应”形式宣扬佛典所言非虚,强化了民众对于佛教劝善止恶功能的信奉。在此背景下,唐传奇亦被该佛风所浸染。正是佛教信徒们强烈的弘教意识,才使得宣传果报的“感应”传奇小说层出不穷,也使得“感应母题”得以经久流传,并成为中国文学中重要的母题之一。
[1]月天.故事海[M].黄宝生,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25-26.
[2]季羡林.五卷书:译本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
[3]高楠顺次郎,等.大正新修大藏经:卷三[M].台北: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0(影印):17.
[4]郭良鋆,黄宝生.佛本生故事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186.
[5]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19[M].北京:中华书局,2011:834.
[6]王晓平.佛典·志怪·物语[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181.
[责任编辑 王金茹]
On the Induction Motif in the Chuanqi Fiction of Tang Dynasty and Buddhist Stories
WANG Yong-dan1,2,TAN Xiao-chuang1
(1.Foreign Languages School of Jilin Normal University,Siping,Jilin 136000,China)(2.College of the Humanities of 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Jilin 130012,China)
The induction motif is one of the common motifs in the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ture.This motif appears in the early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It also occurs in the Indian folktales and Buddhist stories.The ex⁃aggeration and absurdity and illusion reflected in the Buddhist stories related to the induction,have greatly influ⁃enced the Chuanqi fiction in Tang dynasty.And the combination between karma advocated by Buddhism and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induction has greatly promoted the popularization of this motif.
Chuanqi fiction in Tang dynasty;induction;motifs;Buddhism
I206.2
A
1007-5674(2014)04-0047-04
10.3969/j.issn.1007-5674.2014.04.008
2014-05-30
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佛经文学与唐传奇母题的关系研究”(编号:2013BS23);吉林省教育厅“十二五”社科基金项目“唐传奇母题与佛经文学渊源研究”(编号:吉教科文合字【2014】第123号)
王永丹(1979—),女,吉林榆树人,吉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吉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佛禅与中国文学;谭晓闯(1982—),女,吉林大安人,吉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