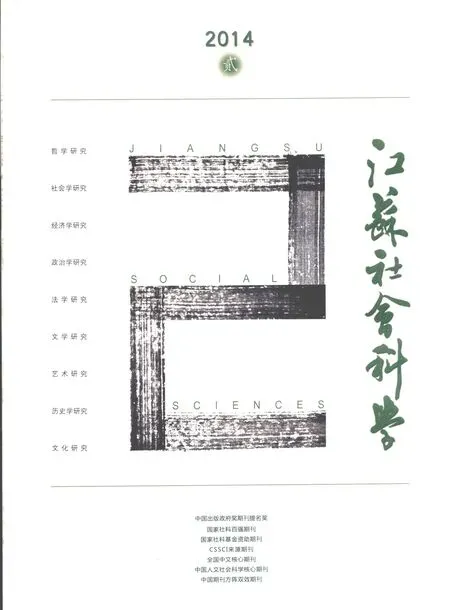抗战时期江南城镇的生活与变化
林 涓 冯贤亮
抗战时期江南城镇的生活与变化
林 涓 冯贤亮
抗战时期,以太湖平原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处于中日战争的前沿,城乡普遍遭受重创,经济萧条,社会秩序更形混乱;而且很多城镇在沦陷后,还受到日伪的经济封锁和清乡扫荡。在此期间,不少城镇却出现了短暂的畸形繁荣,与那些饱受兵燹的城镇相比,呈现了一幅异样的图景。但不管怎样,八年抗战,仍使尚未从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的严重影响下恢复过来的中国,再度陷入深重的灾难,打断了地方工业化即现代化的进程,无论城乡,所蒙受的巨大创伤,主要在于经济的萧条、社会秩序的混乱、人口的损失或流失、城镇的破毁等方面,无不显现出彼时民生的苦痛。
抗日战争 江南 城镇 生活变化
一、引言
唐宋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最为繁荣的地域江南,一直是全国的财赋重地、人文渊薮。其经济、文化等方面发展的中心,主要呈现于各类规模不等的城市与市镇,在明清时代显得十分昌盛[1]参樊树志:《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就江南的核心太湖平原而言,环太湖的大城市,到民国时期就有上海、苏州、无锡、常州、嘉兴、吴兴(湖州)、杭州等。至于市镇,在数量上就显得更多一些。
从1912到1936年,江南的发展,虽然也经历了齐卢之战、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期的经济危机,但在总体上,较中国其他地域为良好,从而也成了世人向往的重要生活地域。民国时人就说,这个“江南”是“一个多重性格的流域”,即从经济上看,“江南是一个都市线”;从人文的观点上看,“江南是物质文明最高度的区域”;从政治上看,“江南是现在政治机构的中枢”[2]刘翔:《江南社会的解剖与再造》,《新运月刊》1936年第34期,第51页。。
江南地域不广,仅包括苏南镇江以东的苏锡常,上海市,浙北杭嘉湖地区和杭州市及其所属余杭县,但是人口繁密,河网密布,聚落庞杂;到1987年时的统计,这个地区共有县城镇25个、县(市)属镇243个,乡镇832个;地域分布均衡,城镇网络极其密集[1]宋家泰:《江南地区小城镇形成发展的历史地理基础》,原载《南京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收入氏著《宋家泰论文选集——城市-区域理论与实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01页。。城镇经济与民众生活,从明清时代以来一直显得颇为繁华。即使在抗战前比较偏僻些的金山县虹桥地方,在传教士们看来,这里的居民“大概都是小康之家,能够自给自足;生活情形比了旁地的农民,要宽裕得多”[2]振华:《金山虹桥的日军暴行》,《圣心报》1945年第11期,第272页。。上海作为江南城市群的中心,更是成了“内地人”眼中的“圣土”,到上海去感觉好像中土僧人能去灵山圣土,不仅生活瑰丽,且遍地黄金[3]沈伯经、陈怀圃编:《上海市指南》,〔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版,第152-153页。。
所以于外在表现上,江南城镇的生活风光华美,生活世界有序、安逸,以及“家给人足”的景象,很令人向往。像苏州,人们的生活都很会“享受”,饮食衣饰、居室园林,“无不讲究精美”,但若无经济基础和文化积累,也是办不到的[4]周邵:《葑溪寻梦》,〔苏州〕古吴轩出版社1999年版,第73页。。有蚕桑业作经济生活依靠的地区,民间生活之安逸更是令人艳羡,丝业经营使得家给户裕,生活优游闲散[5]刘大钧:《吴兴农村经济》,〔上海〕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1939年版,第127页。。直到1936年,在费孝通调查的开弦弓村,当地民众除去税收及各种盘剥外,因为有了丝织业的补助,生活上依然不错[6]张祖道:《江村纪事》,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7年版,第14页。。
1926年冬天,河南辉县人马员生坐沪宁铁路从南京到上海,他说:沪宁火车干净、舒适,车上的男女旅客都很文明,衣服整齐,秩序也好;天也不太冷,车走得很平稳。车窗外树木还绿,不时看到溪水缓流,小船荡漾,农民住宅,几家成一个村子,“江南风光真是名不虚传”[7]马员生:《旅苏纪事》,〔北京〕群众出版社1987年版,第55页。。在他眼中的江南生活,让人觉得很美好。确实,对北方人来说,江南像乌镇这样的小镇,就感觉有北方的二等县城那么热闹了,而且很摩登:“镇里有的是长途电话(后来你就知道它的用处了),电灯,剪发而且把发烫曲了的姑娘,抽大烟的少爷,上海流行过三个月的新妆,还有,——周乡绅六年前盖造的‘烟囱装在墙壁里’的洋房。”[8]茅盾:《大旱》(1934年9月),收入氏著《茅盾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70页。
然而,江南的经济发展与生活之“现代化”,因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而被打断。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江南城镇普遍深受战争的影响,出现了与以往十分不同的面貌。这在学术界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心,不过资料整理与相关研究的重点在于沦陷的大城市、日寇的经济掠夺、汪伪的“清乡”与基层控制等方面[9]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上海市档案馆编:《日本在华中经济掠夺史料(1937-1945)》,上海书店2005年版;余子道:《日伪在沦陷区的“清乡”活动》,〔北京〕《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2期,第109-135页;章伯锋、庄建平主编:《抗日战争》第6卷《日伪政权与沦陷区》,〔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周章森:《抗日战争时期日伪对浙江的经济掠夺》,〔杭州〕《浙江学刊》1994年第1期,第116-121页;王士花:《“开发”与掠夺: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在华北华中沦陷区的经济统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日〕三好章:《汪兆銘の“清鄉”視察》,愛知大学現代中国学会《中国21》,第31卷,风媒社2009年版;潘敏:《江苏日伪基层政权研究(1937-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等。,对于整个城乡地区生活变化的系统考察,稍形不足。以故,本文即以江南为中心,对抗战时期的城乡生活与变化情况,作一系统的清理和初步的探讨,重点仍在于城市和市镇,并在一定程度上勾勒出抗战期间城乡生活的概貌。
二、战争与生活危机
对江南人而言,到1937年时局已变得很坏。杭州人骆憬甫就很担忧:“首都南京沦陷了,杭州还保得住吗?”但他听说杭州-桐乡班轮船还在开行,就准备坐船走,看到本来闹闹嚷嚷的南星桥轮船码头一带很是萧条:店铺、旅馆全都上起了排门,好像大罢市一般;沿路只有些香烟、烧饼、水果等地摊,都没精打彩,连叫卖的声音也没有。他感觉时局越过越坏,尽管战火还没有烧到杭州城,但城里人已经很少了,而城内警报声听起来比往常更加凄厉、恐怖[1]骆憬甫:《1886-1954浮生手记——一个平民知识分子的纪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57、159页,第145页。。
1937年11月5日,日军从全公亭、金山卫两处登陆,9日由金山犯松江,15日陷嘉善,19日陷嘉兴,23日陷石门,至12月23日陷崇德[2]蔡一:《乡史拾遗》,〔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139页。。城乡民众真正陷入了大恐慌与危难之中。
当年11月中旬,昆山、苏州沦陷的消息传到了镇江,镇江城内的学校就停课散学,公务人员搬家。时值内务部下令要求沿江沿海、沿铁路公路的妇孺,一律迁走,更使得全城人心惶惶,纷纷迁徙。城内市面一片萧条,商店关门,银行停闭,马路上的清道夫已解散了,到11月底,连警察也无影响无踪了[3]张怿伯:《镇江沦陷记》,嵇钧生编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
骆憬甫对战争带来的社会危机感,有一个宏阔地回顾,他说:记得民国以来的几次内战,如民国二年的二次革命、民国十三年的齐卢战争、民国十五年的国民革命军驱逐北方军阀,杭州城里都是逃得空空如也,独有民国二十一年的“一·二八”淞沪中日战争杭城没逃一人,这次抗战爆发伊始、战火未及杭城时也是没人逃难,足见杭州市民是多么信赖本国的军队;单单上海一隅,和敌军相持了两个月之久,敌军虽然用海陆空三方的环攻,我们只须空陆两军就足够抵抗敌人。“所以四百市里外的上海,虽然是炮火连天,烽烟匝地,而杭嘉一带依然是农耕于野,商贾于市,工忙于厂,学生弦诵于校。我们的家日处危城之中,也一点不觉得惊慌。”[4]骆憬甫:《1886-1954浮生手记——一个平民知识分子的纪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57、159页,第145页。这样的景像真是让人感到奇怪。不过,类似的记忆还是不少。
嘉兴人朱生豪在常熟女友宋清如的帮助下,于沦陷期间化名朱福全领了“良民证”,寄住在常熟城内。常熟是当时日伪所谓“清乡”的重点,交通要道都设有岗哨,但市民的日常生活在他觉得“尚属平静”;1942年底,他返回嘉兴城。嘉兴同样是沦陷区,朱家的前门有油瓷店掩护,他住在后宅,还能够“不受侵扰”。平时朱生豪足不出户,但物价飞涨,使其生活变得十分穷苦[5]宋清如:《朱生豪与莎士比亚戏剧》,原载《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一期,收入宋清如编:《寄在信封里的灵魂——朱生豪书信集》,〔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442、444页。。
1942年时,由于米价高涨,苏州城中有户籍可查的30万人中,约有7万人已“不敷生活”,至于“赤贫”之人更是“衣食无着”,何况那些在城内打工的无籍农民了[6]宁之:《苏南沦陷区的农村经济》,《中国农村》1942年第2期,第21页。。
杨绛的父亲在抗战时期,带着两个女儿东逃西藏,无处安身,仍然只好冒险逃回苏州。杨绛后来回忆说:“苏州已是一座死城,街上还有死尸。”不过,在他们的家中,却是灯火通明,“很热闹”;但四邻的小户人家,都深受日寇的蹂躏[7]杨绛:《将饮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9、115页。。让人感觉外面的混乱不安,还到不了她们家的这个小世界。
不管“外面”的世界如何变化,每个家庭的生活小世界还是要维续的。南浔人周子美的夫人罗庄在《初日楼遗稿》中,言及抗战爆发时在浔溪(南浔)的逃亡情况,十分生动[8]周子美纂修:《南浔镇志稿》卷四《大事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稿本。:
(九月)初九日,平望、震泽避难者群麕至,初十日来者更多,知事急……先是,邱氏姊言浔西北乡间之大唐兜,有姨弟俞诚如君先期避此,如宣城不得走达,可返浔至此地依之……薄暮抵大唐兜,其地乃一乡村,在浔镇西北三十里,距太湖七里……十六日夕,见东南火光烛天,辨其方,正属镇区。意数椽老屋,悉付劫矣。次日有自镇奔至者,谓上日下午,浔镇陷落,晚间遂起大火也。……时杭垣已失,不可复经;闻乌镇尚安,交通较便,遂决先至乌镇以待。时十二月廿七日,两家束装买舟同行。正月初七日遂雇舟赴青浦,初八日抵朱家角,初九启椗,初十晨曦甫上,距沪已不远;
两岸旁错落皆兵士尸体,服装完整,冬寒不坏……。
周子美后来说,他当时由宁波经杭州,一路寻访家人至南浔乡间,共住两月,沦陷情况所见较多。罗庄的笔录,则真实再现了抗战初期人们的逃难生活与城乡的一般景况。
在嘉兴西面的崇德县城,陷落之前,居民们已扶老携幼,纷纷向城外西北乡间避难。一些匪徒乘各家逃难之机,破门窃取衣物,大部分商店虽未被毁,但一样被窃得十室九空。沦陷之后,人们觉得到处都是死路,还不如回到城中老家去。蔡一(1923-2009)一家就是这样于1938年1月中旬回到城中。蔡一回忆说:原来城中最好的建筑是农民押贷货款的银行,已成了日军的驻所;原国民党崇德县党部,变成了“大日本驻崇警备队”;“晚村小学”成了日军的马场;在城里生活的人们都成了“顺民”;而亲日的“维持会”也建立起来了,称作“崇德县自治会”,设有总务、文书、财政、警务、教育、商务六个科,与原来县政府的架构完全一样。但这个自治会的“政令”是出不了县城的范围,因为离城二三里,就是游击区了[1]蔡一:《乡史拾遗》,〔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143-145页。。
1937年以后,人口密集的上海城,大米已十分缺乏,抢米暴动时有发生。仅在1939年12月,上海就发生了75起。当时工部局的Eleano Hinder对这样的社会危机有过描述:“高物价带来的令人沮丧的后果之一便是‘扫米’,米价不断上涨,‘扫米’成为街头常见的一景(确实,‘扫米’之外,还抢夺其他商品如原棉)。当运米车驶入交通拥挤的十字路口时,便有一群衣衫褴褛者,有大人,有小孩,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行动如闪电一般。一眨眼间,几个米包便被用刀子戳穿。珍贵的大米就顺路洒下,有的用手捧,有的用扫帚扫,大米夹着灰尘,装入备好的袋子。警察赶来之前,‘扫米者’早已溜之大吉。”[2]〔美〕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0页。
就1912至1949年仅30余年的短暂时光而论,社会混乱与战争不歇,很少有十分安定的时期。江南生活的平静与有序常被打破,民间生活的不安全感时刻存在。在茅盾笔下“老通宝”的眼中,自从市镇上有了洋纱、洋布、洋油这类洋货,而且河里有了小火轮船以后,他自己田里生出来的东西就一天一天不值钱,而镇上的东西却一天一天贵起来[3]茅盾:《春蚕》(1932年),收入氏著《茅盾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6页。。社会生活中的这些诸多变化,无疑都让人感到紧张。
三、沦陷时期的状况
受战争的影响,江南城镇变化最明显的,主要在于经济的萧条、社会秩序的混乱、人口的损失或流失、城镇的破毁等方面,但无论哪一方面,无不显现出彼时民生的苦痛。
苏州在民国前期商业贸易较为活跃,经济繁荣,仅小本买卖业有7178家,牙行业247家,代理业29家,居间及货贷业各19家,承揽业37家,典当业40余家,旅馆业27家等;到1937年抗战爆,日机频繁轰炸苏州城,石路商业区首当其冲。苏州沦陷后至抗战胜利结束后的数年间,由于大宗货源依赖上海等地供应,物价飞扬,风潮迭起,整个市场长期处于动荡之中。1948年,五洋业、百货业、布业、西药业关闭约800家,粮行倒闭了近400户[4]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苏州市志》第六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4-386页。,都是因战争的影响所致。
无锡是沪宁交通的一个重要据点,1937年10月间即遭到了日军的轰炸,全城顿成萧条之象,各商店相率闭市,街头巷尾到处可见扶老携幼趋往乡间避难的民众。常州的情况也很相像,城内居民大部分已迁避乡间,商店歇业,市面极形萧条[5]《中国旅行社无锡分社致总社函》(1937年10月7日)、《中国旅行社常州分社撤退情形报告》(1937年12月2日),收入上海市档案馆编:《日本在华中经济掠夺史料(1937-1945)》,上海书店2005年版,第111-113页。。
原来兴盛的宜兴陶瓷业多在鼎山、蜀山二镇,在日军入侵后,许多窑座和厂房相继遭到破坏,窑厂大部分停业。抗战胜利后,又因原材料价格的波动,窑户经济拮据,加上销路阻滞等原因,陶瓷工业日益凋敝。到1949年,全产区仅有49座窑,开工者寥寥无几[1]江苏省宜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宜兴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4页。。
常州的情况更是惨不忍睹,在未沦陷之前就已遭受过四次大轰炸,在地方守军撤走后,城内十分混乱,尸体纵横。类似的,太仓城在轰炸后,房屋被焚毁殆尽,东南北三门外仅剩十余幢屋,西门内外已成一片焦土[2]潘敏:《江苏日伪基层政权研究(1937-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15页。。
1937年12月8日,日军攻占镇江,放火烧了十余天,城内繁盛区域被烧的有东坞街、西坞街、日新街、鱼巷、山巷、柴炭巷、太保巷、中华路、二马路、南马路、大江边、盆汤弄、姚一湾、小营盘、杨家门、五条街、大市口、南门大街等;城内原有的5家典当行,全被烧光[3]张怿伯:《镇江沦陷记》,嵇钧生编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页。。
当年冬天,日军占领了古城松江,大火昼夜不熄,店面房屋尽毁,居民尸体随处可见[4]何惠明主编:《松江图志》,〔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5年版,第60页。。1938年1月据报纸报道,城中的荒凉与破坏之情况,“颇难以形容”,也“令人可怖”[5]上海市档案馆编:《日本在华中经济掠夺史料(1937-1945)》,第71页。。
海盐县西北部的水运枢纽和商业重地沈荡镇,当地曾有谚语称“东市有木行,中市有钱庄,东西两爿当,还有三十六爿稻米行”,可见其繁华之态。在1937年遭受兵燹之灾,镇上千余间房屋被烧毁。海盐县的治地武原镇,在1932年时曾被分置为中大镇、西大镇、北大镇与南塘镇,在战前镇上还有6O余条街巷,多“世家故宅”;但在抗战初期,即遭日军轰击焚烧,镇上90%的建筑被毁,全城变成废墟[6]嘉兴市志编纂委员会编:《嘉兴市志》(上册),〔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37-538页。。到1938年时,从袁花镇、海盐县到乍浦镇的沿海一线,“甚少完整之屋宇”;而从余贤、新篁沿铁路区域,北达平(湖)嘉(善)的松江、嘉善、金山之间,“几为残壁断墙之鬼窟”[7]朱偰:《勗故乡海盐》,《新民族》1938年第16期,第9页。。
抗战爆发后,从杭州至余杭镇的输电线路被炸毁。余杭在沦陷期间,遭受日军的烧杀抢掠,溪北城内的房屋大部被焚毁。蚕丝、茶笋、竹木等土特产,因敌伪贬价收购,加之时时物资封锁,运输困难,农业经济奄奄一息,市场萧条,民生凋敝。在临平镇,若不计络麻与甘蔗的贸易,沦陷期间每年损失丝16000担、生姜25000担、麻布4170担[8]李晓亮、虞铭主编:《余杭商贸老字号》,〔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第9、24-25页。。
处在沪、杭交通要道上的重镇嘉兴,1937年11月19日,日军攻进城后,从东门车站附近至中山路及北门塘湾街(现北京路),纵火焚烧全部的店屋民房;午夜之后,城区的商业闹市北门大街(现建国路)、中街(现中基路)、南门大街等处房屋,都被烧毁[9]郑国光:《日本军国主义者入侵我嘉兴时犯下的滔天罪行》,嘉兴市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嘉兴市文史资料通讯》第4期,1985年7月20日,收入《嘉兴文史汇编》第1册,〔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年版,第121页。。城中居民纷纷逃难下乡。城里城外,火光烛天,一片废墟。不到一年,日军就将整个烟雨楼强占为“华中铁道公司食堂”,名为食堂,实际上就是旅馆,用来接待日军来往的官员[10]吴藕汀、吴小汀:《抗日战争时期的烟雨楼》,嘉兴市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嘉兴市文史资料通讯》第1期,1984年9月,收入《嘉兴文史汇编》第1册,第29页。。
嘉兴县的王江泾镇虽早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被战火所毁,但在20世纪初再度出现了繁荣。1930年代,镇上已有丝行绸坊7家、米行4家、车行2家、商店2O0余家。1937年日军入侵时,又被纵火焚烧了三昼夜,全镇再次化为一片灰烬。沪杭铁路线上的小站王店镇,原来也颇繁华,但从1938年遭受战火开始,到1940年情况已是十分惨淡,这年因驻扎王店的日军与抗日游击队的多次交战,镇上店屋被烧100余间,南塘烧到财神弄,北塘烧到石槛弄,西面烧到塘桥街,东面烧到张家备弄,使王店镇严重损毁[1]嘉兴市志编纂委员会编:《嘉兴市志》(上册),第435、476页。。
嘉兴南面的新丰镇,1938年沦陷后,该镇被纵火焚烧,除东市尚幸存三四家、中市五六家完整之外,其余民房店屋均付诸一炬。这个长达约三华里、素以盛产生姜、大蒜、草籽、油菜籽、西瓜等土特产著称、商业繁盛之市镇,几乎全部焚毁,变成了一片瓦砾废墟,是嘉兴所辖乡镇中被毁最重的,致使数千同胞无家可归。此后,镇人只能搭建几间简陋的草舍棚屋,开设几家茶店和酱油、烟什货摊,以维持生计[2]郑国光:《日本军国主义者入侵我嘉兴时犯下的滔天罪行》,嘉兴市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嘉兴市文史资料通讯》第4期,1985年7月20日,收入《嘉兴文史汇编》第1册,第122页;沈宗堙:《日军在嘉兴城区破坏的大概》,嘉兴市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嘉兴市文史资料通讯》第14期,1995年5月5日,收入《嘉兴文史汇编》第2册,〔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年版,第60页。。
嘉兴县的另一个大镇新塍,其西北接壤江苏吴江,西南毗邻桐乡,向西至崇德、德清县境,越京杭国道之台头镇一带,可达后方浙东、於潜及天目山之浙西行署,在军事交通上颇为重要。在1938年四五月间,被日军纵火焚烧,约占全镇十分之六以上的房屋均付诸一炬,东南半镇都毁,死难多人[3]洪凌源:《日军侵略军在新塍镇的暴行》,嘉兴市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嘉兴市文史资料通讯》第1期,1984年9月,收入《嘉兴文史汇编》第1册,第31页;郑国光:《日本军国主义者入侵我嘉兴时犯下的滔天罪行》,嘉兴市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嘉兴市文史资料通讯》第4期,1985年7月20日,收入《嘉兴文史汇编》第1册,第124-125页。。
大运河北岸的陡门镇,是濮院到新塍的必经之地。1938年9月下旬,被日军烧掉房屋及草屋达100多间。在大批房屋被烧后,民众只能搭建草房居住,以后再也没有恢复元气,现在就叫陡门村[4]高照乡抗战史料征集组:《日军焚烧陡门镇》,嘉兴市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嘉兴市文史资料通讯》第14期,1995年4月5日,收入《嘉兴文史汇编》第2册,第105页。。
孝丰县城内,原来最热闹繁盛的南门大街,半里路长的房屋,被焚毁后只剩下了城门脚旁破旧的14间;东门直街的房屋,也大都成了战争的牺牲品;北街四十九号起至六十一号,全被烧毁,所有的景象是“满目荒凉,一片瓦砾场所,和曲折高低不平的断墙残垣”[5]安甫:《孝丰见闻》,《战地》1939年第5期,第17页。。
从1932年“一二八”战祸后,嘉善地方天灾人祸不断,农业歉收,窑业不振,商业日趋衰落,倒闭了大小商店407家。抗战爆发后,嘉善成了浙江最早沦陷的县,日机对县治所在魏塘镇狂轰滥炸,自东城门至西门学宫一带商店、住宅尽成瓦砾,被毁房屋600余间,死伤多人。全县原有的27个行业1127家商店,大多遭受日军的焚烧抢掠,城中与县境内一些市镇中的繁华热闹街市,顿成一片瓦砾,市场更处于混乱状态[6]嘉善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嘉善县志》,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3、470页。。
因“一二八”战事的影响,上海的闸北一带受祸较烈,一切的新建设都成了断垣残壁,市街毁坏,居民逃离。而此后的“八一三”战事、抗日战争烽起,使上海的南市闸北“半成焦土”,变成了所谓“魅魍出没之所”。比较起来,租界依然是“乐土”景象,当然也出现了人满之患。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租界的景象也不再是桃源乐土,生活一样困难,住处侷促,一部分人又搬入了南市闸北,从而使这个“魅魍出没之所”渐有人烟可见[7]冷省吾:《最新上海指南》,上海文化研究社1946年刊本,第2-3页。。
1937年8月开始,桐乡地区多次遭受日军空袭。日机轰炸的主要目标就是乌镇、石门、濮院等几个大镇。其中石门镇遭受损失最重,仅1938年11月间即被空袭轰炸12次。在日军占领石门湾后,又在全镇大举纵火焚烧,被烧民房达1000多间[8]桐乡市桐乡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桐乡县志》,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第1080-1081页。。据丰子恺回忆,石门湾在遭日机轰炸时,开始只是东市烧了房屋、死十余人,中市毁了凉棚、死十余人;此后而死的有一百余人。这个四五百户人家的小镇,在一片恐慌中,残生的石门湾人互告道:“一定是乍浦登陆了,明天还要来呢,我们逃避吧!”是日傍晚,全镇逃避一空,“全镇顿成死市”[1]丰子恺:《告缘缘堂在天之灵》(1938年),收入氏著《缘缘堂随笔》,〔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5页。。
平湖人冯宗孟在抗战时留居城内,亲历了沦陷后的社会变化,逐日记下了日军的暴行和沦陷区人民的苦难。从1937年11月6日,日军飞机轰炸平湖开始,到19日日军入城进行了大屠杀,并纵火焚屋,县东至城门口大小街房屋焚毁最多。此后其他被焚劫的主要市镇,还有不少。例如,在霓堰镇,房屋数十间被焚毁,居民死伤数人;新篁镇的南市房屋被焚毁十之二三,北市则无恙;向称安靖而繁盛的凤喈桥镇,民房被焚毁数百间,略有市面的西塘桥市则在此前二日就被焚了;新埭镇民房最初被焚毁数十间,后来又被纵火焚烧;县境北部的钟埭镇,虽在战争爆发时市面似较以前繁盛,开始也未遭兵火蹂躏,但在后来镇中心的房屋被焚百余间,数十人被烧。平湖东乡的市镇多次遭受焚劫之灾,1940年5月6日在日军的扫荡下:“衙前镇受祸最烈,焚毁房屋亦多,杀死良民一百三十九人,大半皆新港附近农人”,“赵家桥全镇焚毁过半。新庙、广陈、泅里桥、全公亭诸镇或焚毁十之四五,或焚毁十之二三,人畜死伤无算”,同样,“新仓镇焚毁近半,后数月又去扫荡,芟夷几尽”[2]冯宗孟:《当湖蒙难录》,民国间稿本,第3-56页。。
在苏南地区,日军曾在芦墟、莘塔、北厍、周庄四镇进了大屠杀(1942年2月到3月)。当然,在八年抗战中,有计划的集体大屠杀,发生于南京。1942年2月,日军在吴江县东南地区制造了又一起大屠杀事件。其规模虽比不上南京大屠杀,但其惨状亦可称骇人听闻。吴江县原第六区所辖芦墟、莘塔、北厍、周庄四镇(现莘塔改为乡,周庄划归昆山),位于县境东南边缘,其四乡除与本县同里、黎里相领外,又分别与嘉善、青浦、昆山及吴县接壤。全区河港纵横交叉,湖荡星罗棋布。这里以往全靠船只出入,交通很不方便。淞沪战争后期,日寇在金山卫强行登陆,国民党军队向西撤退后,部分游兵散勇,留在河网地带,先后拉起两支打着抗日旗号的队伍,一支由田岫山(当地人称田湖子)带领;另一支以陈耀宗为首,此人独眼,故人称陈瞎子,他们曾和日寇接仗大小数十次,结果因力量悬殊而溃散。当地百姓因而遭受日寇烧杀之灾[3]《日寇在芦墟、莘塔、北厍、周庄四镇的大屠杀》,引自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汪的清乡》,〔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438-439页。。
湖州地区在战时成了各方力量角力的据点。像乌镇(旧属湖州),在1937年被战火洗礼后,又于1942与1943年遭受了两次大的焚劫,损失惨巨,房屋被焚毁百余间,造成乌镇的空前浩劫。时人冯千乘有过简单的概括:“自湖城沦陷以后,敌人便在沿公路一带,像南浔、祜村、晟舍、升山杨家埠、菁山埭溪等各村市镇驻兵做了据点。天天到附近村庄市镇,奸淫掳掠杀人放火,菱湖、双林、和孚、荻港、乌镇、练市、织里、义皋等地,虽无敌人长驻,但也常常遭受兽蹄窜劫蹂躏。”最后他说:“吴兴本称文物富庶之区,抗战八年,每个市镇、每个村落,无不均遭敌伪兽蹄蹂躏、烧杀劫掠,直接间接损失之巨,难以数计。”[4]冯千乘编述:《抗战八年的吴兴》,湖州档案馆藏油印本,1945年。
在南浔镇,1937年11月被日寇占领,沦陷期间被焚烧的房屋据统计有5000多间[5]周子美纂修:《南浔镇志稿》卷一《灾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稿本。。其详细的调查在1938年3月完成,当时统计被焚房屋在镇之运河南北的有4993间,具体工作由镇人章芝圃、章增福负责,并报告给旅沪的南浔公会[6]周子美纂修:《南浔镇志稿》卷四《大事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稿本。。
四、城镇的畸形繁荣
到1941年,日汪为了将政治力量渗透并强化至江南农村,决定自7月1日起开始实施“清乡”工作。第一期“清乡”就长达五个月,实行地区在昆山、苏州、无锡、常州一线[1]原载《满洲评论》第21卷第3号,1941年7月19日,引自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汪的清乡》,第58-59页。。为加强对“清乡”地区的控制,攫取更多的行政权力,先是在吴县、昆山、常熟、太仓四县分设特别区公署,监督处理全区一切行政事宜。随着“清乡”区域的扩大,到1942年7月,在嘉兴成立了“清乡”委员会驻嘉兴办事处,8月在上海成立“清乡”委员会上海分会;次年6月,在杭州成立了“清乡”办事处。各种“清乡”都设有专员公署、特别区公署和各地“清乡”机构[2]杨元华:《试析日伪对华中的“清乡”活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第106页。。
当然,“清乡”工作中为配合汪伪政权对于江南的基层控制,保甲制度仍是首要的,所谓“清乡要政之核心工作”,并贯穿其始终。就其保甲制的内容来说,则与其他时间并无二致,也是以户为单位,户设户长,十户为甲,甲设甲长,十甲为保,保设保长。推行保甲的目的,当然是要有效抽取沦陷区的人力物力[3]潘敏:《江苏日伪基层政权研究(1937-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7-88页。。到1943年,根据所谓“清乡委员会”的报告,“清乡”地区扩展至太湖东南地区,包括了青浦、吴江、松江、嘉兴、嘉善、海宁、吴县、昆山、南汇、奉贤、川沙等县[4]《清乡委员会工作报告节录》(1943年1月),引自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汪的清乡》,第233页。。
在“清乡”期间,汪伪政权在苏州地区暨太湖东南地区各县分设所谓所谓“大检问所”,大多其实就是城乡间处于重要交通干道的市镇。大检问所的具体驻地名称如下[5]《江苏省宣传处关于该省两年来的清乡工作报告节录》(1943年7月),引自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汪的清乡》,第377页。:
吴县:唯亭、畣直、车场、尹山、蠡墅、胥口、光福、金墅、横泾、苏州站、官渎里、相门站、外跨塘、浒墅关、望亭;
昆山:真仪、安亭、泗江口、茜墩、天福庵、陆家浜、昆山站;
常熟:十一圩港、浒浦、福山、白茆;
太仓:南码头、葛隆镇、浏河镇、浏新镇、七丫口;
无锡:东无锡、大庄桥、南方泉、五里湖、石蒋里、石塘湾、洛社、周泾巷、无锡站;
江阴:黄田港、张家港、护漕港、申港;
武进:常州南、常州东、常州西、戚墅堰、圩塘、横林、连江桥、魏村、戚墅堰站、横林站、新闸站、常州站;
松江:枫泾、石湖荡站、三七号桥、三一号桥、松江站、松江东门、明星桥、新桥、新桥站、莘庄、莘庄站、北沙、欢庵、盛梓庙;
青浦:七宝、吴家巷、陈思桥、纪王庙、万家宅、黄渡;
吴江:吴江、吴江站、八坼站、平望水路、平望陆路、平望站、盛泽、盛泽站、南厍、溪江;
金山:金山卫。
在城市管理中,为了缓和矛盾,对统制政策作了一定的改善。1944年10月,日军对杭州市城门的经济管制进行了调整,主要如下[6]《日军关于杭州城门经济封锁的布告》(1944年10月),收入上海市档案馆编:《日本在华中经济掠夺史料(1937-1945)》,第494-495页。:
一、米量每人在八公斤以内者可自由搬入;
二、香烟量每人在五十支以内者可自由搬出;
三、其他物资仍依以前之规定。
至于搬出、搬入之时间,是从午前七时至午后六时,其他时间及其他不合规范的行为,都将受到严格控制与惩治。
总之,1941年至1945年的“清乡”,就是对沦陷区城乡民众的经济封锁和经济掠夺,直接指向即为苏南的纺织业与面粉业、杭嘉湖一带的蚕丝业等[1]余子道:《日伪在沦陷区的“清乡”活动》,〔北京〕《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2期,第109-135页。。
尽管如此,江南某些城市与市镇却出现了短暂的“畸形”繁荣。
1937年至日伪所谓的“清乡”前,即1941年,常熟地方(人口约8万)物资比较丰富,价格低廉,远比日伪统制得力的地区物资丰富、品种繁多、价钱便宜。这种现象的出现,表明常熟的物资是不通过统制网而大量走私运至上海的。常熟附近的一个村落全都是走私者,这一地区很是繁荣,物资流动非常活跃[2]《关于清乡工作》(1941年7月),原载《东亚》第14卷第8号,1941年8月;引自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汪的清乡》,第65-66页。。尽管遭受了日机的轰炸,粮食、花边、木行、皮货等行业受害极重,损失较巨,但是常熟城内的客栈、饭店、赌场、烟馆出现了畸形繁荣[3]常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常熟市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45页。。
在苏州城的阊门区,虽处日伪统治之下,货物也多遭禁运,货源仅由日商配给,但投机商、掮客、跑单帮应运而生,这类商业经济活动在石路一带十分繁荣,发展显得有些畸形[4]金阊区志编纂委员会编:《金阊区志》,〔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6页。。
1942年进入日汪“清乡”的第二年,除了镇江、苏北、吴江、青浦、松江等地之外,嘉兴、嘉善两县的一部分也进入了“清乡”的新范围。“清乡”使一些地方的商业“日趋繁荣”[5]《江苏省宣传处关于该省两年来的清乡工作报告节录》(1943年7月),引自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汪的清乡》,第372页。,应该也有其现实的背景。
上海沦为“孤岛”后,“一切都畸形发展起来”。由于无锡、常州一带的针织工厂都被日寇破坏,上海的针织工业得到了大发展,完全恢复了以前黄金时代的情况[6]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3页。。抗战伊始有人从上海逃到湖州的菱湖镇避难不到半年,成为“孤岛天堂”的上海因“商机奇佳”,又诱使人返回上海做生意[7]倪丙业:《菱湖旧事》,无出版社,2002年刊本,第175页。。1942年清乡时期,上海地区因设有封锁线,工农业产品与生活日用品被日伪政权统制,沿封锁线一带和地处市区边缘的集镇,成为商贩偷贩大米、工业品的中转点,米业带动了其他行业,市场出现了畸形繁荣,漕河泾镇有米店、米摊30多处,七宝镇上的坐商发展到236户,形成了程家桥等新市镇[8]上海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74页。。
嘉兴县城内的钱庄业到1935年时,受银行业务的竞争以及市场的影响,已全部歇业了[9]邵寿璇:《旧中国嘉兴工商业概况》,嘉兴市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嘉兴市文史资料通讯》第49期,2007年4月5日,收入《嘉兴文史汇编》第5册,〔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年版,第376页。,但在沦陷时期,源昇、同昌、协鑫、鑫泰、福康、厚中、源丰、久盛、大丰、振丰等这么多钱庄仍在经营[10]董巽观、金仁寿:《解放前嘉兴钱庄及金融业之概括》,嘉兴市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嘉兴市文史资料通讯》第49期,2007年4月5日,收入《嘉兴文史汇编》第5册,第393页。。
由于日军曾严格控制船只进入上海港,许多船舶被迫改道停驻平湖的乍浦港,这就使得乍浦的市况依然堪称良好[1]孙意诚:《乍浦港史话》,载中国人民政协浙江省平湖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平湖文史资料》第二辑,1989年刊本,第7页。。
长兴县的大部分集市在抗战期间因受战争影响,或停业或迁移。而鸿桥属于长兴县的“阴阳”地界,即敌我势力交叉地带,市集畸形发展,成为临时性的商业中心[2]长兴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长兴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53页。。到1940年,长兴的商业据点,如泗安、虹星桥、夹浦、鼎甲桥、天平桥、白阜埠、亩桥、煤山、车渚里、合溪等,市面都仍然流行日货或者是被改头换面后的日货,商业贸易“一般都比战前繁荣”;尤其是鸿桥、蒋埠桥、南庄、小桥头等,“是敌货倾销中心,市场更其热闹”[3]浙江省战时合作工作队游击区直属分队:《长兴之经济调查》,《浙江建设》1940年第3期,第129页。。
德清县的新市镇因僻处水乡,在战争爆发后的二年里,其他地方的城市相继陷落时,它却成了“烽火不到的避难所”,一时间嘉兴、湖州一带的避难者群集于此,“显出畸形的繁荣”[4]心真:《水乡市景(新市通讯)》,《杂志》1944年第6期,第171页。。
而在上海市近郊的龙华镇,根据日本军人荻岛静夫在1938年2月23日的记录,景况良好:那时“春天已经来了,就像日本国内3月下旬的气候。我和桑野两个人去龙华镇的慰安所游览,这里日本人和中国人都有,非常热闹,令人吃惊。”[5]四川建川博物馆藏:《荻岛静夫日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3页。
地处偏僻的一些小镇,都是这样在抗战时期忽然变得繁荣起来。例如在新塍镇,因不是铁路、公路沿线之地,战争刚爆发时还未受到干扰,所以有不少外地人到新塍避难,人口增加,市面很好[6]邵寿璇:《回忆童年时代的新塍镇》,嘉兴市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嘉兴市文史资料通讯》第31期,2001年3月20日,收入《嘉兴文史汇编》第3册,第396页。。而在西塘镇,1937年时仍不过是嘉善县北部的一个水乡小镇,但至晚在1942年,成了日伪“善兴特别区公署”的所在地,市面因而繁华,人口也有增加,“俨然成一县治”[7]《汪曼云致汪精卫签呈》(1942年8月7日)附“陪同李秘书长巡视清乡地区工作经过报告书”,引自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汪的清乡》,第811页。。这种情况,与嘉善县其他地方在抗战期间商业整体的凋敝局面比较起来,就显得十分“独特”了[8]嘉善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嘉善县志》,第468页。。
五、余论
江南城镇在抗战期间大多遭受重创,更使尚未从1929年经济危机的严重影响下恢复过来的民生,再度陷入深重的灾难。沦陷区的工业资产遭受损失的百分比,上海达52%、南京达80%、杭州为28%、无锡为64%、武汉为12%、广东为31%等。中国工业的精华地带几乎全部遭到重大破坏,从而至少使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延误了20年时间[9]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16-317页。。
1944年底编的《浙江省经济便览》,比较清楚地揭示出,抗战期间浙江地方社会经济所遭受的严重程度:杭州的丝绸交易额,从战前的2500万下降到了二三百万;吴兴县的六成农民从事的养蚕业,城内有工厂30多家,月生产生丝可达7万担,到此时下降至400担;杭州的金融业中,银行曾有20家、钱庄37家、证券业1家、典当行14家、保险业57家,受战争影响,几乎损失殆尽[10]荣维木、江沛等:《笔谈/抗日战争与沦陷区研究》,〔北京〕《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1期,第136页。。
而从社会秩序的层面来看,则更形混乱。据粟裕的回忆,抗战初期的江南地区,“人民是半以上没有看见过中国军队了,当时虽有些所谓‘游击队’,但他们成分的最大部分是流氓、地痞、土匪,也有散兵游勇。纪律很坏,每每花天酒地,自然不会积极打日本……他们的本领,莫过于跆躏人民,不仅是敲诈、抢劫、奸淫,而且是大肆烧杀。”[1]潘敏:《江苏日伪基层政权研究(1937-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页。内乱外患,都使江南城乡遭受严重的摧残。
一般来说,在1936年前,商品市场的物价总体比较平稳,但1937年战争爆发到1949年,物价逐年上涨,在1949年前的三年内,更疯狂上涨。在金山县,通过1937年与1946年两个年份日常食用品的物价对比,清晰地揭示出抗战时期物价飞涨至数千倍甚至两万倍的事实[2]参金山县鉴社编:《金山县鉴》第三期第七章《实业》,1947年2月印行本,第22-24页。。战时的物价变化极其巨大,主要原因当然在于战争的影响以及所谓“法币”的贬值。货币购买力的巨大不确定性,使时人论价都用米来计量,如工价每工以米几升计、房屋则以米几百担计、砖瓦以米十几担计,甚至草台学戏,每天也以数十担米来计算[3]朱履仁等编:《金山县鉴》第四期第八章《社会》,1948年铅印本,第49页。。在吴兴县,除了城区及市镇的洋货与奢侈品价格较高外,一般的衣、食、住之费用,本来都较低。因受抗战的影响,物价就飞涨起来,一般贫民的生活就很难维持了[4]浙江省战时合作工作队游击区直属分队:《吴兴之经济调查》,《浙江建设》1940年第3期,第151页。。上海在“八·一三”之前,繁荣之态已在逐步褪色,人口也有所下降,社会购买力日益萎缩。在报纸的分类广告栏,以及马路旁的电线杆上,空屋出售或出租的告白日见其多。不少大商店登载“大拍卖”、“大放盘”的巨幅广告,宣称“不顾血本,推销存货”。许多旅馆、酒楼、舞场、出租汽车行等,也都门庭冷落,大非昔日可比[5]陶菊隐:《孤岛见闻——抗战时期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页。。沦陷之后的上海城中,普通民众的生活同样十分艰苦。不过最苦的时期仍是在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到1945年间。杨绛回忆道,那时日本人分配给市民的主食是黑面粉与粞米,当时流行的歌谣是:“粪车是我们的报晓鸡,多少的声音都从它起,前门叫卖菜,后门叫卖米。”[6]杨绛:《我们仨》,〔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15页。这个歌谣应该是电影明星周璇在1944年1月出演黑白故事片《鸾凤和鸣》中,主唱的插曲《讨厌的早晨》中的一部分,因而广为流行,多少反映出当时人生活日常的一些真实情态。
直到抗战胜利后,江南百业不振的阴影很难迅速扫除,而这又影响到了乡村民众的生活,由于运输不便、成本昂贵,已无力从事副业经营,使整个产业经济出现了衰微停顿。对抗战期间中国民众及其财产的影响与损失,曾有很多量化估算[7]袁成毅:《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若干“量化”问题》,〔北京〕《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1期,第101-110页。,但仍然不能全面概括彼时中国社会所蒙受的巨大创伤,而且这对战后地方社会的影响,十分深远。
〔责任编辑:肖波〕
The Social Life Changes of Towns and Cities in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during the Anti-JapaneseW ar
Lin Juan Feng Xianliang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the front line of the war,suffered such a lot that they were experiencing an econom ic depression and more turmoil in social order.Moreover,many towns and cities were subjected to Japan's econom ic blockade and sweep.However,quite many towns and cities saw short-lived abnormal prosperity,different from those suffering the war.Nevertheless,Eight years'war brought China,which had not recovered from 1929 econom ic crisis,into a greater disaster,breaking the course of modernization and damaging cities and peop le's livelihood.
Anti-Japanese W ar;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towns and cities;life change
林涓,复旦大学政治学系讲师 200433
冯贤亮,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200433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09CZZ003)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