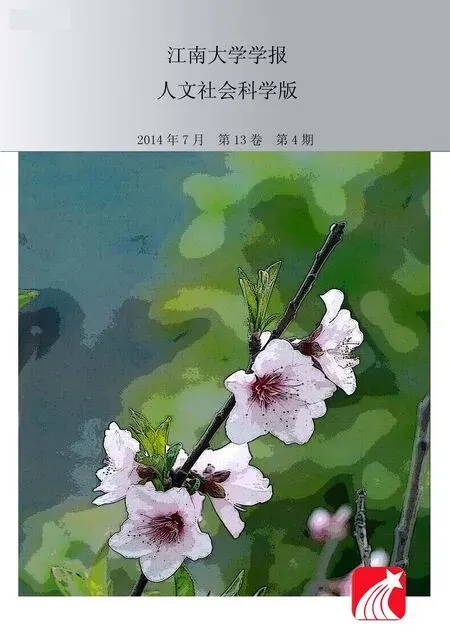气节砥砺:晚明文学家社群结盟进程中的精神洗礼
张 涛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51)
一
在详细探讨社群如何以“气节”培养社群文人的人格品性,以及社群文人在立身处世方面如何表现自己的“气节”之前,我们有必要理清“气节”的内涵。
“气节”其实为儒家思想体系的一部分,并作为士阶层人格价值取向的道德标准成为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精神。主要包含两个层面的内涵:“气”与“节”。
“气”本指充塞宇宙的作为形而下的“器”,万事万物皆秉气而生。后被儒家引申为合“道义”为一体的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一种挺拔屹立的人格“骨气”。孟子对这种“浩然之气”的解释为:“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1]345-346孟子把这种“气”引入了儒家思想体系,形成天地间一种普遍的价值理想,士得此“气”而具最理想的人格魅力,即如孟子所说的:“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1]395有“气”之士,即可成为具有儒家“仁、义、礼、智、信”思想的完美之人。
“节”在《左传·成公十五年》中已有表述:“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意思是说,圣人通达礼节,次者坚守礼节,而“下人”则往往“无节”,甚至“失节”。这种“节”其实代表的先秦时期贵族阶层的“等级关系”,体现的是一种等级贵贱分明的统治秩序。这种统治秩序就是要求人按照这个既定的“节”来行事,既不能超越这个节,又不能违背这个节,他体现的是儒家礼乐的“中道”原则,即为人处事要“有理有节”,不能“犯上”,也不能“乱下”,要讲求“秩序”。以后之“节”又具有了“节操”的人格品性。所谓“节操”,我以为主要强调“士”人立身要有所不为,士人有所不为,才能有“节操”。后世之“节”倾向于士人的“修养”与“内涵”。
因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士阶层往往“气”“节”连用,士既要有“气”的精神品性,又须符合“节”的做事原则。“气节”其实表现的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层面的道德品性和经验层面的立身品性。这就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气节”内涵。
文人士大夫的这种“气节”品性在明末清初社群文人士大夫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可以说,“气节”是社群塑造社群成员精神品质的重要内容,也是社群立社的重要标志之一。如复社文人吴梅村在复社后期成为社群领袖与文坛领袖后,就教育和鼓励文坛新秀——“孚社”诸子继承先辈诸子的“气节”品性,立身要有“品节”,他说:
一曰持品节。先达如山阴、桥李、归安、练川、吴门诸先生,或讲学而标正直之风,或清操而笃匪躬之谊,或三事公孤,或承明侍从,皆文章政事,彪炳一时,而遭患处变,风霜不改。今朝廷褒忠之典方下,无非欲维持名教,风励人伦。吾党生于其乡,景行在望,当于群居论道之时,求颠沛不失之义。所谓品节之宜持者此也。[2]
可见,“气节”成为社群培养士品士节的重要内容,那些有“气节”的文人志士也大多出自社群的培养,复社文人杜登春就说:
说者谓,明朝国运,夺于党人社局,未必非中綮之论。盖以君子小人之难出,同朝各为己私,各争己是,而置国是于度外也。本朝定鼎则不然,小人之种类已无孑遗,立朝尽皆君子,以佐我尧舜之君于上,即分门别户,互有宗师,而琢磨道德,扶植纲常,人人无不自命为正人君子者。原其自,诸公皆从社中来,理学气节,与声教文章,固同源而共贯者也。[3]2
杜登春批评明季诸公党争误国,认为清初朝廷皆君子显然是一种献媚新朝的行为,但其所言立朝之“君子”皆由社中而来,多由社群培养却是事实。社群培养文人士子的“气节”品性可以说是明末社群的重要特征之一。
二
源其自,明末社群重视培养社群成员的“气节”品性还是基于当时社会现实需要,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明代万历中叶以后,阉人专权,朝政日趋腐败,东林君子在与阉党小人的斗争中所表现出的高尚“气节”与顽强斗争精神成为士林表率,社群继承东林“气节”,成为与阉党小人斗争的主力,对社群文人立身处事具有很大影响。王应奎在《柳南随笔》“东林气节”一条中言:“明季东林诸贤,批鳞捋须,百折不回,取次拜杖阕下,血肉狼藉,而甘之者如饴,其气节颇与东汉党锢诸人相似,一时遂成风俗。其时有儿童嬉戏,或据地互相痛扑,至于委顿,曰:‘须自幼錬铜筋铁骨,他时立朝,好做个忠臣也。’闻者莫不笑之。然而流风所被,鼓动振拔,儿童犹知兴起,廉顽立懦,其效不可观乎?”[4]东林人士在与阉党的斗争中所表现的气节及社群文人具有很大的影响,社群中的文人士子皆以东林诸子的“气节”为立身处事方向,如锁绿山人《明亡述略》(卷下)称侯方域“少从其父恂宦京师,习知朝中君子小人之故,矫矫立名节。……著名于复社”[5]。而复社文人方以智被左光斗与上疏力主移宫而与阉党魏忠贤斗争的伟大“气节”所感动,曾亲自撰诗凭吊他:“持归骸骨与灰残,贯日长虹气正寒。血在狱中荒土碧,心悬阕下暮云丹。碑铭成帙千篇哭,鼎镬当前一死难。拜手读公行状略,移宫两疏更充冠。”[6]从明代末年阉党专权,正人君子尽遭迫害,东林君子在朝内与阉党的不屈斗争得到广大文人士子的认同与同情,而且把是否献媚阉党作为文人士子是否有“气节”的标准,瞿式耜在《陈时政急着疏》中说:“夫人立身,止此名节,或以官评之劣,受黜考功;或以一节之差,见摒有道,皆可饰说自解。独至媚党,而终身不可对乡闾,丑莫甚矣!”[7]可见,是否媚阉党作为士大夫立身有无“气节”的精神走向。
明末文人社群的大规模的兴起主要以天启四年(1624年)应社的成立为标志,天启四年正是朝内东林君子与阉党小人斗争正炽的时期。那些组建文社的年轻士子不仅亲耳所听东林诸子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而且各地文社成员在京参加会试期间又亲眼目睹了“丑类”狂态,深深感到“正绪”衰落,士气不振,士风不正,各地在京的社群诸子于崇祯元年(1628年)成立“燕台社”继续与阉党进行斗争,激励士气,振吉士风。特别是崇祯二年(1629年)张溥联合各地文社组织成复社联盟,在入社成员的考察上更加重视入社成员的道德品性,把对社群成员“气节”品性的培养作为社群立社的宗旨之一。也就是说,文社要为政府培养有“气节”德行和“经世”才干的封建官吏。正因为文社组织重视对社群成员“气节”品性的培养与鼓励,所以在明末的政坛上与阉党等小人进行斗争的多为社群中人。
(二)社群重视对社群成员“气节”品性的培养还在于士风日下、世风日腐,这也是社群倡导“气节”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说,自明中叶以后,科举考试已沦为科举诸生猎取功名的工具,所选拔的科举“人才”多无经世之实学,而且最主要的是丢弃了儒家的“涵养”功夫,不能深入体贴儒家“性命之学”。黄宗羲曾言,“事功必本于道德,节义必原于性命”[8],不能深入体贴儒家“性命之学”必士无品节,为官多鱼肉百姓、逢迎上司、献媚阉党,可谓“士节”尽丧,礼仪尽失,士风因此而日坏,钱肃乐本家兄弟钱启忠(崇祯戊辰进士)曾上疏朝廷痛陈此事:“臣观崔、魏乱政,奄祠遍天西,干儿义子,人头畜鸣,斯孔孟学术一大厄也。三尺童子,犹知笑之,而中朝诵功劝进,转相效尤者,正以诸臣平日理学不明,不识节义为何物。但知有身家,不知有君父;但知迎合流俗,不知反照良心。”[9]对士风、世风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陈际泰也痛陈明末士子品性低下而无“气节”:“君父忧危,而文臣工于处堂,武臣拙于死难,乌男子而巾帼者?诹之有心有骨之士,反噤噎不获一吐气。”[10]张岱《快园道古》也言:“思宗曾谕廷臣曰:‘岳少保言,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则天下太平。如今日,文武官与前大不同。文官爱钱不怕死,武官怕死又爱钱。’大哉王言,可为切中时蔽。”[11]社群本质为培养科举人才,在培养怎样的科举人才上,各地文社大都以复社所倡导的“尊经复古”为指向,士子为学大多能根柢圣人经书,注重内在心性的涵养功夫,社群由此成为培养具有“气节”德性科举人才的场所,社群对文人士子“气节”的品性的塑造也使得社群成为转变士风、世风的重要方式。
三
由于社群重视士子“气节”品性的培养,社群成员之间也以气节相砥砺,气节成为社群文人立身处事的基本道德标准,在当时形成一种砥砺气节,注重士品的社会风气。如几社陈子龙“当明之季世,与闇公、夏瑗公等结几社于云间,以志节相砥砺,博达宏通,毅然以经世自任”[12]。河南商丘雪园社领袖侯方域也指出当时文人士子多以“气节”相砥砺,他说:
岁在己卯,中原秦晋之间,虽有盗贼之警,而江南太平富庶,朝廷之上,虽门户角立,渐有党锢之祸,而其公卿之贤而爱名者,皆愿求天下清流之士,引以自助,天下之士亦莫不砥砺节行,唱和声气,相聚于豊镐旧京之地以文学为贽而修同人之业。即以龙眠雪苑之一邑论之,其首事者咸有数人,推之天下,盛可知矣。[13]
再如吴应箕写信给复社同人沈眉生、周仲驭、顾子方以东汉“气节”相勉:
(《答沈眉生书》)弟(吴应箕)昨诒书仲驭谓,留东汉之再世,气节也。魏晋贱守节而汉亡,留南宋之一隅者,理学也,韩侂胃禁伪学而宋亡。且自古至今,上无直节之臣,则下必有怀忠之士……迩来文章气宜,一唱众和者,惟贵邑耳。[14]
(《复顾子方书》)弟尝谓,留东汉之天下者,气节也,留南宋之人心者,理学也,而为是二者非皆高官尊第之人也。今之时事已如此,在廷之臣又如此,然则危言直节之,明道正训,得志则行事见于当时,不得志则议论有所砥定,毋使汉宋诸贤笑后来寂寂者,正在我辈。[15]
社群诸子的“气节”品性我们可以从诸多方面看出,也就是说,社群诸子以“气节”相砥砺,使得他们在自己的行为与思想上处处表现出一种高尚“气节”。
从社群诸子日常生活而言,社群诸子多以“气节”观照自己与他人,如复社领袖张溥称张采“端身行,慎好恶,练学达志,见一不正之人,不正之事,则沐在容,有怀桥柱,思挺而掊其譑;闻一不正之言,累日乌乎苦伤,愁气内出。”[16]社群所倡导的“气节”精神在社群诸子的思想中可谓牢不可破。
从社群诸子立朝做官而言,社群诸子也表现出铮铮“气节”。这在东林社诸子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东林诸子立朝坚持正义,为官光明磊落,在与朝内奸党小人的斗争中尤表现出铮铮骨气,即使面对死亡也毫不妥协。复社文人吴应箕言:“足下(陈贞慧)试观诸贤(东林诸子)当日所以死徙杖谪,终身不悔者,无非急君父,尊国家,爱名节,重气宜,虽嫉恶过严,而辅道甚力,此于汉之气节,宋之理学兼而有之,真本朝之光辉,百代之仪表也。”[17]东林诸子的铮铮“气节”可谓气贯长虹,激励着社群诸子与阉党小人进行顽强斗争,并在与阉党小人的斗争中同样表现出一种“气节”,如复社诸子以《留都防乱公揭》驱赶阉党余孽阮大铖就是一例。复社的“驱阮运动”可谓大快人心,不仅象征着士林正义的胜利,而且教育了读书人“知名节”[18],也“为高皇帝留读书种子之心”[18]——气节。
而社群文人士子的“气节”品性在明亡后表现得尤为突出。清兵的南下一下子使得社群诸子成为遗民群体。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期,社群诸子多抛开个人恩怨,共同投入到抗击清兵的斗争中。如复社成员杨廷麟、刘同升与赣巡抚李永茂结“忠诚社”,在保卫赣州之时誓死不屈,表现出社群诸子坚强不屈的民族气节,徐鼒《小腆纪年》就言,“忠诚社”领袖——督师大学士兵部尚书杨廷麟与兵部侍郎左副都御使江广、总督万元吉、吏部尚书郭维经等死之,“观赣州死事之烈,可以见杨、顾诸公忠诚之结,抚循之劳矣”[19]。 即使旧与东林、复社诸子怀有仇怨的原复社成员周之夔,此时也起兵报国甚勇,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气节。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社群诸子“皆捐妻子,弃坟墓,出入虎穴”[20],在民族大义面前坚持民族气节,为此而死难者多为社中人①明亡后,社群诸子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对清兵的反抗,据杜登春《社事始末》记载,其中复社、几社中人死难者:候峒曾与其子元演、元洁,黄淳耀与其弟金耀守连川死;史可法守淮上死;祁彪佳守邗沟死;张国维守京口死;沈犹龙与李存我、章简守松郡死;徐勿斋、杨廷枢于吴门破日,夏允彝于松江破日,周简臣、周仲驭于金沙破日,陆鲲庭于杭州破日,均不受降而投缳死;黄道周起兵死徽州;陈元倩未临起兵死六和塔;冯元飚起兵死宁波;陈子龙、张子服以吴胜兆案死;夏元初匿陈子龙自缢明伦堂;候岐曾、顾咸建与其侄顾大鸿一门以匿陈子龙死;华允诚死梁溪;左懋第以讲好不屈死;刘公旦与夏完淳以奉表唐藩死;杨伯祥与杨以任均以举义死;吴易建义旗于泖淀死;徐世威死黄蜚兵变;施召征死粤东;吕石香死太仓;张肯堂、朱永佑皆入海死于兵。终生披缁者:熊鱼山、许誉卿、方密之、倪伯屏、张若义、张冷石、梁盼之、林垐、林之蕃、王镐、祁豸佳。隐居者:陆丽京卖药、蒋驭闳黄冠、归元恭、张洮侯酒狂;黄心甫、朱云子诗癖;王玠石名世兄弟躬耕海上;侯秬园、研德伯仲混迹圜中;葛端五、陈言夏、华干龙、陈济生、魏交让、钱彦林、钱素润、张子退、吴日千、计子山、叶圣野、金道宾、穆宛先、张来宗、唐服西、王周臣、彭仲谋、林平子、白孟调、范树鍭、徐昭法、马端午、许九日、沈东生、许在公、陈子威、陆亮中、杜徕西等人皆“终身高隐,不懋功名”。,杜登春《社事始末》言:“乙酉、丙戌、丁亥三年之内,诸君子之各以其身为故君死者,忠节凌然,皆复社、几社之领袖也。”[3]11“一时诸君子慷慨就义,视死如归,就复社、几社中追数之已若干人,此外孤忠殉义,死而不传者不知凡几,使非平生文章道义,互相切劘,安得大节盟心,不约而同若此哉。”[3]12
由此可见,诸如复社、几社等社群文人士子不管是在日常的行为,还是在立朝品性,或者在抗击清兵的民族斗争中多能坚持“气节”品性,这与社群诸子平日以文章道义相切靡,以“气节”相砥砺恐怕是难以分开的。
总体而言,明末文社的兴盛对此期文学家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而影响最深刻的无疑还是社群文人的门户观念、趋同意识,以及由他们对社群的依赖而产生的归属感。但是,文社对此期文学家的影响并不是一个静态灌输过程,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社群性质的变化,社群文人的思想心态亦随之变化。
在文社初起的明代末年,文社士子的科举功名观念十分突出。我们知道,以天启四年应社成立为标志,以研讨科举八股文的文社开始兴起,文坛亦逐渐由诗社的文学论争而转向了文社的科举之争。为获取科举功名,各地文人士子相互尊师取友,组建文社,共同研讨科举八股文作法。因而,在文社初兴期,文人士子获取科举功名的观念十分强烈。在这种强烈的科举功名利益驱使下,此期文人大多专心举业,定期课文会艺。即使政治性较强的复社组织,在初建时,亦不过为吴江大族吴曾羽 配合县令熊鱼山讲学论艺服务;而熊鱼山请时为应社领袖的张溥至吴江讲学,亦不过仰慕他所领导的应社培养出很多科举人才,于是请他到吴江传授科举经验,帮助提高本县诸生科举能力。因此机会,张溥才酝酿成立具有联盟性质的新的复社组织。因而,在明万历末年文社初起之时,科举功名观念在社内文人士子的思想观念中占据主导地位,文社诸子也多围绕科举考试开展活动。
但文社士子并不是生活在一片安静的乐土中,他们追逐科举功名的强烈愿望逐渐被此后愈加黑暗的社会现实所粉碎,其思想观念中的参政意识逐渐凸显。
可以说,天启年间阉党横行,即已激起文社诸子的愤愤不平,文社士子思想观念中的反阉参政动机即已萌发。如当时无锡奇士马素修(后为复社成员)就感慨“熹宗之朝,阉人焰炽,君子道消,朝列诸贤,悉罹惨酷,老成故旧,放弃人间”,“痛东林旧学,久闭讲堂,奋志选文,寄是非邪正于《澹宁居》一集”[3]2,希望通过选文活动来辩明朝政是非,流露出其参与政治的决心与愿望。但此时文社大多初建,社内诸子多未中第为政,社群势力较为弱小,文社士子思想观念中的参政意识虽已萌发,但并不突出。
文社诸子参政意识的凸显,可以以京师燕台社的成立为标志。崇祯元年(1628年),各地社群成员聚集京师参加会试,如应社张溥、张采、徐汧、周钟等人,杜麟征以贤书、夏允彝以乡荐也相聚京师,江西豫章社罗万藻、艾南英、章世纯等人也来到京师②关于燕台社成立时间,朱倓认为是在崇祯三年(1630年) (朱倓:《明季社党研究》,商务印书馆,民国三十四年版),误。据杜登春《社事始末》载,燕台社是在张溥、周钟二人并以明经贡入国学在京师所创,但未明确时间,而据张采为张溥所作《行状》记载,张溥以贡入国学是在戊辰年,即崇祯元年(1629年),而陆世仪《复社纪略》载,张溥崇祯三年(1630年)到南京参加乡试并中经魁,张溥借此乡试机会组织了复社的金陵大会,而非燕台社,蒋逸雪也主张燕台社成立于崇祯元年(蒋逸雪《张溥年谱》,齐鲁书社,1982年版)。。此次京师之聚,来自各地的社群成员不仅相识订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而且也亲眼目睹了朝内“丑类”的猖狂,以至“正绪衰息”[21]。于是,由张溥出面,联络当时在京的都门王崇简、米寿都,闽中蒋德璟、陈肇会,吴门杨廷枢,江右朱健、朱徽,华亭宋征璧等二十余人成立“燕台社”。此时朝内东林君子受阉党迫害已所剩无几,惟有黄道周、郑鄤、项煜等东林人士对“燕台社”的成立给予了支持。燕台社显然是为了反对阉党与发扬正气而立,这标志着以张溥为领袖的文社士子开始由对科举的倾心,转向了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心。
此次京师燕台之盟,诸社成员在思想上经历了一场政治洗礼,南还诸子所举社事在性质上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文社组织不再纯粹进行科举训练,而是开始“昌明泾阳(指东林社领袖顾宪成)之学,振起东林之绪”[21],提出“兴复绝学”的治学思想;其二,关心国家大事,“副崇祯帝崇文重道,去邪崇正之至意”[21],希望通过与朝内“丑类”的斗争,改变当前社会黑暗现状。可以说,文社诸子的燕台社盟奠定了他们参与社会政治革新的基础,极大地激发起他们发自内心的参政热情。如复社文人张岂山,崇祯四年(1631年)在其游历京师期间,就因数次上书朝廷,畅言天下大事而名震天下①岳蛻:《岂山文集序》,张自烈《岂山文集》,四库禁毁书本。。即使在家里期间,他也经常规劝同社乡绅为朝廷效力,为百姓谋福,并且还亲自为乡里百姓作了很多有益之事②详见张自烈《与省直同社乡绅书》,《岂山文集》卷三,四库禁毁书本。。同社友人吴应箕是这样评价他的这种参政热情的:“予闻岂山里居,凡郡邑公祖父母,有交游者,始终不干以私。独地方利病,岂山必尽言极诤,求裨益小民而后已。请蠲赈,汰蠹弁,革猾吏,移书当事者数矣。”[22]
其后,社会政治形势愈加恶劣,文社诸子思想观念中的参政意识随之增强。他们纷纷呼吁社会革新,参与社会改良,同阉党余孽进行生死斗争。文社诸子这种强烈的参政意识,可以说是社会历史发展之必然。
虽然文社诸子积极参与社会革新,但无奈大明江山已病入膏肓,走过了二百七十多年的大明王朝终于难堪重负,而于1644年画上了它的历史句号。社群文人士子被这突如其来的社会巨变所震惊,他们最初所热衷的科举功名不仅化为泡影,而且还得为躲避战争颠沛流离,心境变得十分凄凉悲苦。经历过流离之苦,亡国之痛的复社文人沈寿民对此深有感触,他说:“甲申(1644年)难发,窜身避地,至今未还,羁鸟伤弓,痛定思痛,此根复何敢操人褒贬。”[23]甚至有些文社士子抛弃家室,远离故乡,在极度艰难的环境中辗转抗清,心境变得更为悲苦而凄凉。如几社文人徐孚远追随鲁王与郑成功至厦门、台湾后,即与张煌言、陈士京、沈佺期、卢若腾和曹从等人创立海外几社,与抗清队伍集结在海外条件极为艰苦的孤岛内。他们在艰难的抗清斗争之余,往往寻找岛内“仙洞、虎溪”等幽胜之地举行社集活动,以诗歌倾诉他们的离乡孤寂之情,流露出他们有家不能回、有亲不能见的悲苦凄凉心情。孤岛社集没有了往日社集“南园看杏邀新月,西泖移樽候午潮”[24]的惬意,而是变为“即今诗酒知谁在,欹坐荒山感泬寥”[24]的凄凉之感。
由此看来,这一时期文学家的思想心态既呈现复杂多样性,又呈现动态流变性。这一特殊文人心态的形成,与明清易代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以及随社会变化而性质发生变化的文人社群不能说没有关系,特别是社群文人群体多种形式的文学运作对他们的思想心态具有重要影响。
[参 考 文 献]
[1] 朱熹.四书集注[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
[2] 吴梅村.致孚社诸子书[M]//吴梅村全集: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3] 杜登春.社事始末[M].北京:中华书局,1991.
[4] 王应奎.柳南随笔·续笔[M].北京:中华书局,1997.
[5] 任道斌.方以智年谱[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
[6] 方以智.流寓草:卷六·重吊左少保公[M]//任道斌.方以智年谱.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
[7] 瞿式耜.瞿式耜集:卷一[M]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8] 黄宗羲.明名臣言行録序[M]. 黄宗羲全集:第十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9] 黄宗羲.朝议大夫奉提督山东学正布政司又参议兼按察司佥事清溪钱先生墓志铭[M]// 黄宗羲全集:第十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10] 陈际泰.府君行述[M]//己吾集.台湾:伟文图书有限公司,1977.
[11] 张岱.快园道古[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12] 姚后超.书陈卧子先生安雅堂稿后[M]//陈子龙.安雅堂稿.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
[13] 侯方域.送何子归金陵序[M]//壮悔堂文集. 续修四库全书本.
[14] 吴应箕.楼山堂集:卷十五.答沈眉生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5] 吴应箕.楼山堂集:卷十五.复顾子方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6] 张溥.试牍正风序.七录斋论略[M].台北:伟文图书有限公司,1997.
[17] 吴应箕.楼山堂集:卷十五·答陈定生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8] 吴应箕.楼山堂集:卷十五·与友人伦《留都防乱公揭》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9] 钱仲联.清诗纪事:明遗民卷[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20] 钱澄之.藏山阁文存:卷二·上熊鱼山书[M]//藏山阁集.黄山书社,2004.
[21] 陆世仪.复社纪略[M].上海书店,1982.
[22] 张自烈.与省直同社乡绅书[M]//岂山文集:卷三.四库禁毁书本.
[23] 沈寿民.复王石幢明府[M]//姑山遗集:卷二十四.四库禁毁书本.
[24] 徐孚远.钓璜堂存稿:卷十三·忆昔[M].民国15年(1926)金山姚氏怀旧楼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