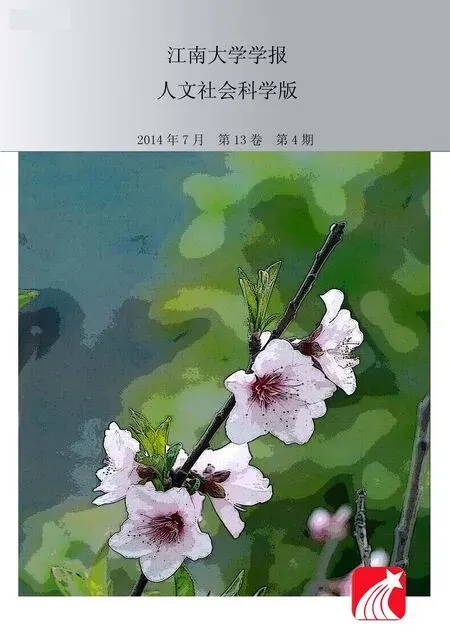休谟的“真正宗教”之意
——基于《自然宗教对话录》的分析
丁朝阳;董 鹏
(1.香港浸会大学饶宗颐国学院,香港 999077;2.卡莱(梅州)橡胶制品有限公司计划部 广东 梅州 514759)
一、引言:甚么是“宗教”?
“宗教”(religion)一词从汉语或英语来说,也不止单单指涉于具体宗教组织的意义。汉语的“宗教”一词,它的意义并非纯为英文“religion”的转译,“宗教”一词的连用最早广泛地使用可追朔到六朝至隋唐时代(约公元400-600年),如梁朝的袁昂曾言:“信寻圣典,既显言不无,但应宗教,归依其有。”而“宗教”一词的古义大概本于“宗”的“宗旨”义与“教”的“实践”义结合,最早使用在佛经,后来道教和儒家传统也相继使用。至于英语的“religion”,H.J.Rose在《牛津古典词典》中指出在希腊文或拉丁文中也没有和“religion”完全对应的词语,根据学者考察并指出“Chistianity”一词在18世纪末几成为“religion”的代名词,在近代西方“religion”的观念中,基本上指向于基督宗教(包括天主教、更正教和东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然而,现在宗教学研究中,已把“religion”的概念进一步内在化和扩展化,如蒂利希(P.Tillich,又译田立克)以“终极关怀”(ultimate concern)来定义“religion”,即宗教实在是人类精神生活中最终极和无条件的一面。①对“宗教”或“religion”的论述,可参考彭国翔着《儒学传统:宗教与人文主义之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P.5-9)。从这一个角度来说,“甚么是宗教?”的问题,至少并没有一个固定不移的答案,甚至乎可能产生某些反对“宗教”思想而实具有精神层面上“宗教”倾向,②例如:基督宗教的潘霍华就曾提倡以“非宗教的解释”或“非宗教的基督教”来论说“基督宗教”,即不依从一般意义(具组织性的)的“宗教”来论说“基督宗教”,其言:“我的脑中不断地出现一个问题:对于今日的我们,基督是甚么?基督究竟是谁?用语文来解说宗教──无论是从神学或纯粹出乎虔诚的观点来说──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内在及良心的时代,就是宗教的时代”(潘霍华着、许碧端译《狱中书简》,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99年,P.137)即是说,潘霍华已将“宗教”的意义理解为从神学思考与纯信仰的想法已不能表述他所论说的“基督宗教”之意义。如休谟反对“自然宗教”却认同具有某种意义之下的“真正宗教”。
英国哲学家休谟(David Hume, 1711-1776),其思想常被标签为“经验主义”或“怀疑论”。对于“宗教”的思考,无论从形式上或内容上来看,也有其别具哲学意涵的地方。简言之,在形式上,休谟从逻辑分析和经验论的方式来反驳“自然宗教”论;在内容上,休谟认为:“宗教的正当职务在于规范人心,使人的行为人道化,灌输节制、秩序和服从的精神。”[1]73③本文所使用的《自然宗教对话录》的中、英文译本为:Dorothy Coleman, eds, David Hume Dialogues concerning Natural Religion and Other Writing,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实际即是“宗教社会化”或“宗教道德化”的。本文的写作目的在于据《自然宗教对话录》来重构休谟的“宗教”观念,即其所言的“真正宗教”,最后尝试从当代宗教哲学家保罗.蒂利希(Paul.Tillich,又译田立克,1886-1965)的“终极关怀”(ultimate concern)来检视休谟的“宗教”观念。④关于休谟的“宗教”观念,在他的《宗教的自然史》也有所论述,然而,在《宗教的自然史》中,休谟的主要用心乃是从人类的宗教倾向之历史来考察“人性”。故此,从正面地以哲学思考、论辩形式来讨论“宗教”的《自然宗教对话录》作比较之下,讨论休谟的宗教思想,还是应该以《自然宗教对话录》作为主要材料。
二、简述《自然宗教对话录》的“自然宗教”与对话形式
《自然宗教对话录》是采取对话的形式来表达对“自然宗教”的讨论,当中所谓的“自然宗教”是指从设计论、神义论为来证明上帝存在的思想,即《自然宗教对话录》所讨论的“自然宗教”并不是指向宗教信仰的全部,而是指向于哲学思考的宗教教义,奥广纳(D. O'Connor)对于《自然宗教对话录》的名称曾表明有误导成分而说:“自然宗教并不以宗教而说,乃从哲学而论。自然宗教是属于理性的而不关乎于信仰的。尽管这类的思考有时可称为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但自然宗教这一名称是容易作出误导。”[2]换言之,休谟的宗教讨论并不是信仰,而是从哲学式反省思考的角度来讨论“自然神学”式(即以设计论和神义论来证明上帝存在的思想)的宗教观。在《自然宗教对话录》中,休谟就借第美亚(Demea)和斐罗(Philo)的口说出他们讨论的重点是在论说神的性质而并不是神的存在,⑤在《自然宗教对话录》中,第美亚说:“问题不在神的存在,而在于神的性质。(The question is not concerning the BEING but the NATURE of God.)”(P.18)斐罗也说:“当合理的人们讨论这些论题时,他们的问当然决不会是关于‘神’的存在,而只是关于‘神’的性质。(But surely, where reasonable men treat these subjects, the question can never be concerning the being but only the nature of the deity.)”(P.19)即是说,休谟所说的“自然宗教”实际是以哲学的合理性来辩说神的性质之问题,而不是从信仰的立场说“神的存在”的问题。如此来说,在《自然宗教对话录》中所谓“自然宗教”的讨论,实际是从哲学的合理性角度来论说“自然神学”(主要是设计论和神义论)的问题。
另外,休谟在《自然宗教对话录》是采取对话的形式来表达,使读者产生一些问题:在《自然宗教对话录》的说话者中,哪个才是代表休谟本人的想法呢?又,为甚么休谟要以这种形式来表达对“自然宗教”的讨论呢?先说后者,据休谟自己的说法:“任何哲学问题,是那样晦暗和不定,人类的理性对它不能得到一个确实的答案者;如果这种问题依然是应该加以处理的话,似乎也自然地使我们采取对话和交谈的方式。”[1]8即是说,休谟认为“自然宗教”的讨论中似乎是比较难于提出确实不移的答案,而采取对话的形式则表明“自然宗教”仍然有讨论的余地。从休谟仅以哲学的反省式思考角度来讨论“宗教”,则可见休谟认为在宗教上可讨论的“余地”正在于“自然神学”仍然是可以作出争论的,因此,休谟便采取对话形式作为讨论“自然宗教”的表达方式。至于“自然神学”仍然具有可争论地方则在后文加以论述。再说前者,在《自然宗教对话录》中,休谟透过三个人的对话来完成,他们分别是:第美亚(Demea,代表正统神学家的思想)、斐罗(Philo,代表怀疑论者的思想)和克瑞安提斯(Cleanthes,代表理性主义者的思想)。艾尔(A. J. Ayer)曾说:“在《自然宗教对话录》的安排中,斐罗说的话最多,这就是为甚么我们说他是在为休谟说话的理由之一。”[3]157-158然而,高策先生也指出:“虽然斐罗遵循着休谟一贯的思维特色,但是,克瑞安提斯的很多观点也是休谟赞成的,因此不能说休谟就等同于《对话录》中的某个人,休谟的观点实际上可以视为斐罗和克瑞安提斯的混合。”[4]本文则认为在《自然宗教对话录》中并不能随便说是哪个角色就是休谟的代言人,理由在于:如果休谟是认为相关“自然宗教”(自然神学)的讨论是仍然“应该加以处理”的题材,则其中所讨论的题材乃是应该别具争议性,我们可以把《自然宗教对话录》视为一个思想的争议历程,在这个讨论过程中的结论,我们才可以当作为休谟的代表言说,即提出所谓“真正宗教”的说法。
三、休谟对“自然宗教”的辩破
在《自然宗教对话录》中对“自然宗教”的辩破主要环绕着两个重要的议题:设计论和神义论。休谟对“设计论”的辩破主要在《自然宗教对话录》的第二至四篇;对是“神义论”的辩破则主要在《自然宗教对话录》的第十至十一篇。以下即按其问题意识而重构当中的论证。
所谓“设计论”是从一种经验式的模拟来证明“上帝存在”。在《自然宗教对话录》中是由克瑞安提斯所提出,其说:“我要简单说明我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看一看周围的世界:审视一下世界的全体与每一部分:你就会发现世界只是一架巨大机器,分成无数较小的机器,这些较小的机器又可再分,一直分到人类感觉与能力所不能追究与说明的程度。所有这些各式各样的机器,甚至它们的最细微的部分,都彼此精确地配合着,凡是对于这些机器及其各部审究过的人们,都会被这种准确程度引起赞叹。这种通贯于全自然之中的手段对于目的奇妙的适应,虽然远超过于人类的机巧、人类的设计、思维、智能及知识等等的产物,却与它们精确地相似。因此,既然结果彼此相似,根据一切模拟的规律,我们就可推出原因也是彼此相似的;而且可以推出造物主与人心多少是相似的,虽然比照着他所执行的工的伟大性,他比人拥有更为巨大的能力。根据言个后天的论证,也只有根据这个论证,我们立即可以证明神的存在,以及他和人的心灵和理智的相似性。”[1]19换言之,“设计论”的论证形式是:世界的运作“就像”一个机械的运作,而“世界”这机械的运用之精巧和准确是非偶然性的,从经验的机械设计来看,“世界”的设计非能人依从规律与知识所可比拟,只能从“造物主”具有巨大的能力才能完成。即从“世界的运作‘就像’一个机械的运作”的结论,我们只能以“‘造物主’”具有巨大的能力才能完成”作为解释。这样,“设计论”的论证方法实际是一种“超越分析”的论证方式,①冯耀明先生曾指出“超越分析”的论证程序,其言:“典型的超越论证通常具有这样的程序:它开始于一个被大家接受的语句"p",然后去寻找一个使"p"成为可能或被接受为真之先在条件或必要条件的语句"q"。"q"必须是真的,因为"p"是真的;而且除非"q"是真的,否则"p"是不可能为真的。许多哲学家认为:"p"和"q"的关系乃是一种‘预设’的关系。”(冯耀明着〈超越分析与逻辑分析:当代新儒学的方法论问题(I)〉,载于冯耀明着《“超越内在”的迷思:从分析哲学观点看当代新儒学》,香港:香港中文大学,2003年,P.145-146)其中的关键在于“模拟推论”的思维方式,结论则是是“神人相似论”。在《自然宗教对话录》中对“设计论”的辩破即据“模拟推论”与“神人相似论”的思想作展开讨论。
关于“模拟推理”的问题。
“模拟推理”的论证强度是有程度性和相关性的,即过度的“模拟推理”实是无效的。斐罗的说法正是对着“模拟推理”而来的,他说:“我对于这个论题(按:设计论)所主要怀疑的,并不是克里安提斯将一切宗教的论证都归结于经验,而是它们甚至还不像是后天论证中最确定、最不可非难的一种论证。”[1]20而斐罗更引出几个例子作出说明:
(一)精确的相似程度。“石头会下坠,火会燃烧,泥土有坚实性等等我们不知看到过几千遍了;当和这些性质相同的任何新的例子出现时,我们会毫不迟疑地得出习惯的推论。这些情况的精确的相似,使我们对于一个相似的事件有完全的保证;我们便不希望亦不搜求更有力的论证了。”[1]20
(二)削弱了的相似程度,即从相同的物种作出个体化的推论。“但只要你稍微远离这些情况的相似性,你就比例地削弱了这个论证;最后并且可以使这证明成为一个非常不可靠的模拟,这种模拟显然容易陷入错误和不定。我们有了关于人类血液循环的经验之后,我们无疑知道在张三和李四身体内亦有血液循环”。[1]20
文中图像识别技术所采用的分类器算法为BP神经网络算法[6]。为了建立铆接位置图像与位置之间的输入-输出模式映射关系,使用MATLAB建立了BP神经网络算法,并将上述Access数据库中的训练组数据中每个位置图像的特征值作为BP神经网络算法的输入数据,位置信息作为输出数据,训练后可以得到输入层和隐层之间的连接权值阵v、隐层和输出层之间的权值阵w、隐含层阈值阵θ以及输出层阈值阵γ。测试组数据则用来检验训练得到的网络对位置识别的的准确率。BP神经网络模型参数如表1所示。隐层节点个数m为:
(三)更弱了的相似程度,即从一个假设相近的物种作出推论。“但从蛙及鱼体内的血液循环,我们去推知人类及其他动物身体中亦有血液循环,就只是一种假设,虽然因为是从模拟而得,可算是一个有力的假设。”[1]20
(四)从试验中发现一个假设相近的相似性是错误的。“若我们从血在动物体内循环的经验推出植物液汁亦在蔬菜内循环,这种模拟的推论就更脆弱;而那些遽然信从那种不完全的模拟的人,由于更多精密的试验,结果却发现是错误的。”[1]20
以斐罗的例子来说,他认为“模拟推理”论证效力在于相似性,而相似性本身是一种假设,是有待经验的测试作出验证的。然而,克瑞安提斯响应说:“假若我们看见一所房子,我们就可以极有把握地推断,它有过一个建筑师或营造者;因为我们所经验到的果与果所从出的因恰是属于一类的。但你却决不能肯定宇宙与房子有这样的类似,使我们能同样可靠地推出一个相似的因,或者说这样的模拟是完全而又完善的。两者之间的差别如此显著,所以你在这里所推出的充其量也不过是关于一个相似因的一种猜想、一种揣测、一种假设;……在一所房子之内与在宇宙之内,对于达到目的之手段的全部安排、最后因的法则、每一部分的秩序、比例、与排列,竟是如此漠不相似的吗?”(同上)换言之,克瑞安提斯是从一个秩序、比例、排列等的结构性作出“相似性”的“模拟推理”,并不是从一种“假设”推出推论,所以其“相似程度”并不是更弱了的程度。
不过,在于克瑞安提斯说出以秩序、比例、排列等的结构性作出“相似性”后,斐罗也回应说这种“相似性”的不恰当,他认为只有在经验中的证明才可以使这种“模拟推理”产生论证作用,他说:“根据这个推论的方法,可以推出(这实在是克里安提斯自己所默认的):秩序、排列、或者最后因的安排,就其自身而说,都不足为造物设计作任何证明;只有在经验中体察到秩序、排列、或最后因的安排是来自造物设计这个原则,才能作为造物设计这个原则的证明。就我们先天所能知道的,秩序的本源或起因可能就包含在物质自身之中,犹如它们包含在心灵自身之中一样;物质各个组成部分可由于一个内在的未知因而构成一个最精细的排列,正像物质各个组成部分的观念,在伟大的普通心灵中,可由于同样的内在的未知因,而构成同样精细的排列,两者是同样不难想象的。这两个假设的同等可能性是可以容许的。但在经验中我们发现(依照克里安提斯所说)它们之间是有差异的。将几块钢片扔在一起,不加以形状或形式的规范,它们决不会将自己排列好而构成一只表的;石块、灰泥、木头,如果没有建筑师,也决不能建成一所房子。我们知道,只有人心中的概念,以一个不知的、不可解释的法则,将自己排列好而构成一只表或一所房子的设计。因此,经验证明秩序的原始原则是在心中,不是在物中。从相似的果,我们推出相似的因。宇宙之中与在人类设计的机器之中,手段对于目的的配合是相似的。所以原因也必须是相似的。”[1]21-22这是顺着克瑞安提的“相似性”的“模拟推理”而说,“设计论”的可行性即在于“原因”的“相似性”,而“设计论”的问题正在于“神人相似论”的问题。
关于“神人相似论”的问题。
“神人相似论”是“设计论”的推理的关键,然而,斐罗明确地指出:“我必须承认,我从开头就反对神人相似的说法;我认为这种说法隐含着对于至高存在的贬抑,凡是笃实的有神论者都是不能忍受的。因此,第美亚,凭着你的帮助,我想要对于你所恰当地称谓神性的值得赞仰的神秘性加以辩护,对于克里安提斯的推论加以批驳;假如他认为我对这个推论的陈述是公平的话。”[1]22在《自然宗教对话录》内,不单止斐罗是反驳“神人相似论”,连被斐罗称赞为“留心及时使你孩子们心中早具一种宗教的虔敬”的第美亚也是反对“神人相似论”的。
第美亚的反对理由主要在于人的有限性并不能与无限性说成“相似”,他说:“当你说神与人的心灵或智力相似时,你实在是主张了什么。人的灵魂是什么?它是各种能力、情绪、意见、观念的一种组合,诚然是结合成为一个自我或一个人,但仍然彼此各别。当它作推理时,作为它的讨论中的部分的各种观念会自己排列于一定的形式或秩序下;而这种形式或秩序并不能完整地保存片刻,却立刻又变成另外的一种排列。新的意见、新的情绪、新的情感、新的感觉起来了,它们不断地变更心灵上的情况,并且在其中制造出极大的错综性,和可能想象的最迅速的递换。这个怎能和一切真正有神论者们归诸于神的完全不变性和单纯性兼容呢?”[1]30
而斐罗的反对理由则从“观念”的角度来反对“神人相似论”,其主要的想法是指出克瑞安提斯认为物理世界与观念世界的“相似性”是有问题的,甚至强烈反对认为从“神人相似论”而能追溯出一个“观念的世界”,而斐罗的意见也环绕着这个“观念世界”的可能问题。斐罗说:“我要把你所拥护的神人相似论的困难更清楚一点地告诉你;并且要证明,假设世界的计划是由包含着不同的观念的(这些观念且有不同的排列的)神的心灵所构成,如同一个建筑师在他的头脑中构成一所他想要建造的房子的计划一样:这个假设是没有根据的。”[1]31他所持的理由是从“理性”与“经验”两方面作立论的。
从对于“设计论”的两个关键观念(“模拟推理”和“神人相似论”)的辩破中,《自然宗教对话录》屡屡强调了知识的来源关键在于“经验”,斐罗说:“一切关于事实的推论都以经验为根据,一切根据实验的推论都以因的相似证明困亦相似。”[1]22“设计论”的“模拟推理”的根据正源于“经验”,然而,在“设计论”的“神人相似论”却由于在“经验”中不容易得到考证而难于成立。
在休谟的“自然宗教”讨论中,除了“设计论”外,还有“神义论”。所谓“神义论”是“指为上帝的公正性进行辩护的学说。源于希腊语theos(神)和dike(公正)。其目的是为了协调基督教的上帝全能和仁慈的教义与世间存在的罪恶现实的矛盾。该学说最早由古罗马奥古斯丁较系统的提出。认为上帝只创造善的东西,恶并非出自上帝。只有当本质上为善的人类滥用了上帝赋予的自由而变得腐败和堕落时,世界上才有恶出现。”[4]“神义论”的说法主要是维护着人普遍心里既有宗教倾向的心理,在《自然宗教对话录》中,第美亚说:“每个人亦可谓是在他自己的心里感觉到宗教的真理;是由于他感觉到自己的懦弱和不幸,不是由于任何的推理,才引他去追寻人及万物所依赖的那个“存在”的保佑。生活中即使是最好的景况也是如此的懊恼和烦厌,所以未来始终是所有我们的希望和畏惧的对象。我们不息地向前瞻望,又用祈祷、礼拜和牺牲,来求解那些我们由经验得知的,足以折磨和压迫我们的不知的力量。我们是多么可怜的生物啊!假如宗教不提出些赎罪的方法,并且平服那些不息的刺激和磨难我们的恐怖,那么在这人生的数不清的灾难之中,我们有什么办法呢?”[1]53甚至乎,连一直抱持怀疑主义的斐罗也指出:“我确是相信,使每个人得到确当的宗教感的最好的而且实在是唯一的方法就是对于人类的悲惨和邪恶作恰当的描述。为着这个目的,一种雄辩和丰富的想象的才能,比起推理和论证的才能来,更为需要。因为不是有必要去证明每个人内心的感觉吗?有必要的只是使我们,假如可能的话,更亲切地和更锐敏地感觉我们内心所感觉到的。”(同上)换言之,个人在内心的宗教倾向是缘于从人类面对世事的悲惨与无奈而产生的,“神义论”的说法正好是巩固宗教中的上帝的神圣性及解释世间的悲惨问题,为个人在内心的宗教倾向作出了一个既能保存“上帝”的完善性质,又能平衡经验中的“恶”悲惨之出现。
然而,在《自然宗教对话录》中却认为“神义论”的说法也是有问题的。
从观念来说,“神义论”是荒谬的,即“上帝”既然是完美的,又怎可能容许“恶”与悲惨的出现呢?斐罗说:“我们承认他的力量是无限的:凡是他所意欲的都实现了:但是人类及其他动物都是不幸的:足见他并不意欲人及其他动物的幸福。他的智慧是无限的:他从不会在选择达到目的的手段中出错:但是自然的历程并不倾向于人类或动物的幸福:足见自然的历程并非为这个目的而设的。在人类知识的全部领域中,再没有比这些推论更可靠,更无谬误的了。……他愿意制止罪恶,而不能制止吗?那么他就是软弱无力的。他能够制止,而不愿意制止吗?那么他就是怀有恶意的。他既能够制止又愿意制止吗?那么罪恶是从那里来的呢?”[1]57这样看来,“神义论”至少不能为“上帝的属性”作出恰当的说明。
在社会现实的经验看,“神义论”的问题并不能对“设计论”作出补充的说明,更不能为到“自然宗教”的想法作出证明。斐罗指出四个相关于“恶”的出现与“设计论”的关系条件之问题。
(一)从设计和法则来看,痛苦与快乐同样来激发一切动物的行为,并使它们在自我保存的伟大工作中保持警惕。这就能解释痛苦的设计是必然地存在吗?斐罗说:“那么为什么要使动物有痛苦这种感受呢?假若动物能脱离痛苦一个钟头,他们就尽可以永远享受免除痛苦的自由;而且,为了创造痛苦的感觉,就需要对它们的器官作一个特殊的设计,好象为它们创造视、听或其他任何的感觉一样。难道我们就可以毫无理由地揣测,这样一个设计是必要的吗?难道我们可以把这个揣测作根据,就如以最可靠的真理作根据一样吗?”[1]63
(二)世界是由一般规律管制的,如果没有这个条件,那么痛苦的感受力就不会单独的产生痛苦的,而这对于一个很完善的存在时不必要的,即是说,不能由特殊的意志(完善的存在)来消除“恶”吗?斐罗说:“难道不可能由神来了结各处发现的一切的恶;并且不用任何准备或因果的悠长的进程,就创造出一切的善吗?”[1]63
(三)造物的完善运作的可能在于节约原则,即能在造物的各方面作出配合,从而消除“恶”的出现,斐罗说:“造物主是有不可思议的力量的:他的威力是被认为伟大的,如果不是无穷尽的话;就我们所能判断的而言,也没有任何理由使他在调配他的众生时也遵守这种严格的节约原则。假如他的力量是极端有限的话,那么最好是少创造些动物,而多给予它们一些为它们幸福和生存所需的能力。一个建筑师,如果他执行的计划,超过了他的材料能够使他完成的限度,就决不能算是智虑聪明的。”[1]64
(四)假如从“设计论”的运用来看,“恶”的出现正由于自然运作的不精确的,从而体现出“设计论”并未能展示出“上帝”的“完善”之属性。斐罗说:“比方,风对于在地球表面运送气体、帮助人的航行,是必需的;但又多么常见其激起而成为风暴和台风,而变成有害的呢?雨对于滋养地球上的动植物是必需的;但雨又多么常常地有害呢?多么常常地过分呢?热对于一切动物生活和植物生长都是必需的;但并不总是能够经常保持适当的比例。动物的健康和昌盛依靠身体上的体液和腺液的调和及分泌;但是这各部分并不能总是有规律地完成它们的正当的功能。有什么比心灵所具的野心、自负、爱情、忿怒等等的情绪更有用处?但它们是多么常常地冲破它们的界限,而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变乱呢?在宇宙中最有利益的东西,总是常常因为过分或缺陷就变成有害的;自然也没有以必需的精确性来防止一切的紊乱或混淆。这种不规则性也许决不至于大到可以毁灭任何族类;但常常足以使个体陷于毁灭和不幸。”[1]65
综言之,在《自然宗教对话录》中,休谟透过第美亚、斐罗和克瑞安提斯的对话,对于“自然宗教”的两大说法(“设计论”和“神义论”)提出严厉的批判,指出从合理性的角度来看,“自然宗教”并不能恰当地说出“宗教”的特性,其中最重要的是并未能合理性地描述“上帝”的属性。如此,从哲学思考的角度来看,又应该如何看待“宗教”呢?
四、休谟对“真正宗教”的论述
休谟在《自然宗教对话录》中是反对宗教信仰吗?艾尔指出:“他在许多方面展开了反对宗教信念的运动,但是他最希望的,是保持哲学不像神学那样,陷入 ‘放肆的幻想和假设’的泥坑之中,我们已经看到,他不是一个始终如一的典范,但至少在他的自然主义方面他是坚定的:他坚持每一门科学都要札根于经验。”[3]162休谟在《自然宗教对话录》中透过斐罗和克瑞安提斯在第十二篇的说话,表明了对于“宗教”或“设计论”的肯定,即他对“自然宗教”的质疑主要在于对“上帝”属性的描述,他自己则提出了“真正宗教”的说法。
休谟透过一直抱持怀疑主义的斐罗口中说:“最疏忽,最愚笨的思想家都随处可以体会到一个目的、一个意向、一个设计;没有人能在荒谬的理论系统中硬起心肠,在一切时候都对于目的、意向、设计加以摈斥的。自然不作徒劳无益的事是在一切学派中已经成立的一条公则,这条公则仅仅是根据对于自然的作品的观察而得,没有任何宗教上的目的;由于对这条公则的真理的强固的信心,一个解剖学家在他看到一个新的器官或管道时,一定要同时发现它的用处和目的,否则决不会满意的。哥白尼系统的一个伟大的基础是这条公则,即是,自然用最简便的方法而活动,并选择最适当的手段来完成任何目的;天文学家常常不知不觉地为宗教和虔敬安设下这个有力的基础。”[1]69即是说,斐罗的说话反映对“设计论”的质疑主要在于依此而论述的“上帝”之属性,如“神人相似论”、“神义论”等,除此以外,他反而是相信于“宗教”的,斐罗明确地说:“由于我对于真正宗教的虔敬,也就增加了我对于通俗迷信的厌恶;我承认,我是特别乐于对这样的原则有时穷究到使它们显为荒谬,有时穷究到使它们显示为不虔敬。你知道,所有迷信的人,虽然他们厌恶不虔敬更甚于厌恶荒谬,却通常是同时触犯这两种罪过的。”[1]72至此,斐罗为休谟提出了“真正宗教”(True Religion)的说法,甚至乎,克里按提斯也说:“宗教,不管是怎么坏的,总比根本没有宗教的好。”[1]72换言之,休谟并不是反对“宗教”的,不过,究竟他所谓的“真正宗教”是甚么呢?
休谟的“真正宗教”主要可从社会或道德的功能与哲学思辩两方面而说。
从社会社会或道德的功能来说,休谟透过克瑞安提斯的口说出的,他说:“宗教的正当职务在于规范人心,使人的行为人道化,灌输节制、秩序和服从的精神;由于它的作用是潜移默化,只在于加强道德与正义的动机,它就有被忽略以及和这些其他动机混淆的危险。当它自己独立一格,作为一个独立原则来控制人类,那么它就离开了它的正当范围,而只变成内乱或野心的掩护了。”[1]73即是说,休谟认同的“真正宗教”是具有社会或道德上的功能的。不过,斐罗对于这种功能化的“真正宗教”则提出迷信与狂热分子的反例作出了质疑,克瑞安提斯则为“真正宗教”提出了三个步骤的功能说明:
第一,“真正宗教”在理性及情感上都深具慰藉的作用,他说:“(按:宗教)这是生活中主要的、唯一巨大的慰藉;又是我们在所有逆运袭击中的主要的支持。人类想象力所能提出的最合意的想法是纯正的有神论的想法,它将我们看作一位全善、全知、全能的‘存在’的作品;他创造我们来获致幸福,他既在我们身上栽植了无量的向善的欲望,将会把我们的存在延长到永恒,把我们转移到无数的不同境地中去,藉以满足那些欲望,并使我们有完全而持久的幸福。我们所能想象到的仅次于这样一个‘存在’自身的(假如容许这种比较的话)最幸福的命运,就是在他的保护和庇佑之下的命运。”[1]75-76
第二,“真正宗教”特别能激动个人的情绪而作出行动,他说:“宗教中有恐惧,也有希望;因为这两种情绪,在不同的时候,同样激动人心;每一种情绪都构成一种适合于它自身的神性。但当人在心情快乐时,他适宜于做事情,交朋友,或从事于任何种类的娱乐;他自然而然地专心去做这些事情,而丝毫不想起宗教。在悲伤和丧气之时,他只好默想着不可见的未来世界的恐怖,让他自己更深地陷入苦难之中。的确,他以这种方式把宗教的看法深深印入他的思想和想象中之后,也可能产生一种健康或景况的改变,会恢复他的好心情,引起他对于未来欢乐的期望,使他走到快乐与得意的另一极端。但我们仍然必须承认,由于恐惧是宗教的基本原则,所以它是在宗教中占主要地位的情绪,只容许快乐的断续的出现。”[1]76
第三,“真正宗教”是哲学思辩式的,如此,它才可以拒绝那些迷信和狂热分子。他说:“塞内卡说,理解上帝也就等于是礼拜上帝。所有其他的礼拜实在都是荒谬的、迷信的、甚至是不虔敬的。所有其他的礼拜都将他降到爱好央求、恳求、献礼和阿谀的人类的低级情况。而这种“不敬”还是迷信所犯的罪恶中之最轻微者。通常,迷信把神贬到远低于人类情况之下;视他为一个反复无常的魔鬼,无理性地、无人地道施展它的威力!假如神真要见罪于他所创造的顽愚的凡人的罪恶和愚蠢,那么最通俗的迷信的信徒的命运就当会是十分恶劣的了。那么,也就没有人值得他的恩宠,只有很少的几个哲学的有神论者,他们对于他的神圣完善性,抱有或努力设法抱有适当的概念:配得上神的慈恩和厚爱的人们只是哲学上的怀疑主义者,这也几乎是同等罕有的一派人,他们由于自然地怀疑自己的能力,对于如此崇高、如此非常的一些论题,一概采取或致力于采取悬而不决的态度。”[1]77换言之,“真正宗教”乃是一种以社会或道德上的功能化来看待个人内在的宗教倾向的思想,这种思想的内在形式是从哲学思辩的角度来论述,主要的内容则是从社会或道德的功能作论述。
从哲学思辩来说,“真正宗教”也是一种哲学思想。休谟透过斐罗而说:“假如自然神学的全部,像某些人所似乎主张的一样,能够包括在一个简单的,不过是有些含糊的,或至少是界限不明确的命题之内,这命题是,宇宙中秩序的因或诸因与人类理智可能有些微的相似;假如这个命题不能加以扩大,加以变动,也不能加以更具体的解释;假如它并不提出足以影响人生的推论,又不能作为任何行为或禁戒的根据;假如这个不完全的模拟不能超出以人类理智为对象之外;不能以任何可能的样子推至于心灵的其他性质;假如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最善于探究的,最善于深思的,最有宗教信仰的人,除了每当这个命题出现时,即予以明白的哲学的认可,并相信这个命题所藉以建立的论证胜过对于它的反驳以外,他还能做些什么呢?诚然,对象的伟大性会自然地引起某种惊奇,它的晦暗性会引起某种伤感,也会引起某种对于人类理性的蔑视,因为人类理性对于如此非常而如此庄严的一个问题不能抬予更满意的解答。”[1]77
综言之,在《自然宗教对话录》中,休谟提出的“真正宗教”并不是一种具有教义内容的“宗教”,它是别于“自然宗教”的思考形式,而从道德或社会功能上看待个人内在“宗教”倾向的“真正宗教”。高策先生曾指出:“休谟的‘真正宗教’包含以下三个方面要素:(1)理智上承认‘一个有些含糊的,界限不明确的命题“上帝是存在”的’;(2)这个上帝并非通常意义的上帝;(3)根据(1)和(2),可知真正的宗教除了使人免于迷信和狂热之外,对于人类行为没有任何影响。”[4]如此,休谟的宗教思想可以说是没有宗教内容的“宗教”。
五、结论:从“终极关怀”看休谟的“真正宗教”
基督教神学家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又译田立克,1886-1965)对“宗教”提出了一个深层的意义解释:“终极关怀”,其言:“宗教是人类精神生活所有机能的基础,它居于人类精神整体中的深层。‘深层’一词是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是,宗教指向人类精神生活的终极、无限的、无条件的一面。宗教,就这个词的最广泛和最根本的意义而言,是指一种终极的关怀。”[5]7-8又说:“宗教是一个被终极关怀抓住的存有状态。此终极关怀限制所有其余关怀为初步而非终极,而其本身包含了对我们生命意义的问题之答案。”[6]3换言之,“宗教”就是对于人类的存在、意义、疏离和局限性等问题作出一个终极性的关怀,作为“终极关怀”的“宗教”并不局限于生命的某个范畴,如知性、感性、德感或美感等层面,“宗教”即成为渗透人类生命每个部分,延伸至人类的灵性深处,成为人类灵性生命的依据。区建铭先生更从“神圣”的层面而说“终极关怀”,他指出:“‘终极关怀’关乎人与神圣(holy)的关系,因此,每一个宗教经历都是神圣的,而所有宗教都指涉神圣。甚么是神圣?神圣的特质是甚么?若根据奥托(Rudolf Otto)的现象理念,我们可以作出以下结论:第一,神圣不是属于这个世界,但它是能够被世界所接触的。……第二,神圣呈现会产生一些禁忌的特质。……第三,神圣的呈现会带出神秘的特质,而这些特质恰恰表明人类世俗理性的方法是不能接近它的。……第四,虽然神圣不能用世俗方法来接触,但它是世人永恒的关怀。”[7]从“神圣”的特质来看“终极关怀”,即人类的内在宗教倾向,实即是精神层面上对终极(神圣)的意义追求。
依“终极关怀”说“宗教”的意义来看,休谟在《自然宗教对话录》所说的“真正宗教”则只能算是一半的“宗教”。休谟的“真正宗教”观念正面肯定人有内在的宗教倾向,即对于人的精神层面的的存在状态具有一定的理解;然而,休谟对于“真正宗教”的肯定却建基于社会的或道德的功能上,容易造成宗教的社会化或道德化的现象,即非从宗教的特质来肯定宗教存在的意义,而仅从社会(包括从道德的规范性)功能来确定宗教的存在价值,这是将宗教当作工具化的倾向。从这一角度来看,休谟的“真正宗教”并未能掌握成为一个当代较能承认的真正的宗教。可是,从《自然宗教对话录》的论述脉络来看,休谟所讨论的正是不从宗教信仰的立场来说“宗教”,乃是从哲学反省性思考的角度来辩破“自然宗教(神学)”来表述的“拟似”哲学式或合理性的思想。换言之,休谟所提出的“真正宗教”乃是从哲学思考来肯定“宗教”的价值,这样,其以社会的或道德的功能来肯定“宗教”仍是可理解的。
[参 考 文 献]
[1] 休谟.自然宗教对话录[M].陈修斋,曹棉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2] D. O'Connor, Hume on Religion, London : Taylor & Francis-Library, 2001, P.24.
[3] 艾尔.《休谟》[M].曾扶星、郑莹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157-158.
[4] 高策.休谟《自然宗教对话录》中的宗教思想研究[D],河南大学硕士论文,2007,12.
[5] 保罗.蒂利希.《文化神学》[M].陈新权、王平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7-8.
[6] 保罗.蒂利希.《基督宗教与世界宗教相遇》[M]// 陈家富.蒂利希与汉语神学,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6.
[7] 区建铭.蒂利希的“终极关怀”理念对比较神学的贡献[M]// 载于陈家富编《蒂利希与汉语神学》,P.3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