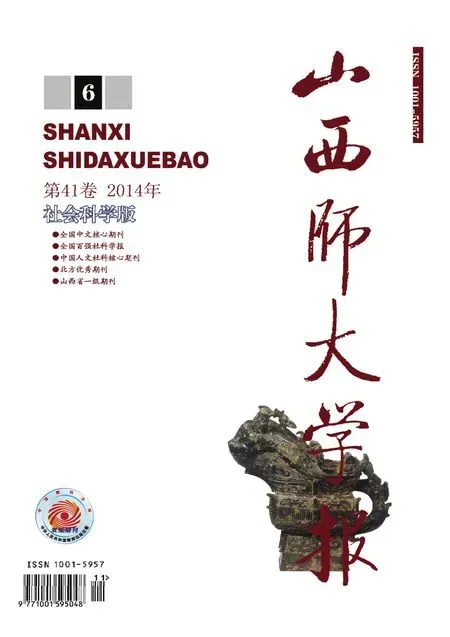“气运”与“气韵”再辨析
——兼评张锡坤“气韵”说
管 才 君
(扬州大学 文学院, 江苏 扬州 225002)
对于气运与气韵的关系,有学者提出通假一说,引起颇多争议:“中古时人之审美中气运生动的‘运’字,和文艺审美中气韵生动的‘韵’字曾一度相通”[1]27,近人张锡坤也据此考证气运即气韵。他从音韵学角度考订在秦汉时期“韵”和“运”可以通假:“实际上气韵源于气运,是气运从哲学到文艺审美的延伸。易学中的阴阳气化宇宙论是其哲学基础,气韵就是艺术作品中气之运化节奏和谐的显现”[2],并以姚最《续画品》“至于气运精灵,未穷生动之致”之语为证。张锡坤将气运考订为气韵,气韵即气的运行化感或运行化感的气,所谓“气韵生动”乃是说一件艺术品要“生动”起来和“活”起来,或者说由于气的运行才使得作品生动起来。笔者认为,通假说有其合理之处,先秦两汉无“韵”字,以“运”代“韵”确偶有可能,但将气韵直接等同于气运,进而将其意义仅仅归结为气之运化节奏和谐,则完全忽视了气韵深厚的美学意蕴,明显过于狭隘,本文对此进一步加以辨析。
一、“运”与“韵”
《说文解字》:“运(運):移徙也。从辵,軍声。”其本义为运行、运转、转动。又《广雅·释诂》:“转也。”《方言》:“日运为躔,月运为逡。”注:“犹行也。”《庄子·逍遥游》:“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简文注:“运,徙也。”《庄子·天道》:“天道运而无所积,故万物成”。成玄英疏:“运,动也,转也。”《汉语大词典》对运的解释多达16条,其中主要是运转、移动以及引申出的使用、运载、运用、世运等。词典列举了运的四种通假情况:一通“煇(暈)”,日月周围的光圈;二通“暈”,眩晕、昏厥;三通“渾”,浑浊;四通“鄆”,古地名。[3]1901未见与“韵”通假的说法。《广雅》:“韵,和也。”指声音的节奏和谐,有律动,旋律之意。先秦文献无“韵”字,汉代碑文、铜器铭文中也无“韵”。汉末蔡邕《蔡中郎集》外集三《弹琴赋》:“繁弦既抑,雅韵乃扬。”始见“韵”字。曹植《白鹤赋》:“聆雅琴之清韵。”陆机《演连珠》:“赴曲之音,洪细入韵。”嵇康《琴赋》:“改韵易调,奇弄乃发。”《晋书·挚虞传》:“施之金石,则音韵和谐;措之规矩,则器用合宜。”均是指抑扬顿挫的和谐音律、旋律。刘勰《文心雕龙·声律》:“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即指声音的旋律、韵致。入晋,“韵”演变为品藻人物的“风韵”、“风神”,凡人物的言辞答问、动作举止、音容笑貌所呈现的风度意致,动辄以“韵”相称,《世说新语》多有记载,《赏誉》:“庾公曰:‘卫风韵虽不及卿诸人,倾倒处亦不近。’孙遂沐浴此言。”《品藻》:“頠性弘方,爱乔之有高韵。”《任诞》:“阮浑长成,风气韵度似父,亦欲作达。”从中可知,截至魏晋,“韵”的两重含义并立,并成为一个重要的审美范畴,或指音乐性的和谐律动,或指人物形体或动作的神态风韵。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知,“运”与“韵”文字起源不同,历史跨度巨大,“运”的意义比较单一,未作为审美范畴出现并使用,而“韵”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开始作为审美范畴广泛使用,“韵”的内涵与使用范围远远超过“运”。因此,“运” 与“韵”不能等而视之。
二、“气运”与“气韵”
气运与气韵都以气为核心,吸收另一个词语或审美范畴,构成一个新的复合型气之范畴。气运的意义单一,而气韵内蕴丰富,气韵共生,气韵的意义远大于气运。气运较早出现在东汉王符的《潜夫论·本训》:“气运感动,亦诚大矣,变化之为,何物不能。”气运乃元气的运行变化。三国曹植《节游赋》:“感气运之和顺,乐时泽之有成。”这里的气运指节候的流转变化。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伤逝》:“戴公见林法师墓,曰:‘德音未远,而拱木已积;冀神理绵绵,不与气运俱尽耳。’”宋沈括《梦溪笔谈·象数》:“小则人之众疾,亦随气运盛衰。”这里的气运都可解释为气数,命运。需要指出的是,在历代文艺品评中,出现过少数使用气运的情况,明汪砢玉《珊瑚网》:“文章关气运自是千古定论,方在气运中,人自不觉,及异代观之,毫发不能掩。”清倪涛《六艺之一録》:“至元初,士大夫多学颜书,虽刻鹄不成尚可类鹜,而宋末知张之谬者乃多尚欧,率更书纤弱,仅如编苇,亦气运使然耶。”这里的气运可理解为时运或时代风气。唐张怀瓘《书断》:“流芳液于笔端,忽飞腾而光赫,或体殊而势接,若双树之交叶,或区分而气运,似两井之通泉。”元盛熙明《法书考》:“郭若虚云:‘气运本乎游心,神采生于用笔。’”这里的气运均为生气运行,即生命之气的运行贯通。
气韵作为审美范畴第一次出现是南朝齐谢赫的《古画品录》:“六法者何?一气韵生动是也。”其后,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也讲气韵:“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蕴思含毫,游心内运,放言落纸,气韵天成。”这两论一说绘画,一说文章,使气韵作为全新的审美范畴在魏晋南北朝勃兴。至唐,率先将气韵用于艺术品评的是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气韵被赋予了更丰富的美学意义,并作为审美范畴大量使用,对后世影响深远。气韵的美学意蕴,主要体现为形神的融合一体和生命节奏韵律两者的有机统一。
首先,气韵是形神的融合一体。陈传席先生认为,“韵”是“一个人的形体(包括面容)所显露出的神态、风姿、仪致、气质等等精神状态的美”[4]165—166;徐复观也说:“它指的是一个人的情调、个性,有清远、通达、放旷之美,而这种美是流注于人的形相之间,从形相中可以看得出来的。把这种神形相融的韵,在绘画上表现出来,这即是气韵的韵。”[5]152叶朗说:“‘气韵’的‘韵’是从当时的人物品藻中所引过来的概念,是就人物形象所表现的个性、情调而言的。”[6]220因此,“韵”既关涉人物内在的才情、智慧和精神品质,也关涉人物外在的仪容风貌、态度举止,“韵”内含形与神,是两者的高度融合与统一。
许多学者都将气韵释为传神。杨维祯在《图绘宝鉴》序中则直接将传神等同于“气韵生动”:“传神者,气韵生动是也。”今之学者也多承认气韵即“传神”。葛路说:“气韵生动……要求表现出生动的精神和性格特征,尤其以笔墨气韵强调精神气质”[7]30。叶朗也认为:“谢赫的‘气韵生动’的命题,同顾恺之‘传神写照’的命题一样,包含有老子美学的影响。”[6]223袁济喜说:“所谓‘气韵生动’就是要求在人物的外形描绘中,表现出生动的神气韵润,这同顾恺之‘以形传神’说大致相同。”[8]32这些观点有合理性,但都较片面。徐复观则把气韵规定为“形神合一的‘风姿神貌’”[5]152,他认为,与顾恺之的“以形传神”不同,谢赫的“气韵生动,正是传神思想的精密化”[5]153。关于这一点,何楚雄先生有独到的看法,“谢赫并非完全不重视对象内在精神的表现,只是主张其内在精神依附于生动的外在形姿显现罢了。……谢赫绘画对象的美学追求,是以逼真的形体动态为前提的”,“他特别强调形似之妙,认为形妙然后传神韵。形之生动是传对象真精神的载体”[9]69—70。姚最评谢赫云:“写貌人物,不俟对看。所须一览,便工操笔。点刷研精,意在切似。目想毫发,皆无遗失。丽服靓妆,随时变改。直眉曲鬓,与世事新。别体细微,多自赫始。”可见其刻画人物细致精微,两者的差异很明显。在顾恺之看来,为了传神,是可以对原型加增删或美化的,为了表现裴楷的“朗俊有识”,可在其颊上“益三毛”。顾恺之为了传神不惜忽视和改变形体风貌,而谢赫的传神重在形体形态的生动刻画和精雕细琢,由此可见,气韵确是传神,但这种传神不是简单的“以形传神”,而是“形神兼备”,这也正是由于“韵”所强调的人物形体动作的形神高度统一的风韵所形成。
其次,气韵也是生命的节奏韵律。气韵的节奏性、韵律性是“气”和“韵”的内在固有特性。中华民族最根本的宇宙观认为,气分阴阳,宇宙才能创化,继而显示出节奏、旋律和乐感,“阴阳二气化生万物,万物皆禀天地之气以生,一切物体可以说是一种‘气积’。这生生不已的阴阳二气织成一种有节奏的生命”[10]131。在宗白华的眼中,阴阳二气之和谐运动创造了宇宙万物,同时也创造了我们节奏化、音乐化的生命和心灵,而中国的艺术更是直取气之生命节奏:“一片明暗的节奏表象着全幅宇宙的氤氲的气韵,正符合中国心灵蓬松潇洒的意境。故中国画的境界似乎主观而实为一片客观的全整宇宙,和中国哲学及其他精神方面一样。”[10]133在他看来,气韵的节奏性就来自于“气”与“韵”的节奏性,气韵生动就是要表现作品生命之气生生不息的流动之美。“气韵,就是宇宙中鼓动万物的‘气’之节奏、和谐。绘画有气韵,就能给欣赏者一种音乐感。……中国的建筑、园林、雕塑中都潜伏着音乐感——即所谓‘韵’。”[10]51—52“气”是一种运动的生命力或生命力的运动,是有节奏、韵律的,是流动的,“韵”本身就是指具有音乐性的音律、旋律,其自身的节奏和韵律是一种与生俱有的特质,气韵的结合必然就会体现出一种运动的规律和节奏所产生的美感或韵律感。因此,宗白华断言:“中国画的主题‘气韵生动’,就是‘生命的节奏’或是‘有节奏的生命’。”[10]132这一见解非常精到,中国的艺术无不符合阴阳变化之道,具有鲜明的生命节奏感、韵律感,体现为生生不息、创化流行之气韵生动。
三、结语
笔者认为,张锡坤教授将“韵”与“运”相等同,进而将气韵的意蕴简单化为气之运化节奏和谐,是片面的。“气”作为一个传统的哲学范畴,其本身不仅具有生命性、生态性、整体性、概括性,还具有笼统性、模糊性、弥散性、流动性、节奏性、创变性。“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认为世界万物的产生是由阴阳二气相互作用;《庄子·则阳》:“阴阳者,气之大者也。”《周易·系辞上》:“一阴一阳谓之道。”气本身就具有节奏和谐性,气运的节奏和谐实际上来自于气,将气运归于节奏和谐,进而推演出气韵之节奏和谐,本身就是同义反复。其次,此种考据并无多大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价值。气本身就是变动不居、运动不止的一个生命之体,其涵盖面非常之广,已包含气运所有的方面,气运的范围不可能超越气。由气运考订气韵,并将其意义联系起来,只会将气韵的内涵简单化,最多只能释气,而“韵”的真正意义却在不知不觉中被忽视和消解。笔者以为,先秦两汉无“韵”字,“运”与“韵”如通假,其意义也仅限于表述节奏韵律,但汉末“韵”字出现,且一出现即具有强烈的审美意味,至魏晋,“韵”涉及到人物的神态风韵,已经成为重要的审美范畴广泛使用,两者意义差异非常显著,此时再以通假论之,则歧义之处难以自圆其说。谢赫提出“气韵生动”之后,气韵亦开始作为独立的审美范畴运用于艺术品评,气运与气韵的意蕴截然区分,使用范围明显不同,更不能用通假之说简单比附。
总之,气运表示元气运行、节候流转、气数命运、时代风气、生气运变等,极少作为审美范畴使用。气韵源自绘画品评,一出现即为复合型审美范畴,既是形神的高度统一,也是生命的节奏和谐,有着丰富的美学内蕴。两者历史来源不同,意义差别明显,地位差距巨大,不能以通假之名将其完全等同。
[1] 于民.气化谐和[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2] 张锡坤.气韵范畴考辨[J].中国社会科学,2000,(2).
[3] 罗竹风.汉语大词典:第10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
[4] 陈传席.六朝画论研究[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85.
[5]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
[6] 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7] 葛路.中国古代绘画理论发展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8] 袁济喜.六朝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9] 何楚雄.中国画论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10] 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