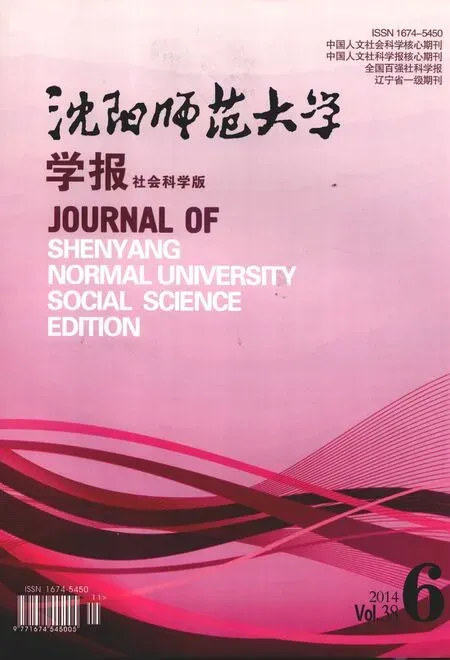文化·消费·媒介——当代西方娱乐文化研究谱系考
臧 娜,许学宁
(1.沈阳师范大学 戏剧艺术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4;2.沈阳广播电视大学 对外合作学院,辽宁 沈阳 110003)
从网络文学创作领域涌起的玄幻化书写热潮,到“开心麻花”打出的“为人民娱乐服务”戏剧创作旗帜,直至呈燎原之势的平民选秀之火,当代中国文艺的娱乐功能维度在诸多娱乐化症候的推动下日益凸显。然而,在文化全球化传播的历史语境下,要拨开浮华的娱乐表象,探寻当代中国文艺娱乐化之变的根本动因,单凭本土理论资源难以进行深入其里的理论阐发。资本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文化取向、传播媒介、消费观念等方面的同一化变革,悉心审视西方理论资源,无疑会为学界深入理解当代中国文艺的娱乐化之变提供重要的理论参照。
西方娱乐文化研究的理论进程开启较早,韦尔施、赫伊津哈、列菲伏尔、德勒兹、鲍曼等众多学者都曾经在理论研究中论及“娱乐”相关论题,并且在长期的思想对话与交融中,形成了文化研究、消费社会研究、媒介文化研究等几个较为清晰的娱乐文化研究理论向度。
一、文化研究中的快感与政治
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学术话语始于20世纪50年代英国的伯明翰学派,代表人物霍加特和威廉斯在著作《文化之用》(1958)及《文化与社会》(1958)中,分别表达了自己对于大众文化的理解与认同。始建于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也是文化研究领域的重要力量,与伯明翰学派对于大众文化的认同立场不同,该学派的文化研究建立在“批判理论”基础上,其大众文化理论及大众传播研究建构起了文化研究的初期模式。
从社会批判的理论视野出发,法兰克福学派始终致力于将“快感”问题与“政治无意识”相互勾连。主要代表人物阿多诺就曾经在《论流行音乐》一文中揭示了“标准化”特质在流行音乐生产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流行音乐的整个结构就是标准化了的,即使为了克服标准化所作的尝试也是如此。从最基本的到最特殊的特征,标准化无所不在”[1]197。在此基础上,阿多诺又深入剖析了音乐产品接受者置身其中的文化背景及其对艺术接受者产生的心理影响,他认为,“心神涣散是与现存的生产方式相关,与大众必须直接或间接遵从的合理化、机械化的劳动程序相关。这种生产模式能够导致对于失业、收入流失以及战争的恐惧与焦虑,这与娱乐有着‘非生产性的’关联。或者说,消遣与全神贯注根本没有关系,人们需要的是娱乐”[1]205。可见,在对于现实世界的快乐逃逸中,大众陷入程序化的娱乐经济“逻各斯”中而不自知,阿多诺的此种论断事实上正代表了他对文化工业本质特征的理论判断和价值立场。
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者们大多从“政治无意识”的理论视角出发,以批判性和政治性的理论姿态介入到社会政治运动中来,与这一理论旨趣具有家族相似性特征的还有美国文化批评学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詹姆逊延续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思路,并将其推进到后现代批判的理论当中。詹姆逊的批判理论研究始于对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商品化”文化特质的深刻体验中,大众沉浸在由电视、广告、录相等文化商品汇聚成的视像化海洋中,成为散在的、表面化和去中心化的零散主体,体现了后现代精神在这一时代所占据的主导地位。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詹姆逊在指认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后现代精神特质的同时,还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辩证法思想,对其进行了肯定性思考。詹姆逊精神视域中的后现代主义和大众文化,往往给人一种欣喜若狂的欣快体验,这事实上“提供了一种富于启发性的美学模式”[2]180。他曾经对一首名为《中国》的诗歌进行语意剖析,“我称之为精神分裂性的(句子)断裂或文字所表现出的方式,尤其是当其被概括为一种文化风格时,不再享有与病态内容,即我们所联想到的精神分裂这样的术语的关系,而是能被用于更欢快的强度上,用在那恰恰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替代了焦虑和疏离这种旧感觉的欣快症上”[2]184。对于精神分裂性文本背后蕴含的独特欣快体验的揭示,体现了詹姆逊对后现代文化文本进行辩证考察的理论路径。
然而,詹姆逊对快感问题的思考并没有驻足于美学层面,而是从“政治无意识”视角出发将其拓展至意识形态领域。从阿多诺在激进学生运动中郁郁而终,到德勒兹·伽塔利哲学借“欲望机器”对资本主义所做的“精神分裂分析”,詹姆逊欣喜地看到了“快感”在“政治无意识”层面的积极意义,“一个具体的快感,一个肉体潜在的具体的享受——如果要继续存在,如果要真正具有政治性,如果要避免自鸣得意的享乐主义——它有权必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并且能够作为整个社会关系转变的一种形象”[2]150。如果说“阿多诺们”倾向于从资本理性层面出发批判性地审视娱乐经济“逻各斯”中的快感,那么詹姆逊则触摸到了快感的意识形态向度及其潜在的颠覆性特质,这无疑是对传统理论的辩证延展。
二、消费主义视域中的“交换”与“诱惑”
法国著名哲学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提出的消费社会理论为当代西方娱乐文化研究贡献了宝贵的理论资源,从“象征性交换”到“经济性交换”直至“诱惑”,不但推动了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理论走向纵深,而且历时性地揭开了“诱惑”的神秘面纱,揭示了“诱惑”在媒介普遍化的消费主义语境中所处的尴尬境况。
“象征性交换”融合了莫斯礼物交换思想和巴塔耶“耗费”经济学的理论主张,在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理论中居于核心地位。莫斯礼物交换思想(《论礼物》,1925)对原始部落交换制度进行人类学考察,发现了一种被称为“礼物”的交换方式。在原始社会,将某物馈赠给某人这一事件就是呈现自我的过程,而物自身的出场正蕴藏了某种神性力量,与“经济性交换”无涉。莫斯认为,功利主义的价值交换是晚近社会发展的产物,“在最具伊壁鸠鲁主义色彩的各种古代道德中,人们追求的是善和快乐,而不是物质利益”[3]。莫斯对于象征交换的思考极大地影响到了巴塔耶,他在《耗费的观念》(1933)一文中提出,“耗费”与“奉献”是人类获得自身意义的一种本能需要。巴塔耶于1945-1955年间形成了《有用性的界限》《被诅咒的部分》和《黑格尔、死亡与献祭》等几部著作,对莫斯理论进行哲学化、政治化改良,基本完成了对于耗费经济学逻辑架构的理论建设。
莫斯和巴塔耶对于“交换”行为与“耗费”观念的理论阐发开启了鲍德里亚关于“象征性交换”的思想旅程。与“经济性交换”不同,鲍德里亚的“象征性交换”仅仅在“象征性”意义上展开,它超越了那种由政治经济学逻辑设计出来经济交换体系,具有独特的本真性内涵,即“在释放、耗费、奉献、挥霍和象征的过程中,人的感性本能得以释放,它能够破除政治经济学中的拜物教,使人们回归到本真的交往方式中来”[4]。在此基础上,鲍德里亚又展开了对于资本主义体系和消费理性的批判式审视,借助莫斯和巴塔耶对于“交换”行为与“耗费”观念的理论思考,鲍德里亚看到消费符号的生产与流通事实上是将特定的交换价值赋予客体对象,而原本蕴含在物品象征性价值之中的本真内涵则被遮蔽了。
从《符号政治经济学》《生产之镜》,到鲍德里亚系统性理论生涯的尾声之作《论诱惑》,这种乌托邦式的理论构想贯穿始终。在《论诱惑》中,鲍德里亚延续了“莫斯、巴塔耶”观念体系的批判精神,借助“诱惑”概念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逻各斯”进行了反思与颠覆,从而深化了以往对于“象征性交换”本真特质的理论思考。鲍德里亚首先将对“诱惑”的思考置于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时代,此间占据主导地位的女性特质为“诱惑”概念赋予了隐秘与挑战的深度意味,并以表象游戏方式传递着某种模糊的非确定性本质内涵,而正是这种混沌的状态具有强大的诱惑力量,消解了男女两性间的二元对立关系,使女性气质自身获得主体性表达,进而实现了对既有理性秩序的消解。与此相关,象征性交换中包蕴的“可逆性”自我呈现意味,则通过前现代性反生产交换方式续写了“诱惑”的本质内涵,通过象征性交换,人的感性本能得以释放,展现出“诱惑”特有的非确定性魅力,实现了对于确定性、线性、预设性生产秩序的超越,体现了鲍德里亚批判生产秩序与资本理性的价值立场。
在此基础上,鲍德里亚进一步将目光投向当下这个媒介普遍化的消费社会,多媒体技术构造出一派超真实“表象”,“表象的游戏”这一“诱惑”所崇尚的前现代呈现方式,在媒介文化时代得到充分实现。
然而,媒介文化时代的“诱惑”不同于原始社会中的“诱惑”,在媒介技术营造的“超真实”幻境中,获得新生的“诱惑”逐步抛却了隐秘的本真性内涵,转而与政治理性、资本理性、技术理性相勾连,成为消费主义诱发人类感性本能、满足快感体验的社会运作模式。鲍氏描绘出了古老“诱惑”在当代社会文化语域中的尴尬姿态,从而推动西方学界对消费社会中的媒介文化进行深度理论挖掘。
三、麦克卢汉媒介文化思想的理论延展
加拿大著名媒介理论家麦克卢汉从媒介文化视角出发的理论研究,是当代西方娱乐文化研究的重要理论向度。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对学界影响深远,鲍德里亚基于后现代消费社会提出的“内爆”概念就是对麦克卢汉“内爆”理论的一种延展。麦克卢汉曾在《理解媒介》中提出了“内爆”概念,指出在电力技术时代,人的感官功能由于电力技术的发展而得到强化,从而在技术性“时空压缩”的过程中产生内爆,由此表达了他对于通向自由“地球村”媒介景观的乐观态度。而鲍德里亚认为,后现代消费社会中,大众传播媒介营造出一派拟像仿真世界,由符号构筑的超真实存在占据主导地位,拟真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界限逐步破除,这正是后现代消费社会的“内爆”。以此为基础,鲍德里亚展开了“内爆”与“诱惑”的间性思考,他指出诱惑所崇尚的“表象游戏”及其蕴含的神秘象征意蕴,在后现代超真实媒介视界中日益蜕变为一种更为充分的现实景观。如黄色淫秽的产业化生产与传播,“给性别空间补充一个维度,使该空间比真实的空间更加真实”[5]46,而在这场超真实色情展演中,真正的性爱和它无限美好的意蕴死去了!“高保真音乐”的凭借多维度的技术拟真效果,使人们沉浸在由“四维音乐”构筑的超真实听觉空间,第四听觉维度的技术性添加虽然营造出几近完美的听觉效果,但音乐思维和想象空间却被大幅度压缩,因为“它剥夺了你任何细微的分析性感知,而这种感知本该是音乐的魅力所在”[5]49。这不仅体现了鲍氏对于后现代媒介哲学的深刻领悟,也彰显了鲍德里亚“对布尔乔亚社会中新的拟真形式(后现代)认识的深化”[6]8。
美国著名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对“娱乐至死”的深刻阐述,也体现出与“超真实”和“诱惑”相似的媒介文化价值取向。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透彻剖析了电子媒介(主要是电视)影响下的泛娱乐化境况。他以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即讯息”理论命题为基础,从传播学层面指出,《圣经》“第二诫”中提出的“不可为自己雕刻雕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7]11,是为了防止习惯于图像性思维的以色列人继续膜拜某个抽象的神灵,阻止文化中出现新的上帝。波兹曼认为“某个文化中交流的媒介对于这个文化精神重心和物质重心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更具创造性的是,两部著名的反乌托邦文学作品《一九八四》(乔治·奥威尔,1949)和《美丽新世界》(奥尔德斯·赫胥黎,1932)作为核心性文本共同出现在《娱乐至死》的开篇,作者在对其进行间性解读的过程中,提出了极具洞见的思想主张,即“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这本书想告诉大家的是,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而不是奥威尔的预言”[7]前言2。作为麦克卢汉媒介文化理论的追随者,波兹曼并没有延续前者的乐观主义价值取向,而是猛烈抨击了电子媒介对于社会公共生活领域的侵蚀,这种饱含人文主义精神和道德关怀的文化立场在《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童年的消逝》等著作中亦俯拾即是。
鲍德里亚与波兹曼虽然同样触碰到了麦克卢汉媒介文化思想,但与其乐观主义态度迥异,鲍德里亚和波兹曼从不同的视角切入理论研究,共同表达了他们对于迅速发展的当代媒介文化的反思态度,这无疑为媒介文化快速崛起的当代中国社会文化语域提供了重要的价值论尺度,引导学界对文艺娱乐化问题作出更具人文主义色彩的价值判断。
结语
不论是在文化研究视域下展开的对于快感与政治无意识相互关系的剖析,还是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理论围绕“诱惑”与人类感性本能展开的辩证审视,抑或是鲍德里亚和波兹曼为麦克卢汉媒介文化理论注入的理论反思意识与人文关怀,本文始终致力于从文化、消费和媒介的多元理论向度出发,对当代西方娱乐文化研究的思想路径进行典型性剖析与考察。在当代社会语域中,单纯从文艺本体出发审视文艺娱乐化问题很难得到较为有力的理论阐发,文化、消费、媒介等他律性因素的介入无疑有助于对论题进行深入其里和全方位的理论界定。与此同时,资本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文化取向、传播媒介、消费观念等方面的同一化变革,虽然地域不同,但出现的问题可能具有相似性和共性,西方学界理论资源的介入,无疑会为国内学界深入理解当代中国文艺的娱乐化之变提供重要的理论参照。
[1]Theodor W.Adorno.On Popular Music[G]//John Storey ed.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A Reader.Prentice Hall,1998.
[2]詹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M].王逢振,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3]张一兵.启蒙的自反与幽灵式的在场[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7:106.
[4]臧娜.当代文艺娱乐化问题研究[D].沈阳:辽宁大学,2012:15.
[5]波德里亚.论诱惑[M].张新木,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6]张一兵.诱惑:表面深渊中的后现代意识形态布展——鲍德里亚《论诱惑》的构境论解读[J].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8-9.
[7]波兹曼.娱乐至死[M].章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 王凤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