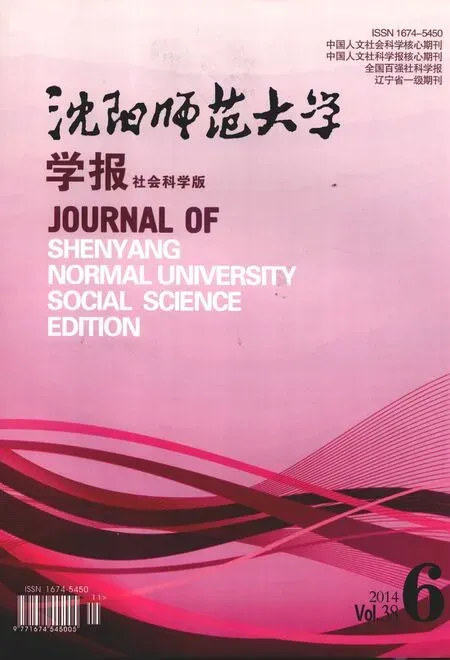当代西藏农户的宗教生活考察——以扎囊县朗色林村、拉孜县柳村为例
秦永章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 100081)
我国农村社会正处于剧烈的转型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着深刻变迁,可以说“变迁的气息弥漫在社会各个层面的社会安排之中”[1]。同我国其他地区一样,目前,西藏地区的各方面也发生着深刻的社会变化,其中包括藏族群众的宗教生活。本文以笔者2012年夏对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区扎囊县朗色林村、日喀则地区拉孜县柳村的入户个案访谈资料为基础,对随着时代和所处社会环境的变迁,西藏农村藏族信教群众的宗教信仰的变化情况做一个初步的考察,以期对人们了解目前西藏农村的宗教生活有所裨益。
一、调查点简况
(一)朗色林村(以下简称A村)
A村现属于山南地区扎囊县扎其乡,在雅鲁藏布江中游南岸的山谷地带,是一个山口洪水冲积形成的宽谷,南面靠山,北面临河(雅鲁藏布江),地势较为平坦。当地平均海拔3620米,属高原温带半干旱季风气候区。冬春多风,气候干燥,雨季降水集中,日照充足,无霜期短。该村主要以从事农业为主,主要农作物有小麦、青稞、土豆等。耕地总面积1828.94亩,人均耕地2.35亩。该村村民均为藏族,截至2011年10月,全村总户数161户,总人口779人,其中男性310人,占总人口的39.8%;女性469人,占总人口的60.2%;在读大学生33人、高中生35人、初中生26人、小学生62人。
(二)柳村(以下简称B村)
B村系日喀则地区中部拉孜县柳乡的一个行政村,系纯藏族村落。在历史上被称为日喀则上部地区,藏语称“堆巴”(Stod Pa)。当地海拔 4100米,气温较低,温差大,日照强烈,干湿明显,冬春季少雨雪多大风。国道318线即中尼(中国——尼泊尔)公路从村内通过。截至2012年6月,全村有262户,1494人,其中男性711人,女性770人,60岁以上老人约60多人。全村共有耕地3348亩,主要农作物为青稞、小麦、豌豆,蔬菜主要为土豆、萝卜等。与A村相比,B村的自然、经济条件不如A村。
二、宗教设施的恢复和重建
历史上,西藏大多数村庄都有其供施的寺院,另有拉康、佛塔、拉则等宗教设施,寺院及宗教上层在乡村具有较高的权威性。1959年,西藏实行民主改革后,包括上层僧侣的西藏三大领主的封建特权被废除,实行政教分离,寺院权威在民众宗教生活中的地位下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西藏同全国其它地区一样,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遭到严重破坏,宗教活动场所及设施受到了严重破坏。“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西藏重新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以前被损毁的宗教活动场所及设施逐渐得到恢复和重建。A、B二村的个案则具体地反映了这一变革过程。
A村村民均信仰藏传佛教,村里有寺庙、“拉康”(即佛堂)、白塔各一座,均系20世纪80年代以后恢复和重建。
寺院名称“桑阿曲郭林”,位于该村东南面的山坡上,现在是一个只有3名僧人的小型寺院。据该寺僧人介绍,该寺建于12世纪初期,系宁玛派寺院。民主改革以前,该寺归属当地著名的朗色林庄园,1959年以后逐渐颓败,僧人被迫还俗,“文革”期间几乎损毁殆尽。1993年,附近村民捐资12万元重建该寺,1996年获准开放。目前,寺院内没有转世活佛。现在该寺的主要建筑是大经堂及护法神殿,二层还设有图书室等。A村信教群众的宗教活动基本上由该寺僧人承担,寺院的主要收入也来自本村群众的供养。
拉康位于村委会南侧的农田中央,内有平房5间,其中一间是用溪水动力转动的转经轮房,一间是供奉佛像的佛堂,另外三间分别是厨房、库房及庙官的宿舍。该拉康供朗色林村3个社共用。据拉康管理人嘎玛老人介绍,该拉康是1982年重建的,以前的拉康在文革期间被毁。由于拉康内的空间狭小,以村落为单位的集体性的宗教活动不多,主要是附近的村民来转经。
白塔(土制的白色佛塔)位于该村的东侧,呈圆钵形,高10米,直径12米左右,白塔周围还设有转经筒,正面设有煨桑炉和经旗杆。该塔于1988年由村民出资兴建。该白塔除供村民们转经使用外,还是本村不少集体活动如望果节的始发地。
B村目前没有寺院。由于该村距离日喀则较近,加之民主改革前,该村系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庄园,因此,即使今天,扎什伦布寺任然是当地村民前去朝拜等宗教活动的主要场所之一。此外,距离B村更近的著名的萨迦寺以及该县的增寺也是当地村民前去朝拜的重要寺院。
B村有小型白塔一座,位于村中央,系该村村民拉巴捐资1万多元于2007年建成。白塔旁边还有一座小型的玛尼转经房,系另一村民出资所建。
紧邻村落的西侧山坡上,设有一个间简易的拉康,山顶上设有一处插满经幡、白墙砌就的“拉则”(即敖包)。据村民说,这两处设施均系20世纪80年代重建,原来此山上就有一个拉康,在民主改革后遭毁。
三、村民日常的宗教生活
A、B二村群众普遍信仰藏传佛教。尽管每个家庭的宗教生活存在差异,但就整体而言表现出很大的相似性,形成了较为固定的家庭宗教活动模式。据调查获知,现在,开春天气转暖以后,当地绝大多数家庭的青壮年男性基本上都去外地打工了。他们在新环境中无法维持原来的宗教活动。家里剩下的多是老人、妇女和孩子(儿童),这些老人和妇女除承担家务活及农事劳作外,还要承担家庭的宗教活动。这些老人日常性的宗教活动主要是诵经、煨桑、点供灯、磕头等。一般而言,上述这些宗教活动由家里年长的女性负责进行,如果年长女性已经去世或不在家,则由年长男性负责宗教仪式。而家里的晚辈和学童对长辈们的诵经、煨桑活动可谓是耳濡目染,却似乎又熟视无睹,除非遇到特殊的事情,一般都较少参与。
(一)诵经。诵经是村中老人们最主要的宗教活动之一。这些老人的每一天以口诵经文开始,又以念诵经文结束。平常他们都是在自家的“却康”(佛堂)一边转“嘛尼”经筒一边诵经。由于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外出务工,这无疑加大了留守在家的老人们从事家务的时间,因此,也有不少老人是一边做家务,一边诵经。大多数老人不识藏文,也不会诵读长篇的经文,所以念诵的经文一般都是简短的“六字真言或“莲花生大师心咒。据调查,每个人诵经的时间长短不一,根据农忙或闲暇程度灵活掌握,但是一般而言,早、晚合在一起,一天至少需要1小时以上。
西藏乡村还有村民们集体一起诵经的“嘛尼会”,当地人称作“嘛尼措巴”。B村的嘛尼会现有成员44人,一般人年龄在50岁以上,其中多是女性,男性只有10人。嘛尼会还设有一名管理者,据说每五年要换一次。藏历每月的八、十、十五、三十日,嘛尼会的成员们都要集中在村内的“嘛呢康”一起诵经。在四月十五日的萨噶达娃节(系释迦牟尼降生、觉悟与圆寂三大纪念日),要连续念诵三天。这些人一般都是上午十点钟去,太阳落山后回家,中午饭如糌粑及奶茶等要自备。村中有人去世或举行特殊法会时,也邀请嘛尼会的成员去村民家诵经,并提供餐饮。诵经结束后,嘛尼会集体会得到100元左右的布施,以及一脸盆的青稞和一块砖茶。
实际上,B村的“嘛尼措巴”是一个以藏传佛教信仰为纽带的民间宗教社团,亦系一种宗教性的地方社会组织,它完全由民众自发组成。虽然该组织相对松散,没有入会和退会仪式,进出自由,也没有正式的规章制度,但该组织无论对藏族村民还是在整个村落都发挥着一定的社会功能。平日里它是老年村民们进行情感交流以及锻炼身体的一个重要途径和手段,而且它在维护宗教信仰、保持传统文化、整合藏族社区等方面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也表现出藏族民间宗教活动的特色,反映出藏区民间宗教生活的丰富性。
(二)煨桑。“煨桑”也是西藏农村村民不可或缺的日常宗教生活之一。在每户藏家的房顶或庭院内设有煨桑用的简易的祭烟炉或专门烧制的陶质祭烟炉。煨桑一般在早晨举行,主要原料是柏树枝、糌粑、酥油、砂糖等物。将柏树枝点燃后,把其他物品放在上面,祭祀诸神。有些人家每天坚持煨桑,有些人家只在重大的节庆日煨桑,据村民说,桑烟袅袅上升天际,就可沟通神、人之间的信息。
(三)朝拜寺院。去寺院、神山朝佛也是一项重要的宗教活动,但此项活动不是每天都有的。去寺院朝佛的频度、去哪个寺院都根据家庭及个人的具体情况而定,比如经济条件、特殊事由、身体状况等。无疑,去离家最近的村落内的寺院的频度最高,时间上一般选择藏历初一、初十、十五、二十、三十等特殊吉日。一年中的藏历新年、萨噶达娃节、雪顿节期间成为当地藏族信众到寺院朝拜的高潮。但是,村落内的寺院规模小,僧人少,很少举行大型的法事活动,所以不少群众去附近著名的寺院朝拜,观看和参与法事活动。如A村的群众经常去本县境的敏珠林寺、桑耶寺等,也有人去拉萨三大寺、大昭寺及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等大寺院朝拜。在寺院的主要活动便是点酥油灯、磕头及贡献布施。
(四)转佛塔。转佛塔即按照顺时针方向绕着佛塔转,信众认为顶礼佛塔和转绕是对佛陀的礼敬,更是积累福德资粮,消除业障及障碍的最便捷的一种方法。由于白塔周围安置有供大众转经用的转经筒,因此,在转佛塔的同时,也顺手转转经筒。更多的老人则是一手转着自己携带的小经筒,一手拈着佛珠,喃喃念着六字真言绕塔行走。当转累的时候,在转经道旁的石头上休息片刻,和一起转经的老人聊聊天。关于转佛塔的时间由自己把握,每天或一次、或两次、或几天一次。绕转的次数因人而异,一般人每次绕转的圈数3或3的倍数,也有不少人绕转的次数是自己的岁数,也有人要转1000次、10000次甚至更多,但这要分几次甚至几天完成。为了便于记住转塔次数,不少老人用小石头作记号,如每当转够10次,则在转经路旁的石头上放置一颗小石子。因此,在村落佛塔旁的石头上,经常能看到转经者放置的一堆堆小石子。
以上列举的是西藏藏族村民比较突出的宗教活动,实际上,在西藏农村藏族人的生活中,藏传佛教的影响无处不在,如婚丧嫁娶、家人患病、小孩出生、建筑新房、更换经幡,甚至孩子考学等,不少人到寺院延请僧人卜卦、诵经,或延请僧人来家诵经、举行法事。宗教信仰已经民俗化和生活化,宗教信仰活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当然,每个家庭的宗教生活都有差异,有老人家庭的宗教活动相对频繁一些,也有人家多年来未举行过任何大的宗教法事活动。从信众的年龄结构来看,老年人视佛法为精神皈依处,修行是为了有一个更好的来世,同时也使一切有情众生得到快乐幸福;中青年人信仰佛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现实利益,如家庭平安、发财致富、考上大学等。
四、村民的宗教支出
西藏农村群众的宗教支出主要用于宗教物品和宗教法事活动等费用,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类:
(一)宗教用品消费。日常宗教用品的消费,如佛龛、佛像、唐卡、经书、敬水碗、供灯、转经筒、念珠、灯油、藏香等。在A、B二村,基本上每家每户都设有佛堂,只是大小、简繁规模不同。有的专设一间房做佛堂,但大多数村民家的佛堂设在正室内,室内置有沙发、茶几、电视等家具、电器,兼做活动室使用。佛堂内置有木质佛龛,供奉着释迦摩尼等各种佛像、菩萨像、唐卡等,也有人家置有电动转经筒。大多数家庭的佛堂里还供着十世班禅、十三世达赖喇嘛、附近寺院活佛等人的像片以及不同版本的新中国领袖像。佛龛下的供案上从左至右一字排开,整齐地摆放着铜质的净水碗、酥油灯,一般分别摆放7盏。佛龛柜内还储放着法器、经卷及香供等。墙壁上方挂着唐卡,少则数张,多则数十张。酥油灯一般是在藏历每月的初一、十五、三十等点燃,据说在这些吉日供施,功德、福报加倍。在此类支出中价格最贵的可能是“耐用”的宗教用品佛龛了。佛龛按照材质、大小、工艺等差异其价格也有所不同,一般都在数千元;其次是佛像,也按其材质、大小、工艺水平不同,价格也从几百元到数千元不等。在西藏农村还有一种习俗,如果家中老人去世后,则要购置一副唐卡供在佛堂内。A、B村的村民们购置的唐卡一般都在1千元以内,200元左右的居多。
(二)周期性宗教活动的消费。去寺院或神山朝拜等周期性宗教活动的支出,是藏区民众的一项重要宗教支出。这种支出的程度与去寺院巡礼的频度、寺院的距离等密切相关。前去朝拜者都是家里的老人,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老人是家庭的一个代表。从A、B二村的调研来看,每个家庭用于此项的支出每年在几十元至数百元,甚至数千元不等,这从以下一些个案略见一斑。
A村噶玛央吉(女,63岁),一般是每月去一次村里的寺院(桑阿曲果林寺),每次去一般要布施10元钱,另外自己带上几元钱的灯油。
A村索南多吉(男,65岁),于当年四月十五,到山南加查县的达拉岗布寺巡礼,住在亲戚家里,除自己从家里带去的一块酥油外,花了100多元;于五月初十,到附近的敏珠林寺朝拜,观瞻了该寺每年一度举行的大型法事活动,观看寺院僧人跳法舞“羌姆”。这次朝拜花去车费20元、布施了20元,另外从家里带去了一块11元的酥油供灯,一共花了50余元。索南多杰老人说:“家里不给我零用钱,自己每月领取的55元养老保险金基本上都花在佛事上了。如果没有政府发放的养老金的话,我不可能去比较远的寺院朝拜。”
B村尼玛次仁(男,62岁),一家三口每年去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朝拜2-3次,每一次布施等花销50元左右,往返路费60元,合计110元,一年3次合计要花300多元。
B村拉巴(男,62岁),夫妻二人每年到扎什伦布寺、增寺或萨迦寺朝拜一次,除点灯的酥油从自家带去外,每次布施花100元左右。一般都是乘坐儿子的小汽车去,所以都当天回来。
B村扎西旺堆(男,72岁),每年平均去寺院朝拜两次,主要是去扎什伦布寺、萨迦寺或增寺,除路费外,一般每次要花50元。
巡礼藏传佛教神山在藏族信教者眼中是一件重要的善供,因此朝拜神山也成为他们宗教支出的重要内容。需要说明的是,朝拜神山不是村民们的经常性的宗教活动,尤其是距离较远的佛教名山,只是几年、甚至几十年乃至一生中朝拜一次。而且巡礼神山的费用也与距离远近密切相关,如A村村民次仁旺杰(男,46岁)去位于藏北阿里的藏传佛教四大神山之一“岗仁波齐”朝拜的支出是5000元。他解释说:“‘冈仁波齐’是佛主释迦牟尼的道场,是我们藏民非常尊崇的神山。转山不仅可洗去一生的罪孽,还可免去死后的地狱之苦。两年前我曾到阿里朝拜神山“岗仁波齐”,花了3天时间,转了3圈。这次转山花了近5000元,其中车费花了600元。转一次山得到一次轮回,因此这次转山很值得,家里人都没有意见。”同是A村村民的恩珠嘎姆(女,现年73岁),她说2013年藏历三月初十日,去山南地区的贡布日神山朝拜,当天就回来了,除了十几元的路费,再没花别的钱。
(三)法事活动消费。延请僧人到家诵经,或因家人亡故操办法事活动成为村民们最大的宗教支出。一般而言,每个村落延请僧人在家诵经的费用约定俗成,比如在A村,现在请一名僧人到家里诵经一天的布施一般是30至50元,而经济条件相对较差的B村一般是20至30元。
现在,在西藏乡村用于丧葬方面的宗教支出比重最大。以B村尼玛顿珠(男,45岁)家为例,全家11口人,三代同堂,有26亩地,粮食刚够全家食用,没有多余粮食出售,家里还有一名大学生需要供给生活费等,家庭最主要的经济来源是两个儿子去外地的打工收入,还有一点是自己从事藏袍缝制的收入,家庭一年的总收入大约1.8万元左右,经济条件在B村属于中等偏上的水平。他认为宗教支出是家里的一项重要支出,觉得负担较重。他家2011年花了3万元盖新房,同年花了5 000元买了一个新的佛龛,另外花3 000元买了3尊佛像,又花1 000元买了12函佛经,合计当年的宗教支出是9 000元。2012年6月,82岁的父亲去世,去世后请3名僧人在家念经3天,给3名僧人各给了100元钱布施,合计300元;另给每人砖茶1包、青稞1脸盆、羊肉半扇。此后,七七四十九天的第七天都要请僧人念经,每次请3人,一次给僧人布施30元,合计90元,七天合计630元。“三七”那一天还要点108个酥油灯,加上当天还要请村民们吃饭,需要准备青稞酒、肉粥、奶茶等,给每家1包茶叶及三四元钱,这些又合计花去了7000元。父亲去世后,又买了一个镀金的佛像,花了2000元。由此可知,如果家中遭遇成员亡故等突发性变故时,其支出是庞大的,仅仅在丧葬方面的宗教现金支出近1万元,其中不包括给僧人伙食及其他实物布施。这种支出几乎是一年全家的总收入,一般家庭难以承受。
(四)宗教捐资。这类支出主要是指恢复和重建、维修当地寺院、白塔等宗教设施时群众负担的费用或“捐资”。对藏族信教群众而言,参与修筑宗教设施是一件极具功德的事情,所以他们的参与度很高,除无偿提供劳力外,也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捐资布施,从几十元至几百元甚至几万元不一。据笔者调查,A村的寺院在文革中被毁,1996年由格勒顿珠等3名还俗僧人外出募化两年,筹得5万元重修该寺庙。当时A村每个家庭捐50至100元不等,最多的捐了300元。也有人布施青稞、木材等实物,以及其他建筑材料。A村的白塔亦系当地村民于1988年集资建成。B村的白塔系村民拉巴个人捐资1万多元兴建。虽然这类“捐资”名义上是自愿,但由于周围舆论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强制性。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宗教捐资还有一种赢得外部赞扬、尊重、羡慕的意义。捐资活动与家庭荣誉乃至社会地位关联起来,形成超乎宗教信仰外的一种新的心理满足感。
就A、B二村宗教支出方面的调查而言,每个家庭的差异性较大,其中家庭经济收入、以及是否遭遇家人病故等突发性事故是影响宗教支出的最主要因素。举行佛事活动的次数,因具体的家庭而有所不同,家境殷实,家中有老人者举行的次数较多,反之则少,布施的情况亦如此。收入低,生活比较贫困的家庭,他们的宗教费用支出也较少。收入较好的人家,在宗教费用方面的支出相对较高。大多数法事活动的举行,有明显的现实功利目的,即通过法事活动的举行,实现个人的愿望,包括家人的平安、健康、免除灾祸,使家庭能够兴旺发达,达到幸福的生活。
结语
综上所述,对目前西藏农村群众的宗教生活及其变迁情况,可以总结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西藏农村得到了较好的贯彻和落实。目前,各种宗教活动正常进行,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民主改革及“文革”期间损毁的宗教场所得到修复或重建。信教群众家中普遍设有经堂或佛龛,经常进行转经、朝佛、请寺庙僧尼做法事等宗教活动。而且藏族信教群众宗教信仰的自由度加大,他们的宗教信仰完全成为个人的私事。
第二,藏传佛教在西藏农区广大信教群众的社会生活尤其是精神文化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信教群众的宗教信仰已经民俗化、生活化和世俗化,宗教信仰活动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虽然西藏农村信教群众的宗教信仰呈现出一定的个性差异,但是宗教信仰逐渐由神圣化转向世俗化是当代藏族宗教生活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趋势。
第三,西藏农户的宗教消费趋于理性,即把这项消费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有钱多花,没钱少花。当然,一个事实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因外出务工、减免学费、发放养老金等原因,家庭现金收入的增多,宗教支出也逐渐增多,不少老人甚至将不多的养老金全部用于宗教消费。毫无疑问,这就抑制了百姓正常的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影响了他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产的发展。因此,如何降低信教群众的宗教支出,成为我们当下应该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第四,藏传佛教寺院发生了深刻变革,它在藏区政治、经济和文化三大领域中固有的宗教功能逐步式微,尤其是其政治功能基本消失,文化功能与以往相比有了很大萎缩,经济功能虽仍有一定程度体现,但今非昔比,已一落千丈,地处偏僻的小型寺院更是如此,如本文A村寺院规模小,僧人少,也无转世活佛,加之地处偏僻,当地民众贡献稀少,而外来朝拜者、旅游者无法到达,没有市场经营的有利条件,没有任何经营性收入,生活条件艰苦,自养困难,个别僧人不得不还俗另谋出路。这也导致了寺院在当地教育、医疗、调解,尤其是经济活动等方面影响力的下降,以及传统的宗教畏惧感、神圣感的退化。
[1]史蒂文·戈瓦.社会变迁[M].王晓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99.
【责任编辑 詹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