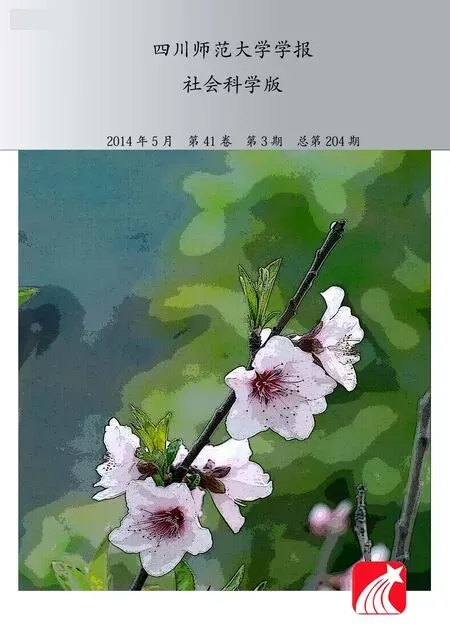谈论的兴盛与汉晋思想变迁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成都 610066)
汉晋之际的思想变迁是学界历来关注的热点,但对思想转变原因这个问题的探讨却相对薄弱。虽然出现了许多通过心理分析来解答这一问题的成果,但相比于生产、生活方式等物质基础的变化而言,心理的变化只能算是第二位的上层建筑,因此这些研究未能触及到问题的本质。只有从分析生产、生活方式所出现的变化入手,才能在根本上解答思想变化的原因。因此,本文拟通过对谈论活动这一新的士人生活方式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入手,来尝试解答这一问题。
之所以将谈论视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是因为谈论活动是东汉士人交游的纽带及主要内容。从学术方法看来,两汉今文经学主要是通过师生授业而完成的,但谈论兴起后,士人之间自发的相互讨论逐渐成为新的学习方式;从交友形态看来,在谈论活动兴起之前,士人主要依托权势获得发展和晋升的机会,士人与权势集团的交往是社会关系的主要方面,但谈论兴起后,士大夫之间的交往遂成为社会关系的主流。随着这些生活方式的改变,士人的思想也随之急剧地发生改变。
一 论经活动的兴盛与今文经学的衰弱
“游谈起太学”[1]114。太学是东汉谈论最初发轫的地方。这也意味着谈论初兴时的论题是经学问题。但以经学为论题的谈论活动最初却不是士人自发举行的,而是由官方主持的,我们姑且称这种谈论形式为“论经”。论经有两种形式,分别对应今文经学发展中的两个问题:一种是今文经学各派内部旨在争夺官学席位而展开的论经活动,即“求立”之争;另一种则是为了弥合今文经学在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逐渐繁富、忽略义理等弊端而展开的更为广泛的论经,著名的石渠议经和白虎观议经都属于这种情况。对于“求立”的论经,大家都很熟悉,不需要解释。对于为弥合今文经学弊端而产生的论经活动,需先从今文经学的特点入手谈起。
今文经学最显著的特点有两个:一是依靠严格的师法和家法代代相传,二是以章句之学为根本治学方法。严格的师法和家法的传承模式导致各学派间差异不断扩大;章句之学是一种重在解释经文字句、考证名物的方法,它的不断发展既导致自身不断繁富又严重影响了对经书本义的阐释。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各派章句日渐繁富,学派间的差异性成为了各派无法调和的主要矛盾,这严重掩盖了经书的“义理”,致使今文经学成为“破坏大体”[2]1599之学。范晔对今文经学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曾概括说:“守文之徒,滞固所禀,异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2]1212—1213今文经学在发展中遇到的这些问题仅凭借各家之间的讨论是无法解决的,因此像石渠议经和白虎观议经这种综合各派的大讨论就势在必行了。
关于论经活动,本是具有一定的规范的。鲁丕《上疏论说经》就对这种规范有详细的记载:“说经者,传先师之言,非从己出,不得相让;相让则道不明,若规矩权衡之不可枉也。难者必明其据,说者务立其义,浮华无用之言不陈于前,故精思不劳而道术愈章。法异者,各令自说师法,博观其义。”[2]884按鲁丕所说,论经活动的主旨是为了“明道”,即阐发经书义理,并判别正误;其具体操作办法是“各令自说师法”,即严格按照各自师法传承来阐释自身的观点。鲁丕所处的时代,今文经学的畸形发展已经很难做到“阐发义理”了,而且“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3]1723的繁琐章句显然也仅能存在于书面状态,却根本无法适应口头层面进行的辩论。
但古文经学却并不存在这种情况,古文经学仍坚持着私人教授和“训故”的治学方法。“训故”又作“训诂”,颜师古谓“故者,通其旨义也……今流俗《毛诗》改故训传为诂字,失真耳”[3]1708,《汉书·扬雄传》云:“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3]3514,可见两者名异实同。郜积意详细考证了这种治学方式,认为“训故为训解大义,不及古言古字,章句必然就落实到这些古字古言的诠释上”[4]46。因此古文经学既保存着简短的形式,又针对经书义理而发,是解决今文经学弊病的一剂良方。这一点汉朝统治者也注意到了,白虎观论经实际已经引入了古文经学的方法和观点。与此同时,汉章帝也采取一系列措施提倡古文经学,建初八年(83)冬十二月曾下诏云:“《五经》剖判,去圣弥远,章句遗辞,乖疑难正,恐先师微言将遂废绝,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其令群儒选高才生,受学《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以扶微学,广异义焉。”[2]145可见,古文经学是为解决今文经学弊病而被引入官学界的。
将古文经学纳入太学生的学习范围,为弥漫着章句之学繁冗枯燥气息的学界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从此士人开始逐步接受古文经学。这个转变最初的表现就是治学方法发生改变。钱穆先生说:“东汉之季,士厌于经生章句之学,四方学者,荟萃京师,渐开游谈之风。”[5]141—143皮锡瑞说:“汉儒风之衰,由于经术不重。经术不重,而人才徒侈其众多;实学已衰,而外貌反似乎极盛。于是游谈起太学,而党祸遍天下。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实自疏章句、尚浮华者启之。”[1]114二人都认为“游谈”直接导致了今文经学的衰弱。还需注意,皮锡瑞还引出了“浮华”一词,并认为“尚浮华”是诱发“游谈”兴起的直接动力。“浮华”一词又见于《后汉书·儒林传》“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2]2547,直接将“浮华”与“章句”对立起来。实际上,“游谈”与“浮华”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都是古文经学引入而产生的后果。“游谈”是指受古文经学的冲击,学生摒弃今文经学师法、家法相教授的治学方式,并将自发性的学理探讨作为新的学习方法;“浮华”指的是太学生“游谈”的内容不再依靠各家章句,而是重在用古文经学的方法探讨经学本身的义理。汉晋时人对这一过程已有充分的认识。王充曾概括今文经学的教学方法为“南面为师,旦夕讲授章句,滑习义理,究备于《五经》可也”[6]555,学生受利禄影响学习起来也只是“不肯竟经明学,深知古今,急欲成一家章句,义理略具”[6]538。但到了安帝时期,这种情况改变为“博士倚席不讲,儒者竟论浮丽”[2]1126,即学生之间自主讨论的方法取代了博士教授的方法。
学习方法的改变必然会影响其所学内容。徐防在其疏奏中云:“伏见太学试博士弟子,皆以意说,不修家法……今不依章句,妄生穿凿,以遵师为非义,意说为得理,轻侮道术,浸以成俗。”[2]1500—1501可见太学生在谈论潮流中已完全摆脱了章句之学,而习惯于通过讨论来阐发经书义理。从现存汉末延笃《仁孝论》、刘梁《辩和同之论》等论作来看,其论题都与古文经学重在阐发义理的旨意一脉相承,皆针对某一哲学问题,而非针对经典的字句。比较东汉中期班固《白虎通论》中关于古代礼法名物的讨论,还可以看出在对义理的不断追求下,论题有逐渐进化的趋势。即当统治者将古文经学纳入论经范围时,论题以解决今文经学弊端为出发点,具有具体的针对性;然汉末谈论盛行之时,谈论的话题已发展为蕴含更高“义理”的抽象性问题。所谓“今文守家法,古文尚兼通”[7]247,谈论话题的变化既反映了东汉士人厌恶今文经章句之学,逐步采纳古文经学阐发义理的治学旨要,并在对义理的不断追求下,逐渐将谈论话题深化的过程,也反映了今文经学地位不断受到冲击的过程。
综上,太学生在面临已然畸形的今文经学时,并没有一味盲从,他们本着求真的目的,果断吸收了古文经学的旨要,以自发性的谈论为手段来探讨义理问题,这便从根本上打破了今文经学家法、师法的传承模式,也冲垮了章句的传统。谈论的盛行是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因为它的出现标志着治学方法这一根本问题发生了变化。可以说,谈论对今文经学的打击是具有根本性质的,而这也使两汉禁锢于儒学的思想开始松动,为后世思想的持续变革做好了铺垫。
二 谈论对儒家思想控制的冲击
谈论的兴起促使古文经学取代今文经学仅是汉末思想转变的第一步,受谈论的发展和时局变化两方面的影响,时人思想必然取得进一步发展。在学理类讨论中,逐渐出现一批诋毁圣人的反儒声音,并且随着对“义理”探讨的深入,思想界不可避免地引入老庄道家思想;面对纷乱的时局,时人关于政治的讨论也无法囿于儒学范畴,法家、兵家等其他子学思想随之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两者的共同作用终于打破了两汉儒术独尊的格局。有谈论就有胜负之分。为了取得胜利,士人通常会采用两个办法:一是注重谈论之时言语、音声等形式;二是标新立异,使自己的论题惊世骇俗。后者就是王充所说世人著作“多欲立奇造异,作惊目之论,以骇世俗之人;为谲诡之书,以著殊异之名”[6]167。正是基于这种心态,才会使“仁孝之先后”、“圣人优劣”、“圣人喜怒哀乐之情”等类似先有鸡或先有蛋的问题在士人中产生并持续流行。因此,谈论一经流行,其发展便不能被某个士人的思想掌控了。
曹操杀孔融,为安抚人心下令云:“此州人说平原祢衡受传融论,以为父母与人无亲,譬若缸器,寄盛其中,又言若遭饥馑,而父不肖,宁赡活馀人。”[8]373便是站在传统儒家之立场,批判孔融违背礼教、仁孝言论。路粹《枉状奏孔融》亦云:“(孔融)又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缻中,出则离矣。’”[2]2278
“父母与人无亲”、“宁赡活馀人”等论虽并不代表孔融的真实心意①,但曹氏用官方途径将其公之于世,便可说明这种言论在当时是有影响力的。从“论圣人优劣”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圣人在时人心目中的地位已不如往日,士人可以对圣人评头论足,这些讨论最终导致刘陶“仲尼不圣。何以知其然?智者图国,天下群愚,如弄一丸于掌中,而不能得天下”[8]449之论的产生。孔融、刘陶等人的论点虽然并不是当时的主流观点,但都客观反映了儒学思想在汉魏时期的式微。这些直指儒家“圣人”、“孝顺”等思想核心的讨论,虽然亦在学理讨论范围之内,但它的结果却会导致儒家思想的颠覆。从这个角度看,谈论的发展对儒家思想的突破是不言而喻的。
受感染成为木马和僵尸网络程序控制服务器的主机IP数量最多的三个设区市分别是南昌、上饶和赣州,占到全省被感染总量的60%。地域分布情况如图7所示:
谈论对义理的不断追求与论题的愈发精妙是相互推动的。越是讨论精妙之话题,越能体现论者的谈论水平。因此,随着谈论对“义理”的不断追求,士人必将追寻到“义理的根源”——即“三玄”所蕴含的哲学道理,此时儒家思想便不足以支持讨论的进行了,这无疑推动思想界吸纳道家思想。以《周易》为例,汤用彤云:“《易》学关于天道,辅之以太玄,在汉末最为流行。……汉代旧《易》偏于象数,率以阴阳为家。魏晋新《易》渐趋纯理,遂常以《老》、《庄》解《易》。”[9]61在追求义理的谈论之风下,士人对《周易》的解读首先在方法上发生了从“象数”到“义理”的转变,进而便引入老庄思想来解读《周易》,从而在思想上完成了由儒入道的巨大转变。对这一过程,荀粲的故事堪为典型:
(荀)粲诸兄并以儒术论议,而粲独好言道,常以为子贡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然则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粲兄俣难曰:“易亦云圣人立象以尽意,系辞焉以尽言,则微言胡为不可得而闻见哉?”粲答曰:“盖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今称立象以尽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系辞焉以尽言,此非言乎系表者也;斯则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蕴而不出矣。”[8]319-320
这则故事至少说明了三个问题:其一,荀粲时代执道家思想进行谈论的并不多见,但“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这句直接抨击儒家经典的话语,说明儒学的思想控制力已经衰退;其二,荀粲是依靠儒家“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之语而选择道家思想的,既体现了思想由儒入道的过渡,又暗示了谈论话题的进化是导致思想转变的直接原因;其三,荀粲解读《易》的目的在于阐发《易》所蕴含的宇宙哲理,这种论题的产生是对“义理”不断追求的结果。因此,代表中国古代哲学最为精深的玄学思想在魏晋时期重新获得生命力并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汉末浮华谈论之风逐渐发展的必然。
除了在学理类的讨论中引入道家思想不断冲击儒学阵地外,由于汉末局势混乱,对时局的讨论也推动思想界引入其他子学思想。魏晋时期是历史上又一个子学昌盛的时代,葛洪云“魏代以来,群文滋长,倍于往者,乃自知所未见之多也”[10]660,可见其一斑。汉代子学是将其思想精髓寄托在儒家范围内而缓慢发展的,以法家为例,其名称自“罢黜百家”后就消失了,但其旨要却转化为儒治的工具,因此才有王充“法律之家,亦为儒生”[6]564之语。东汉有许多以法传家的世族,累世不衰,如“郭氏自弘后,数世皆传法律,子孙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中郎将者二十余人,侍御史、正、监、平者甚众”[2]1546,说明法家是寄身在儒学之下悄然发展的。但汉末政局混乱,两汉子学的这一发展模式被打破了。
史载“汝南范滂等非讦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节下之。太学生争慕其风,以为文学将兴,处士复用”[2]1752,袁宏进一步解释“非讦朝政”为“上议执政,下议卿士”[11]624,这些围绕时局、政事的讨论是无法在儒学范围内展开的,儒家经典也无法为这些讨论提供足够的佐证,所谓“六奇之策,不出经学”[2]1506。这些讨论需要打破儒家的范畴,从刑名、法、墨、兵等其他子家吸收营养,这就为其他子学浮出水面创造了契机。实际上,东汉中期子书《论衡》有不少篇目针对时政而发,后世评其为“乍出乍入,或儒或墨”[10]423,即批评其不能专守儒家一门。而汉末局势已非王充时代可比,其谈论话题更是涉及军事、政治等方方面面,确如战国一般。《三国志·刘晔传》云:“太祖征晔及蒋济、胡质等五人……内论国邑先贤、御贼固守、行军进退之宜,外料敌之变化、彼我虚实、战争之术,夙夜不解……及见太祖,太祖果问扬州先贤,贼之形势。”[8]444-445可见,随着对时局、战争等问题讨论的深入,思想界引入其他子学思想是必然的,而这无疑打破了两汉儒术独尊的思想格局。
三 博学风尚的流行与雅俗观念的重构
刘勰说魏晋子书带有“璅语必录”[12]308的特点。这个特点实际标志着汉晋思想发生了由重道统、轻流俗向道、俗并重的巨大转变,而推动这一变化的根源便是谈论。
随着谈论的发展,论者原有的知识结构因不能满足谈论的需求而受到挑战,论者积极寻求更为广泛的知识来源,从而谈论界兴起了一股追求“博学”的风尚。
需要注意的是,谈论对于博学的要求是今文经学不能满足的。今文经学的博学是关于章句的“博学”,即徐干所谓“鄙儒之博学也,务于物名,详于器械,矜于训诂,摘其章句”[15]13,而谈论话题之博却远远超出这个范畴。《后汉书·郑玄传》云:“时,大将军袁绍总兵冀州,遣使要玄,大会宾客,玄最后至,乃延升上坐……绍客多豪俊,并有才说,见玄儒者,未以通人许之,竞设异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辩对,咸出问表,皆得所未闻,莫不嗟服。时汝南应劭亦归于绍。”[2]1211袁绍帐下宾客“竞设异端,百家互起”的特点,说明当时讨论之话题不囿于儒学,颇有“百家争鸣”之象。这场讨论是宾客“见玄儒者,未以通人许之”之后展开,说明在时人心目中,儒者是不能称为博知万物的“通人”的。这场辩论又因“玄依方辩对,咸出问表”,使得宾客感到“皆得所未闻,莫不嗟服”而结束,说明博学对谈论胜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以博学见称的应劭也参与到了这场讨论中,这场谈论的话题广度可想而知。
这里还有一条有趣的材料。《三国志》裴松之注引《搜神记》云:“昆仑之墟……有火浣布……汉世西域旧献此布,中间久绝;至魏初,时人疑其无有。文帝以为火性酷烈,无含生之气,著之《典论》,明其不然之事,绝智者之听。及明帝立,诏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论,不朽之格言,其刊石于庙门之外及太学,与石经并,以永示来世。’至是西域使至而献火浣布焉,于是刊灭此论,而天下笑之。”[8]118曹丕《典论》认为不存在火浣布,因此当此物作为贡品引入时,皇家立即“刊灭此论”。很显然,皇家刊灭此论的原因就是怕曹丕因“孤陋寡闻”而被天下笑。
以上郑玄的例子并没有明确出现所讨论的事物,但火浣布的故事却生动反映了时人谈论的话题——一种神奇到类似传说的事物,这足以看出时人所追求的博学是包容古今一切知识之“博”。这两个事例都表明一股追求博学的风尚在激烈的谈论中产生了,这也促使一大批类似应劭《风俗通义》、张华《博物志》等并无明确思想主旨、旨在网罗轶闻的子书得以产生。
应劭《风俗通义序》云:“俗间行语,众所共传,积非习贯,莫能原察……今俗语虽云浮浅,然贤愚所共咨论。”[16]16张华《博物志序》云:“余视《山海经》,及《禹贡》、《尔雅》、《说文》、《地志》,虽曰悉备,各有所不载者,作略说。”[17]7可见两书作者的动机就在于搜集、考证古往今来各类事物和传说,两书的内容也确实符合其创作动机。
需要指出的是,两书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思想界发生了另一个重要的变化。两汉士人膺服儒学,思想上有一种天生的清高感,他们站在道统的角度认为两书“俗间行语”的内容属于“小道”,并对此非常鄙视,《风俗通义》便被指“文虽不典”[2]1614,鸿都门学“陈俗闾里小事”的作法也成为士人猛烈抨击宦官集团的口实[2]1992,这都表明两书的内容在传统士大夫心目中属于“流俗”的范畴,与儒家道统思想有着强烈的抵触。然而随着博学风尚的流行,士大夫这一自命清高的思想又被打破了。从现存书目看来,魏晋士人整理轶闻趣事这一“俗务”已然成为潮流。《隋书·经籍志》著录除了上列两书,仅魏晋两代便出现了张华《张公杂记》、曹植《列异传》、戴祚《甄异传》、干宝《搜神记》、王嘉《拾遗记》、葛洪《西京杂记》、崔豹《古今注》、陶潜《搜神后记》等书。这说明随着谈论“博学”风尚的流行,原本受轻视的“俗间行语”成为时人的“雅好”,标志着两汉士大夫原有的雅俗观念发生重构。这个转变也推动了中国古代小说家的发展。
注释:
①冈村繁认为孔融是名副其实的士人领袖,他之所以会做出反名教的言论,是旨在借此讽刺、抨击曹氏专权,而并非其本意。参见:冈村繁《汉魏六朝的思想和文学》第二章《孝道与情欲——论孔融的儒教观》,陆晓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参考文献:
[1]皮锡瑞.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8.
[2]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郜积意.刘歆与两汉今古文之争[D].上海:复旦大学,2005.
[5]钱穆.国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6]黄晖.论衡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
[7]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8]陈寿.三国志[M].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82.
[9]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10]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7.
[11](晋)袁宏.后汉纪校注[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12](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注[M].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13]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1.
[14]李昉,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0.
[15]徐湘霖.中论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2000.
[16]应邵.风俗通义校注[M].第2版.王利器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
[17]张华.博物志校证[M].范宁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