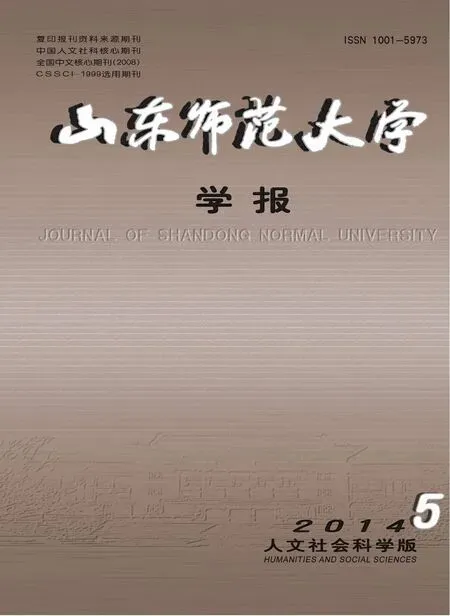关于文学典型问题的当代思考*
周 波
(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250014 )
关于文学典型问题的当代思考*
周波
(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250014 )
文学典型理论近年来被搁置或被冷落,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一种文学理论的价值要根据其自身意义以及发展变化了的创作实践与社会现实来进行评判,对其本质的把握要靠学理的深入探究。在回顾新时期以来关于文学典型问题讨论的基础上,力求遵循文学形象的固有属性与叙事文学的自身规律,着眼于多元文化和文学的广阔视野,从哲学、美学、艺术、文学等多种视角重新阐释典型的本质特征,并融会现代思想理念、联系创作现实探讨文学典型概念向典型情节、典型意象、典型情境的顺势拓展,以及文学典型的现实生态与发展前景等问题是有其重要理论意义的。
文学典型;典型意象;典型情境;顺势拓展;当代思考
文学艺术典型研究是建国以后乃至新时期初文艺理论界的“显学”。朱光潜在20世纪70年代末再版的《西方美学史》中引用别林斯基“没有典型化,就没有艺术”之说,进而指出:“典型问题在实质上就是艺术本质问题,是美学中头等重要的问题。”①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695页。可见,直到改革开放初期典型问题仍被看作文艺与美学的核心问题。当然典型问题之所以被提到如此高度,在很大程度上还因为在当时的政治化语境下,它是一种意识形态性很强的文艺理论范畴和话语。
然而时过境迁,今天提起文学典型话题来似乎面临着这样一些令人困惑的问题:一是关于典型问题向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难以说清道明。二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典型理论似乎已经“式微”了,典型论已被认为属于陈旧的观念。例如有学者指出:“文学典型学说的沉寂是20世纪文论话语中一个显著的事实。”②舒开智:《马克思主义“文学典型”学说的当代价值与生命力》,《甘肃联合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有人甚至说:“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关于典型的如火如荼的论争已渐趋消歇,典型论被打入‘冷宫’,如日经中天的繁华景象被切换成日暮途穷的黄昏景观。”③叶虎:《20世纪中国文学典型论局限分析》,《沈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三是当今文学创作中已经不重视塑造典型了,研究文学典型似乎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了。
毋庸置疑,文学典型理论近年来被搁置或被冷落已是不争的事实,典型研究已从学术“热点”变成了“冷点”。不过一种文学理论的价值不能仅凭学界的“热”或“冷”来判断,而要根据其自身意义以及发展变化了的创作实践与社会现实来进行评判。理论的“热”或“冷”只是瞬息万变的社会文化思潮冲击下的文化现象,而对其本质的把握却要靠学理的深入探究。况且,经过了一个历史阶段的沉寂之后,再回过头来重新检讨典型理论问题,或许更能够客观冷静地进行审视,从而作出实事求是的评判和阐释。
本文拟在回顾新时期以来关于文学典型问题讨论的基础上,重新探讨典型的本质特征,并联系创作现实论述文学典型理论的建设及其当代意义等问题。
一、新时期文学典型问题讨论的回顾
新时期以来关于文学典型问题的讨论尽管涉及到典型的创造规律、典型的发展史、典型的内涵、典型的理论建构等一系列问题,但总的来看其核心问题是关于典型本质内涵的理解认识。围绕着对文学典型的反复阐释,学者们展开了漫长曲折的学术研讨过程,形成了典型问题研究的连绵不断的主线。
新时期关于文学典型的讨论大致上可以分为两个历史阶段:改革开放初期至80年代中期为第一阶段;80年代后期至今为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可称为“争鸣期”。新时期初开始的关于典型问题的讨论是继20世纪50年代中期、60年代初期两次大讨论之后的第三次大讨论。这次讨论不仅程度热烈且前后持续时间长,至80年代中期以后才逐渐风平浪静起来。
此期关于文学典型问题的讨论争鸣与理论建设大致可分为两个层面:第一层面主要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典型理论和文学艺术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理论框架内对典型问题进行阐释、讨论。问题集中于典型与阶级性的关系、典型的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的关系等。
此层面的典型研究仍然延续着传统的路数进行,有两个基本的出发点:一是在创作实践上以鲁迅小说中的阿Q形象为基本案例。自从20世纪20—30年代阿Q形象的典型性得到普遍认同以来,这一形象便被作为文学典型的标本。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在新文学发展的第一个十年里,阿Q形象与西方典型理论的碰撞,发出了耀眼的火花,大家普遍承认阿Q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典型。……从此,阿Q形象便与典型紧紧地连在一起了;谈到阿Q,就要讲典型;讲到典型,也一定要谈阿Q。”*陈学超:《阿Q与中国现代典型理论探索述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6年第4期。
二是在理论上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文艺观尤其是恩格斯的现实主义、典型论为理论基础和思想来源。自从20世纪30年代初恩格斯的现实主义、典型论引进中国以来它便成为典型阐释的理论依据,关于文学典型的个性与共性、典型的现实主义特征等问题往往成为讨论的焦点。例如80 年代初中期围绕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二者关系问题的一场长达数年的争论,就是因徐俊西发表的题为《一个值得重新探讨的定义——关于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关系的疑义》的论文而引起的。争论的焦点主要是关于恩格斯给哈克奈斯的信中某些观点和论述是否“具有科学定义的性质”问题*徐俊西:《一个值得重新探讨的定义》,《上海文学》1981年第1期。,其主导倾向是试图破除对典型理论庸俗化、公式化的认识。争论双方的意见分歧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的不同理解。与此类似,当时不少研究论文大多是从学习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典型的论述出发谈论对此问题的感受、理解,或者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语境下对典型理论与实践问题作出一定程度的探讨,出现了不同认识的碰撞。
关于典型的阐释,主要是普遍不满于60年代以来的“共性与个性的统一”说,试图寻求确切表述或另辟蹊径提出新说:或强调共性,或突出个性,或主张典型是特殊——中介等,种种论争主要是在哲学层面上展开的。其中较有突破性的观点是陆学明等人提出的“特殊——中介”说。论者以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关于“我们在思想中把个别的东西从个别性提高到特殊性,然后再从特殊性提高到普遍性”的观点,及其对黑格尔“个别性、特殊性、普遍性”三个逻辑范畴划分的充分肯定,指出:“艺术典型的质的规定性就是逻辑范畴的特殊性”,“它的本质特征就是蕴含在社会生活中的某种特殊本质或规律的艺术再现”。*陆学明:《论典型的本质特征》,《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2期。这种把典型定位于特殊,认为它是处于个别性与普遍性中介的看法为典型的阐释开辟了新的视角。
一些学者继续进行典型理论的坚守,坚持以开放的态度开展传统典型理论的深度开发。此期出版的有关学术著作包括杜书瀛《论艺术典型》(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田丁等《艺术典型新议》(文化艺术出版社1983年版),李衍柱《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概述》(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被称为“我国典型理论研究史上的第一批专著”*李希贤:《文艺典型系统引论》,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2页。。这些著作都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和美学观,从学理上或理论渊源以及文学实践上对文学典型问题作了较为具体深入的探讨,力图摆脱“文革”中左的政治化、阶级化的思想束缚,重新进行典型理论建设。其中李衍柱《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概述》属于最为系统和富有历史研究纵深的典型理论著作,该书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典型理论的历时性研究思维视角,以及史证与阐释相结合的考辨式研究方法,为马克思主义典型理论观的深度探讨和典型理论史的系统建构提供了成功案例。
此期的这类论文与著作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典型理论框架内寻求对典型内涵的理解,力求超越“共性与个性统一”说,进而作出更为深入精到的解说。虽然无论从研究观点到方法均未出现较大的突破,但坚持实事求是进行典型学术探索的活跃气氛逐渐形成了。
第二层面主要是受到欧美各种文化思潮及文学创作的影响在多元文化语境下讨论典型问题。80年代以来随着欧美各种现代社会文化思潮和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的涌进,使典型理论面临着巨大的冲击和挑战。叙事文学创作中出现的抒情化、散文化、情节淡化、非典型化倾向更使典型理论陷入了困境。文学理论界对典型理论的态度发生了分化,出现了维护典型与非典型、反典型等不同观点的碰撞,关于典型问题的争鸣趋于白热化。其实当时文学典型理论遇到的困境无非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不能准确解释或定义典型的理论内涵;另一方面无法说明不断发展变化着的当代文学现象。对待典型的态度无非有三种:一是坚持传统的典型观念,使其只限于解释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及一部分当代文学;二是扩大典型的内涵,使其能够适于解释一切文学现象;三是创造新的理论术语取而代之,弃置典型概念。尽管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声音,不过坚持、调整、建设是此期典型研究的基本取向。与其把这一阶段看作所谓“典型的崩解”*旷新年:《典型概念的变迁》,《清华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时期,不如说这是典型理论接受严峻考验而试图坚守与突围的时期。
一些学者为寻求典型理论突围,逐渐采用新的观点和方法研究文学典型问题。大致有两条线索:一条是另辟蹊径借鉴西方的新观念、新方法对人物性格进行深入研究,从而使典型的研究得到深化。从刘再复的《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刘再复:《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文学评论》1984年第3期。、《性格组合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提倡所谓“二重组合性格”或“圆形性格”*刘再复:《圆形人物观念与典型共名观念》,《当代文艺思潮》1985年第6期。,到林兴宅《论阿Q性格系统》*林兴宅:《论阿Q性格系统》,《鲁迅研究》1984年第1期。,运用系统论方法研究文学典型、提倡系统性格,都极大地拓展了典型的理论内涵,促进了典型理论肌理的细化。
另一条线索是面对西方现代文化思潮的挑战,力图从更为广阔的视野探讨文学典型问题,以寻求文学创作观念的突破或进行典型理论重建。当时对传统的文学形象塑造理论产生巨大冲击的是高行健《现代小说技巧初探》(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中提出的现代小说观念和王蒙关于文学创作的新观点。而对文学典型理论提出直接质疑和要求突破的是王蒙1982年底发表的《关于塑造典型人物问题的一些探讨》一文。他强调:“不能把塑造典型人物这一要求‘单一化和绝对化’”,“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命题”并“不是无所不包的、更不是唯一的创作规律”,此外还有其他规律。他以契诃夫的《苦恼》和《带小狗的女人》、海勒的《第22条军规》等小说为例,说明它们并非以塑造典型人物为主,而是以事件或逻辑为主;指出“某些(不是全部)神话、寓言、童话的主人公,与其说是人物的典型化,不如说是某种典型的精神、特质、遭遇的象征”。*王蒙:《关于塑造典型人物问题的一些探讨》,《北京文学》1982年第12期。其后吴亮在《“典型”的历史变迁》中则直接以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为诠释目标,提出扩大典型的内涵,把典型观念包容进去。*吴亮:《“典型”的历史变迁》,《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4期。
总的看来,此阶段典型研究由于逐渐摆脱了单一的理论视角,立足于广阔的多元文化背景,因而能够在观点和方法上产生突破。但是急剧的文化转型和创作上的改弦易辙使得典型理论研究相对滞后,缺乏通观圆照式的见解与深度的理论探讨,跟不上创作实践的发展。
第二阶段可称为“反思期”,此阶段的总体表现是经过80年代前中期的热烈讨论之后,在相对沉寂的状态下对典型问题展开冷静的历史反思。尽管90年代以后文学创作更趋于多元化,却很少有成功的文学典型出现,典型理论似乎已经失去了赖以存在的源头活水,但是学界对文学典型问题的探讨却并未消歇。一些学者致力于总结反思典型理论沉寂的原因,提出种种突围和重建典型理论的设想,尝试从各种不同角度开辟新的阐释途径。如李希贤《文艺典型系统引论》(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以系统论为方法论对艺术典型的结构作了综合、系统的分析研究和理论建构。陆学明《典型结构的文化阐释》(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力求从文化的广阔视野运用符号学、神话原型批评等方法对典型作出新的阐释。王一川《中国现代卡里斯玛典型——二十世纪小说人物的修辞论阐释》(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借用西方社会学和政治学中的“卡里斯玛”概念,以独特的视角分析说明20世纪中国小说中典型的特殊形态及其发展流变。
此阶段较有突破性的理论主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突破传统典型理论研究的局限,广泛涉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领域以验证典型理论的普遍适用性和艺术规律性。李衍柱《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史纲》在第十章“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的历史命运”中讨论了“典型理论发展中出现的二律背反”、“典型范畴在现代主义和表现说理论体系中的地位”,致力于探讨典型理论发展的规律与典型范畴的现代拓展和延伸问题。通过对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作家的创作及其言论进行考察,力求说明他们并不是排斥或否定人物及典型人物的塑造的,典型理论在当代西方文艺创作中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李衍柱:《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史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12-326页。其二,针对现当代文学创作发生的巨大变化,扩大典型的理论覆盖范围,提出新的典型概念。张梦阳根据黑格尔关于“抽象的艺术品”、“有生命的艺术品”、“精神的艺术品”划分,进而修正冯雪峰主张的“思想性的典型”之说,提出了“精神典型”概念。认为“精神典型是艺术典型这个大概念中的一个小概念”,在其塑造过程中“达到了陌生化、寓言化的以形象的人物反映抽象的哲理的高境界与深层次,实现了具象性与普遍性的高度统一”。*张梦阳:《阿Q新论:阿Q与世界文学中的精神典型问题》,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13页。
此期关于文学典型内涵的阐释体现了更为开放的态势,超越了80年代前中期执着于人物性格的探讨,而着眼于典型理论内涵的建设与外延的扩展,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果。不过这些成果并未能改变典型研究所处的边缘化局面,亦未能使典型理论摆脱已有的困境,典型理论的探讨和建设仍然任重而道远。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关于文学典型问题的研究历程,是在逐渐摆脱阶级化、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深入探讨的过程。学者们在特定历史阶段对典型的思想内涵作出了步步递进的探索,不同程度地推动了典型理论的建设。但是,鉴于典型问题的历史积淀的深厚性和自身的复杂性,今天需要在更广阔的理论和文化视野中进行文学典型问题的讨论与理论建构。也就是说,需要超越现实主义典型观,把文学典型问题放在整个叙事文学的广阔视野和背景中进行研究。不仅把文学典型问题看作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理论问题,而且将其看作世界多元文化与文学中的普遍性理论问题。这就涉及对文学典型本质内涵的重新阐释、典型概念的扩展以及典型理论的现代生态与前景的审视等问题。
二、文学典型本质内涵的再阐释
正如阿Q的典型性问题被称作“鲁迅研究界以至文学理论领域的‘哥德巴赫猜想’”*张梦阳:《阿Q新论:阿Q与世界文学中的精神典型问题》,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1页。一样,文学典型问题也可以说是文艺理论界的“哥德巴赫猜想”。学者往往毕生钻研亦未必猜出满意的结果。例如终生研究文学典型问题的蔡仪在晚年《致王世德》的信中说:“至于我提出的典型说,我自己也认为至今也没有能够充分证明,因而在我向研究生说明时,也说它还只是一种‘假设’,只是有些事实根据,有些理论根据的‘假设’ 而已。”*《蔡仪文集》第10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第294页。蔡仪此说自然是一种自谦之词,但学界至今尚未对典型内涵取得共识却是不争的事实。看来无论能否找到正确的答案,人们总是还要继续假设、猜想下去。
近年来,不少学者都指出过上世纪以来关于文学典型问题研究尤其是对于典型内涵探讨中普遍存在的问题:理论渊源上主要从马克思、恩格斯上溯到古希腊而很少涉及现当代理论家;创作实践上往往局限于现实主义文学而很少关注现当代作家和文学创作;研究方法上过多着眼于哲学视角而缺乏多元的视角和广阔的视野。的确,我们今天对于文学典型本质内涵的阐释,需要从哲学、美学、艺术、文学等多维视角审视,以便全面把握其多重本质内涵。
不过“典型”与“经典”、“意境”之类的术语一样都是含义宽泛的开放性、模糊性、普泛性概念,无法进行准确定义。作为能指它具有多种所指,从不同的向度可以解读出各种不同的含义。而要探讨文学典型的本质问题,关键是要厘清典型与非典型的区别究竟何在?在我看来主要有四个关捩点:
其一,典型是揭示了某种普遍本质或真理的特殊形象。近年来人们对从哲学上阐释典型的理论提出了质疑,以为此种理论并不能揭示典型的文学或美学特质。其实要阐释典型的内涵首先还是需要从哲学入手,因为典型问题本身包含着丰富的哲学内涵。无论是亚里斯多德《诗学》中所说的“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古希腊]亚里斯多德著,罗念生译:《诗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29页。,还是恩格斯《致敏·考茨基》(1885年11月26日)的信中所说的“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73页。,都说明文学典型包含着深刻的哲学蕴涵。
建国以来,文学理论界关于典型本质内涵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以“共性与个性统一”这个哲学命题为基点而展开的。“共性与个性统一”作为哲学命题适于解释包括文学形象在内的一切事物,文学典型属于文学形象,当然也适于解释文学典型。关键是需要回答:文学典型不同于一般文学形象的特质究竟是什么?于是人们基于这个哲学基础作出了种种解释:或侧重于强调“阶级性”、“社会性”的共性;或侧重于强调“鲜明性”、“独特性”的个性;或指出介于二者之间的“中介——特殊”性等等。其实文学典型区别于一般文学形象的本质特征主要在于其特殊形象体现着某种本质或真理。文学形象作为特殊形象由于深刻揭示了某种本质或真理就是体现了普遍性、规律性,本身就是一种典型形象。早在60年代初李泽厚就指出了这一点。他从本质与现象、必然与偶然的哲学范畴中考察典型,强调“其实质正在于它是在偶然性的现象中体现着必然性的本质或规律”。*李泽厚:《典型初探》,《新建设》1963年第10期。
很多理论家、思想家都曾指出过文学艺术通过特殊形象对普遍本质或真理的揭示:例如马克思称赞“现代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他们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686页。。别尔嘉耶夫指出:“莎士比亚、陀思妥耶夫斯基、列·托尔斯泰、司汤达、普鲁斯特·马塞尔等人在理解人的本质方面,比学院哲学家和学者(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贡献更大”。*[俄]别尔嘉耶夫著,张百春译:《论人的使命》,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年,第67页。按照海德格尔关于艺术“解蔽”的说法,“艺术就是真理自行设置入作品中”。*[德]马丁·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艺术作品的本源》,[德]马丁·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林中路》,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25页。总之,优秀作家艺术家所塑造的各种特殊的形象因为蕴含了深刻的真理或本质而同那些缺乏深刻思想蕴涵的一般形象区别开来。梵高《农夫的鞋》(1866)中所画的鞋子之所以不同于一般的鞋子,是因为它体现了农夫“充满劳绩”的苦难人生;果戈理《外套》中的外套之所以不同于一般的外套,是因为它体现了底层小公务员人生的悲酸;海明威《老人与海》中的桑提亚哥之所以不同于一般的老人和渔夫,是因为他体现了人在与自然的生死搏斗中不屈不挠的生命本质。正是典型形象的特殊性里蕴涵了普遍性与共性的特质,才使其超越了这个形象自身而成为普遍真理或本质的化身。黑格尔说:“形成真正的美和艺术的中心和内容的是有关人类的东西。”*[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2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63页。王国维指出:“夫美术之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惟美术之特质,贵具体而不贵抽象。于是举人类全体之性质,置诸个人之名字之下。”*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徐洪兴编选《王国维文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第178页。可见,文学形象对本质或真理的揭示是衡量典型的首要标准。对此,李泽厚说:“所谓典型,是着重在它的共性——本质——必然这一方面的。这一方面是典型本身中内在矛盾的矛盾主要方面。”*李泽厚:《典型初探》,《新建设》1963年第10期。
任何文学形象作为成功的艺术形象都是鲜明生动可感的具体形象,典型形象不同于一般形象的个性特征何在呢?其实,典型形象的突出个性特征是其特殊性。歌德提出“诗人究竟是为一般而找特殊,还是在特殊中显出一般”的问题,他主张“在特殊中显出一般”,强调“艺术的真正生命正在于对个别特殊事物的掌握和描述”。他认为“一个特殊具体的情境通过诗人的处理,就变成带有普遍性和诗意的东西”。*[德] 爱克曼辑录,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10页;第6页。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说“在欧仁·苏的小说里,阿娜斯塔西娅·皮普勒是巴黎看门女人的典型”*《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3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28页。,意在指出在皮普勒太太身上既体现了巴黎看门人的普遍特质,又表现了她自身性格和行为的特殊性,比如“嘴上刻薄”等特征。另外如《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与周进,同为旧科举制度下经历穷达变化、跌宕起伏的戏剧性人生的知识分子,二人都曾因科场失意而精神失常,然而周进参观贡院伤怀中风倒地终不如范进得知中举之后竟至于喜极而疯更有特殊性,因而也更富有典型性。《水浒传》中林冲与王进同为东京80万禁军教头,都曾受过奸臣高俅的迫害,然而王进之遭遇终不如林冲屡遭连环迫害之特殊,因而林冲比王进更为典型。
其二,典型是体现了某种理性观念或精神的独特审美形象。如果说从哲学角度来阐释文学形象和典型主要是讨论普遍与特殊的关系的话,那么从美学的角度来阐释文学形象和典型则主要是讨论观念或精神与具象直观的关系。西方美学家无论是康德、黑格尔还是叔本华都把美的形象看作是观念与具象的统一体。康德说:“美(无论是自然美还是艺术美)一般可以说是审美意象的表现”;又说:“观念在本质上是一种理性概念,而理想(Ideal)则是把个别事物作为适合于表现某一观念的形象显现。因此,这种审美趣味的原型一方面既涉及关于一种最高度(Maximum)的不确定的理性概念;另一方面又不能用概念来表达,只能在个别形象里表达出来,它可以更恰当地叫做美的理想。”*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403页;第395页。对此,朱光潜指出,“康德所说的‘审美意象’正是艺术典型,也正是他在‘美的分析’中所说的‘美的理想’”*朱光潜: 《西方美学史》下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402 页。。黑格尔强调“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又解释理念说:“按照这样理解,理念就是符合理念本质而现为具体形象的现实,这种理念就是理想。”*[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42、92页。按照朱光潜的说法:“黑格尔所说的‘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是美的定义也是艺术的定义,其实也就是典型的定义。典型在他的《美学》里一般叫做‘理想’,它是理性内容与感性形象的统一。”*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703页。康德、黑格尔关于艺术形象体现美的理想或理念的思想也为叔本华所继承。叔本华论艺术说:“艺术复制着由纯粹观审而掌握的永恒理念,复制着世界一切现象中本质的和常住的东西”。*[德]叔本华著,石冲白译:《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58页。即主张艺术是对理念的直观表现。无论康德、黑格尔还是叔本华所说的包含着理想或理念的美的形象其实也就是典型形象。对此,蔡仪曾指出:“个别之中丰富地显著地具现着一般,就是典型,因此也就是说,典型的东西是美的东西,美的本质就是典型的典型性。”*《蔡仪文集》第1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第239页。
一切艺术形象都是包含观念的直观形象,那么典型形象有何特征呢?其实,典型形象的突出特征在于它所体现的不是一般、普通的观念,而是某种有普遍性的特定观念。康德所说的理念是“一种最高度(Maximum)的不确定的理性概念”、黑格尔说“理念就是理想”、叔本华称之为“永恒理念”,可见他们心目中的理念是一种超出一般观念之上、更具有普遍意义的精神观念。
作为艺术形象来说,这就涉及一个问题:不仅典型所体现的是某种有普遍性的观念,而且这个特定审美形象自身必须具备丰富性和包孕性,而足以显现这种观念的全部内涵。康德曾指出“朱匹特的鹫鸟和它爪里的闪电是这威严赫赫的天帝的状形标志,而孔雀是天后的”,“这些东西给予想象力机缘,扩张自己于一群类似的表象之上,使人思想富裕,超过文字对于一个概念所能表出的,并且给予了一个审美的观念,代替那逻辑的表达”。*[德]康德著,宗白华译:《判断力批判》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161页。审美意象包括人物意象、事物意象,它与一般形象的不同在于蕴涵了某种观念或理念而超出了自身的意义。
文学典型的范围自然十分广泛,并不限于“审美意象”,其所体现的观念、精神也是复杂多样的,不过其作为有代表性的观念、精神的形象显现却是一致的。比如阿Q性格的丰富多面性及其所体现的精神胜利法,堂·吉诃德形象的戏剧性及其所显现的传统与现实相冲突的观念都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并且达到了观念精神与形象显现的和谐统一。
其三,典型是具有深刻的现实性又富有传奇虚构性的艺术形象。从艺术的角度来看,任何文学形象都具有思想现实性与艺术虚构性,即都是基于某种现实生活而进行艺术创造的结果。尽管文学史上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不同派别的作家按照不同的原则来反映社会生活,但是在文学形象的塑造上却大致遵循着共同的规律。通常认为“典型化”是文学典型创造的规律。而较早提倡“典型化”之说的是别林斯基,他在1839年评《现代人》里说:“典型化是创作的一条基本法则,没有典型化,就没有创作。”*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543页。过去我们提倡典型化,指作家运用概括化与个性化的方法把生活中的原型或故事熔铸成文学典型形象。不过此种方法既适于文学典型的塑造,同时也适于一般文学形象的塑造。按说典型化应该是塑造典型形象的方法,这种概括化与个性化结合的方法其实是一切文学形象的塑造方法,应该叫做艺术化。例如关于概括化,马尔克斯就曾说过:“文学的真实并非照相式的,而是概括的。而获取这一概括能力的基本因素,则是叙事艺术的一个秘密。”*[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门多萨著,林一安译:《番石榴飘香》,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186页。关于典型化为何又是文艺创作的一般规律,蒋孔阳解释说:“由于文学艺术都应当塑造典型,都应当通过鲜明的艺术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某些方面的本质规律,所以典型化也就成了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了”;至于作者能否真正塑造出成功的典型形象,那就要看各自努力的程度。*蒋孔阳:《形象与典型》,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第162页。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那些成功地塑造了典型形象的作者秘诀何在,典型塑造有没有不同于一般形象塑造的独特规律?塑造典型形象的真正奥秘可能就是那种凭着非凡想象力把生活或艺术中不够典型的形象进行意蕴的扩张和诗艺的升华的独特能力。那种真正的典型化应当是更高境界的艺术化,从而将一般生活原型或艺术形象提升为典型形象。
如果说文学典型与一般文学形象塑造都遵循着共同的艺术规律,那么文学典型与一般文学形象在艺术上的区别就不仅仅在于艺术塑造方法的不同,而在于艺术质量的不同。一方面,文学典型比一般的文学形象具有更为深刻的现实思想意义,承载着更为丰富的社会人生内涵。黑格尔论史诗时指出:“如果一部民族史诗要使其他民族和其他时代也长久地感到兴趣”,它就必须“能深刻地反映出一般人类的东西”。又说:“荷马史诗在直接的宗教伦理的题材,优美的人物性格和一般生活,以及诗人把最崇高和最猥琐的事物都写得活灵活现的艺术手腕这几方面都显得是一部永远有现实意义的不朽著作。”*[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3卷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24页。另一方面,文学典型比一般的文学形象又具有更为突出的艺术虚构性和传奇性、夸张性。例如《堂·吉诃德》中的主人公堂·吉诃德比桑丘·潘沙更为典型,《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比陈宫更为典型,并不仅仅在于作者把他们分配为一号或二号人物,而在于他们身上前者比后者蕴含了更为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体现了更多的传奇性与虚构性。从艺术上来说,典型的本质就是高品质的艺术形象。而这种高品质正在于其在思想与艺术表现上、现实深刻性与艺术虚构性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亚里斯多德在《诗学》第二十五章一段残缺的文字里曾提到,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著名画家宙克什斯绘制古代美女海伦像时,从全城少女中挑选出五个最美的女子,然后把她们各自美的特点集中起来。*[古希腊]亚里斯多德著,罗念生译:《诗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101页。这种美的叠加方法其实是艺术典型塑造中最为基本的艺术概括和虚构方法。
文学典型性格往往是一种复合结构,例如有的学者曾指出阿Q具有“二重组合性格”或“系统性格”。阿Q体现的现实深刻性、思想丰富性自不必言,其艺术虚构性、夸张性也达到了极点。不仅像阿Q这种具有所谓复杂性格的典型形象,就是具有某种单一性格特征的典型形象比如孔乙己、严监生等在其体现的现实深刻性与传奇虚构性方面也都是极为突出的。由此可见,是否具有复杂性格、是否圆形人物等因素只是划分典型形象级别高低的参照,并非区分典型形象与一般形象的标准。
其四,典型是能够成为某种典范或范式的诗性语言形象。以上我们分别从哲学、美学、艺术的视角来阐释文学典型的内涵,如果从文学自身的角度应该如何对典型作出解释呢?过去人们对文学典型的讨论很少从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本身进行考察,其实这是一种需要弥补的缺憾。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涉及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在由灿若群星的无数文学形象构成的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典型形象是其中最为明亮的星辰,它们作为某种典范或范型昭示着后来的一代代读者和作者。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典型都有“范型”、“典范”或“范式”之义,也就是说,其最初的含义是指的一种铸造某物的模具或模型,起着一种规范形状的作用。例如狄德罗在《演员奇谈》中要求画家或演员达到“理想的范本”或“理想典范”;莱辛在《拉奥孔》中称荷马对海伦美貌的描绘为“典范中的典范”;黑格尔称典型为“理想”等等。某种概念、范畴的原始含义往往体现着其最基本的内涵,后来的多种内涵都是在此基础上派生出来的。的确,在中外文学史上,正是阿喀琉斯、哈姆雷特、浮士德、安娜·卡列尼娜、诸葛亮、孙悟空、阿Q等一系列典型形象作为典范辉耀着文学的殿堂,引领着后世的阅读欣赏和创作。
另一方面,文学形象作为一种以语言为材料而塑造的形象,无不带有语言艺术塑造的特征,而作为典型形象则更加充分体现出语言塑造的独特方式与功能。譬如语言对人物性格特征与内在心灵的得天独厚的剖析、描绘,对象征、隐喻等艺术表现手法的全面运用等等,使得文学典型的复义性、多面性、深刻性达到了其他任何艺术都无法达到的程度,因而这些典型往往成为诸如绘画、雕塑、影视等其他艺术形象的母体。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人们称我为心理学家:不对,我只是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即刻画人的心灵深处的全部奥秘。”*[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冯增义、徐振亚译:《陀思妥耶夫斯基论艺术》,桂林:漓江出版社,1988年,第390页。歌德塑造的浮士德这一典型形象体现着深厚的原始蕴涵,有学者指出“《浮士德》涵盖全剧的主题是‘生命的金树才是长青’”,并指出其渊源:“《浮士德》的‘生命的金树’就是产生在‘树崇拜’原始文化积淀层的一个古老原型,它直接来源于《圣经·创世纪》,并在内涵上与《圣经》哲学及其近代诠释相承接。”*蒋世杰:《<浮士德>潜藏的原型象征体系》,《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又如关于典型人物塑造的多样化文学手法,有人曾指出塑造阿Q等典型运用的变形手法就有人物变形、精神变形、情节变形、意象变形、结构变形、语言变形等数种之多。*张梦阳:《阿Q新论:阿Q与世界文学中的精神典型问题》,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93-195页。
雨果论天才时曾将其比喻成红宝石,指出:“天才与凡人不同的一点,便是一切天才都具有双重的反光:……红宝石与水晶和玻璃不同就在于它有着双重折射。”*[法]雨果著,柳鸣九译:《莎士比亚的天才》,《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3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101页。可以说,典型与一般形象的不同也如同红宝石与水晶和玻璃的不同一样在于它有着双重的反光或折射。无论我们立足于任何不同角度都能够从正反两方面透视到其独特个体与母体发出的双重光照,感受到其瑰丽的色彩与迷人的魅力。
三、文学典型概念的顺势扩展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为了应对汹涌而至的欧美各种社会文化艺术思潮的挑战,摆脱典型理论不能解释文学现实的困境,有些学者提出了扩展典型概念的意见。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主张有两种:一是80年代初有人考察文学形象的变迁,尤其是典型由外在化走向内在化的趋向,提出了“新典型观”,指出“典型完全可以是某种典型观念、典型情绪感受、典型体验或典型心理”。*吴亮:《“典型”的历史变迁》,《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4期。90年代初有人更推进典型的泛化,进而提出“典型可以是典型人物、典型环境,也可以是典型主题、典型结构、典型情节、典型意象、典型气氛、典型心理、典型情绪等等”。*陆学明:《典型结构的文化阐释》,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209页。二是90年代中期有人从分析阿Q典型形象入手提出“精神典型”的新概念,认为阿Q、哈姆雷特、堂·吉诃德、奥勃洛摩夫、高略德金以及浮士德等世界文学中的著名人物形象都属于精神典型。
上述主张在当时文艺理论界引起了不同程度的争论。这里实际上涉及两个问题:一是文学典型概念能否扩展;二是文学典型概念究竟应当向何处扩展?关于前一个问题,需要分析随着文学的发展文学形象与典型是否还存在,如果二者仍然存在只是改变了形式,那么就需要反观一下我们对形象与典型的阐释是否恰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出调整或进行重新阐释。关于后一个问题,需要分析对典型概念的扩展意见是否合乎典型的本质特征,是否合乎叙事文学的规律。我们只能在符合上述条件的基础上对典型概念作出顺势扩展调整。因为文学形象与典型的共同本质特征就是它们必须是一种直观的形象显现,而不可能是直接的观念、心理或精神,因而那种试图把典型扩展为“典型观念、典型情绪感受、典型体验或典型心理”乃至“典型主题、典型结构、典型气氛、典型情绪”及“精神典型”的说法都是不妥当的。尽管论者强调“精神典型”是包含在形象之中的,是指“一种既有活生生的具象性又表现出普遍人类精神特征的典型人物”*张梦阳:《阿Q新论:阿Q与世界文学中的精神典型问题》,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97页。,但“精神典型”其实也就是“典型精神”,仍属于观念形态,不仅含义宽泛,而且概念本身体现不出文学典型形象显现的本质特性。关键问题在于文学艺术典型不同于人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典型:前者必须是具体形象;后者可泛指一切有代表性的、典范的事物。须知文学典型作为一种审美的形象是不能像标签一样随便贴到任何无法直观显现的抽象事物上的。对于文学典型的理解和阐释,这是一种不可逾越的界限。
如何在不违背形象与典型以及叙事文学的本质特性的情况下对典型概念进行顺势扩展呢?在我看来,大约有三个可以补充拓展的概念:
一是典型情节概念。如果稍微留意就会发现在传统的典型理论中存在着一个不合逻辑的现象:一般文学理论普遍认为人物、故事情节、环境为叙事文学的三要素,可是为什么通常只提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甚至典型细节而很少提典型故事情节呢?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大概有二:其一,典型理论主要是在叙事文学发展到以塑造人物为主的时代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而人们的关注点集中于典型人物及其性格。例如黑格尔曾说:“性格就是理想艺术表现的真正中心。”*[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300页。巴尔扎克说:“‘典型’这个概念应该具有这样的意义,‘典型’指的是人物,在这个人物身上包括着所有那些在某种程度跟他相似的人们的最鲜明的性格特征;典型是类的样本。”*《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10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5年,第137页。其二,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典型问题的论述中,只提到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而没有提到典型故事情节。现在需要辨析的问题是:首先,叙事文学作品中的故事情节是不是文学形象?其次,到底有没有典型故事情节?其实根据动、静之不同,文学艺术形象可分为静态形象与动态形象:人物性格与环境等属于静态形象;特定环境中展现人物性格的一系列行为动作即故事情节则属于动态形象。
历来对故事、情节、事件有不同的解释,其实情节就是写进文学作品中的故事或事件,其间并无本质的区别。一般说来,通称为故事情节或简称为情节较为规范合理。故事情节包括三个层次:即全书整体性故事或事件、书中某类故事或事件、具体的故事或事件的细节。例如《水浒传》叙述了北宋末年梁山起义及其失败的故事,这是全书的整体情节;其中林冲被逼上梁山过程中的一系列事件就是具体的情节;而林冲夫妻岳庙烧香被高衙内调戏却忍气吞声便是其中的细节。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中说“如《水浒传》七十回,只用一目俱下,便知其二千余纸,只是一篇文字。中间许多事体,便是文字起承转合之法”,即指全书整个情节而言;“《水浒传》一个人出来,分明便是一篇列传。至于中间事迹,又逐段逐段自成文字”,是指一系列事件而言;“如景阳冈勤叙许多‘哨棒’字,紫石街连写若干‘帘子’字等”,便是指细节而言。*陈曦钟等辑校:《<水浒传>会评本》(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6页;第17页;第20页。典型情节的功能和意义早已引起学者的关注,如有学者指出:“按照高尔基的理解,情节也是‘人物之间的联系、矛盾、同情、反感和一般的相互关系,——某种性格、典型的成长和构成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写出了典型人物的作品情节,未尝不可以比作或视为典型人物联系其环境的艺术纽带。凭借这条纽带的艺术活力,典型人物及环绕并促使典型人物活动的环境,才可以成为不可分割的浑然一体了。”*李希贤:《文艺典型系统引论》,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8-39页。
其实典型情节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古今很多理论家和作家都曾论及典型故事情节问题。亚里斯多德说:“悲剧是行动的摹仿,而行动是由某些人物来表达的,这些人物必然在‘性格’和‘思想’两方面都具有某些特点,(这决定他们的行动的性质〔‘性格’和‘思想’是行动的造因〕,所有的人物的成败取决于他们的行动);情节是行动的摹仿(所谓‘情节’,指事件的安排)”。在他看来,情节是由人物与事件共同构成的,行动是中心,“悲剧是行动的摹仿,主要是为了摹仿行动,才去摹仿在行动中的人”。正是着眼于情节、事件,他指出诗与历史的区别:“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并进一步解释道:“所谓‘有普遍性的事’,指某一种人,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会说的话,会行的事。”*[古希腊]亚里斯多德著,罗念生译:《诗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20页;第23页;第29页。其实,亚里斯多德这里所说悲剧是描述“有普遍性的事”即强调悲剧所叙故事的普遍意义,就是指的具有典型性的故事情节。既然文学形象中可以有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那么除了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之外,必然还可以有典型故事情节。巴尔扎克论典型一方面强调人物的重要性:“‘典型’指的是人物,在这个人物身上包括着所有那些在某种程度跟它相似的人们的最鲜明的性格特征。”*[法]巴尔扎克:《〈一桩无头公案〉初版序言》,见《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10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5年,第137页。另一方面指出事件的典型性:“不仅仅是人物,就是生活上的主要事件,也用典型表达出来。有在种种式式的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处境,有典型的阶段,而这就是我刻意追求的一种准确。”*[法]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前言》,《文艺理论译丛》第二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13页。恩格斯于1859年5月18日在《致斐迪南·拉萨尔》的信中提倡“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刻画一个人物不仅应表现他做什么,而且应表现他怎样做”,体现出对故事情节的高度重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57-558页。阿·托尔斯泰说:“艺术要进行概括不在于追求实验的数量。艺术寻求典型的事例”。*[俄]阿·托尔斯泰:《致青年作家》,见《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165页。蒋孔阳说:“在文学艺术作品中,不仅人物形象应当是典型的,具有典型性;就是情节事件、场面、自然风景等,也都应当是典型的,具有典型性。”*蒋孔阳:《形象与典型》,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第33页。可见,典型故事情节或故事情节的典型性几乎是文艺理论界公认的概念。
只要仔细分析一下那些具有艺术典型的文学作品,就可以看出,其实很多作品都是既有典型人物又有典型故事情节。《阿Q正传》、《哈姆雷特》、《堂·吉诃德》、《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各种文学名著中,每个典型人物都有典型的故事情节。
许多作家强调讲故事是小说写作的头等事情。福斯特说:“小说就是讲故事。故事是小说的基本面,没有故事就不成为小说了。可见故事是一切小说不可或缺的最高要素。”*[英]爱·摩·福斯特著,苏炳文译:《小说面面观》,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第23页。小说可以不塑造人物性格,却不能不讲故事。卡夫卡说:“我不描写人,我只讲故事。(人物——引者)这是图象,只是图象而已。”*叶廷芳主编,黎奇、赵登荣译:《卡夫卡全集》第5卷(随笔 谈话录),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22页。周大新强调:“故事其实是小说思想意蕴的负载者”,“小说家要想把自己对世界的哲学思考,对人生、对社会、对自然界的一些新的认识和体验表达出来,应该而且必须借助故事”。他甚至比喻说:“故事在这里就像一辆运行终点为读者心区的大车,作家把自己的所有思考装进这辆车上,大车便会平安地拉到读者心里。”*周大新:《漫说“故事”》,《文学评论》1992年第1期。莫言说:“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并谈到在其小说中对典型故事情节的创构:“在《丰乳肥臀》这本书里,我肆无忌惮地使用了与我母亲的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但书中的母亲情感方面的经历,则是虚构或取材于高密东北乡诸多母亲的经历。在这本书的卷前语上,我写下了‘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话,但这本书,实际上是献给天下母亲的,这是我狂妄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一样。”*莫言:《讲故事的人》,《文学报》2012年12月13日。
在很多情况下,文学作品之所以具有典型性并不是因为塑造了典型人物,而是主要叙述了典型故事。例如果戈理的小说《外套》中主要讲述的是小官吏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买外套、丢外套因而丧命及其化作专扒外套的幽灵的故事;贺敬之的《白毛女》叙述的主要是喜儿被地主逼迫逃走住进山洞变成野人以及解放后得救的故事。这类故事的典型性主要在于其所体现的普遍社会意义与事件的独特性、传奇性。
典型故事情节是多种多样的,不过其最为突出的特点是意蕴的普遍性与故事的传奇性。西方传奇故事如亚当与夏娃被赶出伊甸园、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耶稣死而复活、特洛伊战争、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生死恋等;中国传奇故事如牛郎织女、梁祝、白蛇传、天仙配等,无不如此。中国古代小说批评理论一方面非常重视传奇性,如:烟水散人徐震在《赛花铃题辞》中说:“予谓稗家小史,非奇不传。然所谓奇者,不奇于凭虚驾幻,谈天说鬼,而奇于笔端变化,跌宕波澜。”*朱一玄编:《明清小说资料选编》下册,济南:齐鲁书社,1990年,第837页。毛宗岗说:“作演义者,以文章之奇,而传其事之奇,而且无所事于穿凿,第贯穿其事实,错综其始末,而已无之不奇,此又人事之未经见者也。”署名金人瑞实为毛宗岗《三国志演义序》又谓:“三国者,乃古今争天下之一大奇局,而演《三国》者,又古今为小说之一大奇手也。”*朱一玄、刘毓忱编:《三国演义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52-253页。另一方面又强调故事的普遍意义,如:金圣叹《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指出:“想来姓王字实父此一人亦安能造《西厢记》,他亦只是平心敛气向天下人心里偷取出来。”又说:“总之,世间妙文,原是天下万世人人心里公共之宝,决不是此一人自己文集。”*伏涤修、伏蒙蒙辑校:《西厢记资料汇编》上册,合肥:黄山书社,2012年,第264页。他认为《西厢记》叙述的内容属于天下人心里共同拥有的故事,极其富有普遍意义。此种典型故事或者与典型人物、典型环境相得益彰;或者凭着故事本身的典型性而使文学作品获得不朽的价值和永恒的魅力。沿此路径我们不仅可以分析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而且能够解释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某些作品中的文学形象。例如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的典型意义不仅在于塑造了老布恩迪亚、乌苏娜、奥雷连诺等典型人物,而且在于叙述了体现封闭孤独症结的家族兴衰的具有传奇色彩的典型故事;卡夫卡的《变形记》与贝克特的《犀牛》虽然没有塑造典型人物,但是却述说了体现现代社会人性变异的人变甲虫、人变犀牛的具有象征意义和荒诞色彩的典型故事。因此它们都是富有典型意义的文学杰作,或者说它们都创造了具有不朽价值的文学典型。
二是典型意象概念。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探讨典型概念扩展时已经开始关注文学意象概念了。有学者指出:“现在,有许多人开始把意象视为各类艺术意蕴的最基本的载体,不管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还是现代主义,只要还有资格被称为艺术的,就都不能拒绝意象。典型难道不就是意象的最充分展开的一种形态吗?……意象,可能就是可以把典型领引到各类叙事性艺术里去的使者。”*柳万:《典型:说不尽的艺术理论话题——读叶纪彬的〈中西典型理论述评〉》,《文艺理论与批评》1995年第2期。亦有学者说:“自然主义、现代主义文学以来,典型并没有淡出舞台,而是结合新时代的生存境遇,与意象这一形象形态的‘他者’互参互证,形成同谋关系,从而获得了鲜活的发展。”并指出:海明威晚期作品《老人与海》中的桑地亚哥形象,明显不同于早期、中期表现压力下风度的“硬汉子”典型,而成为涵盖力更强的象征人类的意象。有限与无限相统一、抽象思维的直接介入,是典型与意象共同的审美机制。*常海波:《文学典型的审美机制》,《延安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根据形象中观念成分的多少,文学形象可有形象与意象的区分:一般所说的形象主要是具有某种自发性格的人物形象与自然的物象;而意象则是指体现某种观念或理念的人物与事物。意象一般分为抒情意象与叙事意象。中国传统文论中所谓意象主要是针对抒情文学而言的;西方所说的意象则是侧重于叙事文学而言的(当然美国以庞德为代表的意象派主要是受中国意象观念影响而产生的,其所倡意象侧重指抒情意象)。根据一般逻辑推理,既然文学形象中有典型形象,那么文学意象中也必然会有典型意象。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典型形象除了典型人物、典型情节、典型环境之外,还应包括典型意象。
西方意象理论中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康德关于审美意象的阐述。康德所说的审美意象是指包含着某种观念内涵的具体审美形象,而这个具体审美形象又是能够体现复杂蕴涵的特定形式。他在论及诗歌时指出:“诗开拓人的心胸,因为它让想象力获得自由,在一个既定的概念范围之中,在可能表达这概念的无穷无尽的杂多的形式之中,只选出一个形式,因为这个形式才能把这个概念的形象显现联系到许多不能完全用语言来表达的深广思致,因而把自己提升到审美的意象。”在康德看来,有很多形式可以显现某个概念,不过只有一个形式最能显现其全部丰富内涵。对此,朱光潜说“不难看出,康德所说的‘审美意象’正是艺术典型”。*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401页;第402页。
如果说康德所说的“审美意象”就是典型形象或典型意象的话,那么他所指的就是一个最能代表这种特定观念的审美形象。在叙事文学作品中,这种典型意象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侧重于意谓的实体意象;另一类是侧重于意念的隐形意象。不过二者往往都带有丰富而深刻的象征性或隐喻性。实体意象如“伊甸园”、“特洛伊木马”、“阿喀琉斯之踵”、“达摩克利斯之剑”、“潘多拉的盒子”、艾略特的“荒原”、卡夫卡的“城堡”、博尔赫斯的“迷宫”、钱钟书的“围城”、托尔金的“魔戒”、莫言的“蛙”等;隐形意象如斯芬克斯之谜、俄狄浦斯情结、木乃伊之咒、西西弗斯之怪圈、第二十二条军规等。典型意象中有不少属于心理意象。此类意象可称之为心灵中的幻影或幻象,是想象中的具象化存在,而非纯粹观念或精神的存在。
分析心理学派所说的“原始意象”或“原型意象”就属于这种典型的心理意象。荣格说:“一个用原始意象说话的人,是在同时用千万个人的声音说话。他吸引、压倒并且与此同时提升了他正在寻找表现的观念,使这些观念超出了偶然的暂时的意义,进入永恒的王国。”毫无疑问,作家就是这种“用原始意象说话的人”,因此,创作过程“就在于从无意识中激活原型意象,并对它加工造型精心制作,使之成为一部完整的作品”。*[瑞士]荣格著,冯川、苏克译:《心理学与文学》,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122页。当然在我们看来,文学中的典型意象不可能都是“原始意象”,现代生活方式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十分广泛、丰富的生活原型,作家依此创造出了更多现代意义上的典型意象。
三是典型情境概念。情境通常指某种情绪状态或生活处境。就抒情文学而言,情境侧重指由情景的描绘产生的情感状态或情绪氛围。而就叙事文学而言,情境侧重指人物特定处境中的生命情状。刘鹗《<老残游记二集>自序》云:“若百年后之我,且不知其归于何所,虽有此如梦之百年之情境,更无叙述此情境之我而叙述之矣。”*刘鹗:《老残游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220页。此处所说“情境”即意谓作者所处的特定生存状态。
西方美学中的情境理论以黑格尔的观点为最有代表性。在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有关艺术理想的论述中,“情境”是从“一般世界情况”过渡到“动作(情节)”的中间环节。如果说“一般世界情况”只是动作(情节)的前提的话,那么“情境就是更特殊的前提,使本来在普遍世界情况中还未发展的东西得到真正的自我外现和表现”。朱光潜在“情境”标题下注释道:“依黑格尔,艺术形象的决定因素首先是‘普遍的世界情况’,即一个时代的总的情况,其次是‘情境’,即某一个别人物和某一个别情节所由产生和发展的具体情境。例如歌德的《浮士德》所写的普遍世界情况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人生理想,其具体情境就是浮士德的个人遭遇。”*[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54页;第251页注①。在黑格尔看来,情境与外部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他认为外部环境的重要性体现在对人的关系和心灵的意义上:“它的重要性要看它怎样为个别人物所掌握,因而成为一种机缘,使个别形象表现的内在心灵需要、目的和心情,总之,它的受到定性的生命,得到存在。作为这种更切近的机缘,有定性的环境和情况就形成情境。”也就是说,情境是与人物内在心灵交织在一起的特定人生境遇。黑格尔特别指出情境的重要性:“情境供给我们以广阔的研究范围,因为艺术的最重要的一方面从来就是寻找引人入胜的情境,就是寻找可以显现心灵方面的深刻而重要的旨趣和真正意蕴的那种情境。”*[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54页。从黑格尔对情境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情境与通常说的环境既有密切联系又有差别,环境侧重指外在、客观的总体情况,而情境则侧重指内在、主观的个人境遇。例如《哈姆雷特》中哈姆雷特对于“活着还是死去”的生存焦虑、《第二十二条军规》中尤索林对于无法冲出生活怪圈的困惑等,所体现的就是一种典型情境。
除了黑格尔所说的情境之外,荣格提出的“原型情境”和“典型情境”,可以看作是典型情境的现代扩展。荣格指出:在文艺创作中,“一旦原型的情境发生,我们会突然获得一种不寻常的轻松感,仿佛被一种强大的力量运载或超度。在这一瞬间,我们不再是个人,而是整个族类,全人类的声音一齐在我们心中回响”*[瑞士]荣格著,冯川、苏克译:《心理学与文学》,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121页。。这种原型情境由于把个人的体验与全人类的体验融会在一起因而也就成为一种典型情境。荣格进而指出典型情境的特征:“人生中有多少典型情境就有多少原型,这些经验由于不断重复而被深深地镂刻在我们的心理结构之中。这种镂刻,不是以充满内容的意象形式,而是最初作为没有内容的形式,它所代表的不过是某种类型的知觉和行为的可能性而已。”*[美]霍尔等著,冯川译:《荣格心理学入门》,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44-45页。
另外,雅斯贝尔斯的“边缘情境”说也为典型情境提供了理论依据。雅斯贝尔斯提出的“边缘情境”说,系指一个人面临严重变故或陷入绝境时的一种存在状态。他指出:“人类由于面临自身无法解答的问题,面临为实现意愿所做努力的全盘失败而认识自己——所有这一切都以坚不可摧的秩序和善与恶的鲜明对照为背景。”*[德]卡尔·雅斯贝尔斯著,亦春译:《悲剧的超越》,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年,第10页。加缪《局外人》中的莫尔索、卡夫卡《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和《诉讼》、《城堡》中的K等,都属于这种处于边缘情境中的人物。
上述典型情节、典型意象、典型情境等概念的顺势扩展,体现了典型理论发展的必然趋势,进一步扩充了典型理论的内涵和适用范围,使之具有更大的包容性,不仅可以解释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也可用以解释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各种文学现象。
四、文学典型的现实生态与发展前景
我们对文学典型问题的认识既不能仅仅局限于文艺理论界众说纷纭的争论,更不能依据那些言过其实的观点,而应当根据叙事文学自身的规律与文学创作发展的现实来正确判断文学典型的生态现状。
通常认为源自西方的典型理论是针对叙事文学的;而中国的意境理论则是针对抒情文学的。当然也有学者主张典型既可用于叙事文学,也可用于抒情文学,它与意境二者之间是可以打通的。如李泽厚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曾提出:“‘意境’的创造,是抒情诗、画以至音乐、建筑、书法等类艺术的目标和理想,‘意境’成为这些艺术种类所特有的典型形态。”*李泽厚:《典型初探》,《新建设》1963年第10期。近年来又有学者主张:“艺术典型的基本含意是以个别偶然现象表现一般必然本质。叙事艺术重刻画典型性格,抒情艺术则重创造典型意境。”*杜书瀛:《中国古典美学的典型理论——中国和西方典型理论的对比》,《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典型理论作为一种揭示文学艺术普遍规律的学说,当然也可以解释抒情文学,不过它是从叙事文学中归纳出来的,与叙事文学有着更为密切的有机联系,其理论生命力更需要通过发展变化的叙事文学来验证。
典型理论的困境主要在于叙事文学现实的改变,关键的问题是叙事文学的发展是否将会使典型在创作实践上走向终结?这里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叙事文学的现代发展是否会消解形象与典型存在的基础?答案是否定的,其原因有二:
其一,文学以对现实的阐释和关注为根本出发点,基于现实的言说和讲述是叙事文学的本质特征之一。无论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还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创作其叙事方式发生了怎样的发展变化,但是叙事文学的现实基础却是始终不变的。正如有学者所说:“从陀思妥耶夫斯基敏感而小心翼翼的探索开始,到目前欧洲小说、戏剧、电影对于非人化的现实所作的强烈的批判为止,整个欧洲文学的发展构成了不断阐释现实的主要线索。所不同的是,卡夫卡运用寓言的方式,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更加关注现实在个人心理上投下的阴影的分析,更加注重个人充满激情的反叛,而罗伯·格里耶则创造了与物化现实相仿的文本结构。”*格非:《小说叙事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0页。基于现实的叙事或者说阐释现实的叙事必然离不开对现实的感悟,仍然要表现社会人生的主题。也就是说,文学的使命仍然是通过形象显现揭示社会与生命的本质或真理,仍然需要塑造形象或典型。不过这个典型既可以是典型环境中的人物,也可以是典型情节或者典型意象、典型情境。
其二,所谓叙事就是讲故事,因此叙事文学的标志是讲故事,或者说故事是叙事文学的基本形态。尽管叙事文学在叙事方式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叙事本身却不可能取消。例如就小说而言,有学者把传统小说与现代小说分别称之为“小说叙事的故事时代”和“小说叙事的小说化时代”,指出“在小说的故事时代,一切叙述都是围绕‘故事’来进行的;而在叙事的小说时代,一切叙述都要服从于‘人之内心感觉’来进行”;“传统小说写的是‘故事化的生命和社会’,而现代小说写的则是‘生命和社会化的故事’”。早在19世纪后期,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就曾在《小说的艺术》一文中说过:“如果要给小说下一个最宽泛的意义,那就是个人对生活的直接印象。”*倪浓水:《小说叙事研究》,北京:群言出版社,2008年,第32页;第72页;第39页。从个人感受出发而不是从外部写实出发的写作为现代小说开辟了更为广阔的表现领域、更为复杂多变的表现形式。例如意识流小说对人的内心世界的深入展示,“新小说”派对叙事的多样化探索,结构现实主义对小说结构的创新等等,都体现了现代叙事的丰富多彩和标新立异。不过透过五光十色的现代艺术表现方式,我们仍能够看出讲述故事依然处于核心位置。无论是福克纳《喧哗与骚动》中那种通过变换视角讲述的故事,还是海明威《老人与海》中那种通过心理呈现讲述的故事,故事情节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是十分典型的。由于现代作家叙事视野变得更加开阔、叙事方式变得更加多元,往往通过内在视角表现外在现实或有意留下空白以与读者互动,文本中的故事可能变得不够完整甚至残缺不全,不过那些优秀小说中的故事情节即使显得支离破碎,也往往是非常典型的。
另一方面,叙事文学特别是小说叙事的意象化发展趋向会不会冲击甚至消解典型本身?答案也是否定的。现代小说的意象化发展趋势似乎已是公认的事实。其实小说的意象化并非始于现代,某些古典小说早已带有意象化特征。例如有学者指出:“贾宝玉的形象,半是现实的,半是意象的”,或者说贾宝玉是意象化的小说人物,是作家的心灵的映象*袁世硕:《贾宝玉心解》,《文史哲》1986年第4期。;孙悟空也是“一个完全意象化的形象”*朱占青:《孙悟空:一个完全意象化的形象》,《飞天》2011年第4期。。至于现当代文学中的意象化趋向则更为明显,有人指出阿Q、狂人“两个人物是严格的人物意象”,“都具有极强的典型性”,“又都具有鲜明的意象性”。*邢海珍:《小说的诗意空间与意象化努力》,《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3期。至于沈从文、张爱玲、苏童、余华等现当代作家小说中的意象化现象更是普遍存在。小说的意象化发展表明叙事文学跨越边界向抒情文学靠拢,或者说是由客体再现向主体表现过渡。其实这种意象化的发展趋势乃势所必然。一是以外在视角讲述故事、塑造人物、描述环境毕竟不如以内在视角叙事来得方便,并且更能使人感同身受。二是无论叙事文学还是抒情文学最终所致的目标无非是要表达某种思想意图——对社会人生的体悟,讲述故事、塑造人物、描述环境只是表现手段而已,那隐藏在背后的思想主旨才是作家最终的底牌。如此说来,假如通过内在心理的意象化叙事能够直接表达某种思想感情,那么何必要去花费大量心思和笔墨去塑造人物、叙述故事、描写环境呢?不过这里有两条不可逾越的底线:一条是必须通过形象来显现的底线,也就是说作家不能直接说出某种立意主旨,而需要以具体的形象来呈现。另一条是必须运用叙述的方式而非直接抒情表意的方式来体现主题意旨。逾越了第一条底线便走出了文学的边界;逾越了第二条底线便走出了叙事文学的边界。无论是对西方意识流、超现实主义、荒诞派文学创作,还是对深受西方现代派、后现代派影响的中国当代“新潮”、“先锋”派任何标新立异的创作,这二者都是不可逾越的红线。
另外,对于意象化的叙事文学来说,还有两个衡量其价值的条件:第一是看作品中表达的观念意旨与形象显现是否达到了和谐恰切的程度。康德强调审美意象通过表象所表现出的观念应当是最为充分的,它是别的任何概念都无法代替的。黑格尔一再指出通过感性显现的理念必须是理念与形象之间最为和谐和恰如其分的,这才是美的理想。只有观念意蕴的形象显现达到充分完美的程度时才是典型之作。第二是文中塑造的形象是否体现了某种普遍性的特殊形象。特殊与一般的关系问题,不仅是古典文艺理论家、作家探讨的重要问题,例如歌德、黑格尔等有过深入的论述,而且也是现代心理学家、作家普遍关注的中心问题。例如荣格提出的“原型”或“原始意象”理论强调个人的意识中积淀着“集体无意识”,这种“集体无意识”是一种既有历史纵深性又有社会普遍性的思想意识。这种理论为意象化叙事文学中的“原型”或“原始意象”的创造奠定了思想基础,进而拓宽了典型的适应领域。又如艾略特提出的“非个人化”主张,强调文学创作不是为了表达作家纯粹的个人思想感情,而是表达一种普遍性的思想感情。他说:“一个艺术家的前进是不断的牺牲自已,不断的消灭自己的个性”;“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美]艾略特著,卞之琳译:《传统与个人才能》,杨匡汉、刘福春编:《西方现代诗论》,广州:花城出版社,1988年,第76页;第80页。其实这种非个人化的创作思想暗含着向传统的回归和对普遍观念的表达,使个人的哲思与人类共同的观念融合为一。一部意象化叙事作品如果其所创造的特殊形象充分体现了某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深刻观念,它便成为具有典型意象的优秀作品。
我们从创作实践上考察文学典型问题,既要关注现当代文学创作中意象化发展的变相,又要注意传统文学创作方式发展的常态。首先,如果把那些实验性的先锋文学创作与受大众欢迎而产生普遍影响的畅销书对照起来看,就会发现后者往往都是一些人物相对鲜明、故事情节较为完整或采用传统叙事方法的作品。此种畅销书一类如: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海明威的《太阳照样升起》等;另一类如罗伯特·詹姆斯·沃勒的《廊桥遗梦》、渡边淳一的《失乐园》、尼古拉斯·埃文斯的《马语者》、托尔金的《指环王》、罗琳的《哈利·波特》等等。其次,如果从小说改编成电影的情况来看,也是那些人物、故事、环境等叙事要素比较齐全的作品才容易被搬上银幕,而那些过于意象化的作品则难以为观众所接受。例如表现主义代表作卡夫卡的《城堡》与《变形记》,后现代主义特色较强的纳博科夫的《微暗的火》、克劳德·西蒙的《弗兰德公路》、博尔赫斯的《交叉小径的花园》之类的小说似乎至今仍未被搬上银幕;而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流年》、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等意识流小说在电影改编时大多把通过心理呈现的现实变成直接的视觉现实。尤其是《老人与海》(美国1958年)不得不用大量画外音与主人公独白来推动故事的进展;根据约翰·福尔斯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法国中尉的女人》(法国、意大利1999年)不得不把小说开放式叙事所提供的三种不同结局只保留一种结局;而根据扬·马特尔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影片《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国台湾2012年)则通过主人公讲述的方式以表现对故事的双重解读。中国当代小说被改编成电影的情况大致也与此相类似。例如张爱玲的《金锁记》、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红高粱》、余华的《活着》等,概因其人物鲜明、故事性较强、环境具有特色而被搬上银幕,而那些过于意象化的作品则难以改编且很难受到观众的欢迎。
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它像镜子一样折射出一些带有普遍性、本质性的问题:叙事文学作品与叙事艺术作品有着共同的叙事规律,那就是对人物、故事情节、环境基本要素的保留。作为小说的叙事文学可能对意象化(包括人物、故事及语言的意象化)情有独钟,但作为电影(故事片)这种视觉性、叙事性很强的叙事艺术却要求有更为直观的形象展现和艺术表达。同时还反映出叙事艺术审美接受的规律,那就是作为接受主体的观众也是更易接受那些形象鲜明、故事完整、环境优美的艺术作品。文学与电影两方面反映出的情况可能体现了叙事文学与叙事艺术所应遵循的某种共同规律,对人物、故事、环境基本要素的坚守不能看作是对传统叙事的留恋或者是保守落后的表现,它很可能是叙事艺术发展中始终处于基础层面的稳定性的恒态。而那些不断变换的叙事策略,诸如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丰富多变的叙事策略方式可能是处于基础层面之上的非稳定的动态。叙事文学意象化发展走向极端化的尽头很可能再也无路可行,只能另辟蹊径或者反过来向传统的叙事方式回归。
只要叙事文学与叙事艺术仍然存在,文学和艺术叙事的规律就不会被取消;只要在文学艺术创作与审美接受中形象与典型仍然受到关注甚至普遍欢迎,典型理论就不可能废除。文学典型问题与典型理论将会在对不断发展的文学艺术的全面观照中,寻求更为合理的解答和科学的阐释。
Contemporary Thinking on the Problem of the Typical (Tupos) in Literature
Zhou Bo
(School of Liberal Arts,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250014)
It is an undisputable fact that the theory of the typical (Tupos) in literature has been laid aside or ignored in recent years. However, the value of a literary theory should be judged by its own meaning and the developed creative practice and social reality. The mastering of its essence should rely on delving into its academic theory. It is, therefore, of important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to review the discussion of the typical (Tupos) in literature carried on since the new period, and, based upon this, to strive to follow the inherent nature of literary image and principle of narrative literature, and, with an eye to cultural diversity and literary vision, to re-interpret the essence of the typical (Tupos) and integrate modern ideas into 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y, aesthetics, art, literature etc. so as to explore the resultant expansion of the concept of the typical (Tupos) in literature into typical plot, typical image and typical situation in relation to the creative reality, and the issues of the actual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of development of the typical (Tupos) in literature.
the typical (Tupos) in literature;typical image;typical situation;resultant expansion;contemporary thinking
2014-08-21
周波(1952—),男,山东枣庄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I025
A
1001-5973(2014)05-0025-18
责任编辑:孙昕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