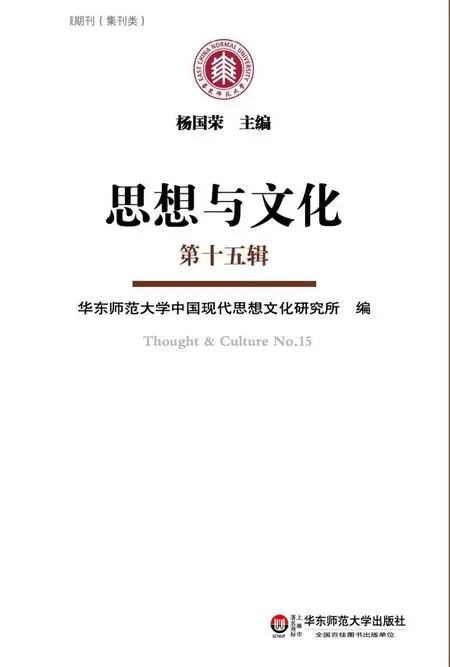尊祖—敬宗—收族:宗法的结构与功能*
●
关于宗法的意义,《礼记·丧服小传》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祢也。”《礼记·大传》云:“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义也。”“自仁率亲,等而上之至于祖,自义率祖,顺而下之至于祢。是故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
收族,收族故宗庙严,宗庙严故重社稷,重社稷故爱百姓,爱百姓故刑罚中,刑罚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财用足,财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礼俗刑,礼俗刑然后乐。”如果说《大传》是解释《仪礼·丧服》的,那么《丧服》对宗法的意义有何阐发呢?《丧服传》“齐衰期”章:“大宗者,尊之统也。禽兽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筭焉?都邑之士,则知尊祢矣。大夫及学士,则知尊祖矣。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统上,卑者尊统下。大宗者,尊之统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绝。”《丧服传》“齐衰三月”章:“尊祖故敬宗,敬宗者,尊祖之义也。”不难看出,理解宗法的功能与意义,必须理解以下三个关键词:尊祖、敬宗、收族。《礼记》所载七十子后学对宗法意义的论述就集中在这三个概念及其关联上。但要深刻地理解三者及其关联,必须思考宗法结构的三重向度,这就是以子继父、以兄统弟、以嫡统庶。
一、 宗法的内在结构之一:以子继父
宗法系统的纵向结构便是“以子继父”。以子继父将祖与宗加以关联,从而使得尊祖与敬宗之间,具有相互构成、彼此支撑的结构:尊祖所以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祖作为先人,是已经去世了的亲人,宗是祖死后其继续存在的形式,故而由“继”祖而后有宗,宗之为宗在于以继祖为前提。尊祖是亲亲原则的自然展开。《丧服传》有“父子一体”、“父子手足”之说,父子基于血缘的一体性,因遗传基因、血型等而有气质上的家族相似与人格上的类型相应。*贾公彦的疏解是:“谓子与父骨血是同为体,因其父与祖亦为一体,又见世叔与祖亦为一体也。……人身首足为上下,父子亦是尊卑之上下,故父子比于首足。因父子兼见祖孙,故马云首足者,父尊若首,加祖在期,子卑若足,曾孙在缌也。”郑玄注、贾公彦疏:《仪礼注疏》卷30《丧服》,《十三经注疏》(整理本),第11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663页。是故《礼记·祭义》云:“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父子关系具有绵延性,父母精血之结合而后乃有其子,出生之后,脱离了父母之躯体,但遗传等因素仍然维持着生物的一体性,而通过发生在家中的共同生活,父母则以无意识的习惯与有意识的教化提升了这种一体性。由父而上及祖,由子而下及孙,由此而构筑了父系家族的一体绵延,此即《丧服小记》所谓的“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其意即由自己出发,上亲父,下亲子,是为三;又因父而上亲祖,下亲孙,是以三为五;又因祖而亲曾祖、高祖,因孙而亲曾孙、玄孙,是以五为九。从自己出发,从三(父—己—子)到五(祖—父—己—子—孙)到九(高祖—曾祖—祖—父—己—子—孙—曾孙—玄孙),亲情渐渐疏远,而丧服亦渐渐由重而轻,《丧服小记》所谓“上杀,下杀,旁杀,而亲毕矣”。由此可以看出,一般人由己而亲父亲子,扩展到亲祖亲孙,实是亲亲原则由近及远之扩展。《玉篇》将“祖”界定为“父之父”,但一般地人们也将高祖、曾祖等先人称为祖。《说文》认为,祖的本义是“始,庙也”,段玉裁注:“始兼两义。新庙为始。远庙亦为始。故祔祪皆曰祖也。《释诂》曰:‘祖,始也。’《诗毛传》曰:‘祖,为也。’皆引申之义。如‘初’为衣始,引申为凡始也。”但现代学者已经发现,祖在甲骨与金文中一般做“且”,不加“示”旁。“且”的意思可以这样理解,“一”意味着地,而“一”上面的部分或者意味着游牧时代屋宇之形,盖谓祀先之所,或者神主之象形,且即主也。*李圃主编:《古文字诂林》第一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第139—144页。故而《说文》以“始庙”释“祖”有其深刻意蕴,依照王筠,“始庙”当读为“始,庙”也。一则谓祖为先人,一则谓祖为对先人的祭祀。先人固然从血缘的意义上已经为祖,此是祖的被给予义,其被给予的主体是死者而不是生者;但祖更在生者的祭祀活动中成其为祖,此是祖的构成义,其构成的主体是生者,而不是死者。《广韵》谓“祖”为“始也,上也,本也。”即以祖与生者之关系而立论,祖在自然的意义上构成生人之始、之上、之本,但尊祖乃是生者之崇本、报始、追上之人文情怀。《丧服传》云:“禽兽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则知尊祢矣,大夫及学士则知尊祖矣。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从禽兽到野人,从野人到都邑之士,从都邑之士到大夫及学士,从大夫及学士到诸侯,从诸侯到天子,可以看到其从不知父到知父而不尊父,再到尊父而不尊祖,再到尊祖、尊太祖、尊始祖的层层上推,随着生者身份地位及内含在身份地位中的德能之变化,其所尊之先人,愈来愈远,这也就将“报本反始”的活动不断推向时空上的远方,从而形成“本支百世”的宗族世系绵延的意识。在“本支百世”的宗族意识中,祖虽然已经死去,但特定的生者(宗子)仍然构成其继续存在的载体,甚至是其临在形式。由此而获得的先祖与其历代世嫡之间的一体性,便不再是自然人的血缘意义上的一体性,而是作为宗族体现意义上的一体性,是宗族祭祀不绝(香火不断)的保证。《丧服传》解释父为嫡长子的丧服何以是最高最重的斩衰三年时说:“正体于上,又乃将所传重也。”*《仪礼注疏》卷29《丧服》,《十三经注疏》(整理本),第11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640页。相比之下,父亲为庶子为后者则不得服三年之丧,原因就在于庶子为后虽可继父但不能继祖。郑玄以“重其当先祖之正体,又以其将代己为宗庙主也”解“正体传重”,贾公彦疏云:
云“正体于上,又乃将所传重也”者,此是答辞也。以其父祖嫡嫡相承,为上已又是嫡承之于后,故云正体于上。云又乃将所传重者,为宗庙主是有此二事,乃得三年。云“庶子不得为长子三年,不继祖也”者,此明嫡嫡相承,故须继祖乃得为长子三年也。
云“重其当先祖之正体”者,解经正体于上。又云“又以其将代已为宗庙主也”者,释经传重也。云“庶子者,为父后者之弟也”者,谓兄得为父后者是嫡子,其弟则是庶子,是为父后者之弟,不得为长子三年。此郑据初而言,其实继父祖身三世,长子四世乃得三年也。*《仪礼注疏》卷29《丧服》,《十三经注疏》(整理本),第11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640页。
简单地说,“正体”意味着以世嫡身份出现的宗子与先人为一体,虽然先人的子孙都可与先祖为一体,也即皆可“体于上”,但唯有世嫡是“正体”。作为世嫡的“大宗是远祖之正体,小宗是高祖之正体。”*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三十四《大传》,《十三经注疏》(整理本),第14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1176页。“传重”意味着为宗庙主,负责主持祭祀先祖,而在“国之大事,在祭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的社会—政治形态中,主祭权无疑是极为重要的权力,它与采邑、禄田的持有以及宗族的共同财产的管理关联在一起,后者支持并强化了主祭的权力。正体与传重结合在一起,刻画了世系相继的几种可能性,也就是孔颖达区分的正体承重的四种情况:“一则正体不得传重,谓嫡子有废疾,不堪主宗庙也;二则传重非正体,庶孙为后是也;三则体而不正,立庶子为后是也;四则正而不体,立嫡孙为后是也。”*《仪礼注疏》卷29《丧服》,《十三经注疏》(整理本),第11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641页。对以正体承重为正体的宗道而言,上下世代的嫡嫡相承,其核心是以嫡庶之分为基础的“以子继父”,而以继祖、继曾祖、继高祖、继始祖则是以子继父原则的延伸。这一点可以从上文所谓的亲亲之道“以三为五,以五为九”的论述中看出。王国维所谓的“宗必有所继”,意味着宗道是以“以子继父”的原则为基础的,而继祖、继曾祖、继高祖、继始祖则都可以分解为不同世代的以子继父及其叠加。例如,正体传重的继祖必然是嫡子继嫡父,而此“嫡父”以嫡子身份继祖。由以子继父及其延伸的世系上通过继而达到的一体性,就构成了“宗”。祖即便去世,但其宗仍在,而继祖继祢的嫡子被称为“宗子”。尊祖必然敬宗,“尊崇其祖,故敬宗子,所以敬宗子者,尊崇先祖之义也。”*《礼记正义》卷三十四《大传》,《十三经注疏》(整理本),第14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1176页。而“以子继父”则在祖与宗之间加以连接,故而它是宗法结构中重要的一个环节。
“以子继父”中的“继”,金景芳先生指出,是指人的继续。金氏以《仪礼·士冠礼》“天子之元子犹士也,天下无生而贵者也。继世以立诸侯,象贤也”与《公羊传》文公九年“是子也,继文王之体,守文王之法度”为例,阐发“继”的意义:“继体之君,事实上虽然无可怀疑是在独立地行使自己职权,但在理论上却须这样说,他是始封之君的继续,他所执行的是始封之君的职权,不是自己的职权。正由于这样,明明鲁隐公元年是周平王四十九年,可是,《公羊传》解释《春秋》‘隐公元年春王正月’时,却说:‘王者孰谓?谓文王也。’其道理就在于此。……可知继别的继字,其意义,是由嫡长子继承,为先人的继续,意思是说,人虽然不能永世长存,有了继承人就与本人长存一样。”*金景芳:《论宗法制度》,舒星、彭丹选编:《金景芳儒学论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第649—650页。通过“继”,死去了的先祖得以通过其继承人(宗子)继续存在,而宗子本身也通过“继”而使得自己符号化了,“父子一体”,他不再仅仅作为个人,而是作为死去的先祖的代表,以代表先祖作为全族的统纪之中心去统理族人。“继”的观念使得宗子具有了来源于先祖的正当权力,同时也使得宗族成员由此而有世代生成的时间意识。在周人的意识深处,王者与诸侯具有鲜明的“系世”意识。《小史》“掌邦国之志。尊系世,辨昭穆。”这里所谓的“系世”,郑玄注云:“谓帝系、世本之属是也”,贾公彦疏谓:“天子谓之帝系,诸侯谓之世本。”*《周礼注疏》卷二十六《小史》,《十三经注疏》(整理本),第8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821页。《瞽矇》:“世奠系。”郑玄注曰:“世奠系,谓帝系,诸侯卿大夫世本之属是也。小史主次先王之世,昭穆之系。述其德行。”*《周礼注疏》卷二十三《瞽矇》,《十三经注疏》(整理本),第8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725页。这种系世体制化的努力构成《史记》叙述结构之蓝本,司马迁《史记》中,记录有天子者名为“本纪”,而诸侯则名为“世家”,而卿大夫则有“列传”。周人的“本支百世”的系世意识不仅在天子诸侯那里得以体制化,而且在士大夫阶层也根深蒂固,《诗经·大雅·文王》不只说“文王孙子,本子百世”,更谓,“凡周之士,不显亦世”。不仅仅文王之子孙嫡者为天子,庶者为诸侯,皆得以百世绵延;而且,凡周之士人,亦得以继世而食禄,由此而有深层的世代意识。这种时代生成的时间与世系意识,深深地根植在周人心理的深处,周人不断地用植物等对于这种意识加以阐发。*参看高木智见:《先秦社会与思想——试论中国文化的核心》,何晓毅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第60—69页。所谓的“本支百世”,其中的“本”与“支”正是以树为喻,将内在于宗法中的世代生成的时间意识予以揭示,在这种时间意识中,每个人都可以在宗族世系之树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且通过宗族共同体的绵延而使自己的生命得以承传。后来以“万岁”、“千岁”、“万世”等一系列词语所表露的仍然是这种指向不朽的系世意识。在这种系世意识中,死去了的先人以承受祭祀的鬼神的方式,在其继承者那里继续存在,参与生者的生活,于是,“人神一体”,使得宗族本身不再仅仅是社会的人伦共同体,更重要的是人神共同体,因而宗族本身由继而获得了某种神圣性。“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此之谓“世禄”,而将世禄体制化的方式则是天子与诸侯的世及制度与世卿制度,在这一制度中表达了“盛德必百世祀”*《左传》昭公八年。的世代绵延意识,而这种世禄在更深层的意义上被视为因为有德而得以配享的“天禄”,“三代令王,皆数百年保天之禄”,*《左传》成公八年。周人忧虑的是“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论语·尧曰》。《尚书·大禹谟》:“慎乃有位,敬修其可愿,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这就是隐藏在“以子继父”中深层的世系意识的宗教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宗法的意义,则庾亮(289—340)的陈述值得注意:“是以祖宗之正不易,则本枝昭穆历百代而不乱,此立宗之大旨也。”*杜佑:《通典》卷七十三,《事宗礼》,北京:中华书局,1988,第1994页。
二、 宗法的内在结构之二:以兄统弟
如果说“以子继父”是宗法结构的纵向原则,它以连接生者与死者、人与鬼神的方式,缔造了充实时间的系世意识,那么,宗法结构中另一重要原则则是“以兄统弟”,它是宗法结构中的枢纽与核心。所谓的“敬宗”,就是群弟尊重、敬重作为先祖之现实体现者的嫡兄。宗法可以解析为宗之者(宗人、支子)与所宗者(宗子)之间的关系。郑玄在解析“继祢者为小宗”时说:“别子庶子之长子,为其昆弟为宗也。”*《礼记正义》卷三十二《丧服小记》,《十三经注疏》(整理本)第14册,第1123页。这就将宗人与宗子的关系界定为兄弟关系,嫡兄为宗子,其庶昆弟宗之。孔颖达的疏解对于这种关系予以了再次确认:
言“或继高祖,或继曾祖,或继祖,或继祢”者,以别子之后,族人众多,或有继高祖者,与三从兄弟为宗,或有继曾祖者,与再从兄弟为宗,或有继祖者,与同堂兄弟为宗,或有继祢者,与亲兄弟为宗,不废族人。一身凡事四宗:事亲兄弟之嫡,是继祢小宗也;事同堂兄弟之嫡,是继祖小宗也;事再从兄弟之嫡,是继曾祖小宗也;事三从兄弟之嫡,是继高祖小宗也。于族人唯一俱时事四小宗,兼大宗为五也。*《礼记正义》卷三十二《丧服小记》,《十三经注疏》(整理本)第14册,第1123页。
“继祢者为小宗”,谓父之适子,上继于祢,诸兄弟宗之……“小宗四”谓:“一是继祢,与亲兄弟为宗;二是继祖,与同堂兄弟为宗;三是继曾祖,与再从兄弟为宗;四是继高祖,与三从兄弟为宗。”*《礼记正义》卷三十四《大传》,《十三经注疏》(整理本)第14册,第1175—1176页。
换言之,在作为宗法基本关系结构的被宗者与宗之者之间,其关系的主体样态是兄弟关系。同父的兄弟宗其继祢的嫡兄,同祖的堂兄弟宗其继祖的嫡兄,同曾祖的再从兄弟宗其继曾祖的嫡兄,同高祖的三从兄弟宗其继高祖的嫡兄。同始祖的群兄弟在其诸小宗的统领下去宗别子的“世嫡”,而这一世嫡在理论上也当在群兄弟之间为兄弟关系。程瑶田(1725—1814)推进了孔颖达对宗法精神的上述理解,而将宗法概括为“兄道”,大小宗宗子以嫡兄的身份统领他的庶兄弟与族人。“宗之道,兄道也。大夫士之家,以兄统弟而以弟事兄之道也。”*程瑶田:《宗法小记》之《宗法表》,《程瑶田全集》卷一,合肥:黄山书社,2008,第137页。程瑶田进而指出:“宗”本身是“主”的意思,所谓的继别为宗,因此就是“继别者,一人而为群弟之所共主也。由是继别者,与其群弟皆各为其子之祢,而其子则各有一人为嫡,继其祢以各为其庶弟之所宗,是之谓小宗。而诸继祢之宗,其为继别子之所自出者,犹是继别之宗也。众小宗各率其弟而宗之,世世皆然。”*程瑶田:《宗法小记》之《宗法表》,《程瑶田全集》卷一,合肥:黄山书社,2008,第137页。这意味着,典型意义上的宗法虽然面对的是上下世代之间的纵向关系,但实际上主要以处理同代而不同世的诸兄弟之关系为主轴。兄弟们之间的亲疏远近要通过是同父、同祖、同曾祖、同高祖等而分别出不同的世数,由此而彼此之间有亲兄弟、堂兄弟(从兄弟)、再从兄弟、三从兄弟等的亲疏远近的差别。兄弟之间的血缘关系越远,就要通过对越来越远的祖先(从父到祖,再从祖到曾祖、高祖,直到始祖)的祭祀等方式来凝聚,而担负这些不同世数兄弟之间收族任务的就是大小宗的宗子。以过去先祖之名义收现在之兄弟,使之按照血缘亲疏远近的程度而构成不同的宗法共同体。就此而言,宗法之道的核心是横向的而不是纵向的,是兄弟之道,而不是父子之道。大宗与小宗之间并不是上下两代或几代的关系,而是同代基于嫡庶之别而产生的兄弟关系。毛奇龄意识到:“立宗,为兄弟而设。《周礼·大宗伯》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故凡宗人燕飨,其为诗诵叹,多称兄弟,如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类。而《左传》‘华亥欲代其兄’,则左师曰‘汝丧而宗室,与人何有?’”*毛奇龄:《大小宗通绎》,《清经解清经解续编》第9册卷十,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第91页。大宗与小宗的区分作为周代宗法制度的极为重要的特质,它与周代分封制度产生的兄弟之“国”与兄弟之“家”这样的政治文化现象息息相关,是周人一统之策的一个部分。而且,即便是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这一基于周代社会构造与文化机理的宗法在西周之前并没有出现,而在战国之世就已经瓦解,尤其是在封建制度解体之后,大宗之法在战国以后就再也没有实行过。
作为王制的宗法所针对的兄弟关系,并不是战国以后核心家庭形态之内的兄弟关系,而是宗族内部具有血缘关系并具有政治身份的大夫、士之“家”之间的关系,这个“家”在西周的政治文化脉络中是构成宗族的基本政治—社会单位。就宗法作为兄道而言,《尚书·君陈篇》所谓的“孝乎唯孝,友于兄弟”*《论语·为政篇》引用时作“乎”,但皇本与汉石经本作“于”。的意思,正是宗法社会精神的概括。孝为善祖先,友为善兄弟,宗法在本质上是将孝先祖与友兄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孝先祖”的宗教礼仪被提升为“友兄弟”的人文体制。铜器铭文中的“孝友惟型”(《暦彝》,载《攈》卷二之二)、“惟辟孝友”(《史墙盘》)等,都将兄弟关系特别提了出来。关于两周的传世文献中亦颇多记载:如《诗经·皇矣》“维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尚书·康诰》“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等等。周代人取名多用“友”字,如太史友、内史友、郑桓公友、多友等,“友”亦与“兄弟”之谊相连。“友”本身在西周语境中即有兄弟之义,而且是本家族亲兄弟之外的同族兄弟,有时甚至亲兄弟也可包含在朋友之称中。*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版),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第292—297页。《左传》文公十五年:“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贺善、吊灾、祭敬、丧哀,情虽不同,毋绝其爱,亲之道也。’”*史佚,原名尹佚,尹逸,西周初年太史,今唐兴镇东关村史家圪垯人。这些都道出了宗法所针对的关系主体主要是兄弟关系。事实上,王国维先生在论述宗法时,所引用的诗句中有不少提到了兄弟:
其在《诗·小雅》之《常棣序》曰“燕兄弟”也。其诗曰:“傧尔笾豆,饮酒之饫。兄弟既具,和乐且孺。”《大雅》之《行苇序》曰:“周家能内睦九族也。”其诗曰:“戚戚兄弟,莫远具迩。或肆之筵,或授之几。”是即《周礼·大宗伯》所谓“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者,是天子之收族也。……又在《小雅》之《楚茨》曰:“诸父兄弟,备言燕私。”
在这里,大量“兄弟”词汇的出现,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修辞。沈长云发现:“无论《诗经》、《尚书》或铜器铭文,强调兄弟同宗之谊的地方比比皆是:‘凡人之人,莫如兄弟’(《诗·常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诗·斯干》),‘庶邦享作,兄弟方来’(《书·梓材》),‘用召诸考诸兄’(《伯公父簠》),‘用怀柔我多弟子’(《沈子簋》)等等。由是可知,强调兄弟关系也是西周宗法制度的一项基本原则。”*沈长云:《上古史探研》,北京:中华书局,2002,第244页。“如果没有对同宗兄弟至高无上的情谊,则大宗、小宗之间的特殊关系将失去其存在的依据。”*沈长云:《上古史探研》,北京:中华书局,2002,第244页。的确,《诗经·杕杜序》云:“君不能亲其宗族,骨肉离散,独居而无兄弟,将为沃所并尔。”*《毛诗正义》卷六(六之二),《十三经注疏》(整理本),第4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458页。对于周人而言,若宗法不行,则其后果必是“骨肉离散,独居而无兄弟”,反之,宗法具有团结兄弟(兄弟之家、兄弟之国)的重要功能。《诗经·大雅·思齐》:“至于兄弟”、《诗经·大雅·皇矣》:“同尔兄弟”。郑玄笺解“兄弟”为“兄弟之国”,朱熹《诗集传》曰:“兄弟,与国也。”朱凤瀚指出:“可见此二诗中‘兄弟’未必是指兄弟个人,而是指同宗的小宗分支。”*朱凤瀚:《商周家族制度研究》(增订本),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第235页。“未必是指兄弟个人”,原文作“未必是指的兄弟个人”,略有不顺,故而引文略变而通之。另外,朱凤瀚先生由此而推断文王时代宗法业已形成,则不敢苟同。按照此种逻辑,以《公刘》“君之宗之”之毛传而言,则吾人甚至可以断言,周人在公刘时代即已经形成宗法。其实更应该从追溯的视角来理解《诗经》对公刘与文王的歌颂,而这种歌颂本身不是出于历史与考古的兴趣,而是介入现实生活本身的方式。
宗法的核心是兄之道,但这并不意味着所宗者与宗之者之间就完全被限定在兄弟关系的架构之内,而只是说在嫡庶之制的基础上以兄统弟、以弟尊兄构成宗法指向的人伦关系的主体。万斯大不无道理地指出:“小宗虽有四,而宗之者无定,故凡礼经唯称宗子,而不别言某宗,独《曾子问》载摄主之辞宾,有宗兄、宗弟、宗子之异,亦可见宗之者不唯兄弟,而孔疏为未尽也。”*万斯大:《学礼质疑》卷二《宗法二》,《经学五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第49页。的确,在宗法的成立过程中,对于别子之子的这一代,宗子与庶子的关系完全是兄弟关系,但从别子之孙这一代开始,宗子与庶子的关系虽以兄弟为主体,但也可能出现代际之不一致,例如继别者已经是别子的嫡孙,而别子之庶子依然在世,那么二者之间就不是兄弟关系,而是叔侄关系。但这并不影响,随着大小宗的不断分衍,宗法关系仍然以兄弟关系为主体。在这个意义上,宗法的实质可以概括为横向的“以兄统弟”。当然,在大小宗分衍的情况下,“以兄统弟”意味着作为大宗宗子的兄统率众多的小宗宗子的弟以及他的宗人,而作为小宗宗子的弟在其各自的小宗内部又是以嫡兄的身份统领着作为复数的庶弟及其宗人。
三、 宗法的内在结构之三:以嫡统庶
宗法结构中上述两个基本原则,即“以子继父”与“以兄统弟”,都根基于另一更具奠基性的基本原则,即“以嫡统庶”。王国维清楚地认识到,嫡庶之制构成了宗法的基础:“其所宗者皆嫡也,宗之者皆庶也。”正如程瑶田所指出的那样,“自后世而溯之,则同父之嫡兄曰继祢之宗,同祖之嫡兄曰继祖之宗,同曾祖之嫡兄曰继曾祖之宗,同高祖之嫡兄曰继高祖之宗。……而彼继别者为收族之大宗,则一族之人所同于别子之嫡兄也。”*程瑶田:《宗法小记》之《宗法表》,《程瑶田全集》卷一,合肥:黄山书社,2008,第137页。在这里,嫡庶是区分宗法最基本关系——所宗者与宗之者——的根据,是故纪大奎云:“礼之所谓宗,以嫡为宗而已矣。”“再世之嫡,则一世之嫡宗之。三世、四世之嫡,则再世之嫡宗之。凡嫡之所宗皆曰宗。继祢者,一世之嫡而已矣。必祢嫡而后谓之宗,是故祢嫡则谓之继祖,祖嫡则谓之继曾祖,曾祖嫡则谓之继高祖。”*纪大奎:《宗法论三》,《皇朝经世文编》卷五十八,《魏源全集》第16册,长沙:岳麓书社,2004,第236页。如果离开嫡庶之制,则宗法完全无法理解,亦无从实践。是故魏晋时期的范宣云:“凡母弟及庶昆弟所谓庶宗、大宗,正论其一代之嫡庶耳。”*黄以周:《礼书通故》,北京:中华书局,2007,第293页。即便是为祖的别子其与世子之别,亦为庶嫡之分,故而黄以周谓:“国君之庶昆弟必爵为大夫而始立大宗,别子之为大夫士者,皆可为大宗,此嫡庶之分也。”*黄以周:《礼书通故》,北京:中华书局,2007,第296页。在小宗中宗子为嫡,而宗人为庶;在大宗中,小宗宗子相对于继别而言是庶而宗子为嫡。宗子与宗人实由嫡庶而分。金景芳先生指出:“假如不是实行这样继承制——即嫡长子一人继承其先人产业,更全面地说,即如《公羊传》隐公元年所说‘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而是认为兄终弟及和父死子继同样合法或用其他种继承形式的话,就不会有这种宗法制度。为什么呢?应该指出嫡长子继承制的特点,在于体现了严格的等级制度的精神。这种严格的等级制度的精神,简单说,就是‘以一治之’。……嫡长子继承制跟其他继承制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的合法继承人只有一个,而且不须临时考虑,早已十分确定。这种继承制是以区别嫡庶、分辨长幼的等级制度为其前提条件的。显然,只有依赖于区别嫡庶、分辨长幼,世世由嫡长子一人继承这个制度的存在,而后才可能产生宗法的弟统于兄、小宗统于大宗的严整体系。”*金景芳:《论宗法制度》,《金景芳儒学论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第649页。《礼记·丧服四制》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一治之也。”的确,嫡长子继承制是“以一治之”原则的极佳贯彻方式。嫡长子的唯一性,是息争的基础;而嫡长子“定之以天”而非系之于人,更使其具有来源于天的客观性与确定性。在统治权力的金字塔结构中,最上的天子与稍下的诸侯以及最下的大夫士的世系之法定继承,都贯彻了以嫡统庶的原则。这就使得在政治与社会两个层面,上下世代的继承制度得以完满解决。对于以“本支百世”为指向的宗法而言,嫡者为“本”而庶者为“支”,“本”与“支”的分判便建基于嫡庶之制上,由此,王国维对嫡庶之制构成宗法基础与继统法乃至整个周礼基础的洞见,的确是不刊之论。
四、 尊祖—敬宗—收族:宗法的意义与功能
如前所述,宗法的结构中纵向的上下结构——“以子继父”与横向的左右结构——“以兄统弟”,都建立在“以嫡统庶”的基础之上。由“以子继父”而有宗法的尊祖,由“以兄统弟”而有宗法的收族,由“以嫡统庶”而有宗法的敬宗。敬兄意味着尊敬宗子,而宗子通过“以子继父”产生,通过“以兄统弟”而发生其作用。明白了宗法结构中的上述三种关系,就更容易理解宗法的性质。而事实上,宗法将纵向的结构“以子继父”、横向的结构“以兄统弟”这两者与嫡庶之制上的“以嫡统庶”,三者结合起来,其中“以嫡统庶”贯穿在以子继父、以兄统弟之中,故而王国维谓无嫡庶之制则无宗法,宗法的基础在嫡庶之制;而在纵向的“以子继父”(以孙继祖、以曾孙继曾祖等等都是以子继父的扩展形式)与横向的“以兄统弟”之间,前者指向生者(现在之族)与死者(死去之祖)的关系,后者指向生者与生者的关系,纵向的关系最终归宿在横向的关系,由此以兄统弟才是宗法中三者(以子继父、以嫡统庶、以兄统弟)关系的指向与归宿,这是由于宗法的现实功能在于收族,而收族所采用的方式便是以兄(宗子)统弟(族人)。
《周礼·大宰》谓:“宗,以族得民。”*郑玄注:“宗,继别为大宗,收族者。郑司农云‘主谓公卿大夫,世世食采不绝,民税薄利之。’玄谓:利,读如‘上思利民’之利,谓以政教利之。”贾公彦疏:“谓大宗子与族食族燕,序以昭穆,故云‘以族得民’,民即族人也。”《周礼注疏》卷二《大宰》,《十三经注疏》(整理本),第7册,第47—48页。但小宗与大宗的收族方式不同。《礼记·大传》云:“同姓从宗,合族属。”又云:“四世而缌,服之穷也。五世袒免,杀同姓也。六世,亲属竭矣。”纪大奎发现,《大传》在此实际上是区分了“亲属”与“族属”,“亲属”指四世以内的同宗者,亲与亲相属,尚在“五服”之内,可及于三从兄弟;而“族属”则可在五世以外,族与族相属。小宗的团结族人发生在“亲属”的架构之内,而大宗则由“亲属”而扩展到“族属”,因为“同宗”,即同始祖,故而同姓者可以合其“族属”。*纪大奎:《宗法论四》,《皇朝经世文编》卷五十八,《魏源全集》第16册,长沙:岳麓书社,2004,第238—239页。换言之,在亲属关系竭尽之处,五世、六世、七世甚至百世的兄弟,仍然可以共同始祖的名义而为大宗所收族。由此不难看出宗法的意义,从纵的方面来说,是继祖尊祖,但从横的角度来看,是不同分支世系但却可以归属于同一个始祖的兄弟们乃至整个宗族共同体之团结,即收族。而现实的收族功能往往通过尊祖的方式达成,并与尊祖彼此互相强化。尊祖、敬宗、收族三者之间构成宗法意义的三个交互构成的共属性环节。敬宗是对当时历史状况下存在着的祖先崇拜的转化与提升,宗子构成先祖在生者那里得以继续存在并发生影响的“正体”,故而尊祖与敬宗一体而不可分割。大宗之所以能收族,因为它是尊之统;而其所以为尊,乃是因为继承了先祖的正体。杜正胜认为:“凡周之同族皆能因尊过去之祖而敬目前的宗,以达到收族的功效,这是大小宗的精义。”*杜正胜:《古代社会与国家》,台北:允晨文化实业有限公司,1992,第409页。这一说法看到了尊祖以敬宗为目的,但敬宗并非宗法的精义,因为敬宗实以收族为指向。是故方苞(1668—1749)有一更直接的说法:“古之宗法,所以收族,乃为生者而设,非使各领其族以祀先祖也。”*郝懿行:《郑氏礼记笺》“丧服小记”,《郝懿行集》第2册,济南:齐鲁书社,2010,第1338页。万斯大对宗法的意义做出了更为精到的总结:“愚谓宗者,统族人以奉祀也。祭已往之祖而收见在之族,祖分而祭亦分。故一族不止一宗。”*万斯大:《经学五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第66页。这里的关键是“祭已往之祖而收见在之族”,道出了尊祖与敬宗的实质指向,以尊死去之祖的名义所导致的是宗族成员的团结。
由此,由宗子主持的祭祀,指向的并不是作为鬼神的先祖,而是生者对先祖的仪式化与象征化追念,这种追念方式是生者(祭祀者)而不是死者(被祭祀者)的秩序构建之方式,也即族人共同祭祀的方式被提升为族群组织的方式,这就是周人在殷商以来遍祀群先的宗教意识下开采出来的人文意识。宗法的政教意义通过宗子实现,而宗子在先祖与族人之间加以连接。因为先祖的庙立于宗子之家,对先祖的祭祀要在宗子之家进行,并由宗子来主持;这就使得宗子成为族人与先祖之间的中介。因而,敬宗并不仅仅是族人态度的体现,还表现在具体的礼仪规范中。
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丧服小记》)
庶子不祭祢者,明其宗也。(《丧服小记》)
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大传》)
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礼记·曲礼下》)
祭与不祭是宗子与庶子各自权能之界限。程瑶田指出:“宗子者,庶子之所宗者也。庶子者,别于宗子者也。苟无庶子以宗之,则何有于宗子之名哉!故欲明其宗之为祭主,以庶子之不祭明之;欲明宗之继祖祢,以庶子之不继祖祢明之。”*程瑶田:《宗法小记》之《庶子不祭明宗说》,《程瑶田全集》卷一,第159页。宗所以继统传重,不祭则无重可传。“传重者,传所受宗庙、土地、爵位、人民之重也。”*陈立:《白虎通疏证》卷四《封公侯》,第152页。是以宗子最重要的职权是主祭权。而此主祭权则关联着立庙、宗族的公共财产,以及宗族的治理权。此等职权继承自先祖,宗子亦是代先祖而执行这些职权。故而尊祖必敬宗,而敬宗落实在宗子享有的权能中。《白虎通》:“宗者,何谓也?宗者,尊也。为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礼》曰:‘宗人将有事,族人皆侍。’古者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长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群弟,通于有无,所以纪理族人者也。”*陈立:《白虎通疏证》卷八《宗族》,第393—394页。由此,宗子因为为先祖主,故而有权纪理族人。基于共同先人的血缘关系,宗法对于群体达成了如下的分类形式:或是同姓者、同氏者、同族者、同宗者;或是同父者、同祖者、同曾祖者、同高祖者、同始祖者;或是亲兄弟、同堂兄弟、再从兄弟、三从兄弟等等。这些分类形式,本身就具有一种连结的功能,它加固了群体归属性与认同感,从而达到“长和睦”的作用。宗子虽然因其特权而有族人处于尊卑有别的不平等的关系之中,但正是这种特权,授予他维持宗族祭祀不绝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丧服小记》云:“士不摄大夫。士摄大夫,唯宗子。”这就是说,大夫无后嗣而死,其亲属中爵位为士的,不能代为丧主而主持丧事,因为爵位不同,但爵位士的宗子却可以摄代丧主,因为宗子上承宗庙,下统族人,地位在一族之中最尊。而《礼记·内则》强调:一旦庶子富贵,也不能用富贵的排场进入宗子之家,众多的车马随从都要停在门外,而只能带一二随从去拜见宗子,即便受到了赏赐,也要将其中上等的器物献给宗子,然后自己才敢享用次等的。设若某些器物不适合宗子之身份,非所当献,就不能将之带入宗子的大门,更不能仰仗富贵而凌驾于父兄宗族之上。小宗宗子如果家境富贵,则当将上好的祭品献给大宗宗子,到大宗庙中助祭完毕,才敢回到小宗宗庙中祭祀先祖。*《礼记·内则》:“嫡子庶子,只事宗子宗妇。虽富贵,不敢以富贵入宗子之家。虽众车徒舍于外,以寡约入。子弟犹归器。衣服、裘衾、车马,则必献其上,而后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献,则不敢以入于宗子之门。不敢以贵富加于父兄宗族。若富,则具二牲,献其贤者于宗子,夫妇皆齐而宗敬焉,终事而后敢私祭。”如果宗子为士,庶子为大夫,那么,则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礼记·曾子问》记载:曾子问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为介子某荐其常事。’若宗子有罪,居于他国,庶子为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执其常事。’摄主不厌祭,不旅,不假,不绥祭,不配。布奠于宾,宾奠而不举,不归肉。其辞于宾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国,使某辞。’”曾子问曰:“宗子去在他国,庶子无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请问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为坛,以时祭。若宗子死,告于墓而后祭于家。宗子死,称名不言‘孝’,身没而已。”庶子供牲而宗子主祭,宗子有罪居他国而庶子遂贵为大夫其祭也犹称宗子,庶子无爵而宗子在他国、必宗子死而告于墓、祭于家犹称名而不称孝……所有这些,都体现了敬宗之意,在祭祀的问题上,敬宗不仅仅是族人对待宗子与先祖的态度,更是被体制化、制度化了的习惯、风俗、传统与行为,它最大的原则是一庙只有唯一的一个祭主,即宗子,这就是庶子不祭以明其宗的含义。
如果说祭祀中庶子不祭以明宗子的尊贵,此中体现的是尊尊之义,那么,宗族的另一集体活动,祭祀之后的燕饮,则以亲亲为原则。《礼记·中庸》谓:“宗庙之礼,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贵贱也;序事,所以辨贤也。旅酬下为上,所以逮贱也。燕毛,所以序齿也。”郑玄注云:“祭时尊尊也,至燕亲亲也。”*《礼记正义》卷五十二《中庸》,《十三经注疏》(整理本)第15册,第1681页。同宗之人,一如《礼记·祭统》所云,“凡有事于大庙则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伦”,祭祀时依据亲属远近嫡庶尊卑而有差等,旅酬燕饮则仅仅依照昭穆秩序,也就是世系行辈或辈分,不以尊卑。“昭为一,穆为一,昭与昭齿,穆与穆齿。凡群有司皆以齿,此之谓长幼有序。”*《礼记·祭统》。昭穆秩序重在分别父子长幼,而不是远近亲疏,即便毫无政治地位,也不居宗子之位,只要辈分高者在燕饮时仍然受到尊敬,居于上座,而宗子向之敬酒。《礼记·文王世子》有谓“虽有三命,不逾父兄”,在燕饮时,政治身份退后,朝命爵位亦不在其内,而是以年齿为饮酒之序的标准。此即《礼记·大传》所谓的“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缪(穆),别之以礼义,人道竭矣。”燕饮之礼则成为宗族在祭祀之后“藉饮酒的和谐融洽气氛弥补氏族分裂后治人与治于人的感情缺憾,提醒大家原同出于一宗氏,宜上下合作,戮力同心。《周礼·大宗伯》所谓‘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者也。”*杜正胜:《古代社会与国家》,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第403页。
尊尊之祭、亲亲之燕,则构成了宗族组织建构秩序的主要方式。何休云:“族所以有宗者,为调族理亲疏,令昭穆亲疏各得其序也,故始统世世继重者为大宗,旁统者为小宗。”*《春秋公羊传注疏》卷八庄公二十四年,《十三经注疏》(整理本),第20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196页。宗族秩序建构主要是按照亲疏远近的原则,与昭穆(区分行辈、辈分)的原则,对于共同活动中的族人予以相应之礼加以对待。正如杜正胜所云:“兄弟共权的昭穆制与族长专权的大小宗是截然有别的。但在疏远的没落王孙、公孙身上,二者却吻合无间,不能不说是周族宗法的绝大特色。这是新制,为前世所未有。周人重姓,以昭穆制广收宗族,以大小宗统系亲疏,大概和他们以少数人口统治多数东方氏族有关。在政权结构上,征服初期虽能恢复某种程度的氏族共权遗习的昭穆制,殖民运动终止或减缓之后,缺乏源源不断的土地占有,周族内部也不能不以亲疏贤愚之差别建立大小宗。当宗其继别子者与宗其继高祖者有所区别后,有的人百世之后仍然属于亲贵,有的人五世之后就沦为庶民,这就明白宣判氏族共权遗习死亡了。”*杜正胜:《古代社会与国家》,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第411页。
祭祀与燕饮固然是宗族集体的大事,但宗族成员的人生大事,成年、结婚与去世,也都被纳入到宗族共同体的生活世界:“五庙之孙,祖庙未毁,虽为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练祥则告。”*《礼记·文王世子》。晋贺循的《宗义》告诉我们:凡是宗族之内的祭祀、嫁女、娶妻、死亡、生子、行来、改易名字,都必须上告宗子之家;倘若族内有吉凶之事,宗子还率领宗党前往帮忙。*《通典》卷七十三《事宗礼》,北京:中华书局,1988,第1999页。所有这些,都使得宗族具有伦理共同体的特点,它抗拒因氏族分化、亲属既竭而带来的宗族人心的离散,而附远厚别,互通声息,维系宗族作为同一家族成员的归属感。宋儒陈祥道云:“人生而莫不有孝弟之心,亲睦之道,先王因其有是道而为之节文,故立为五宗,以纠序族人,而使之亲疏有以相附,赴告有以相通,然后恩义不失,而人伦归厚。此《周官》所谓宗以族得民也。……又《礼书》曰:百夫无长,不散则乱,一族无宗,不离则疏。先王因族以立宗,敬宗以尊祖,故吉凶有以相及,有无得以相通,尊卑有分而不乱,亲疏有别而不贰,贵贱有系而不间,然后一宗如出乎一族,一族如出乎一家,一家如出乎一人。此礼俗所以刑,而人伦所以厚也。”*卫湜:《礼记集说》卷八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781—782页。这就指明了宗法的意义,通过共奉同一血缘上的祖、宗,宗族成员在生存中彼此联结,由此在氏族社会解体之后宗法铸造了“家族”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结构性意义,个人无法自外于宗族之家,也因宗族成员彼此之间的睦族振穷、相附相通而具有使人伦归厚的政治—伦理的意义;即便是在中唐以下“一王孤立于上”而“众民散处于下”*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第653页。的格局下,特别是“在一种以个体小农为主体的农耕经济里,‘散处’的本来状态等类于散落与离析,而以‘慎终追远’和‘敬宗收族’串联宗族与家族虽然着眼的是血缘,但这种由血缘关系所生成的聚合却使‘散处’的众民得以脱出离析,并以其自相抟结而‘吉相庆,凶相吊,患难相恤,出入相及’为两千年中国社会构成了广袤而且恒久的底层组织和基本单位。有此构筑,而后始有一朝一朝的经济过程、政治过程和文化过程。就这个意义而言,汉代之后的中国历史已与宗族和家族剥离不开。”*杨国强:《历史中的儒学》,《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3年4月7日。在周代肇始的“身—家—国—天下”的政治社会的构造中,宗法毫无疑问构成“齐家”的方式。故而程瑶田云:“宗法者,为大夫、士立之,以上承夫天子、诸侯而治其家者也。”*程瑶田:《宗法小记》之《宗法述》,《程瑶田全集》第1册,第171页。齐家的意义落实在收族上,“‘大宗收族’以统于上,群小宗别其庶姓以分统于下,旁治昆弟,家家而修之,族族而理之,周公之所以造周者,用是道也。”*程瑶田:《宗法小记》之《庶子不祭明宗说》,《程瑶田全集》第1册,第160页。对于有天下的周人而言,齐家是内治与自治,其意义则远远超出齐家本身,而是与“家齐然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关联在一起。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曾经发掘了宗法的政治意义。
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而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矣。古之王者不忍以刑穷天下之民也,是故一家之中,父兄治之;一族之间,宗子治之。其有不善之萌,莫不自化于闺门之内;而犹有不帅教者,然后归之士师。然则人君之所治者约矣。然后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意论轻重之序、慎测浅深之量以别之,悉其聪明、致其忠爱以尽之。夫然,刑罚焉得而不中乎?是故宗法立而刑清。天下之宗子各治其族,以辅人君之治,罔攸兼于庶狱,而民自不犯于有司。风欲之醇,科条之简,有自来矣。《诗》曰:“君之宗之。”吾是以知宗子之次于君道也。*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六“爱百姓故刑罚中”,长沙:岳麓书社,1994,第222—223页。
宗族内部的事务悉归之宗族,于是不善之萌可以自化于闺门之内。宗法不仅仅是君道的有益补充,而且在这里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是将天下之事交付给天下来处理,因而可以成就“风欲之醇,科条之简”的无为之治。这与《礼记·大传》所说的“收族故宗庙严,宗庙严故重社稷,重社稷故爱百姓,爱百姓故刑罚中,刑罚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财用足,财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礼俗刑,礼俗刑然后乐”,形成义理上的呼应。顾炎武更云:
民之所以不安,以其有贫有富。贫者至于不能自存,而富者常恐人之有求,而多为吝啬之计,于是乎有争心矣。夫子有言:“不患贫,而患不均。”夫惟收族之法行,而岁时有合食之恩,吉凶有通财之义。本俗六,安万民,三曰联兄弟,而乡三物之所兴者。六行之条曰睦、曰恤,不待王政之施,而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矣。此所谓均无贫者,而财用有不足乎?至于《葛藟》之刺兴,《角弓》之赋作,九族乃离,一方相怨,而缾罍交耻,泉池并竭,然后知先王宗法之立,其所以养人之欲而给人之求,为周且豫矣。*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六“庶民安故财用足”,长沙:岳麓书社,1994,第223页。
顾炎武提醒我们,宗法的收族“养人之欲,给人之求”,做到宗族内部的自给自足,不待王政之施而族人皆能有养,由此人们不必在漫长的无道过程中期待一个圣贤降临或救世主的福音与救赎,而是集宗族之力,自济自救,自给自养,分享吉福,共御凶祸。就此而言,宗法虽然不同于政治,然而它实际上构成周人政治构造的重要环节,由此而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思想对政治的理解。程瑶田深刻地指出:“今夫宗道,先王者之所以一天下者也。”*程瑶田:《宗法小记》之《宗法表》,《程瑶田全集》第1册,第1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