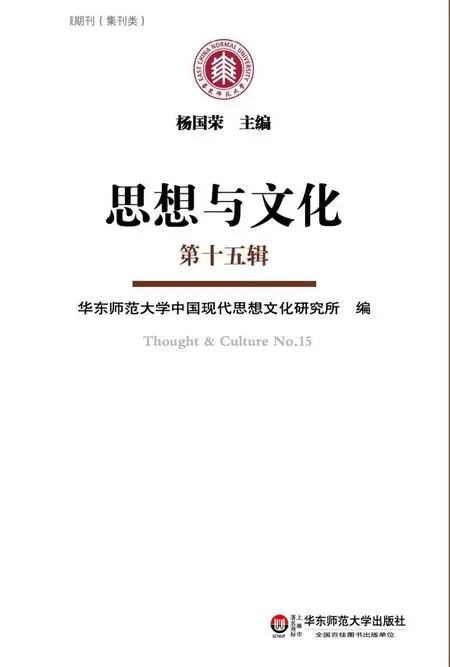李泽厚与莫里斯·石里克论美的本质
●[]· ;
我初闻李泽厚的美学理论[Ding, 2002, pp.246-259.],即震惊于他与莫里斯·石里克观点何其相似。后者是20世纪初的德国哲学家。由于多年研究石里克哲学*参见拙文《美,游戏与生活意义》(Beauty, Play and the Meaning of Life),Philo Vol 12, No. One (Spring—Summer, 2009), pp.24-30.,我自然有意于探索两位哲学背景迥异的哲学家的这一相似。
石里克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即与美学相关[Schlick, 1909.],另一篇讨论人生意义问题的文章发表于1927年[Schlick, 1927.],我手头关于李泽厚的主要文献是《华夏美学》和他与Jane Cauvel合写的英文著作《美学四讲》。我将探讨两位哲人观点的异同,希望能澄清他们的观点,以俟更多样的理解。*从两人都研究康德哲学却采取了不同的进路这一点中可以看到区别。李泽厚似乎接受了康德的物自体不可知的观点,而石里克则否认这一点,并认同科学现实主义,后者认为科学知识即是关于物自体的知识。
石里克仅有两篇短论谈及美学,在深度和广度上不及李泽厚,后者在美学问题上著述颇丰。*石里克对美的分析远较李泽厚为少。[参见Li, 2006, pp.54-55,以他对艺术的讨论为例。]此外,李泽厚以其通透的中国美学知识和马克思早期作品作为资源,而它们对石里克毫无影响。不过,19世纪哲学家特别是康德和席勒却共同影响了他们。李泽厚有研究康德的大作,而受教于德国的石里克熟稔于康德、席勒和19世纪的新康德主义者。
本文关注了两位哲人为自己设定的三项工作。其一是讨论以科学或因果关系来解释人类的审美能力是否可能。这个难题很特别,因为引起审美愉悦的对象通常是无关于目的或实用价值*对此不无疑问。通常,艺术作为人类活动的产品是“无用的”,而有时似乎审美愉悦才是“无用的”。李泽厚说“审美经验是生产劳动的自然结果,它没有实用的目的”。[Li, 2006, p.144.]其他时候“无用”的是美。本文不求解决这些问题,因为重新措辞将会需要太多的辩护。的,因此这个问题是“自然选择理论”所不能包容的。论文的这一部分我命名为“美的历史—因果本质”。工作二是探究美的观念性本质。可以从提问以下问题开始:审美评价是命题性表达吗?评价词如“漂亮的”是描述性的吗?(如果是,描述内容是什么?)这部分题为“美的哲学本质”。第三部分是“美的目的”,在这里我回到“审美愉悦是非实用的”这一看法,同时指出,虽然方式不尽相同,但石里克和李泽厚两人实质上承认了审美愉悦有一定的目的。
一、 美的历史—因果本质
石里克从美的启蒙视角观——艺术因无功用而立——入手。他明确定义功用为促进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生存。假定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是正确的,石里克力图回答的核心问题便是:“怎么可能是与功用、自我保存、种族繁殖完全无关的事物引起了愉悦?”[Schlick, 1909, p.8.]李泽厚也赞同艺术就其本身而言无关功用,不过他并没有强调这一观点是达尔文意义上的。《美学四讲》中仅有一处与美学无涉的地方提到了达尔文,《华夏美学》中则全无达尔文。他提及进化时,并非意指生物学意义上的智人进化,而是着意于人类意识。后者经历了从动物意义上的纯实践意识到审美意识和道德意识的进化。
虽然对达尔文及自然选择有不同的态度,但两人都首先着手于说明审美感受的发生,或依李泽厚言,在审美经验的起始处即史前状态中发掘美的本质。他们都认为将在大量、细致的人类学和考古学工作,以及人类对特定对象或特质的审美经验所做的实验报告中发现美的本质。李泽厚聚焦于对史前人类尤其是中国人的考古发现。石里克受达尔文影响,关注更早期的人类,他认为研究类人猿的行为对探源审美经验或将是有价值的。[Schlick, 1909, p.5.]
虽然都承认审美是无功用的,两人还是都认为审美经验和艺术起源于实践和实用活动,特别是创造工具、武器、身体改造等人造物以及穿着衣饰,尤其是李泽厚所说的图腾舞和巫术仪式。他认为是在仪式中“人的自我意识超越了动物”。实践中的外在限制塑造了人的心灵。[Li, 2010, p.12.]两人都提到了食物在人的生理性受激性味觉愉悦转变为对食物特别是水果的审美愉悦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他主张“审美意识最初对与实用功利和道德上的善不同的美的感受,是和味、声、色所引起的感官上的快适分不开的。其中,味觉的快感在后世纵然不再被归入严格意义的美感之内,但在开始却同人类审美意识的发展密切相关。”[Li, 2010, p.7.]食物的色香带来的愉悦可以在食欲消退后持续。李泽厚同样认为“……逐渐解决物质匮乏、吃饱穿暖的问题,于是人类往何处去,即人类命运问题,个体寻觅其存在意义问题,等等,不也就变得更为突出了么?”[Li, 2006, p.37.See also, 2010, p.7-8.]他进而把人生意义归结于艺术愉悦,石里克也如是认为。
虽然李泽厚强调了中国文化对自然风光的偏爱,但他同时认为这在审美经验中是相对晚近的,并把审美感受归原于对手工制品的生产和观赏。这与马克思对他的影响高度一致,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形态乃是其上的文化、精神发展的基础。李泽厚说:
美、艺术、美感的本质植根于人类最早的社会和物质实践中。人对工具、环境的塑造及后者对人的反塑造,就是最初的审美活动,而由之带来的愉悦是最早的审美愉悦。[Li, 2006, p.5.]*本段系英译本《美学四讲》前言(preface),在中文本原著中并没有相应内容,故根据英文意译。——译者注
这与石里克的观点相似,他直言:“我们的任务就是把审美本能归结为自保本能或性本能。”[Schlick, 2009, p.11.]这些本能都植根于求种族生存的奋斗,所以两人都将美的产生置于了人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中。因为美学植根于改造自然的活动,最初是为了求生存。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实践使得人领悟了自然美并产生了人化自然的观念。*支持李泽厚论断的关键一点是,人类或其祖先只有在开始制作工具之后才发展出了获得审美愉悦的能力。相对的假设则是,人类祖先在其动物经验比如审视水果或其他食物中,就在先地发展出了审美愉悦,这一点是两人都提到的。从性爱、狩猎甚至是搏斗中获得的其他身体愉悦,也先于制造工具的深思。详见本文第二部分。石里克曾表示,自然是最后的审美对象。动物的摹本,或许起初便因奇妙的目的,而远远早于脱离了实物和皮来源意义之后的动物本身而有审美功用。李泽厚强调史前绘画和雕塑并无意于欣赏自然。[Li, 2010, p.21.]身体的性吸引力是为求种族延续,它早于任何审美活动,对身体的审美最初以肢体的残断或美饰的形式出现,很久之后才采取了身体本身的形式。
石里克和李泽厚都将审美悟性定义为专注于感受所谓形式及形式结合为艺术。李泽厚强调,自然的形式与人类意识的形式是同构的。石里克则谈论道,先是对多样的人造形式带来的实用愉悦的感受,再是对人造形式的审美领会,最终才是对自然形式的把握。
李泽厚明说,是“特定的形式”给予了审美活动。特定形式的含义是“获得了社会性内涵的自然形式”。[Li, 1994, p.20.]这类形式的获得需要概念化、想象力和一定程度的理解力。[Li, 1994, p.21.]“社会性内涵”的想法与李泽厚关于积淀的看法有关,参与后者的是我们在故事及口述历史中使用的语言形式,以及激发和引导了我们的想象力的那些仪式舞蹈和巫术仪式。
这个积淀的观念对李泽厚至关重要。审美活动和艺术进入到社会文化世界,不停留于代际相传,而是在代代相传中内化、继承和增益,进而构成了客观的积淀。这一点在文化学习中可以显见。人类的审美能力以相同的方式随时间增益。李泽厚强调了审美悟性在人类感性力量增强之中的作用。他说,
我们能够欣赏抽象艺术和所谓丑作品,反映出我们的感受性和审美能力的提高。这一提高显示了视听力和精神生活的进步,以及我们审美能力的发展。[Li, 2006, p.115.]*此段按照《美学四讲》英译本译者的标示,并未查找到相应的中文原文,故根据英文意译。——译者注
李泽厚强调,艺术活动作用于“塑造人类心灵”以“使内在本性人化”和培育“性情”。[Li, 2006, p36-37.]依他而言,如果没有某些理性因素的参与,审美愉悦是不可能的。在他看来,一个参与的方式便是对味道、颜色、口音和其他官能进行语言上的区分。[Li, 2010, p.9.]两人都强调理智在美的创造和欣赏中的作用。李泽厚评论道:“审美经验不同于动物的感官愉悦,因为其中含有理想和想象的元素。”[Li, 1994, p.20.]这似乎在定义上区分了物理性愉悦和审美经验的不同。然而,石里克却将美学溯源至食色这两种种族生存的本能。[Schlick, 1909, p.11.]这意味着在心理愉悦和审美愉悦间没有鸿沟。
李泽厚的论说总是像是二元论。他说:“我认为人的存在不同于动物不是因为意识或语言而是广泛而必要的制作和使用工具。”他强化说:“制造和使用工具是人类知识和道德的真正基础。人类语言和仪式的本质也得自这一主要的实践。”[Li, 1999, p.174.][Li, 1999, p.175.]
与之相关我们问:文化的内在基础是物质生产还是生物性的心灵?有没有证明心灵是美的本质的例子呢?石里克在关于类人猿研究的论述中提到了。假设如下:早期前人类的人科种族大脑发生了基因改变,产生了更高级的抽象能力,因此发展出了人类语言、逻辑推理能力和道德感情,进而使他们在社会分工中更独立了。*对此,李泽厚明确加以否认,他说:“我们对从猿到人的研究,也说明从人手、人脑到人性心理—结构(包括如逻辑、数学观念、因果律观念等智力结构、意志力量等伦理结构和形式感受等审美结构)都源起于上述使用—制造工具的漫长的人类现实物质性的生产活动中。”[Li, 2006, p.56.]他断言:“比例、均衡、对称是人用以处理(实践)从而理解(认识)客观世界的基本规范。总之,各种形式结构、各种比例、均衡、节奏、秩序,亦即形成规律和所谓形式美,首先是通过人的劳动操作和技术活动(使用—制造工具的活动)去把握、发现、展开、和理解的。”[Li, 2006, p.68.]心灵能力的拓展对有意识地制造工具是必要的,尤其对感知“形式”的能力是必要的,后者在李泽厚所谓创造性地制造工具这一跳跃中必不可少。结果,人类的社会意识不能源于工具制作。相反,工具制作和李泽厚提到的诸如图腾舞蹈和巫术仪式等活动,产生于抽象的思维和语言以及道德感情,是后者奠基了社会关系,从而使得仪式有了意义。*李泽厚说仪式使得人获得了“超越动物的自我意识”。[2010, p.12.]然而相对的观点坚持认为人只有首先超越动物,才能使参与仪式有意义。
所以,既然工具制作、舞蹈和仪式是人类文化的历史演进中的重要元素,智人的人化或许大大先于工具制作。*由前人类的社会生活中的依赖于语言交流而进化出来的道德感情,对于种族的人化,或许比获得审美愉悦有意义得多。李泽厚强调仪式是审美感受的来源之一,然而他也提到如果没有理性甚至是道德感情的参与,仪式是不可能的。或许人类的人化还早于智人的出现。我提供不了证明,仅仅是作为一个对待的可能性提出来。
二、 美的哲学本质
“美”到底指什么,众所周知是个难题。“道德的善”好似指某种客观的东西,就如“重量”指某种客观特性一样。人们或许会认为“美”是形容,像“美的”一词指向事物中给予了美的那些特质。
另一方面,与前述“客观式”理解不同的另一进路相似于阿尔弗雷德·艾耶尔的非认知主义思路。*艾耶尔,《语言、真理和逻辑》(Language, Truth and Logic)。石里克或许接受了同一观点。详见他的《伦理学问题》(Problems of Ethics)(Dover edition, 1962) p. 118-119,原版1930年。实际上,康德关于审美判断的观点与此相近。在《判断力批判》中,他认为审美判断不表示知识,而关注主体感受。他认为评价是非命题性的,不论是对道德、美还是口味的评价,他们非真非假。或许“美”或“美的”根本不指任何特征、特质。说“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真美”,在非认知的意义上,没有说出任何真或假、可被证实或证伪、可被确认或否认、可被接受或质疑的东西,因为评价词并不指向任何东西。句子表示了对一次第九交响曲演奏的感受,却没有描述包括人的主观感受在内的任何东西。如果不接受传统语言学对句子的看法,这些评价在本质上仅是非命题的面部及肢体表达。
李泽厚同时拒斥严格的客观进路和艾耶尔的非认知进路,[Li, 2006, p.18-19.]他说“艺术既然作为情绪感叹难以言说,有文字凭据可供分析的便只有批评了。于是美学便只能是元批评学或分析美学”。[Li, 2006, p.19.]不过艾耶尔没有谈论艺术,他谈论的是表达艺术评价的句子,而不是对审美经验的描述或对美的感受产生的客观条件的描述。他只是认为,如果对“美”一词没有描述性的定义,那么这个评价不能成为命题。
李泽厚认为,美学是个宽泛的题目,包括了对各种审美经验的社会学的、人类学的、心理学的、历史的和文化的分析。当然,在以上研究中可以找到许多命题式表达,因为他们本来就是科学研究。艾耶尔也会同意,不过他会将这样的研究直接归入科学。他将美学严格地区分开来,仅限于对艺术美和自然美的规范化评价,进而特别限于审美评价的说明和论证问题。他当时正在处理这一问题。李泽厚说艾耶尔本人的回答隐含了特定的规范化审美原则不可能的意思,这可能是非常正确的。
李泽厚要求中道。他似乎认同美是社会主体*李泽厚创造了一个新英语词“主体的”(subjectality)来代替“主体的”(subjective)。当他使用“主体的”一词,并不总是指个体的心理主体状态。新词表示在具体实践中塑造出来的社会人的主体性。主体的反应取决于在“积淀”进程中随时间而变的文化环境。这个词也反映出李泽厚或多或少的实用或传统中国形上倾向,即拒斥主客分野。交于客体、时间或景色的客观特征的一个性质。他说“一个事物能不能成为审美对象,光有主观条件或以主观条件为决定因素还不行,总需要对象上的某些东西,即审美性质”。[Li, 2006 p.50,他强调。]这非常接近于认为美是主客交互的继现性质,或许正是继现于由积淀而发展出的社群。于是我们说,以积淀为条件,美作为在主体感知了客体的特定特质后产生的特定主观态度,有了作为认识对象的维度,所以用美来形容经验到的客体可能有对错之分。然而,当这样定义时,美是什么,美在何处仍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这对于任何认知进路的美学理解都是一样的。*并不清楚李泽厚是否倡导这个关于美的观念。虽然他谈到了“社会客体性”和艺术美的“客体品格”。然而一个反对是,我们可以在大脑里为主体的心理反应给出时空定位,而要定位以客体方式来定义的美却很难。可感形式在客体中,而主体反应在主体中。如果以客观方式来认知美,就很难假设可以定位客观美,或是确认它是否存在。
如前所述,石里克和李泽厚都认为能够理解和摹写形式对于审美来说是必要的。例如,在绘画中是形式和结构创造了美,而不是颜色。石里克讨论了一个通过叠加面部修饰来产生普遍综合形式的所谓美容诱导效应。这样产生的脸型看起来更美。李泽厚提到了一个实验发现:看椭圆的脸比看圆形的脸更愉悦,虽然圆的观看本身就能带来愉悦。如果做更多实验和研究,我们或许可以得到一个造美的统计学典范。这些诱导美的因素或虽不普遍,但他们能从多角度和深度说明美的元素的客观性。李泽厚强调音乐的节奏与和谐,[Cauvel, 1999, p.152-153.]并把这些推用到其他艺术形式。他提出了“比例律、对称律、和谐律、秩序律、多样统一律和黄金分割律”等作为美的客观属性。[Li, 2006, p.51.]他明显偏好于认为多样的(我想同时是好听的)音乐形式分享了共同的普遍特性。[Li, 2010, p.23.]
试图具体指出产生了美的那些客体的客观属性的精确本质是危险的,因为这将不得不推至客体内容的消失。此外,评价词能否准确无误地运用到其他艺术类型也值得怀疑,即使词汇的含义非常宽泛。比如,音乐中的和谐(harmony)使用到绘画中便不是同一义。就此而言,能够提升美感的那些特质能否在运用上跨越到其他艺术种类,也是不明了的。甚至一些重要的特质在其他情况中变成了缺陷。我们当然要考虑总体的情况。然而真正的问题是当我们类推,我们就是在冒着使谓词减损至无意义处的风险。当我们认识到需要考虑美的程度、美的事物间的巨大差异以及审美口味的变化时,也产生了一些其他问题。
对于口味的问题,李泽厚强调了天才在创造新的美的形式中的作用。*李泽厚关于天才的观点要更复杂,详见Cauvel的讨论。这似乎隐含着美的观念可以有新的特质加入的意思。艺术创造当然不能被涵盖在规则之下。然而,对天才的呼唤似乎有悖于存在着先定的产生美的客观特性这一看法。肯定天才似乎意味着承认非美可以随时间流逝而变为美。李泽厚甚至承认人类文明中的丑陋和野蛮甚至也能随着时间的改变而变为美的。*详见Cauvel, 1999, p.167, 论李泽厚对美和丑以及不快和极度痛苦的态度(on Li’s attitude toward beauty and the ugly, the miserable and the painfully cruel)。[Li, 2006, pp.115 and 181.]我们并不希望严格限制美的含义以至于不包容随时间改变而有的文化多样性。一个例子是,标志着一个阶段的社会主义者的现实主义审美表达是注定要被取代的。[Li, 2006, p.32.]李泽厚承认美的易变,他说“每个时代都有自己审美的标准。”[Li, 2006, p.65.]如果产生美的和谐、比例、融合本身可以被非和谐、非比例、非融合等等东西代替,人们可能开始发现艾耶尔的非认知主义是对的:美是主体自身对客体的回应。我们不过碰巧被社会以几乎同样的方式塑造了对客体特征的相似回应。而这个社会塑造随时而变。
不过,人们或许能确证几样非常普遍而又永恒的美的特质,天才在其中创造了新的形式却不过是表达了同样的普遍特质。这似乎与李泽厚的主客体形式同构的论说一致。在其中,李泽厚试图解释为什么特定的形式可以产生美:因为在主客形式间有相符,存在于带给主体愉悦的经验中的形式的同构。*这个以同构论理解的关于美的假设并不易懂。比如,它似乎隐含着意思:如果和声形式是美的客体的一个客观特征的话,那么和谐形式因其自身而美的原因便是它相符于主体内的和谐形式。然而,聆听美妙音乐时,意识内唯一的结构或形式只不过是音乐留下的印象。当听的人感知了和谐和节奏,他或许能产生一种同构的感受,然而主体却并非通常或必须先认知和谐和节奏才能听音乐。另一方面,至少在音乐中,当先现音弹奏完毕时有巨大的愉悦,而这不过是相似,且并不需要先在。一个人可以诉诸无意识、模糊的和谐或者某种能力来体验同构。李泽厚在谈论“隐”和“秀”时暗示了这一点。“隐”是一种无意识功能,“秀”是一种“突如其来、先获我心似的顿悟式的领会”。[2006,p.105.]“似的”一词很重要,它暗示了没有必须在先的可确认的主体形式。不过不知这是否能帮助理解同构。[Li, 2006, p.51.]不过,或许有非常普遍且不变的客体形式,与其同构的多种多样的主体形式还有待艺术天才的创造。
三、 美的目的
如前指出,两位思想家都沿着弗里德里希·席勒指出的把审美和游戏联系在一起的道路前进,虽然这一联系因石里克相较李泽厚更多的强调而变得越发直白。李泽厚在只是早期在《华夏美学》中谈到了游戏,[Li, 2010, p.5-6]他似乎把游戏界定为审美经验起源中的一个要素,而不像石里克把游戏看做人生的意义。实际上,石里克对游戏作为人生意义的强调,或许在李泽厚看来把审美平凡化了。不过,石里克是在非常广的意义上使用“游戏”一词的。他谈道:“游戏,就我们看来是任何以自身为目而发生的活动,不考虑其结果和影响。”[Schlick, 1927, p.115-116.]
石里克将劳动和游戏列为相反概念,不过并非有相反的指物。他将劳动视为有意识地获取外在于活动的东西的劳作。游戏概念则意指只为所获得的愉悦自身而做,并不考虑功用或种族的生存。
石里克在审美经验中所确证的这种愉悦,给予了人生以意义。石里克说“日用常行可以因充满了美感而具有意义”。[Schlick,1927,p.119.]李泽厚也同样看到了游戏与人的自由、审美经验之间的密切关联。他提及席勒对游戏的强调后评论道:“人只有在游戏时,才是真正自由的。”[Li, 2006, p.94.]所以,两人以不同的表述强调了游戏观念与人生中心价值的关联。
石里克将审美愉悦确认作人生的终极意义,看作行动的终极目标,他认为审美活动对种族延续这一价值无用。李泽厚也把审美经验看做人生的目的。相较石里克更多地把人生的意义看做那些不超出自身的愉悦,李泽厚论述道,艺术使人“进入某种对人生、对宇宙的整个体验的精神境界”。[Li.2006, p.164.]李泽厚有时似乎认为审美经验中有“宇宙性”的意义。他谈到了审美如何“沟通天人”(unified heaven and humans)并“使人与天地交融”(integrated the human and the universe),相信伟大的艺术带来“天感”(cosmic feelings)。*Cauvel讨论了李泽厚哲学中中国观念“气”的地位。气是生命力的原则或者现实的根本质料。气是同构说的基础。李泽厚是否在形上意义上使用气并不清楚。[Cauvel, 1999, p.165.]对“气”的定义参见《中国古代哲学读本》(Readings in Classical Chinese Philosophy), 编者Ivanhoe 和 Van Norden (Hackett, 2001), p.391.[Li, 2006, p.180.]*引用出处系英文版《美学四讲》附录,内容为两位作者的对话,中文版并无对应,故根据英文意译。——译者注艺术是为了抓住“天地的节拍”(rhythm of the universe)。*同上。只是他所使用的“精神的”“天人合一”“天地感”和“天地的节拍”等概念的确切含义是未澄清的。不过他也可能并未在形上的意义上使用它们。他解释道:“对中国人来说,天意味着通达更高的存在,对现实有更深刻的体会,并且不脱离现实。”[Li, 2006, p.172.]*同上。这表示他不是在谈论外部的现实而仅是谈论人类感受的升华。然而他又提到“超出自身的事物”并将审美经验比作西方的神秘宗教体验。*常有评论说审美经验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与宗教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相似。这或许可以说明为什么李泽厚专注于审美经验的社会和道德意义,而石里克更关注审美的生存愉悦的意义。[Li, 2006, p.180. Also see p.163.]
李泽厚的表述或许反映出了他受儒家将天“道”贯彻于伦理、社会行为以及艺术表现之中这一主张的影响。他常提到自然之“律”。不同于科学之律,道之律如孔子所言是规范性的。李泽厚容忍对律的违背,所以看来这不是自然的科学律。*李泽厚接着康德强调自由意志是非现象的,这可以克服仅适用于现象界的自然律的对人的束缚。详见Cauvel的讨论,1999, pp.153-154.
石里克可能会反对李泽厚哲学中的这种宇宙性的关联。而且,即便我们承认直接的感官愉悦和审美愉悦有根本的不同并且承认审美对人类心灵的巨大意义,然而把审美愉悦的意义看做“宇宙性”的还是有些过了。一类愉悦不需要有“宇宙性”的意义,就能够比他种更持久,或更深地影响情感,或更激起想象,或更使人脱离世俗的关切,等等。“天人合一”似乎让审美经验有了自身之外的意义。审美经验只要没有自身之外的目的,他就没有宇宙性的目的,不论这目的的内容是什么。
李泽厚和石里克在人生意义这个观念上可能有根本的分歧,李泽厚也时常将人生意义讲作人生目的或重要性。从石里克的看法来讲,他用“人生意义”(the meaning of life)一词可能是个误用。首先,意义用单数隐含着只有一种意义或目的的意思。其次,“of”搭配“life”使用暗含着意义外在于人生的意思。此外,用“life”而不是“living”暗含了人生已完结。所以,我认为石里克用“人生意义”(the meaning of life)一词表达的,其实是“生存的愉悦”(the enjoyments in living)一词的含义。我不认为,对他来说审美愉悦还有不同于愉悦或游戏的意义。然而,李泽厚对审美经验这一观念的理解要更丰富。*Cauvel说李泽厚认为“艺术和审美经验是人类从其源头进化的驱动性力量”并且“二者也有使人进化到超人的潜能”。[Cauvel, 1999, pp.151-152.]如果她正确理解了“从其源头”的意思,那么这意味着李泽厚关于进化的看法与拉马克有点类似。[参见Li, 2006, p.163.]不过或许她仅是指变化,而不是物种源头的进化。
另一方面,李泽厚曾谈论审美经验说“它没有除自身之外的更多目的”。[Li,2006,p.178.]*引用出处系英文版《美学四讲》附录,内容为两位作者的对话,中文版并无对应,故根据英文意译。——译者注所以,两人同多于异。或许他评论宇宙时,只是说宇宙能产生的意义不落在对美的经验之外。如果是这样的,再同意对美的经验是“游戏式领会”的,那么他与石里克的看法就很接近了。
不过,强调审美愉悦内在于自身或对于种族生存无用会自相矛盾。而如果把审美与人生意义相联系,就不显得那么无用了。石里克说“……愉悦的每一盈余对于个体来说都使其生存更有价值”,因为有了审美愉悦的可能,“厌烦所产生的不安没有了”。[Schlick, 1909, p.19.]这里提供了两处可让功用进入讨论的空间。可以料想,一个人越珍视他的生命,他就越可能排斥那些威胁其生命(或他的后代的生命)的状况,也越有可能制造那些对保全生命有用的物件。如果我们摆脱了厌烦情绪,我们或许会根除自杀的倾向。个体的存活有助于种族的存活。这或许能帮助理解李泽厚对审美产生人生意义这一功能的强调。
这一矛盾或许可以通过澄清有用这一范畴是意指有助于种族生存的东西而不是意指使生存延续的心理动机而得到克服,石里克强调了这一点而李泽厚含糊其辞。有意制作工具可以仅为了审美,也可以同时为了它的使用和审美价值。从其理想形态看,所有的劳动不仅因其促进种族生存而有价值,也可因其产生愉悦而有价值,后者被心理学视为内在的善。同时,审美愉悦虽然以自身为目的,并不考虑功能,却如李泽厚所见仍然可以有教化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