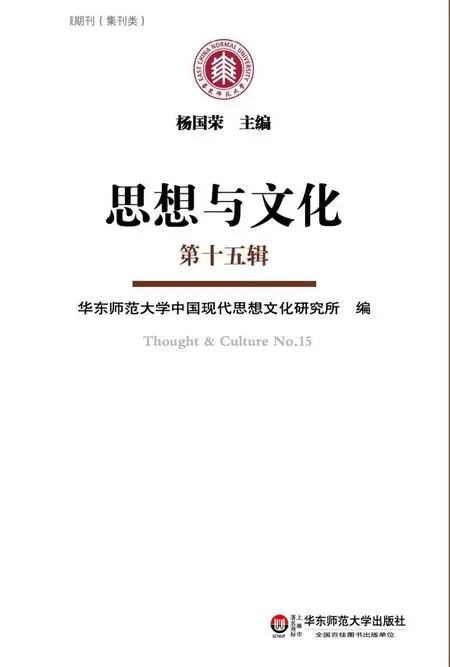围绕着承认意义的斗争:身份,正义还是自由?
●[]· ; ;
我对自我的知识,是在一场成功的追寻中找到的东西;我对他者、与我有别的他人的知识,则是某种找到我的东西。——斯坦利·卡维尔(Stanley Cavell)
一、 正义的问题还是自我实现的问题?
我认为,阿克塞尔·霍耐特和南希·弗雷泽之争的核心并非在于再分配或承认问题,他们争论的关键是承认意味着什么,做什么,为何以及为谁。在这场争论的早期,南希·弗雷泽这样写道:“承认真的是正义的问题,亦或是自我实现的问题?”*RR refers to Nancy Fraser and Axel Honneth (2003) Redistribution or Recognition? A Political-Philosophical Exchange, London:Verso.(RR27)这或多或少表明,我们仍纠结于承认的社会及政治意义——“被承认”意味着什么,我们“承认”个体或群体或要求“被承认”时,我们意指为何。争取承认的斗争也引发了关于承认的充满争议和不断变换的含义的争论。*此处我试图补充图利(Tully)的重述,他将争取承认的斗争当成围绕着承认规范的斗争。即便行动者因无法忍受他们的遭遇而质疑一种(典型为法律的)承认规范时,他们质疑的也不仅是那个特殊规范造成的特殊伤害,而是也暗中试图重新定义承认的实然与应然。我要感谢图利对我正开展的承认意义的斗争的帮助。
从表面上看,弗雷泽与霍耐特的承认观极为不一致。对阿克塞尔·霍耐特来说,就像对查尔斯·泰勒一样,承认是一种“根本的人类需求”*Charles Taylor(1994)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Amy Gutman(ed.), Multiculturalism: Examining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p.25.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是与“人类的主体际性”(RR145)关联的一个根深蒂固的人类学事实。我们不仅渴望承认,而且需要多种多样的承认,诸如在政治领域里获得尊重,在社会领域里实现自尊,在家庭领域里得到关爱。缺乏这些内在关联的承认经验,我们就无法获得充分的“自我实现”:无法成为我们想成为的人,无法过上想过的日子。霍耐特认为,由不承认与误认造成的伤害是社会不正义的最坏形式;的确,承认是整体上解决社会不正义的关键(RR133)。据此看来,不承认或误认的经验损害了那些与对我们的认同要求加以社会认可或肯定相契合的、超历史的规范性期待。如果缺乏这种社会认可,我们就不能发展出“完整的”个人身份,这也意味着我们将不能作为充分自我实现的行动者来行事。霍耐特声称,在公共承认斗争的门槛之下,在这种或那种偶然的历史形态底部,存在着一个“前政治痛苦”(prepolitical suffering)的层面。他认为这个层面可以用作道德理论和社会批判的经验参照点以及规范性资源。从以上材料中,霍耐特构造出一种无所不包的正义理论和社会批判理论。
另一方面,对南希·弗雷泽来说,承认在正义理论中扮演着一个重要却有限的角色——从规范上扩大平等的意义和实践。这需要从一种“伦理的”正义规范框架切换到一种义务论的框架,前一框架的核心是自我实现的超级善(hyper-good),后一框架的核心则是“参与平等”(participatory parity)的道德—民主理念。她不把承认看作个人自我实现的工具,而是看作让人在社会交往中获得真正伙伴地位的工具。她论证指出,承认最好被当成一个与社会地位(social status)有关的问题,而不是被当作一个形成“完整”个人身份的必要(显然也是充分的)条件起作用的人类学常数。我们理应关注的是那样一些文化价值模式,正是它们将某些个人和群体建构为“低等、受排斥的,完全的他者或纯粹不可见者”。在此类情形下,我们就能正当地谈论“误认以及从属地位”(RR29)。对这类情况下的非正义进行“补救”的措施就是将这些滋生了误认和从属地位的文化价值模式“去制度化”。这里召唤我们去做的调整不是去修复社会成员被扭曲的主体性或受伤害的身份,而是去恢复他们作为社会交往中真正伙伴者的地位。
霍耐特与弗雷泽基本不认可对方的观点。弗雷泽对霍耐特的批评尤其尖锐,她对霍耐特的整个规划表示怀疑,认为霍耐特的规划过于雄心勃勃,有一元论和基础主义之嫌。我相当认同她对霍耐特所做的一些批评,我在别处也做了类似的和补充性的批评*Nikolas Kompridis(2004)‘From Reason to Self-Realization? On the “Ethical Turn” in Critical Theory’, Critical Horizon 5(I), repr. in John Rundell, Danielle Petherbridge, Jan Bryant, John Hewitt and Jeremy Smith (2004)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in Critical and Social Philosophy. Brill Leiden.。然而,我也同样对弗雷泽本人的进路表示严重关切。正如无论把正义还原为承认还是还原为再分配都是不明智的一样,把承认斗争还原为正义或还原为身份同样是不明智的。以上两种非此即彼都建立在错误的反题上,继续讨论不会带来任何收获。此外,由于不仅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承认的意义本身是可争论的,因此更为明智的做法也许是不把它关联到这种或那种规范理念,来过于严格地定义它的含义。
二、 无痛苦主体的误认
现在我想仔细考察弗雷泽承认理论的两个内在关联的特征,她相信正是这两个特征:(1)公平性(impartiality)和(2)公开性(publicity)标准的结合,使她的观点在规范上优于霍耐特的观点。由于她将承认当作义务论道德框架内的正义问题,在义务论框架内,正当与善分离并且正当优先于善,弗雷泽就无需像霍耐特一样,为了自我实现观而不得不做出引起争议或宗派之争的举动,诉诸一个历史或文化上特定的善观念。对她来说,所有的工作都可交由参与式平等的非宗派主义义务论规范去做。由此,她相信她的承认理论能诉诸一个与价值多元论及深度多样性兼容的、公平的规范立场。可是,我不认为靠着采取另一个立场来摆脱一个有争议的规范立场,就必定能使她的承认观优于霍耐特的承认观。因为毕竟也可以理所当然地认定,弗雷泽的公平性标准所依赖的正当与善的明确区分已成为历史。那些仍在传播的有力论证回答了在价值多元论和深度多样性的挑战面前,为何强大的公平概念只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案。这些论证其中之一显明了任何争取承认的斗争,围绕着承认的意义和要求的斗争,“总是隐含着我们刚刚开始认识正当和善的区分的复杂方式”*James Tully (2006) ‘The Practice of Law-making and Problem of Difference: One View of the Field’, Omid Payrow Shabani (ed.), Multiculturalism and the Law: A Critical Debate. Cardiff: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那种认为我们能保护正当免除于善,并使它不受来自多元论与多样性的挑战的看法是不攻自破的。因此,我们要抵制一个仍具诱惑力的观点,认为存在一种无可争议的、随时待命的公平规范,我们可以在处理承认诉求和“文化诉求”时将它作为解决问题和化解冲突独一无二的最佳程序。这种想法同样难逃规范一元论的窠臼,即便它没有霍耐特主张的那样明显。
弗雷泽所诉诸的公共性标准也困难重重。尽管弗雷泽也同意,误认(misrecognition)确实具有泰勒和霍耐特描述的、负面剥夺性的“伦理—心理后果”,她却坚持“误认的错误不依赖这些后果的存在”。(RR32)在她看来,“一个被制度化规范削弱了参与式平等的社会,无论那些规范是否扭曲被压迫者的主体性,在道德上都是站不住脚的。”(RR32)但这是否意味着在道德层面,误认的后果也无关乎对其错误的判断?确实我们很难想象在真实的、有历史重要性的误认案例中,这些伤害的后果不存在。同样也确实难以想象当那些后果不存在时,人们如何能意识到对他们自己或他人的误认。如果回避误认造成的痛苦,那么这个概念的可理解性,它在道德话语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也变得不可思议。是否只要造成剥夺性“伦理—心理”后果的制度化规范不违背“参与式平等”的原则(假设真有可能的话),弗雷泽就打算接受它们吗?这些后果的出现不正意味着我们当前对平等规范的建制化出了问题吗?并且这难道不是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已经成为当代民主的规范性语汇一部分的原因吗?那么是什么促使弗雷泽将误认的“伦理—心理”后果与对其错误的判断脱钩的呢?
显然弗雷泽这样做是出于对客观性的考虑。对她而言,“误认是一种外显的,可公开验证的伤害,它妨碍某些人成为充分意义上的社会成员。”(RR31)如果我们要将“真正应得之名的不正义(what reallymeritsthe title of injustice),而非仅仅被体验到的不正义”(RR205)概念化,就必须拒绝诉诸一种无法被公开验证的、独立且“原始的”主观经验领域。我们所需要的是一种根本不同的策略,即不从直接的主观经验出发,而是从去中心,去个人化的正义话语和社会批判出发。因为这种“无主体”的话语为评估承认诉求,提供了一个远较“难以言表的痛苦”(inarticulate suffering)更可信和客观的经验参考点。不像后者,前者不“躲避公开争论”,还具有“能接受开放论辩的批判性审查”(RR205)的显著优点。
然而我必须承认,“真正应得之名的不正义,而非仅仅被体验到的不正义”的区分在我看来是很令人担忧的。尽管主观体验作为辩护的源泉是出了名的不可靠,但它同时也是可理解性(intelligibility)不可替代的、绝对必要的来源。值得考虑的痛苦不可避免地是第一人称的。即使我们把这样的观点先搁置起来——在辩护中公开有效的辩护标准人人都可用,从来都相持不下并始终受到质疑——我也很难否认,要成功地确定误认,必须同时通过主体经验和无主体话语这两方面的检验。正如无主体话语必须矫正、检查主观体验一样,主观体验也必须矫正检查无主体话语。我们必须确保在主观体验与无主体话语之间存在相互的循环或反馈过程。确实,主观体验必须渗透在无主体话语之中,以确保话语言之有物,不造成另一重异化:被误认者必须要能够在无主体的承认话语中肯定自己的处境,并经由它来理解自己的痛苦。弗雷泽打算以牺牲主观体验为代价,赋予无主体话语以特权的做法,暴露出她思想中的某种实证主义残余,仿佛我们不需要一个受苦的主体就能对误认做出解释*对弗雷泽的补充批判以及从阿多诺的视角出发的关于误认和痛苦的有启发性观点,参考Jay Bernstein(2005) ‘Suffering Injustice: Misrecognition as Moral Inquiry in Critical Theo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Studies, Special Issue on ‘Rethinking Critical Theory’, I3(3):303-25.。
在应得之名的不正义和仅仅被体验到的不正义之间的区分还有一些令人担心之处,具体地说,跟这样一种隐含的假定有关:只有当一种经验是“外显的且公开可证实”时,才能算作一个有效的误认案例。这里假定了,目前可用的提出诉求的语汇与无主体话语,就是我们用来表达承认诉求以及为其辩护所需的所有语言。这也假定了,误认具有一种已为人熟悉的公共形式。但如果我们需要申诉的事情不能以目前可用的词汇和话语做“外显的、公开可证实”的表达,我们也不可能单单在一夜之间无中生有般创造出所需的话语和词汇,那么对这种预设现行话语和语汇已经足够用于评价和辩护的所谓公开可证实性标准,我们又能有多大信任呢?
我对弗雷泽这里的立场感到困惑,因为在她之前的著作中,她已经承认那些因为身份受伤害而遭受痛苦的人,需要改变承袭下来的身份语汇“以扩大他们的行动领域”,将无能的身份(a disable identity)转变为“一种赋权的身份(an enabling identity),一种人们愿意去宣称的身份”。*参见Nancy Frazer (1991) ‘From Irony to Prophecy to Politics: A Response to Richard Rorty’, Michigan Quarterly Review, 30(2):259-66.如果人们不是亲身体验过那些承袭下来的身份语汇如何造成声音被抹除,能动性丧失的后果,又怎么会意识到这种需要?
这就是我们为何不能假定现行话语和语汇已经足以去辩护的理由,这也是为何必须一直将主观体验作为一个不可消除的规范参照点,用于反抗、争辩和转化的理由。
然而,弗雷泽的公共性标准还存在着另一个成问题的潜在假定,假定承认诉求跟直接的真理诉求和某些道德诉求一样,是充分明言和确定的(fully explicit and determinate)。而这正是她有关地位的承认模式对待诉求的方式。可是,由于承认诉求并非完全是正义之事,它们同时还与我们的身份以及诸种相关联的善交织在一起,就一定充满了不确定性。因此,要用表达承认诉求的现行语汇去完全满足承认的要求和需要是基本上不可能的。因为何时一开始诉求,“难以言表的痛苦”就必定获得了表达。因此,这将导致一种情况:需要提出的诉求无法先于成功的言述或表达(articulation or expression)被提出。在此情况下,“正义是得不到伸张的,相反,有些东西必须被显示。”*Stanley Cavell (1990) ‘Conditions Handsome and Unhandsome’, in The Constitution of Emersonian Perfectionism, p.112.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任何言述的“成功”都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显示出了在未经言说前我们就看不见的不正义。通过对承认(误认)的公共实践,以及更一般的制度化规范和安排所具有的道德相关性特征(这些特征在先前未被主题化或未被重视)的揭示,这样的言述阐明了为何在未经显示前,正义就不能得到伸张。
一旦我们认识到承认诉求的高度不确定性,以及内在于其本质中的不可言说性,也许我们会对不可言说的一个面向,我们称之为失音(aphonia)的体验,那种无法言说、无法表达的体验,变得更加敏感。这同样是误认造成的一个剥夺性后果,而且在我看来驳斥了弗雷泽的公共性标准。这里的问题不在于不愿冒公开争辩和批判审查的风险,更直接的问题在于缺乏一种声音,更确切地说,没有自己的声音。因为除了自己的声音之外,其他声音都不能反映、甚至体察自己的痛苦和不幸。我们不仅缺乏恰当的言词来充分言说自己的不正义体验;而且在字面和象征意义上,我们也变得哑口无言。只有找到我们自己表达那种不正义的声音,给它命名,才能将对不正义的体验转化成名副其实的不正义。如此一来,我们寻找声音的斗争,对迄今为止无以名之的不正义体验赋予名称,就扩展了这场斗争的道德视野;同时提醒我们,公共理性不可被还原为辩护性话语:如果不正义被视为不正义的话,它必然包含一个语义学上创新的解决问题(例如,使无可言表的痛苦得到言表的问题)的维度。这也警戒我们,公共之光如何在带来光亮的同时又使人目盲。由于公共之光的照射,我们可能会看不见一个议题或冲突的道德相关性特征,正因此,我们需要靠着解除公共之光本身所造成的遮蔽,来不断适应光亮。这也意味着我们要在实践理性的公开应用中加入解蔽和言述的作用。*关于理性的“世界—解蔽”角色,参考(2006)Critique and Disclosure: Critical Theory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我想暂时离开对弗雷泽的讨论,转向霍耐特的语义—政治斗争的承认理论,引出它给非正义和认同的新表述所带来的意蕴。根据霍耐特,一旦我们认识到我们的声音本身处于危险境地,则克服无言状态、重获“我们的”声音的斗争,就不能被充分地解释为是一种争取承认的斗争(甚至在动机上也不是),既然它更根本上是一个争取或围绕着表达展开的斗争的话。有关自己声音的问题也许是在误认的语境下产生的,但它不能由任何恰当形式的承认解决,而是通过承认,我们才能最终确保是我们自己的声音在说话,我们自己的力量在行动。我们企图确保我们所说的、所做的都属于我们自己,这种企图只能部分地得到满足。甚至即使在最理想的社会政治条件下,我们所寻求的“满足”也只是暂时的,且经常受到规范的挑战以及自身引发的怀疑的制约,因为我们必定会发现“满足”出现在“渴望”最初产生的地方:在承认既被赋予亦遭否定的主体际性条件下,“满足”会轻易转变为“不满”或被“不满”所取代。
霍耐特的承认理论夸大了我们为了实践自身的能动性(agency)、为了用自己的声音言说而需要承认的程度。虽然我无法在这里详述,但黑格尔关于主奴辩证法的分析确实会令霍耐特尴尬,因为“奴隶”在不平等和误认的条件下仍可以实践新赢得的能动性并获得一种新的自我理解。黑格尔至少部分地证明了,不接受对霍耐特而言达到能动性和个人身份的充分必要条件的那种承认,同样能解决由不满足(也不可满足)的渴望所带来的“认识论危机”。确实,正是拒绝给予“奴隶”理应获得的承认以及随即引发的认识论危机,迫使“奴隶”重新思考,转变自我理解。所有这些的要点不在于误认真的对我们有好处,以至于我们不需要对遭误认过于担心;要点在于承认和误认不足以决定我们的身份以及我们对自身作为行动者的感受。我们塑造自身身份和实践自身能动性的力量并不严格依赖于先前所得的恰当承认。即使在承认被拒绝或缺失的情况下,我们也能一而再地做出行动。此外,就我对黑格尔的理解而言,误认的体验并不必然包含一种不正义。误认可能意味着一种与他人的激烈危险的相遇。在那种情形下,我们遭遇的他者挑战了我们声称自己拥有的承认,挑战的目的不在于维持统治和不平等的条件,而是为了开启自我理解的转变,以及我们与他人相互关系的转变。*对此更详尽的论述见(n.4),pp.346—9.
从这里得出的另一层意蕴是:世上所有承认都既不能确保我们自己的声音,也不能代替我们自己的声音。霍耐特承认观的“至善论”关切,缺失了由爱默生,尼采,海德格尔以及更晚近的卡维尔加以主题化的某种东西,即对“自我实现”构成了“内部”障碍的那些因素的意识或充分把握——爱默生称之为“从众”或“一致性”,尼采称之为“怨恨”,海德格尔称之为“常人”*Ralph Waldo Emerson (1990) ‘Self-Reliance’, Essays:First and Second Series, New York:Vintage. Friedrich Nietzsche (1969) 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s, tr. Walter Kaufmann and R.J. Hollingdale, New York, Vintage. Martin Heidegger (1962) Being and Time, tr. John Macquarrie and Edward Robinso, Part I, ch.4. New York: Harper & Row. 关于这点的论述参见Kompridis的Part II (n.9) and (即出的)‘Intersubjectivity, Recognition and Critique’.这又是一个为什么我认为弗雷泽放弃关注自我、身份,以及所谓“前政治痛苦”经验的进路是错误的理由。自我与社会的二分已经过时。弗雷泽的做法受一种形而上学图景的影响,后者建立在一系列关于内在/外在、主观/客观、私人/公共等二分基础上,但这些二元区分都是成问题和带有偏见的。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泰勒,卡维尔的写作就是批判这类图景的范例。。不是所有对我们能动性的自由实践,或对我们的一种更自由、更实践的关系构成阻碍的东西,都是“外在的”阻碍。(在阻碍面前)我们会发现我们对自己变得不可理解、不透明,“似乎我们受制于一些我们无法表述、无法辩护的要求,似乎我们的生活谴责着它自身。”*Cavell (n.8) pp.xxxi-xxxii.即使得到应有的承认对这一局面也于事无补,因为正是承认关系本身,使得争取我们自己声音的斗争变得要紧和不可抹煞。
另一方面,我觉得霍耐特认为我们需要一种痛苦现象学的主张是正确的。只要它不是基础主义的,进行这一工作就无可厚非。从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例如更敏感地关注到对现有公共话语不足以言说的痛苦,以及我们的实践和制度中未曾注意到的方面,那些方面可能会造成名副其实的不正义。遗憾的是,霍耐特并未提供这样的现象学。他所提出的是一种痛苦分类学,它事先产生于一种过于雄心勃勃的尝试,即试图将一切反对不正义的斗争必定在其中发生的规范空间加以概念化。然而,即使一种适度的现象学也需要一种尼采式的痛苦谱系学来加以补充和平衡。藉此我们方能更好地理解隐藏在我们承认需求之下更深的动机和复杂性。*Wendy Brown (1995) ‘Wounded Attachments’ , States of Injury, pp.52-76,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三、 使承认工具化
到现在为止,我仅仅聚焦于弗雷泽与霍耐特之间存在的深层分歧,但他们的承认观也有一些共同假定,这里我想分析其中一个。霍耐特和弗雷泽都秉持工具主义的承认观,即,他们都将承认视为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无论目的是完整的个人身份还是完全的社会参与。并且他们都认为承认是明确或外显的(explicit or overt),是某种我们能够处理,能够凭国家行动或个人意愿动员起来的东西,就好像一旦一个承认诉求被公开证明为正当,接下来要做的就只是以恰当的程度和方式进行管理。正如弗雷泽挂在嘴边的那样,承认就这样被当作对不正义的“治疗”。
对这种工具主义的承认观我有两点质疑。这里我也想重新聚焦弗雷泽的理论。首先,工具主义的承认观使承认、身份以及公正问题医学化(medicalize),就好像我们是在对付身体政治中的疾病,需要对症下药。*霍耐特尤其表达了这种医疗化趋势。对这一趋势的批判参考Kompridis (n.4)。其次,工具主义的承认观试图将根本上无法工具化的东西工具化。承认不是我们可以任意处置,给合适的人适时适量地开出药方的事情。经济资源可以通过国家机制的运作加以再分配,但承认不行。这部分是因为承认不是一个可轻易估量、重新部署的东西。诚然,为了与非法的排斥、不平等抗争,承认的法律形式确实创立了承认规范。但是,尽管法律机制在改变承认实践时很重要,我认为对于理解承认斗争总体上的重要性来说,法律承认还不是一种足够复杂的模式。(不仅因为承认的法律规范本身总是有待质疑的)。
无论承认是什么,如果它确实是一种可界定的实践的话,看起来都在一种再教育过程、在我们认知定位以及规范期待的改变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是一个更大的学习过程的组成部分,其结果,就它是一个真正的学习过程而言,是不可预见和出乎意料的。制度性措施是促进这一学习过程的方式之一,但即使承认的法律形式有其必要,本身也不足以在日常实践层面为我们带来所需的象征的及文化上的改变。此外,正如弗雷泽和其他论者指出的,产生这一改变的法律机制本身也会遭到拒绝甚至抵制。因此,弗雷泽要回答的问题是,当她谈论“文化价值模式的去建制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时,她所设想的是何种改变。这一改变是否要以“建制”的方式达成,例如通过法律机制?这里,我们是否用了正确的规范和概念化的语言以达到一个在规范上,文化上更为复杂的过程?
当我们考虑弗雷泽的“解构的承认”意思以及指望它所起的实践作用时,这些问题就变得相当切中肯綮了。尽管她与霍耐特一样持有传统的承认观,认为承认是一种能在不同社会背景下以多样方式表现出来的明确的认可行为,她也同样认为某些误认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承认,这些误认所需要的“治疗”不在于肯定受不义侵害的群体身份,而在于解构那些群体差异被阐明出来的特定术语。作为肯定的承认(affirmative recognition)或多或少地保全每个人的身份,而作为解构的承认 (destructive recognition) 将“改变每个人的社会身份”(RR13, 75)。
显然,解构的承认是保守的肯定承认的“激进的”对立面,但在实践中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并非显而易见。解构文本是一回事,解构身份则是另一回事。对文本的解构不需要将自身的任何东西置于险地,确实,只要开始解构,其结果就自动出现且基本在预料之中。但解构我们的身份则会将几乎所有与我们相关的一切置于险地,我们不知道接下来如何发展或期待什么。毕竟,解构我们的身份不可能是我们真的在行或实践上有把握的事情,对这一领域的掌控意味着失败而非成功。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的身份抗拒解构,或者我们同时是解构的“主体”和“客体”,而且因为解构的过程和结果是我们无法控制或预见的。
因此,关于“解构的承认”能否构成一项社会实践的问题就自然产生了。无疑,如果它成为我们能规范地支持的实践,它就必须是一项民主的实践,需要得到所有人的合作和同意。但这将给一个开始就高度不确定的过程引入更多的不确定性。此外,假如“解构的承认”以某种方式成为一种民主实践,那么它的为“每个人的社会身份”带来改变的“激进”抱负,就不得不因为与多元主义的面对面遭遇而缓和——事实是,有些人有充分理由去保留并延续他们某些方面的身份,希冀把这些身份传承下去而不是任其流失。*Nikolas Kompridis (2005) ‘Normativizing Hybridity/Neutralizing Culture’, Political Theory, 33(3):318-43. 此文中论及的话题,参考Seyla Benhabib(2006)‘The Claims of Culture Properly Interpreted: Response to Nikolas Kompridis’, Political Theory 34(3):383-8,及我的回应(2006)‘The Unsettled and Unsettling Claims of Culture: Reply to Seyla Benhabib’, Political Theory 34(3):389-96。
我刚才所描述的与弗雷泽的有点不同,她试图将解构的承认作为一种可行的社会实践。她提议将“改良主义改革”作为“中间道路,将其置于一种政治上可行却有实质缺陷的肯定策略,和程序上说得通却在政治上不可行的转变策略之间”。(RR79)但我完全不认为“解构的承认”在程序上是说得通的;相反,我认为由于弗雷泽假定承认是可工具化的,因此她的概念化作为一种可能的实践遭到了严重削弱,以至于她错误地理解了文化上的转变能够和应当怎样发生。*我要补充的是我觉得将“非改良主义改革”概念运用到再分配的做法更有前景。
如果我们注意到通过“解构的承认”这一概念,弗雷泽无意中将承认问题与身份这个她当初极力要与之区别的问题重新联系了起来(姑且称之为被压抑的复归),我们差不多又绕回了原地。现在我们认识到承认既是平等的问题又是身份的问题,既是公正的问题又是能动性的问题。然而,我们仍不确定承认是怎么回事,既不明白它对我们的意义,也不明白我们希望或需要它在社会生活中起什么规范的或政治的作用。
四、 承认的话语和反话语
一直以来我们处理的是一种本质上是治疗性的承认话语,它区分好的和坏的承认,并将前者看成毫不含糊地是好的,是对后者所造成伤害的可靠补偿。同时,一种更怀疑的反话语多多少少出现了,对承认的反话语来说,承认包含在一个社会建构的复杂过程内,是我们要持续和无情地加以解构的。令人钦佩的是,虽然不成功,南希·弗雷泽还是力图将这两种话语合并,以克服它们各自的局限。
但或许我们所处理的实践与期望实际上是异质的,它们远不像承认理论家阿克塞尔·霍耐特所相信的那样明确,那样稳定。如果这一印象是对的,那么我们就需要一种更为多元的、语境主义的承认观,无论它有多么复杂,内部有多么分化,而非一种一元论的承认观。霍耐特的承认观偏向某种形式上的善理论,其核心是一个极具争议和有缺陷的自我实现理想,为自身的目的来塑造承认的实践。
我认为詹姆斯·图利(James Tully)在正确方向上迈出了重要一步,他将争取承认的斗争重塑为围绕着承认规范的斗争,而不是对个人合法身份的斗争。通过将焦点转移到承认规范上,图利将围绕着主体间规范的斗争与我们希望如何被统治的斗争联系了起来。因此,承认变成了自由的问题,而不仅是公正或身份的问题,误认变成了对自我统治之自由的一种不正当剥夺。由于围绕着承认规范的斗争同时也是对承认和被承认意味着什么的斗争,就不存在一个终极的、完美的承认状态,根据后者所投射的规范之光,我们能理解当前的承认实践和形式的不足与缺陷。如图利所指出的,就像所有道德,政治规范一样,承认规范具有规范的功能和标准化功能,这两者都会引起抵制和反对。无论承认规范的出发点或意图有多好,无论它如何具有相互性或互惠性,它在实践中的结果总是可质疑、可争论的。确实,我们可能同样要担心相互性、互惠性承认规范所具有的强制力量。*Tully (n.5).
也许现在是问我们究竟想从承认中得到什么的时候了,因为我们可能已经将承认规范化,标准化到一个程度,以至于使它承载了过多的社会政治要求。也许现在该思考不仅哪些是承认能为我们做的,而且哪些是不能为我们做的;是时候思考哪些是我们能从承认那里获得的而哪些不是。也是思考承认的局限的时候了。我认为有理由说,充分完整的承认是一种妄想。任何承认,甚至最好的承认都是部分的,是不完整和片面的。由于我们在行动时无法充分认识行动的后果,由于我们的动机和行为对我们来说不是完全透明的或充分可预见的,因此产生误解的可能性就包含在每一个承认的行为当中。无论好坏,这种可能性都在我们诠释和运用现行承认规范的实践中实际体现了出来。
我不仅想表明,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令承认概念负担过重,而且想表明,我们在一定程度上错误地理解了它所表现的善以及指望它具有的效果。有充分理由去质疑我们对承认的渴求,去质疑指望它去满足的愿望。我们对承认的欲望可能最终只是一种“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望,哪怕是来自同等者的承认,个中原因值得给出比目前更好的理解。对我来说这种质疑标志着在承认以及与承认有关的话语中的一个新方向。*除了Jame Tully的著作之外,我在此想到的是Wendy Brown (n.13) and Patchen Markell (2003) Bound by Recogni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参见James Tully (2006) ‘On Reconciling Struggles over Recognition: Toward a New Approach’, in Avigail Eisenberg (ed.) Equality and Diversity: New Perspectives,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pp.15-33 (2004a); ‘Exclusion and Assimilation: Two Forms of Domination’, in Melissa Williams and Stephen Macedo (eds) Domination and Exclus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191-229(2004b); ‘Recognition and Dialogue: The Emergence of a New Field’, Critical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7(3):84-106。在这一承认的反—话语的脉络中,参考Andrew Schaap (2004) ‘Political reconciliation through a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Social and Legal Studies 13(4):523-40。
或许我们需想象一种不同的承认实践,不在肯定的实践与解构的实践之间做清晰划分的实践。或许我们该朝着这样一种承认实践努力:它在我们社会生活中没有既有的形式或定位,它们富有表现力却经常伴随着自我批评,以我们尚未描画的方式融入被误认者和误认者。我无法就此谈论更多(我希望我可以)。尽管我同意批判理论在经验现实中需要一个规范立足点,但它更需要力量来揭示不同的可能性,那些我们尚未涉及的可能性。*对这种可供选择的批判理论概念的系统表述,参考Kompridis (n.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