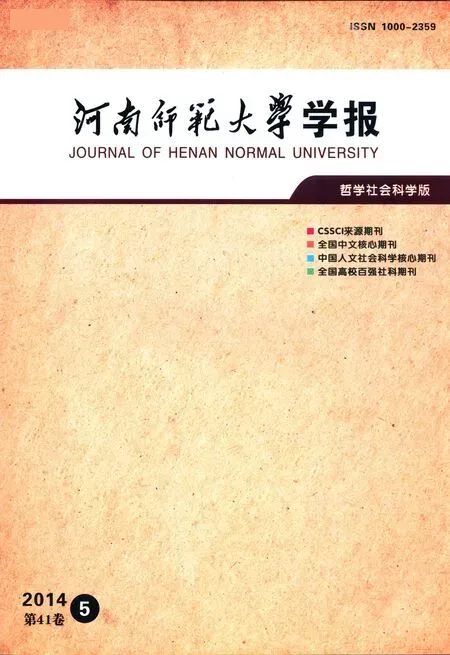作为“他者”的农村形象——“非虚构”农村文本的写作之反思
葛丽娅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基础部,河南 郑州450044)
“非虚构”文学在我国诞于2010年2月,由《人民文学》开辟出“非虚构”专栏的力倡而得名,但在传统分类学的视野之下,“非虚构”写作似乎无法归入任何一类,从广义上说,一切以现实元素为背景的写作行为,均可称之为非虚构写作。在一个开放和平等的社会背景下,非虚构可能带来的是平等性的叙事竞争,但对于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来说,非虚构恰恰缺少平等竞争的可能性,因此,非虚构自身所具有的标签和实际写作行为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悖论。而这一问题在有关非虚构农村文本的写作中则体现为更加明显。中国农村形象会在不同的文本中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知识精英、权力精英和资本精英以不同方式叙述农村,并塑造出了不同面貌的农村形象。但因为历史的原因,农村一直以一种被书写者的他者形象存在,在书写者拥有的特权中被各种目的性的塑造。
一、拯救者:书写者的自我神话
在历史上,或从政治的角度进行的书写农村,“将其塑造成为革命、改革和建设的一个基础部分,并通过宏大的政治话语对农村进行着系统的权利剥夺”[1];或从文化的角度来书写农村,则存在较为复杂的态度,其中较为明显的两种态度中,一个是贱农思想,另一个则是农村乌托邦思想。贱农思想在各个领域里存在,从日常生活中媒体对于农村的丑化到专家学者对于农村的厌恶和消灭的学术冲动,无不强烈地体现出对农村的歧视。但与此形成对抗的则是农村乌托邦思想,但这种思想与其说是指向农村本身,毋宁说是指向对抗现代文明的一种符号空间,与农村和农民的生活史本身没有关系,与此同时作为社会和生命史的一部分的农村则是沉默的。非虚构的写作假定了书写者对于历史的客观性,以中立的立场和方式去呈现历史的面貌,试图让农村和农民本身说话,呈现出强烈的拯救者意识,虽然农村和农民历史的处于被书写的位置,在一个更大的社会历史中必须等待书写者,但书写者的拯救者意图与农村和农民的生命史本身并不能得到完全的认同,书写者的态度和目的就成为一个根本性的障碍。
非虚构强调的是对自我生活的客观表述,但非虚构写作中的政治性决定了自我生命史书写的空缺。在我国的文学发展中,书写自我的生命史的载体更多体现为文学的方式,以一种更加符合艺术标准的方式展现出来,而不是“以自我生命体验的方式展现出来”[2]。但在西方的写作发展中,因为跨文化交流和意识形态的原因,在早期的商人、探险家和传教士中慢慢形成一种独特的写作模式,并且成为现在西方较为成熟的人类学写作模式。但在中国传统的写作养成中,并没有将这一写作能力当做一种能力加以训练。因此,在试图以呈现特定社会中社会和个人生命的过程的时候,并不能找到恰当的写作基点。对于一个成功的人类学式写作来说,田野工作是进行写作的必要前提。而这一工作寻找的是对于被书写者的一种理解式认同,而非书写者在自己的立场上对于被书写者的目的性塑造,在文化上的抽离使得这一写作带上了一种沉重的拯救意味,认为农村本身天然是沉默的,或者农村方式本身是天然沉默的,只有通过一种现代化的和人文性的拯救才能让农村发声。较早以客观眼光看待中国农村的当属张五常,在一系列关于农村的文章中,非常独到的指出了农村发展的进步意义,从而将农村从完全被动的拯救者的位置开辟了另一种可能性。对于中国社会学中一部分以人类学方法研究农村的学者来说,更是沿着吉尔茨所形成的深描路线,从一个个的个案乡村出发,将农村和历史和农民的历史深入的描述出来,而这些都深深的嵌入在一个更大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中,而不受任何先定的书写者拯救意识的影响。
因此,尽管“梁庄们”被抽象化为中国农村,并且借助费孝通有关乡土中国的逻辑结构证成其正当性,但作为非虚构写作来说,更加重要的应该是运用人类学式的训练,而不是作为一个带有猎奇意味的农村故事的编撰,在一个更加满足写作圈子内部游戏规则的层面上,借助于农村和农民的苦难开辟自己的突围阵地。
二、代言者:自我抑或乡村
作为最受关注的非虚构文本,如梁鸿“梁庄”系列文本写作中有作者曾坦言自己实际上无法抛弃先验的观念,只能作为一个具有高度警醒的书写者,时时提醒自己先验观念对写作的影响。但依靠一种自觉显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所以梁鸿干脆自认了“必须要进行语言的编码,要经过隐喻才能呈现给大家”[3]3,这一隐喻的过程本身已经决定,你的叙事只能是文学的、而非彻底的真实。但这种哲学意义上的无力感并不能为其非虚构写作提供解决方案,相反,作者的态度依然回归到了自我,回归到了一个经历了对乡村的悖离,受到整个社会和文化关于农村苦难描述的影响,进而以农村血脉的使命感开始自己的写作,但也只能是自己的写作,并最终无奈转向了一个重新模糊化的方向,“而是重回生命之初,重新感受大地,感受那片土地上的亲人们的精神与心灵”[3]5。这一思考的过程即便不是一个道德感过重的文学写作者的一个不成熟的思考,也无法以自己道德上的高尚和感情上的真挚来置换乡村。实际上,这一无奈的思考过程,与其说是成就了农村,到不如说成就了梁鸿等文学写作者自我成长的蜕变,完成了一个从农村出来,并以远远悖离农村方式拥抱城市之后,在社会和道德想象的压力之下内心的焦虑感和对农村的负罪感。通过一个类似心理治疗的宣泄过程,以可以自我治疗的方式展现自我心中的农村。
因此,作者非虚构写作者的身份和立场充满了歧异的色彩,成为在文化和情感上双重分裂的局面。从文学内部来说,非虚构写作本身并不是因为社会的发展和被书写者自身觉醒的结果,而是文学内部发展中解决自身困境的一种救赎。写作者的职业和文化限定中某种程度上原谅了自己对于被书写者的暴力入侵,并且通过更为隐秘的方式使得书写者本身成为一个更为神圣的身份,从而完成了一个吊诡的书写者和被书写者在言语的所指和能指之间的倒置,一个更加形象生动的农村出现的时候,也恰恰是农村从现实中消失,并被非虚构写作重新符号化的时候。除了文化上的分裂,还有内在的情感上的分裂,关于农村题材的非虚构写作,都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其写作的内在动力上,都会回归到情感的驱动上,尤其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以感性为特点的思维方式更是推崇情感上的优先。因此,带有亲近和同情农村的情感态度为写作在道义上的正当性提供了更多的依据,但这种情感上的推崇并没有基于对农村和整个中国的社会现实的完整基础,而是从对于写作者自己从农村走出,在自身在城市生活中得到了基本的成功之后,以感恩或者反哺的心态来回报农村,并且以带有文学色彩的方式来表述的时候,也完成了自己情感上的升华。
在这种双重分裂中,非虚构的面貌变得模糊不清,这不仅仅是非虚构写作者所面临的两难问题,也是非虚构写作传播过程中的两难问题。对于写作者来说,只有具备了可以远远审视和评判农村的资格的时候,才获得相应的话语权力,但这一话语权力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以悖离农村文化为基础的,因此,天然的意味着书写者和被书写者之间具有文化和社会上的巨大差距,尤其是在农民的价值观和生活体验上,可以说之间具有无法弥补的差异,非虚构写作中如何弥补这一差距,就成为非虚构写作至为重要的问题。
三、暴力抑或温情:非虚构的道德两难
在关于农村的非虚构写作中,书写者和整个社会的主流价值成为表现和评价农村和农民的重要基点,并且将这一基点泛化为道德正当性的当然前提,从而展开对农村和农民的展示、评价和救赎,但这一过程中,农村和农民处在话语权力的他者位置,而不具有主体性。非虚构写作一方面以话语的暴力方式将农村和农民乃至更为广义的底层社会纳入固有的话语体系,通过遥远的话语谱系来叙述现代的农村和农民的命运,并试图将这些纳入一个可供历史正当性解释的话语体系中。但为了获得道德上的正当性,并将非虚构写作纳入一个符合人文的谱系中,展示文学对于人和社会的历史责任感,又无法摆脱文学中温情的外衣。
从我国文学发展的传统来说,一直无法脱离对社会和主流意识的功能的束缚。写作本身就是思想和意识形态实现的重要工具,是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精神支配手段。在中国城乡呈现为现代的二元分化格局的过程中,从文化、经济、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的全方位身份支配体系得以建立,一个庞大而系统的暴力侵害体系逐渐形成。在1952年以前,农村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战争和自然灾害的伤害之后,虽然出现了愈发衰败的景象,但这种衰败并不涉及对于农村社会和价值评判的问题,更不涉及对整个农村的否定性评价。但自1952年开始,因为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原因,农村成为一个特殊的对象,并被国家整体性的定义为与社会主义追求不相容的需要严格改造的对象。但改造的方式并没有采取让农村向城市方向发展的方式,相反,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置,将农村与城市隔离开来,形成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化的格局,并将农村和农民隔离在一个与现代化近乎绝缘的位置。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农村和农民开始向城市流动,正像有的学者所说:“中国的乡村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经历了短暂的‘黄金期’之后,终是要与‘田园风光’告别,并不得不迎接势如破竹般的城市化,而‘城市’最先则一定是要以‘物’的方式进入乡村,进而控制人的感觉结构。”[4]
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关于农村的写作变成了各种书写者的竞技场,用来论证经济、文化和政治等理论、观念和思潮的正确与否,而农村和农民则是被从各方面被深度审视。其中具有标志性的文本是陈桂棣和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从这本书开始,一种具有浓厚的悲悯情怀的书写在有关农村的非虚构作品中一直贯穿,事实上,在梁鸿叙述完梁庄之后,其思绪并没有在关于农村的非虚构事件上追问下去,而是一个更有文化情怀的方式展开了对农村的命运的思索,也一直困惑于乡村是否是一定要按照全球化的模式来定义,以“陌生人社会”和“个体化”的社会替代“熟人式的”、“家园式”的乡土文化。以至于在乡土终结之后,我们应该寻找一个新的适合中国农村的发展模式。而在张柠的笔下,农村与其说是一个地理或者政治的存在,不如说是一个文化审美的存在,在《土地的黄昏》中,“农村和农民是一种与自然天道相吻合的一种生活方式,而带来这种天人合一的秩序失衡的力量是城镇和市民”[5]。是一种利用智性所营造出来的一个虚拟空间,而这一空间如此真实,以至于自然离开农村和农民的距离越来越远,与土地相关的土地经验、乡村经验、农民经验正在迅速消失,出现了土地的黄昏,并且认为这是即便不是悲剧性的,也是无奈的选择。
在这一叙述过程中,一个依赖于对于农村和农民的污名化过程就呈现为两个相悖离的离心力。一个方向上是对农村和农民的污名化前提,即在写作者和农村及农民之间的悖离,其中纠结着对农村和农民的内在的愤怒和怜悯。这种思路是如此的久远和深入人心,以至于当鲁迅在揭示出来所谓的“阿Q精神”的时候,虽然用的是国民性的标签,但毋宁说是关于农民的一个标签,是一个关于农村文化的一个标签。在最初离开农村的逻辑之下开始在城市生活,当站在现代城市的经济和文化精英的位置上重新审视自己曾经生活过的农村的时候,一种对于农村和农民的语言暴力在不经意之间自我设定了正当性。在另一个方向上,关于农村和农民的书写又潜藏着对于农村和农民的文化眷恋。以一种稍显悲壮的方式来显示农村和农民在文化和道德上的正当性,并将农村看作解救城市病的一个药方。作为一个城镇化的目标。但这种文化和精神层面的追求,如解决农民和农村在生活中的行动逻辑,则是脆弱的,是一些所谓文化追求的一个道具而已。因此,关于农村的非虚构就内在的存在温情和暴力之间的两难。或者说,从精英视角开始的非虚构写作,需要暴力来获得非虚构写作的权力和支配力量,并由温情来获得道德上的正当性。
四、结论与反思
关于农村和农民的非虚构写作存在着诸多两难问题,其根源在于农村和农民在非虚构写作行为中没有主体性,而是交由写作者按照文学内部的突围和道德上的拯救为动力进行叙述,农村和农民的自主逻辑和经验逻辑在非虚构写作中则付之阙如,只能通过精英的视角来呈现农村和农民的生命史和生活史,但两难问题使得这一写作行为叙述主体的精英和作为他者的农村与农民之间存在偏差,无法从农村和农民的生活和生命内部发出声音,只能通过间接的叙述予以表现,但是否是农村和农民的本来面目,存在诸多疑问,因此带来的关于农村和农民的表现也无从准确考证。
但造成这些两难的原因并不单一的在于非虚构的缺陷,从其根源来说,一个以排斥农民为基础的社会结构,才是导致出现将农村和农民置于他者地位被审视和被表现的位置的根本原因。要想让非虚构中的叙述者和被叙述者具有更加一致的视角,尤其是让叙述者和被叙述者具有内在生命史的一致性,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基础就必须建立起来。当叙述者和被叙述者之间具有内在一致性的时候,农村和农民才会更少的被排斥,更弱的处在他者的位置,农村和农民的主体性才能够更好的呈现出来,一个具有竞争性和平等性的非虚构写作才能展现自己的真实价值。
[1]孟繁华.百年中国的主流文学——乡土文学/农村题材/新乡土文学的历史演变[J].天津社会科学,2009(2).
[2]吴宁.传教士与人类学家[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2(5).
[3]梁鸿.中国在梁庄[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4]戴哲.性或性的叙述:从农民到女农民工[J].海南大学学报,2013(4).
[5]张柠.土地的黄昏[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