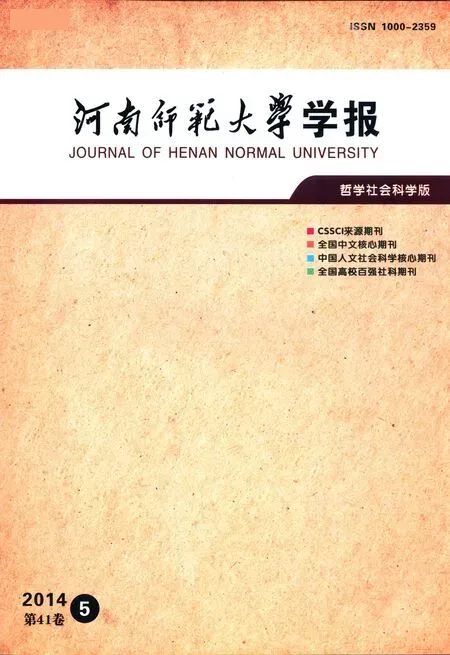论先秦美学中的乐与舞
姬 宁
(郑州师范学院 音乐与舞蹈学院,河南 郑州450044)
我国自古就有“诗、乐、舞三位一体”之说,《毛诗·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1]可见,诗、乐、舞的最终目的都是为表达情感的需要,并且三者可以互相补充,才能使内心的情感得以充分表达。先秦时期的乐舞思想不独立,或者依附于诗歌理论,或者作为诸子学说的补充,等等,其中儒家“尽善尽美”论、道家“天人合一”的天乐论、墨家“非乐”论最具代表。
一、儒家“尽善尽美”论
儒家思想是先秦贵族阶层利益的代表,其核心思想认为现在的社会礼崩乐坏,需要恢复周礼,而艺术被认为是其主要的方式和手段。由此,儒家思想肯定审美与艺术的作用,譬如,孔子认为艺术对现实生活有着积极作用,他认为人要成为“仁人”就需要修身,即修养自身的道德品格,换言之,成为“仁人”的关键与人自身的愿望、自我修养有着紧密关系,“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2]123“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2]74。而艺术由于同人的情感的表达有关,也因此对人的精神施以重要的影响,并进而对修养人性起着重要的作用,正如有的学者所讲:“审美与艺术对于人的精神的影响特别深刻有力,所以审美和艺术在人们为达到‘仁’的精神境界而进行的主观修养中就能起到一种特殊的作用。”[3]
“仁人”的外在表现是尊礼,孔子认为舞有示礼之能。其乐舞思想也是如此。《论语·八佾》曰:“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2]23八个人为一行,这一行就是一佾,八佾就是八行,八八六十四人,这是只有古代天子才可享用的乐舞规模,而季氏却享用了八佾的乐舞规模,这是非常不合礼数的。如果季氏连这种不尊礼的行为都做出来了,那么他还有什么事不能做。孔子由此认为季氏不尊礼,是不可能成为“仁人”的。乐舞还有通政之能,由乐舞能看出当时的政治状况。《礼记》曰:“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社会太平时的乐舞是安详、欢乐的,政治也一定是和谐的;社会混乱时的音乐是怨恨、恼怒的,政治也一定是混乱的;国家灭亡时的乐舞是哀伤并怀有忧思之情的,其国家的百姓也一定是生活困苦的。
儒家的乐舞思想究其根本是其礼乐思想的体现。孔子对“八佾舞于庭”表示的不满,也正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为此,他提出了乐舞的“合礼”观:“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晏乐,损矣。”[2]176合乎礼的乐舞才是真正可以实行的对人们有益的乐舞,但是什么样的乐舞才能达到这一标准呢?《论语》曰:“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侫人。郑声淫,侫人殆。’”[2]164颜渊向孔子问治理国家的方法时,孔子并没有对这一问题做出正面回答,而是从礼的角度阐释了自己的观点,并以《韶》乐为例,提出了“尽善尽美”的乐舞观。《韶》乐是舜时的乐舞曲,因为舜的天子之位是禅让得来的,所以孔子说舜时的乐舞声音形式是美的,内容是善的。《武》乐是周武王时的乐舞曲,声音形式是美的,但是因为周武王是伐纣得来的帝位,其内容没有做到善。由此可知,孔子所讲的“尽善尽美”既要求形式是美的,也要求内容是善的,只有达到这两方面的统一,才算得上是合乎礼的乐舞。
要实现尽善尽美的乐舞思想,需要做到“文质得宜”。《论语·雍也》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2]61这是孔子对君子人格的要求,但是与尽善尽美的乐舞思想相通,“文”与“质”相宜,也就是“美”与“善”的统一。《论语》曰:“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2]109孔子提出先学习礼乐而后再做官的人,是家中未曾有过爵禄的平民;先做了官然后再学习礼乐的人,是家中有爵位的子弟。如果要选用人才,孔子主张选用先学习礼乐的人。因为先学习了礼乐的人就是修养了内在品质的人,可以做到“文质彬彬”,达到美善统一。孔子选用“从先进”也就是主张“礼乐”的“文质得宜”。
总之,儒家的乐舞思想以“尽善尽美”为核心标准,强调乐舞就应该是合乎礼的,之后,孟子、荀子等人对乐舞思想的阐释,也大体是在这一基础上进行的。
二、道家“天人合一”论
道家思想中也有关于乐舞的论述,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天乐观是其主要代表。所谓天乐观首先是要求音乐遵循人情,符合自然发展规律,即顺应天道,“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礼义,建之以大清”[4]166。这样演奏出来的乐声曲调就如四季更迭,能达到“其卒无尾,其始无首;一死一生,一偾一起;所常无穷,而一不可待”[4]166的效果。其次是要求阴阳交合。阴阳调和,乐声“能短能长,能柔能刚;变化齐一,不主故常;在谷满谷,在阬满阬;涂郤守神,以物为量。其声挥绰,其名高明”[4]166。从而达到“形充空虚,乃至委蛇”的境界。最后是要求演奏者在演奏的过程中达到“心斋”、“坐忘”的境界,演奏者排除自己内心的利害观念,涤除一切私心杂念,与乐声合而为一,一起进入乐曲自然的生命进程中,遵循其自然的韵律,“奏之以无怠之声,调之以自然之命”[4]167。演奏出其应该有的自然之声,“或谓之死,或谓之生,或谓之实,或谓之荣;行流散徙,不主常声”[4]167。
由于这种天乐之声,是生命本然的自然抒写,所以当观众欣赏之后,会产生“听之不闻其声,视之不见其形,充满天地,苞裹六极”[4]167的效果。《庄子》曰:“乐也者,始于惧,惧故祟;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于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载而与之惧也。”[4]167欣赏这样的乐章,从开始的惶惶不安,到接下来的心境松缓,最后以迷惑不解结束全篇。欣赏者由于迷惑不解而显得愚钝,但是庄子认为这无知无识的浑厚心态,是最接近大道的一种状态,而一旦接近了大道就可以借此与大道融合相通了。
在庄子看来,天乐是最终感悟大道的途径方式,然而如何创造天乐?庄子认为需要有达到“天人合一”境界的技法。《庄子·养生主》曰:“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4]35庖丁解牛之所以游刃有余,是因为庖丁“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4]35,即他依照事物的发展规律,而不仅仅是一般的技法、技艺,所以才能在解牛时达到自由的“道”的境界,艺术创作也是同理,“艺术家的艺术创作,也是一种劳动和创造。艺术家也必须达到自由的境界,才能创造出艺术的美”[3]122。李泽厚在谈“道”与“技”的关系时曾说:“‘道’并不想有意地做成什么,也没有为之而劳力苦心,但它却自然而然地、完全合规律地生出了天地万物。‘道’在它的运行和活动中表现出它是合规律的,同时又是合目的的,所以才是自由的。作为艺术创造活动来看的‘技’恰好也具有这样显著的特点。”[5]在庄子的语境中,“道”与艺术的关系也是这样。那么,“道”与乐舞的关系是否也遵循着同一个原则?庄子认为乐舞属于艺术的范畴,必须通过一定的技法才能实现。乐舞有自身的规律,乐舞表演者在演奏时应该遵循其自身的乐舞规律,才能通过纯熟达到自由的境界,而此时对表演者来说,他的注意力应该在追寻乐舞的规律上,丢掉自己所有的生理欲望和私念,于是在无利害冲突的追求中,表演者实现了“天人合一”的至境。
总之,道家的乐舞思想以“天人合一”为最高的审美境界,“应之以人事,顺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应之以自然”[4]166,这是对乐舞的要求,也是对表演者的要求,是二者的辩证统一。
三、墨家“非乐”论
如果说儒家思想是先秦贵族阶层利益的代表,那么,墨家思想则是以底层民众的利益为出发点的。墨家思想中也有关于乐舞的阐述,墨子认为乐舞不会对社会生活起到积极作用,如果统治者们喜好乐舞表演,那么他们很可能会为此劳民伤财,严重影响底层人民的社会生活,所以,他指出乐舞是“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6]251,进而提出“为乐,非也”的乐舞观。
墨子曾作《非乐》篇,专门阐述他的主张和观点。首先,他认为乐舞表演需要制造乐器,这些乐器的制造需要花费许多钱财,而它们最终都被摊派到了底层的民众身上,“今王公大人,虽无造为乐器,以为事乎国家,非直掊潦水,折壤坦而为之也,将必厚措敛乎万民,以为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6]251-252。关键是乐舞表演对于统治者管理国家起不到任何的作用,“然即当为之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而扬干戚,天下之乱也,将安可得而治与?即我未必然也”[6]252。所以,墨子不提倡乐舞,这是一层含义。其次,他认为乐舞表演需要乐舞表演者,这同样需要消耗大量钱财。统治者招募大批乐舞表演者,一方面要花费钱财来养食他们,另一方面,这些人一旦成了乐舞的表演者,就脱离农业耕作,这对国家的劳动力生产有着重要的影响。所以,墨子不提倡乐舞,这是第二层含义。第三,他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出发,认为乐舞也不值得提倡。他指出,王公大臣们独自欣赏乐舞自然无趣,于是就会找寻同观者,不是找君子,就是找普通民众,这样找君子一起观赏乐舞将会荒废君子治理政事的时间,与普通民众一起观赏乐舞也将浪费民众耕种劳作的时间,并且也会荒废自己管理朝政事物的时间。然后,墨子以齐康公不许乐舞表演者穿粗衣、吃糙食为例,指出表演者不仅自己不能劳作,还要依靠别人养食,这种行为就是在掠夺底层民众的衣食和财物,所以,墨子不提倡乐舞,这是第三层含义。最后,墨子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份内之事,王公大臣、君子、农夫和妇人皆是如此,但是乐舞表演使人们沉迷其中,最终会导致国家的动荡,由此,墨子不提倡乐舞,认为“乐者,非也!”
显然,墨子论述乐舞与道家不同,他并没有就乐舞自身展开论述,而是从他对国家、民众的影响效果来看的,在这一点上,他与儒家相同,但是在方向上却基本相反。因此,从民众的立场出发,他看到的基本上都是乐舞对国家和民众的危害之处,如王公大臣们为了乐舞表演的欢愉,而耽误朝政,搜刮民众财物等等。但是墨子也并不完全一味地否定乐舞,他认为欣赏乐舞是有条件的,人们在衣食无忧之后,才会关注自己的精神生活,“食必求饱,然后求美;衣必求暖,然后求丽;居必求安,然后求乐”,由《节用》《节丧》等篇目中的节用、节丧思想可以推断出,墨子并不是要完全否定乐舞艺术,而是反对铺张浪费的乐舞表演,禁止劳民伤财的乐舞。
总之,墨家强调“非乐”,是其民本思想在乐舞论述中的体现,但是从总体来看,他将乐舞的功能定位在娱乐,能缓解劳动的疲劳,“昔诸侯倦于听治,息于钟鼓之乐;士大夫倦于听治,息于竽瑟之乐;农夫春耕、夏耘、秋敛、冬藏,息于聆缶之乐”[6]38-39。但是反对劳民伤财的乐舞表演。
综上所述,先秦时期的乐舞理论并不独立,它依托在诸子的思想当中,而关于乐舞理论阐释比较详细的有儒家、道家和墨家等,它们的论述各有侧重,并不尽同,代表了当时乐舞理论的最高水平。
[1]郑玄,孔颖达.毛诗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4.
[2]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4.
[3]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43-44.
[4]曹础基.庄子浅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7.
[5]李泽厚,刘钢纪.中国美学史:第1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276.
[6]孙诒让.墨子闲诂[M].北京:中华书局,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