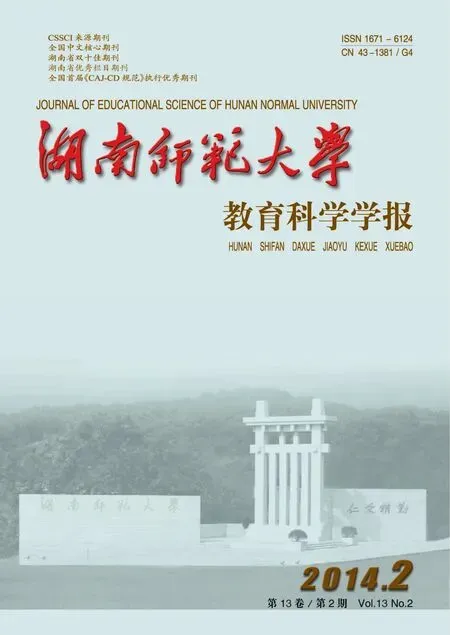重塑对教育的信仰:古德莱德的儿童教育观
罗 辉
(湖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古德莱德是美国当代颇具影响的教育理论家和改革家,他主张对美国教育进行全面系统的改革。从纵向看,改革应涵盖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各个层次;从横向看,改革应涉及教育活动的各个方面,如教师培训、儿童早期教育、学校风气、学校文化、不分级学校、课程改革及学校革新等。古德莱德继承了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小学推行教育研究和改革实验,将自己的教育理想付诸实践。他强调儿童是教育的中心,主张培养身心健康的儿童。在尊重儿童个体差异的前提下,全面发展儿童的个性,从儿童的健康、尊严、审美、情感和社会适应等方面出发,最大可能地发展儿童的潜能,使其成为美国民主社会的一员。美国人对学校教育的不满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是否有能力改革学校教育缺乏信心。古德莱德指出:“如果我们没有信心,教育就会失败。”[1]因此,他坚定自己的信念,把儿童作为教育革新的出发点,积极组织和参与美国教育实践,不断探索行之有效的教育思想,以促进教育革新。古德莱德的儿童教育观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享有公平受教育权
美国在一战前就普及了小学义务教育,二战后普及了中等义务教育。义务教育表面上体现了教育公平,但实质上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公平。“我所设想的学校是大家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场所,是维持人类和自然的生活环境,……为每个人提供追求个人兴趣和特殊才能的机会。”[2]古德莱德认为,儿童享有公平受教育权应体现在从入学到学校教育的组织和实施上,要保证儿童享受公平获得知识和技能的权利。
早在种族隔离的年代,古德莱德就强调种族平等。他指出:“我主张种族平等,并认为世界上只有一种人,我们都属于它。”[2]虽然儿童出身背景不同,但他们应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当越来越多的移民进入美国后,美国少数族裔儿童的数量也慢慢庞大起来。古德莱德意识到少数族裔儿童在教育中的劣势地位,开始关注他们的入学问题。他注意到土著居民与黑人在美国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认为长期以来学校都排斥这两类群体。同时,他发现不同学校在教育资源分配等方面也存在着不平等,要求州政府肩负起对地方学校所负的责任,确保郊区与城市学校之间享有平等的资源分配。
随着1964年美国《民权法案》的颁布,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开始取消。然而该法案出台后的几十年间,美国仍然存在很多种族歧视。古德莱德认为,家境贫寒及少数族裔儿童虽然获得了进入学校的机会,但由于自身所处的种族环境和家庭条件不同而导致了他们虽能进入学校,获得公平的受教育权,却没有平等地获取知识与技能。这毫无疑问制约了儿童的发展,产生了新的不公平教育,反过来也影响了美国学校教育的质量。他认为分级制教学对每周的授课时间、教学进度及其他决策的规定具有随意性,通常会导致获取知识的不公平。在组织实施教学的过程中,古德莱德强调要给学生提供多种多样的教科书、读物、补充材料等学习资料,满足多种阅读能力的需要,并引导他们获取学习知识的最佳途径,从而减少和消除儿童在知识获取上的不平等。对于不同水平的儿童,“通过选修课和取消按能力分组,随意编班或按学生程度不同来编班。这样,在获得知识方面就有了平等的机会”[3],也有利于保持和提高教学质量。
1992年古德莱德创立了“美国教育研究协会”,为推进民主社会中的教育改革议程,协会寻求让“国家所有的年轻人,不管其种族、宗教、性别、社会经济地位、性取向或者民族语言,都能拥有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以过上令人满意的、有责任感的生活”[4]。
二、尊重儿童个性差异
古德莱德认为,儿童不仅在体力、情感、社交方面有个别差异,其理解力也有所不同。他要求正视儿童个体的差异性,按照儿童自身的能力特点分班教学,选择适合个体差异的教材组织教学,并按照适合儿童能力发展的步伐指导他们进行学习。同时,对儿童的评价也不是千篇一律的分数,而要根据个体差异有所区别。他强调:“我们要正视学生个体及同年级学生群体之间都存在着个性差异这一惊人现实,必须看到为儿童学习进步作出安排的分级制与儿童的个性发展的现实是极不相称的。”[5]
1946年古德莱德在其博士论文《升级和留级对儿童个人与社会适应的一些影响》中,认为留级并不能给儿童第二次进步的机会,相反他们适应社会的能力低于升级生。在论文中他提出了不分级学校的教育理念,认为“学校是为了塑造成人的一种创造物”[2],而分级制度的学校教育基于等级体系来衡量和测评儿童的发展,没有考虑儿童的个性差异,分级体制下的教科书常常偏向每个年级的最低水平,教师也很少为了满足学生个体差异而共同决策。儿童被置于一个没有差别的学习模式中,无法进行有差别的学习。这样培养出来的儿童很难适应社会发展,也无法达到学校为民主社会培养人才的目的。
古德莱德认为:“每个个体都是独特的,应恰当地给予尊严和尊敬。个体之间的差异应当予以推崇。”[5]儿童在成长过程中,都会不断地发表自己对事物独特的见解和认识。不分级学校的分班没有固定模式,既可以按照多年龄段分班,也可以按照儿童的兴趣、某种学习能力(如阅读能力)分班。教师可以在一个较为自主的环境下教育学生,根据儿童的独特需要、兴趣、能力、学习效率、学习风格等,为儿童提供个别化教学。学校要为儿童提供丰富的教学材料,教师要引导儿童制定自己的学习目标,以帮助他们发展。“教育工作者要从教材中心转向儿童中心,现在是把关于儿童、教材、学习过程等方面的知识整合进教学过程的时候了。”[6]教师应鼓励、支持和帮助儿童培养探究、评价及解释等技能。通过教育革新实验及调查研究,古德莱德认为不分级教育能正视儿童个性差异,满足儿童个体的教育需求,能最大可能地发展儿童的潜力,并能促进他们的身心健康,培养积极的学习态度,从而造就可持续发展的儿童。
正因为儿童个体存在差异,对于儿童的发展评估不能只用死板的分数来决定。古德莱德认为,从幼儿园开始就可以为儿童建立一个记录他们成长和学习的档案,以使教师及家长能准确把握他们的发展情况及特点。“儿童的学习成绩是由其自身能力的发展及其远期目标的达成情况来决定的。”[5]儿童评价的报告应当考虑儿童的审美、身体、智力、情感以及社交能力这五个方面,而不要仓促地对儿童的这些能力作出结论。另外,对不同的儿童应有不同的期望,要依据对他或她的潜力评估来评价其成绩,对儿童的评价必须是持续和综合的。
三、培养儿童健全心智
古德莱德认为,儿童健全心智的培养有助于他们积极乐观地学习,让儿童更加勤奋,有利于培养他们的创造力。“不关注心理成长的节奏和性格,是教育呆板无用的一个主要来源。”[2]焦虑感是影响儿童健全心智养成和学习能力的主要因素,古德莱德认为儿童健全心智的培养首先要从消除儿童的焦虑感开始。
焦虑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儿童关心自己的成绩报告书,关心父母对自己成绩的反应,由此产生了焦虑。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让儿童参与到教师和家长的见面会中,让他们了解教师和家长所关心的事情,同时也让儿童表达自己的想法,加强儿童与教师及父母的沟通。古德莱德认为,不分级学校可以促进儿童身心健康以及培养积极的学习态度,分级制下的儿童后进生及留级生会产生焦虑情绪,并且会有一种耻辱感。他主张让后进生与能力强的学生一起学习,一起进步,这样他们的焦虑感就会慢慢消失。同龄班儿童一起学习会产生竞争或相互的侵犯,而在不分级体系下复合年龄的分班模式可以营造和谐的学习环境。在传统的分级制教育体系中,儿童成了工具化教育的牺牲品,过时、单调、枯燥乏味的教材以及死板的教学方式,使儿童失去了生命的本真与活力。在具体的个案研究中,古德莱德发现“学业失败、失望、学习兴趣下降、好斗争宠、过失等行为连环反复、频繁出现,足以令人担心”[5]。
儿童还会为自己的错误和失败而焦虑,古德莱德认为儿童的错误与失败应得到宽容。“对待儿童在学校里遇到的问题的最明智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把儿童的失败看做是需要帮助的信号,而不是看做要惩罚的信号。”[5]在学习过程中,教师要激发儿童的学习动机,尊重儿童的个性,恰当地运用正面的语言,让儿童心情愉快地学习。学校要鼓励儿童进行广泛的和创造性的探索,为儿童营造心理自由的氛围,让他们有心理的安全感。在分级制班级学习的儿童,常常会受到直接或间接的指责,从而使这些儿童产生困惑、失望、灰心丧气,甚至愤怒。
儿童健全心智的培养也受到教师个性健康与否的影响。古德莱德认为教师是促进儿童学习的因素,通过为儿童制定目标来鼓励他们迎接挑战,在失败面前也不要害怕,以此增强儿童的自信心。与在严格的年级制气氛下工作的教师相比,不分级学校的教师具有更轻松的心理状态,也能更好地引导学生走向知识的制高点。此外,评价儿童成绩的方式对于培养心智健全的儿童也非常重要。古德莱德强调对儿童成绩评价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让儿童树立自尊和发展自我能力。他要求为儿童营造心情舒畅的学校环境,因为在快乐情境下学习的儿童更具创造力,能更好地应对未来更严格的学习任务,更能应对未来复杂的社会环境。
四、为民主社会做准备
古德莱德把教育看做是一项道德事业,认为学校通过培养公民和促进个人发展而推动民主社会的进步。国家公民的培养关系到民主社会建设的好坏,而民主社会建设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古德莱德继承了杜威关于民主主义与教育的思想,认为“教育是民主社会不可剥夺的权利”[7]。社会所有成员一定要受到一种训练也即教育,使他能够承担民主社会和政府的管理责任。教育能够影响社会,在民主社会中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也需要教育来维持。古德莱德认为美国的民主社会已经饱受诟病,被一些特殊利益团体占据和操纵,公民的声音已经越来越被边缘化了。古德莱德创立“美国教育研究协会”的任务,就是要培养美国儿童参与民主社会政治的技能、思想、能力及知识。个体需要提升智力,以理性应对越来越复杂的民主社会,而学校教育则肩负着培养重建民主社会所需人才的重任。学校教育目的在于全面发展儿童的潜能,为民主社会培养有创造力的建设人才。他认为学校教育的危机并不是儿童考试成绩不佳,而是学校没有能够培养儿童让脆弱的民主政治保持健康发展的知识和技能。
古德莱德认为学校教育的目的既重视个人也强调人类,一个理性的人应该有责任心、有才能,他不以自我为中心,能自由地发展。他说:“教育不是实现某种目的的一种工具,教育是个体自身(self)的发展。”[8]发展不是要改变世界,个体无法改变世界,但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参与对世界发展产生影响。儿童要保持与社会的接触,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了解社会和世界发展的价值观,形成关于社会和世界发展的认识。他认为课程改革是引领儿童步入民主社会的一个重要途径,强调要从内容和知识结构上对课程教学进行改革。从小学任教伊始,古德莱德就尝试进行课程教学的改革,将不同的课程融入到教学中,激发儿童多种兴趣,引导儿童获取新思想和新理念,培养儿童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以适应复杂多变的民主社会,适应美国要面临的全球化挑战。
古德莱德认为学校教育给儿童带来的进步有学术发展、社交发展、公民发展、职业发展及性格发展,这些技能的发展都有利于儿童将来全面参与民主社会生活的对话。“学校是国家培养年轻一代适应政治民主社会的唯一机构。教学过程就是传递美国理想、培养公民民主政治观、价值观的过程。”[9]学校要为儿童将来步入民主社会,积极有效地参与民主社会生活做准备。但“教育的根本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国家的繁荣,而还应该使每一个个人的自我能力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开发”[10]。儿童在未来的民主社会中扮演着四种角色:工作者、公民、父母及个人。在教育过程中,要恢复对人性的教育,将自由、尊严、责任等思想融入儿童的心灵。学校要帮助儿童理解和欣赏来自不同社会、文化及种族背景的人。通过提升儿童承担责任的能力,培养儿童对民主社会的本质形成批判性的思维,以帮助儿童应对迅速变化的世界,进而培养出有自觉意识的社会公民。公民要参与到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去,民主社会的存在有赖于社会中的成员。培养儿童的创新能力,有助于帮助儿童实现自我,更好地服务于民主社会。
五、结束语
古德莱德认为过去六十多年以来,美国学校出现的教育问题基本上都是同样的,而解决问题的办法从根本上说也没有多大差别。这不免让人对教育改革产生失望和怀疑。但是教育工作者必须对教育改革充满信心,相信教育改革的力量。必须正视儿童在学校教育中的核心地位,儿童教育的方式、方法及措施是教育改革的重要环节。他认为培育儿童自由对民主国家的自由发展非常重要,缺少了儿童的参与,教育将不是教育。儿童的教育对于国家发展至关重要,它决定了未来民主社会的走向,并影响国家在全球竞争中的地位。古德莱德的儿童教育观,对当下我国教育改革有不少启示和借鉴之处。在我国教育改革和实践中,如何看待儿童的地位,给儿童何种教育,把儿童培养成什么样的人,儿童教育目的与教育实践是否一致?这都是我们每一个教育工作者要思考的问题。笔者相信古德莱德的儿童教育观,能让我们重塑对教育的信仰。信仰的落脚点在“仰”,它强调价值意义上的真实,反映一种虽不能至而向往之的极度尊崇的心态[11]。重塑对教育的信仰,能使我们找到开启和通达儿童心灵的钥匙。
[1]Antony Smith.A Review of John I.Goodlad’s What schools are for[M].Phi Delta Kappan International(USA),2006.
[2]古德莱德.学校罗曼诗:一种教育的人生[M].周治平,黄文琴,詹丽琼,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0.
[3]单中惠,杨汉麟.西方教育学名著提要[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
[4]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Inquiry.Agenda for Educaiotn in a Democracy[EB/OL].http://www.ieiseattle.org/index.htm,2014-01-16.
[5]古德莱德,安德森.不分级小学[M].谢海东,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
[6]赵祥麟.外国教育家评传(第4卷)[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7]Goldberg,Mark F.An Interview with John Goodlad—Leadership for Change[J].Phi Delta Kappan(USA),2000,(1):82-85.
[8]Carol Tell.Renewing the Profession of Teaching:A Conversation with John Goodlad[J].Educational Leadership.ASCD(USA),1999,(8):14-19.
[9]刘 静.20世纪美国教师教育思想的历史分析[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10]顾玉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信仰构建的三重维度[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60-63.
[11]杨建朝.育“人”:教育精神的时代诉求、物质与意义[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2,(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