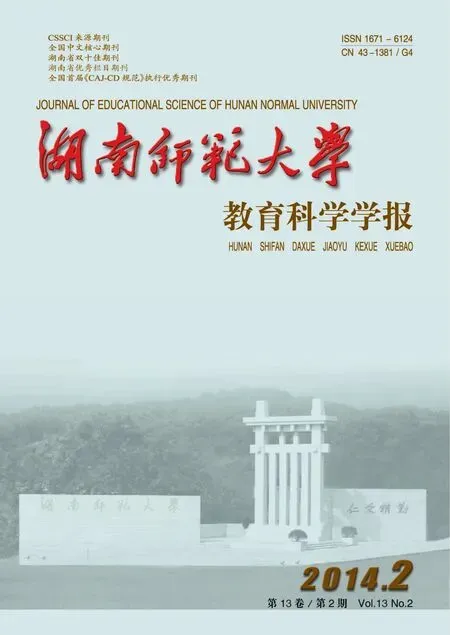经典教育与生命滋养
刘铁芳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荷马史诗》中,《伊利亚特》讲的是出征、出发,而《奥德赛》讲的则是回归,似乎预示着出发与回归,乃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伊利亚特》蕴涵的是人类生活的‘出征’模式,即那种为美而战斗而牺牲而捍卫尊严的永恒精神;而《奥德赛》则意味着‘回归’模式,即那种出征之后返回自身、返回家乡、返回情感本体的永恒眷念。”[1]人类的出发点无疑是自然,文明发展到今天,我们从自然素朴出发已经很远了,如果说回归是永恒的主题,那么,置身现代文明幽昧之中,不断地向着人类的出发之地回返,以求得健全生命底气的滋养,避免文明的过度濡化,应该是现代人不可或缺的基本功课。
从人类发展意义上而言,回归的基本路径就是回到古典,返回古代经典。守护古代经典文化实际上乃是滋养当下人生命情怀的最重要的精神资源。加强古典教育,就是要强化今人与初民之间的精神联系,它的根本意义在于让我们回溯人类最初的生命精神,从而获得现代人最基本的生命滋养。经典本身就代表着人类的优良经验,就是人类记忆的结晶。经典教育本身就意味着唤醒我们对人类优良经验的“记忆”,或者说把人类的“记忆”植于个体之中。柏拉图所言教育即回忆,无疑显明古典教育的核心旨趣。个体成长的过程乃是分享人类成长经验的过程,教育的起点包容在人类初始性经验之中。柏拉图在对话中,总是不断地讲述古典的神话,隐含的旨趣就是把教育的起点往前延伸,把个体精神生活之根置于古代经验之中。古典经验唤起个体对人类过去经验的感知,唤起个体的人类记忆。这种记忆不仅仅是个体性的,而是人类性的,重温古代经典的根本意义就是以回忆的唤醒来重温人类、民族的早期经验。
这种记忆弥足珍贵,绝非可有可无。正如柏拉图在《斐德罗》中所言,如果一个人正确地运用回忆,他就可以变得完善。在这个意义上,文艺复兴实际上就是一场运用回忆、复兴古希腊经验的运动。人文主义的根基或者说实质,就是古典教养。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重新考量神话、童话对于现代人、现代教育的意义,神话、童话并不是荒诞不经,神话与童话恰恰可能是原始初民生命精神的真实写照。经典教育则是要强化我们与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心灵之间的联系,一部经典往往就代表了一个时代,甚至远远地超越了时代,它们乃是人类心智的杰出代表。“任何一位古代高人所写的东西都远远高于或遥遥远于我们之所想”[2],经典之为经典,正在于其穿越时空所呈现出来的恒久的生命意义,与经典的接触,乃是促进个体心灵充分地类化。
“在人们重温柏拉图、莎士比亚的著作时,他们将比其他任何时候生活得更加充实,更加美满,因为阅读经典作品将使人置身于无限深蕴的本质存在,使人忘掉他们短暂纷杂的现实生活。永恒完整的人性不仅过去存在,而且永远存在,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能够伸展自己探寻的指尖触摸到它,这样做将不断完善我们那不完满的人性,它的种种缺憾常常使我们难以忍受和宽待。在那些经典著作中的客观的实在的美依然令人赏心悦目。我们必须在今日学生们的心田上的那块不大友好的田野上,小心翼翼地保护和培植那些伸向这些伟大思想的幼苗。尽管事过境迁、环境变化,我们的人性依然如旧,因为在今天我们仍然面临着同样的各种问题,如果它们有什么变化的话,那也只是在外表方面,人类仍然有着紧迫的需要去解决它们,哪怕我们的知悟和力量或许正在衰退。”[3]经典其实就是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在现实中很难实现却能在经典所敞开的精神世界之中获得完整人性的可能性。经典教育的根本意义,就在完整人性的感召与温润之中。重温经典,乃是我们面对当下人性的荒疏——虽不是唯一,但却是不可或缺——的基本路径。
“许多书——可能是一些最重要的——有着独立的地位,给我们带来洞穴外面的光芒,没有这些光我们会变得盲目。”[4]古典与经典教育,究其实质而言,就是要保持现代个体置身人类、民族历史之中永远的家园感。黑格尔曾说,古希腊对西方人而言总有一种家园之感。施特劳斯的经典教育也是倡导回到古希腊经典。“因为伟人们有助于今天对事物的洞察,所以他们必须被仔细地研究,对他们的取代也必须如此。理性只能理性地被放弃;未经这样严肃的思考,现代观念就会变成空洞而危险的废话。”[4]对于急切地谋求现代价值实现的我们而言,一种厚实的古典情怀乃是必不可少的,这不仅仅是裨补现代价值背后的内涵虚空,更重要的是续接民族的精神底气。
对于我们而言,学习西方经典,或者说跟着西方回到古希腊经典,在人类精神的高度去接近它们,无疑是不可或缺的部分;但仅有这点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切实地激活民族经典于当下,重新激活山海经、诗经、诸子百家、唐诗宋词、《红楼梦》,以至现代“五四”新文化精神代表的鲁迅作品等的精神联系。超越儒家经典,从前诸子百家时代的经典,到诸子百家,到礼教之外的杰出文学艺术经典的重温,乃是重新触摸民族内在精神结构、在现代化的背景中孕育新的民族精神的重要基础,或者说基本路径,是我们直面民族生存的根基,承续民族精神,孕育家园感的重要基础。
杰出的经典就是思想的迷宫,我们在迷宫中行走,获得心智的历练。经典往往不会自明地显现人生的答案,而是把个体引向自我人生的不断询问之中。阅读经典,极大限度地敞开自我,灵魂获得充分的撞击,让我们的内心世界变得丰富而具有韧性,从而使得我们的灵魂对日常生活中虚无之侵蚀的抵挡成为可能。也正因为如此,经典教育绝不是让我们成为经典的奴隶——真正的经典并不创造奴隶,而不过是唤起我们眼前的“神圣、珍贵,美妙无比,神奇透顶”[5]。正如维柯所言:“记忆有三个不同的作用,当记住事物时就是记忆,当改变或模仿时就是想象,当把诸事物的关系作出较妥帖的安排时就是发明或者创造。”[6]为经典所敞开的回忆既是“记忆”,也是“想象”,更是“创造”。经典并非记忆本身,而是唤醒记忆的通道。记忆本身并不是简单地重复,经典教育作为一种回忆,其实质乃是一种唤醒,唤醒我们的“记忆”,焕发我们的“想象”,唤起我们的“创造”,从而在人类心灵的意义上,提升个体生命的境界。
当然,经典阅读虽然重要,但阅读经典乃是一个过程,在阅读的初始阶段,最重要的是培养良好的阅读趣味,也就是对美好阅读的感受力,从小就启迪个体内心对经典的开放性,把经典阅读的可能性植入儿童的生命品质之中。我们需要反思一种急功近利的经典阅读,也就是那种试图从低龄儿童开始的成人化经典阅读形式。经典是需要缓慢地进入个体精神成长的历程之中,经典阅读如果不能启发儿童内心的阅读趣味,反会成为个体向经典开放的真正的可能性。少年读经,尽管可能给个别人的长远发展提供幼学的支持,但从整体精神发展的视角而言,由于少年对以《三字经》等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经典并不能有足够的认识,盲目地提倡少年读经,实际上达不到促进当下儿童精神发展的作用,却可能适得其反。少年读经本身,就是一种理性的倒置。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小心地选择适合个体不同发展阶段的经典,以促进个体精神的健全发展。
经典教育渗透在个体成长的教育历程之中,其中最重要的阶段是大学,大学必须越过现实的功利而怀抱一种古典情怀。大学教育的古典情怀意味着大学要悉心守护经典,亲近古代经典。世俗生活往往是急功近利的,而大学就应该站在人类文明的立场来观照时代与社会,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以古典情怀来守护我们生命的家园,而不是简单以现实需要为依据。在这个意义上,施特劳斯学派所倡导的细读经典,可谓开启了一种用古典资源滋养精神血气的重要的大学教育方式,这对于越来越心浮气躁的现代人之心智历练,无疑大有裨益。大学应该切实加强经典教育,增加经典阅读与解释的课程,大力扶持经典阐释方面的研究与教学。
正如沈从文对“希腊小庙”的悉心守护:“我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7]经典阅读的意义不在经典本身,而在以经典激活优良的人性,人的健全发展才是经典阅读的根本目的。这意味着我们既要重视经典阅读,但又不能把经典阅读反过来变成个体生命的负担,而是要变成生命积极成长的精神滋养。最好的东西也不能强加于人,我们不能动辄摆出非经典不可的态势,以经典压人①。经典教育也需因材施教,因人而异,而非以标准化的方式强加给每一个人。不仅如此,强调经典教育的重要性,决不意味着经典教育就是一切,经典教育本身不应该成为个体成长的圈隅,而是要成为个体积极面对时代和社会的精神滋养。换言之,我们需要倡导个体在经典阅读的过程中直面时代与社会,以全面孕育个体理性,人格的健全发展需要理性的操持与时代生活的历练。
经典阅读绝非固守经典,而是在回望中甄定人类生活的方向,滋养时代的精神底蕴,为当下个体生命的发展重新寻找到内在的起点,不断地回归人之为人的原点。倡导经典阅读,并不是为了寻求精神的蜗居,而恰恰是为了精神的独立,为了健全生命的孕育,为了现代文明围裹中的个体生命的质朴与丰盈。正如赫拉克利特所言,“上升与下降之路是同一条路”,看似回归、下降的路,难道不是向前、上升的路?
注 释:
①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在中小学里慎提国学经典教育,儿童接近中国古代经典,可以更多地以游戏的形式进行,一旦上升到“国学”的高度,就很可能导致对学生选择性地抑制,增加儿童在“国学”面前的无力感。
[1]刘再复.红楼梦悟[M].北京:三联书店,2006.
[2]刘小枫.〈斐德若〉义疏与解释学意识的克服[M]//刘小枫.赫尔墨斯的计谋——经典与解释(第7 卷)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3]布鲁姆.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M].缪 青,宋丽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4]布鲁姆.巨人与侏儒(增订版)[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
[5]柏拉图.柏拉图的〈会饮〉[M].刘小枫,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6]维 柯.新科学[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7]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M]//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11 卷).香港,广州:三联、花城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