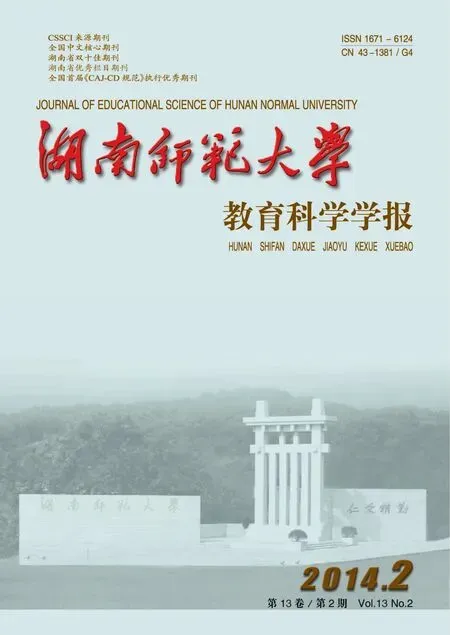经典教育三题
董云川,周 宏
(1.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讲师,博士)
一、经典教育之应当
工具,从刀耕火种的“刀”、结绳记事的“绳”,一直到4 核6 核乃至N 核(N)的计算机,无一不是人之器官功能的延伸。随着“装备”的不断升级,人改造自然、创造世界的活动和成果也不断升级。然而,人的器官外化延伸也不可避免地催生着人的分化与异化。渐渐地,现代人在工具的泛滥与失控中积重难返,只得不断饮鸩止渴,直至完全迷惑自我、迷失在人一手造就的纷扰与喧嚣中。
传统经典文本的诞生及其魅力恰恰位于人类“迷思”而未“迷失”之际,彼时人们沉浸在人与世界关系的迷思中不能自拔,虽然世界对于人来说是未知的,但那未知的世界尚以相对原初的样态存续着,并未遭受过人类无节制的鲁莽异动而面目全非,人的世界与自然世界之间还没有如今这样过多的阻隔和遮蔽,关于人与世界关系的反思和追问能够得以在朴素、简单的基础上开展;而人一旦迷失于自设的困局,反而无法更透彻地反观自身以及与世界的关系。
现代人并不曾停止和放弃对意义的反思和追问,但终不得自拔于虚无与迷惘的困扰,这些困扰源于表象相对于真相的片面一致或似是而非。人们在对“伪真相”和“现象真实”的追求中更加深陷于迷醉和无助。在这个意义上,来自古典世界的经典文本堪称为人类守候着暗夜里照亮回归精神家园之路的火种,为现代人放飞失重的灵魂点燃归途的发动机。
二、经典教育之误区
经典教育的价值为教育家所洞悉,这是教育之幸,也是学子与社会之幸;但经典教育的形式,一旦被教育事功地利用起来,也就难免会滑向它的反面。
教育是育人的事业,“成人”是教育的宗旨。但“成人”如若沦为事功的靶子,那么这种急于求“成”的教育仍然无法脱离“制器”的命运,只不过这一次“制器”的模子是按“成人”来打造的,是更隐秘的“制器”而已。须知,成“功”不可教,成“人”尤未可。
教育欲“成人”,需要启发教育对象“为人的自觉”,这一自觉至少包括对“人”的追问与“作为人活着”的强烈意愿。树立“为人”的意识、了解“为人”的意义、明确“为人”之道、持守“为人”之志……在以上“身为人”、“作为人”、“如同人”的各个环节中,个体对自身为人的价值觉悟尤其关键,对人及人生的意义追问十分可贵,觉悟和追问一方面离不开社会成员身体力行的反思活动,另一方面经典阅读对主体而言无疑是需要的和必要的。经典文本跳过意识形态的“主义”和社会发展的“阶段”,贯穿于全部人类社会历史、覆盖所有具体社会形态的“共同”中,去拯救、发掘、传递和支撑着人类文明生生不息一路走来的精神力量。
教育能否“成人”,依赖于在社会成员那里是否发生了“为人”的自觉及其觉悟程度,“自觉”和“觉悟”都是无法教的,而经典恰恰蕴含着这种无形的力量,同时具备发人深省的客观作用。在经典阅读中,读者作为主体存在,经典成为有而不在的干预要素,使得读者在自主的选择和自愿的认同中接受文本所承载的人类思想的结晶和文化的精髓。在形式上,这是一个读者自我教育的过程,究其实质,同时也是一场来自杰出心灵的教化演讲。
这样一来,采取经典教育形式就无法不面对一个现实:“觉悟”这个东西跟“潇洒”一样,越故作越远离。如若被形式绑架,那么经典教育的效果至少是大打折扣的。既然经典教育的效果需要在潜移默化中达成,大张旗鼓地推行经典教育并不妥当,那么经典教育中教育者与教育对象在恰当氛围中的融和就显得极为重要。反过来,那个恰当的氛围更为重要:教育活动双方关系的氛围、教育组织的氛围,乃至社会的氛围……比如,在一所学校中创设恰当的气场,校长、教师、学生具有自觉追求觉悟的价值共识,那么就容易形成经典教育共同体,学生对追随经典文本中的“大道”乐此不疲;反之,经典文本非常容易沦为灌输“大道理”的工具和幌子,学生由于排斥这种“被伪装”了的说教,反而与经典所揭示的真理和正义的内容擦肩而过或从此心生罅隙。
三、经典教育之难题
经典发自伟大心灵,更源于杰出先进们所处的伟大时代和适宜的社会发展状态——而伟大的时代和适宜的社会无疑体现着人类历史中孕育宏才大略的可能;所以,经典标志着人类思想可能的高度和已达到的水平。经典凝结着人类思想的最高智慧,经典文本和经典阅读可以作为教育的元素为教育所用,经典教育体现着教育价值自觉和教育行动智慧;同时,经典经由伟大心灵的折射而展现人类思想的高度和大成,其价值和意义无疑又高于和广于任何具体教育活动本身。经典教育的意义不仅止于选择性地在社会成员思想中建立特定观念和认知,经典阅读对于个体的意义也绝不仅止于成全自我,至少要超脱个体的肉身及其感受、心灵及其状况而达至人性的层面和高度。
鉴于以上原因,经典教育的难题至少有三:
难题一:方式和形式。因为对自我的意识、对自我的认知以及自我一致性的保持,可以在不同境界、不同水准下实现,而经典教育期许的“自在”是以“自觉”为基础的,“自觉”又显然以觉悟为指向。为实现使命,经典教育无法绕过的一个重要课题是,如何以恰当的方式引导教育对象对生命和生活的自觉,激发他们追问和反思的热情,促成自觉觉悟的主动。不恰当的方式则很容易使“引导”、“激发”和“促成”转向自身的对立面。是采取自上而下的教育行政决策作为推动,还是在恰当氛围下教育组织各主体平等自主地参与和开展?是以考试考核的方式加以检测和督促,还是在兴趣和自主意愿的原则下将阅读经典内化为主体的学习和生活方式选择?
难题二:内容的甄别。经典教育一旦以正式的形式出现在教育中,其操作必然涉及经典书目厘定的问题。即使对“何为经典”、“古、今、中、外是否都应有作品在经典书目之内占有一席之地”的问题存而不论,仅就中国古代经典而言,梁启超先生和胡适之先生两位国学大儒之间就发生过《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之于《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实在的最低限度书目》的笔墨官司。对于广大学者和普通读者而言,经典评定和遴选更是莫衷一是的难题。
难题三:师资的遴选。经典教育虽与单纯“说教”、“讲授”不可同日而语,但执行中始终离不开具有一定视野和高度的师者加以点拨。俗话说“经师易得,人师难求”,经典教育不是读经教学,它要求教师既有“经师”的技艺,又要有“人师”的资格,所以经典教育教师的遴选又成为实施经典教育的又一难题。而当下“经师”的介入,完全有可能诱发不同的价值取向,将“本经”念成“歪经”,把“庄子新解”变成“庄子曲解”,一番“戏说”之后,真经难免“悲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