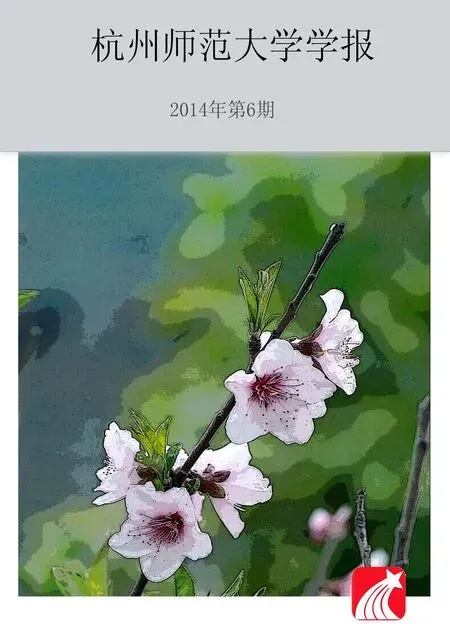“形式”转换:从形式主义到结构主义
杨 磊
(昆明理工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云南 昆明 650050)
在俄国形式主义和布拉格学派的关系问题上,学术界普遍承认两个学派间有密切的联系。仔细加以辨析,这些观点仍然存在差异,并可分为两类。一种观点认为布拉格学派是俄国形式主义的延伸,布拉格学派只是在重述俄国形式主义的主要理念和学术见解,是从俄国形式主义到法国结构主义的中介与过渡;另一种观点认为在继承了俄国形式主义的同时,布拉格学派已经超越了前者,建立了成熟的结构主义理论体系。就目前来看,前一种观点获得了大部分人的认可。然而在这种观点的背后,隐藏的却是对两次转折的忽视,一次是20世纪20年代俄国形式主义的内部转折,另一次是30年代发生在布拉格学派内部的转折。这两次转折分别促使俄国形式主义由早期过渡到后期,布拉格学派则由形式主义转向结构主义。就此而言,重新甄别、厘清俄国形式主义和布拉格学派的关系史,对我们重新认识布拉格学派思想体系及其对20世纪以来的文学、美学的影响,既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
一、作为手法的艺术
众所周知,《作为手法的艺术》是俄国形式主义的奠基性文献。它的最大贡献就在于揭示了文学实践中广为存在的“陌生化”现象。从反对把艺术等同于形象思维这样的经典理论着手,什克洛夫斯基认为,诗歌中存在形象,但形象只是诗歌创作的一种方法,和其他施加于诗歌语言上的手法完全相同,目的是为了增加对事物的感受。[1](P.7)形象思维的手法和感受在文学和艺术实践中尽管具有重要意义,但它只有通过陌生化才能得以实现。
早在为俄国未来主义辩护的檄文《词语的复活》中,什克洛夫斯基就指出,“人们在平时说话中,并没有把话完全说出来,听话人也没有听到完全的话,因为已经成了习惯”。对文学艺术而言,这种状态是致命的。未来主义诗人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试图使用生动而不是僵死的形式和词语,由此创造出一些属于未来主义的“随意的、派生的”词。什克洛夫斯基认为,未来主义诗人笔下的“新语言是不好理解的、难懂的”,因此,“词像古老的钻石一般又恢复了过去的光辉”。[2]在他的辩护中,隐含着此后出现在《作为手法的艺术》中的几个关键观念。首先,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是认知而不是感受事物,文学艺术则与之相反,是感受而不是认知事物;其次,艺术的关键在于其形式,人们通过艺术感受到的可能不只是形式;最后,达成如上效果的是艺术家的技巧,正如未来主义诗人“使用”生动的词,甚至“创造”出新词一样。
为此,什克洛夫斯基以“陌生化”来深化这些思路。在《作为手法的艺术》里,他认为日常生活是一种自动化状态,吞没了一切。这种状态同样会发生在艺术作品之上。任何一部艺术作品,只要被多次感受过,就会“从诗走向普通文字,从具体走向一般”,从感受转向认知。艺术实践的目的与此相反,是从认知走向感受。因此,他把艺术的目的视为把人从自动化状态中拯救出来,恢复其感受。在这个时候,就可见出陌生化手法的重要意义。陌生化手法把“形式艰深化,从而增加感受的难度和时间”,“在艺术中感受过程本身就是目的,应该使之延长。艺术是对事物的制作进行体验的一种方式”。[1](P.10)基于此,诗歌不像他反对的波捷勃尼亚所理解的那样(是节省创造力的语言方式),而是一种“困难的、艰深化的、障碍重重的语言”。[1](P.21)进而言之,艺术作品就是对艺术手法的暴露,是手法的总和。
雅各布逊几乎在同一时间提出了另一个重要术语——文学性。文学性就是那些使文学成为文学的东西;文学研究者的目的就是发掘并阐释文学性。借助这个术语,雅各布逊表达了对传统文学研究的不满,他把传统文学研究者比喻为在街上捉小偷的蹩脚的警察,他抓住了除小偷之外几乎所有的对象。在文学研究中,这些对象就是作家的传记、社会、文化、历史等等,尽管它们和文学有关,但都不是文学。韦勒克和沃伦把这些研究对象称为“外部研究”。显然,“文学性”的提出意味着文学研究向内转,在这个转向过程中,消减了所有外部因素。
综合两者来看,这是一种典型的形式理论,通过陌生化对文学性的探讨,最后被归结为对文学形式的探讨。细察陌生化,可以发现该理论实际上继承了自古希腊以来的固有的两种形式观念。形式在古希腊具有三重含义,分别为对事物的各部分的安排、对事物的外在表象(或美)和事物的轮廓。[3](PP.253-265)但对事物的外在表象和事物的轮廓之间没有根本的区别。具体到“陌生化”,对事物的外在表象体现为使欣赏者把欣赏对象感受为“陌生”。外在表象也正是传统研究的关注点,它把文学和社会文化联系在一起。但什克洛夫斯基说,“在文学理论中我从事的是其内部规律的研究”,他以著名的棉纺厂的例子说明,他的研究关心的是“棉纱的标号及其纺织方法”,而不是棉布市场和托拉斯的政策。[1](P.3)由此他转向对文学的内部组织的研究。
“内部组织”正是什氏所说的,“各种诗派的全部工作归根到底都是积累和发现运用与加工词语材料的新手法”。[1](P.6)如果说外部表象把文学表象为陌生,那陌生的基础完全在于如何组织和架构内部材料。在《情节编构手法与一般风格手法的联系》里,他很好地阐释了这一点,详细讨论了民俗、文学中广泛存在的诸种手法,认为这些手法的目的正是为了使作品被表象为陌生而服务。在更广的范围内,俄国形式主义把文学实践的材料视为“本事”,陌生化手法施加于本事之上后,所产生的艺术作品乃是“情节”。对于他们来说,重要的是本事如何变为情节,情节中隐藏着什么手法。
总的来看,对陌生化的阐释是富有创见且令人信服的,对陌生化(和文学性)的探讨以及由此引起的文学研究中的语言转向在20世纪文学研究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如佛克马所说,“欧洲各种新流派的文学理论中,几乎每一流派都从这一‘形式主义’传统中得到启示”。[4](P.13)然而在这巨大的影响背后,隐藏着种种缺陷隐患。
我们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是,艺术手法应以什么样的理由被整合到一起?前期俄国形式主义学者并没有对此做出充分阐释,而是简单地认为,艺术作品就是手法的总和。这显然只是一种机械的整体观念。其次,只关注内部规律意味着把艺术作品视为一个封闭的整体,导致了三个方面的恶果:一是忽视了艺术作品的历时变化过程;二是切断了作品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三是把艺术作品简化为恢复读者的感受。正是这些缺陷,促使了俄国形式主义内部的转折,即由前期转向晚期。
二、俄国形式主义的内部转向
既然存在如此严重的缺陷,早期俄国形式主义者为何仍然如此执著地从事他们的封闭研究?实际上,什克洛夫斯基早已意识到必须在“所有艺术作品”这个前提下从事具体的艺术研究。[1](P.31)从大的范围来看,这是在现代性条件下,各个学科分化在文学研究中的具体体现。在较小的范围内看,这实际上是俄国形式主义采取的研究策略,诚如厄利希所言,早期形式主义已经意识到文学不是在真空中产生的,他们没有否认文学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去社会化”只是一种权宜之计,非美学原则;只是评论家的兴趣判断,而非文学艺术的本质。[5](P.118)什克洛夫斯基也认为,语言受到其他语言或社会需求的影响。在文学与生活,美学与非美学之间,没有不可衔接的鸿沟,没有固定的边界。[5](P.120)在这种策略遭到严厉批评、苏维埃政权开始介入到文学研究中之后,相关反思也在形式主义内部出现了。
日尔蒙斯基认为,不能将艺术作品简化至语言的层面,不能把手法作为文学研究唯一关注的内容。他指出,“艺术作为手法”是可行的,但它包含了“文学作品作为一个审美体系”。[5](PP.96-97)托马舍夫斯基认为,手法在艺术创作中具有重要地位,艺术家和“最热心”的读者首先关心的就是手法,对手法的强烈兴趣正是推动艺术发展的根本动力。他同时指出,把文学作品整合为一个整体的有效路径即“主题”,“在艺术表达中,具体的句子按意义进行组合,形成由思想共性或主题共性联合起来的结构。主题是具体要素的意义统一”。[6](P.107)
托马舍夫斯基进一步讨论了主题选择需要考虑的诸多因素。他详细论述了两种不同的主题,一种为“迫切性”主题,一种为具有永恒意义的主题。后者正是在人类文化中甚至“未经根本变化”的永恒主题,即爱和死的问题。迫切性的主题有应景和暂时的特性,这些主题的“容量”较小,存在时间较短,其意义也就较小。与之相反,意义较大的主题容量、存活的时间远胜于迫切性主题。当然,聪明的艺术家往往擅长以迫切性主题为外在的掩护,来描写具有永恒意义的主题。[6](PP.108-109)在托马舍夫斯基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他揭示了主题的选择不是自然的行为。在艺术家的创作实践中,主题必然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出现。这个社会历史条件包含了作为自律系统的艺术史自身,也包含了外在于艺术史的社会历史文化。与此同时,艺术家的创作还需考虑到读者的兴趣。如果把创作看作一个交流行为,那艺术家实际上是和一个可能不在场,却存在的读者交流,也就是说,他的创作不是“自言自语”。总而言之,主题的选择不是自由的,而是受多方面因素限制的。
其他形式主义学者,如艾亨鲍姆、泽特林、阿瓦多夫等,都从不同方面反思了前期形式主义的弊病。总的来看,他们的反思都卓有成效,但也保留了形式主义一以贯之的琐碎、难以系统化的弊病。当然,也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会有蒂尼亚诺夫对前期俄国形式主义的系统反思。这些反思集中体现于1928年和雅各布逊联合发表的《文学和语言研究中的问题》。这篇文章有很重要的意义。厄利希指出,这篇文章为俄国新形式主义(Neoformalism,亦即晚期形式主义)提供了比什克洛夫斯基和托马舍夫斯基更稳固的理论基础。[5](PP.134-135)
这篇文章的第二部分是关键之处,蒂尼亚诺夫在此声称,“文学史(或艺术史)和其他历史系统是密切联系的”。[7](P.116)这句话里至少包含了三个方面值得我们注意:首先,文学作品是一个自律的系统;其次,这个系统处于和其他系统的联系中;第三,以“历史”来描述系统,确立了系统既是共时的,也是历时的。总体而言,蒂尼亚诺夫建构了“诸系统之系统”(system of systems)这样一个整合艺术作品、艺术与社会的新范式。为了区别早期形式主义的机械整体论,蒂尼亚诺夫特别强调,无论是什么样的材料,都必须从功能的角度予以检视,才能被文学作品使用。惟其如此,作品才是有机的系统,也必然在更大的系统中发挥某个功能。
“功能”在蒂尼亚诺夫的理论中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通过对功能的阐释,蒂氏揭示了语言材料、语境、语境中隐含的规则之间的关系。他首先指出,“词没有一个确定的意义。……‘词’的抽象体就像一只杯子,每次都重新按照他所纳入的词汇结构以及每种言语的自发力量所具有的功能而被装满”。[6](P.41)蒂氏在此强调了两种因素,即词本身,以及它所属的词汇结构和言语(亦即系统)所具有的功能的重要性。这里所谓功能的重要性是指,在没有进入词汇结构和特殊的言语中时,也就是在确定用法之前,作为一种功能单元的词的意义是不明晰的。同时,不同的用法又会导致它具有不同的意义。
蒂氏进一步论述道,“一种语境与另一种语境的区别取决于语言活动中各种条件及功能的区别”;“一般的‘词’是没有的,词在诗中所起的作用完全不同于在谈话中,在散文(各种体裁)中所起的作用又不同于在诗中”,在更广的意义上,“每个词都有自己的词汇特性(由时代、民族、环境所建立)”。[6](P.51)蒂氏已经意识到语境不只是言说的“上下文”,还是言说活动涉及的一整套复杂的交流机制。狭义的语境,即上下文使词的功能变得清晰;广义的语境,即复杂的交流机制则赋予了词隐蔽的涵义,因此,这套机制其实和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等紧密相关。
至此可以看到,蒂尼亚诺夫建立起了一整套完善的文学—社会系统。这套系统有效地克服了早期形式主义中存在的诸种弊病。当然,仔细加以辨别,我们仍然能够发现其中存在的诸多缺陷,比如作为社会系统中的一部分,文学到底如何建立与社会之间的交流?令人遗憾的是,蒂尼亚诺夫没有回答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这或许是其囿于自身的局限,也或许是由于“十月革命”的胜利所致。
三、布拉格结构主义的兴起
在对《文学和语言研究中的问题》的评价上,厄利希认为,这篇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捷克版”形式主义的信条。[5](P.135)姑且不论厄利希把布拉格结构主义视为“捷克版形式主义”正误与否,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这篇文章既在俄国形式主义内部造成了一次转折,也在宏观的形式主义范围内造成了一次转折,后一次转折形成了布拉格结构主义。正如厄利希把布拉格学者的努力视为“捷克版”形式主义一样,学术界常常把布拉格结构主义视为俄国形式主义在捷克的延伸。这个判断适合1930年之前的布拉格,之后布拉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集中体现于1934年发表的《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捷译本序言》。
在这篇评论里,穆卡洛夫斯基在肯定什克洛夫斯基以及俄国形式主义的成就的同时巧妙地指出,什克洛夫斯基的工作是以重形式来反对重内容,因此从一开始,什克洛夫斯基就走向了结构主义。因为,当把作品中的一切成分都归之为“形式”时,形式的含义必然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形式。[8](PP.511-512)在这里,穆卡洛夫斯基的潜台词显然是,什克洛夫斯基的研究是一种矫枉过正的研究;“形式主义”已经不再适合当前的研究,需要改称为“结构主义”;某个成分既是结构的成分,同时也是独立的结构。这其实把“诸系统之系统”改造成了“诸结构之结构”。
沿着这个思路,穆卡洛夫斯基首先修正了什克洛夫斯基关于“棉纺厂”的比喻。他认为,虽然“纺织方法”仍然是注意的中心,但同时也要关注世界棉纱市场的行情。[8](P.514)具体而言,文学实践受到内、外两种力量的干涉,它既是自律的,也是他律的。值得注意的是,穆卡洛夫斯基没有使用“决定”这个具有强制意义的词,他显然意识到诸结构之间的关系不是决定性的,他指出,社会、语言、道德等诸多独立发展的结构,“其中任何一项都不能被先验地置于其他各项之上”,[8](P.515)它们的关系会随时发生变化。
沿着这个思路来看,任何一个结构的变化,都会导致其他结构的变化。对于单个文学结构而言,穆卡洛夫斯基用“前景化/背景”这样一对术语来描述它的变化。随着社会文化结构的变化,文学结构的不同成分会被前景化。这也就暗示了结构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前景和背景间是一种辩证的关系:背景可能会被前景化,前景也可能会被还原至背景。穆卡洛夫斯基特别提醒我们,没有完全的前景化,完全的前景化意味着新的自动化。[9](P.20)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学者把前景化理解为捷克版陌生化,维尔特鲁斯基甚至认为“在否定了形式方法后……这个概念越来越多地阻碍了后来的发现”。他认为,前景化这个术语和穆卡洛夫斯基对结构的精炼、复杂的界定完全不相符。[10](P.134)但这显然是误读:在前景化和背景的辩证转换中,一个动态的、复杂的结构其实已经呈现了。更值得关注的是,不同成分的前景化程度是不一样的,只有处于最高位置的才是该结构的“主导因素”,它主宰、支配着结构中的其他成分。
前景和背景承担着不同的功能。首先,前景必须依靠背景才能感知,同时,前景化也是对自动化的背景的去自动化。不同于陌生化直接依赖读者的感受,前景化有赖于前景和背景之间的语义转换,然后才能诉诸读者的感受。这样,前景化就祛除了俄国形式主义试图祛除、却仍留有残渣的心理主义弊端。其次,当前景化发生、某个作品被视为艺术作品之后,“我们的关注点立刻就转向了相关的文本组织”。[11](P.66)在这个意义上,前景化并没有建立和社会的联系,而是向内转。然而这里不能忽略文本中仍然有背景。背景是一个完全自动化的成分,它承担着交流功能。基于此,作品和社会之间才能建立有机联系。可以说,它比陌生化往前走了一大步。第三,由于语境转变导致前景化成分不同,艺术作品和作者的意图之间的单一联系就被打破了——艺术作品是一个可以比索绪尔意义上的符号传递更多信息的符号,因此,“作者意图”也就有了比将之等同于作者某时某刻的心理、经历更深广的内涵。
基于对把前景化误解为陌生化的变体、被等同于语言的扭曲、变形的不满,穆卡洛夫斯基在保留前景化的前提下,逐渐开始采用“功能”,并区分出两种功能:直接功能和间接(符号)功能。前者又可分为实践功能和理论功能,后者可分为审美功能和象征功能。这四种功能是人对待客体的四种不同态度。实践和理论功能力图改造实在,审美和象征功能的客体并不是实在,而是符号。符号在审美中充当了本体,在象征中则充当着工具。[12](P.43-44)在直接功能中,符号充当着工具。象征功能不同于直接功能,象征功能强调的是人,而直接功能强调的是实在。
在这四种功能里,审美功能有着特殊的地位。穆卡洛夫斯基认为,审美功能“在功能中的地位就像围绕着一些客体的空气”,[12](P.244)失去了这些“空气”,其他功能也就失去了存活的可能。这个特殊的地位使审美功能充当着组织、架构其他功能的角色,[13](P.245)它可以促使某种实用功能的实现,如一个外形更具美感的事物更容易引发关注,由此导致对它的使用,也可以保留那些已经失去其现实意义的实用功能,如把某些废墟视为具有审美价值的客体而保留下来,从而提供了对已经逝去的历史的认知功能。当审美功能自身试图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它就会尝试阻碍、否定其他功能,从而使对象成为艺术作品;与此同时,其他功能一方面会被投射至艺术作品的语义平面上,它们赋予了审美符号“指称性”,从而使艺术作品至少间接地和实在联系;另一方面,会通过材料、主题、欣赏者等进入作品中。[13](PP.363-367)换言之,艺术作品保存了和社会的交流。
雅各布逊讨论了语言承担的表情、指称、元语言、交际、意动、诗歌等六种不同的功能。这些功能的区别在于它们的侧重点不同,前五种的导向都是外在于语言的实在世界,如表情功能导向说话人,指称功能侧重实在世界;和这些实用功能不同,诗歌功能是一种“导向信息本身,因其自身的原因而聚焦于信息”的功能。[14](P.69)尽管讨论的对象不同,区分的功能形式也不同,但雅各布逊还是和穆卡洛夫斯基达成了一致:这些功能都由同一个客体承担,在不同的语境、不同的使用条件下,它们会以某种功能为主导。
无论是穆卡洛夫斯基的四分法还是雅各布逊的六分法,它们并存于一个结构,又会在结构内部发生转换。这一现象提示我们,诸功能在结构中的地位并不是稳定的,它们随时间、语境的变化而变化。正如穆氏所言,“某个特定对象是否被视为艺术,与该对象所处的语境紧密相关。在一段时期、一个国家被视为艺术的,在其他时期、国家则未必如是”。[15](P.3)功能的载体呈现出何种功能,被视为何种对象是基于和语境的紧密关联,而非任意的。这样一来,就构成了一个近乎精密的结构。
四、结 语
“今日流行的巴黎结构主义,只不过是这里所谈的一切的重演——唯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说,它是结构主义思想的进一步发展。”[16](P.92)比利时学者布洛克曼高度肯定了布拉格学派的成就。事实上,随着对布拉格学派认知的深入,布洛克曼的论断日益得到了印证,“重访布拉格”日益成为学术界的兴趣动向之一,我们在俄国学者格利亚卡洛夫对穆卡洛夫斯基的研究中即可窥见一斑。[17](P.127)
在此,我们并不否认法国学者在结构主义研究上的辉煌成就,同时也必须承认法国结构主义在符号学、叙事学等诸多方面已经超越了布拉格学派——正如布拉格学派对俄国形式主义的继承与超越。
[1]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M].刘宗次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
[2]什克洛夫斯基.词语的复活[J].李辉凡译.外国文学评论,1993,(2).
[3]塔塔尔凯维奇.西方六大美学观念史[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4]佛克马,易布斯. 二十世纪文学理论[M].林书武,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
[5]V. Erlich.RussianFormalism:History—Doctrine(3rdedition)[M].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1.
[6]方珊.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C].北京:三联书店,1989.
[7]托多罗夫.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C].蔡鸿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8]《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美学文艺学方法论(下)[C].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
[9]J.Mukarovsky. Standard Language and Poetic Language[C]// P.L. Garvin.APragueSchoolReader. Washington, D.C.: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1964.
[10]J. Veltrusky. Jan Mukarovsky’s Structural Poetics and Esthetics[J].PoeticsToday,1980-1981(winter),Vol.2,No.1b.
[11]J. Mukarovsky. Two Studies of Poetic Designation[C]//J. Burbank, P. Steiner.TheWordandVerbalAr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77.
[12]J. Mukarovsky.Structure,Sign,andFunction:SelectedEssays[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78.
[13]L. Matejka, I. R. Titunik.Sound,SignandMeaning[M].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Michigan,1976.
[14]R. Jakobson.LanguageinLiterature[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15]J. Mukarovsky.AestheticFunction,NormandValueasSocialFacts[M]. tra by Mark E. Suino,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Michigan,1979.
[16]布洛克曼.结构主义[M].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17]A.格利亚卡洛夫.扬·穆卡若夫斯基美学:结构——符号——人[C]//外国美学:第21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