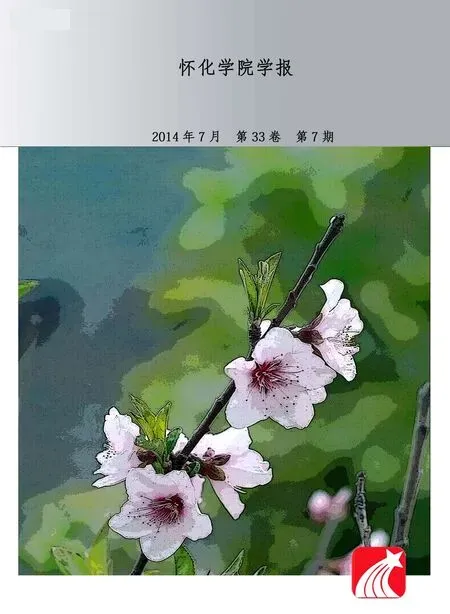朱熹知识论的伦理说教与理性之光
刘克兵
(怀化学院 教育科学系,湖南 怀化418008)
在朱熹的知识论中,他很是强调以格物致知之功,穷究天下万物客观之理。但在终极目的上,他把格物穷理规定为一种实现道德境界的修养方法,在直接意义上又把格物穷理作为求知的手段,更多地容纳了追求知识的内容。通过格物以完成其道德上的目标,体现了朱熹知识论的伦理说教性;追求知识,则凸显了其知识论中的理性之光。这二者并立存在于朱熹的知识论中,体现了朱熹知识论的重要特色。
一
朱熹知识论的伦理说教明显,可谓是儒家修养工夫与内圣之学的有力补充。我们由他所说的:“人入德处,全在致知、格物”[1]487可窥一斑,下详述之。
首先,朱熹在诠释“格物”之“物”时,把“物”主要还是解释为“事”。“物,犹事也。”[1]17朱熹把“物”解释为“事”,“物”就与人发生了关联,指构成人类社会实践的政治活动、经济活动、道德活动与教育活动等。当然,在这些社会活动事务中,朱熹又主要指向了道德活动,即伦理道德方面的人伦之“事”。这从基本上使得朱熹所格之“物”理的知识多为道德方面的知识,这些道德知识又可促进人的道德修养与行为合乎儒家“理”的规定,从而体现了朱熹知识论的伦理说教性质。
其次,朱熹指出格物的直接目的在于“明明德”,最终目的在于“明心之体用”,从而入于圣贤之域。这是在《大学》“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框架下来谈的。由于《大学》中的内在规定,格物致知的直接目的在正心诚意、在明明德,这就使得朱熹的知识始终还是不偏离仁、义、忠、孝、恭、敬等伦理规范之类的道德知识。另外,朱熹在《大学章句》的最后,强调他所作的补格致传“乃明善之要”[2]28,要求把一切格致之功归结到使“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道德境界,从而入于圣贤之域。“成圣成贤”是理学家们共同追求的最高境界,此点自不待言。朱熹所认为的圣贤境界,是指对个人生命道德与学问的最高境界。为了使圣贤境界这种人生理想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朱熹从“理”本论上解释了常人成为圣贤的可能性,并且谈到了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性的方法——读书。他说:“读书以观圣贤之意。”[1]314“然读书且要虚心平气,随他文义体当,不可先立己意,作势硬说,只成杜撰,不见圣贤本意也。”[1]713儒家经典是“圣人之言”的记载,所以通过读书获取知识的活动,是一种与圣人相遇“见圣贤之意”的活动。朱熹在通过对读书这一格物的首要途径而获取的知识活动中,指出读书这一活动是身心修炼、变化气质从而最终成就圣贤人格的必由之路。朱熹说:
圣人千言万语,只是说个当然之理。恐人不晓,又笔之于书。自书契以来,《二典》、《三谟》、伊尹、武王、箕子、周公、孔、孟都只是如此,可谓尽矣。只就文字间求之,句句皆是[1]345。
在朱熹看来,由圣人所表述的天下“当然之理”,已经完整无疑地包含在作为知识获取的主载体——儒家的经典之中,“可谓尽矣”。通过格物的主要途径——读书,即所谓“文字间求之”,就会最终通向圣贤人格的道路。在此,朱熹明显地把格物作为了入于圣贤之域的修养工夫。对此,陈来先生指出:“朱熹的格物学说首先是为士大夫和官僚阶级提供一种旨在最终提高人的道德境界的基本方法,在这个意义上当然也即修养方法。”[1]297作为朱熹知识论组成部分的格物理论和知识的目的理论,它们与儒家成圣在途径与目的上的联系,很明显体现了朱熹知识论中的伦理说教。
此外,朱熹知识论的伦理说教特色主要还体现在他对知识与道德关系的反思中、以及对知识与实践之间的关系主要指向道德知识与道德践履之间的关系。朱熹在对知识与道德关系的反思中,突出了知识是道德的必要前提,也强调了道德对知识的范导意义与知识的道德指向。可以说,作为道学家的朱熹,从根本上维护了儒家下学上达的基本精神以及儒学的核心理念——道德。朱熹在对知识与实践之间关系的解读中,常常把知行问题表述为致知与涵养、穷理与居敬等的关系,使其知行学说主要讨论的是道德知识和道德践履的关系。
二
相对于儒家传统知识论来说,朱熹的知识论则闪烁着理性之光,就格物而获取知识的中间过程而言,尤其如此。
首先,朱熹的知识论关注客观世界对象的范围广泛,同时注意有所选择。在朱熹的思想中,大而天地,小而一物,他都主张应当穷之而获取知识。他说:“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须着逐一件与他理会过。”[1]477他还说:“大而天地阴阳,细而昆虫草木,皆当理会。一物不理会,这里便缺此一物之理。”[1]3688朱熹求知的范围之广,为人所周知。同时他又认为“物”是客观存在的,不是虚幻的。朱熹对“物”的客观性解释立场及“物”与知识的联系,体现了朱熹知识论的理性精神。朱熹经常指出,格物的“物”应是客观事物,失去这一基础,知识的获取也就不可能。这一理解,显现出朱熹独特的理性。李翱虽释物为万物,但主张心不应外物,如此,格物就与知识不相关联,而只与修养有关。谢良佐虽有“物理”之说,然其所穷之理主要是人伦的道德法则,穷理的过程本质上也是一个使“我”复归于“真我”的过程,多与知识无涉。杨时反身格物,即主要在自己身上格物,忽略外界万物,主观色彩浓厚,也不可能把握万物之理,从而获得有关万物的知识。陆九渊虽在“格”字的理解上与程朱一致,但在“物”的理解上同样并不重视外在事物的规律,而是“我心”。他说:“格物者,格此者也。”[1]478这个格此者即指格心。可见,他们都没有朱熹在“物”的理性立场。当然,朱熹还在“物”的选择上强调必有先后缓急之序,区别体验之方,注重选择,也是其知识论富于理性的体现。朱熹说:
伊川先生尝言:要“凡一物上有一理,物之微者亦有理。”又曰:“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小而一物之所以然,学者皆当理会。”吕氏盖推此以为说而失之者。程子之为是言也,特以明理夫之所在,无间于大小精粗而已。若夫学者之所以用功,则必有先后缓急之序,区别体验之方,然后积习贯通,驯致其极[3]3493。
然亦各有次序,当以其大而急者为先,不可杂而无统也[1]291。
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随事遇物也有经验上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知识的摄取不但有范围上的限定,也有先后秩序的选择,“当以其大而急者为先”。朱熹在此强调对“物”的拣择,同样体现出其知识论思想中的理性之光。
其次,朱熹的知识论还注重知识获取上的循序渐进,同时注意权变。朱熹强调“其功有渐”,意为格透一物获取有关该物的知识后,再格另外一物以获取此物的知识,否则就会有逃避困难之嫌。但是,如果遇到真正难以克服的困难时,朱熹则体现出了权变的智慧,主张绕开去另穷一物。《语类》载:
仁甫问:“伊川说‘若一事穷不得,须别穷一事’,与延平之说如何?”曰:“这说自有一项难穷底事,如造化、礼乐、度数等事,是卒急难晓,只得且放住。……延平说,是穷理之要。若平常遇事,这一件理会未透,又理会第二件;第二件理会未透,又理会第三件;恁地终身不长进。”[1]605
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平常当按渐进之序,逐步积累。但由于人难免会遇到“卒急难晓”之事,这个时候,朱熹在知识论中强调“只得且放住”,从而体现出其知识论思想中的权变智慧。
第三,强调积累——贯通——推类的理性方法揭示出了认识的辩证过程。在朱熹的知识论中,十分注重“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的积累工夫。同时,他认为知识的豁然贯通之得来所依赖的也正是一日一件、日日增进的知识积累。在格物穷理的具体步骤上,朱熹主张通过由积累而贯通、由贯通而推类的思想,虽然并不是现代严格意义上的归纳推理方法,但不能否认,它的确反映了人类学习知识的一般途径,揭示了认识的辩证过程,从而表现出朱熹知识论中鲜明的理性精神。
此外,日用即道的思想也使朱熹把目光始终放在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就格物致知的中间过程来看,人必然要经过具体的实践活动而掌握客观事物的本质与规律,从而获得有关客观事物的知识。正因如此,朱熹很是注重实践,在其知识论的构建中也对实践与知识的关系予以了高度重视和解读,从而使得其成为朱熹知识论富有理性之光的又一重要体现。在对知识与实践之间关系的解读中,朱熹认为知识是实践的前提与条件,强调行为实践必须接受理性知识的指导,在这一点上,是包含理性因素的。同样,他讲的实践是检验真知的标准之观点,近似于现代唯物主义论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观点,他认为人是否有“真知”,一定要见到实践行动才能作最后的判断,这点也含理性因素。
三
在朱熹知识论的思路中,由于他把知识领域的事情归入了人格涵养与求知的二重境界,从而使得其知识论被赋予了伦理说教与理性精神的双重特色。朱熹的知识论思想中,无论是对生知之“理”的认识、格物所致之知基本是道德知识的限定、格物的目的——“明心之全体大用”的无疑,还是知识的主体与对象活动所最终达至“心与理一”目标的认识、知识的目的是为道德的强调,都显示出朱熹的知识论含有伦理说教的特性。而朱熹知识论中对知识独立性的强调、对格物范围的扩充,以及格物具体途径中所含积累、贯通、类推等科学方法的指出,又表明朱熹的知识论包含了本身所具有的独特理性精神。
单纯的道德本位或是知识理性本位,除去其自身具备的优点外,无疑也会产生这样那样的弊端。道德本位的价值取向存在偏颇,主要在于其不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知识理性本位下的人固然会获得较多的知识,但其结果只能催化唯工具理性的进一步恶化,导致人的情感的荒漠化和生命的平面化,使人的可用性和能用性仅在于人的知识层面,从而成为知识的附属物。
有幸的是,对朱熹的知识论思想而言,他一方面成功地开辟出了儒学在认知理性意义上的新领域。与此同时,由于朱熹始终没有放弃儒学传统的伦理道德建设,使得他一贯坚持的伦理说教也在知识论的建构中,得到了新的巩固。可以说,正是知识理性与伦理说教二者在朱熹知识论中的结合,使得朱熹的知识论思想把世人引向了一个无限的知识与道德互发的高峰,引导后来者在孜孜于知识攀登的同时,亦应在求知历程之中变化气质、注重伦理,从而实现由知识而内圣进而外王的人格与事业。
[1]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朱子全书·朱子语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2]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朱子全书·四书章句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3]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朱子全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访陈嘉明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