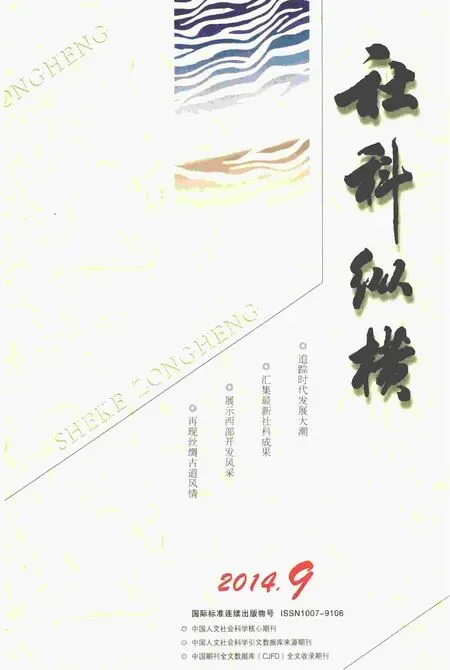萧红创作中的性别、乡土与民族观念解析
丁 琪
(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天津 300191)
萧红的短暂一生犹如充满着悖论的传奇,她数量不算太多的创作也如谜团一样吸引着想深究下去的众多研究者和读者。她的成长经历包含着太多的矛盾性因素以致于我们无法用一些思维定势来解释,她的创作也同样交织着冲突的内涵使研究者不会轻易的妄下论断,我们只能是根据不断发现的新资料一点点走近她,试着了解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一个弱女子并不屈服的灵魂,以及她在贫病交加、家国破碎的威胁中坚持书写的心灵史。她的创作虽然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复杂,但是女性、乡土、民族这些词汇依然是构建起她的生命轨迹和创作大厦的骨架和支撑,是我们走进萧红情感和精神世界的导引,这三者并非并列的存在,而是内在的纠缠牵绊在一起,如血脉一样贯穿在她的创作中,揭示其内在复杂关系也成为萧红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
一、乡土大地上的性别秩序
身受封建父权家庭幽闭和封建包办婚姻之苦的女作家萧红,在逃离了那片让她无数次梦魇的乡土大地转而以文字表达她的乡土感受时,她的思想和情感是复杂的。乡土带给她的切身之痛使她的创作打上了启蒙精神的烙印,“启蒙,就是拿了西方先进的文明思想武器来开启民众的心智,提高民众的素质,这是启蒙文学的基本特征。”[1]启蒙文学对乡土的呈现方式是居高临下的、批判性的,乡土成为愚昧、落后、专制、前现代的一个象征体,而支撑乡土这些表征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落后的性别文化秩序。乡土与性别文化之间在1920年代的乡土文学中形成了一些流行的叙述关联:乡土女性处境悲惨、乡土上的性别压迫无所不在,乡土性别关系是封建专制文化的表现,它作为现代性的对立面理应受到批判。愚昧落后同时也是受害者的乡土女性形象成为控诉前现代的最有力证据。比如《祝福》中的祥林嫂,《离婚》中的爱姑,《菊英的出嫁》中的菊英的母亲,都以性别文化符号的形式牵动着人们对中国传统乡间落后的婚姻制度、封建礼教、迷信等内容的思考和反省。萧红在一定意义上继承了这种乡土启蒙叙事成规,但她又不止于简单机械的复制,而是创造性的继承。这种创造性表现在她的文本不再简单的把女性与封建专制文化相对接成为控诉前现代的一个符号,而是在一种民间话语场域中演绎着独特的乡土性别秩序,并塑造了在乡土伦理法则和道德观念下求生存的更加生动复杂的女性群体形象。
萧红对乡土性别秩序的进入与呈现有一种不动声色的冷静与残酷,她所揭示的犹如东北自然地理环境一样粗犷凛冽的性别关系是触目惊心的,也是其他东北男作家所不曾书写过的。她的作品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异性隔膜”表现倾向,即异性之间很少交流,男女之间没有对话,没有情感沟通,没有家庭中的亲昵举动和温馨场景,而只有辱骂、暴力、虐待、欲望和粗暴的占有。《生死场》中写到的性别关系都是极其野蛮残酷的,例如金枝和成业青春当时,偷尝爱情禁果,这本来是充满浪漫、充满刺激的爱情经验和感受,但在萧红的笔下,他们这种结合充斥着男性的本能、欲望、粗暴的引诱和强力占有,女性成为一个被动的接受者,尤其未婚先孕的事实使女性充满惊慌、恐惧和无奈。小说前几章里所写的金枝和成业的关系具有符号的阐释意义,代表着乡村未婚青年男女之间的一种性别权利和秩序,在同样的生理本能和激情驱使下,男性成为主动进攻者和事后免受责任和惩罚的人,但女性却成为被动接受者和道德伦理谴责的对象,她会被父权贞洁观念任意解释,这样一种不对等的性别权利关系完全基于生理性的本能、欲望基础之上,而非真实恒久的爱情。它像黑土地上的暴风雨一样裹挟着力量而来,又像暴风雨一样留下它摧残后的落花、泥水和余威而去。文本里还写到的乡村的夫妇,如二里半和麻面婆,赵三和王婆,月英和她的丈夫,他们之间的性别关系都是极其相似的,都是辱骂、呵斥、虐待、愤恨,完全没有爱情和温情可言,是基于生存之需的物质和经济联系。二里半一出场就是找山羊和骂他愚蠢的妻子,在他眼里,山羊比妻子更重要。赵三在王婆服毒后没有悲伤,也不是想办法抢救,而是在王婆还在挣扎时就给她订棺材、掘坟地,看到王婆仍气息未断,“他好像为了她的死等待的不耐烦似的,他困倦了,依着墙瞌睡。”[2](P47)夫妻间已经没有任何情分可言,这是何等的麻木和冷漠!而月英的丈夫在月英患了瘫病后视其为生活上的累赘,任其自生自灭,臀下生了蛆就撤了被子用砖头把女人围起来。曾经是打渔村最美丽的女人被折磨的人不人、鬼不鬼。在这些已婚夫妇中隐含着一种性别权利关系,男性总是强悍有力、粗暴无礼的,但女性往往是弱小无助的,很多是结局悲惨的,男人对女人的身心压迫是不需要找任何借口的,也是毫不遮掩的,是自然而然的。这种无形的性别政治甚至于可以凌驾于其他伦理道德之上,成为乡土民间无所不在的最基本的压迫形式。
萧红在写到同性之间的关系时却完全不同于异性间的冷漠、隔阂、辱骂和身体暴力,显示出同性间的心理默契和联合互助,无论是乡村女性之间还是男性之间都有一种默契、融洽和合作在他们之间流动。《生死场》中写到冬闲时节,“女人们像松树籽那样容易结聚,在王婆家里满炕坐着女人。”[2](P25)她们唠着家常、说着粗俗的玩笑以打发寂寞的时光。在月英遭到丈夫的嫌弃和虐待时,王婆和五姑姑来探望她,倾听她对丈夫的愤怒和憎恨,帮她擦洗已经腐烂生蛆的身体,姐妹似的深情和安慰让垂死挣扎的月英体会到了人间的一点点温暖。女性之间姐妹情谊依赖的是这种倾听、谈笑、关爱和温情脉脉的东西,而男人之间的联系更多的体现在生死关头的结盟和浴血奋斗。在青年赵三等人组织的“镰刀会”同地主的斗争中,男人们“天天夜晚计算着”,但都瞒着、躲着自己的老婆,仿佛这是男人之间才可以交流的事情,而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的妻子却没有知道的权利。小说写到在日本入侵之后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村民们积极行动起来并举行了“为生而死”的宣誓仪式,男性群体在反抗的激情和民族身份的斗争中站在一起,成为一个坚不可摧的共同体。他们一起呼喊、一起嚎啕、感天动地,在面对敌人的共同斗争中他们结盟在一起,体会着亲兄弟般的情谊,这个关键时刻女人往往是不在场的或是被有意排斥在外的。
萧红所书写的这种独特的性别关系是基于乡土大地的生存真相,是萧红以自己敏锐的眼光、善感的心灵观察和体验的结果。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曾精辟解析过中国乡土社会的性别特征,他说求稳定的宗旨决定了中国乡土社会遵循男女有别的原则,“‘男女有别’是认定男女间不必求同,在生活上加以隔离,这隔离非但是有形的,所谓男女授受不亲,还且还是在心理上的,男女只在行为上按着一定的规则经营分工合作的经济和生育上的事业,他们不向对方希望心理上的契洽。”所以“在乡村里,夫妇之间感情的淡漠也是日常可见的现象”,“做的好,没事,也没话;合作得不对劲,闹一场,动手动脚,说不上亲热……乡下,有说有笑,有情有意的是在同性和同年龄的集团中,男的和男的在一起,女的和女的在一起,除了工作和生育事务上,性别和年龄组间保持着很大的距离。”[3](P50)男女有别的伦理造成了男女间的隔膜,最终形成了类似“男女有仇似的”状态。这种性别权利关系劳固的矗立在乡间大地、渗透于每一个家庭,它是从弱肉强食的乡土生存法则和等级森严的乡土伦理关系中生长出来的一种现实法则,是乡土社会生存凌驾于情感之上、道德超越法律的民间真相的体现。萧红所揭示的老东北黑土地上的愚夫愚妇们的关系正是如此,异性间应有的爱情、默契、惺惺相惜都被同性间的情意所代替,同性间的交流、相知、合作更加反衬出异性间关系的扭曲。这种独特复杂的性别关系的展开远远超出了启蒙作家批判前现代的思考范畴,是真正立足于民间立场的一种睿智的洞察和逼视,它使作家的性别书写区别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而呈现出先锋和异类的特征,同时也丰富了现代乡土人物形象,并延展了人们对作家与表现对象价值立场问题的思考。
二、民族国家话语下的隐形性别书写
萧红对时代和民族命运有着强烈感受和责任担当意识,她的很多作品纠缠着时代主题与女性命运的双重话题,因而女性与民族议题的复杂性与特殊性在她的文本中得到了充分展现。在她的创作中,性别主题始终是伴随着民族国家话语的一种隐形书写,虽然在作家萧红那里,女性意识是清晰而强烈的,但在文本中它是被压抑的和隐藏的,是伴随在主流话语里的附加意义,不能独立支撑起文本的意义空间。比如她早期最重要的代表作《生死场》,前十章表现的都是愚夫愚妇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在这里土地不过是他们生生死死的场所,生和死不过意味着自然生命的开始和结束。而后七章则表现了当时被认为是时代主题的民族抗日话题,愚昧的农人们开始自发的为生而死的战斗,土地成为民族和国家的象征,在为国家和民族而战的豪情壮志和生死搏斗中,生和死的意义获得了超越和升华。这是我们解读这部作品所不能绕开的主题,也是作品在当时和后来能产生反响的意义所在。
但是一个优秀的作品总是一个丰富的、存在无限阐释可能和众多意义生长点的文本,不同的人会看到它的不同侧面。在《生死场》中女性主义者恰恰看到的是在民族国家话语、生与死的哲学话题背后的性别思考。但这种思考是隐形的,不能成为文本的主导意义空间,而是夹在主导话题中的附加表达。在作品中,关于性别的话题作者并没有为它建构一个完整的叙述体系,而是穿插在主导情节中的零散片段,隐现着作者的点点滴滴的性别思考,当我们把作品连缀成一个整体时,它表达的依然是有关民族抗日的主题,而十章的日常生活片段甚至是对这一主题的铺垫。比如作品中写到的二里半和麻面婆的关系,写到王婆和赵三的生活细节,还有患了瘫病的月英和丈夫的悲惨故事,虽然它们在特定语境下能够指向性别压迫的意义单元,但都不是贯穿始终的人物和故事情节,他们的关系也并非作品要展现的重点。另一方面,这种性别议题之所以会被我们注意到就是因为它并非是被完全压抑、隐而不显的,恰恰相反,作者借助表达主导的民族国家话语的各种机会表达她的女性思想:女性恋爱时的被动,女性生育的痛苦,女性被男性压迫的事实,女性在异族入侵时刻身体和精神的被蹂躏,等等。这些细节的不断出现提示我们作者一种性别视角的植入和强烈女性意识的喷薄欲出。
民族国家话语对萧红创作的批评垄断不应该成为我们指责批评家的借口,它应该成为我们反思这种隐形书写模式的由头。我想特定年代妇女与民族国家话语内在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冲突是形成这种书写模式的重要原因。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的土地被日本的铁蹄所践踏,萧红在逃亡异乡的路上开始表达东北人民奋起抗日和强烈思乡的主题,这在那个战火纷飞和抗战形势异常严峻的时刻是最合时宜的现代性创作主题。自近代始,中国的现代的民族国家意识就在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过程中不断形成,独立、民主、自由、统一的观念伴随着中国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一次次胜利不断深入人心,也被赋予了现代性的内涵,成为主宰现代性文化的核心理念。甚至其他的很多东西被忽视,无法真正进入现代性文化的视野。我们一直缺乏反思的是,这种民族民主观念是否考虑到了妇女的利益,是否注意到了性别平等,我们所想象的一个现代民族民主国家是否给予妇女以充分的权益。
这种性别议题本质上与一个现代化民族民主国家有内在的一致利益,首先由半封建半殖民国家迈向一个现代化国家就不能排除女性的能量,另外一个真正的现代化国家必然包含着性别平等的政治诉求和现实行动。但是在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特定年代,这种性别的议题往往又是被压抑的话语,或者是以某种特殊的形式涵盖在更宏大的民族国家话语里。在这种情况下,强烈的女性意识和国家民族话语的纠缠就成为很多文本的一种特征,往往民族国家话语是显性的、主导的,而性别话题是隐形的、附加的,而且这种隐形的性别书写在作家那里表达是有区别的,萧红的性别书写就不同于同是东北作家群的萧军,也不同于同是女作家的丁玲。
三、乡土书写中的悖论与萧红的精神追寻
在现代文学史中,萧红是个典型的乡土作家,对老东北黑土地的状述与表达成为贯穿其创作始终的一个元主题,但萧红对乡土的矛盾态度和悖论性书写也是其创作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悖论表现在萧红曾经是一个逃离乡土的激进叛逆者,但在逃往异乡的人生旅途中她又成为执著的乡村情趣的歌咏者;而且在对乡土的状述和审视中,她也始终无法安放自己疲惫的心灵,一直处在乡土批判和精神家园两种精神立场间徘徊游移。
中国现代乡土小说自1920年代兴起后,对乡土文化的认知经历了由乡土批判到乡土神话的心理发展过程。1920年代的乡土作家蹇先艾、王鲁彦、彭家煌、台静农、许杰等深受鲁迅乡土批判的启发,以冷静逼视和自我放逐的心态展现各自乡土的民风民俗和农民的生存真相,形成当时流行的隐含乡愁的戏谑、反讽、暴露的叙述风格,共同推动了现代乡土文学的勃兴。而之后的沈从文、废名、汪曾祺等则发展了鲁迅的归乡创作模式中反城市情绪,在对乡土宗法制农村的回眸凝望中倾情构筑着乡土神话,乡土大地孕育的自然生机、原初的性灵、生命中迸发的欲望和自由的意义,构成了文本书写的内在精神支撑,在貌似反现代化和乌托邦式的浪漫书写中开启了现代化的另一种想象和可能。萧红创作中隐秘的呈现出了怀乡和归乡两种情绪的复杂纠缠,如“大泥坑子”所隐喻的污浊、晦暗的生存状态和蜂飞蝶舞、阳光明媚的“后花园”指涉的自由生命空间冲突的出现在一个文本中,造成深情和戏谑两种叙述语调的内在分裂,使文本情感指向变得模糊、游移,这在某种意义上反映出作家处于文化启蒙和乡土神话的双重诉求下精神归属的困惑。这在《呼兰河传》中体现最为明显。在这个百年不变的小城镇,生活着许多本性善良但又愚昧麻木的人们。他们的生活单调、刻板、寂寞,在这贫乏死寂、毫无生命活力的生活中,人们没有什么追求,只要有一个大泥坑子就能一年四季带给他们无限的乐趣和谈资。所以作者充满趣味地描绘了东二道街上的那个赫赫有名、给全村带来不少了乐趣和苦恼的五六尺深的大泥坑子。大泥坑子隐喻北方小城镇的卑琐无聊的生存状态,作者的情感和精神指向犹如鲁迅是“哀其不幸,怒气不争”,落脚在批判愚昧麻木的国民劣根性上。但在《呼兰河传》中还同样存在一个充满梦幻色彩的大花园:
家有一个大花园,这花园里蜂子、蝴蝶、蜻蜓、蚂蚱样样都有。蝴蝶有白蝴蝶,黄蝴蝶,这种蝴蝶极小,不大好看。好看的是大红蝴蝶,满身带着金粉。
蜻蜓是金的,蚂蚱是绿的,蜂子则嗡嗡地飞着,满身茸毛,落到一朵花上,胖圆圆地就和一个小毛球似的不动了。
花园里边明晃晃的红的红,绿的绿,新鲜漂亮……
一到后园里,立刻就另是一个世界了。决不是房子里的狭窄的世界,而是宽广的,人和天地在一起,天地是多么大,多么远,用手摸不到天空。而且地上所长的又是那么繁华,一眼看上去,是看不完的,只觉得眼前鲜绿的一片……
一到后园里我就没有对象地奔了出去,好像我是看准了什么而奔去了似的,好像有什么在那儿等着我似的。其实却是什么目的也没有。只觉得这园子里无论什么东西都是活的,好像我的腿也非跳不可了。
——《呼兰河传》
“后花园”的描写改变了呼兰河的整体色调,这在萧红整个乡村书写的过程中是一个非常突兀的异质化的审美空间,它与后花园以外的乡村世界在审美品质上和叙事格调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差,文本内部呈现出了巨大的分裂和冲突。从另一个角度讲,叙事文本的内在分裂也指向叙事主体的不确定和分裂状态,即作者徘徊于理性的启蒙者和具有原始思维特征的儿童双重身份之间,时而以戏谑的方式揭开乡土麻木凝滞的生存状态,时而以感性的笔触抒发着儿童对原乡记忆的深深依恋。
萧红对乡土民间的这种悖论性书写折射了作家本人的内在精神困惑,这种困惑不仅包括外在的她所生活过的乡土民间带给她的精神困扰,还包括萧红对自己所经历过的个人精神史的深切反思。就像研究者陈思和所讲的那样,民间文化本来就是藏污纳垢、鱼龙混杂的一种状态,既保留着民间乡土淳朴善良、自由自在的文化精粹,又伴随着愚昧落后、保守凝滞的精神传统,作者在逃亡异乡的路上,在风风雨雨的人生历练中渐渐偏离了五四启蒙传统对民间的否定性认识,逐渐让自己的血脉融入民间大地,让自己的心灵贴近故乡的父老乡亲,民间本身的生机和力量才逐渐在文本中显示出来。萧红对此有朦胧的认识,她在同聂绀弩的一次谈话中曾讲过:“鲁迅是以一个自觉的知识分子,从高处去悲悯他的人物……我开始也悲悯我的人物,他们都是自然的奴隶,一切主子的奴隶。但写来写去,我的感觉变了。我觉得自己不配悲悯他们,恐怕他们要悲悯我咧;悲悯只能从上到下,不能从下到上,也不能施之于同辈之间。我的人物比我高。”[4](P402)这种对乡土、乡民的态度转变也意味着一种审美方式的转变,因而故乡、民间的经验在她的作品中变得生动富有生活质感,并呈现出乡土伦理的自在性、自生性和自主性,这在作于生命后期的《呼兰河传》中最为明显。记忆中乡土的残酷伴着记忆中乡土的温热带着泥土气息扑面而来,它反映了一个被启蒙精神照亮的作家如何在启蒙与传统之中游走与挣扎的过程,这同时也是五四一代作家在面临民族现代化的征程如何经历拔根的痛苦与欢欣的真实写照。就萧红个人来讲,作家独特的人生经历也为这个问题的解释掺杂进更加复杂的因素。在萧红短暂的一生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她漂泊在故乡以外的人生羁旅中,这种漂泊流浪生活的源触发点就是对故乡的抵抗、对自由的追求,那时故乡成为父权、专制、落后的象征使她跋涉在异乡的旅途中,但是民族的苦难和个人多次不幸的婚姻又无情的击碎了她的自由梦想,在自己的故乡成为日本人的土地,自己的爱人离自己远去以后,她脆弱敏感的精神世界变得无所归依,她只能退回到生命的原乡去找寻童年的记忆来抵御精神追求的空虚和恐惧。所以有些研究者称萧红后期的乡土歌咏是“落寞的精神还乡,隐藏着自我救赎的隐秘企愿”[5](P150),这恰恰注意到了萧红在特定历史情境下的一种无奈和抗争。萧红颠沛流离的羁旅生涯不断的触动她对自己精神之旅的反思和修正,乡土民间也正是在这个不断反思和修正的流动状态中悄然发生着变化。
[1]陈思和.启蒙视角下的民间悲剧:《生死场》[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4(1).
[2]王平编.现代小说风格流派名篇[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
[3]费孝通.乡土中国[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
[4]萧红.萧红散文名篇[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
[5]王光东等.20世纪中国文学与民间文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一本能够让你对人生有另一种认知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