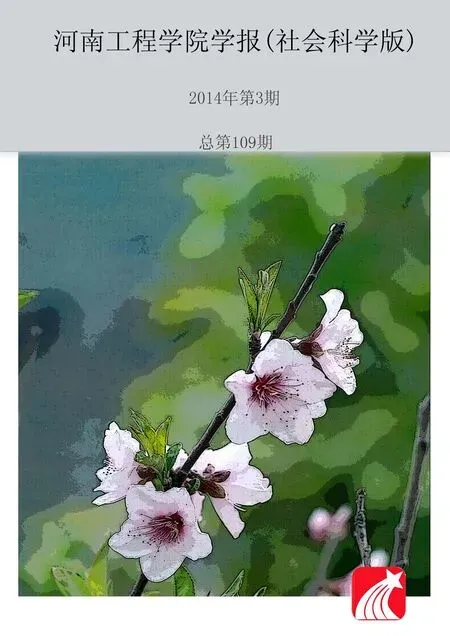“文革”地下娱乐类手抄本的城市想象与叙述
——以《一只绣花鞋》为例
井延凤
(河南工程学院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河南 郑州 451191)
“文革”地下手抄本文学中曾存在着这样的一类手抄本:功能以娱乐和消遣为主,叙事粗糙且缺乏逻辑,人物设置类型化、概念化。这类手抄本以《一只绣花鞋》为代表,被国外研究者称为娱乐类手抄本。它们虽然以手抄、口传等方式在民间秘密流传,但其叙事并没有摆脱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学”的影响。很多情况下,为了叙事的安全,这类手抄本小说的创作者们往往会采取一个被国家权力意志和主流意识形态认可的叙述框架。比如,反敌特题材中“敌(特务)”“我(共产党英雄)”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基本上沿袭了主流文学中的“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不过,细读这些粗糙的手抄小说文本,我们会发现,这类小说在追随主流叙述时不时地溢出对城市现代性的想象,尤其是关于现代城市形态的想象。这些叙述一方面体现出“两条路线斗争”对于普通民众思维模式的影响,另一方面也给予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和把握那个时代民众内心真实诉求的讯息和路径。
一、大陆城市:“纯洁”而“空洞”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没有哪一部作品会像《一只绣花鞋》一样,其人物活动会涉及如此众多的城市,关于现代城市形态的种种叙述在其中也比比皆是。与之相反,“十七年”文学和“文革”主流文学中,城市题材文学往往会回避关于城市形态的具体叙述,即使涉及也多限于能够体现“新”中国面貌的城市空间。这部作品却不同,其中既有关于中国大陆城市的描述,如:大连、南京、北京、重庆、武汉、桂林、大同,也有关于中国香港、台北的叙述,更有关于异域城市的想象,如:缅甸的仰光、马来西亚的吉隆坡、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苏联的莫斯科和高尔基城以及A国的某城等。为了呈现人物活动涉及的不同地域的城市空间,作者几乎穷尽了自己有限的地理知识,让故事中的人物频繁地来往于不同的城市之间,而反敌特题材又为人物忽而国内、忽而国外的行为提供了充足的理由。叙述者和读者(听众)则借助人物和故事实现着对中国城市和异域城市的想象和叙述。这些叙述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了那个时代人们所可能的对城市的认知和想象。
在作者有关城市的叙述中,大陆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城市总是显得很“纯洁”,而其具体面貌又显得很“空洞”,我们来看一段对大连的描写:
大连的夜,幽静极了。
天上的流星偶尔拖着长长的尾巴,无声无息地从夜空坠落;迷人的月亮,睨着拥抱着城市的大海,温柔,慈祥;夜风像个调皮的姑娘,摇碎了天上的月光,摇碎了天上的繁星。在灯光和月光的映照下,大海撒出一把闪光的碎银,亮得刺眼。几只海鸥仿佛并不困倦,追逐着海面的碎银,偶尔掀起的浪花微笑着嘲弄着他们的双翼……[1]1
在张宝瑞的笔下,1963年的大连的夜,安静、温柔而平和。作者的叙述展示着大连这个城市应该具有的社会主义“新”城市的气象和面貌。“纯洁”且毫无资产阶级城市的豪华与奢靡,是作者透给我们的最主要信息。在这段文字中,大连与大海融为一体,与自然融为一体,显得无比和谐与安宁;而就是在这样安宁的夜晚,大连却发生了凶杀案。这样的叙述正好契合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气候,一方面新生政权已经建立,和平、安宁的整体局面已经奠定,另一方面战争文化的影响、台湾反攻大陆的威胁、复杂的国际政治形势,又使安定团结的局面笼罩着一层阴影。
又如对北京的叙述:
“旅客们,北京就要到了,前面是丰台站,请大家做好准备。”广播里传出播音员清脆柔美的声音。
那声音在车厢里回荡:“北京是我国的首都,同时北京又是驰名中外的文明古都,它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南襟河济,北枕居庸,形胜甲于天下。它曾是辽代的陪都、金中都、元大都、明、清的都城。北京,既是全国各族人民萦怀向往之地,又是世界各国友人渴望游览的圣地,有巍峨壮观的八达岭长城、庄严雄伟的天安门、风景优美的颐和园、建筑奇特的十三陵、金碧辉煌的故宫、设计奇巧的雍和宫……北京的名胜古迹,不可胜数,北京的山川风物,千姿百态……”[1]65
在这段文字中,叙述者对北京的描述是通过播音员的声音转述的。列车播音员的身份决定了其播音内容的官方意识形态性,而作者对此的转述又使作者对北京的叙述具有某种意识形态性。这种意识形态性首先表现在北京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北京“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所在地”,“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作为新中国象征的新北京的合法性却要由“文明古都”来证明与加强,而作为社会主义新城市的北京的城市形态是怎样的,在这里却被搁置不谈。搁置不谈的原因应该在于,北京作为新中国政治中心的意义是抽象的,除了天安门、中南海等具有高度政治意义的空间之外,北京的新国家意义是不能被具象化的。
再如对武汉的描述:
登上武汉江关钟楼,极目四望,天空高阔,楚地生辉。飞架的长江大桥犹如长龙卧波,横索龟江。长江、汉水在脚下合流,激浪扬波,奔腾东去。在这里很难领略当年苏东坡所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千古绝唱。长江,这条母亲般的河流,孕育过华夏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也孕育了武汉这颗璀璨的明珠。武汉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内地的重要商埠。远在秦汉之际,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在此地繁衍生息,依江筑城。三国时代,夏口(汉口)和沙羡(汉阳)就以商业繁荣而著称。岁月更替,斗转星移,明清之际,汉口就成了“十里帆船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夜明”的闹市,同朱仙镇、景德镇、佛山镇并称为中国四大名镇。
武汉地处长江流域的要冲地段,雄踞中原,承东启西,支撑南北,在中国交通运输战略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1]199
在这段关于武汉的叙述中,叙述者的语调类似于教科书和播音员的语调,这样的语调因其具有的意识形态性质,保证了叙述者叙事的安全。在这段文字中,叙述者强调的是武汉重要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地位,而作为新中国的重要现代城市,叙述者只提到了“飞架的长江大桥”。有关这座城市的具体形态和面貌,叙述者同样处于“失语”状态。
从以上例证可以看出,作者对中国大陆城市的描写侧重这些城市的自然风光、名胜古迹、历史沿革。如果把这些关于中国城市的叙述放到整个文本中去看,我们就会发现,后现代主义式的剪接、拼贴的叙事风格,在这些接力传抄的故事中并不少见。我们的英雄与特务斗争的紧张故事和各种关于城市的空洞词条被并置在一起,紧张激烈的斗争时时会被嵌入其中的口号式的朗诵语调所延宕和间离。这或许只是因为故事最初的口述性质和后来传抄者的添加、修改造成的,但这样做的客观效果却是对主流城市叙述的疏离和反抗,使中国大陆城市的形象在对字典词条内容和教科书语调的“戏仿”中变得空洞而抽象。
二、异域城市:“堕落”而“多彩”
社会主义城市形象的“纯洁”而“空洞”并不意味着这一时代的人们对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形态缺乏想象与认知。相反,现代城市的声光电化对于大部分民众并不陌生,甚至耳熟能详。不过,这些想象和认知只属于香港、台湾和异域的“资本主义”城市。在作者的叙述中,这些城市“流光溢彩”,“富丽堂皇”,奢靡无比。我们来看作者笔下的香港:
鳞次栉比的商店,灯火辉煌,样式繁多的小汽车穿梭往来,像一条彩色的河在流动;摩天大楼令人仰叹,破旧阴暗的房屋又比比皆是。五光十色,令人眼花缭乱的广告灯,交相辉映;醉态的男人,花枝招展的妓女,大腹便便的商人,耀武扬威的外国水兵,使这个城市显得更加不协调。[1]38
虽然受意识形态的规约,叙述者指出了香港这个殖民地城市的堕落之处,比如:“醉态的男人,花枝招展的妓女,大腹便便的商人,耀武扬威的外国水兵”,还有阶级悬殊中贫民居住的“破旧阴暗的房屋”,但对于穿梭往来的“小汽车”和令人仰叹的“摩天大楼”的津津乐道,分明泄露了叙述者心底的向往。“灯火辉煌”“五光十色”是叙述者和读者心目中现代城市形态应有的基本面貌,也是繁华都市的表征。但在“文革”甚至“十七年”的语境中,现代城市的这些特征都被赋予“资本主义”属性。因此,叙述者只能将类似的想象和叙述赋予异域城市。
再来看作者笔下的缅甸首都“仰光”:
夜晚,仰光是一片流光溢彩的世界,尤以迷人宫最动人心弦,远处望去,犹如一颗水晶葫芦,在半空中摇曳,闪闪泛光。迷人宫富丽堂皇的大厅顶上,吊着蓝色的精巧的大宫灯,灯上微微颤动的流苏,配合着五彩缤纷的塑料花木和天鹅绒的紫色帷幔。乐队奏着豪放粗犷的西班牙舞曲,一群珠光宝气的艳装妇人,在黯淡温柔的光线中,被搂在一群着装时髦的先生的胳膊上,妇人的皮鞋后跟响着清脆的声音。[1]72
对于资本主义城市“仰光”,作者主要描写了娱乐场所“迷人宫”。这里有“蓝色的精巧的大宫灯”“五彩缤纷的塑料花木”“天鹅绒的紫色帷幔”“豪放粗犷的西班牙舞曲”“珠光宝气的艳装妇人”,现代城市的消费性在这里表现得极为充分。在对这些“堕落”场景进行描述时,作者的意识已经不受意识形态的规约,甚至连对香港那样的“佯装”批判的姿态都没有了。
关于国民党盘踞的台北,作者是怎样想象的,我们来看:
龙飞来到1204号房间门前,伏在门上听了听,屋里没有任何动静。他走回自己的房间,又来到凉台上,只见华灯齐放,几十万瓦的霓虹灯把大厦打扮成辉煌的灯山,无数盏街灯把台北市熔成一片闪闪烁烁的广袤灯海。那基隆河、淡水河摇曳着彩虹、光柱,幻化成一道五彩斑斓的洪流,漾动于星的海、灯的天,真是如诗如画,如梦如幻。[1]85
虽然作者没有对台北作过多的具象描述,但霓虹灯装扮的大厦,摇曳着彩虹、光柱的河流,无数街灯闪烁的台北市分明是现代繁华都市的典范,作者甚至发出“如诗如画,如梦如幻”这样的赞叹。把敌人的城市描绘成这般繁华景象并且对此毫无保留地认同和赞叹,肯定是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所不容的。
作者对异域城市的叙述和想象有着明显的相似性,比如多描写夜晚的城市形态,这些城市形态的消费性特质突出等。这样的想象一方面来源于意识形态中对于资本主义城市的定性,但另一方面作者关于城市形态的具体描述更多地延续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海派对于城市形态的描述,以及“十七年”文学中对于旧时上海、南京等城市的批判性叙述。“花花世界”的城市是不见容于当时的中国的,因此,出于本能,作者把这样的城市形态叙述给予异域城市和旧时城市。这些城市都是社会主义城市的“异己者”,但作者在叙述时,常常会情不自禁地对之认同和赞叹。这一点是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因为它透露了民众心底对“堕落”而“多彩”的现代都市的莫名向往。
三、差异的内在逻辑:城市的生产性与消费性
不难看出,叙述者对中国大陆城市的叙述与想象和对香港、台湾以及国外城市的叙述与想象,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对大连、武汉、北京的自然风光与风景名胜进行描绘时,大连、武汉、北京显得“纯洁”与“安详”。但是,这些中国大陆城市在彼时是怎样的真实模样,作者却处于“失语”状态,作者甚至回避了主流叙事中基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城市大工业化叙事。而像香港、仰光这样的资本主义城市,却有着完全不同的面貌,它们五光十色、多姿多彩,充满了现代城市的“魅惑”。
为什么作者对大陆和大陆以外城市的叙述与想象存在如此大的差异?这是由中国现代性的特殊性和当时的政治环境造成的。“五四”以来的中国的现代性实践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是在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下进行的。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目睹了资本主义扩张的本性,留学归来的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曾亲眼看见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因此,他们理想中要建立的现代民族国家是克服了资本主义国家种种弊端的新的国家。中华民族特殊的历史境遇以及这个民族对资本主义的带有保留的批判态度,使这个民族最终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革命的成功是在“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上取得的。中国革命成功的这一范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城市的态度上,城市成了有可能使革命胜利果实变质的“危险”场域,城市的空间似乎充满了危险的资产阶级的气息。因此,新生的政权对城市充满了“不安”与“警惕”。消除这种不安的办法就是城市“清洁化”运动,就是取消城市的消费性,凸显城市的生产性意义。
在主流意识形态中,一直存在这样的认知:消费性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是会腐蚀我们的工农兵的。这种意识形态观念在文学上的典型表现就是《千万不要忘记》和《霓虹灯下的哨兵》这一类作品的出现。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时期,文学中对城市的描写显得呆滞与缺乏想象,城市被赋予国家主义意义,往往显得“纯洁与神圣”。这就是为什么娱乐类手抄本尤其是《一只绣花鞋》中出现的大陆城市都有着迷人的自然风光,因为自然风景是无所谓姓“资”也无所谓姓“社”的。同时这些城市还拥有令人顿生骄傲之情的名胜古迹。就像北京,“既是全国各族人民萦怀向往之地,又是世界各国友人渴望游览的圣地”。手抄本的作者或许为了在专制的政治文化中获取叙述的安全,也可能是受当时国家权力意志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对中国大陆的城市多采取了这样一种叙述策略。
而对于香港、台湾和国外的许多城市,叙述者却做了充分的“资产阶级想象”。香港、台湾、仰光无一不是充满了“魅惑”的花花世界。这里有闪烁的霓虹,有让人堕落的歌舞厅,有歌女与阔太太。当然,这类城市是作为大陆“社会主义”城市的他者“资产阶级”城市而存在的。作者对这两类城市的描写并没有跳出“两条道路的斗争”的套路。但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作者在对这类城市进行资产阶级想象与叙述的时候,本意是为了批判,但批判却显得如此无力,“艳羡”之情溢于言表。香港的小汽车穿梭往来,“像一条彩色的河在流动”,摩天大楼“令人仰叹”;仰光的迷人宫“最动人心弦,远处望去,犹如一颗水晶葫芦,在半空中摇曳,闪闪发光”。这说明,尽管国家意识形态在千方百计地取消城市的“消费性”,但正如马克思认为的生产最终为了消费,没有消费,生产便难以为继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样,只要肯定了城市的生产性,其消费性就是不可取消的。尽管国家权力机关可以通过配给制来遏制城市的资本性和消费性,国家权力意志可以通过意识形态对此予以压制,但对“灯红酒绿”的具有消费性的城市的想象与渴望,就像暗流在底层涌动,一如在黑暗中、在油灯下不断被传抄复制的手抄本。
[1]张宝瑞.一只绣花鞋[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