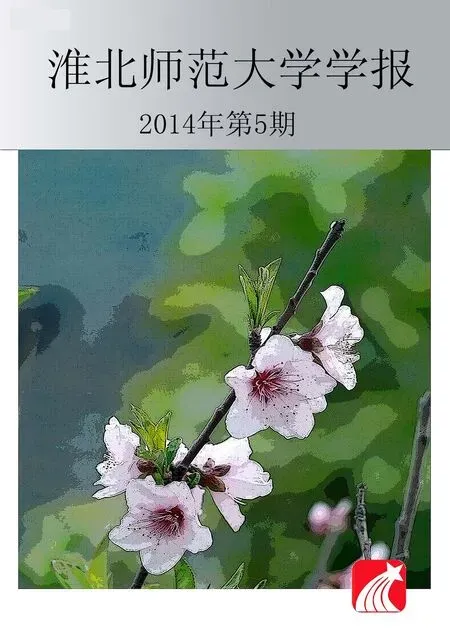陈登科《风雷》文本生产的社会学考察
施学云
(淮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一段时期,1950-70年代文学研究众声喧哗,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界新的理论增长点。尤其在李杨、程光炜、董之林等学者努力下,一批研究佳作应运而生,革新了大众日益庸常的审美视野,引起了人们更多的关注和效仿。遗憾的是,大部分研究大抵脱不了民间、革命话语的藩篱,索隐情结和话语阐释先见也昭示着这种研究思潮必然逐渐回落。出于实用主义的考量,研究者们对于解读文本的选择煞费苦心,很多红色经典文本重新返回公共视野(如(《红岩》《红旗谱》《红日》《创业史》《艳阳天》等),重复同质研究问题颇为突出。这种惰性选择不仅造成了学术研究资源的浪费,同时也可能遗弃了某些更有价值的文本。这里不得不提到已为主流研究界所遗忘的——陈登科和他的长篇小说《风雷》。窃以为,与柳青、浩然等农业合作化题材作家相比,某种意义上陈登科其人其作文学的和文化的审美空间可能更具拓展性和包容性。面对《风雷》,我们并不打算凭借民间、日常生活等话语介入小说文本,竭力发掘其间隐藏的异质因子;抑或依托人道主义、审美自律等话语,提出不合时宜不近人情的批判与指责。这里的想法是,回到文本产生的时代,探究作家的创作驱动力,理清文本生产、传播的具体情境,看一下《风雷》在合作化叙事体系中可能蕴涵的复杂特质。
一、忏悔与冒险:《风雷》文本创作心理机制分析
考察陈登科创作长篇小说《风雷》的心理动机,直接关系到小说的主题表达和意义指向,某种程度上也规约了文本的审美维度。爬梳史料,关于《风雷》的创作动机,作家曾经这样说过:
我为了向党和人民赎罪,我又重新到淮北去生活,和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真正了解人民,听取人民的呼声,反映人民的疾苦,结构了《风雷》。《风雷》是我向人民赎罪的产物,她也为我招来了五年多的铁窗生活。……我不能将那三年生活真实地反映出来,我是无颜面见淮北人民的,我也有愧于中国的历史,我便撇开《风雷》,另起炉灶,结构了《三舍本传》……但是在全书中的真话,也不超过百分之七十,仍有百分之三十的官话与废话……[1]378-379
当然,仅凭作家新时期自述来判断未免有些武断。结合陈登科人生成长经历分析,我们发现作家与小说主人公情感存在着某种同构性,陈登科身上也具有类似于祝永康的卡里斯玛特质。陈登科参加过淮海战役,在淮北任过区委书记、公社书记、大队书记,兼任食堂主任,对淮北这片曾经战斗、工作和生活过的土地怀有深沉的感恩情怀。1958年间陈登科创作出系列散文特写、短篇小说和电影剧本,如《春水集》《柳湖新颂》《卧龙湖》等,作品对乡村经济政治生态的描写,与其后来构思创作的《风雷》差异较大。这种创作上的转变,印证了作家情感上的变化并非虚言:出于朴素的感恩情愫,陈登科因自己对乡村的非现实主义书写产生了沉重的愧疚体验和赎罪心理,这也直接触发了《风雷》的产生。基于此,窃以为作家的这种“忏悔说”(或“赎罪说”)是可靠的。
与陈登科这种特殊情感不同,一些作家在进行合作化小说写作时大多怀有雄心勃勃的史诗心态,竭力彰显社会主义改造这一方针政策的合法性和必然性,反映历史进化的本质规律。如柳青坦言:“《创业史》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①山东大学中文系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内部资料),1979年,第249页。浩然也曾说道:“设想它(《艳阳天》)是反映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全过程的‘农村史诗’式的小说。”[2]22在不同创作心理机制的统摄下,小说给我们描绘出了不同的乡村生态。《创业史》《艳阳天》呈现出厚重深沉、慷慨激昂的文本特征,在揭示社会主义改造复杂性、渲染两条路线斗争严重性的同时更加强调明朗、乐观、亢奋的乡村氛围。《风雷》中的乡村生态意绪格外低沉,在展示农村阶级斗争主线的同时让人切实感受到了当时农村地区经济凋敝、社会人心紊乱、基层政治权力倾轧的现实,让人看到了乡村社会赖以传承的顽强的自我救赎能力,以及农民为改变自己的生存困境而作出的自发奋斗。乡村生态描写的差异性,固然可能与作家扎根的具体乡村环境有关联,但更深刻地来源于作家本身创作心理机制的分歧。由于对于乡村生态负面因子的深度披露,某种程度上冲淡了社会主义合作化的必然性和正义性,影响到了合作化小说政治主题的表达,《风雷》一度被人批评为“暴露小说”。当前研究者批评“十七年”合作化小说时,大多对乡村生活细节描写艺术给予认同,而对作家的现实主义精神抱有诸多质疑。我想,至少在这个层面上,尽管陈登科自己坦承只讲了七分的真话,也足以使其从“十七年”合作化小说这一群体中区隔开来,赢得人们更多的关注。
《风雷》小说中提到农村经济衰败凋敝、农民自负盈亏编织苇席等情景,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时已被斥责为“黑暗风”“单干风”,与合作化运动主流方向背道而驰。那么是否意味着与柳青等作家相比,陈登科缺乏基本的政治敏感性?写就《风雷》之初,陈登科已经意识到自己是在“冒险”,
既然看出风险,为什么还要去写呢?在我当时的想法,说来也很简单,我要前进,我要往前走嘛!我是立意要探索一下,社会主义文艺,如何接触真实与现实的问题。[1]383
战争岁月的磨砺使陈登科具备了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对于政治形势不大可能产生误判。强烈的愧疚体验和赎罪意识,迫使陈登科冒着政治风险,作出了他创作历程中第二次“危险的尝试”,这次尝试就此改变了他的人生命运。反观作家柳青,他总是想及时跟上主流政治话语的步伐,终因政治风云的急剧变幻,让谨慎的他迷失了政治判断力,才会在刘少奇即将平反时仍抱病对小说文本作出不合时宜的改写。需要指出的是,《风雷》的写作是有限度有节制的冒险,同时经由小说文本生产的社会学考察,我们还发现由作家、编辑和出版社等力量构成的文本生产组织整体呈现出一种谨慎的避险意识。
二、妥协与坚持:《风雷》文本生产的社会学考察
建国后新中国社会文化思潮呈现出一体化的发展态势,文学领域莫不如此。文学的一体化指的是“这一时期文学组织方式、生产方式的特征,包括文学机构、文学报刊、写作、出版、传播、阅读、评价等环节的高度‘一体化’的组织方式,和因此建立的高度组织化的文学世界。”[3]1881950-70年代小说的生产、传播,是社会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产物,编辑、出版社、文学政治权威、出版审查机构(甚至包括读者)等权力主体在一体化思维的规约下共同参与塑造着小说的审美形态,成为小说文本的潜隐“作者”。通过《风雷》文本生产的社会学考察,不难发现这种特殊的生产范式深刻影响着小说审美形态的生成。
中国青年出版社成立于1950年,隶属于团中央,下设三个编辑室,其中第二编辑室负责文学读物,又称文学编辑室。在文学编辑室主任江晓天的带领下,汇集了萧也牧、张羽、毕方、黄伊、周振甫、王扶等当代颇有影响的编辑。文学编辑室的工作惯例是,先是大家一起审读、讨论小说稿,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然后确定某一人为责任编辑。在他们的努力下,“三红一创”、《李自成》等重要小说相继诞生。1958年初夏,江晓天在了解到陈登科关于《风雷》的创作构想后与其初步达成了签约意向。其间,因稿约的问题还与作家出版社产生了些许争议。三年后,张羽从陈登科处带回了《风雷》(时名为《寻父记》)的铅字印稿。由于文化知识和创作素养的缺失,陈登科的《风雷》结构框架、主题基调、思想艺术方面都需要做大的调整修改,但是中青社认为题材意义重大,符合当时形势需要,于是决定作为重点书稿推出,由江晓天担任责任编辑。“编辑劳动具有评论、发现和医治三种性质和作用”,针对“半成品”就要“花费更多的心血,与作者一起,诊断书稿的‘病症’,商讨‘医治’的办法”[4]。围绕中青社领导和文学编辑室的集体意见,江晓天和陈登科采取流水作业,逐章修改,终于1963年底脱稿排印。
面对农业合作化题材,曾因农村问题受过撤职处分的江晓天是在坚辞不得的情况下担任责任编辑的,自然更加谨慎。江晓天坦言,《风雷》是他“花费时间最长、精力用得最多、最为精心谨慎的”长篇小说稿子。[1]205他把《风雷》排印稿送给众多政治人物征求意见,企图最大程度地规避政治风险。排印稿先后送给安徽省委负责人陆学斌等、国务院农办主任谭震林、刘少奇农业秘书姚力文、中办农村工作问题研究组专家,以及主管文艺的官员林默涵、邵荃麟等人审阅把关,并请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题写书名。其中中办农村工作问题研究组部分专家和姚力文、邵荃麟等人提出了修改意见,总体给予肯定,尤其从政策上看,没有问题。陈登科、江晓天综合审阅意见,花了三个多月时间在京集中修改。即便如此,江晓天仍然迫切地从毛泽东关于《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批文按语中寻找话语支持,在读到毛泽东关于《机会主义的邪气垮下去,社会主义的正气升上来》一文的按语时以为获得了最高指示的话语授权,相应享有了政治的豁免。至此,《风雷》在经历了政治场域内各种权力主体的考量后才正式出版。
《风雷》的文本生产过程,交织着文学与政治的妥协。修改过程中,江晓天、陈登科尽量淡化了文本的阴郁低沉氛围,如:加强祝永康、万寿年等正面人物形象的塑造,压缩有关因春荒引发群众暴动的情节,强化万春芳思想政治觉悟的描写,删除与内部材料中有关事件对号入座的细节,调整容易与1960年代初某些具体社会生活现象等同的描写,修改万春芳上京为祝永康伸冤告状的结尾等等。但是《风雷》的主要构思仍然保留了下来,对乡村经济政治生态的深度揭示(如颇具政治敏感性话语的固执保留、乡村经济社会状况的贫穷困顿、对农民经济行为的同情性理解、家族与乡村政治权力斗争、寓讽于颂的隐语式情感表达)等异质因子仍坚实地矗立在文本里。面对政治化的审美主潮,陈登科、江晓天等人依托朴素的现实主义情怀,选择了妥协,放弃了依附。然而妥协没有带来圆满的结局,还是给《风雷》和他的作者、编辑们带来了悲剧。《风雷》被认为是“中国赫鲁晓夫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的一个罪证”,刮的是“单干风”,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寻的是“中国赫鲁晓夫和他那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5]陈登科、江晓天以及和《风雷》有直接或间接关联的人都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政治迫害。当批评者深文周纳地把《风雷》视为党内高层政治斗争的产物时,再来谈文学的审美价值就显得过于天真了。
三、合奏与独语:《风雷》合作化叙事审美新质的生成
在一体化的政治文化语境中,“十七年”合作化叙事主题、表现形式、形象塑造和情节营构等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固定模式。作家对这种叙事成规的过度尊崇和依附,集体生产出了合作化叙事的高潮。由此,作家在叙事成规限定的千人一语中能否实现新的开拓,发出个体独特的声音,成为考察一部合作化小说是否具备审美新质的重要标杆。而能否突破合作化叙事成规,首先关涉到一个核心的理论问题:即作家如何处理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或说如何写现实。
面对文学与生活,陈登科众人皆信奉文学的生活源泉论。1951年周扬曾赞扬陈登科,“他写出了劳动人民的强烈的真实情感和力量。在他的作品中,简直不是作者在描写,而是生活本身在说话。”[1]13文艺理论权威赋予“生活本身在说话”的角色定位,成为陈登科终其一生坚持的写作律条。柳青提过“三个学校”的观点,“三个学校”指的是“生活的学校,政治的学校,艺术的学校”,其中“基础是生活的学校”,要“培养一种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精神。要想写作,就先生活。”①山东大学中文系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内部资料),1979年,第36-37页。浩然则更直接地表明,要“创作出受人民大众欢迎的好作品,就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到人民大众的社会生活中去,到这个唯一的创作源泉中去不断地改造和提高自己”,“人民大众的社会生活是创作源泉的这一理论,不仅属于颠扑不破的真理,其涵义也是相当深广的。”[2]39
那么怎么理解作家们都为之坚守的“生活源泉论”以及由此引申出的现实性、真实性范畴?这里,笔者无意对真实以及这一总体性范畴下衍生出的生活真实、历史真实或本质真实等亚范畴作进一步的探讨。窃以为首先需要厘清的是,作家心目中的文学与生活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关系构成,在这样的关系思维框架里,作家能否突破叙事成规,一定程度上实现审美价值的超越?陈登科众人的共识是,文学作品应在坚持党性原则和正确阶级立场的前提下,如实地反映现实生活,通过纷繁复杂且充满斗争性的乡村生活的细致描写,揭示出现象背后的历史本质规律和必然性。出于对阶级斗争叙事的迷恋,作家们不可避免地需要提纯、改造生活,把生活纳入党性原则和正确立场限定的成规内,这样一来,小说中的乡村生态往往理想化、片面化。如浩然曾经提出处理文学素材的办法,其中之一就是改造,“把不正确和落后的东西,用我们的原则精神、正确的思想标准加以改造。同时把与之对立的正确的、先进的萌芽状态的东西加以发扬——把不合适的原材料,加上钢,放进我理想的‘模子’里溶解,脱出个全新的‘型体’,树立一个榜样,让做了错事的同志看了以后有所启示,有所自觉,而且效仿它。”[2]34-35这种政治实用主义的考量,必然导致文学审美真实性的缺失。
陈登科对于文学与生活的理解并未脱离政治化审美观的影响,小说也留下了深重的极“左”政治思潮的印痕。我们不做翻案文章,非要把他塑造成反抗者的角色。但是面对农村苦难的现实生活,陈登科还是游走于合作化叙事成规的边缘,突破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思维框架,在一体化书写中通过隐晦的方式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这种独语特质赋予了合作化叙事新的内涵,也是《风雷》区隔于其他合作化叙事文本的重要体现。个别学者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认为“文学采取韬晦和讽刺的形式来表现其流行的时代和社会,住在那儿的人们是不幸的……”。[1]152董之林则指出,“由于叙事中多种因素存在,如果只考虑作品产生的政治背景,阶级斗争模式的小说竟无法与任何一条清晰的政治线索合拢。实际上它游走在各派政治意见的边缘,主要行使的依然是适合人们阅读人生的文学职能,无怪小说无法与规范一一对应。”[6]陈登科在规范之外,凭借深刻反省与自我否定,一定程度上坚持了内心的独立性,在与外界政治达成最大程度妥协的同时表现了自我对现实乡村人生的真切感受。并且,1980年代陈登科对这种妥协作出了反思,“一九五九年我写了《风雷》,现在看来这部作品的真实性只能三七开,百分之三十的假话,百分之七十的真话”[1]387。“生活本身在说话”的文学理念催促晚年的他结构了《三舍本传》,尽管这部小说艺术上有些粗糙,但是深切坦直的暴露性和批判性,在早期伤痕反思小说中亦是颇为醒目尖锐。
陈登科能够在叙事成规之外作出一定的探索,与其性格禀赋和身份认同有莫大关联。性格方面,由于特殊的战争生活体验,他顽强、耿直、机敏、敢斗争、敢说话。身份认同方面,他有着浓厚的农民情怀,陈登科从农民到抗日战士,从战士成为新闻记者,继而走上文学道路的传奇人生,都离不开一个很重要的空间——乡村。深刻的乡村生活记忆和与农民的精神血脉,使他的文学叙事主要聚焦于革命斗争和合作化运动这两个时段的乡村社会。同时他又有着强烈的知识分子意识,他始终热烈地关注现实,与其他工农兵作家相比,创作题材更为广泛,如关注农村革命斗争(《杜大嫂》《活人塘》《淮河边上的儿女》)、城市青年婚恋(《爱》《第一次恋爱》)、水利工程建设(《移山记》)、农村合作化运动(《风雷》)、文革政治批判与反思(《破壁记》)、知识分子人生命运(《徐悲鸿》)、乡村运动史诗(《三舍本传》)。艺术生命更为恒久,新时期以后仍有重要作品发表,也敢于指摘文坛问题,甚至不惧再被扣上帽子。《风雷》对政治化语境中现实与真实性问题的探索实验,不妨看作是作家“游离在叙事成规边缘的有限度的尝试,是在无产阶级文艺新人身份建构与农民作家身份认同间作出的一次妥协”[7]。当建国后老作家创作“迟缓了,拘束了,严密了,慎重了”[8],甚至失语,新作家应景应时之作频出的时候,陈登科这一由主流政治培育成长起来的农民作家,能够在这部忏悔之作《风雷》中发出有限度的隐语,应是陈登科能够凝结为一种文化现象的重要因由。“文学史写作者要贯彻自己的文学观念,并以此剪裁文学事实和历史”[9],因此像陈登科这样的工农兵作家往往被认为难登文学史大雅之堂,文学史少有提及,研究者不屑关注。藉此希望有更多人来关注陈登科和他的小说。
[1]陆志成,主编.中国,泥土里走出个陈登科[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2]孙达佑,梁春水,编.浩然研究专集[G].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
[3]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4]阙道隆.谈谈编辑劳动和编辑家//1985年出版研究年会文集[G].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74-75.
[5]安学江.彻底砸烂中国赫鲁晓夫篡党复辟的黑碑——批判陈登科的反动小说《风雷》[N].人民日报,1968-07-08.
[6]董之林.旧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55.
[7]施学云.从身份认同视角看“陈登科现象”的生成[J].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13(4).
[8]孙犁.谈赵树理[N].天津日报,1979-01-04.
[9]赵普光.书话与现代中国文学的经典化[J].文学评论,20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