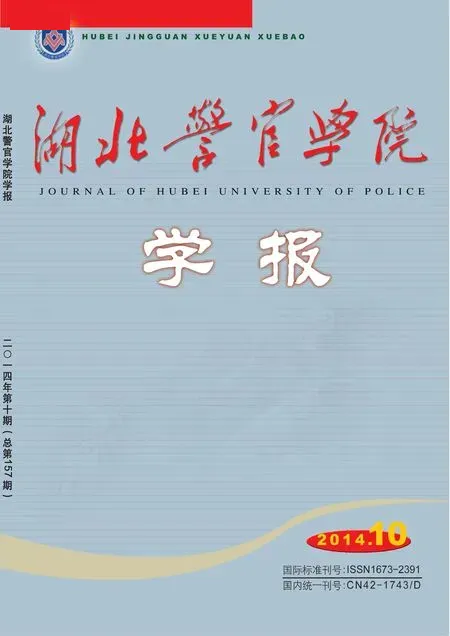冤假错案的成因分析及防范
——重提杜培武案
李夏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江苏苏州215006)
冤假错案的成因分析及防范
——重提杜培武案
李夏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江苏苏州215006)
随着最高院一系列平反冤假错案举措的实施,大量冤假错案得以曝光。冤假错案的防范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应当从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进行反思。侦查机关应当注重文明、科学,检察机关应当做好“守夜人”,法院应当完善刑事准备程序,同时向审判人员注入“无罪推定”的价值理念。防止冤假错案的产生仍需要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当务之急在于向办案人员注入人权保障的价值理念,防范可能出现在各个程序中的潜在危险,保障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抗辩权和沉默权。
杜培武案;刑讯逼供;非法证据;无罪推定;控辩对抗
一、杜培武案:从警察到囚犯,从囚犯到警察
1998年4月22日,昆明警方在一辆昌河面包车内发现一男一女被枪杀,死者身上财物被洗劫一空。调查得知,死者为两名警察,男的叫王俊波,是石林彝族自治县公安局副局长;女的叫王晓湘,是昆明市公安局通讯处民警。通过一系列的工作,死者王晓湘的丈夫、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民警杜培武进入了专案组的视线。在对杜培武进行了一系列的鉴定、测试、检测后,专案组将杜培武确定为重大嫌疑人。杜培武开始一直拒不承认,后来作了有罪供述。在市检察院办案人员依法提讯时,他又推翻了原来的认罪供述,诉称曾遭侦查人员刑讯逼供。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最终于1999年2月5日以杜培武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后杜培武上诉,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该案事实存在若干问题和疑点,改判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2000年6月14日,昆明警方一举破获了杨天勇劫车杀人团伙案,意外发现杀害王俊波、王晓湘的真正凶手。2000年7月6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改判杜培武无罪,当庭释放。
公安机关侦查、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审判机关负责审判,层层把关且法律监督贯穿始终的司法体制为何会在杜培武案中失灵?通过对杜培武案的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在杜培武案中,侦查人员非法收集证据、检察人员未充分尽到检察职责、审判人员带着“有罪推定”的思维定势以及庭审程序中控辩缺乏真正意义的对抗。这是一起侦、检、审司法不公的“合力之作”,也是一个系统性的冤假错案。正是这几个方面的原因导致了杜培武“从警察到囚犯,从囚犯到警察”的生死两重天。
二、文明与沉默:侦查机关的反思
冤假错案一般在侦查阶段就已经埋下祸根。可以说,侦查阶段一旦出现问题,必然会对起诉和审判产生消极的影响,进而导致冤假错案的产生。在侦查程序中,最容易导致冤假错案产生的三个原因是:刑讯逼供、科学证据的采信和沉默权问题。
(一)刑讯逼供
崔敏教授将刑讯逼供分为狭义的刑讯逼供和广义的刑讯逼供。笔者比较赞同崔敏教授关于狭义的刑讯逼供定义的观点:狭义的刑讯逼供,特指在刑事诉讼中,从事侦查、检察和监管工作的人员(包括警察,检察官,监狱、看守所的监管人员以及协助上述人员从事讯问、监管工作的辅助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证人等,采用拷打、体罚、威逼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摧残其身体或实施精神折磨,强迫其作出有罪供述或检举揭发他人罪行的行为。[1]在杜培武案中,侦查人员不准其睡觉、电警棍击打、罚跪等,这些刑讯措施一直不间断地使用,直至杜培武作出有罪陈述。刑讯逼供为何一直存在,并且无法杜绝,这与我们的司法理念以及侦查人员的主观思维有关系。
要想解决刑讯逼供问题,首先要改变以往的硬性指标制;其次要对侦查人员进行教育,使其认识到刑讯逼供的危害性,使“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价值理念入脑入心。当然,还需建立起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机制。“解决刑讯逼供问题,不能仅仅从公安机关的自律角度出发,搞‘运动式治理’,而应当从建立实体性制裁和程序性制裁的双重机制入手。”[2]所谓实体性制裁,主要是从刑法的角度对刑讯逼供受害人予以保护,对刑讯逼供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所谓程序性制裁,是指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刑事证据的采信上对于刑讯逼供所取得的证据予以排除。
(二)科学证据的采信
与原始的仅靠个人经验办案相比,当前先进技术的融入确实提高了侦查人员的办案能力,使一些疑难案件得以解决。杜培武案中,侦查人员对杜培武进行了GPS心理测试,而对于测试的几个与案件有关的问题,杜培武都作了如实回答,但测谎仪上显示杜培武说的为谎言。此外,警犬气味鉴别技术也运用到此案当中,侦查人员用10只警犬对杜培武进行了43次气味鉴别,41次认定杜培武的气味与车上的气味同一。在此案中,还有一些其他先进技术的使用,笔者不再一一介绍。杜培武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先进科学技术如何在侦查中运用的机会。
对于一些犯罪现场的事实,仅凭肉眼是无法断定的,因此必须要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对犯罪现场进行技术侦查,但一些冤假错案的出现使得科学证据的采信备受质疑。张斌副教授认为:“用事后可检验的科学方法标准固定科学证据的生成,用懂得这些方法标准的专家帮助法官评价科学证据的生成。科学方法标准是知识外显的,因而是客观的;专家评价是知识内隐的,因而是主观的;前者构成客观标准,后者构成主观标准。科学证据采信标准的设立,即是这种客观标准与主观标准的统一。在相关的科学领域中,能否寻找到这样的主、客观相统一的判断标准,是科学证据采信疑难能否解决的关键。”[3]笔者认为,这种主客观相统一的判断标准,确实是解决科学证据采信难的一个重要途径。
(三)建立刑事“沉默权”
刑事沉默权(therighttosilence)是指刑事诉讼中嫌疑人和被告人所享有的可以对司法人员的讯问保持沉默而不自证其罪的权利。[4]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沉默权,却规定了与沉默权直接对立的“供述义务”。在我国的侦查阶段,如果犯罪嫌疑人保持沉默而拒绝回答侦查人员的提问,会被视为“抗拒”而受到从重处罚。沉默权的建立不但不会放纵罪犯,反而会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应该看到,沉默权的确立将迫使侦查机关努力搜集口供以外的证据,因而对装备条件、技术手段、侦查策略、侦查人员的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就这一点而言,侦查破案的难度和成本显然是要增加的,但这种增加相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人权而言,是一个承诺实行民主宪政的政府必须予以保障的。”[5]
冤假错案的不断出现让我们对沉默权的建立有了更多的期待,但沉默权的建立却面临着一系列的难题,比如有限的司法资源与居高不下的犯罪率之间的矛盾如何协调,律师辩护的不足与行使沉默权之间的矛盾等。沉默权的建立,有利于加强对犯罪嫌疑人基本人权的程序保障,促进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进一步民主化。从中国法治和社会发展的宏观背景来看,应当尽快建立沉默权制度。沉默权是以正当程序理念为基础的,它所关注的不是结果的正确性,而是过程的正当性。[6]因此,建立沉默权制度之前,首先应当转变“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思想倾向,把刑事诉讼的关注点从案件处理结果转向过程。
三、“守夜人”:检察机关的角色定位
检察制度的产生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在刑事诉讼中监督警察的活动,以保障基本人权;另一方面,通过控审分离、不告不理等原则制约法官的审判,以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独立。[7]在杜培武案中,有两个细节性问题值得注意:第一,市检察院办案人员在对杜培武进行依法审讯时,杜培武推翻原来的认罪供述并诉称遭受刑诉逼供;第二,在庭审中,杜培武强烈要求公诉人调取、出示驻所检察人员当时拍摄的证明刑讯逼供事实存在的照片,但公诉人却称照片丢失。基于此,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做好“守夜人”:
(一)侦查监督
侦查监督是检察院的职能之一,是指检察院对侦查人员在侦查程序中的侦查行为进行法律监督,对侦查人员违法的侦查行为予以纠正,进而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和人格尊严。侦查监督是基于侦查活动基本上由侦查机关封闭进行,不受外部监督和制约,极易发生侵犯犯罪嫌疑人权利的问题而提出来的。侦查监督一方面是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实施法律监督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也是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的重要措施。
与“检警一体化”相比,我国的检警关系是一种“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在现有的司法体系下,我国的检警关系中“分工负责、互相制约”确实对于打击和遏制犯罪、实现刑事司法的重要目的产生过良好的效果。“互相配合”虽然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犯罪嫌疑人在侦诉阶段的防御能力。陈岚教授对“互相配合”的负面影响的描述非常全面:“犯罪嫌疑人被动地进入诉讼,其人身自由又经常性地受到限制,其在侦诉阶段的防御能力本来就非常低下。由于“互相配合”所形成的侦控合力,犯罪嫌疑人在侦诉阶段的防御能力就更为弱小。若在侦查监督不能有效行使的情况下,那么可以说,我国犯罪嫌疑人就具有沦为追诉客体的危险,其在侦诉阶段的主体地位就难以保障。”[8]他还进一步指出,频频发生的冤假错案与“互相配合”的检警关系存在很大的关联。基于此,笔者认为,我国现存的检警关系应当进行调整,同时加大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力度。
(二)检察官的客观性义务
我国检察机关的角色定位,对检察官履行职责有客观性义务的要求。林钰雄先生认为:“检察官在刑事诉讼法上,与法官同为客观法律准则及事实正义的忠实公仆,‘毋纵’之外还要‘毋冤’,‘除暴’之外还要‘安良’,并非也不该是片面追求攻击被告的狂热份子。”[9]有的学者对检察官的客观性义务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检察官应当尽力追求实质真实;在追诉犯罪的同时要兼顾维护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通过客观公正的评价案件事实追求法律公正地实施。”[10]客观性义务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理想化的概念,其实现程度是有限的,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要求。在审查起诉阶段的客观性义务要求,检察官在收集证据时,不仅要收集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的事实和证据,还要收集证明犯罪嫌疑人无罪、罪轻的事实和证据;在保护被害人权利的同时,还要保护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在杜培武案中,有利于杜培武的证据并未收集,明显违背了检察官的客观性义务。
如果检察官收集和审查杜培武案证据之时遵循客观性义务,将证明杜培武案件刑讯逼供的照片予以展示,全面、客观地审查杜培武案的证据,那么完全可以将该冤假错案阻断在审查起诉阶段。我国虽然将检察官定位为客观中立的地位,但法律并未对其实现作出具体规定,违反客观义务的后果也没有明文规定,使得检察官客观义务难以实现。因此,为了有效遏制冤假错案的出现,我国应当具体规定检察官的客观性义务,并建立相应的制裁制度,使检察官的客观性义务成为实现司法公正的真实要义。
四、最后的救济:审判需要“对抗”
杜培武案中,法院的一些行为使我们对法院的权威性产生了动摇:当杜培武在庭审中申辩没有杀人并遭受了刑讯逼供时,审判长居然要其拿出证明其遭受刑讯逼供的证据,最后竟然以“无充分证据支持”为由驳斥本案辩护人的无罪辩护。法官应当是一个乐观理性主义者,乐观、理性和客观应当是其在推定过程中坚持的底线。审判机关如此对待杜培武有关刑讯逼供的辩护意见,如此草率处理无罪的举证责任,是值得深思的。笔者认为,在审判阶段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防止冤假错案的产生:
(一)审判人员“无罪推定”思想的注入
“违法诱供、刑讯逼供以及其他非法取证、任意限制人身自由等官方行为均是怀疑有罪的心理不受法理理性制约的结果。可以想见,拒不承认无罪推定原则,只能放纵官方非理性行为。”[11]在杜培武案中,侦查人员“怀疑有罪”的办案思维以及审判人员“有罪推定”的思维定式正是导致杜培武冤假错案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疑罪不敢从无”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来自新闻媒体的压力,也有来自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方面的压力,还有党政机关领导的干预和来自被害人家属、亲友的压力。这些因素使得法院“疑罪不敢从无”。
如何面对“无罪推定”的阻力,马贵翔教授指出,“有罪推定”是中国传统法文化的组成部分,无罪推定在中国是一个新概念,除了加强对公民乃至司法人员的宣传教育力度外,根本的还要靠依法治国的逐渐推进和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12]疑罪从无判决所导致的非理性案件毕竟只是少数,在日益注重程序正义的今天,程序公开、公正的逐步实现,我国大多数当事人及其家属对法院的判决还是能够接受的。无罪推定之所以难以贯彻,是因为司法人员头脑中既定的“有罪推定”思维的抵触。
无罪推定能够克服确证偏见,而确证偏见的克服有助于我们防止冤假错案的产生。杜培武虽然已经无罪释放,但杜培武案的出现对杜培武本人而言是伤害极深的,对司法体制而言也是值得深思的。新刑事诉讼法对无罪推定原则的完善是我国司法的一大进步,也彰显了我国司法机关坚持无罪推定的勇气和信心。在培养程序正义的观念、规范程序正义操作和完善程序正义的有关立法正在不断出台和完善的年代,如果司法人员在现阶段办案的过程中坚持人权保障的内心信念,敢于同无罪推定的阻力作斗争,那么无罪推定的彻底实现将不远矣。
(二)控辩对抗
控辩对抗是指案件移送法院以后开始,直至整个案件结束的这段过程中的辩护方与公诉方的对抗。辩护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诉讼职能和基本权利,其基础权是辩护权,与检察机关的控诉权相对应。“辩护权的科学行使,确实有利于司法机关审理查明案情和事实真像,作出正确裁判,防止冤假错案,保证司法公正,体现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13]辩护制度的设置以及辩护权的行使对于冤假错案的防范至关重要。但在司法实践中,辩护人在从事辩护的过程当中经常遇到阅卷难、调查取证难等各种阻力,这些因素使得被告人的辩护权并不能得到有效的行使。
控辩真正对抗的前提是控辩平等,控辩平等的价值基础在于个人本位主义,即个人与国家在法律地位上是相同的。刑事诉讼中国家与个人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不能以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为逻辑前提,认为控方代表的是国家利益,辩护方代表的是个人利益,就推导出控诉方的诉讼地位高于辩护方诉讼地位的逻辑结论。[14]控辩平等所要求的不仅仅是法律地位的平等,还有“武器”平等和平等保护,真正实现辩护权与控诉权的平等对抗。
一个能够与控诉权相抗衡的辩护权,必须要有相应的制度保障来弥补两者在事实上的不平衡状态,其举措可分为两种:一是对控诉权的行使叠加层层障碍,以增加其指控成功的难度;二是加强辩护方自身能动性,以能够与控方进行真正的抗衡。[15]在司法实践当中,一方面对辩护人的辩护权予以充分的保障,使得辩护人敢于同控诉方进行对抗;另一方面,应当对控诉权进行一定的限制,使控诉权的行使得以规制,不至于违背控诉权设立的初衷。
(三)完善刑事审前准备程序
现代刑事诉讼中,国家权力介入诉讼活动的深度、广度不断加强,审前准备对案件处理结果的影响力不断增大。“是否有许多无辜的人被判断有罪则可能取决检察官对他们案件的甄别程度和细心。如果检察官从来就没有起诉过那些事实上无罪的人的话,那么即使证据标准可能如同人们所期望的那样低,仍然不会有无辜者被判定有罪。相反,如果检察官不进行甄别,而是对任何被指控的人都提出起诉的话,无辜者被判有罪的比例也许就很大,因为陪审团只需要合乎情理地肯定被告有罪就可判定他有罪。”[16]波士纳的这些话是在告诫我们刑事审判前程序的重要性。
即使刑事审判前程序将真正的犯罪人推入了庭审的视野,决定犯罪人是否受到惩罚的仍然不是法庭的审理活动而是审前活动。可以这样说,真正决定防止冤假错案在审判阶段产生的阶段是审前准备阶段。笔者认为,若要防止审判阶段的冤假错案,应在审前程序中完善以下内容:第一,增加法院裁定驳回公诉的权力,即当法院认为公诉机关移送的案件证据不足或者事实不清时,直接以裁定的形式将案件驳回。第二,增设当事人非法证据排除的动议权,即当事人认为存在刑讯逼供等违法的侦查行为或程序时,有权向审判机关申请动议,排除违法取得的证据。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防止冤假错案的产生。
[1]崔敏.刑讯考论:历史现状未来[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5.
[2]顾永忠.中国疑难刑事名案程序与证据问题研究(第一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5.
[3]张斌.科学证据采信的基本原理[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
[4]龙宗智.英国对沉默权制度的改革以及给我们的启示[J].法学, 2000(2).
[5]孙长永.侦查程序与人权:比较法考察[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0:374.
[6]冀祥德.控辩平等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129
[7]陈国庆.检察制度原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103.
[8]陈岚.我国检警关系的反思与重构[J].中国法学,2009(6).
[9]林钰雄.检察官论[M].台北: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31.
[10]程雷.检察官的客观义务比较研究[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05(4).
[11]张成敏.论无罪推定的逻辑基础[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S1).
[12]马贵翔.刑事司法程序正义论[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 204.
[13]王顺义.辩诉对抗论[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236.
[14]冀祥德.控辩平等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100.
[15]李昌盛.论对抗式刑事审判[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280.
[16][美]波士纳.法理学问题[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274.
D631.2
A
1673―2391(2014)10―0025―04
2014-05-19 责任编校:边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