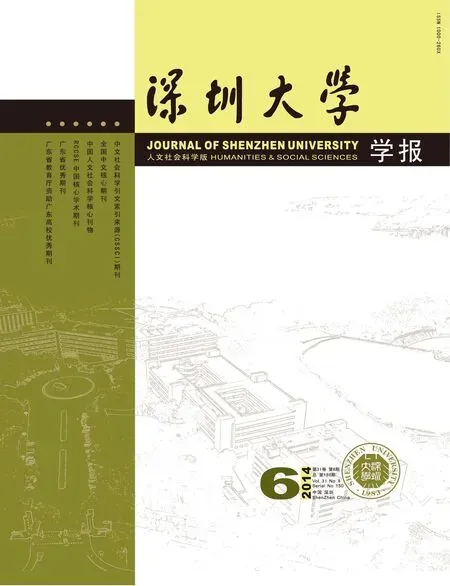近代日本西化的路径选择与中日甲午战争
郑毅(北华大学东亚中心,吉林 吉林 132013)
近代日本西化的路径选择与中日甲午战争
郑毅
(北华大学东亚中心,吉林 吉林 132013)
明治维新开启了日本近代社会全面西化的大幕,天皇在日本西化过程中成为传统与西化的合体,并化身为帝国日本的缔造者和象征。福译谕吉等知识人的启蒙思想和民族主义意识成为催熟日本社会西化的助推剂;英国政体与德国的军制成为日本西化的模范样本,近代日本以对外侵略战争方式完成了构建帝国日本的主要路径选择,在日本完成全面西化的同时,也产生并固化了对亚洲尤其是中韩两国的蔑视型认知体系。
明治维新;西化路径;西化模式;亚洲认识;甲午战争
明治维新对日本意味着什么?对东亚世界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似乎有多种答案和解释的历史问题。我以为明治维新是日本制度文化层面西化的启幕,是日本近代国家性格塑造、定型的原点。
明治维新作为一场社会变革运动,将日本从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封建国家改造成资本主义国家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关键环节。若是从塑造近代日本的国家性格视角来审视的话,由明治维新运动开启的全面西化的国家发展路径,20多年的西化过程将近代日本塑造成为同时兼具舞者与武士两个面具的国家。一个国家形象是如同舞者趋炎附势在西方列强之间周旋、寻找最强者与之结伴起舞;另一个国家形象是恃强凌弱,危害邻国、称霸东亚的军国日本。
从明治维新到中日甲午战争乃至之后的日俄战争,是近代日本社会西化过程的三个重要节点,近代日本的国家性格与发展战略则是基于日本西化的路径选择而定型、固化的。
一、天皇成为传统与西化的合体
日本社会从科学文化层面对西洋文明的仰慕和吸收,可以上溯到18世纪70年代的兰学运动,据1852年出版的《西洋学家译述目录》统计,1774年至1852年的78年间,日本翻译欧洲的医学、天文、历法等书籍多达470余种,从事翻译西洋书籍的学者有117人[1]。
日本社会从制度文化层面的西化,则是从明治维新之后真正开始的。明治新政府推出的 “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三大国策等都强烈地表现出一种迫切西化的社会心理。同时代外部世界的列强争雄为日本的西化提供了模仿的对象和发展空间。19世纪最后的30年,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西方列强对海外殖民地的争夺达到白热化程度,日本以西化为目标的国家发展战略正好与之相契合,从明治维新伊始日本用了20多年的时间初步完成制度文化层面的西化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日本的明治天皇发挥了重要的聚合社会的作用,使近代绝对主义天皇制的构建过程与日本社会的全面西化进程相重合,“第一,如果没有天皇的存在,就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幕藩体制瓦解和中央集权国家的确立,王政复古,意味着借助天皇的名义解体了武家和公家结合的传统体制;第二,作为文明开化的推动者,天皇率先断发、喝牛奶,着洋服、食牛肉,明治天皇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第三,正是因为天皇确保了在意识形态上的主导权,才使急剧的西洋化得以正统化,并因此确保了天皇在近代日本的统治权。”[2]所谓“和魂洋才”是日本西化的一个模式,而天皇则是“和魂”的内核。
日本社会对西方文明延续了从“顺从”到“吸收”的传统外来文化吸收方式,以乖巧顺从的态度,贪婪吸收之,全面融会贯通之。“从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乃至大东亚战争,近代日本的基本国策就是通过模仿西方的思想文化强化自己,进而跻身于西方列强之林。 ”[3]
“日本经过明治14年(1881年)的政变确立了萨长藩阀的权力统治,并明确选择了普鲁士式君主立宪的天皇制国家道路,由此开启了日本帝国的征程。”[4]
明治天皇对近代日本社会而言具有怎样的存在感,经过明治维新的西化过程,明治天皇不仅仅是作为精神领袖而存在的,他实际上在扮演着引领日本构建帝国的政治领袖作用。为建设近代海军,1887 年3月,明治天皇带头捐内帑30万日元,连续拨捐6年,并要求文武官员捐缴薪俸1/10,作为海军造舰购船资费。
日本前首相吉田茂认为明治天皇是日本取得两次对外战争胜利的关键因素,称:“借此,日本方能够在帝国主义时代勉强摆脱它所处的严峻的国际环境。不幸,日本不得不进行日清战争和日俄战争,在这两次战争中,由于明治天皇发挥了他的领导才能,并且集中了与之相呼应的国民活力,日本方能够一反世界的预料而在两次战争中都取得了胜利。”[5]
天皇制作为日本传统价值观的内核,发挥了引领国家整体西化的领袖作用,明治天皇成为帝国日本的缔造者和化身。同时代的中国社会也追求西化,曾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西化路线。福泽谕吉曾指出中日两国西化的差别所在,“支那人迟钝,对于(西洋)文明一无所知,近来有少许采用西洋之物,但仅止于其器之利用,对文明之主义如何则不加考问。”[6](P49-50)的确,当时的中国社会中的所谓“中学为体”是儒学思想的空洞化泛指,缺乏具体而明确的内容。慈禧太后是政治权力中心,但无法成为社会精神的核心。中国的洋务运动侧重于器物层面上的西化,在制度文化层面上未有触及,这是中日两国西化过程中最本质上的差异所在。
二、思想意识的西化助推帝国的构建
1871年12月,岩仓使团历时1年零9个月遍访考察欧美12个国家。新政府核心成员的集体游学是日本明治政府彻底拜西方为师的重要环节,极大地影响了近代日本社会的历史进程。所谓“始惊、次醉、终狂”是岩仓使团成员的共同感受。如果说英法等国的工业化为日本实施“殖产兴业”为代表的经济近代化提供了模仿样板的话,那么普鲁士容克贵族的铁血外交理念,则更多地刺激了日本固有的扩张意识。德国首相俾斯麦对岩仓使团曾提出如下忠告:“方今世界各国,虽以亲睦外交礼仪相交,但皆是表面含义,于其阴私之处,则是强弱相凌,大小相欺……”德国参谋总长毛奇明确地告诫来访者,“法律、正义、自由三理虽可保护境内,但保护境外,非有兵力不可。万国公法者,乃是小国之事。至于大国,则无不以其国力来实现其权利。”[7]
一个社会的转型时期,思想意识的先行是前提和基础。思想意识的西化和帝国化是日本近代社会全面西化的领航者和推动者。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对国际交往的认识与德国政治家有完全相通的强权理念,“各国交际之道只有两条:消灭别人或被别人消灭”,“百卷万国公法不如数门大炮,几册友好条约不如一筐子弹。拥有大炮弹药并非为主张道理所准备,而是制造无道理的器械。”[8]
思想家德富苏峰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提出了“大日本膨胀论”,鼓动日本要成为“文明的引领者”、“人道的扩张者”、“文明的使者”,肯定日本对清战争的正当性。
福泽谕吉明确提出“脱亚论”,主张“为今之谋,我国不可等待邻国开明而期盼振兴亚洲,宁愿脱其伍,与西洋文明国家共进退,至于其对待支那、朝鲜的方法,也不必因为是邻国而要特殊加以解释,只能按照西洋人对待两国的方法处理之。”[6](P240)
以文明启蒙自诩的思想家们催熟了日本社会蔑视中韩邻国的国家优越感,而狂热追求比肩西方列强的自卑情结,促使日本不断在对外侵略战争的胜利之中寻找到一种成就感。近代日本整个国家和社会蜕变成一部高效的战争机器,思想家们的文明启蒙理论和国权扩张主义主张实际上起到了润滑的助推作用。福泽谕吉的文明观和脱亚论,将日本化身为西方文明的优等生,而中国、朝鲜等邻国则是与西方文明背离的愚昧国家,日本侵略征服这样的邻国是完成文明传播的正当行为,日本在东亚社会里应当且必须承担这样的国际责任。有学者指出:“福泽谕吉提出的‘脱亚论’曾经在19世纪末和本世纪前半期留下了沉重的历史遗产。‘脱亚论’不仅引导日本走上了宰割和瓜分亚洲邻国的道路,给亚洲邻国造成了无数灾难,而且它还导致日本在其后走上穷兵黩武的道路,一味迷信‘实力政策’,为其后走上对外扩张侵略的道路提供了理论依据,成为日本民族最终在本世纪走上悲剧道路的思想基础。”[9]近代日本知识人阶层为帝国日本的霸道国家行为装饰出王道的外衣,实为缺少独立思想力的一种病态表现。德富苏峰在所发表的“大正的青年和帝国的前途”一文中曾对两次对外战争赋予这样的历史使命,他称:“日清战争是日本国民的帝国的觉醒时期,而日俄战争则是(日本)帝国被世界认可的时期。”日本近代知识人将日本的近代化成功与对外战争的胜负联系在一起,用战争的胜负证明日本西化道路选择的正确性和合法性。这样的文明意识无疑成为日本从帝国转化为军国日本的推动力。
美国学者西里尔·E·布莱克等人在对比近代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发现并得出这样一种认识,“在19世纪,有些人认为,在战争中取胜比在市政建设方面取得的成绩,更能证明现代化的成果。日本和俄国都把发展陆军和海军放在非常优先的地位”[10]。《马关条约》中的赔款割地条款,助长了日本社会以战争立国的强权意识,而日俄战后日比谷骚乱又从另一个侧面验证了日本社会对战争附属品的极度渴望和沉迷。
三、以英为师、以德为范的西化模式
政体、外交等领域以英美为师,军事领域以德为范,直接复制西方列强的各自强势制度与文化是日本西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英国作为19世纪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在近代国际体系中具有分量极重的话语权,它也是西方列强中第一个承认明治政权合法地位的大国,在西方世界具有示范效应。明治政府在建设以西方国家为样本的近代国家过程中,英国的影响和印记是极为深刻的。例如,明治4年(1871年)政府雇佣的外籍顾问中有119名英国人、16名美国人、10名法国人;各地方政府雇佣的外籍顾问中有50多名英国人、25名美国人、19名法国人,英国籍顾问专家占绝对多数。明治时期日本外务省是聘用英美籍顾问最多的部门,日本外务省的外交电报也全部采用英文,与西方各国的交涉文案同样依赖英美籍顾问来负责。因此,明治时代出现以亲英美为特征的霞关外交也是很自然的事情,西化过程中强势的英美基因决定了近代日本对英美结盟、协调的外交性格。
近代日本海军从建立伊始就明确地以英国式近代海军为模版实现英国化,甲午战争中任“浪速号”舰长。日俄战争时期任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的东乡平八郎曾留学英国8年,是绝对的亲英派。日本海军士官的培训是由英国教官担当,日本学者内山正熊甚至有这样的结论:“英国海军是养育日本海军的父母。”[11]中日甲午战争前,日本为加速海军近代化大量购置西式战舰,特别是订购英国军舰,日本联合舰队的主力舰全部都是英国建造的军舰。到日俄战争时也是如此,日本海军主力舰队全部为英制战舰,巡洋舰队的主力舰也全部是英制战舰,有少量法、德制造舰只作为补充配置。无一艘日本自己建造的军舰参战[12]。
与外交领域追随英美的战略相对应,日本在“富国强兵”确立近代军事体系过程中英式海军和德式陆军成为建军的铁律。
明治3年(1872年)日本陆军领袖人物桂太郎、大山岩访问德国后,将幕府以来沿袭的法式军制改变为德式军制,大力招募外国教官帮助日本建设近代化的陆军体制,尤其是德国籍军事顾问梅克尔最受器重,德国成为日本陆军改革的模范国家,德国军事制度、战争理论和战法等皆被日本效仿。
1878年12月,日本以德国为军事改革的模版,废除陆军参谋局,设立陆军参谋本部,本部长由“敕任”将官担任。参谋本部不受陆军卿和大政大臣的管辖,直接隶属于天皇。“日本参谋本部的设立,意味着日本形成了以武力推行对外政策的权力机构。”[13]
普鲁士在俾斯麦首相领导下以“铁血政策”通过三次对外战争,完成了德国的统一,并奠定了德国在欧洲大陆的强国地位。德国成为欧陆大国的成功经验对日本有很强烈的示范效应,日本参谋本部成立后就积极筹备对中国大陆的侵略战争准备,1887年2月推出的《征讨清国策案》可以视为日本正式准备对华开战的计划书,其中明确提出:“欲维持我帝国之独立,伸张国威,进而巍然立于万国之间,以保持安宁,则不可不攻击支那,不可不将现今之清国,分割为若干小邦……英国保持富强,要在不可无此印度。也即我当掠取土地于支那,以之为附属防御物,或以之为印度也,更何况彼我之间有终究不能两立之形势……最当留意者,适值时运,故而当乘其尚在幼稚,折其四肢,伤其身体,使之不能活动,始可保持我国之安宁,维持亚细亚之大势也。”[14]
征服朝鲜,是日本向外扩张的第一步,历史上就是如此。明治时代“征韩论”也同样是主基调,山县有朋将朝鲜提升为日本的利益线,称“我邦利益线之焦点,实为朝鲜。”[15]参谋本部德国籍顾问梅克尔进言朝鲜“是指向日本心脏的匕首”,必须确保不能由第三国控制。德国籍军事顾问的军事观点进一步强化了日本控制朝鲜的紧迫感。
德国因素在日本近代陆军发展过程中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存在,日本陆军的这种浓厚的德国情结,也是日后在20世纪30年代军部势力挟持政府放弃亲英美政策,选择日德结盟的重要历史原因。
四、战争成为构建帝国的阶梯
通常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在正处于上升阶段时,大多数是采取顺应周边国际环境,尽可能地避免同强于自己的一方发生正面冲突,以时间的长度来增强自身国力的厚度。但近代日本帝国的崛起历史有悖于近代历史上的大国崛起规律,它是以一种急迫的心态,在短短十年间就连续发动了两次极具冒险性的对外战争,以飞奔的速度跻身帝国主义俱乐部,并完成了帝国的构建过程。
正是由于在短时期内就通过非常规方式构建了一个帝国,明显缺乏历史的沉淀和思想意识的扬弃,因此,近代日本帝国的意识中更多地是充斥着对侵略战争的依赖和迷恋,刚性的军国主义倾向浓厚,对外扩张的疯狂程度和欲望尤为强烈。当日本的对外扩张政策与英美的亚洲殖民利益相协调时,英美就自然成为其同盟者和帮凶,近代日本能够在两次赌国运的战争侥幸获胜,实有赖于此;但当日本的扩张势力危及到英美的亚洲利益时,英美就会限制和规范日本帝国的疯狂行为,近代日本外交传统中的亲英美协调主义,就是为平衡这种矛盾而产生的。
明治政府在全面向西方文明靠近的过程中,最先模仿并长期运用的就是以战争方式,向东亚邻国索取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所享有的帝国权利。从此,日本成为奇特的国家,一方面它与西方列强间有不平等的国家间条约存在;另一方面它又迫使东亚邻国接受同样不平等的国家间条约。这种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两种国家角色的并存与不断转换,使日本在成为帝国过程中其国家性格具有矛盾性和分裂性。
“日本领袖中有许多人都视全球国际秩序为‘西方/其他人’或‘现代/非现代’这种文化二元对立的地缘政治学表达,将‘文明’国家视为一个双重系统,一方面是其活力和技术能够使它建立起帝国,而另一方面则是那些‘原始’社会变成它的殖民地。日本领袖们要把自己的国家放在前面那个集团中……将日本提升到那个美妙的 ‘大国’圈子中的第二种方式,就是让它的领导人扮演帝国主义政策中两种笨拙相连的角色:一是帝国建构者,一是那些落后民族的文明开化者。即使没有朝鲜作为外国危险来源的那个一直存在的战略问题,朝鲜如此靠近日本,也使得它成为这种帝国主义进取的首选目标。”[16]
日本前首相大隈重信曾坦言,“对东方,我们乃西方文明之说明者;对西方,我们乃东方文明之代表者……此乃我国国民之理想,日本帝国之天职也。”[17]
甲午战争胜利对近代日本而言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使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非西方的强大帝国。这种国家角色的突然转换,使日本社会上下都产生出非理性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的产生主要是来自西方国家对日本的认可,在日本冒险发动侵略战争的前夕,1894年7月16日,英国为联手日本遏制南下的沙俄,在伦敦同日本签订《日英通商航海条约》,废除日本城市内分隔的飞地似的英国租界,并规定五年后取消治外法权。随后,由于日本在对清战争中的获胜,西方各国效仿英国纷纷同日本进行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谈判。日本在完成凌驾于东亚邻国之上的同时,也附带取得与西方各国比肩的国际地位。
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不仅颠覆了东亚的地缘政治传统,而且还彻底改变了中日韩三国在近代东亚历史上的发展道路。“日清战争成了日本资本主义的跳板。清国由于借用外债来偿付巨额赔款而迅速加深了殖民地化。与此相反,日本则由于巨额赔款的流入,一面进行以扩充军备为核心的产业革命,另一方面获得了采用金本位制的资金,也就拿到了参加以伦敦为中心的国际金融市场的通行证。日本资本主义依靠地理上靠近中国和拥有较多的专管租界,取得了比欧洲列强更为有利的条件,登上了开拓中国市场的新旅程。”[18]
中国学者武寅指出,“对于发动了这场战争的日本来说,本应在战争结束后进行一番彻底的回顾与反思,然而,此时的日本却陷入战胜的亢奋和受制的愤懑双重刺激下不能自拔。巨大的战争红利使它赌红了眼睛,更加坚信战争的威力,而列强的‘逼宫’则使它受辱,它不想就此善罢甘休,发誓要卧薪尝胆,报这一箭之仇。也正因为如此,甲午战争成为日本坚持要走武力称霸道路的负面开端,它使日本从此铁下心来,沿着这条通往灭亡的道路越走越远。”[19]
对外战争胜利的狂喜之下,整个日本社会充斥着蔑视中韩邻国的优越感意识。福泽谕吉甚至将这场对外战争上升到是“文明对野蛮”的圣战高度。军国主义情境下的狂热爱国主义,使日本知识界也深陷狂热之中。德富苏峰认为日本战胜中国给了日本过去不曾受到的国际社会的尊敬。他说,现在西方认识到了“文明不是白人的专利”,日本人也有“和伟大成就相符的特征。”他对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赋予了帝国主义式的合理解释,称:“我国之所以采取此种方法(对华战争),目的在于日本国的对外开放。对他国发动战争,目的在于给予世界上的愚昧以一大打击,把文明的荣光注入野蛮的社会中去[20]。”
日本著名民本主义者吉野作造在《日清战后的支那观》一文中写道:“……然而,打起仗来一看,支那是意想之外的柔弱,我国在列国环视下堂堂正正地大获全胜,轻而易举博得了意外的大捷。这对我国来说,固然是莫大的喜事和福分,另一方面却又大大地激起我国人的自负心,酿成一反旧态、轻侮邻邦友人的可悲风潮……尤为引人注目者,是我国在战争中为鼓舞、振奋国民的敌忾心而广泛推广了‘惩膺猪尾奴’的歌曲,它像一剂过量的猛药,使蔑视支那的风潮格外激烈地流行开来。”[21]
陡然产生的民族优越感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就是对中国人及其文化的蔑视。这是从原来千百年来对中华文化的尊崇感和依附中挣脱出来后的一种极端表现,这种对中国的蔑视感不仅流露在像福泽谕吉这样著名知识人的笔端,而且它是以一种通俗文化的形式流行在日本社会的底层,对造就整体国民的对华蔑视意识具有莫大的影响力。
知识界领袖的民族优越理论,辅之以流行的通俗文化熏陶下的国民意识,日本近代的蔑视型对华观,以及连带产生的亚洲认识就这样在侵略战争这一特定背景下发酵、酝酿直至形成。甲午战争成为近代日本社会蔑视型对华认知体系形成的固化剂。
西化也即近代化,是19世纪后半期世界的一种潮流和趋势,日本追求西化本身也是顺应当时的世界潮流,“文明开化”、“殖产兴业”政策本身对日本社会的近代化是比较成功的西化政策,而“富国强兵”则是建立在对中韩两国侵略战争基础上实施的损人利己的错误国策。日本自身西化的所谓“成功”是借助甲午战争来验证的,日本帝国是建立在以中韩两国为殖民地基础上实现的,以阻断中韩两国的近代化进程为代价日本实现了“脱亚入欧”。
[1](日)辻善之助.增订海外交通史话[M].东京:内外书籍株式会社,1930.747.
[2](日)岩波新书编辑部.日本近现代史·10·日本の近现代史をどう見るか[M].东京:岩波书店,2010.36-38.
[3](日)土居健郎.日本人的心理结构[M].闫小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中文版,29.
[4](日)子安宣邦.两个六十年与日中关系[A].读书杂志:亚洲的病理[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173.
[5](日)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M].孔凡,张文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25.
[6](日)福泽谕吉.福泽谕吉全集:第 10卷[M].东京:岩波书店,1961.49-50.
[7](日)久米邦武.特命全权大使米欧回览实记:第1卷[M].田中彰校注.东京:岩波书店,1985.82-83.
[8](日)福泽谕吉.通俗国权论前篇[A].福沢谕吉全集:第4卷[C].东京:时事新报社,1898,51-52.
[9]高增杰.“脱亚论”的形成——福泽谕吉国际政治思想变化轨迹[A].日本研究论集:4[C].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403.
[10](美)西里尔·E·布莱克.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一份进行比较的研究报告[M].周师铭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175.
[11](日)内山正熊.日本における亲英主义の沿革[J].法学研究,37,(12):230.
[12]内山正熊.日清战争百年——先と影[A].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国际政治:第109号,终战外交と贺卡后构想[C].1995. 145-146.
[13]米庆余.近代日本的东亚战略和政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09.
[14]米庆余.日本百年外交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9.
[15](日)大山梓.山县有朋意见书[M].东京:原书房,1960.185.
[16](美)康拉德·托特曼.日本史:第二版[M].王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324-325.
[17](日)大隈重信.新日本论[A].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走向亚洲的航踪[C].张学锋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8.
[18](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1853—1972:上册[M].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293.
[19]武寅.甲午战争:日本百年国策的负面开端[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07-25.
[20](日)德富苏峰.战争与国民[A].和田守,竹山护夫,荣泽幸二.近代日本和思想:2[C].东京:有斐阁,1979.32.
[21](日)河原宏.近代日本の亚洲認識[M].东京:第三文明社,1976.41.
【责任编辑:陈红】
【】【】
The Westernization Path of Modern Japan and the Sino-Japanese War
ZHENG Yi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North China University,Jilin,Jilin 132013)
The overall westernization of modern Japanese society started from Meiji Restoration.The emperor became the fusion of tradition and westernization in the course of westernization,and was incarnated as the founder and symbol of imperial Japan.Cultural elites such as Fukuzawa Yukichi brought the ideas of enlightenment and nationalist consciousness to Japan,which accelerated the westernization of Japanese society. British monarchy and German military system became the model of Japan's westernization.Modern Japan established himself as an Empire through waging invasive wars.Moreover,In the process of westernization,Japan also generated a disparaging cognitive system for Asian neighbor countries,especially China and South Korea.
Meiji Restoration;Westernization path;Westernized pattern;understanding of Asia;the Sino-Japanese War
K 256.3
A
1000-260X(2014)06-0147-06
2014-10-17
郑毅,法学博士,北华大学东亚中心主任、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从事中日关系史、日本外交政策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