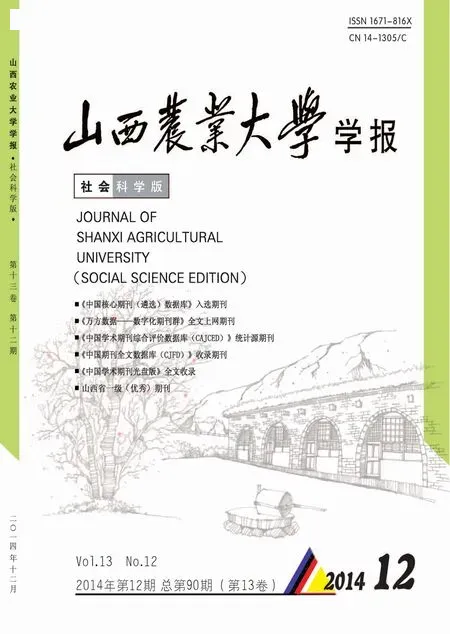池莉小说爱情观的道德悖论
李金泽
(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中文系, 安徽 亳州 236800)
池莉小说爱情观的道德悖论
李金泽
(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中文系, 安徽 亳州 236800)
“不谈爱情”是池莉的一个文学命题,也是她对现实生活的价值判断。在池莉看来,爱情是超离现实生活的,本真的生活现实中只有实实在在的婚姻和日子,没有高雅的爱情。池莉以此表达对现实生活中世俗男女的同情和启蒙,突显存在就是强者的人生哲学。这种哲学带给世俗的是冰冷的夫妻和婚姻观念。池莉的这种爱情——婚姻观中存在着道德悖论,降低了文学对现实的审美价值,带来文学对现实生活的错误认知,彰显了池莉小说媚俗化审美取向。
池莉小说;不谈爱情;生存哲学;道德悖论
池莉作为新写实小说的代表性作家,曾经为新写实在文学界的立足奉上多篇力作。她的小说多涉及爱情与婚姻的对立主题。作者以“新孩子”的“新眼光”发现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生活的本真相,从平凡人物的生活中得出不谈爱情的命题。围绕这一命题,池莉创作了《不谈爱情》、《你以为你是谁》、《绿水长流》、《太阳出世》等与爱情有关的小说,以此来支撑自己的命题:“我编这个故事仅仅是为了让我对爱情的看法有个展开的依托”(《绿水长流》)。在池莉看来:贫穷人家夫妻是没有爱情的,贫贱夫妻百事哀;政治家们也没有爱情,高级知识分子、体面的国家干部,都没有爱情可言,他们只有婚姻。因此,爱情不存在于现实生活之中。在金钱拜物的当下,爱情只是一种幻想,在现实生活中,取代爱情的是普通而平淡的生存以及多种形式的婚姻,不管用什么方式,只要求取得生存,相处轻松愉快,就是幸福。池莉因此也获得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广大读者的钟爱。
但是,在池莉的文学视野中,建立在对世俗不假分辨基础上的存在性认同,无疑用存在哲学把爱情的光环淘洗殆尽,只剩下物质与肉欲的男女婚姻。在池莉看来很平常、很正常的这种婚姻形式,实质上已经被淘空了夫妻恩爱的婚姻意义,而成为男女互相利用、互相依靠的一种生活手段,再也与爱情无关,因而池莉说“不谈爱情”。池莉的这种爱情——婚姻观适应了社会转型期价值观念模糊不清、丢失自我的一代人的荒芜心理,而且,成为一个时代撕裂爱情与婚姻的道德关联、认同庸俗现实存在的代表性观点。美好爱情与庸俗婚姻在道德伦理上形成悖论。
一、不谈爱情:逃避理想的精神自慰
像池莉一样,上世纪80年代,很多知识分子在经历了对理想、崇高、宏大政治叙事的颠覆之后,很快迎来了价值多元、金钱拜物风气日盛的社会转型期,先前所接受的远大的理想、信念和美好的理想、向往,在短时间之内难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存在的形式。面对权利、金钱的现实诱惑,他们迷惑了,并且对此前所接受的传统的道德伦理、理想信念,甚至人生信仰,都产生了怀疑,“我终于渐悟,我们今天的这生活不是文学名著中的那生活。我开始努力使用我崭新的眼睛,把贴在新生活上的旧标签逐一剥离。”[1]
池莉所“剥离”的是现实生活外衣所披挂着的旧思想、旧观点,这是池莉作为具有新思想、新审美观点作家的优越品格和独创之见。
然而,在使用“新眼睛”发现新问题的同时,池莉对传统的爱情观也进行了“剥离”。“不谈爱情”是一种很坦然、很自信的与传统剥离和决绝。在池莉看来,现实生活中有婚姻,但没有爱情,所以她在《绿水长流》中写道:最好的结局不过是不吵不闹相依为命罢了。人与人出于人怕孤独的本性结伴过日子,这决不叫爱情。不论是贫贱人家,还是富有人家都没有爱情,宋美龄与蒋介石是郎才女貌,一座价值连城的花园别墅成为夫妻之间的礼物,但是结局是政治吞噬了爱情。池莉在《绿水长流》中把被蒙上神秘色彩的初恋,写成是“被你们文学家写得神乎其神了。其实狗屁,不过是无知少女情窦初开,又没有及时得到正确引导,做了些傻事而已。”
在物欲横流的当下时代,人们忙于追逐名利和财富,彼此间相互利用,人与人之间缺少真诚,更多的是欺骗。所以,在池莉看来,即使是夫妻之间,也只是看中彼此的财富、地位和名利,现实的利益取代了美好和真诚,爱情更是成为获得名利、地位和财富的一个名利双收的托词。《不谈爱情》中的庄建非与吉玲之间的结合,完全不是爱情做根基,庄建非完全被吉玲和其母亲掌控,言听计从,永远也挣脱不掉。《太阳出世》中的赵胜天和李小兰之间的结合,不是传说中充满传奇色彩的爱情,而是两个不经世事的年轻人的随意结合,结婚当天,赵胜天和别人打架打掉一颗门牙,李小兰当众骂赵胜天混蛋马大哈,他们结婚之后的成长,是因为经过了生活的磨砺,明白了生活的责任和意义,在生活中成为了有责心的人,长成了人,但并没有成长出爱情。《生活秀》中的来双扬与卓雄洲之间似乎有着彼此的喜欢和爱慕,真正到了要走到一起的时候,却因为一次极不协调的男女欢爱而导致他们之间的爱情神话彻底幻灭,爱情在这里成为了不能实现的性幻想。在池莉看来,爱情与生活根本就无关,与婚姻也没有必然联系,好情人不是好丈夫。
但是,池莉只是把标贴在生活和婚姻之外的美丽的爱情标签撕去,让崇高与平凡、诗意与现实、爱情与婚姻剥离开去,而她并没不彻底的否定爱情的存在。既不肯定现实生活中有美丽的爱情,却又不否定爱情在一定的情境下仍然存在。那么,池莉所说的爱情在哪里呢?池莉将爱情从现实婚姻生活之上剥离之后,一下子把爱情送到了可想不可见、飘渺无根的虚幻世界中去了,让你只可以去想象和欣赏,不能在生活中享受。在《绿水长流》中,作者编造的“我”与“他”之间,心中有爱却不能结合,终成永远思念的朋友。这种彼此倾心、愉悦、轻松愉快的爱情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向往的爱情观,以及像牛郎织女式的爱情一样,都是两情相悦,却不能相聚。只不过是传统文学作品中把这种爱情多写成了悲剧故事,而池莉则是极力赞成这种爱情的美好:“上天好像并没有安排爱情。它只安排了两情相悦”,“有一种方法可以保持男女两情相悦的永远。那就是两人永不圆满,永不相聚,永远彼此牵不着手。”(《池莉小说精选·绿水长流》)这样的爱情是飘渺虚无的,是梦幻般的爱情,是抓不到、看不见的,这是池莉对现实生活苍白婚姻的审视之后找到的一种心理自慰。作者认为这种爱情才能带给人美好的向往:“我们萍水相逢,如闲云野鹤,超凡脱俗,自得其乐。相安无事,君子之交淡如水。”爱情在池莉的文学世界中已经从现实生活之中飘逸而去,成为一种幻想式的心仪。
“不谈爱情”实际上是作者面对现实的一种无奈的心灵自慰。作者不是不向往爱情,而是现实生活中找到的是与美好爱情不相适应的种种失望和庸俗。对于心存爱情、两情相悦的人来说,现实总让他们“永远彼此牵不着手。即使人面相对也让心在天涯,在天涯永远痛苦地呼唤与思念。”作者是一位受过良好传统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崇高的理想、远大的志向、坚定的信念,都在她的心中早已扎根,但是,面对金钱拜物、争名夺利的生活现实,理想、信念和生活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反差和碰撞的伤痛。作者对美好的爱情报以幻想,又对毫无爱情可言的现实不得不给以认同与尊重,这种自相矛盾的世界观,也正催生了池莉一样的知识分子内心的矛盾与纠结,面对现实产生了无限的困惑和尴尬。摆脱这些困惑与尴尬的最好办法是放弃美好的爱情,不谈爱情。
二、活着的意义:存在就是强者哲学
从美好的梦幻与想象中走回来,面对多元价值观念并存的现实人生,池莉认为“人的基本生活有四个字可以概括,就是:衣食住行。”[1]对于人而言,存在就好,生存就好,只要活着就是强者。不要谈什么崇高与伟大,理想与信仰。池莉认为,“我没有仗可打,我没有知青可当,我没有大学可读,我没有工作可做,我陷入在我苍白的历史阶段之中。”(《让梦穿越我的心》),心中已经失去了伟大的理想和向往,一代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的变迁中迷失了方向,从崇拜高尚、追求理想的山巅一下跌落在经营生计的现实之中,心中自然在寻找新的人生哲学。放弃不现实的崇高、宏大、神圣,回归生活的本真之中,自然就成了“新写实”小说家们的审美选择,池莉是这一哲学的忠实信奉和推动者。她在很多作品中,都以存在就是强者的哲学思维给人物安排了回归现实生活的命运。
《烦恼人生》是池莉的早期成名作。印家厚是一位有技术、有责任心和集体荣誉感的工人代表,他受过传统道德教育,在工厂里很有影响,原本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分到房子,拿到高额奖金,带着老婆孩子过上好日子。可是,十多年过去了,没有分到房子,没有提干,连理应摊上的一等奖金也被别人算计而去。重活、累活都能找到他,唯独好事找不到他。在家庭,唠叨、刻薄的老婆让他终日找不到自尊和自豪,生活中充满烦恼。徒弟雅丽给他的美好爱情却只能成为不敢接受的恐慌,只能抛去美好的梦幻,回到现实生活之中。也许是为了抚慰受伤的、烦恼的心灵,池莉在小说的结尾给印家厚设置了一个温馨的家庭关怀,让他沉浸在质朴的现实家庭生活。
《来来往往》中的康伟业,《你以为你是谁》中的陆武桥,都是改革开放之初下海经商的弄潮儿,他们精明强干,抓住机遇,首先致富,成为成功男人。成功之后,康伟业梦想抛弃糟糠之妻,另寻新的爱情,陆武桥则梦想与年轻漂亮的女博士宜欣结合。他们的梦想终成为泡影,最终回到现实的生活之中,重新走进平凡的人流。
《你是一条河》记载了中国现代史上饥饿动荡的特殊时期的故事,主人公辣辣成为那个时代的见证者,亲身经历了从贫穷到改革的社会变迁,命运对她来说是不幸的。丈夫在一次火灾中身亡,年轻的辣辣成为一个拖着8个儿女的寡妇,还要应对不定时间来到的政治批斗。为了生存,为了让自己和孩子们活下来,她可以卖血,可以出卖自己的肉体,一家人的生存成了她活着的唯一目的和意义。而一切道德、尊严、高尚,都退避而去。无数个辣辣就是这样沉沦于日常生活之中走完自己一生的。
《不谈爱情》中的吉玲一家人,为了能够牢牢抓住家庭和社会地位都很体面的庄建非,为了让吉玲从脏破穷乱、名声不好的花楼街走出去,吉玲和她的母亲用了多种手段,把庄建非紧紧地控制在自己手中。而庄建非这样一个胸外科一把刀的高材生,为了自己的工作、名声和晋升,只能任其摆布,陷入平庸无聊的现实生活。
只要活着,只要存在,就有意义。不要高尚,不要浪漫,不要惊天动地,只要平凡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一种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这就是池莉的人生哲学。这种哲学与刘震云、余华等“新写实”小说家的观点是一致的。“新写实小说中的人物普遍表现出务实、去理想化的精神状态。而物质财富的占有的多少也形成了另一种新的衡量标准,促成新一轮对人们的社会地位和身份的重新安排。可以说这种逐渐萌醒并日益壮大的金钱、物质意识恰恰是应和着80 年代鼓励商品经济发展的主流意识形态,为90 年代以后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主义“观念盛行而铺下了基石。”[2]
池莉是很认同这样的生活哲学的。在《真实的日子里》,池莉写自己平淡、庸常、吃喝住行、与家人和谐相处的家庭生活,在写作之余,做些家务活,与女儿交流感情,为女儿穿衣起床,每天都是一种平常人的生活。隐匿了激情和浪漫,不去追求轰轰烈烈的轰动效应,归入平淡、放弃崇高,沉浸在安逸祥和的真实日子之中。
如果说这一种平淡就是一种理想的、温馨的生存方式,那么,这种生存方式无疑适合于众多平凡人家,没有什么创新之处。这种生存哲学是中国人早已熟悉和习惯了的媚俗哲学,在20世纪的末期、在改革开放的转型期已经成为一种宿命式哲学。显然,池莉的这种哲学已经没有什么创新意义。正如刘川鄂所说的:“在我看来,池莉如此走红,既是正常的也是不正常。说正常,是从现实的客观实情出发;说不正常,是从理性价值判断出发。在一个普遍媚俗的时代里,本来就媚俗的大众‘媚’上了特会媚俗的作家,是自然而然的;但文学不应媚俗,理性不会媚俗。理性要对媚俗说‘不!’,理性从来不会庸俗地套用黑格尔‘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句名言。”[3]
池莉钟情的是平凡而祥和的实实在在的生活,但是,池莉却又在一些小说中塑造了并不甘愿平凡的生存者。也许他们的生存或者是一种无奈,或者是一种迷茫的不安定,但与池莉一贯认可的安于现状的人物竟然不同,这让我们看到了池莉价值观的矛盾性。
在《小姐你早》中,作者把戚润物、李开玲、艾月塑造成三个带有女性解放思想、与现实抗争的形象。戚润物为了报复致富之后背叛自己的丈夫王自力,找来年轻漂亮、涉世经验丰富、有着悲苦命运遭际的艾月充当诱饵,并拉来经验丰富、城府很深的李开玲作参谋,三位女性密谋了一个让王自力自食其果、人财两空的计划。实施这个计划的结果是,王自力真的上当,倾家荡产,成为穷光蛋。戚润物们的胜利,是现代社会现实下女性对男权和男性暴力的抗争的胜利,是女性自发抗争的一次斗争性胜利。但是,如果说,戚润物她们是作者塑造的理想化女性形象,那么,这些女性无疑是用了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报复手段求得了反抗的胜利,并不高明,也不高尚,这种似乎不择手段的反叛,体现的恰恰是一种只为了生存而生存的哲学。戚润物伙同李开玲、艾月三人密谋骗取了丈夫王自力的钱财从而实现了自己的报复计划,让王自力式的男人栽了大跟斗,得来的是什么呢?是戚润物这些女性们的尊严和解放吗?不是,只是一种失去理想追求之后的本能报复心理。“新写实小说日常生活叙事,特别关乎从吃到住等一系列贫困生存问题的聚焦,实际上是作家自觉不自觉地将国家——民族现代性诉求及其间现实举步的无奈与迷惘投射到日常生活中,从而达到一种对日常经验的非历史性的重组,这也就使它从根本上区别于此前十七年小说、新时期小说由革命和社会主义的震荡所形成的日常生活叙事,并且使之开始彻底从集体记忆中抹去,这是多么令人无奈又为之惋惜的事。”[4]
三、回归世俗本真:道德伦理的遮蔽
池莉信奉的是回归生活的本真状态,以期找到真实的“日子”,为平凡人物的生存寻找合理的依据,撕裂传统文学中崇高、伟大和理想。池莉小说中,所有人物都信奉存在哲学,都从美好的理想追求中回到了功利性十足的现实,现实生活成为疗救他们信念丢失、理想迷茫的镇痛剂。回归到生活,安于现状,不再膜拜崇高和理想,把一切美好的追求都悬挂在高不可攀的想象世界里而不再问津,一切伟大、崇高的理想都成为虚无缥缈的东西,理想信念已经被生活彻底的埋葬起来,这是一种理想信念的虚无主义。文学一旦带给读者这种虚无的信念,艺术将成为生活的流水账,再也泛不起美丽诱人的想象和智慧启迪。
《烦恼人生》中印家厚原本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技术人才,只因不善钻营,生活困难,在现实生活的挤压下,回到平平淡淡的生活现实之中,不再去奢想那些美好的事业、爱情,甘愿坠入平庸。如同印家厚对生活的理解,生活就是一个字:“梦”。在这么一个道德标准含混的词语里,平庸与高雅、自私与高尚、功利与理想,都失去了界限,人的生活也失去了清醒的目标,做人的准则降低到只要守住生存的底线。
《你是一条河》中的辣辣,为了生计不惜出卖自己的身体,丧失了做人的尊严。如果说,这是池莉借助辣辣的故事对现实进行的批判,那么这种批判之后给人带来的希望是什么呢?辣辣在利用自己的身体换来的是一家人的生存,但是,她除了给予子女生存以外,对子女的人生影响只能是很多负面教育了。所以他的几个儿女,背叛的背叛,怒目的怒目。就是这样一个女人,作者还设置了王贤良这样一个人物,对辣辣终身钟情,其中逻辑的荒诞性是值得读者深思的。
《小姐你早》中的戚润物,是一位高级知识分子,位高品端。丈夫王自力发财致富之后意图抛弃她。戚润物为了报复王自力,不惜拿艾月这样一个已经受过人格伤害的世俗女性作投注,彻底摧毁了王自力的美梦。小说的题目是“小姐你早”,其中的一层含义是可以这样理解的:在金钱享乐主义漫布世俗人家生活之中的社会转型期,艾月为代表的受害女性首先觉醒了。那么,戚润物、李开玲、艾月的觉醒形式,是以非道德的手段对付非道德的现实,这种手段与暴力对抗、黑吃黑的算计是否同出一辙?作为现代男权世界下的女性觉醒的一种形式,实在不能给人们带来灵魂的觉醒。女性自身的独立与价值追求,才是摆脱男权和物欲束缚的最有效办法。
《不谈爱情》中的吉玲与庄建非,很难说上他们之间有什么爱情,吉玲预谋的计划,把庄建非紧紧套在自己设好的婚姻圈套中。作者总是让庄建非屈从于这种现实性很强的生活,尽管庄建非婚后认识到吉玲的修养不高,自己婚姻不幸,但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庄建非还是屈从了吉玲。吉玲生在充满世俗风味的花楼街,庄建非对吉玲的屈从,寄寓的是高雅文化对庸俗文化的屈从。为了自己的逻辑合理性,池莉把庄建非与吉玲的结合归结为性欲这一基本生理因素,完全抽空他们之间的感情,让庄建非完全失去了高雅和爱情原则。这也许就是池莉送给平凡人物的一种混沌的生活哲学吧。
池莉所处的时代,是中国社会政治上拨乱反正、文化上对宏大叙事传统的批判否定、经济上开放搞活的社会转型期,对金钱、享乐的钟爱无疑成为社会的一种心理猎奇。作为一度对传统文化教育有着背叛思想的池莉,对此前文学宏大主题叙事、假大空文学风气给予批判和否定。随着开放大门而进入的西方存在主义思潮,对中国80年代文学创作带来了新的觉悟和思维方式,反传统成为当时流行的文学风气。但是,在反传统、反崇高的文学观念大旗下,作为本土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道德、文化也被贴上怀疑的标签,遭遇嘲笑和奚落。池莉作为新写实作家,在探索新写实创作之路上并没有找到清晰的、明确的逻辑体系,简单装束,带着模糊不清的道德伦理判断,匆匆踏上文学创作之路,带给读者的是一种充满感性而不是理性的道德启迪。这种价值偏差很大的道德引导,恰恰迎合了当时社会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却暴富的广大中国人的心理,让生活在现实中的小人物们盲目地回归到一种变异的现实之中,抛弃坚持多年的理想和崇高、责任和高雅。有论者说:“在池莉对于生存的意义的价值判断中,最值得讨论和引起重视的是另一种类型的价值取向,即在池莉的作品中,生命、生存的价值是高出于其他方面的人生价值包括道德价值之上的。”[5]池莉的这种对传统的撕裂,是一种没有合理的道德建构的撕裂,没有明确目标的反叛。
在没有合理的道德建构支撑下,池莉只能给了她小说中人物以极强的宿命式的安慰。这也是“新写实小说”共通的一个思维方式,“新写实小说渗透在爱情观和生存观之中的是随遇而安的宿命论,正是这点虚无缥缈、若有若无的浅浅的宿命观,使市井人民甘心于眼前的生活,使他们对现状努力无效后改为平静地默默接受。”[6]
印家厚在辛苦一天之后,收获的是一个个烦恼,对造成自己烦恼命运的原因是什么并不清楚,只能发出无限的感慨,只能用一个“梦”字来自我安慰,非常相信自己的这个绝好的概括,于是就安心的入睡了。在宿命的观念中,一切烦恼都不再存在,这是否是一个带有佛教教义的宿命呢?而池莉的这种宿命安排,恰恰证明了她并没有找到人生新的道德准则和伦理规则。这是一个时代的朦胧与模糊,还是池莉自己的模糊与朦胧呢?
撕裂了传统的道德,背弃了伟大、崇高、高雅,掩藏了理想、信念,又没有设定新的道德伦理规训,在撕裂与重建之间,产生了强烈的道德悖论。
四、真实的日子:爱情的道德悖论
也许是文学家喜欢浪漫,池莉编制了很多浪漫的爱情故事,但又都把它们撕裂得粉碎,抛向高空重重地摔落在地。池莉找不到理想爱情与现实生活的契合点,所以只能借印家厚之口说:“原来爱情与婚姻是两码事。”
池莉笔下的美好爱情有两大特点:一爱情形式的传统性。池莉认识到的是,爱情真的很美好,带有传统的才子佳人色彩。符合中国传统爱情的审美观,也说明池莉的反传统并不是理性的、创建性的,是一种模糊不清的背叛,或者说是带有一种很强的个人化色彩的倔强拒绝。二是爱情的虚幻性。爱情与婚姻一直走不到一起,爱情不存在于婚姻之中,与婚姻无关。不论是印家厚与雅丽、陆武桥与宜欣,还是“我”与“他”,都只是美好爱情中的看客,并不能成为爱情中人。美好爱情作为一种人生幻想,永远结不成婚姻的正果,倒是随意结合的婚姻成为生活的主要形式。能够走到一起的是带有不同世俗和功利因素的婚姻,而不是两情相悦的爱情。
为什么美好的爱情,在池莉的小说中永远不能成为婚姻的支柱?我认为,这就是池莉为芸芸众生设置的一个人生谶语。
池莉认为,爱情只是一种诗意的神话。爱情是纯洁的,高尚的,与功利无关。两个人永远都相爱,却永远不要走到一起。而婚姻是现实的社会现象,要解决一些具体的社会问题和家庭问题,要建立在衣食住行等具体生活基础上,永远离不开现实生活,爱情与婚姻不能结合起来。
这就要分析一下池莉所谓的爱情。在池莉看来,爱情是美好的,美在一派沉默,美在一派超脱,美在一派坦荡。爱情是两情相悦,只能是给人带来美好想象的,“浓雾和一对神仙情侣”的描述,是多么切合池莉对爱情的想象。这种爱情与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牛郎与织女、贾宝玉与林黛玉、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多么相似。这样超脱现实生活的爱情,怎么就被池莉用物质和肉欲的追求所取代了呢?由此可以看出,池莉所谓的爱情,其实还是古典文学中的一种爱情想象,并不是现实生活中的爱情。
婚姻离不开衣食住行,离不开家庭责任和义务。所以,池莉在《绿水长流》中借兰惠心的话说:“他是好情人,但不是好丈夫。我也是他的好情人,但不适合做他的好妻子”,属于爱情的风流只能是婚姻的死敌。在池莉的婚姻观中,夫妻之间要和谐相处,性格温和,会体贴人,要有良心,这是婚姻择偶的标准,这种标准与爱情无关。这就是池莉的一种僵硬的设置与辩解。爱情就一定是传统意义上的风流吗?如果不是,那么,带有才气、高雅、脱俗的风流带来爱情的火花,不是对现实婚姻的稳定更好吗?
池莉认为,与爱情无关的是日常生活,婚姻属于日常生活,所以与爱情无关。这一逻辑的结果是:夫妻之间只要尽到义务和责任,和睦相处,就会带来婚姻的稳定。这是简单的社会逻辑,这种逻辑之下,生活将会风平浪静,毫无情趣。印家厚为什么还有烦恼呢?仅仅是因为物质生活吗?进一步说,这种婚姻如何来维持呢?婚姻的维持仅仅靠物质和利益吗?戚润物与王自力的婚姻一直没有解体,但其名实相副吗?池莉给他们强制注射了一剂麻醉药。“她笔下的人物,要么是环境的奴隶,要么是金钱的奴隶,没有自由意志,没有人性飞扬。诚然,作为一种生存状况,这种生存的被动性甚至是依附性是一种实际的存在。但作者基本采取了一种认同的态度,这就缺乏了现代知识分子应有的批判精神。”[4]
与爱情无关的婚姻,是一种不确定的现实判断。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正常的婚姻,想追求这种婚姻关系中的性格温和、体贴人、有良心,只能是知识分子坐在书桌前的一种幻想。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而且是对当下社会道德伦理建设的一种误导。现实生活中的价值多元、物质财富在家庭稳定中的作用已经很大,但是,这并不能证明现实生活中的婚姻没有爱情。
当下,家庭伦理中,婚姻与家庭责任密不可分,更与爱情密不可分,没有爱情的婚姻不能适应现实社会发展。池莉带给我们的道德悖论,让我们更加清醒地审视文学应如何与现实结合。
[1]池莉.池莉文集(4)[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157-240.
[2]陈小碧.“生活政治”和“微观权力”的浮现——论日常生活与新写实小说的政治性[J].文学评论,2010(5):47-51.
[3]刘川鄂.池莉热反思[J].文艺争鸣,2002(1):39-43.
[4]于淑静.试析新写实小说中的生存问题[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0(3):100-103.
[5]於可训.池莉论[J].当代作家评论,1992(5):54-62.
[6]汪红霞.从池莉创作看新写实小说的人生主题[J].青年文学家,2009(19):39.
OntheMoralParadoxoftheViewofLoveinChiLi'sNovel
LI Jin-ze
(DepartmentofChinese,AnhuiBozhouTeachersCollege,BozhouAnhui236800,China)
"No mentioning love" is Chi Li's literary proposition and her judgment on real life.In Chi Li's opinion, love is detached from reality, and what exists is marriage and daily life without elegant love, through which she provides sympathy and enlightenment for the secular men and women, and highlights the life philosophy that existence is winner. Such philosophy impresses people with the pessimistic view of love and marriage, between which was the moral paradox. Her view restrictes aesthetic perspective that literature brings to reality, causing its cognitive errors and manifesting Chi Li's vulgarizing aesthetic orientation in her novel.
Chi Li's novel; Not mentioning love; Philosophy of existence; Moral paradox
2014-09-06
李金泽(1968-),男(汉),安徽亳州人,教授,硕士,从事现当代文学方面的研究。
亳州师专校级基金(BZSZKYXM201312)
I02
A
1671-816X(2014)12-1259-06
(编辑:佘小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