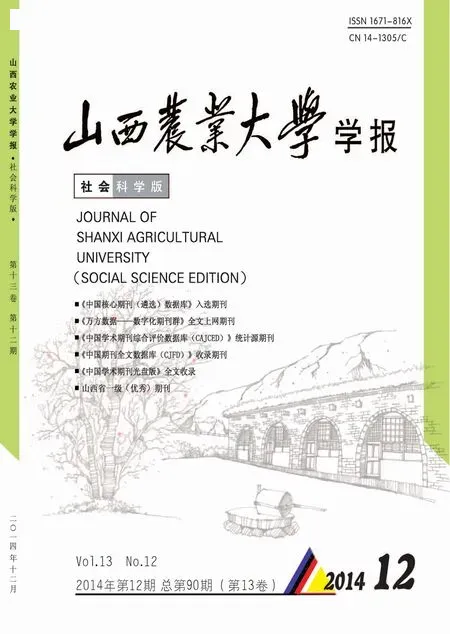当场劫持人质索要财物问题定罪研究
魏超
(南京师范大学 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0)
当场劫持人质索要财物问题定罪研究
魏超
(南京师范大学 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0)
绑架罪是单行为犯,故建立在复行为犯学说基础上的索取财物及是否存在“近亲属般切身忧虑者”,都不是绑架罪与抢劫罪的界限。只要当场劫持人质,无论是索要财物还是提出不法要求,都应当以绑架罪定罪。当场劫持人质行为对人质的人身安全侵害可能性比典型的绑架罪要轻。绑架罪的社会危害性还体现在其所带来的社会负面效应,即群众所产生的恐惧心理。
绑架罪;抢劫罪;当场;法益侵害
一、两个当场及支配领域说的否定
案例一:2009年7月12日,北科大学生黎某潜进学校内的中国银行,拿出菜刀劫持顾客,要求银行工作人员拿钱,银行只得交付赎金,黎某逃走后被公安人员抓获。案例二:2009年4月30日,商某在北京市某银行内劫持该银行保洁员乔女士,要求银行工作人员拿出14万元人民币,得到赎金后,商某挟持乔女士从银行逃走,随即被公安人员抓获。[1]对这两起发生在京城的相同案例,却存在着前一案例认定为抢劫罪,而后一案例认定为绑架罪的奇怪景象。
对于此类当场劫持人质并索要财物的案件,有学者根据行为人的心理状态、取财行为的当场性等方面认为,该行为更加符合抢劫罪的构成要件,并提出了两点理由,其一:考虑到被实施暴力胁迫的人和交付财物的人空间距离很近,对于暴力胁迫和财物的交付之间应当作整体评价,符合抢劫罪实施暴力胁迫后“当场”强取财物的构成要件规定。其二,在此情况下,应当认为行为人只有强取财物的意思,没有控制人质然后勒索财物的意思,从主观方面看,也更符合抢劫罪的故意。[2]
但是笔者以为,该学者及前述认为构成抢劫罪的检察院受通说中抢劫罪“两个当场”要件的制约,认为凡是符合“两个当场”的强行劫取财物的行为均构成抢劫罪,而忽略了绑架罪与抢劫罪在法益侵害性及行为模式上的区别。犯罪的本质是由客观的违法性与主观的有责性构建而成,[3]而“解释一个犯罪的违法构成要件,首先必须明确该犯罪的保护法益,然后在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内确定违法构成要件的具体内容。”[4]故清晰准确的认识绑架罪的法益与构成要件,对区分两罪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甲劫持人质,并向在场第三人索要金钱的行为,侵害了受害人的人身法益,亦符合绑架罪的构成要件。 在此情况下,行为人完全是利用人质的安危向第三人勒索财物,而非直接使用暴力向他人强行取财,故此时侵害的主要法益是人质的人身安全,而抢劫罪中的主要法益则是财产所有人的财产权。如果认为成立抢劫罪,则会造成法条评价与事实侵犯的主要客体相分离之情况,故此时认定为抢劫罪,恐怕有本末倒置之嫌。有学者认为,这种情况下应当根据被控制人与其利害关系人的关系的紧密程度,来判断被勒索的利害关系人有没有选择的余地,即“如果被劫持者与被勒索的利害关系人的关系密切,如父母与子女或夫妻关系等,则行为人对被劫持者使用暴力,正如对其利害关系人使用暴力一样,可以视为直接对其利害关系人本人当场进行的胁迫,行为人并未给利害关系人留下选择的余地,应认定为抢劫罪;但是,如果被劫持者与被勒索的利害关系人的关系并不那么紧密,如某歹徒劫持了一名职员到其老板家中,声称老板若不付赎金就把该职员杀死,则被勒索的利害关系人尚有一定的选择余地,并不能视为对该利害关系人自身直接的暴力胁迫,因而不符合抢劫罪的构成要件,只符合绑架罪的犯罪构成。”[5]本文不赞同这种观点。绑架罪必须向“近亲属般切身忧虑者”[6]提出要求的观点是建立在绑架罪是复行为犯的基础上的,即“绑架罪的实行行为无疑应是一种复合行为:其一为绑架行为,使用暴力、胁迫、麻醉等方法将他人控制在自己实力支配之下;其二为以加害人质相威胁,向第三方提出作为或不作为的胁迫要求的行为。”[7]但是通说认为,绑架罪是典型的单行为犯,即“绑架罪,是指利用被绑架人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人对被绑架人安危的忧虑,以勒索财物或满足其他不法要求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劫持或以实力控制他人的行为。”[8]行为人只要内心存在以他人为人质之目的,便可以成立绑架罪,又何必多此一举的认定所谓的“亲属关系般的第三人”?[9]详言之,只要行为人出于勒索财物之目的绑架了被害者,哪怕并没有向任何人提出要求,也已经成立绑架罪的既遂,何况行为人已经提出了勒索财物之要求?因此,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不当的增加了绑架罪的构成要件,缩小了绑架罪的成立范围,延后了绑架罪的既遂时间,不利于保护法益。退一步而言,何为像近亲属那样切身忧虑者,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如果两人虽然是近亲,却素有嫌隙,形同陌路,老死不相往来,是否可谓近亲属般的忧虑者?或者一个女孩极度厌恶的狂热追求者,又是否可以成为女孩的切身忧虑者?简言之,所谓的切身忧虑者,是一个极为主观的构成要件要素,运用在审判中,将会助长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而侵害国民的预测可能性,但是明确性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之一,在刑法法规内容模糊暧昧,一般人难以客观理解的场合是无效的,因为此时规定的内容并不明确,人们无法据此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进行预测,这种规定照样会使公民由于不能预测自己行为的后果而产生“寒蝉效应”。[10]而且,在刑法条文之外增加其它构成要素,将会缩小或者扩大罪名的成立范围,因此我们应当思考是否真的有必要增加这种要素。现实生活中经常出现劫匪为了逃避追捕,劫持群众的事件,此时围观群众均与被劫持者素不相识,如何判断现场有无切身忧虑者?按照近亲属说,如果没有忧虑者,则劫匪的行为只构成非法拘禁罪或者敲诈勒索罪,但这显然不符合群众的心理。更为荒谬的是,此时劫匪构成的犯罪,竟然不是取决于自己的行为,而是完全取决于周围的群众中有没有人质的亲属。这是不可思议的。
其次,空间距离并不是衡量抢劫罪还是绑架罪的标准。有学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指出:绑架罪……与抢劫罪的区别在于:第二,行为手段不尽相同。抢劫罪表现为行为人劫取财物一般应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具有“当场性”;绑架罪表现为行为人以杀害、伤害等方式向被绑架人的亲属或其他人或单位发出威胁,索取赎金或提出其他非法要求,劫取财物一般不具有“当场性”,因此当场提出要求的,应当构成抢劫罪。[11]但是,此解释中明确指出:绑架罪只是“一般”不具有“当场性”而已,故在某些情况下,绑架罪也可以具有当场性。如果拘泥于当场性的约束,认为当场提出要求是区分抢劫与绑架的界限,那么在行为人并未索取财物,而是当场提出不法要求时,则会出现难以定罪的现象。但是该学者同时又认为:当场提出其他不法要求的,又属于“绑架他人作为人质”,亦构成绑架罪。这种解释确实可以起到保护法益上的作用,但却难免让人感到疑惑:为什么劫持人质并且当场索取财物就是抢劫罪;而劫持人质提出不法要求,就变成了绑架罪?而且,“当场性”的观点将绑架犯罪提出取财的时间限定为“非当场”,实际上就是把绑架罪的成立时间固定在了“事后”,人为的缩小了绑架罪的成立范围,与通说认为绑架罪是侵害人身法益的观点不符。按照此观点,在行为人劫持他人作为人质后,当场提出了取财要求,并未得到满足,随后行为人将人质带离现场,再次提出了取财要求之时,行为人便构成了抢劫罪(未遂)与绑架罪(既遂),应当数罪并罚。但是此时倘若数罪并罚,则对针对人质的人身安全的暴力行为进行了双重评价,这并不妥当。
再次,即便行为人只抱着强取财物的意思劫持人质,我们也不能认为行为人只成立抢劫罪。有学者认为空间距离很近的场合,应当认为行为人只有强取财物的意思,没有控制人质然后勒索财物的意思,从主观方面看,也更符合抢劫罪的故意。但是,按照该学者的逻辑,行为人只有取财的故意便认为是抢劫罪,则所有的行为人在行为触犯了重罪的情况下都会辩解自己只有实施轻罪的故意,而且,以行为人的意思来定罪,会出现行为人的计划越周密,定罪难度越大之情况,这显然不利于保护法益。因此,行为人的主观故意,并不能成为绑架或抢劫的区分标准。笔者认为,定罪应当从客观到主观,即先分析行为人客观上造成了何种法益损害,再分析行为人的主观心理,能否将客观的法益侵害归责于行为人。我国有学者指出:故意的认识内容包括:(1)明知自己行为的内容与危害性质。(2)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某种危害结果。此时行为人的劫持人质行为,很明显认识到了自己行为的内容与社会危害性,也知道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他人的人身安全受到侵害,故完全可以认为行为人具有劫持他人作为人质的故意。既然行为人主观上有劫持人质的故意及取财的故意,客观上行使了劫持行为及取财的要求,其行为已经完全符合绑架罪的构成要件,如果只以抢劫罪定罪,恐怕有违全面评价原则之嫌疑。
最后,笔者认为该学者的观点有以刑治罪之嫌疑。该学者认为:实施暴力胁迫的人和交付财物的人空间距离很近,对于暴力胁迫和财物的交付之间应当作整体评价,符合抢劫罪实施暴力胁迫后“当场”强取财物的构成要件规定。但是,首先,为何空间距离很近的情况下,就应当做整体评价,该学者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其次,如果行为人此时并没有取财的故意,而只有其他不法要求的故意,按照该学者的观点,则有可能不构成犯罪。因为抢劫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取公私财物的行为。[12]则在行为人劫持人质,而又没有造成伤害的情况,也很难以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而我国又没有强制罪等罪名,故部分情况下,行为人甚至可能不构成犯罪,或者只成立非法拘禁罪,但是这显然不合适。试想,如果行为人用刀劫持人质后,面对大量特警强行要求政府释放在押罪犯,却只构成非法拘禁罪,这是不可思议的。在此时,有学者便会认为此行为严重侵害了法益,属于“绑架他人作为人质”应当以绑架罪定罪,但是这种观点难以解释的是:为什么劫持他人当场索取财物的,被劫持者不是人质,不构成“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不成立绑架罪;在劫持他人提出非法要求时,被劫持者又成为人质而成立绑架罪。显而易见,此观点在逻辑上存在自相矛盾。因此,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建立在处罚犯罪的必要性上来判断行为人是否值得科处刑罚,在发觉行为人的行为严重侵害了法益之时,便认为其成立了绑架罪,这种刑事办案的逻辑思路是:先量刑然后找罪名。即在发觉现有罪名的法定刑不足以处罚该种行为后,为了追求罪刑相适,在发现有其他罪名可以处罚此类行为之时,便凭借自己主观臆断行为人的心理,给行为人随便安上一个罪名加以处罚,但是,这种先量刑后找罪名的做法,使得绑架罪的构成要件在定罪过程中的定型性作用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或削弱;这种为了追求个案公正,以刑找罪,而削弱或者舍弃犯罪构成在定罪的规格功能,必将动摇犯罪构成这个支撑刑法现代化的支柱。更为重要的是,出现上述做法完全是因为部分学者没有全面准确的归纳绑架罪所保护的法益而造成了,即刑法本身并没有这种漏洞,而是部分学者在解释的过程中出现了疏漏,造成了这些漏洞,而后又试图用其他的方法去弥补,但是这样反而造成了法律条文中的不协调。
综上所述,索取财物的当场性并不是抢劫罪与绑架罪的区分标准。在实施暴力的对象与被迫交出财物的人不是同一个人时,由于暴力或威胁行为不仅侵害了被害人的人身权利,还侵害了第三人的自决权,如果认定抢劫罪则不能对该行为的所侵害的法益进行完整的评价,因而认定为绑架罪更能体现全面评价原则,也更能做到罪刑相适。
还有学者认为:此种情况下,应当从实质角度加以思考,并提出了“支配领域”的观点:当行为人采用暴力、胁迫手段压制了被害人反抗时,实际上对于当场的人和财物处于一种直接支配状态,行为人处以这样一个“支配领域”内,可以任意支配其他人和财物,即当场各种法益状态的变化取决于行为人,因此,在这种支配之下,行为人取得财物,就构成抢劫罪。而在绑架罪中,行为人虽然支配了被行为人,但对被行为人的亲属或其他相关人的人身和财产并非出于一种直接支配的状态,不存在相应的“支配领域”。[13]
在笔者看来,所谓“支配领域说”,只是两个当场的另一种说法。这种观点同时存在上述两种观点的缺陷:首先,此时行为人并不必然存在对现场人与财务存在直接支配关系。在抢劫行为中,被害人被暴力胁迫威胁,如果不交付财物,暴力行为往往会当场发动,严重威胁被害人的生命安全,此时的被害人往往在外力压制的影响下而难以做出清晰判断,或极大干扰并压制其以健全理性作出正确判断,在此情况下,方可认为存在直接支配关系。但是如后所述,在此类劫持人质事件中,行为人往往不敢伤害被害人,此时交付财物的决定权完全取决于第三人,故能否认为行为人对现场的人与财务存在直接支配的状态,实在值得商榷。
其次,抢劫罪中,被害人为了自己的人身安全不得已而交付财物,实属合情合理,因为没有人会认为钱财比生命更值钱。但是在他人作为人质的场合中,如果有前述的“近亲属般切身忧虑者”,姑且可以认为对现场的人与财物存在直接支配关系,但是如前述发生在银行中的劫持顾客案件中,现场的人与该顾客素昧平生,为何认定行为人可以直接支配那些素昧平生之人的财物,缺乏理由。
最后,这类“支配领域”是否有必要存在,是一个有待商榷的问题。如前所述,笔者赞同学界通说,认为绑架罪是典型的短缩的二行为犯,是以实行第二行为为目的犯罪,但只有第一行为是构成要件,第二行为不是构成要件行为。因此,罪名中的“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只是主观的超过要素,并不需要向任何人提出要求。
二、当场型绑架罪与典型绑架罪的区别
有学者认为:当着第三人的面挟持人质,被害人往往没有选择的余地(而且来不及报警),比非当着第三人的面进行挟持的违法性更重,也对人质的生命、身体安全的威胁更具有现实性,因而认定为绑架罪更能准确评价该行为的违法性。[14]
笔者认可该学者将此行为认定为绑架罪的结论,但认为其理由值得商榷: 首先,从行为人的心理而言,此时行为人虽然具有劫持人质的行为,但其并不敢贸然加害人质。埃里克·沃尔夫教授通过对犯罪原因的调查研究指出:行为人在实施犯罪行为前有一种侥幸心理,以为犯罪后不会被发现、可以逃避刑罚处罚,如果行为人没有这种侥幸心理,则不会实施犯罪行为。[15]在当场劫持人质的案件中,行为人处于重重包围之中,一旦加害人质,自身必然插翅难飞,甚至有被直接击毙的可能。此时的人质反而成为了行为人的护身符,一旦人质遭到杀害,行为人自己的人身安全反而得不到保障。因此,笔者认为,此时除了极少数丧心病狂的行为人外,绝大多数行为人都不会伤害人质。这种情况下,对人质的生命、身体安全的侵害并不必然具有现实性,人质被害的可能性也远远小于普通绑架罪。更加重要的是,当场劫持人质的劫匪,除了极少数亡命之徒或者有精良装备的专业劫匪,大多并没有经过精心策划而是出于一时激愤或迫于无奈,他们在劫持人质之前,早就想到自己难逃法网,行为人之所以会选择当场劫持人质,大多是为了引起社会的注意,已解决自己的问题或者被生活所迫而走投无路,铤而走险实行绑架行为,其内心根本不想杀害或者伤害人质,这种劫持行为对人质的危险甚至更低于普通的伤害罪。
其次,对应从人质的角度而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被绑架人的生命、身体安全反而可以得到保障。众所周知,在典型的绑架罪中,绑架与撕票的行为在现实生活中容易同时发生。首先,即使行为人已经实现了不法目的,也会因为担心被绑架人被释放后通过各种体貌特征识别并告发自己,为了避免刑罚处罚而杀害被绑架人;其次,行为人在没有实现不法目的的情况下,也会为了证明其先前的胁迫内容而杀害被行为人,起到所谓“杀一儆百”之效果;再次,被绑架人在此时一般都会为了自保而听命于行为人,即心理学上所称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人质会对劫持者会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感,劫持者让他们活下来,他们便不胜感激。甚至把劫持者的前途当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视为自己的安危,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反而容易激发出行为人人性的阴暗面,将之残忍杀害。最后,此时行为人并没有后顾之忧(如陷入警察的团团包围),对人质的生命有绝对掌握,即便不杀害人质,警方也不会放弃对其的追捕,在如此强大的心理压力下,行为人会抱着“一不做二不休”的想法将人质杀害。而在当场劫持人质的案件中,行为人甚至要想方设法保住人质的性命,以便作为其不法要求的筹码或者全身而退的资本,如此情况下,人质的性命反而更容易得以保全。而且在当场劫持的过程中,谈判专家有更多的时间与行为人交流,可以迅速有效地稳定缓和劫持者的心理状态,同时通过有效的沟通拖延时间,唤醒劫持者的求生欲望,消散其犯罪激情,让他从不理智的状态回到理智的状态上来。因此笔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人质的人身安全反而更有保障。
再次,从第三人角度而言,在典型的绑架罪中,因为第三人几乎完全无法掌握人质的安全状况,对其自决权的侵害其实更为严重。当场索取财物之时,对人质的生命、身体安全的威胁更具有现实性固然不假,但正因为此时具有现实性,第三人可以直接观察到行为人的各种行为,更好的了解人质的身体状况,安抚人质,让其不至于做出过激举动激怒劫匪;而在非当场索取财物之时,第三人难以估计到人质的状况,对人质安全的掌握完全取决于行为人给予的信息,甚至在某些时刻,行为人杀害了人质以后,第三人仍然不知道情况。因此,行为人当场索取财物之时,对第三人的威胁反而更小,因为此时第三人可以非常清楚的观察到人质的处境,而行为人也不敢轻举妄动,更不敢杀害人质;而在非当场取财之时,第三人对人质的情况可谓一无所知,人质处于一种生死未卜的状态,此时对第三人的心理压制可能更甚于当场的威胁。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当场劫持人质的行为中,对人质的生命、身体安全的威胁虽然具有现实性,会引起第三人及现场群众的担心,但往往不会发生。故当面劫持人质并威胁的行为,无论是对第三人自决权的威胁,及对人质生命身体的侵害,都不及典型绑架罪的类型。
三、两罪名的区分标准:侵害法益的不同
犯罪的本质是侵害或者威胁法益,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因此,要想分清两罪的界限,必须回到两罪的罪质或者法益上进行考虑。
其实在被害与加害的人际格局方面,绑架罪具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双重被害人特征。一方面是被劫持的、失去了人身自由的被行为人,谓之“现实被害人”;另一方面是对被行为人的安危嫉妒担忧的相关人员,谓之“实质被害人”。在绑架案件发生时,人质的生命身体之安全固然遭受了重大威胁,而相关人员的焦虑、担忧等负面情绪对其内心的煎熬,恐怕一点也不会比人质肉体上遭受的痛苦为少。因此,笔者认为,绑架罪与抢劫罪的区分除了侵犯第三人的自决权以外,还在于绑架罪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即绑架罪对普通民众产生的威慑力。美国学者布莱安·詹金斯曾经指出的:“恐怖主义是个剧场,它的目标不是实际的受害者,而是旁观者。”在某种程度而言,此类当场劫持人质行为也是如此。当抢劫罪发生后,只会使得具有相同或者类似经济背景的人群产生恐惧感,而绑架罪一旦公之于众,几乎使得人人自危,可以说,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被绑架的潜在对象,连银行的职员甚至街边的乞丐也不例外,取钱的顾客、校园的学生都可能突然拿出一把尖刀架在他人的脖子上,每个人的生命都得不到保障,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将荡然无存。当今社会,劫持汽车、飞机的事件已经屡见不鲜,从“温州持枪持爆劫持人质案”,到“长春劫持人质案”,再到有国际影响力的“菲律宾马尼拉劫持香港游客案件”,绑架罪因其手段极端、破坏力巨大、社会影响恶劣,形成了对人们生命健康、财产安全的重大威胁,大大提升公众的恐惧感,束缚了民众的行动自由,其对法益的侵害程度远不是仅仅侵犯了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抢劫罪可比的。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当场劫持人质并索要财物之行为既侵害了公民的人身权利,也侵害了第三人的自决权(因为是当场劫持,必然是有人在场才能提出要求,故此时必然侵害第三人自决权,这点与普通的绑架罪有区别),还同时侵害了民众的正常生活秩序,其社会危害性比一般的绑架罪更大,侵害的法益也更为严重,故应当做为绑架罪加以处罚,方能做到罪刑相适。
[1]聂郁蒙.绑架罪争议问题浅析[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4(5):108.
[2]陈兴良,周光权.刑法学的现代展开[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569-570.
[3]张明楷.以违法与责任为支柱构建犯罪论体系[J].现代法学,2009(6):43.
[4]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上)(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353.
[5]黄嵩.论非法拘禁罪与绑架罪认定中的若干难点——从王文泉非法拘禁案的认定谈起[J].法学评论,2004(4):147.
[6][日]山口厚著.王邵武译.日本刑法各论(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09.
[7]谢治东.绑架罪构成要件认定新解——兼论绑架罪限制性解释之废止[J].湖北社会科学,2009(10):108.
[8]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第五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475.
[9][日]西田典之著.王邵武,刘明祥译.日本刑法各论(第六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83.
[10]黎宏.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20.
[11]张国轩.抢劫罪的定罪与量刑[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56.
[12]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850.
[13]张明楷.刑事疑案演习(一)[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328.
[14]陈洪兵.人身犯罪解释论与判例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190.
[15]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第三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40-41.
StudyontheConvictionofon-spotAskingforPropertyfromtheHostage
WEI Chao
(LawSchool,NanjingNormalUniversity,NanjingJiangsu210000,China)
Kidnapping is a crime, so asking for property is related with "close relatives like personal cares" or no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double crimes is not the boundary between kidnapping and robbery. As long as the spot hostage takes place, it is convicted kidnapping regardless of asking for property or posing illegal request. The safety violation of on-spot hostage is less than kidnapping. The harm of kidnapping to the society also displays its negative impacts on the society, that is the public fear.
Kidnapping;Robbery;On the spot;Violating legal interests
2014-09-09
魏超(1989-),男(汉),浙江宁波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刑法方面的研究。
D914
A
1671-816X(2014)12-1238-06
(编辑:佘小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