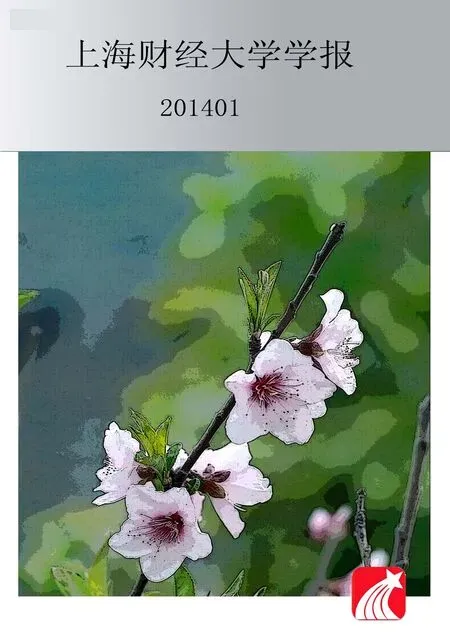财富与需要的内生关系:对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状况的经济哲学探究
马拥军,毛小扬
(上海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433)
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了三个“没有变”,其中之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没有变。从总体情况看,这样表述是有道理的,但从具体状况看,这一表述需要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短缺经济时代的表述。21世纪,中国进入过剩经济时代,使这一矛盾的状况发生了重大改变。“物质文化需要”可分为“物质需要”和“文化需要”。过剩经济本身就意味着物质需要能够得到满足,因为相对于需要来说,财富出现了过剩;现在面对的问题是拉动内需,以及限制过剩的生产能力。如果说,有些人的有些需要得不到满足(如由于全民医保体系和社保体系尚未建立,有些人医保的需要和社保的需要得不到满足),那么这是结构性矛盾,不是由于社会生产能力不足而导致的矛盾。在物质需要能够满足的情况下,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就变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同落后的文化生产之间的矛盾”。由于在提出“物质文化需要”的时代(中共八大提出“经济文化需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修改为“物质文化需要”),中国还是短缺经济,温饱尚未实现,因此当时提出的是“两个文明一起抓,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但首先需要抓的物质文明,就是所谓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现在已经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时代,“文化需要”已经不再仅限于精神需要,而是包含了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需要①。相应地,从个人来说,单纯追求物质财富已经不能再满足人的各方面需要,它只能导致人的片面发展、依附性发展,同社会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的目标是相悖的。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如果对这一基本国情把握不准,方针、政策的制定就必然会出现偏差,因此,从财富和需要内生关系的角度,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发展状况进行考察,就成为当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然而,这一课题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学问题,也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学、文化学或社会学、生态学问题,而是一个经济哲学问题,用马克思主义术语说,它属于一个“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问题。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财富观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财富观经历了一个从效用财富观到货币财富观再到资本财富观的发展过程。这种片面的财富观是导致当前中国出现种种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问题的总根源。
1.效用财富观。效用财富观重视的是使用价值。在这种财富观下,财富表现为使用价值的量,衡量穷和富的标准是有多少“东西”。比如我有三座房子,你只有一座房子,那么我的财富就是你的三倍,因为房子是供人住的,如果一座房子能够满足一户家庭的居住需要,那么三座房子就能满足三户家庭的居住需要。
2.货币财富观。货币财富观重视的是交换价值。在这种财富观下,财富以货币或金钱的形式,表现为交换价值的量。我的三座房子在上海郊区,共值三百万元;你的一座房子在上海市区,值一千万元,那么虽然从效用或使用价值上看,我是你的三倍,但从值多少钱或交换价值上看,你的财富是我的三倍有余。
3.资本财富观。资本财富观重视的是剩余价值,或剩余交换价值。在这种财富观下,财富不是以直接的货币形式,而是以增值的货币形式,表现为剩余(交换)价值的量。我的房子虽然在郊区,但上海金融自贸区要建在那边,因此升值潜力很大,据估算,一年后这三座房子可增值到一千五百万元,那么你肯定愿意跟我交换,因为按照资本价值观,我的财富是你的一倍半。即使把风险因素算进去,你仍然是“赚”的。
中国改革开放以前,国家的政策始终是以农为本,以商为末,重农轻商,“重农抑商”,这实际上是以效用财富观为前提的;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经历了从“全民经商”到“全民炒股”、“全民炒房”的过渡,财富观发生了重大变化,已经由效用财富观过渡到了货币财富观和资本财富观(其背后则是货币价值观和资本价值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家政策仍然以效用财富观为指导,必然会导致种种误会,产生种种问题。比如有人提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住房是商品,商品应由市场调控,并以此为借口,反对国家对房地产进行调控。其实,国家要调控的并不是作为“商品”的住房,而是作为“资本”的住房。作为商品的住房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它是用来满足居住需求的;作为资本的住房则是能够带来剩余(交换)价值的(交换)价值,它不是用来住的,而是用来加价后再卖出去,为了获取剩余价值,为此哪怕造成住房大量闲置也在所不惜。这就势必造成资源的浪费,由此导致种种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问题。对此,国家必须进行调控。要使人们接受调控,就必须进一步研究需要状况的变化,使宏观调控与人们的需要一致起来。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需要状况的变化
一谈到需要,人们马上就会想到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相比之下,人们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需要理论了解得很不够。按照马斯洛的看法,人类需要从低到高,分为生存需要、安全需要、尊重和爱的需要、自我实现需要。在马斯洛看来,一方面,只有低级需要满足了,高级需要才会产生;另一方面,某种需要一旦满足,就不再能成为激励人们行为的力量,这时只有更高级需要才能激励人们的行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关于需要理论的专著,但他们的著作中有着丰富的关于需要理论的内容②。他们不仅从需要的结构方面研究过自然需要、社会需要和精神需要,而且从需要的层次方面研究过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发展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无论是就需要结构还是就需要层次来说,都不能认为需要是单一的,任何人的需要都既有其结构,又有其层次,只是人们往往仅意识到某一种需要,从而使其他需要处于潜在状态而已。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支配人们有意识行为的仅仅是某一种特定的需要,但支配人们全部行为的实际上是包括不同需要结构和需要层次在内的整个需要体系。更重要的是,马克思注意到需要的异化现象,即低级需要满足了,高级需要却没有产生(如守财奴葛朗台);或者低级需要没有满足,高级需要却产生了(如雷锋),尤其是所有需要都化为对货币的需要这种现象。需要的异化和需要异化的扬弃,都是需要生成的环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理论,为我们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人们需要状况的变化提供了分析工具。下面从需要与“想要”、需要与贪欲、需要与信仰三对关系角度,分析一下这种变化。
1.需要与“想要”(偏好)。人们常常混淆需要和“想要”(经济学上称为“偏好”)。实际上,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需要是客观的,“想要”(偏好)是主观的。比如,糖尿病患者需要胰岛素,尽管病人可能根本不知道有这种东西;相反,他(她)想要的可能是糖这种对他(她)的健康有害的东西③。再如,吸毒者需要的是戒毒,他(她)想要的却是毒品。这说明,需要是客观的,尽管人们未必能意识到它,但它对于人们的生存和发展来说却是必不可少的;而“想要”或偏好却是主观的,有时是病态的、必须革除的。马克思主义主张根据需要来矫正“想要”,而不是相反。
需要和“想要”的这种区别,并不必然采取尖锐对立的形式,因为更多时候,人们想要的可能恰恰是他们需要的东西。需要和“想要”只是表示主观与客观相区别的一对范畴。比如一个糖尿病患者一旦意识到什么是胰岛素,他(她)就想要这种东西了。相反,由于人类同动物的单纯本能行为不同,更多的是有意识的行为,因此人类的需要只有上升到“想要”,才能自觉地去满足它。如果不能把需要上升到意识层面,变成“想要”,又怎么可能用需要矫正“想要”?
2.需要与贪欲。人们反驳共产主义的一个主要论据是所谓的“生产力水平悖论”:资源有限,欲望无穷,因而生产力永远不可能发展到满足所有人需要的程度。这种论证的无效性在于先是混淆了“需要”与“欲望”,然后又混淆了“欲望”与“贪欲”。对此谬论,用甘地的一句名言就可以驳倒:“地球上的资源足以满足人类的需要,但不足以满足人类的贪欲。”
这句话特别适用于过剩经济时代的中国。欲望既包括人的动物本能,也包括人的偏好。但其核心是人的偏好,即“想要”。而贪欲是建立在“想要”的基础上的:它意味着超过“需要”的“想要”。曾有学者提出: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有三千万元的财富,就足以满足日常需要。财富的进一步增长,比如再增加三个亿,对他(她)的生活质量几乎没有影响,它要么表现为存折上的一个数字,要么表现为一种奢靡浪费式的“为消费而消费”(炫耀式消费、攀比式消费,等等),因此只是一种虚幻的心理满足,对于客观需要来说没有任何意义。这样的财富增长和消费既会败坏财富拥有者的品质,更无助于社会需要的满足。它是造成人民群众心态不平衡乃至某些人仇富心态的主要原因。
3.需要与信仰。“想要”仅仅是对需要的意识,因而是进一步满足需要的前提。它虽然蕴含着需要异化的可能性,但毕竟不等于需要异化。“贪欲”却是需要异化的典型形态之一。动物界不存在“贪欲”。“贪欲”是一种社会现象。从“想要”到“贪欲”,与特定的社会条件联系在一起。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价值观和资本价值观导致的拜物教财富观,即货币财富观和资本财富观,是导致“贪欲”形成的一个主要社会原因。因此,要克服需要异化现象,就必须在日常生活中以需要财富观代替货币财富观和资本财富观,在信仰层面以人本价值观代替货币价值观和资本价值观。
一般认为,价值是满足主体需要的客体属性。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一方面,需要有其结构和层次,这本身就决定了价值必然是一个体系。另一方面,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已经明确指出:对于“对象”、现实、感性,不能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方面去理解,而必须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必须从实践方面去理解,因此,价值与其说是客体属性,不如说是在实践中生成的“对象”属性④。例如胰岛素,一开始并不存在,它是人们在治疗糖尿病的过程中发现和发明的,因此并不是现成存在的“客体”,而是在实践中生成的“对象”,是为了人并通过人而生成的(即以人为本的)对象性存在物。从两个方面的综合来看,价值并不是天然存在于自然中的,而是由人创造出来并为了人而跃入“存在”的;价值体系说就更不用说了。
既然价值体系并不是既成的事实性存在,而是生成中的现实性存在,它必然与特定的信仰体系联系在一起。有神论者会认为价值体系由神创造,而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价值体系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无神论信仰。因此,无神论并不是单纯的“不相信神”,而是“通过否定神来肯定人”。作为一种信仰,无神论相信不需要通过神,单纯凭借人类自身的力量,就能够创造一切价值,获得幸福与自由。
三、财富与需要内生关系的变化
进入21世纪以后,东部沿海较发达地区,尤其是长三角地区,率先提出了“富口袋,更要富脑袋”的口号。这是改革开放以来需要与财富关系变化的鲜明写照。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需要层次和结构的变化自发地带来了财富观的变化。由于存在需要异化现象,现在的任务是如何使这种变化由自发上升到自觉。这不仅是一个财富观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涉及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问题。
1.价值观。从价值观角度来说,建立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任务还非常艰巨,目前的重点是消解货币价值观和资本价值观,建立人本价值观。
货币价值观和资本价值观的特点,是把所有需要化为对货币的需要、资本的需要。按照这样的价值观,只有能用货币衡量的才有价值,其中,物的价值在于它能交换到的货币量,人的价值在于他(她)所能赚取的剩余价值量。或者说,物的价值在于它值多少钱,人的价值在于他(她)能赚多少钱。因此,货币价值观和资本价值观把所有的需要都化为同一种需要:对货币的量的需要。
人本价值观并不否认货币和资本的价值,相反,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谈论的“价值”和“剩余价值”,恰恰是与货币和资本联系在一起的。但在马克思看来,这并不是根本的价值,而是手段价值,只有人才具有目的价值。按照这样的逻辑,资本作为能够带来剩余(交换)价值的价值,必须服务于(交换)价值的生产;(交换)价值的生产必须服务于使用价值的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必须服务于人的多方面、多层次需要的满足。
2.世界观。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混同于“科学世界观”。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宗教也是世界观,而且是情感世界观,正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世界观,而且是(体现无产阶级改造世界要求的)意志世界观一样。与人本价值观相适应,马克思和恩格斯谈论的“世界”总是指“人的世界”。“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⑤
与人的需要的全面性和层次性相对应,人的世界也是一个对象性世界,或者人化世界。所谓“人化世界”,是指人把整个世界变为满足自己需要的财富。这就是说,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不仅资本、货币和使用价值是财富,凡是满足人的各方面和各层次需要的对象都是财富。人类必须为自己创造一个包括物质财富、社会财富、精神财富和个性财富在内的立体的财富世界。
3.人生观。对于个人来说,全面小康意味着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对于社会来说,全面小康意味着为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创造条件。前者意味着创造一个全面的、多层次的财富体系,后者意味着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的客观需要,特别是健康需要和自主需要。国家应当积极开展民生建设,为这些需要的满足创造条件。
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表现为人类幸福与个性自由的统一。幸福不等于快乐,全面的、多层次的需要的满足是幸福,动物式的、纯物质性的满足是快乐。个性自由不等于任性妄为。任性妄为是“随意”或失去自由意志,而不是意志自由。只有建立在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统一基础上的个性的自我塑造和自我实现才是个性自由。这一切都要以生产力的一定发展即以过剩经济为前提。结构性过剩或相对过剩经济导致的是社会主义,总量过剩或绝对过剩导致的是共产主义。当今时代,全球已经进入相对过剩经济时代,因而具备了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西方发达国家的消费社会表明,它们已经进入绝对过剩时代,因而具备了共产主义的客观条件。然而,由于需要经济学尚未建立,偏好经济学仍占统治地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普遍实现的主观条件尚不具备。然而,单个个体已经完全有可能把人类幸福和个性自由的统一作为生活目标。这是共产主义人生观的核心。
由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研究远远落后于时代,人们缺乏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工具,因而误以为十八大报告所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没有变,就是不仅总体情况也没有变,而且具体状况也没有变。这是完全错误的。随着物质需要的满足,文化需要凸显出来而得不到满足,人们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正产生越来越多的问题。
四、从“偏好经济学”到“人本经济学”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状况的改变,把“创立中国经济学”提上了议事日程。无论是以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目的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在短缺经济时代供改革开放初期借鉴的西方经济学,都已经远远落后于形势的需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向我们提出了扬弃“偏好经济学”、建立“需要经济学”,扬弃“福利经济学”、建立“人本经济学”的任务。
1.“偏好经济学”与“需要经济学”。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不仅混淆“想要”、“偏好”、“欲望”、“贪欲”等概念,而且混淆了“偏好”与“需要”、“需求”,这样的经济学可称为“偏好经济学”。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左翼学者不仅区分了“偏好”(想要)与“需求”(需要),而且区分了异化的需要(欲望、贪欲)和根本的需要。
当代西方微观经济学建立在效用价值论的基础上。所谓“效用”,实际上是商品满足人的欲望或想要的程度。微观经济学没有意识到: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其实并不是围绕普通人的效用,而是围绕资本的效用,即满足获得利润需要的商品、货币或劳务的效用而建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从微观经济学出发无法建构起宏观经济学,因为一旦绕过资本的再生产,微观和宏观之间的联系,即“看不见的手”,就成为一个无法把握的黑箱。
萨伊定律的缺陷就在这里。萨伊混淆了物物交换与商品流通、资本流通,没有注意到:工人需要的满足构成剩余价值再生产的一个环节;资本家仅把工资视为需要不断压低的“成本”,必然导致工人阶级的需要中,有一部分只能作为无效需求而存在。如果任由生产力发展下去,社会总供给总有一天会超过社会总有效需求。
到凯恩斯的时代,这种情况终于出现了。凯恩斯超越萨伊的地方在于,他认识到总供给与总需求能否实现均衡,关键不在于社会总需求,而在于社会总有效需求。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性偏好这“三大心理规律”,国民收入不可能全部转化为总有效需求,其中有一部分会被闲置起来,导致商品过剩和工人失业。要使有效需求达到充分就业所要求的水平,就必须大力刺激工人的消费和资本家的投资。由于运用凯恩斯理论的国家无一例外地获得了长期稳定的经济发展,萨伊定律逐步遭到遗弃。
然而,从需要经济学的角度看,只要不把追求利润或剩余价值的生产目的转变到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上来,过剩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剩余价值必须有剩余使用价值与之对应,否则就只是一种泡沫化的经济增长,而不是真实的经济增长。可笑的是哈耶克式的经济学连凯恩斯的水平都达不到,更不要说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需要经济学”了。
2.“需要经济学”与“福利经济学”。按照马克思的看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而追求剩余价值的生产目的决定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然蕴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这就是由获取剩余价值的冲动所决定的不断增加的社会总供给与由可变资本(工资)作为成本被压缩在特定水平上所决定的有效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只有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否定,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才能克服由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所决定的危机。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一旦生产力的发展达到了总有效需求能够得到满足的程度,过剩经济时代就到来了。最初的过剩只是由于工人的工资过低,导致购买力不足,因此属于相对过剩,或结构性过剩。只要提高工人的工资,把工人无效的刚性需求转化为有效需求,相对过剩的危机就可以获得解决。凯恩斯革命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然而,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获取剩余价值,因此在这之后生产力必然继续发展,直到所有的刚性需求都得到满足,从而达到总量过剩或绝对过剩。那时候,导致资本主义最终灭亡的危机就到来了。
由此可以理解欧洲社会党和美国民主党所推行的福利国家、福利社会的性质。西方左翼学者正是以这种实践为根据,继承马克思的理论,倡导建立“满足需要的政治经济学”。这可以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的一种西方形态。如英国左翼学者莱恩·多亚尔、伊恩·高夫研究了人的需要理论,提出无论是第一世界国家、还是第二世界或第三世界国家,都应当实行“自由民主社会主义”⑥,以建立满足最优化需要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但他们没有考虑,这样做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要坚持利润至上的价值观,福利经济学就必然使全球陷入西方式的消费社会。
邓小平曾经期待创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⑦。这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才能够解决福利社会带来的“高平衡陷阱”难题。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中国学者尚未完成这一使命。
五、新“政治经济学批判”:扬弃“资本经济学”,建构“人本经济学”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只能是“人本经济学”,不能是“资本经济学”。因为它的研究目的只能是通过市场机制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能是获取剩余价值,不能是利润至上。
1.扬弃“偏好经济学”,建立“需要经济学”
作为人本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是满足人的“需要”的经济学,而不是满足资本家的“偏好”的经济学。对于资本家来说,剩余价值或利润才是目的,人只是生产和实现剩余价值的手段。从微观层面来说,正是对剩余价值的无度追求,才迫使资本家不断降低劳动成本,提高生产能力,从而成为整个社会发展生产力的一个基础环节。正因如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必须利用资本,推动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但是资本就是资本,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环境中,还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环境中,它获取剩余价值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既然如此,在利用资本的过程中,就必须防止资本对公共权力的腐蚀。当前中国微观层面出现的权力资本化和资本权力化现象,正是资本逻辑发展的外部表现。执政党只有摆正手段(资本的利用)和目的(人的发展)的关系,才能确保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实现。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必须把执政党的作用作为宏观经济层面的决定因素加以考虑。
2.扬弃“市场经济学”,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
作为人本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是通过交换手段满足每个人需要的经济学,而不是以剥削手段满足部分人欲望的经济学。
交换,代表的是分工和协作,因此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中,马克思通过分析价值形式的历史演变,研究了单一市场经济条件下,抽象劳动如何从具体劳动中分离出来,成为交换价值中的实体性成分,从而为市场经济学奠定了基础。不仅如此,在《资本论》第二篇中,马克思还分析了从市场经济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条件——劳动力成为商品,从而找到了剩余价值的来源,为分析剩余价值的生产和流通奠定了基础。由此可以看出,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通常所说的市场经济不同。通常所说的市场经济无非是以交换为基础的经济,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却是以获取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市场经济。如同巴斯夏所认为的那样⑧,由于通过交换,双方都可以从中得到好处,而没有人受损失,因此对于双方而言都是合算的行为。这是一个正和游戏,而不是零和游戏。就此而言,通过交换所额外得到的,实际上是双方通过分工和协作所形成的效率提高的必然结果。这里所遵循的就是等价交换的原则。但是,如果出卖的是劳动力,而不是劳动产品,那么所形成的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分工和协作的好处就归资本所有者,而不是归交换的双方。换言之,在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情况下,资本家剥削的有可能是他所直接雇佣的工人的绝对剩余价值或其他企业工人的相对剩余价值,但也有可能是本应由劳资双方分享的合作成果。因此,马克思研究剥削,并没有把它当作个别资本家与个别工人之间的关系,而是当作作为特定生产关系代表的单个资本家和单个工人的关系⑨。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剥削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剥削不同,应当有明确的法律界限,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工人的集体谈判权,通过这种权利,工人完全可以在让资本家保证获得一定利润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提高自己的工资收入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容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必须始终使它处于从属地位,不能上升到制度层面。
3.扬弃“纯粹经济学”,建立新“政治经济学批判”
作为人本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只能把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作为最终目标,而不能把经济发展作为最终目标。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最大区别,不在于一般意义上的财产公有还是私有,而在于生产资料是公有或私有,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则表现为资本是公有还是私有。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在私有制下,经济增长(表现在GDP的增长中)或平均收入的增加并不能保证“每个人”的需要的满足,“让我们关心国民生产总值分布的均匀,而不是它增加的速度”⑩。凯恩斯关心就业问题,这曾被右翼指责为“社会主义”,尽管它本质上属于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除了就业问题,还必须关注平等、根除贫穷和实现基本需要(包括健康的需要和自主的需要)。这不仅意味着在分配制度方面,必须建立福利国家和福利社会,更重要的是在生产关系方面,必须确保公有制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不能只满足于私人生产力的发展,而必须把组织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放在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位置上。
就中国目前发展阶段来说,既然物质需要与物质生产之间的矛盾已经能够解决,广义的文化需要,即包括政治、社会、文化、生态需要在内的需要,已经提上日程,这些需要中绝大部分不再具有原来意义的“经济”特征,而是具有“社会”的特征和“人”的特征。如果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试图超越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分立,构建一个市场社会,即以交换为基础的社会;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把“社会”理解为摆脱了经济束缚的自由人联合体。同样,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把人理解为“经济人”,它的唯一需要就是物质需要,从而使人的需要陷入“异化”状态;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把人理解为完整的、有着丰富需要的人,这样的人必定已经超越了经济人、政治人、观念人等的分割状态,成为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具有自由个性的主体。与此相应,“生产”不仅限于物质生产,而是包括了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在内的五位一体的生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除了研究经济发展外,还必须研究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和人自身的再生产,研究需要的“人化”和“人化”需要的满足。这是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理论前提。
注释:
①马拥军、何亚娟:《中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动力机制刍议》,《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
②近年来,对马克思的需要理论,国内外出现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尤其是阿格妮丝·赫勒对马克思“根本需要”(国内学者译为“激进需要”) 理论的研究,对于准确把握马克思的观点,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③参见[英]莱恩·多亚尔、伊恩·高夫:《人的需要理论》,汪淳波、张宝莹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54页。
④马拥军、陈志超:《从需要角度重新审视价值体系概念》,《哲学动态》2013年第5期。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⑥参见[英]莱恩·多亚尔、伊恩·高夫:《人的需要理论》,汪淳波、张宝莹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369页。
⑦《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3、91页。
⑧[法]巴斯夏:《和谐经济论》(上),章爱民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年版,第21页、第25-26页。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到巴斯夏,但中文版通译作“巴师夏”。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102页。“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
⑩[巴基斯坦]马赫布卜·乌尔·哈克:《70年代就业和收入分布:一次新的透视》,载《发展文摘》,1971年10月号,第7页。转引自[澳大利亚]海因茨·沃尔夫冈·阿恩特:《经济发展思想史》,唐宇华、吴良健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