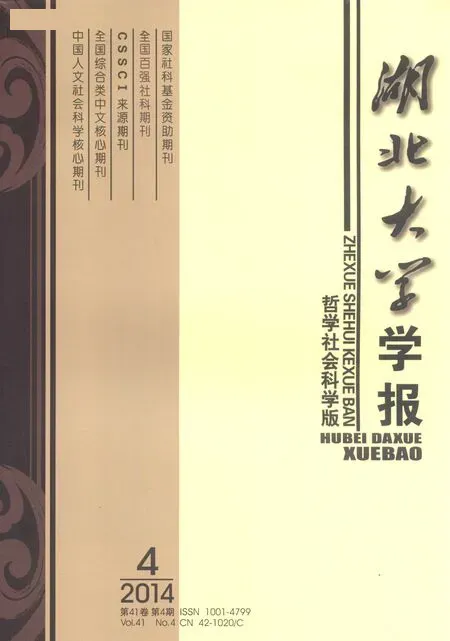论王阳明本体之乐
黄文红
(湖北大学哲学学院,湖北武汉430062)
“乐”本来是一个属于情感范畴的概念,一般认为含有个人的、感性的意蕴,往往给人以纵情享乐、恣情纵欲的联想。王阳明却明确地提出了“乐是心之本体”的命题,把“乐”从七情中独立出来提升到本体的层面,在“心之本体”的框架和前提下来讨论“乐”。这既是王阳明的特殊之处,也是其思想的特色之一。
一、“乐”何以为心之本体
从王阳明心学思想内部特点来看,“乐”能被规定为心之本体、能获得本体的地位有其可能性和必要性。“心之本体”也就是从孟子到陆九渊所谓的“本心”,王阳明也经常称之为“心体”:“圣人心体自然如此”、“惟养得心体正者能之”[1]21。在王阳明思想中,“心之本体”被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他经常强调为学“须于心体上用功,……这心体即所谓道。心体明即是道明,更无二,此是为学头脑处”[1]14。王阳明确立心体观念旨在打破理学析心与理,性与情,道心与人心之分。当有人问:“晦庵先生曰:‘人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此语如何?”阳明回答:“心即性,性即理,下‘与’字,恐未免为二。”[1]15阳明认为朱熹有析心理为二之弊,而直接提出“心即理”,主张心与理的同一性,完全以心为本,从而消解了心与理的二元对立。突破理本体,更多地关注心体,高扬心体地位和本心作用,正体现了王阳明与程朱一系理学的差异,也使“乐”为“心之本体”成为可能。
王阳明所说心体与理同一,是认为理为心的内在规定:“心也者,吾所得于天理,无间于天人,无分于古今。”[1]809在他那里,理完全被理解为道德之理、内心的先验道德法则。他认为“这心之本体原只是个天理”[1]27,“心之本体即是性,性即是理”[1]24。心之本体被赋予了与理与性同样的地位,处于同一层面。但阳明不仅认为心体具有先天普遍的道德之理,还将其与人的感性的存在相关联。他说:“耳目口鼻四肢,身也,非心安能视听言动?心欲视听言动,无耳目口鼻四肢亦不能,故无心则无身,无身则无心。”[1]90~91心虽不同于作为一种感性存在的肉体之身,但与身密切相关。首先,心主宰着身的感性活动,是耳目口鼻四肢之所以能视听言动的决定者,“非心安能视听言动”、“无心则无身”。其次,心包含着感性活动,“凡知觉处便是心”[1]121,并有赖于血肉之躯,没有身,心就无法作用,“心欲视听言动,无耳目口鼻四肢亦不能”、“无身则无心”。心与身的这种关系,也就使心与人的生命存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使心具有了感性存在的内容。王阳明还说到:“但指其充塞处言之谓之身,指其主宰处言之谓之心,指心之发动处谓之意,指意之灵明处谓之知,指意之涉着处谓之物:只是一件。”[1]90~91“身心意知物是一件”[1]90,以身心为一件,虽并非意味着他们是同一的,但意味着心获得了某些感性特质,确立了心与感性的联系,同时也使人的某些感性在与心的关系中得到适当的定位。
王阳明的身心合一论更是突破了朱子的性情二元论,而肯定了个体感性,并导向对最具有感性的个体情感的高度肯定,赋予心以情感的维度。在他对心体的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到:“心一而己。以其全体恻怛而言谓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谓之义,以其条理而言谓之理。”[1]43这里的“恻怛”犹如孟子的“恻隐”,正是最基本的道德情感。孟子以恻隐为仁之端,阳明则直接以心体全体恻怛的情感体验为仁。仁是出于真诚恻怛之情,通过“孝弟”之亲情则最能表现出来。王阳明说:“孟氏‘尧、舜之道,孝弟而已’者,是就人之良知发见得最真切笃厚、不容蔽昧处提省人,使人于事君处友仁民爱物,与凡动静语默间,皆只是致他那一念事亲从兄真诚恻怛的良知,即自然无不是道。”[1]85“孝弟”是“真诚恻怛”最真切笃厚的表现,须有真诚的心为根,“须是有个深爱做根,便自然如此”[1]3,如果没有“深爱做根”,即使“扮得许多温凊奉养是当”,也如同“扮戏子”一样而已。不是出于真情的行为,即使契合道德法则,也不等于具有道德性。因此,不管是仁还是孝弟都是在于普遍的爱,都是出于真诚恻怛的情感。
源于真诚恻怛的情感体验,当然侧重的是道德体验,但也包含着普通的感性情感。道德情感要达到完善的境界亦离不开感性的情感。阳明要求“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1]73,“好善,恶恶”是形上化的道德情感,“好好色,恶恶臭”是具体的感性情感。道德情感(好善,恶恶)要趋于完善、源于自然,就要具有如同好好色、恶恶臭一样的情感认同。在这个意义上,感性情感与精神愉悦的区分也有其相对性,它们都蕴含着经验的内容,只是程度有差异[2]73。王阳明进而把七情视为人心的题中应有之义,则更突出了他对心的情感构成的注重。
一般认为“七情”往往是与“四端”相对而言的,泛指人的感性情感形式。相对于“恻隐、羞恶、是非、辞让”之四端是就人心向善的表征而言,“七情”则被认为是沦为恶的罪魁祸首。而在王阳明那里,认为七情俱是人心原有的,情从来没有被排除于心之外,而是心的主要构成要素之一,阳明所说的无论是道心还是人心都具备情感的成份。“喜怒哀乐之未发,则是指其本体而言,性也。……喜怒哀乐之与思与知觉,皆心之所发。心统性情。性,心体也,情,心用也”[1]146。心在体,指涉性;在用,则指涉情。情是人心的本来蕴涵,从本然意义上看性情一致,从应然意义上看七情为心之发用,确立了七情的重要地位和自然合理性。
王阳明还将情放在一个很重视的位置,认为情感是人最基本的存在方式,他说:“除了人情事变,则无事矣。喜怒哀乐非人情乎?自视听言动以至富贵贫贱患难死生皆事变也,事变亦只在人情里。”[1]185“人情事变”亦即人的情感活动,人生中的事变层出不穷,但它只在人情里,都在情感中发生。事变之所以对人有价值和意义,是因为人在心中产生相应的情。事变有客观的环境和条件,但人情中的事变总是伴随着喜怒哀乐之情,这才是人生。同时人情也是通过事变表现出来的,情总是在具体的事变之中的喜怒哀乐之情。因此,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人“除了人情事变”,就再也没有什么了,也没有什么可说了,“天下事虽万变,吾所以应之不出乎喜怒哀乐四者”[1]155。情涵盖着所有的事,面对所有的事,人皆有相应的人情。王阳明倾向于把人视为置身于特定的生活情境,体验着喜怒哀乐等各种情感的感性生命存在。因而常人与圣贤的区分不在于情感的有与无,“圣人之行,初不远于人情”[1]197。
王阳明完全以心为本,心超越理成为终极的本体,肯定了人的主体性。其身心合一的人性论,则使心体不仅存天理,又离不开个体的感性存在,也使最具有感性色彩的个体情感获得合理地位,赋予心以情感的维度,进而直接赋予心体另一种品质——“乐”,提出了“乐是心之本体”的命题:“乐是心之本体,虽不同于七情之乐,而亦不外于七情之乐。虽则圣贤别有真乐,而亦常人之所同有。”[1]70
在诸多情感形式之中,阳明何以将乐提升到特别的地位。一般来说,在七情之中,乐表达的是一种肯定、满足和愉悦的正面情感经验,是人所欲求的,以此为人的内在本然状态,是容易为人接受和直接感受到的。另一方面,在儒家思想中,乐的观念源远流长,孔颜之乐是孜孜以求的圣人境界。在宋明理学中,乐则更成为一个倍受重视的范畴,“孔颜乐处”亦成为一个重要的论题。自周敦颐开创“寻仲尼、颜子乐处,所乐何事”的话题以来,宋明理学家们都探讨“孔颜乐处”所乐的是什么,力图找到“乐”的根源。通常他们就从自己的思想体系出发来寻找这一根源,认为“乐”作为最高的理想境界,就是主体与他们哲学的最高范畴(仁、理或道)合而为一时,自然而然产生的超越的体验,使“乐”成为一种最高人生境界,也使其具有了本体论的意义,但都没有明确置于理论上本体层次的地位。
宋明理学中对于“孔颜乐处”所乐者何的问题,有着很多差异和分歧,但实质上都认可乐在于乐道,当然乐道不是以道作为乐的对象,而是在体仁践道中内心自乐,即心与道一或心与理一之乐。但由于对心、道、理的内涵以及如何合一的理解不同,因而存在着分歧。在王阳明之前的宋明理学家那里,多是以道或理为其思想的核心,是通过心合于道或理来达到一体,心与道或理终为二,道或理在心外,乐的重点在于道或理。但在王阳明这里,是以心为其思想核心,心即理,良知即天理,不再说理的本体论,而侧重心的本体论。心即理意义下的心,其自身即包含理,乐乃是心之当体自性,真正成为心之乐,乐就在心中。由此,王阳明塑造出体认良知天理即是乐,将情感之乐改造为本体之乐,并赋予乐以境界的内蕴,使其成为人生命最本真的存在。“乐所标志的人生的高级境界,超越了个体名利贫富穷达的束缚,把心灵提升到与天地同流的境地,人由闻道进而在精神上与道合二为一,这样一种经过长期修养才能实现的自由怡悦、充实活泼的心境,……在这个意义上,乐不是作为情感范畴,而是作为境界范畴被规定为心体的”[3]72。
二、心之本体自乐
对于心之本体,王阳明在不同的情形下有不同的规定,他广泛地从心之本体的角度来阐释自己思想中的重要概念范畴,除了说“乐是心之本体”,他亦说:“至善者心之本体”,“心之本体即是天理”,“知是心之本体”,“诚是心之本体”,“定者心之本体”,“良知者心之本体”等,“阳明哲学的心体事实上被赋予了许多规定,这些规定都是正面的价值”[3]70。
王阳明对于心之本体虽然有种种说法,但并不是意味着存在不同的心体。他说:“人心是天渊。心之本体无所不该,原是一个天。……心之理无穷尽,原是一个渊。……于此便见一节之知,即全体之知;全体之知,即一节之知:总是一个本体。”[1]96可见心之本体是一整体,说本体即是说本体的全部,并没有部分或不同的本体,见本体的一节亦即见本体的全体。正如牟宗三先生所说:“凡此皆是就超越的道德本心辗转引申,实皆是分析的辞语。凡言‘本体’皆是当体自己之实性之义,每一实性皆渗透于其他实性而彻尽一切实性。”[4]156心之本体就是指心最内在的本然状态,只是王阳明因所指不同而有不同之名,实皆为同一本体。同时,通过当体本体的某一规定就可知本体的全部。
在王阳明有关心之本体的诸多规定中,最重要的应该是“良知者心之本体”,也最能体现出知本体之一节即可知全体,从体良知就能彻尽本体的其他种种规定。当有学生问:“知如何是心之本体?”他的解释是:“知是理之灵处。就其主宰处说便谓之心,就其禀赋处说便谓之性。”[1]34他还说,“夫心之本体,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灵觉,所谓良知也”[1]24,“诚是实理,只是一个良知”[1]106。良知即是理,即是心,即是性,就其侧重不同,心之本体的种种规定亦是对良知本体的引申。牟宗三先生指出:“至善是心之本体实即等于说良知明觉是其本体,故阳明亦云:‘知是心之本体’。至于‘定是心之本体’、‘乐是心之本体’,乃至‘真诚恻怛是心之本体’,皆是由‘知是心之本体’辗转引申而来的种种说法。”[4]168王阳明用以称谓本体的种种规定亦可用于良知,由良知亦可见本体的种种特性,由此也体现出本体是一个整体,由其部分即体现其全体。
王阳明将乐作为心之本体的规定之一,明确地把乐置于本体的地位来论述,乐也具有了本体的种种特征,为心的本然状态。在这种状态之中,其心自“乐”。天理流行、良知呈现即和畅,和畅处即为心体本然之乐:“乐是心之本体。仁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欣合和畅,原无间隔。……良知即是乐之本体。”[1]194天地生生之理凝聚于心便是心之体,此心体与天地万物融合无间,天地万物一体周流不息,生机活泼无滞,自然欣合和畅。“乐”也就是天地生生之理的体现,心体乐之特性的体现。乐作为心之本体就是以万物一体为核心的生命意识,是生命本真的怡然自得的本然状态。这里乐具有两个基本的内涵:一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一是“欣合和畅”。
本体之乐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就是个体生命与万物浑然一体,在天地无限生意流行中“与物同体”、“与物无对”。王阳明认为天地万物息息贯通,有着共同的本体,他指出:“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岂惟大人,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顾自小之耳。……为大人之学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而已耳;非能于本体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1]968这里王阳明认为,万物之能为一体,在于一体之仁,故人对孺子、鸟兽、草木、瓦石会有恻隐、不忍、悯恤、顾惜之心,也就是仁爱之心,一体之仁的范围遍及整个宇宙。这种对他人、生命万物乃至无知觉之物的仁爱之心,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东西,内在于人类的天命之性。天地万物为一体本是人心的本然状态,此非圣人所独有,而是人心体之同然,虽会为私欲昏蔽,但本体不会有所增益。
天地万物一体也是一种实然存在的状态,人与其他万物都是天地之间的一种自然存在,由同一气构成:“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岂惟草木瓦石为然,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只一体。”[1]107天地万物同此一气,没有间隔。无论我们对“气”作何理解,阳明用“一气流通”、“一气相通”这样的说法是要说明天地万物与人具有一体相通之感,但只有在人这里才可能认识和体验到人与天地万物一体。因为人与其他万物不同,“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1]214,人心作为天地间唯一的“灵明”,能视天地万物一体。这种体悟感觉到心灵超越了一切时空、物我人己界限,而与宇宙万物合为一体的生命本性,在精神上获得与天地同体的永恒,个体的生命存在价值得到了肯定,从而体验到一种“不知天地间更有何乐可代”之乐,也就是真正的本体之乐。
乐之欣合和畅,不仅在于与万物一体,还在于乐既然是心之本体,如本体一样具有廓然大公、寂然不动的虚灵特性,而无所执著、无所滞碍,阳明说:“人心本体原是明莹无滞的,原是个未发之中。”[1]117心的本然状态原无一物,是广大而无限的,是无私而大公的。本体的无滞、无待性使其能不受外在的影响,“心之本体无起无不起,虽妄念之发,而良知未尝不在,……虽昏塞之极,而良知未尝不明……虽有时而或放,其体实未尝不在也,……若谓良知亦有起处,则是有时而不在也,非其本体之谓耳”[1]61。本体无时不在,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会影响其本然的状态。乐之本体就其本然状态而言,亦具有无滞性,不会受外在发用的影响,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会影响其本然的状态,七情虽为人心合有,但心之本体无喜无怒无哀无乐无烦恼。因而乐之本体皦如明镜,七情虽往来心中,但一过而化,无任何一种滞留在心中,本体依然是无的状态,自然欣合和畅。“本体之欣合和畅,本来如是”,本体本自乐,并非因为具体对象而乐,因而乐无所待。一切情感万物对于乐之本体来说都不是它所具有的,听任其往来,乐之本体都无任何执著,“正像明亮的冰面一样,冰面运动的一切物体一滑而过,所以能够如此,因为它们都不属于冰之本体所具有,冰之本体不必、也不想牢牢抓住某些物体去拥有它们,这就叫‘无滞’”[3]190。本体如果有所执著,无论是善念还是恶念,都是本体的遮蔽和障碍,“良知即是乐之本体。此节论得大意亦皆是,但不宜便有所执著”[1]194。同样,乐之本体若有所执著,则会为客气物欲所搅,而始有间断不乐了,“心体本来具有纯粹的无执著性,指心的这种对任何东西都不执著的本然状态是人实现理想的自在境界的内在根据”[3]197。
良知即为乐之本体,通过阳明对良知本体的描述,亦可见心体乐之特性。“夫惟有道之士,真有以见其良知之昭明灵觉,圆融洞澈,廓然与太虚而同体。太虚之中,何物不有?而无一物能为太虚之障碍。盖吾良知之体,本自聪明睿知,本自宽裕温柔,本自发强刚毅,本自齐庄中正文理密察,本自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本无富贵之可慕,本无贫贱之可忧,本无得丧之可欣戚,爱憎之可取舍”[1]211。此处对良知心体的描述更显示出心体乐之特性,阳明以天下至圣所拥有之五德来显示本体的智、仁、勇、义、礼“本自有”的性质,并勾画出本体如渊泉广阔深远源源不绝的自发、活泼的性格;而同时以“本无富贵之可慕,本无贫贱之可忧,本无得丧之可欣戚,爱憎之可取舍”显现出本体的超越性、无待性“本无”的一面,对富贵的羡慕、对贫贱的忧虑、对得失的欣喜和悲戚都不是良知本体有的。良知本体原无一物,廓然大公,圆融自足,充塞流行不息,虽酬酢万变仍从容自若,无一毫人欲之私,不滞于任何一物,不为任何情绪所累。
阳明亦通过敬畏之戒慎恐惧与洒落之关系来展现心体乐之特征:“所谓良知也,君子之戒慎恐惧,惟恐其昭明灵觉者或有所昏昧放逸,流于非僻邪妄而失其本体之正耳。戒慎恐惧之功无时或间,则天理常存,而其昭明灵觉之本体,无所亏蔽,无所牵扰,无所恐惧忧患,无所好乐忿懥,无所意必固我,无所歉馁愧作。和融莹彻,充塞流行,动容周旋而中礼,从心所欲而不逾,斯乃所谓真洒落矣。是洒落生于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于戒慎恐惧之无间。孰谓敬畏之增反为洒落之累耶!惟夫不知洒落为吾心之体,敬畏为洒落之功,……尧舜之兢兢业业,文王之小心翼翼,皆敬畏之谓也,皆出乎其心体之自然也。出乎心体,非有所为而为之者,自然之谓也。”[1]189这里根据阳明的描述,心的本然之体,就是“和融莹彻,充塞流行,动容周旋而中礼,从心所欲而不逾”的一任天理流行,自然和乐不已的状态。天理是心之本体的内容,六个“无所”是心之本体的存在形式,二者是本然的统一,构成了本体之乐有与无两方面的内容。陈来先生认为这种在儒家哲学中所肯认的洒落境界即是人心本然之体,不仅没有牵扰、恐惧、忿懥、歉馁、愧怍、紧张、压抑等各种心理纠纷与动荡,而且是从心所欲不逾矩,是道德境界与本真情态的合而为一[3]228~229。
心体本是一个整体,从其一个特性可以渗透于其他特性,其种种规定亦可看做是本体之乐的规定。从本体之乐的内涵来看,至善、天理和良知是乐的内在规定,心体浑然与天理良知同一即是乐;而诚和定则可以看做是乐的存在形式,真实自然,平静而无烦扰。
三、本体之“乐”不外于七情之乐
乐作为心之本体,已作为一种本然存在于主体之中,“虽则圣贤别有真乐,而亦常人之所同有”[1]74,无论圣凡贤愚都具有这种本体之乐。此乐与良知一般是天赋予人心的,“盖良知之在人心,亘万古,塞宇宙,而无不同,不虑而知”[1]74,“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所同具者也”[1]62。本体之乐是不受外物变化而隐现的,和良知本体一样亘万古塞宇宙而无时无刻不存心中的,是人人皆有,而且人人相同的,每个人就其本心而言就已拥有欣合和畅之乐。本体之乐为人成就乐提供了内在根据,也赋予人能够体验乐的能力。此乐亦如阳明所说:“人人胸中各有个圣人”[1]92,“心之良知是谓圣”[1]280。自我的心体就是完满的,圣人就在“我”自己心中,而不必去圣人那里寻觅圣人气象。“圣人气象何由认得?自己良知原与圣人一般,若体认得自己良知明白,即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矣”[1]59。乐作为心之本体,是最高妙美好的生存状态,是人最理想的安身立命之地,此乐感召人们去呈现“吾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水无缺”[1]793的心灵明莹无滞的“至乐”。不过此乐是以潜在的形式存在,不是现成的,只有复得本体,乐才能成为主体存在的基本情态,并通过七情的形式显现出来。
王阳明说:“乐是心之本体,虽不同于七情之乐,而亦不外于七情之乐。”[1]59本体之乐是就乐的本然状态而言,是本体层面上的“万物一体”之乐,七情之乐则是具体的感性之乐。这样说来,本体之乐自然不同于七情之乐,但是它的发用流行又只能以具体的七情之乐的形式呈现,而七情之乐则须依本体之乐而得,本体之乐亦不外于七情之乐。二者体用不离,有是体则必有是用,有是用则体在其中,“即体而言用在体,即用而言体在用”[1]31。这是王阳明的“体用一源”说在情感体验上的应用[5]280。本体之乐是在七情之乐顺其自然的无滞流行中得以实现的,二者的区别,并不是理性与感性的区别,也和理性与感性的相互对立与排斥无关。另一方面,本体之乐也绝不能与七情之乐混同,本体之乐作为理想精神境界的特征与七情之乐的关系是由“不离不滞”的特殊模式建立起来的[3]228。王阳明亦是在这种模式下论说良知本体与七情的关系。他说:“盖良知虽不滞于喜怒忧惧,而喜怒忧惧亦不外于良知。”[1]65不管是乐之本体还是良知本体本是无一物,本是无,具有无滞性,不执著于七情,但又不能离七情。
对于本体之乐与七情之乐的关系,蒙培元先生认为本体之乐如同真己一样可称为真乐,真乐与七情之乐的关系就是真己与躯壳的关系[5]280,真己是本体我,即良知,躯壳是形体我,则是具体的、感性的。“这个真己是躯壳的主宰”,没有本体真乐也就无所谓七情之乐,而同时“真己何曾离着躯壳”[1]35。真乐作为真己之乐,须在感性我的具体情感活动中来实现。陈少明先生则认为本体之乐同其他具体情感的关系,就同道与万物的关系一样,“乐道之道,不是引起快乐的诸多对象之一,而乐道之乐也不是因不同对象或境遇而喜怒无常的具体情绪”[6]。这是从本体之乐和七情之乐的对象不同上来理解它们的关系,本体之乐是乐道之乐,但乐与道是不可分的,道即乐,乐即道。七情之乐是随万物而变化的具体情绪。道与万物不是同一层面的,道具有本体意义,而其他事物是经验的,具体的。乐道之乐也就为本体体验,七情之乐则为具体存在。
王阳明的七情之乐并非特指七情中“乐”这一具体的情感形式,真乐不能狭义的理解为愉悦,正如七情皆可入乐(y u è),七情之中任何一情亦都能表现“真乐”,此乐已为“忘情之乐”。冯有兰先生说:“忘情者,无哀乐,无哀乐则另有一种乐。此乐不是与哀乐相对的,而是超乎哀乐的乐。”[7]354《传习录下》中有一则记录——问:“乐是心之本体,不知遇大故,于哀哭时,此乐还在否?”先生曰:“须是大哭一番了方乐,不哭便不乐矣,虽哭,此心安处即是乐也,本体未尝有动。”[1]112在此,乐不是一种具体的情感,而是一种情感体验。哀之情发于本体之自然,哀则哭,哭是顺哀之情的行为与表达,大哭一番,内在情感得到了自然的渲露,如此方心安,心安理得便是乐。若不哭,则违哀之情,与顺任本体自然而发之情有所矛盾,故无法心安。但哭并不是为了心安,心安与否并不是预先计较的目的,而是“心体”当喜则喜、当哀则哀的自然情态,虽哭、虽哀,但本体之乐未尝有动。《传习录拾遗》有一则记载:直问:“‘圣人情顺万事而无情’。夫子哭则不歌,先儒解为余哀未忘。其说如何?”先生曰:“情顺万事而无情,只谓应物之主宰,无滞发于天理不容已处。如何便休得?是以哭则不歌。终不然,只哭一场后,便都是乐。更乐更无痛悼也。”[1]1176作为具体情感形式,一般情况下哀乐不会并存,哀若是发于心体之不容已处,出于真情实感,哭完之后虽然哀的情绪可以缓解,但不至于就转换成快乐喜悦。当哀之时尽显哀之情,心则是安,能如此则心总在乐中。
“乐是心之本体。顺本体是善,逆本体是恶。如哀当其情,则哀得本体,亦是乐”[8],喜怒哀乐之情是乐之心体应于物事而发,之所以发出不同之情是依照此物事是否顺乐之心体而定,任何一情只要是依心体而发都能表现本体真乐,都会有乐的体验。真能自知真乐与良知本体者,就能完全循之而行,其意念与行为就能完全地符合良知,如此,也就是心安,但伴随的情感不一定是乐,心安即是“乐”。心安之“乐”是指一种乐的体验,“是整体性的,超越层的,喜怒哀乐不仅可以包括在内,所有的情感都可以包括在内”[5]141。本体之“乐”体现在具体的七情发用上,如阳明说“心无体,以天地万物感应之是非为体”[1]108一般,“乐”无体,以人之七情为体。
[1]王阳明.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2]杨国荣.心学之思[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3]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牟宗三.从陆象山到刘蕺山[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5]蒙培元.情感与理性[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6]陈少明.论乐对儒道两家幸福观的反思[J].哲学研究,2008,(9).
[7]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
[8]水野实,等.阳明先生遗言录[J].中国文哲研究通讯,19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