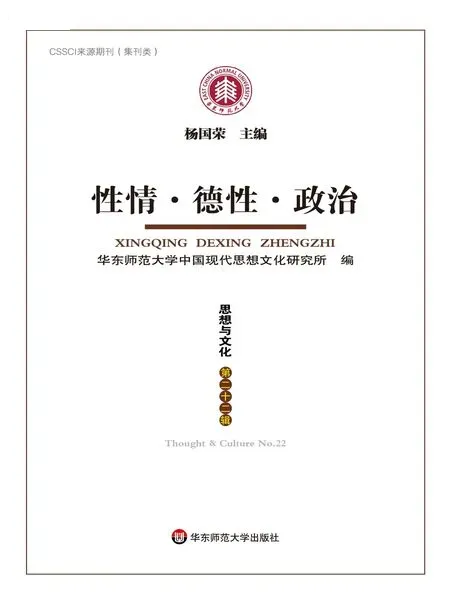韩儒金昌协的四端七情论与“性情经纬说”
●
一、 问题的背景
“四端七情之辩”是朝鲜儒学史中最重要的辩论之一。最主要的两场辩论发生于朝鲜中期的李退溪(名滉,1501—1571)与奇高峰(名大升,1527—1572)、李栗谷(名珥,1536—1584)与成牛溪(名浑,字浩原,1535—1598)之间。自此以后,朝鲜儒学分化岭南学派与畿湖学派,分别奉李退溪与李栗谷为宗师。金昌协(1651—1708),字仲和,号农岩,又号三洲。其父金寿恒(字久之,号文谷,1629—1689)是西人派中老论的代表。老论的领袖宋时烈(字英甫,号尤庵,1607—1689)是李栗谷的嫡系。金昌协师事宋时烈,自然继承李栗谷的学脉。但他的思想并非完全严守李栗谷的立场,而往往试图折中于李退溪与李栗谷之间。关于“四端七情”的问题,他撰有《四端七情说》。本文即以此份文献为中心,来探讨金昌协的四端七情论。
在讨论金昌协的四端七情论之前,我们有必要大略回顾李退溪与李栗谷的相关观点。他们之间最根本的分歧在于 :李退溪主张四端与七情是异质的,李栗谷则主张两者是同质的。因为李退溪认为 :四端是自内而发(“发于仁、义、礼、智之性”),七情则是外感而发。[注]李退溪说 :“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何从而发乎?发于仁、义、礼、智之性焉尔。喜、怒、哀、惧、爱、恶、欲,何从而发乎?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缘境而出焉尔。”见李滉 :《退溪集》,《韩国文集丛刊》第29—31辑,第1册,首尔 :民族文化推进会,第408页。李栗谷则认为 :四端与七情都是外感而发。[注]李栗谷说 :“若以感物而动言之,则四端亦然。……其感物者,与七情不异也。”见李珥 :《圣学辑要·修己第二·穷理第四》,《栗谷全书》第1册,首尔 :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所,1986年,第455页。由这一点又衍生出另一项分歧 :李退溪认为,四端是在七情之外;李栗谷则认为,七情包含四端,四端是七情中的善情。[注]李栗谷说 :“孟子于七情之中,剔出其善情,目为四端,非七情之外,别有四端也。”见李珥 :《圣学辑要·修己第二·穷理第四》,《栗谷全书》第1册,第455页。基于以上的分歧,李退溪提出“理气互发”之论 :“四则理发而气随之,七则气发而理乘之。”[注]李滉 :《退溪集》第1册,第419页。李栗谷只承认后半句,而主张“气发理乘一途”[注]李珥 :《栗谷全书》第1册,第209页。之说。最后一点又预设另一项分歧 :李退溪主张理能活动(“理发”);李栗谷则主张理不活动(“理无为”),但对气有主宰性。[注]李栗谷说 :“无形无为而为有形有为之主者,理也;有形有为而为无形无为之器者,气也。”见李珥 :《栗谷全书》第1册,第248页。
二、 金昌协关于“四端主理,七情主气”说的讨论
金昌协在《四端七情说》一开头便说 :
1) 四端,主理言而气在其中;七情,主气言而理在其中。四端之气,即七情之气;七情之理,即四端之理,非有二也。但其名言之际,意各有所主耳。《语类》“四端理之发,七情气之发”,其意似是如此。退陶说亦近此,但其推说太过,剖释已甚,遂成二歧之病耳。[注]金昌协 :《农岩集》第2册,《农岩续集》,《韩国文集丛刊》第161—162辑,第517页。为了讨论的方便,以下整段引述金昌协的文字,皆依序编号。
金昌协在这段文字中,除了在末句对李退溪略有微辞之外,几乎完全赞同李退溪之说。但其背景须略加说明。金昌协在此引述《朱子语类》中“四端是理之发,七情是气之发”[注]黎靖德编 :《朱子语类》,王星贤点校,北京 :中华书局,1986年,第1297页。之语。这是李退溪主张“理气互发”之论的重要文献依据。由于这句话与朱熹“理不活动”之义有所扞格,奇高峰视之为朱熹“一时偶发所偏指之语”[注]《两先生四七理气往复书》,上篇,第22页下,见《高峰集》第3辑,首尔 :民族文化推进会,1988—1989年,第112页。。连金昌协的同门后辈韩元震(字德昭,号南塘,1682—1751)都断言此语“或是记录之误,或是一时之见”[注]韩元震 :《朱子言论同异考》卷2,《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第2辑子部第2册,重庆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6页。。但金昌协不但不质疑此语,反而认同李退溪的“四端主理,七情主气”之说。因为李退溪说 :“大抵有理发而气随之者,则可主理而言耳,非谓理外于气,四端是也;有气发而理乘之者,则可主气而言耳,非谓气外于理,七情是也。”[注]李滉 :《退溪集》第1册,第421页。金昌协在上述引文的前半部即明白地呼应李退溪的“四端主理,七情主气”之说。
李栗谷并不赞同李退溪的“四端主理,七情主气”之说。其答成牛溪第二书云 :
且四端谓之主理,可也;七情谓之主气,则不可也。七情包理、气而言,非主气也。(人心、道心可作主理、主气之说,四端、七情则不可如此说,以四端在七情中,而七情兼理气故也。)子思论性情之德曰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只举七情而不举四端。若如兄言,七情为主气,则子思论“大本”、“达道”,而遗却理一边矣,岂不为大欠乎?[注]李珥 :《栗谷全书》第1册,第199—200页。按 :()中为原文以小字排印的文句,下同。
李栗谷为何反对“七情主气”之说呢?他在其答成牛溪第一书中明白地表示 :
心一也,而谓之道、谓之人者,性命、形气之别也。情一也,而或曰四,或曰七者,专言理、兼言气之不同也。[注]李珥 :《栗谷全书》第1册,第192页。
简言之,四端与七情均以理为其存有依据,但四端纯依于理,七情还涉及气。因此,四端可说是“主理”,七情则不可说是“主气”。对李栗谷而言,无论是《礼记·礼运篇》所说的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还是《中庸》所说的喜、怒、哀、乐四情,借用康德的用语来说,都是“自然情感”(physisches Gefühl),只是详略不同而已。如果说七情主气,则喜、怒、哀、乐四情也是主气。然则,《中庸》说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难道“大本”、“达道”也是就气而言吗?
对于李退溪的“四端主理,七情主气”之说,以及李栗谷的批评,金昌协站在李退溪的一边。其《四端七情说》中有如下的一段评论 :
2) 以七情为主气,栗谷非之。然此非谓七情不本乎理也。虽本乎理,而所主而言者,则在乎气耳。是以子思论“大本”、“达道”,不曰喜怒哀乐之发,是天下之达道也;而必以发而中节者,为达道者,正以人心气机之动,易于差忒,须是循理而得其正,然后可谓之“达道”也。栗谷却云 :“以七情为主气,则子思论‘大本’、‘达道’,而遗却理一边矣。”夫七情虽主气而言,发而中节,则理便在此矣。“理便在此”一句当更商,何得为遗理也。程子《好学论》亦曰 :“情既炽而益荡,其性凿矣。”伊川非不知情之本乎理,而其言如此者,亦以气为主焉耳。不独此也,古来论七情者,皆有戒之之意,非若四端专以扩充为言。其为主气而言,可见矣。“四端善一边,七情兼善恶;四端专言理,七情兼言气。”栗谷之说,非不明白,愚见不无少异者,所争只在“兼言气”一句耳。盖七情虽实兼理、气,而要以气为主。其善者,气之能循理者也;其不善者,气之不循理者也。其为兼善恶,如此而已,初不害其为主气也。退溪有见于此,而此处极精微难言,故分析之际,辄成二歧。而至其言“气发理乘,理发气随”,则名言之差,不免有累于正知见矣。然其意思之精详缜密,则后人亦不可不察也。[注]金昌协 :《农岩集》第2册,《农岩续集》,第518页。
这段文字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反驳李栗谷对李退溪“七情主气”说的批评。如上所述,李栗谷引《中庸》首章来反驳“七情主气”之说,认为此说会陷子思于不义 :“子思论‘大本’、‘达道’,而遗却理一边矣。”金昌协则为李退溪辩护说 :《中庸》所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系就喜、怒、哀、乐之“发而皆中节”而言,而中节是循理之结果,可见李退溪的“七情主气”之说并不会如李栗谷所言,使子思“遗却理一边”。金昌协所引的《好学论》即是程颐(伊川)的《颜子所好何学论》。[注]见程颢、程颐 :《二程集》,王孝鱼点校,北京 :中华书局,1981年,第577页。
引文2)的第二部分则是质疑李栗谷“四端善一边,七情兼善恶;四端专言理,七情兼言气”之说。此说李栗谷屡言之,如其答成牛溪第一书云 :“情一也,而或曰四,或曰七者,专言理、兼言气之不同也。……七情则统言人心之动,有此七者,四端则就七情中择其善一边而言也……欲说善一边,则当遵四端之说;欲兼善恶说,则当遵七情之说。”[注]李珥 :《栗谷全书》第1册,第192页。上文提过 :李退溪引述朱熹“四端是理之发,七情是气之发”之说来佐证他自己的“理气互发”之论。李栗谷虽未像奇高峰那样,质疑朱熹此语是“一时偶发所偏指之语”,但却对它另作别解 :“朱子‘发于理’、‘发于气’之说,意必有在……朱子之意,亦不过曰 :四端专言理,七情兼言气云尔耳;非曰四端则理先发,七情则气先发也。”[注]李珥 :《栗谷全书》第1册,第198页。
金昌协对李栗谷的批评系针对“七情兼善恶、兼言气”这一点,对于“四端善一边、专言理”并无异议。对金昌协而言,“七情主气”是整个问题的前提,只有在这个前提之下,才有“七情兼善恶”可言 :七情之气循理,则为善情;七情之气不循理,则为不善之情。既然“七情主气”是问题的前提,则说“七情兼言气”,便使问题的重点有所偏移了。因此,金昌协同意李退溪的“四端主理,七情主气”之说,而质疑李栗谷的“四端专言理,七情兼言气”之说。
三、 金昌协对“理气互发”论的批评
然而,在引文2)的最后,金昌协虽表示同意李退溪的“主理”、“主气”之说,但遗憾其“分析之际,辄成二歧”。在引文1)中,他也说李退溪“推说太过,剖释已甚,遂成二歧之病耳”。这便关联到李退溪的“气发理乘,理发气随”之说,亦即“理气互发”之论。金昌协质疑李退溪的“理气互发”之论的理由见诸《四端七情说》中的另一段文字 :
3) 人心有理、有气。其感于外物也,气机发动,而理则乘焉。七情者,就气机之发动而立名者也;四端则直指其道理之著见者耳,不干气事。所谓“不干气事”者,非谓四端无气自动也;言其说时,不夹带此气耳。观四者名目,便见当初立言之意,自与《中庸》、《乐记》不同。恻隐、羞恶,尚与爱、恶无甚异同;而若辞让、是非,则直就道理说,何曾干涉于气?以此推之,四端之异于七情可见矣。[注]金昌协 :《农岩集》第2册,《农岩续集》,第517页。
这段引文中所说的《乐记》当是《礼运》之误,因为“七情”之说首见于《礼记·礼运》篇,而非《乐记》篇。首先,金昌协言人心之动,“其感于外物也,气机发动,而理则乘焉”,这是“气发理乘”之说。说七情是“气发理乘”没问题,因为“七情者,就气机之发动而立名者也”。既然金昌协同意李退溪的“四端主理”之说,他是否认为四端并非“气发理乘”?他的答案是否定的。在他看来,说“四端主理”,只是说四端是理之直接表现(著见),与气无关。但他接着强调 :这并非意谓四端是“无气自动”;换言之,四端与七情一样,亦是“气机发动,而理则乘焉”。这显然预设了李栗谷的“气发理乘一途”之说,而否定了李退溪的“理发气随,气发理乘”之说。最后,金昌协特别解释,他何以认为四端是理之直接表现,与气无关。这点在恻隐、羞恶二端尚不明确,因为人们很容易将它们与七情中的爱、恶之情相混淆。但是辞让、是非二端并不会与七情相混淆,可见它们是理之直接表现,与气无关。李退溪视四端为“理发”,七情为“气发”,故主张两者之异质性。李栗谷则认为七情包四端,两者都是“气发而理乘之”,都是“感于物而动”,故是同质的。金昌协的观点则折中其间。就他同意“四端主理,七情主气”之说,其观点近乎李退溪。就他同意四端与七情均是“气机发动,而理则乘焉”,其观点近乎李栗谷。李栗谷的这个观点又预设 :理不活动,但对气有主宰性。金昌协则继承这项观点,而说 :“理虽曰无情意、无造作,然其必然、能然、当然、自然,有如陈北溪之说,则亦未尝漫无主宰也。是以人心之动,理虽乘载于气,而气亦听命于理。”[注]金昌协 :《农岩集》第2册,《农岩续集》,第519页。
四、 四端与七情的配对关系与包含关系
在引文3)的最后,金昌协触及四端与七情的配对关系。由于李栗谷主张七情包四端,“四端不能兼七情,而七情则兼四端”[注]李珥 :《栗谷全书》第1册,第192页。,四端与七情的配对关系便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李栗谷在答复成牛溪的信中曾作出如下的说明 :
七情之包四端,吾兄犹未见得乎?夫人之情,当喜而喜,临丧而哀,见所亲而慈爱,见理而欲穷之,见贤而欲齐之者(已上,喜、哀、爱、欲四情),仁之端也;当怒而怒,当恶而恶者(怒、恶二情),义之端也;见尊贵而畏惧者(惧情),礼之端也;当喜怒哀惧之际,知其所当喜、所当怒、所当哀、所当惧(此属是),又知其所不当喜、所不当怒、所不当哀、所不当惧者(此属非;此合七情,而知其是非之情也),智之端也。善情之发,不可枚举,大概如此。若以四端准于七情,则恻隐属爱,羞恶属恶,恭敬属惧,是非属于知其善恶与否之情也。七情之外,更无四端矣。[注]李珥 :《栗谷全书》第1册,第199页。
李栗谷的说明是否有说服力,此处可以不论。对本文的目的而言,更重要的是金昌协对李栗谷之上述说明所作的评论。这段评论也见于其《四端七情说》 :
4) 栗谷言 :“四端不能兼七情,七情则兼四端。”其实七情亦不能兼四端。栗谷虽以恭敬属之惧,恭敬之与惧,既不吻合,而所谓辞让,则在七情,又当何属耶?栗谷又以知喜、怒、哀、乐之当否为是非,而此亦未尽是非之意。要之,圣贤论人心性情,互有详略。如子思论喜、怒、哀、乐,亦概举情之大段而言,初非谓四者之外更无情也。《乐记》虽更加三者为七情,而于子思所云,却遗个“乐”字,则亦未为无余情也。不独此也,《大学》“正心”章忿懥、恐惧、好乐、忧患,亦情也;而忧患又《中庸》、《乐记》之所未言也。至孟子而有“四端”之名,则辞让、是非又前所未言。然则所谓“七情”,岂足以尽人心之用哉?[注]金昌协 :《农岩集》第2册,《农岩续集》,第517页。
在这段文字中,金昌协的观点可概括为“四端不能兼七情,七情亦不能兼四端”一语。此语包含两项要点 :首先,无论是《孟子》的“四端”、《中庸》的“喜怒哀乐”,还是《礼记·礼运》(金昌协误作《乐记》)的“七情”,都无法涵盖所有的情,其他的情还有《大学》“正心修身”章提到的忿懥、恐惧、好乐、忧患等情。对金昌协而言,情之样态极其复杂,“七情”之说只是概举其大要而已,而无法穷尽所有可能的样态。其次,四端与七情各有其范围,四端既不能包含七情,七情亦不能包含四端,故二者无法一一比配。因此,金昌协质疑李栗谷对四端与七情的比配。例如,孟子在《公孙丑上》第六章说 :“辞让之心,礼之端也。”在《告子上》第六章则说 :“恭敬之心,礼也。”李栗谷将恭敬比配于七情中的惧,金昌协认为很牵强,何况李栗谷也未交代辞让当比配于何情。
暂时撇开四端与七情的比配问题不谈,引文4)中还有一个隐而未现的问题 :金昌协并未质疑李栗谷的“四端不能兼七情”之说,在此问题上他是否引李栗谷为同调?其后韩元震有《农岩四七知觉辨说》之作。此文摘录金昌协《四端七情说》中的若干段落及其另外两段论“知觉”的文字,逐段加以评论。韩元震于文中引述了引文4)之后评论道 :
其谓“四端不能兼七情”者,语虽同于栗谷,而意则实不同矣。栗谷之意,盖以为 :四端纯善,故七情之善者固四端,而七情之恶者,非四端所可兼也云尔。此录则以为 :四端之为善,理为主而发;七情之有善,气为主而发。于善之中,亦有所发之不同,非但四端不能兼七情之恶,亦不能兼七情之善,而四、七各为一情,不能相兼云也。此所以栗谷之言,只归于未备;而此录之说,却堕于二歧也。[注]韩元震 :《南塘集》第2册,《拾遗》,《韩国文集丛刊》第201—202辑,第438页。
韩元震敏锐地看出 :尽管金昌协与李栗谷都主张“四端不能兼七情”,但他们两人据以立论的思想脉络完全不同。李栗谷认为七情有善有恶,而四端是七情中的善情,故主张“七情包四端”,并且在这个意义上说“四端不能兼七情”。另一方面,如上所述,金昌协赞同李退溪的“四端主理,七情主气”之说(虽然两人立论的思想脉络不同);在这个意义上,四端与七情自然是不相侔的,故四端不能兼七情,七情亦不能兼四端。金昌协虽然以“主理”、“主气”区分四端与七情,但他并不质疑李栗谷的“四端善一边、专言理”之说,这便是韩元震所说的“四端不能兼七情之恶”。就这一点而言,金昌协与李栗谷的观点是一致的。但韩元震进一步指出金昌协与李栗谷的分歧。对李栗谷而言,四端即是七情中的善情,故四端可以“兼七情之善”;但是对金昌协而言,四端与七情无法相比配,故四端无法涵盖七情中的善情,亦即无法“兼七情之善”。
五、 金昌协“性情经纬说”的思想背景
现在让我们回到四端与七情的比配问题。对于这个问题,金昌协进一步申论道 :
5) 朱夫子论性情体用,必以四德、四端为言,而未尝以七情分属四德者,非偶未之及也,盖知其难分属故耳。至栗谷始有是说。此就七情中可以分属四德者言,则可耳;若遂以七情一一分属于四德,则有不通者。如以喜属仁,以惧属礼,费力说来,虽若可通,终有牵强安排处,非自然的确不易之论也。或疑七情既不可分属四德,则人心有性外之情乎?曰 :不然也。情岂有不发于性者,但不当一一分属,各有攸主,如四端例耳。今且以喜言之,则见父母而喜者,仁之发也;诛恶逆而喜者,义之发也;喜习俎豆之事者,礼之发也;喜分别事物是非者,智之发也。以欲言之,则欲孝父母者,仁之发也;欲除恶逆者,义之发也;欲行古礼者,礼之发也;欲辨是非者,智之发也。忧、惧、乐亦皆仿此,此岂可专属一性!盖性为经,而情为纬,错综迭为体用。须如此看,方为活络,且似周尽。
更详爱、哀、怒、恶,却难与喜、欲、忧、惧、乐同例。盖凡爱、哀皆属仁,怒、恶皆属义。今若爱亲属之仁,爱君属之义,如喜、欲例,则又太拘。道理阔大,最忌死杀排定,作一例看。
又怒、恶虽皆属义,然见无礼于其亲而怒之、恶之者,谓之仁之发,亦无不可。其他亦有类此者。此皆道理错综处也。[注]金昌协 :《农岩集》第2册,《农岩续集》,第517—518页。
在这段文字中,金昌协明白提出“性为经,情为纬”之说。他一开始就说 :“朱夫子论性情体用,必以四德、四端为言。”盖在朱熹的义理架构中,四德(仁、义、礼、智)为“性”,四端为“情”,两者分属理、气,为体用关系。接着,金昌协说 :“(朱子)未尝以七情分属四德者,非偶未之及也,盖知其难分属故耳。至栗谷始有是说。”《朱子语类》中有几段关于《礼记·礼运》篇的文字,记录朱熹与其弟子关于四端与七情之比配问题的数则对话,例如,朱熹与其弟子叶贺孙[注]叶贺孙,字味道,生卒年不详,嘉定十三年(1220)进士。的如下对话 :
问 :“喜、怒、哀、惧、爱、恶、欲是七情,论来亦自性发。只是恶自羞恶发出,如喜、怒、爱、欲,恰都自恻隐上发。”曰 :“哀、惧是那个发?看来也只是从恻隐发,盖惧亦是怵惕之甚者。但七情不可分配四端,七情自于四端横贯过了。”[注]黎靖德编 :《朱子语类》,王星贤点校,第2242页。
又如另一则对话 :
刘圻父问七情分配四端。曰 :“喜、怒、爱、恶是仁、义,哀、惧主礼,欲属水,则是智。且粗恁地说,但也难分。”[注]黎靖德编 :《朱子语类》,王星贤点校,第2242页。刘圻父亦是朱熹门人,名子寰,生卒年不详,嘉定十年(1217)进士。
这两段文字似乎证实了金昌协所言 :“(朱子)未尝以七情分属四德者,非偶未之及也,盖知其难分属故耳。”但是韩元震却对朱熹的说法另作解释。他说 :“(朱子)又曰 :‘七情自于四端横贯过了’云,则七情之兼四端,又可知矣。四端、七情,虽不可一一分配,要亦未尝不会通为一也。”[注]韩元震 :《南塘集》第2册,《拾遗》,第438页。韩元震据此提出其“四端七情经纬说”而云 :“四端为经,七情为纬,而错综为一,则七情、四端,果是二物乎?盖四端衍之为七情,七情约之为四端,非有二也。”[注]韩元震 :《南塘集》第2册,《拾遗》,第438页。金昌协的“性情经纬说”与韩元震的“四端七情经纬说”在文献根据方面都援引朱熹所言 :“七情不可分配四端,七情自于四端横贯过了。”但是两说的意涵完全不同。简言之,金昌协的“性情经纬说”以“四端不能兼七情,七情亦不能兼四端”为前提;与之相异,韩元震的“四端七情经纬说”却归结为“四端衍之为七情,七情约之为四端”,亦即四端与七情在范围上的互涵。关于韩元震的“四端七情经纬说”,笔者已在另文讨论[注]参阅拙作 :《韩元震的“四端七情经纬说”》,黄俊杰编 :《朝鲜儒者对儒家传统的解释》,台北 :台大出版中心,2012年,第137—157页。,故此处不再赘言。
此外,必须指出的是 :金昌协的“性情经纬说”实脱胎于张显光(字德晦,号旅轩,1554—1637)的“理气为经纬”之说。张显光属于岭南学派,此说见于其《性理说》。“经纬”是一种譬喻,借自织布机的纵横轴,纵轴为经,横轴为纬。张显光“理气为经纬”之说涵盖三个层面,即太极、天地与人。他分别就这三个层面而论“最上经纬”、“天地经纬”、“在人经纬”。在讨论“在人经纬”时,他也特别提出了“性情经纬说” :
故天地之所流通,庶类之所包囿,万事之所纲领,百行之所根本,前万古,后万世,先天地,后天地,无此人则已;如有此人,则孰有无五常而为人者哉?目之虽有五焉,而五者实一理也,此非所谓在人之经乎?然其所以为性者,只是理也,故为经而常一焉;其发而为情者,便是气也,故为纬而有不一焉。情之目则曰喜、怒、哀、乐、爱、恶、欲,七者之外无他情焉。[注]张显光 :《旅轩先生全书》,《性理说》卷四,仁同张氏南山派宗亲会1982年刊本,第88页。
在朱熹的义理架构中,性即理,情属气,故性情关系为一特殊的理气关系。因此,张显光的“理气经纬说”即涵“性情经纬说”。张显光将仁、义、礼、智、信五常之性与喜、怒、哀、乐、爱、恶、欲七情的关系视为一种经纬关系。表面看来,张显光与金昌协都主张“性情经纬说”,但其意涵实不相同。张显光主张 :“情之目则曰喜、怒、哀、乐、爱、恶、欲,七者之外无他情焉。”金昌协则认为 :“四端”与“七情”都无法涵盖所有的情。此外,张显光认为 :“七情不是外四端而别为情,四端不是离七情而别为端也,就夫七情之中指其各从本德始发无伪者是四端也。”[注]张显光 :《旅轩先生全书》,《性理说》卷四,第101页。这同于韩元震的“四端衍之为七情,七情约之为四端”之说,而不同于金昌协的“四端不能兼七情,七情亦不能兼四端”之说。[注]关于张显光的“理气经纬说”,参阅蔡茂松 :《韩儒旅轩性理学研究》,《韩国学报》,1986年第6期,第15—50页;蔡茂松 :《朱子学说中的体用义与韩儒张旅轩的经纬说》,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n Sino-Korean-Japanese Cultural Relations, Taipei, 1983, pp.93-126.
在引文5)之中,金昌协特别强调 :就性、情为体用关系而言,四德与七情之间为体用关系。在这个意义下,七情当然可以分属于仁、义、礼、智四德,但这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他举例来说明,如七情中的喜与欲可以分别配属于仁、义、礼、智,其他诸情皆然。这显示 :四德与七情之间是一种错综交织的关系。金昌协即援引张显光的“经纬”之说来说明这种关系。
六、 “性情经纬说”的基本意涵
然而,四端也是情,它们与四德的关系为何?在此,金昌协提出两种经纬关系 :
6) 喜、怒、哀、乐分配春、秋、冬、夏,气象意思无所不合。但自此而遂欲分属于四德,如四端例,则又不可。盖性之与情,有本相统属者,有适同分配者。恻隐之于仁,羞恶之于义,恭敬之于礼,是非之于智,是本相统属者也。喜与仁之配春,乐与礼之配夏,哀与智之配冬,是适同分配者也。其中唯怒与义,既是本属,仍又同配,而要亦邂逅耳。[注]金昌协 :《农岩集》第2册,《农岩续集》,第521页。
依此,性、情之间的经纬关系有两种 :第一种是本质上固定对应的关系,如仁、义、礼、智四德之于恻隐、羞恶、恭敬(辞让)、是非四端,他称之为“本相统属”;第二种是偶然配属的关系,他称之为“适同分配”。关于“适同分配”,金昌协在此举喜、怒、哀、乐分配春、秋、冬、夏为例,以喜配春,以乐配夏,以哀配冬。剩下的怒应当配秋。但金昌协又强调 :怒之配秋“既是本属,仍又同配”,因为两者是“邂逅”。按理,“邂逅”应当是一种偶然的关系,属于“同配”,如何又是“本属”呢?金昌协的说法殊不可解,但他也未多作说明。
关于喜、怒、哀、乐与春、秋、冬、夏之关系,金昌协倒是有进一步的说明。他接着说 :
7) 统属、分配之异,固如前所云矣。又须知喜、怒、哀、乐分配四时,亦是自然之理,非人强以意安排也。且如喜时,其气自是和畅融泄,此即春生之木气为之也。乐时,其气自是满盈发散,此即夏长之火气为之也。怒时,其气自是威厉严肃,此即秋杀之金气为之也。哀时,其气自是惨淡凄静,此即冬寒之水气为之也。天人一气,固自如此,非其气象意思偶相似也。
或疑四行之理即四德也,四德之气即四行也。喜怒哀乐,即不分属于四德,则又何以四行之气分之耶?曰 :此等正是理气经纬错综处。但就实处验之,如向所谓诛恶逆而喜者,其理虽原于义,而既曰喜矣,则其和畅融泄,自是木气所为,于金气何干?推之哀、乐,莫不皆然。盖所乘之气与所原之理不必尽同,深体认之,便见其错综变化不可拘之妙,却令人意思活动。[注]金昌协 :《农岩集》第2册,《农岩续集》,第521页。
在这段引文的第一段中,金昌协进一步说明以喜、怒、哀、乐分配春、秋、冬、夏四时,再分配木、金、水、火四行的理由。但令人不解的是,他在此又强调 :这种分配“是自然之理,非人强以意安排也”,且“天人一气,固自如此,非其气象意思偶相似也”。既然如此,金昌协在引文6)中何以说它们是“适同分配”,而非“本相统属”呢?金昌协的另一段话似乎可以稍解我们的疑惑。其文曰 :
8) 喜、怒、哀、乐外,如爱配春木,恶配秋金,亦甚分明。而惧欲当何所配?窃谓惧当配冬水,欲当配春木。盖惧有收敛闭藏意,欲则近于爱耳。然欲之甚而至于重滞沈溺,则其意又近于冬水。此当更商。[注]金昌协 :《农岩集》第2册,《农岩续集》,第522页。
因为喜、怒、哀、乐之外,还有其他的情(如惧、爱、恶、欲)。若将这些情考虑进去,它们与四时及四行的配对关系就不是如此简单分明。
但更重要的是金昌协在引文7)的第二段所作的说明。在此,他特别从喜、怒、哀、乐四情与仁、义、礼、智四德(而非四时或四行)之关系来说明“适同分配”之义。他指出 :喜、怒、哀、乐之所以不能分属于四德,是因为“所乘之气与所原之理不必尽同”。对于这点,金昌协在另一段文字中有更进一步的说明 :
9) 四端,主理而言。故才说恻隐,便见其为仁之发;才说羞恶,便见其为义之发。辞让、是非皆然。盖理无不善,而其体用又各有定分,不容差互,故即其端而可知其所自来也。若七情,则主气而言。故但说爱,未定其为仁之端;但说恶,未定其为义之端。(爱、恶固属仁、义,而如爱货色,恶正直,未可谓仁义之端也。)他情皆然。盖气机之动,或循理或不循理,不能信其皆善也。此是一说。又但说喜,未见其原于何理;但说乐,未见其原于何理。(向所谓见父母而喜者仁之发,诛恶逆而喜者义之发,是也。)惧与欲亦然。盖理气经纬,迭为体用,而不可定其所自来。此又一说也。然则即七情而觅四端,终不可得乎?曰 :何为其不可?七情,固非无理,而自发者观其所发何自,则四端于是乎见矣。向吾所云,乃谓其但见其名,不可定其善恶,又不可定其何所自耳。此无他,以其主气而言也。[注]金昌协 :《农岩集》第2册,《农岩续集》,第521—522页。
这段文字包含金昌协“性情经纬说”的几层基本意涵。第一,四端于四德之所以为“本相统属”,是因为四端主理而无不善,故能在本质上一一对应于四德。第二,七情于四德之所以为“适同分配”,是因为七情主气而有善恶,故无法在本质上一一对应于四德。第三,金昌协并不否定七情亦有理为其存有依据,故能即七情而觅四端,只是他否定七情可与四端在本质上一一配对。第四,四德与七情的关系是理气关系,亦是体用关系,其间错综交织,如经纬然。
七、 结语
总结以上的讨论,我们可知 :金昌协在“四端七情”的问题上试图折衷于李退溪与李栗谷之间。一方面,他赞同李退溪的“四端主理,七情主气”之说,而质疑李栗谷的“四端专言理,七情兼言气”之说。但在另一方面,金昌协质疑李退溪的“理发气随,气发理乘”之说,而赞同李栗谷的“气发理乘一途”之说。再者,李栗谷主张“四端不能兼七情,七情则能兼四端”,金昌协则主张“四端不能兼七情,七情亦不能兼四端”。在这个思想背景之下,金昌协遂提出“性情经纬说”。此说上承张显光的“理气经纬说”,下启韩元震的“四端七情经纬说”。金昌协由“四端主理,七情主气”之说出发,而提出“性情经纬说”,以说明四德、四端、四时、四行与七情的关系,最后又回到“四端主理,七情主气”之说,可见此说是其四七论的基本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