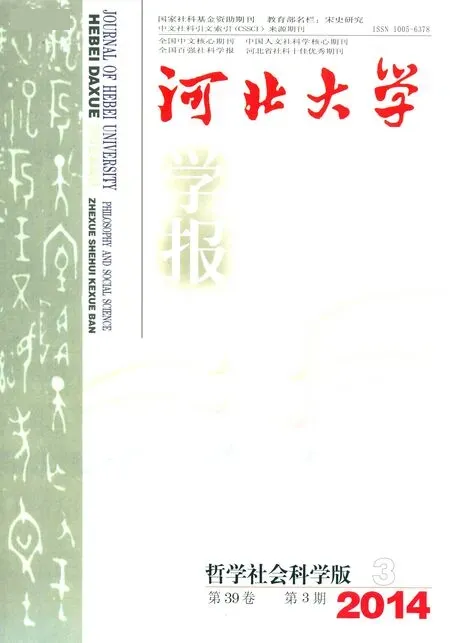韩国李朝《诗经》学以《礼》解《诗》的文化意义
刘毓庆,张安琪
(山西大学 文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李氏王朝(又称朝鲜王朝)是韩国封建制的鼎盛时期,1392年李成桂在朝鲜半岛建立后,大兴儒学,迎来儒学的全盛时代。此时,李氏王朝与中国明清、日本江户并肩组成东亚汉文化圈,形成儒学外传、接受的黄金时代。随着儒学发展,尤其是朱子《礼》学的东传,李朝后期出现了以《礼》解《诗》的文化现象。
一、以《礼》解《诗》的文化背景
《礼》在李朝主要指朱子《礼》学。用朱子关于《礼》的学说来解释《诗经》,是李朝《诗经》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诗》《礼》互证的一种诠释方式。朱子《礼》学是高丽末年伴随着朱子学传播到朝鲜半岛的。当时,《礼》学、《诗》学随着经筵传播,被帝王与士大夫接受;随着科举与图书交流,被普通士子接受;随着“训民正音”的创制,被下层民众接受。《诗》《礼》在传播过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诗》作为情感的载体,而《礼》则被视为李朝社会礼仪的典范,受到儒林的普遍欢迎。其时,李朝士人接受《大学》“家国天下”的理念,推崇由家庭内部的伦理建设进而延展至整个国家,而朱子《家礼》规范的是士大夫家庭内部的礼仪,因而得到更广泛的重视。《李朝实录》记载,王室率先实行《文公家礼》。太祖薨,其丧礼依据《文公家礼》而行之,“上擗踊呼泣,声闻于外,治丧一依《朱子家礼》”[2]16;士人李象靖(1711-1781年)云:“礼之用,散为三百三千,而其关于有家之常体而不可一日废者,惟冠婚丧祭为尤切,此朱夫子《家礼》之所为作”[4],可见《家礼》在社会中根植之深。
《家礼》的广泛传播,使李朝社会礼仪化。即使在乡野僻壤,“礼”也无处不在。五经,包括《诗经》,借助《礼》的传播而至民间。李朝儒者河受一(1553-1612年)作《射说》,通过《诗经》,阐发射与德的关系:
古之君子必学射,射者所以观德行也。射而不失其德,射之善者也。是故,天子以射而观德于诸侯,考其中否,以行黜陟。诸侯亦尽志于射,以习礼乐。故《书》曰:“侯以明之”。《诗》曰:“发彼有的,以祈尔爵”。射之义,大矣哉。孔子之射于矍相也,无勇而偾军者不多与焉,不忠而亡国者不得与焉,贪利者不得与焉。故去者半,入者半。孝悌于幼,好礼于老。能修身以俟死者,得在其位。故去者半,处者半。好学而不倦,好礼而不变,称道而不乱者又在其位。故仅有存者。射之设岂端使然哉。[5]
以礼观德,作者引用《宾之初筵》“发彼有的,以祈尔爵”来证明“礼”在推贤举士方面的作用。《诗》、《礼》互证,《诗》在《礼》的民间化过程中,从上层宫廷走向乡野民间,扩大了《诗》的传播,故到李朝后期,即出现以《礼》解《诗》的诠释方式。
二、以《礼》解《诗》
李朝后期,随着中国朱子学的深入,儒学制度化成为朝廷解决社会问题以及规范民风民俗的重要途径。其中,礼制的实施、《诗》学的传播起到普及儒学的作用。其次,李朝中期经历的壬辰倭乱(1592年)与丙子胡乱(1636年),两次异民族入侵,使得李朝社会经济衰退、社会伦理纲纪混乱。此时,朝廷希望通过礼制的确立、强制执行来收束民心。在这样的文化构想下,士人解《诗》不可避免地融入朝廷礼制的内容,形成以《礼》学解《诗》的文化思潮。
(一)解《诗》中的葬礼
李朝礼制中,以丧礼最为隆重。丧礼不仅历时三年,而且仪式繁复,有“礼莫重于丧”之说。士人关于丧葬的论著亦很多。从《退溪丧祭礼问答》开始,到《栗谷祭仪》《丧礼考证》《奉先诸仪》《丧礼通载》《五服通考》《丧礼抄》《丧礼备要》《丧礼手录》《丧礼正本》《国朝丧礼补编》《丧礼四笺》等。因为重视,士人解《诗》中涉及丧礼的论述也不少。李瀷在《诗经疾书》中论述葬礼。其中,他论述服丧时间:
《杂记》云:妇人非三年之丧不踰封,而吊如三年之丧,则君夫人归。《疏》云:出适为父母期而云三年者,以本亲言也。《礼》所谓不百里而奔丧者,凡奔丧者,日行百里,故妇人及日而入,不可日暮而行,与男子异也。父母之丧可以踰封,况百里乎?此云者本国丧亡,控于大国,非妇人之所处其君不量而轻许其臣,秉义而谏止也,故以穉狂诮之。[6]101
这是李瀷对《诗经·载驰》的注释,但其解《诗》重点却放在丧葬上。李瀷引《杂记》,“妇人非三年之丧不踰封”,可见,服丧时间为三年。李朝对服丧时间有明确规定,“父母逝世以后三年居丧,乃为儒教之丧礼也。”同时,李朝给出子女所以服丧三年的缘由,“凡人脱离开父母怀抱以前,起码要三年的时间由父母照顾之。因此为人之子者,应守三年之丧礼。……在朝鲜三国时代已曾守三年丧之礼,但于民间并不普遍。高丽朝仍然为父母之丧普通服百日丧;至于恭愍王十六年(1367年),依谏官李穑之请,下令皆服三年丧,但亦未彻底实施。改朝为李氏朝鲜,士大夫阶级大概守三年丧制,然一般百姓,尚行百日丧。至于中宗十年(1515年)赵光祖一派之儒教政治改革,下令不管阶级上下,地方之京乡,全体国民皆遵守此礼,始成为国礼国俗也”[7]131。在李朝士人看来,“礼”应该顺乎人情,因为“凡人脱离开父母怀抱以前,起码要三年的时间由父母照顾之”,故“父母逝世以后三年居丧”,合情合理。这种合情合理之想法,上升为统治阶级之意识,由朝廷规定为国家法制,遂成为“礼法”。国礼普世化,“始成为国礼国俗也”。李朝接受中国宋学,尤重朱子。朱子《家礼》关于“丧礼”有一套完整的程序,即“初终;沐浴、袭、为位、饭含;灵座、魂帛、铭旌;小敛衣衾;大敛;成服;朝夕哭奠、上食;吊、奠、赙;闻丧、奔丧、治丧;迁柩、朝祖、奠、赙、陈器、祖奠;遣奠;发引;及墓、下棺、祠后土、题木主、成坟;反哭;虞祭;卒哭;祔;小祥;大祥;禫;居丧杂仪”,而士人解《诗》不可能完全复制《家礼》中有关丧礼的内容,只能是根据《诗经》涉及的内容,结合本土实际,加以变通。《家礼》中“大祥”所须的器具,有香炉、盏盘、玄酒樽、床、盥盆、祝版登,约二十种之多,此为贫寒人家所难达到,故金长生《丧礼备要》变通为,“力不能具者,临时代以常用之器”[8]252。又因迁尸须有床,而李朝民俗不用床,故《丧礼备要》变通为,“无则用门扇”[8]252。李朝的丧葬习俗既取自中国,又本土化,体现出接受者主动的文化选择。
(二)解《诗》中的祭礼
李朝对丧葬之礼的重视,推而广之,上升到对祖先、天地的敬仰,故李朝亦重视祭礼。李朝后期解《诗》中也有对祭礼的论述。祭祀是古代社会最重大的活动之一,故有“国之大事,在祀在戎”[9]861之语。关于祭礼,李朝的《国朝五礼仪》有详细记载,而士人的诗解中,也多有体现。例如,金义淳(1757-1821)解释《采 》时,就涉及到“祭礼”的论述[10]455:
御制条问曰:大夫之祭也。铏爼之荐,籩豆之实,物无不备。采蘩、采 皆烹饪之事而略不以炮爓燔炙杂举而并称,何欤?《特牲》:主妇兩铏铏芼设于豆南,盖爼实男子设之,故只称 藻者,以夫人之所有事欤?《集传》:主妇荐豆,实以葅醢。必举豆实者,以明 藻之。为豆实而爼实之,不必举欤?抑曰蘩曰 曰藻,其称物也芳,则诗人之意,其亦如此乎?
臣对曰: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长,茍可荐者,莫不咸在。蒸荐以品物,禴荐以新味,则南国岁味莫先于 蘩,孟春始芽香脆可荐,则夫人之手执筐筥以供祭祀者,又莫先于 藻矣…… 蘩藻三者俱是物之芳者,则诗人所称盖亦取譬於夫人之徳也。
这里,金义淳举例大夫之祭,重点探讨了祭祀之物的选择。作者认为祭祀之物选择为“ 、蘋、藻”的原因在于“ 、蘩、藻三者,俱是物之芳者”,作者以此类推,“盖亦取譬于夫人之徳也”,可见,作者重视的不是祭礼的形式,而更看重祭礼的义理取向。此外,经筵大臣丁若镛在《诗经讲义》中就《采 》一诗就祭物的个数论述到:
臣对曰:《郊特牲》曰,鼎俎奇而籩豆偶,阴阳之义也。故凡祭礼男子荐爼,妇人荐豆,观於《少牢》《特牲》之礼可验也。不惟是也,二簋四簋六簋八簋皆用偶數,故主妇荐之;三献五献七献九献皆用奇数,故男子献之。主妇唯亚献而已,二籩四籩六籩八籩皆用偶數,故妇人荐之;大羹一镫男子荐之,皆此义也。[11]52
虽然是祭礼,李朝儒者也融入义理精神,用《易》之“阴阳”概念来解释“礼”的内涵,使“礼”也具有了形而上的理论之思。对于祭礼器物,丁若镛引用《效特牲》,“鼎俎奇而籩豆偶”,作者认为是取“阴阳之义也”。丁若镛用具体的祭礼内容来印证此观点,使得以《礼》解《诗》具有了实在的内容。
祭礼是众多“礼”的一种,也具有严格的等级差异。不同等级的人实施祭礼时享有不同等级的待遇。李朝士人许傅(1797-1886)论述了祭礼的等级性:
上曰:祭礼今皆从古否?《五礼仪》或有不遵者,何也?
臣对曰:先王之礼,庙有定数。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二庙,庶人无庙。只祭禰於寢,祭馔有数。鼎爼奇而籩豆偶,《五礼仪》亦因古礼定庙制。祭馔则六品以上亦不过鱼肉饼脯醢各一器,果至数品,庶人则只用菜果。盖古者,大夫有圭田则祭,庶人稷馈。今东俗虽庶人皆用大夫之礼,必祭四代,馔品无数,汩董杂陈,而曰家家。礼僭於上无度,此皆由於侈靡之风盛而时王之制亦不行也,圣王有作,则古礼可复矣。[12]634
许傅论述天子之礼、大夫之礼时,对于庙数、祭物都有具体的规定,不能僭越。许傅在论述古礼时,也论述了李朝接受中国礼学之后,他们实行礼的情况,“今东俗虽庶人皆用大夫之礼,必祭四代,馔品无数,汩董杂陈”,而当时庶人僭越的原因在于,“此皆由於侈靡之风盛而时王之制亦不行也”,指明李朝建设礼制的紧迫性与必然性。
(三)解《诗》中的婚礼
“昏礼者,礼之本也”。《郊特牲》云:“昏礼,万世之始也”。因为婚礼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开始,故《诗经》首篇《关雎》就是一篇婚礼的乐歌。而在婚礼中,蘩、 、荇、蓳是祭祀之物。李朝对婚礼进行拓展,上述诸物也成为其他“始见”仪式的开始。“凡蘩 荇蓳皆涧溪之毛,取于至贱而用之至尊。洁濯而示诚,古道即然。后妃之始,至躬采於沼沚之间,将以芼之也。始见之礼,生则用幣,死必奠菜,其例不独昏因也。於师弟可况也,弟子之求师必用束修,而士初入学则释菜於先师,古道然也。”[6]9“蘩 荇蓳皆涧溪之毛,取于至贱而用之至尊”,不仅用于婚礼,而且也用于拜师之礼,因为“洁濯而示诚”,通过祭物表现出礼义本身的纯洁性与神圣性。因为婚礼包含着宗族性与社会性的功能,故李朝对其采取慎重的态度,且非常注重婚礼的古制:
华桃夭可证,此以时为喻,非指其红白也。非一树二色也。《易》曰:帝乙归妹。《昏礼》即殷汤之所剏也。殷尚白,故賁之六四,云白马翰如匪寇,昏媾礼所以不忘其本,故周人尚赤,而惟昏用白也。《唐棣之华》喻姬车之色白也。箕子,殷人也。布教於东方,白马朝周之说至今流传东人浃,其遗化白衣大冠,千百世不改。大昏则犹白马,故胜国忠宣尚元公主以白马八十匹为礼,可以见矣。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用此互参王姬之白车,亦可旁证。[6]46
李瀷对《何彼秾矣》的诗解,探讨了韩国婚礼尚白的原因。李瀷提出:“殷尚白,昏媾礼所以不忘其本”,而《檀弓》也记载:“殷人尚白”。《淮南子·齐俗训》:“殷人,其服尚白”。《通俗编·服饰》:“三代殷人尚白,其时服色,或通用白无忌,若周则不然矣”。而韩国始祖箕子,“殷人也,布教於东方”。《汉书·地理志下》:“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因箕子为殷人,“殷人尚白”,故李朝婚礼礼服古制尚白,并且以“胜国忠宣尚元公主以白马八十匹为礼”作为例证,间接说明韩国礼制与中国千丝万缕的联系。
此外,丁若镛在注解《摽有梅》时,还就婚礼的程序进行了论述:
请期,六礼之一也,不待吉日而欲迨今日,失礼也?
臣对曰:婚未必六礼也。《谷梁传》只有纳采、问名、纳征、告期,四者之礼,至《士婚礼》六礼 始备。意古者,礼简而后渐繁文也,故曰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不待会礼而行之。又云凶年殺礼多,昏奔者不禁,此圣王察民之意也。《语类》以为商周之际,方变恶入善,未可责备,此其所以为正风也。《左传》范宣子聘魯,赋《摽有梅》取其及时之义,则亦或有惜其芳泽之义,与《桃夭》同也。[11]63
李朝士人丁若镛认为婚礼不必六礼,只要具有基本的四礼即可,因为古礼简而后渐繁复,遵循古礼即可。士人以《礼》解《诗》之婚恋爱情诗,陈列《礼》对婚礼风俗、程序的详细规定,通过《诗》使礼制普及、深入。
三、以《礼》解《诗》的文化意义
李朝儒学在本土化、民间化过程中,《礼》与《诗》的作用是不同的。韩(氵右)劤《韩国通史》曾云:“(新王朝之开国君王及新兴儒臣)以己为标准,而将社会价值以朱子学之价值为规范,而不许其脱离规范。尤其以《朱子家礼》为标准,乃因‘礼’本身具有形式与名分两方面维系社会秩序之最佳方式”[13]219。卢仁淑在《朱子家礼与韩国之礼学》中也阐述到“礼”的作用:“礼为具有形式与端正名分之具体功能,为维护社会秩序之最佳法宝,而《文公家礼》适为维护社会秩序之规范,故《文公家礼》随朱子学之东传,而为当时朝廷及社会所共尊。例如以家庙制度及祭祀仪式之推广实行,即所以图谋其社会秩序之恢复及国家之安定”[7]118。由于《朱子家礼》从形式上规范社会伦理秩序,故在民间化过程中,它以《乡约》的形式在民众中强制执行。关于李朝社会《文公家礼》与乡约施行的特色,黄元九曾论及到,他说:
(文公)《家礼》,在李朝社会中,为上部阶层之权力中心之礼观念,其中具有强制性。乡约是在下部阶层中,为朱子学具有之社会统制之道义规范。……前者具有阶层之普遍性,后者具有地域之特殊性。[14]244-245
《家礼》伴随着乡约,目的是“化民成俗”,使民众通过“礼”的规范,把儒学内化为思维模式,从而奠定民众的意识形态。而以《礼》解《诗》,《诗》在《礼》的民间化过程中通过情感的塑造,内化民众温柔敦厚的情感。《诗》《礼》并行,士人金孝元作《射以观德赋》,于中可见李朝文教之盛:
猗欤美哉,射者之有志。反己而已,争也君子。俨体直而心平,妙圣中而智至。方其泽宫日宴,西序风媚。兽俟初张,羽旌乍倚。歌《采 》而为节,挟乘矢而耦比。历阶钩盈,进退有仪。当物循声,升降中规。注一心于度释,凝四肢于体反。羌执箫而顺羽,迭宫举而商偃。剡注参连,发有的而祈爵。左贤右奇,委纯筹而视获。得隽非私,胜己何怨。艺容两美,礼义交尽。四正具举,周诗道其燕誉。[14]165
作者用骈散相间的语言,讲述了乡射礼礼仪的过程。在该过程中,“歌《采 》而为节,挟乘矢而耦比”。《诗》是《射礼》施行过程中的礼乐部分,《诗》随着礼乐的推行而由朝廷普及至民间,《诗经》学也走向深化。
余 论
李朝后期以朱子《礼》学解《诗》的诠释方式,使得李朝《诗经》学呈现出全方位接受中国朱子学的态势,并在接受过程中,把《诗经》与其他儒学经典勾连起来,形成五经互通的接受体系。此外,充当国家制度的《礼》学,在朝廷向民众的强制推行中,通过《诗》、《礼》互证的方式,以达到《诗》的民众普及,使韩国儒学全方位的走向民间化,为韩国儒学的普及打下夯实的民众基础,并塑造了韩国民众的儒学价值观,为韩国日后近现代化的高速发展涂抹上了文化底色。
[1]太宗实录:卷十五[M].首尔: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1980.
[2]世宗实录:卷二十三[M].首尔: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1980.
[3]李象靖.家礼辑遗序[M]//大山集:卷四十三.韩国文集丛刊,首尔:景仁文化社,1990.
[4]李植.家礼剥解[M]//泽堂集·别集:卷十六.韩国文集丛刊,首尔:景仁文化社,1990.
[5]河受一.松亭集·续集卷二[M]//韩国文集丛刊,首尔:景仁文化社,1990.
[6]李瀷.诗经疾书[M]//韩国诗经集成3.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社,1988.
[7]卢仁淑.朱子家礼与韩国之礼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8]金长生.丧礼备要[M]//金长生全书:卷三十一.首尔:白山学会,1978.
[9]杨伯峻.左传·成公十三年.[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0]金义淳.讲义诗传[M]//韩国诗经集成4.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社,1988.
[11]丁若镛.诗经讲义[M]//韩国诗经集成9.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社,1988.
[12]许傅.经筵讲义-诗[M]//韩国诗经集成·诗经11.首尔:成均馆大学校,1988.
[13]韩(氵右)劤.韩国通史[M].首尔:乙酉文化社,1981.
[14]黄元九.李朝礼学之形成过程[J].东方学志六辑.首尔:延世大学校国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