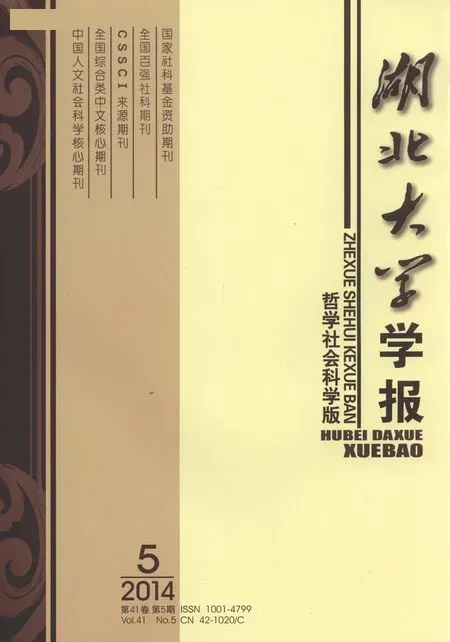谢朓诗赋互文性初探
孙 晶
(烟台大学人文学院,山东烟台264005)
“互文性”这一术语是由法国著名文学理论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于1960年代创设的。克里斯蒂娃说:“任何文本的构成都仿佛是一些引文的拼接,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个文本的吸收和转换。互文性概念占据了互主体性概念的位置。诗性语言至少是作为双重语言被阅读的。……文本是一种文本置换,是一种互文性:在一个文本的空间里,取自其他文本的各种陈述相互交叉,相互中和。”[1]互文性这一理论术语通常被用来指两个或两个以上文本间发生的交互映发、交相发明的互文性关系,“它囊括了文学作品之间互相交错、彼此依赖的若干表现形式”[2]1。“互文性概念对于文学研究的重要,在于它指出了先后产生的文本间存在的一种普遍关联”[3]。克丽斯蒂娃区分了互文性的两个方面:“水平”(horizontal)互文性和“垂直”(vertical)互文性。据此,国内互文性理论研究者辛斌指出:“水平互文性指的是一段话语与一连串其他话语之间的具有对话性的互文关系。这种互文性能使人们注意到话语的这样一种特性,即它回应此前的话语并期待自己得到此后话语的回应。在这个意义上,‘语篇中的词既属于写作主体又属于受话人’。水平互文性典型的例子是会话中相互回应的话轮或往来的信函。垂直互文性指构成某一语篇较直接或间接的那些语境,即从历史的或当代的角度看它以各种方式和与之相关的那些语篇。”[4]126辛斌对克里斯蒂娃所说的水平互文性和垂直互文性作了更明确的阐发。
谢朓是南齐时期冠冕群伦、独步一代的著名文士,他的山水诗和新体诗尤为人们所称道;同时,他也是东晋南朝时期谢氏家族中除谢灵运之外,现存赋作最多的赋家。纵观谢朓的文学创作,其诗赋之间很明显具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这里所探讨的谢朓诗赋互文性主要指这种不同语篇或不同体裁之间的一种互文性关系。在谢朓诗赋文中有两组关系非常密切的作品值得我们注意:A.谢朓《酬德赋》与谢朓、沈约之间的互赠诗歌;B.谢朓《临楚江赋》与谢朓供职荆州西府前后的诗歌和骈文。这两组作品或以水平互文性为主或以垂直互文性为主,构成各自的话语空间。
一、《酬德赋》与沈、谢诗赋的互文性
谢朓《酬德赋》是一篇期望达到预期交际效果的文本,它有一个明确的对话对象,这就是赋序中所说的“右卫沈侯”沈约。赋序是进入《酬德赋》正文的“门槛”,它也是影响读者方面的实用而优越的区域,对于解读整篇赋来说至关重要。与某些他人捉刀代笔而作的赋序不同,谢朓《酬德赋序》出自谢朓本人之手。赋序中说:“右卫沈侯以冠世伟才,眷予以国士。以建武二年,余将南牧,见赠五言。余时病,既以不堪莅职,又不获复诗。四年,余忝役朱方,又致一首。迫东偏寇乱,良无暇日。其夏还京师,且事燕言,未遑篇章之思。沈侯之丽藻天逸,固难以报章;且欲申之赋颂,得尽体物之旨。诗不云乎:无言不酬,无德不报。言既未敢为酬,然所报者寡于德耳,故称之《酬德赋》。”[5]1赋序提到了沈约的两次赠诗以及谢朓未能酬答的原因,但从现存沈约集、谢朓集中都找不到沈约这两篇赠诗的原文。因此,赋的正文以及沈、谢交往的其他诗歌就成了了解沈约赠诗的互文本,同时,沈、谢交往的其他诗歌也是《酬德赋》的互文本。有趣的是,沈约赠谢朓的是诗歌,而谢朓回复时却用了赋体。当然,通读全赋,我们可以了解到此赋并非仅为酬德,其实,它更是一篇谢朓向知己倾述内心苦闷的载体。如果从水平互文性角度看,这篇赋作与沈、谢其他诗赋之间具有互文性关系,赋中的话语回应此前的话语并期待自己得到此后话语的回应。
《梁书·武帝本纪》云:“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高祖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并游焉,号曰‘八友’。”[6]2沈、谢是竟陵八友群体中的重要人物,也是南齐诗坛上的重要作家,他们讲论音律、酬答唱和,极一时之盛。从现存沈约、谢朓诗赋作品看,沈、谢在当时上层社会文人群体的生活中,曾作过不少同题赋作、诗作或相互唱和的作品,如他们都曾奉竟陵王萧子良之命,作过《拟风赋》、《高松赋》;沈约曾作《奉和竟陵王经刘瓛墓》,谢朓有《奉和竟陵王同沈右率过刘先生墓》;沈、谢同作《咏竹火笼》,沈、谢也都有同咏坐上器玩,如沈约有《咏竹槟榔盘》、谢朓有《乌皮隐几》;沈、谢也都有同咏乐器,如沈约的《箎》、谢朓的《琴》。这些诗赋正是《酬德赋》“惟敦牂之旅岁,寔兴齐之二六;奉武运之方昌,睹休风之未淑。龙楼俨而洞开,梁邸焕其重复。君奉笔于帝储,我曳裾于皇穆;藉风云之化景,申游好于兰菊。结德言而为佩,带芳猷而为服”的互文本,《酬德赋》中的这些话语又为沈、谢上述诗赋文本提供了一种氛围,并形成一种呼应。
“所知共歌笑,谁忍别笑歌”,王融《饯谢文学》中的这两句诗,表达了当谢朓被任为镇西功曹,转文学,准备西赴荆州之时,友朋不忍别离的情感。当时谢朓曾写《离夜》三首,表达离情真挚感人,沈约、虞炎、范云、萧琛、刘绘都写下了《饯谢文学》,沈约“一望沮漳水。宁思江海会。以我径寸心。从君千里外”的诗语,比较感人。谢朓又作《和别沈右率诸君》,诗中谢朓想象自己“望望荆台下,归梦相思夕”情景。这些唱和在文学史上留下佳话,但在谢朓《酬德赋》中,则呈现空白状态,可以说沈、谢等人的这些诗以及谢朓为随王文学时沈、谢的同题之作《芳树》、《临高台》等诗,又可称为《酬德赋》的互补型的互文本。
从相互间的对话关系来看,饯送谢朓之时,沈约、王融等与谢朓以诗话别的情形在《酬德赋》中显然已被略过,但《酬德赋》却非常明确地提及了沈、谢等人在齐武帝病殁,南齐朝廷动荡不安之后的多次赠别。此时的谢朓已感到“虽鱼鸟之欲安,骇风川而回薄”,表现出身不由己的忧惧心理。《酬德赋》第一次具体提到的赠别是,萧鸾辅政之时,沈约被出为宁朔将军、东阳太守时的沈、谢之别。谢朓《酬德赋》云:“予窘迹以多愧,块离尤而独处;君纡组于名邦,贻话言于洲渚。怅分手于东津,望徂舟而延佇;虑古今之为隔,岂山川之云阻!”写到当时谢朓等人送别沈约的情形。沈约为东阳太守时有《新安江至清浅深见底贻京邑游好》一诗,在此可视为《酬德赋》的一种互文本,也是一种期待回应类的互文本。二者的关系,时间上,沈约诗在先,谢朓《酬德赋》在后,然而《酬德赋》写话别时的情景,又发生在沈约《新安江至清浅深见底贻京邑游好》之前,因此,这种互文本,也有一个倒叙性与进行时的互涉性。赋中第二次具体提到的赠别情形是谢朓被任命为宣城太守之时,《酬德赋》云:“我舣舟以命徒,将汨徂于南夏,既勗余以炯戒,又引之以风雅;若笙簧之在听,虽舒忧而可假。昔痁病于漳滨,思继歌而莫写。”这一段本身是赋序“建武二年,余将南牧,见赠五言。余时病,既以不堪莅职,又不获复诗”的互文,这是一种副文本(指赋序)与赋之正文的互文。而“既勗余以炯戒,又引之以风雅;若笙簧之在听,虽舒忧而可假”则是我们理解沈约当时赠诗内容的互文本。“昔痁病于漳滨,思继歌而莫写”是谢朓对沈约赠诗而自己未能回应的说明。出守宣城之时,谢朓还有《在郡卧病呈沈尚书》,沈约有《和谢宣城》,这对《酬德赋》来说,又是一种互补型的互文。赋中第三次具体提到的赠别是谢朓被任命为南东海太守时沈约与谢朓的话别。《酬德赋》云:“恩灵降之未已,奉京枌而作傅。临邦途之永陌,怀余马于骐馵;望平津而出宿,登崇冈而兴赋。顾飞幰之南回,引行镳而东驱;何瑰才之博侈,申赠辞于萱树。指代匠而切偲,比治素而引喻;方含毫而报章,迫纷埃之东骛。”这是赋序“四年,余忝役朱方,又致一首。迫东偏寇乱,良无暇日”的一种互文。“朱方”,容易引起误解,有人认为指湘州,实际上当指南东海郡,曹融南引《太平寰宇记》云:“润州,《禹贡》扬州之域,春秋时属吴,谓其为朱方。……宋因置南东海郡及南徐州。”[5]5赋的正文有“奉京枌而作傅”之语,其中的“京”指京口,即南徐州。《南齐书·州郡志》:“南徐州,镇京口。……今京城因山为垒,望海临江,缘江为境,似河内郡,内镇优重。”[7]246“作傅”指“建武四年,(谢朓)出为晋安王镇北谘议、南徐州太守,行南徐州事”[7]826。而“何瑰才之博侈,申赠辞于萱树。指代匠而切偲,比治素而引喻”,也是我们理解沈约当时赠诗内容的珍贵的互文本。“方含毫而报章,迫纷埃之东骛”,同样是一种谢朓对沈约赠诗的酬答。当然这种赋中的酬答之意,在谢朓看来,又都过于简略,所以谢朓在赋中又进一步表达迫于事务而不能及时回复,然而又不能忘怀的拳拳之情。而当谢朓下狱而死之后,沈约又有《伤谢朓》一诗,对谢朓之才深表惋惜,对谢朓之死深表同情。可以说,这又是沈约对谢朓《酬德赋》的一种回赠。
二、《临楚江赋》与谢朓诗文的互文性
《临楚江赋》,《初学记》作《楚江赋》,是现存谢朓赋中唯一写到山水壮阔、秋景迷茫的山水赋,情感极其压抑,但是这篇赋的创作原委却不甚明了。而谢朓之诗《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和笺文《拜中军记室辞随王笺》则与《临楚江赋》形成了一种垂直互文性。也就是说谢朓盘桓荆州西府以及返都建康前后的作品具有互文性,这一时期的某篇作品有其他语篇的片断。这不仅为推断《临楚江赋》的创作时间和原委提供了较为可靠的信息,甚至为解读此赋中的难点即“愿希光兮秋月,承末照于遗簪”,也提供了极为关键的信息。
从谢朓生平事迹及谢朓所处时境与心绪看,《临楚江赋》当作于谢朓任随王萧子隆文学之时。萧子隆为齐武帝第八子,年纪比谢朓小,当时他任镇西将军、荆州刺史,这是萧齐家族中一个才可比曹植的人物,齐武帝曾对王俭说,萧子隆是“吾家东阿也”[7]710。谢朓早年曾为随王萧子隆属下,后又为随王萧子隆镇西功曹,转文学。据《南齐书·谢朓传》记载:“子隆在荆州,好辞赋,数集僚友,朓以文才,尤被赏爱,流连晤对,不舍日夕。长史王秀之以朓年少相动,密以启闻。世祖敕曰:‘侍读虞云自宜恒应侍接。朓可还都。’朓道中为诗寄西府曰:‘常恐鹰隼击,秋菊委严霜。寄言罻罗者,寥廓已高翔。’迁新安王中军记室。朓笺辞子隆……”[7]825萧子显所撰《南齐书·谢朓传》较为详细地记述了谢朓此次遭谗还都的经过,而结撰这段传文的就有谢朓之诗《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和笺文《拜中军记室辞随王笺》的原文,尤其是《拜中军记室辞随王笺》,除了“故吏文学谢朓死罪死罪,即日被尚书召,以朓补中军新安王记室参军”几句以外,其他内容都被录入谢朓本传。从时间顺序上看,“《临楚江赋》一篇,大约是在江陵萧子良幕下所作,其写景部分颇有文采……”[8]157《临楚江赋》虽未被录于谢朓本传,但它当是三篇作品中最先写成的,而《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一诗则写于谢朓从西府还都途中,至于《拜中军记室辞随王笺》则写于谢朓还都之后。然而《拜中军记室辞随王笺》的内容却更为丰富,它所指涉的话语甚或在《临楚江赋》及《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相关话语之前。因此,这三篇作品具有一种垂直互文的关系,文本之间相互映发,可以互释、互证。《拜中军记室辞随王笺》是谢朓还都后,被任为新安王昭文中军记室时所写。此时谢朓的心情,与先前刚刚遭受打击而惊恐畏祸之时不同,他这次回京后心情已稍复平稳,也敢于真实地表白自己先前的感受和对子隆知遇之情的感恩心态。因此,在这篇笺文中,他尽情抒写了自己的百般心绪,文势也大起大落,四六骈句以及设问句的运用给人以回肠荡气之感,淋漓尽致地表白了谢朓与随王萧子隆“契阔戎旃,从容宴语”的交情以及谢朓对随王萧子隆“抚臆论报,早誓肌骨”之意。而先前离开西府之际,谢朓虽然不免思潮起伏,但前途未卜,局势未明之时,他又不得不将内心真实的情感隐藏起来,《临楚江赋》就作于这样的情境之下。《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的“常恐鹰隼击。时菊委严霜”也暗与《临楚江赋》的创作原委相契合。而《临楚江赋》的“忧与忧兮竟无际,客之行兮岁已严”与《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的“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也是具有互文性的离情别境,《临楚江赋》与《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具有多重互文性语话。《临楚江赋》还铺写了“冽攒笳兮极浦,弭兰鹢兮江浔。奉玉罇之未暮,飡胜赏之芳音”的送行情景,这是“笳音缭绕,鹢船待发,玉罇奉举,歌吟道别”的场景。《拜中军记室辞随王笺》也有“轻舟反溯,吊影独留,白云在天,龙门不见”之语,写到送行船只逆流而返而自己吊影独留的一片凄情别绪。只是在《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中没有这种送别的场景,这样,《临楚江赋》又成了《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互补性的互文本。上举谢朓诗赋文形成互文,《临楚江赋》则是这一互文网络中的一个交叉点,它也反过来与其他相关语篇形成不可分割的关系网络。
另外,从文本互文性角度,我们还可以解析“愿希光兮秋月,承末照于遗簪”的具体含义。这里也涉及版本问题,曹融南曰:“承末,原作‘庶永’,《全齐文》作‘承永’。依《初学记》改。”[5]40关于这两句赋文的解读,在有些普及性读物或鉴赏类辞典中,或被解释为“唯希望黯淡的夕晖和秋月给朋友带去恒久的欢乐”,或者被解释为“面对江上的秋月,祝愿荆州的友人健康长寿”。这样的解释似乎也都可通,都把“遗簪”理解为谢朓的朋友了。然而,谢朓《临楚江赋》中的“月光”与“遗簪”又是有所指的,这里的“遗簪”当是自指,而“月光”当代指随王萧子隆。“遗簪”典出《韩诗外传》,《韩诗外传》云:“孔子出游少源之野,有妇人中泽而哭,其音甚哀。孔子使弟子问焉,曰:‘夫人何哭之哀?’妇人曰:‘乡者刈蓍薪,亡吾蓍簪,吾是以哀也。’弟子曰:‘刈蓍而亡蓍簪,有何悲焉?’妇人曰:‘非伤亡簪也,盖不忘故也。’”[9]780从谢朓与随王萧子隆的关系上看,谢朓早年即为萧子隆僚属,自称为萧子隆的故旧较为符合情理。而谢朓如果称其他同在荆州的朋友为“遗簪”,在情理上则有些不通。然而即使这样理解“遗簪”之义,也仍属于读者的推理。尚需从谢朓其他文本中找到佐证,也就是需找到可以作为“遗簪”的互释话语。谢朓《拜中军记室辞随王笺》就有这样的话语:“唯待青江可望,候归艎於春渚;朱邸方开,效蓬心於秋实。如其簪履或存,衽席无改,虽复身填沟壑,犹望妻子知归。”笺文写到这里时,谢朓已对未来满怀希望,他想象着来年春天青江水涨,自己可以在江边恭候随王的归帆,王府大门打开之时,再为随王奉献自己的微薄之力。真挚之情状,溢于言表!然而“如其簪履或存,衽席无改”又是一种设想之词,作者进一步设想如果随王还能念及故旧,那么即使自己身填沟壑,葬身谷底,也在所不惜,而妻子儿女也有所托之处了。这里的“簪履或存,衽席无改”与《临楚江赋》中之“遗簪”同义,均代指故旧。而且除“遗簪”用典外,“履”及“衽席”也是前朝典故。贾谊《新书·谕诚》曰:“昔楚昭王与吴人战,楚军败,昭王走,屦决眥而行失之,行三十步,复旋取屦。及至于隋,左右问曰:‘王何曾惜一踦屦乎?’昭王曰:‘楚国虽贫,岂爱一踦屦哉?思与偕反也。’自是之后,楚国之俗无相弃者。”[10]54《韩非子·外诸说左上》曰:“文公反国,至河,令笾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者后之,咎犯闻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国,咎犯闻之不喜而哭,意不欲寡人反国邪?’犯对曰:‘笾豆所以食也,席蓐所以卧也,而君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劳有功者也,而君后之。今臣有与在后,中不胜其哀,故哭……’”[11]58谢朓借用楚昭王、咎犯以及遗簪妇人之事比喻不忘故人之意。从互文性角度看,也为《临楚江赋》中的“遗簪”作了释证。再看《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的结尾“寄言罻罗者。寥廓已高翔”之语,实际上不仅表现了谢朓摆脱被监视后的喜悦心情,同时,也是报平安信与随王萧子隆等西府朋友,这与《临楚江赋》形成互文,说明离开随王西府前后以及返回京都建康前后的谢朓与随王萧子隆等西府朋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谢朓也始终把随王萧子隆看作可以提携和庇护自己的重要依托。“遗簪”这一话语,正如德里达的文本理论所云:“每一个文本,每一种话语,都是能指的‘交织物’(interweaving)或‘纺织品’(textile),这些能指的所指是由其他话语从互文性的角度来确定的。”[12]因此,《临楚江赋》中的“遗簪”当为谢朓自指。
三、余论:体裁互文性与对谢朓赋论的新观照
谢朓A组和B组作品中都有诗和赋,每组作品中的单篇作品都是其他作品的互文本,也是谢朓体物写情的有效载体。由谢朓诗赋这种互文性,我们可以从体载互文性的角度分析这些诗赋在差异性的叠合方面所表现出的一些特点,并审视谢朓赋论的内涵。
谢朓A组作品在诗赋关系上表现出一些新特点,程章灿说:“以诗歌或辞赋相互酬答唱和,这样的文学现象早已有之,但以赋酬答别人的赠诗,则是南朝赋史的新现象。”[13]238除了谢朓以赋答沈约的赠诗这一实例以外,程章灿还举出湘东王以赋和萧范题诗的例子,程章灿据此论述说:“赋已打破自身的体裁界限,至少在唱酬功能上已与诗合拢。”[13]238也就是说谢朓笔下A组诗赋作品虽然从外在形式上看,还不存在所谓诗赋界域的消融,但诗赋之间的界限又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谢朓A组作品中诗和赋在功能、内容等方面交互影响,形成互文,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诗赋体裁上的互文性。
谢朓B组作品,即《临楚江赋》、《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拜中军记室辞随王笺》三篇作品,则是诗心赋意相沟通的互文性作品。从审美特点上看,《临楚江赋》极富诗情,有诗的审美特点,它睹物兴情,物以情观,自然山水随着作家主体的思想感情起伏流转;它又具有诗歌般和谐的声律,音调铿锵,声韵流畅,楚骚句式和尾韵相押,使赋文具有一种圆美流转之美。谢朓与沈约论诗时曾说:“好诗圆美流传如弹丸。”[14]609“圆美流转”是谢朓诗歌的审美追求,也是其赋的审美追求。而谢朓诗歌《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有沉郁顿挫之气,然而,诗中之纵横跌宕、悲慨淋漓,亦离不开体物之妙笔。如“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苍苍。引领见京室。宫雉正相望。金波丽鳷鹊。玉绳低建章”六句,铺陈渲染了天色将明未明之际眺望京都建康所见之景,银河洲渚、宫阙楼台在星光月色之下,似明似暗,引领可见,这种铺采摛文的写法类似于赋,但语言句式仍是诗歌式的。而从辞藻富丽、典故繁密、声音谐和这些方面看,也与这一时期的赋作有相通之处。至于《拜中军记室辞随王笺》则被明人孙月峰评为“浑似诗赋”(《评昭明文选》卷十)。谢朓善于将发自肺腑的真情实感通过妍丽华美的语言形式表现出来,而且诗赋文兼善兼通。
从谢朓的赋学观上看,谢朓认为赋以体物为主。谢朓之前,西晋陆机在其《文赋》中第一次明确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15]241的观点。谢朓对赋体的认识与陆机相似。谢朓选择赋体作《酬德赋》、《思归赋》等作品的原因,又并非仅仅因为赋能铺叙描摹外物,实际上还在于赋体作品内容涵量丰富,可以尽情铺陈。晋人皇甫谧曾说:“古人称‘不歌而颂谓之赋’。然则赋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体理,欲人不能加也。”[15]641谢朓在赋序中说:“沈侯之丽藻天逸,固难以报章;且欲申之赋颂,得尽体物之旨。”似乎谢朓感到沈约对他的知遇之情难以用三言两语回报,所以他说,用赋体才更充分一些。显然,谢朓认为赋颂的内容涵量要比一般的诗歌大得多。至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云:“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16]134刘勰把《诗经》六义之一的“赋”与文体之赋的“铺陈”特征联系到一起,并认为赋体最基本的特征是铺陈,而这种铺陈渲染,又不是赋创作的目的,而是通过这种铺陈渲染的手段,以达到体物写志的目的,这也就是谢朓所说的“得尽体物之旨”。从谢朓《临楚江赋》、《酬德赋》等的创作看,谢朓作这些赋最主要的目的,是以赋来抒写复杂而又不能一语道尽的思想感情。正如刘熙载所云:“赋必有关著自己痛痒处。如嵇康叙琴,向秀感笛,岂可与无病呻吟者同语?”[17]131《临楚江赋》虽以描写楚江山水为主,却不失为一篇写景抒情的佳篇;而《酬德赋》从本质上说,更是一篇抒写情志的作品。这样看,谢朓在《酬德赋序》中讲“体物”,只是表象而已,他真正的意图仍在抒情写志。可以说,谢朓这种赋体意识在西晋到南朝赋论的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过渡性。
[1]秦海鹰.互文性理论的缘起与流变[J].外国文学评论,2004,(3).
[2]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引言[M].邵炜,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3]蒋寅.拟与避:古典诗歌文本的互文性问题[J].文史哲,2012,(1).
[4]辛斌.批评语言学:理论与应用[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5]曹融南.谢宣城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6]姚思廉.梁书:卷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3.
[7]萧子显.南齐书:卷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2.
[8]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9]屈守元.韩诗外传笺疏:卷九[M].成都:巴蜀书社,1996.
[10]贾谊.新书:卷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1]陈奇猷.韩非子集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12]程锡麟.互文性理论概述[J].外国文学,1996,(1).
[13]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J].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14]李延寿.南史:卷二十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5]萧统.文选:卷四十五[M].李善,注.北京:中华书局,1977.
[16]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17]刘熙载.刘熙载文集[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其它文章
- 略论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哲学基础
- 从“人口治理”到“关怀自身”
——资本、权力与生存美学 - 论晚清时期文官保举的基本特征①关于中国清朝保举制度的研究,无论是通史性,还是断代性的,学界已经有了不少著作,或涉及或设专章进行研究。如李铁的《中国文官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等对中国古代的文官选用、保举、考绩、监察和惩处等进行了分析。陈茂同在《中国历代选官制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中设有“荐举论”专章,认为保举是重要的选官途径,区分和确定了保举类型及标准,分析了保举的利弊。宁欣清晰勾勒“选举”制度变迁脉络,对中国的选人、任官制度进行了论述,其中包括了清朝的用人制度(《中华文化通
- 德沃金对罗尔斯分配正义理论的批评与发展
- 从协同正义看罗尔斯、诺齐克之争
- 德性伦理的启蒙话语
——休谟德性理论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