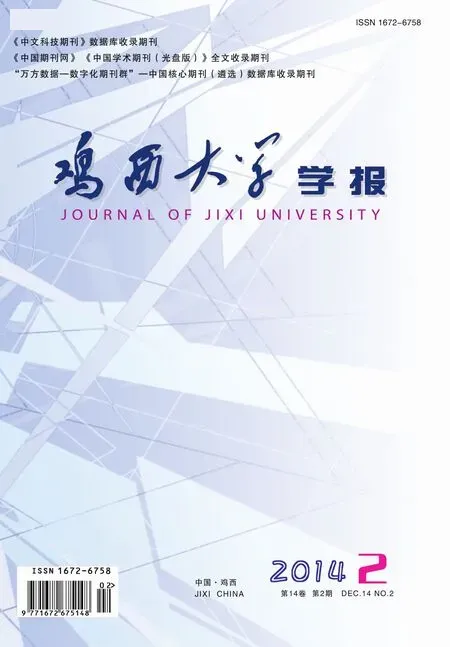奈保尔对人类生存的探索
——解读《抵达之谜》
林 瑛
(福建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半自传体小说《抵达之谜》是奈保尔的代表作,也是作者少数以英国为背景的作品之一。他将一个来自第三世界作家的经历和感受与大英帝国以及整个欧洲文化的衰落融为一体,在这儿,殖民者和受压迫者的界限已经模糊,他看到的是一个个饱经沧桑的生命和匆匆的旅人。对于这部小说的研究,众多研究者主要集中于讨论奈保尔是否实现了其第三世界移民作家的身份与英国身份的融合,这也是许多学者眼中奈保尔的“抵达之谜”。然而,笔者认为作为半自传体小说的《抵达之谜》,讨论的远远不止他的后殖民身份这一问题。事实上,它很好地反映了作者对于生命的哲思。这才是作者真正要寻找的抵达之谜。
奈保尔的创作时期起始于五十年代末,这时正是存在主义哲学在西方的全盛时期。可以看出从小在西方文化熏陶下成长的奈保尔深受存在主义的影响。存在主义力图回答人的精神危机以及人的异化所提出的各种问题。……以研究人的忧虑、悲伤、恐惧、绝望甚至死亡等人生“存在”的情态为自己哲学的对象。[1]而这些情态正是奈保尔在《抵达之谜》中所见所感,也是他所探寻的对象。因此,本文拟从存在主义的角度对《抵达之谜》进行分析,探讨奈保尔对于生命的思索。
一 生存困境:荒诞与异化
存在主义认为,人被抛入这个世界是偶然的,世界也是偶然的。人在世界中寻求生活着的意义、价值,世界却冷漠地给予否定的回答。“荒谬就产生这种人的呼唤和世界不合理的沉默之间的对抗。”[2]“外在世界是没有秩序的、不合理的、偶然的、荒诞的,人们无法借感觉经验或理性思维去认识,从而在它面前茫然不知所措。因此这是一个冷淡无情的。敌视人的、不驯服的世界。它使人感到苦闷、烦恼、估计、厌倦、恐惧,甚至绝望……”[3]而在《抵达之谜》中,作家感受到的正是这样一个世界。1950年,作家离开了自己的家乡英属殖民地特立尼达,要去英国实现他的作家梦。可是当他满怀激情和希望地踏上这次旅程时,他感受到的却是作为非白人的耻辱:出租车司机欺骗他;他没有办法给黑人小费;黑人船客宁可和白人挤在经济舱也不愿和他共住一等舱……在陌生的大城市中,他感到孤独和恐惧。而当他身处童年时心中的完美世界伦敦时,他发现那个世界并不像他想象中的那么完美。
即便是他所深爱的威尔郡也是如此,在美丽的庄园里,与此相对的是世界的荒谬和人的异化。作家在威尔郡最早认识的人之一杰克死后,作家在公共汽车上偶遇了他的妻子,这位妻子在谈起自己丈夫的时候“永远保持一种距离,仿佛在说某个她认识而不是一起生活过的人。”[4]她不喜欢杰克的生活方式,于是杰克的死对她成了一件好事。莱斯利和布伦达这对夫妇在庄园没住多久,就以后者被杀,前者被捕的结局告别了庄园的生活。布伦达性感美丽折磨着莱斯利,使莱斯利处于压力之下。终于布伦达还是去找别的男人了。中途她后悔过,给管家菲利普太太打电话,希望得到莱斯利的只言片语。可是这位表面上与他们很亲密的太太私自拦截了这个信息,造成后来更大的误会,致使最终布伦达被莱斯利杀死。
二 无法逃脱的结局:死亡及其意义
萨特说:“偶然、死亡、生命和真理所难以征服的多元性以及现实的无法理解,构成了荒谬的极端。”[2]荒诞和异化的世界造成了许多死亡提前的降临。《抵达之谜》中出现了许多这样的死亡。菲利普太太故意不转达布伦达的话给莱斯利,造成误会,感到受辱的莱斯利杀了他深爱的布伦达。作家艾伦无法接受现实和幻想的差距,克服不了内心的孤独和表面的伪装的冲突,最终自杀。
海德格尔认为,人处于矛盾之中,他们预示到不可避免的死亡,死亡导致痛苦和恐怖的经验。在英国居住二十年后,由于身体逐渐的衰弱,以及不断感受到的世界的荒谬和人的异化,使得作家在追逐自我和作家身份结合的过程中不断遭遇失望,感到身心极大地疲惫。于是大脑经常被爆裂的梦所困扰。在他五十几岁时,在他看到了许多的死亡之后,作家“被死亡的想法和实物的终结唤醒。”[4]于是作家被人终究会死的恐惧和忧伤缠绕,以致“丧失了一个正常人做事的能力”。[4]
海德格尔认为,一个“强者”就应该要正视死亡。这也是奈保尔在文章最后给自己死亡的梦魇的回答。根据海德格尔的看法,死亡有一种独特的启示意义, 让平时庸庸碌碌的人在片刻之间领会到自己的死,从而强烈地意识到自身独一无二的价值。杰克就是这样一个强者,他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在不遗余力地照看他美丽的花园上得到满足,尽管在别人看来是找累受;星期天,开着车选择颠簸的道路欢呼着到酒馆去喝酒。尽管已是到自己死期将近,还要去酒吧最后一次狂欢,为自己的生命践行。杰克无疑是文章中最具有存在主义特征的人,“在他的一生中,最英勇和最具有某种像宗教意味的事情是他死亡的方式:他所确定的方式,在终结的时候,首要的并不是超越生活的东西,而是生活本身。”[4]作者只有在对于生命有着深刻的领悟后,才意识到杰克的英雄主义般的死亡对于他的影响。那就是,生活本身对于生命的意义。
三 出路——自由与责任
既然在奈保尔笔下人是荒谬的,世界是异化的;人也不可避免地趋向死亡。人永远就被困于烦、畏、死当中吗?显然,奈保尔对于此的答案是否定的。《抵达之谜》中,作家极力追求自我与作家身份的融合,接受自然和世事的繁华与衰落,逃脱死亡的梦魇,在最后,告诉了我们他对于这个世界的感悟。“现在,每个世代都将使我们远离圣洁。但是,我们为我们自己重新塑造这个世界。每一代人都这样做。”[4]
萨特认为,“人是被判决为自由的”。人只要一被投入世界,就具有绝对自由。存在主义以此鼓励人的实际行动。因此,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做自己想做的事。就像文中作家不断追求自己的作家梦;杰克自由地按着自己的方式快乐地生活。但是同时要对自己所做的一切负责,这就是“绝对自由”的代价——绝对责任。然而,面对绝对责任的重压,大部分人选择自欺来放弃自由,园丁皮顿不断地追求时髦,他拒绝自己看上去像个园丁。他的自负和逃避都引来了人们的怨恨,“皮顿根本不懂园艺”的话在坊间流传起来,最后使他不得不离职,并且一直生活在怨恨之中。作家艾伦希望自己可以成为成功的文学家,然而他面对的却是他人成功的威胁和自身的无能。他不断地向人暗示他在写非常重大的作品,事实上,什么也没有。在社交场合谄媚他人、诙谐幽默;背地里孤独酗酒。他的内心世界充满悲观,陷入荒谬的漩涡无法逃脱,最后以自杀的方式躲避绝对责任,同时也放弃了绝对自由。
“人就是他自己所要求的那样的人。他不是什么别的,只不过就是他自己所造就的。”[2]
面对世界的荒谬和人性的异化,萨特鼓励人们利用自己的自由权利,去选择,去行动,去创造自己的未来。奈保尔也在《抵达之谜》接近结尾处告诉我们:
我们重新塑造了世界。我们发现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里……在一定程度上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世界,也是我们心中多渴望的世界,当我们渴望金钱、渴望结束穷困的时候。我们无法回到从前。现在没有古船可以带我们回去。我们已经走出梦魇,而且我们已经无处可去。[4]
奈保尔告诉我们,这是我们选择的生活,纵使它已经不是我们原来期待的那样,我们也需要去接受,而不是逃脱躲避,以致陷于苦闷、畏惧、绝望,被荒谬的世界抹杀生命的意义。而这个哲理,启示他正视死亡。存在主义认为,人只有能正视死亡,才能够克服世界的荒谬,活出自我。
它使得我们不得不正视死亡,它使得我们不得不去面对我一直在睡梦中沉思的死亡。它是一种真正的在忧郁所穿凿的空虚中产生的悲伤,似乎是专门为我此时准备的。它向我显示,生命与人是最具神秘性的,是真正的人的中交,是悲伤与荣耀。而当我面对一个真正的死亡,以及有关人的心的神奇,我才将草稿扔到一边,抛弃了一切犹豫,开始悬河泻水,写杰克和他的花园。[4]
《抵达之谜》是奈保尔的走向作家之路的旅程,是他探究自己精神和文化之旅,更是他思考生命意义的旅程。在这本书中,奈保尔更加全面地定义自己,这是一部关于自己的敏感、内省、冥想和真诚的文本。[5]他受意大利画家基里科的画作《抵达之谜》启发,构思了一个这样的故事:一位带着使命的旅人在旅途中迷失,最后抵达来时码头发现载他来的船已经消失,他也过完了他的一生。作者就是这位旅人,每个人都是。在人匆匆的一生当中,有许多荒谬和异化,我们选择我们自己的路,但是回头看时,却发现我们已经迷路。但在文章的最后,奈保尔给了我们回答:世界充满残酷与荒谬、人生面对着许多孤独与异化,但是只要人们不遗余力地追求真实的自我,承担起自己选择的责任,人生还是充满希望的。尽管他的笔下总是充满了悲伤和痛苦,但他并不像许多学者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告诉我们生命短暂,要自由地去选择,去行动,去创造自己的未来。这就是奈保尔告诉我们的“抵达之谜”。
[1] 全增嘏.西方哲学史下[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767.
[2] 赵稀方.存在与虚无[M]. 北京:金城出版社,1999: 210,211,208.
[3] 徐崇温,刘放桐,王克千.萨特及其存在主义[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2: 42.
[4] V. S. 奈保尔.抵达之谜[M].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 103,367,102,367,378.
[5] Roldan-Santiago, Serafin. Pessimism and Existentialism in V.S. Naipaul. Journal of Caribbean Literatures [J], Vol. 5, No. 2 (Spring 2008), pp. 153-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