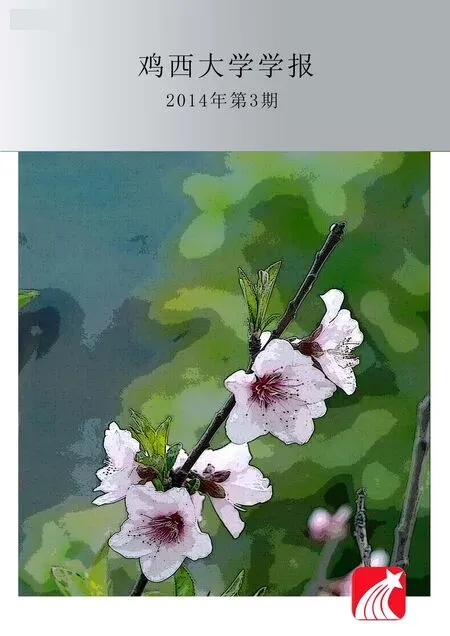沉重的枷锁—《一粒麦种》后殖民女性主义解读
马缓缓
(云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恩古吉·瓦·提安哥(Ngugi wa Thiong’o 1938—)不仅是肯尼亚,同时也是整个非洲20世纪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提安哥既是小说家,又是剧作家和政论家。著有长篇小说《孩子,你别哭》(1964)《大河两岸》(1965)《一粒麦种》(1967)等,其中《一粒麦种》无疑是恩古吉最知名的作品。国外学者对这部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小说中的象征、反讽以及与康拉德的小说《在西方的注视下》的互文性研究,而国内学者对这部小说的研究还相对较少,主要是从后殖民身份以及民族主义角度来研究。此外,朱黎(2012) 从人格三段论解读穆苟成为叛徒的根源,指出作为一个社会人若不能够很好地通过自我去控制本我并且把本我的冲动纳入文明和道德的轨道,便难以为社会及国家做出自己的贡献。这些研究都鞭辟入里,各有建树,但却很少关注小说中的女性角色。鉴于此,笔者将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角度解读《一粒麦种》,分析殖民时期肯尼亚女性背负双重枷锁的生存状态,同时揭示殖民时期白人女性不幸的生存图景。通过这一视角解读,体现作者对肯尼亚女性这一弱势群体前途命运的担忧以及对白人女性尴尬处境的同情和惋惜。
一 黑人女性的枷锁
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既是女权运动的产物, 也是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结果。艾勒克·博埃默在其《殖民与后殖民文学》中提到:“殖民地的妇女,却真的像人们所说的那样,被双重或三重的边缘化。她们低人一等不仅仅是因为性别,还是因为种族、社会阶级……”。[1]《一粒麦种》中女性不仅遭受来自殖民主义的压迫,而且还要忍受来自本土父权制文化的压迫。
1.英国殖民文化的压迫。
在《一粒麦种》中,婉布库是梦碧的朋友,也是基希卡的恋人,得知基希卡被捕并吊死在树上后,她的行为就变得有些奇怪。当她拒绝一个团丁求欢后,“那个人在壕沟里借机报复,把她毒打一顿”。[2]三个月后,她便死了。殖民地的黑人女性除了遭受毒打外,还要遭受白人的性暴力。“法侬认为,殖民主义的本质是暴力”。[3]这种暴力不仅指物质上的暴力,更是心理、文化上的暴力。在肯尼亚,英国殖民文化对殖民地人民、尤其是女性的压迫主要来自圣经《创世纪》。圣经无形中成为英国父权制殖民文化的帮凶。女主人公梦碧被看作是“夏娃”,[4]即“原罪”的诱发者,是她导致男人的堕落。一个是他丈夫基孔由为了能够从拘留营再次回到她的身边而背叛部族、背叛曾经发下的誓言;另一个是一直爱她的卡冉加,为了获得权力而成为白人的走狗,服务于白人统治者。这种判断典型的体现殖民文化暴力对肯尼亚吉库尤女性的影响。
不仅如此,在白人眼中,殖民地时期的肯尼亚女人首先是“被物化的,她们具有商品的属性,可以被任意买卖。其次,她们是从属于男人,由此可见,殖民时期的肯尼亚女性的主体性几乎完全丧失了,它不仅被父权文化吞噬掉了,也被殖民地文化吞噬掉了”。[5]肯尼亚地区的区专员汤普森,曾有一次派卡冉加给妻子玛姬丽送信,玛姬丽喜欢问黑人这样一个问题“你有几个老婆?”卡冉加喜欢梦碧,他回答说:“我还没有结婚。”玛姬丽继续问道:“还没结婚?我以为你们这儿的人——那你会去买个老婆吗?”“不知道”[2]卡冉加答道。可见,在父权或夫权社会中,女性被物格化,女性始终是一件可以随意买卖的商品。
2.肯尼亚本土文化的压迫。
在殖民地,“女性是边缘中的边缘,她们受到的压迫是多重的”。[6]女性不仅仅受到英国父权制殖民文化的压迫,而且束缚于本土父权文化的枷锁之中。这种压迫因殖民而愈演愈烈。
女主人公“梦碧”的名字本身就是吉库尤部族圣母的象征,这种部族文化美丽、纯洁的象征在梦碧身上“转换成了她的枷锁”,[5]她被打上这个部族所有代表女性美好、贞洁的烙印。也就是说,殖民时期“男性以文化价值的名义再次殖民女性的身体和心灵,女性便背上沉重的文化价值枷锁”。[7]作为吉库尤圣母的象征,梦碧受到来自本土文化的束缚与压迫。基孔由曾和很多女人有染,而他却无法原谅梦碧对他的背叛(梦碧屈从于卡冉加)。梦碧背叛他的初衷只是想从卡冉加口中得知他在拘留营里的消息。斯皮瓦克指出,臣属妇女处在父权制传统文化和父权制帝国文化的夹缝中,失去了言说的权力。梦碧始终没有开口让基孔由知道事情的缘由。出于内心的憎恨,基孔由和梦碧之间不是“冷战”就是吵架,在最激烈的一次冲突中,基孔由冲梦碧吼道:“闭嘴,臭娘们!……你这臭婊子,让我来堵上你的嘴!一巴掌扇在梦碧的脸上,接着又是一巴掌”。[2]梦碧无奈之下跑回娘家,父母对此并不表示欢迎,反而说道:“现在的女人还真让人吃惊啊!连男人轻的像羽毛、弱的像呼吸的耳光都挨不得。我们那个年代,女人就算被丈夫打的死去活来,也不会想着跑回娘家”。[2]梦碧挨丈夫的打却无法得到家人的理解。如果没有殖民的到来就不会有梦碧这一系列坎坷的经历,父权制下性别上的不平等在基孔由与梦碧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而且殖民无形中强化了这一不平等关系。
总之,在父权制社会里,男权中心主义对女性的影响根深蒂固。殖民时期的肯尼亚女性遭受着英国父权制殖民文化的侵蚀和毒害,而且殖民环境本身进一步强化了本土父权文化对她们的压迫。
二 白人女性的枷锁
“英国父权制殖民文化价值观中的殖民话语不仅仅影响殖民地的女性,而且还影响着殖民国家的女性,尽管是从不同的方面”。[8]
英国女性琳德博士遭到仆人吉库尤黑人的抢劫和性侵犯。“他们绑住她的手脚,还堵住了她的嘴。”“那个狠心的家伙居然把它(仆人和琳德博士养的狗)砍成了碎块。……事后,他们拿走了放在保险箱里的钱和枪”。[2]也就是说,林德博士受到黑人奴仆的侵犯是殖民话语内化的结果和表征。
杰克逊是紧急状态时期担任融尔地区的区专员,手段毒辣,杀死很多殖民地人民,大家称他为食人者。最后,他被基希卡杀死,房屋和财产也被烧成黑炭和灰烬。“他的妻子和幼子虽然安然无恙,却从此将过着无家可归的日子”。[2]与此同时,殖民时期的白人女性也遭到被殖民男性一种报复性的反抗。烧毁白人家庭赖以生存的家园,让白人女性也体验被剥夺生存地的滋味。随着汤普森(另一区专员)在殖民地的深入管理,玛姬丽发现自己“越来越看不透丈夫(汤普森)那张难以捉摸的面庞,最后甚至就连对他产生一点柔情蜜意都让她感到痛苦”[2]自何时起,他们夫妻之间“形同陌路了呢?”在一次偶然的时刻,玛姬丽遇到范代克。范代克是一位脑满油肠、酗酒成性的气象局官员,之后,便成为她偷情的对象。正是殖民统治这一无形的精神枷锁导致了玛姬丽的放纵。丈夫在外管理殖民地的人民,而与妻子的对话将越来越少。殖民统治无形中窃取白人家庭原有的爱和融洽,取而代之的是冷漠、隔阂与背叛。然而,玛姬丽曾回忆到达殖民地之前“他们一起在伦敦散步,从驻足的圣詹姆斯公园,抬头远眺威斯敏斯特教堂、英国下议院以及更远的地方。玛姬丽喜欢把头靠在汤普森的肩上,希望他能够带着她一起踏上他口中的那些地方,他确实做到了”。[2]殖民前的幸福生活与到达殖民地后的处境形成鲜明的对比,进一步说明殖民统治也成为白人女性无形的枷锁。
综上所述,殖民时期白人女性的生存状况也是不幸的,身体上所受的侵犯加之内心的空虚与不安造就了区专员汤普森与妻子的不幸婚姻。这再一次证明:英国父权制殖民文化价值观中的殖民话语不仅仅影响殖民地的女性,而且还影响着殖民国家的女性。
三 结语
笔者用后殖民女性主义来解读这一文本,以此揭示肯尼亚吉库尤族女性的生存状况,而且关注到英国白人女性的生存图景。殖民时期的女性深受父权制殖民文化与本土父权文化的双重压迫,她们处于边缘的状态,永远没有真实的权力。通过这一视角的解读,揭示了小说作者对肯尼亚女性这一弱势群体前途命运的担忧以及对白人女性尴尬处境的同情和惋惜。
[1]艾勒克·博埃默. 殖民与后殖民文学 [M]. 盛宁, 韩敏中, 译.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257.
[2]恩古吉·瓦·提安哥. 一粒麦种 [M]. 朱庆,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 43.
[3]赵一凡. 西方文论关键词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 202.
[4] Williams, Patrick. Ngugi wa Thiong’o [M].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9: 64.
[5]任一鸣. 后殖民:批评理论与文学 [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8: 233.
[6]章辉. 后殖民理论与当代中国文化批评 [M].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0: 87.
[7]Mishara, Raj. “Postcolonial feminism: Looking into within-beyond-to difference”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glish and Literature,2013(4):129-134.
[8]McLeod, John. Beginning Postcolonialism [M].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0:177.
——评《后殖民女性主义视阈中的马琳·诺比斯·菲利普诗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