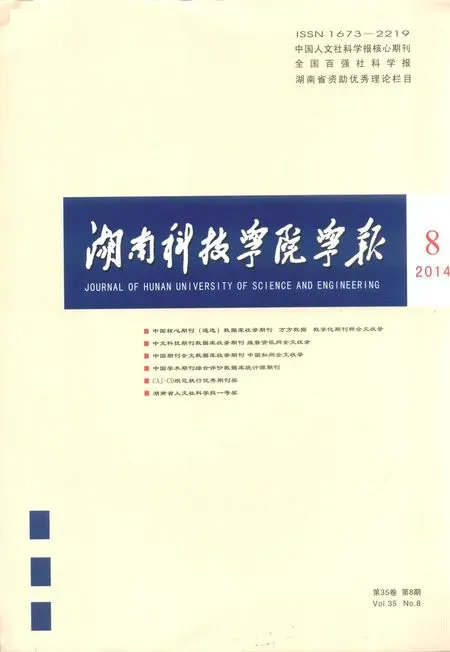颜子所乐何事?——对于理学境界论的一个哲学阐释
周建刚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湖南 长沙 410003)
在理学史上,周敦颐一般被公认为宋明理学的开创者。周敦颐对宋明理学的思想贡献主要有三点:一是《太极图说》所代表的宇宙论;二是《通书》中以“诚”为核心的修养论;三是“孔颜之乐”的境界论。在周敦颐的这三点思想贡献中,《太极图》在后世关注最多,引起的争论也最大,《通书》相对不受人重视,但“孔颜乐处”的思想,宋明理学的各家各派却异口同声地表示赞同。周敦颐所说的“孔颜乐处”,实际上揭示了宋明理学所为之奋斗的共同精神方向,也蕴涵了理学的最高精神境界和人格理想。
一
“孔颜之乐”的问题,主要是“颜子之乐”。在儒学历史上,颜回是一个具有一定神秘色彩的人物。依据《论语》的记载,颜回是孔子的杰出弟子,但终生贫困,并不幸而早死。按照世俗的看法,颜回的一生是不幸而凄惨的。但是《论语》中同时又记载,颜回虽然居陋巷而箪食瓢饮,内心世界却充盈着无比的快乐,“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这就形成了思想史上一个极其吊诡的问题:高度的精神修养是否能够转化现实生活的不幸,或者说,当人们面对简陋匮乏的现实生活时,内心幸福感的源泉究竟源自何处?
“孔颜乐处”的命题,关键在于“乐”。关于“孔颜之乐”,《论语》中有所提示,主要着眼于颜回在困难的生活环境中“不改其乐”,得到孔子的赞赏,但是其“乐”的内涵和实质则语焉不详。值得注意的是,在《庄子》中,颜回的形象得到了凸显,颜子之“乐”的内涵则被描述为“心斋”的精神快乐。此后,魏晋玄学也对这一问题有所提及,主要将颜回之“乐”解释为道家的“体无”精神境界。
“孔颜之乐”在儒学史上成为重大问题,应当发端于北宋的周敦颐与二程。周敦颐与二程的师生授受关系,在历史上是一个纠缠不清的问题,肯定者居多,但反对者也不在少数。但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双方关注的焦点其实都集中于《太极图》,即周敦颐是否向二程“手授”过理学史上的重要文献《太极图》。事实上从二程的自述来看,他们从周敦颐那里所得到的具体指点是“寻孔颜乐处”,这一语指点,对二程理学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现存的《二程集》中,约有三处记载了周敦颐对二程所谈论的“孔颜乐处”。
1.《河南程氏遗书》:“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1]P16
2.《河南程氏粹言》:“子谓门弟子曰:昔吾受《易》于周子,使吾求仲尼、颜子之所乐。要哉此言!二三子志之。”[1]P1203
3.《河南程氏遗书》:“《诗》可以兴。某自再见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1]P59
在上述三处记载中,第一和第二则未说明是二程中何人所说,第三则明确说明是程颢的语录。第一、第二则可综合参看,说明周敦颐是在讲授《易》学的过程中向二程提出“孔颜乐处”的问题,“孔颜乐处”与周敦颐的《易》学观点应有一定关系;第三则虽未明确提出“孔颜乐处”,但程颢所说的“吾与点也”,实际上也反映了儒家在境界问题上的看法,与“孔颜乐处”没有太大的区别,因此与第一、第二则语录可以归为一类。
二程的思想有所不同,明道和易而伊川严肃,这是前人的定评。二程从周敦颐受学,明道领悟较深,伊川则有些隔膜。后世以“周程”并论,实际上说的主要是濂溪与明道。明道得到濂溪“孔颜乐处”的提示后,有“吾与点也”之意,说明他对于这一命题所展示的儒家境界形而上学有所领会。《二程集》中有许多明道的语录,与周敦颐的思想若合符契。相反,伊川对此很少提及。二程的著作中,明道的《定性书》、《识仁篇》展现了高度的哲学“形上学”的洞见,可说是直接濂溪学脉;而伊川的主要著作《程氏易传》则与濂溪易学关系不大。
“孔颜乐处”,是将孔子和颜回并列,提出儒学复兴的一个新的精神方向。“孔颜乐处”的命题,是儒学的境界论命题,也就是如何将儒学的精神境界提升到可以与佛教、道家相提并论、分庭抗礼的地步。这是北宋儒学面临的一大问题。周敦颐提出“孔颜乐处”的命题,就是为了替宋代儒学解决这一时代性的大问题。
“孔颜乐处”的命题。主要是一个境界论的命题。前此与道家的境界论有关,往后则开启明代心学的境界论,如陈白沙、王阳明,乃至于罗近溪,都对“乐”进行了论述。
二
周敦颐提出了“孔颜之乐”的命题,实质上为宋明理学开启了一个新的精神方向。但是周敦颐的“孔颜之乐”,主要体现在他的生命实践活动中,并没有从哲学上进行具体的解说。这一步工作,有赖于现代人代为完成。
首先说明,周敦颐所提出的“孔颜之乐”,实际上是个体生命如何从有限达到无限的问题,这一问题所蕴含的哲学意义至关重大。
就现实生命而言,每个生命个体都受到具体条件的限制,无论是贤愚寿夭、富贵贫贱,都仿佛受到冥冥中造物者的播弄而形成一定的轨迹,个人的力量很难与这种无形的命运对抗。颜回虽是孔子所赞许的“贤人”,也无法逃脱贫贱、早死的厄运;相反,许多作恶多端的歹徒,却反而安富尊荣、寿终正寝。这些现象,让历史上无数富于正义感、道德感的人们痛心疾首,却终究无可奈何。现代存在主义哲学所说的人之存在的“荒谬”,实际上就是对这种不合理现象的反思。如果顺着这一思维而推到极致,也许可以认为人生不过是意义的”荒原”,人接受命运的安排,偶然漂泊于此世,又在一片荒凉中死去,所有的努力都是meaningless(无意义)。
按照周敦颐所开创的宋明理学的思路,“偶然”这个具有存在主义色彩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接受的,不同的是,宋明理学认为,“偶然”并不是存在的全部真相,由“偶然”而达到“必然”,由“有限”而进至“无限”,才能够真正接触到“存在之奥秘”。
“偶然性”是自然世界的根本性标志。在理学家看来,自然世界是一个气化流行的世界,“气”是自然世界得以形成、生长的质料,但万物所禀之“气”却并不均衡,而是有多少、清浊、刚柔之分,并由此而产生人或物的贵贱、贫富、贤愚之别。气化流行的过程形成了经验世界的“万有不齐”,这背后并没有“上帝”或者“理性”之类支配性的原则,一切都是在“偶然性”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当朱熹的一个学生疑问“尧舜之气常清明冲和,何以生丹朱、商均”时,朱熹也只能回答“气偶然如此”[2]P59。
人或物禀受之“气”或清或浊、或厚或薄,这一切都出自偶然,甚至可以进一步说,偶然性就是命运。由此,孔子和颜回在世俗生活中的不幸就可以得到解释。“有人禀得气厚者,则福厚;气薄者,则福薄。禀得气之华美者,则富盛;衰飒者,则卑贱;气长者,则寿;气短者,则夭折。此必然之理。”[2]P80“夫子虽得清明者以为圣人,然禀得那低底、薄底,所以贫贱。颜子又不如孔子,又禀得那短底,所以又夭。”[2]P79说到底,即使是孔子和颜回这样的圣贤,还是生活在和我们同样的经验型日常世界中,他们的生命存在也同样受到经验世界“偶然性”原则的支配,因而飘泊不定,饱受生活的磨难。
如果世界真的仅仅是在“偶然性”原则下形成的自然气化世界,那么意义的缺位就无可避免,因为我们无法从“偶然”中分析出意义,就像无法在孩童随意摆放而凌乱不堪的玩具中总结出什么规律一样。但是理学家认为,“偶然性”并不能触及世界之存在的全部真相,世界存在的“偶然性”之中总是蕴含有“必然性”,用理学的语言来说就是,“气化流行”的过程中蕴含有“天理流行”。如果说“气化流行”揭示的是经验世界、自然世界的相状,那么“天理流行”就为我们揭开了理想世界和价值世界的帷幕。人的全部努力所在,就是由“偶然性”达到“必然性”,实现由自然世界向价值世界的转换,由有限到无限的解放。在这种解放的过程中,人能体验到一种精神性的幸福,这种幸福就是“孔颜之乐”。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这样描述“孔颜之乐”:“人一生都在殊相的有限范围之内生活,一旦从这个范围解放出来,他就感到解放和自由的乐(这可能就是康德所说的‘自由’)。这种解放自由,不是政治的,而是从‘有限’中解放出来而体验到‘无限’(这可能就是康德所说的‘上帝存在’),从时间中解放出来而体验到永恒(这可能就是康德所说的‘不死’)。这是真正的幸福,也就是道学所说的‘至乐’。”[3]P15
冯友兰先生的这段话非常有力地解释了“孔颜之乐”对于人的精神世界的解放作用,同时他也提到了“孔颜之乐”与康德哲学的联系。我们知道,哲学的发展,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离不开对于人的命运的思考。人总是生活在经验世界中,受到经验世界法则的限制和束缚,但另一方面,人又总是试图挣脱这种束缚而投向无限性的超越世界,这是人的本质性的“形而上学冲动”。在康德哲学中,人的有限性体现为“理论理性”对于现象世界的认识,无限性则体现于“实践理性”对于道德世界的认识,而审美判断力则实现这两个世界的沟通。同样,在理学家看来,“理”和“气”的区分,在一定程度上也将有限性的自然世界和无限性的价值世界、超越世界划分开来,而人的努力则在于沟通这两个世界,这种沟通,理学家称之为“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直接效果就是“孔颜之乐”。
三
人的不幸源于经验世界的偶然性,人的幸福则在于破除经验世界的限制,将经验世界转化为价值世界,从而得到精神上的解放,这就是用哲学语言所解释的“孔颜之乐”。问题是,人应当如何努力,才能够从经验世界中得到解放,并得以体味这种神秘的“孔颜之乐”呢?
在这个问题上,周敦颐的答案是“道德有于身”。他在《通书》中这样说:
“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不改其乐。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故颜子亚圣。”[4]P32~33
“天地间至尊者道,至贵者德而已矣。至难得者人,人而至难得者,道德有于身而已矣。”[4]P33
这实际上是认为,颜回虽然身处贫贱之境,但体会到了“天地之间有至贵至爱可求”,这“至贵至爱”者就是道德,“天地间至尊者道,至贵者德而已矣。”颜回追求道德并拥有道德,由此就可以“见其大而忘其小”,对于贫贱和富贵一视同仁。按照这样的说法,颜子之乐的具体内容就是“道德”。
周敦颐对于“孔颜之乐”的解释,从字面意义上看来就是如此。但是这样一来,“孔颜之乐”的内容似乎很贫乏,缺少打动人心的力量,也难以说明这一命题为什么能够称为理学的精神修养纲领,并为二程开启了学问的方向。
实际上二程对于“孔颜之乐”有自己的领会。在《二程集》中,附记有一条这样的记录:
“《胡文定公集》记此事云:……昔鲜于侁曾问:‘颜子在陋巷,不改其乐,不知所乐者何事?’伊川却问曰:‘寻常说颜子所乐者何?’侁曰:‘不过是说颜子所乐者道。’伊川曰:‘若说有道可乐,便不是颜子。’”
“若有道可乐,便不是颜子”,这分明是说,颜子之乐,其内容不是“道德有于身”。周敦颐与二程的这种理论分歧,应该作何解释呢?
让我们试着回到对“孔颜之乐”本身的理解上来。如前所述,“孔颜之乐”体现的是由自然世界向价值世界的回归,在这个过程当中,人从经验性的“有限”世界中挣脱出来,投向“无限”性的超越世界,从而体会到精神性的幸福。从宋代理学的发展思路来看,理学家所认识的超越世界、价值世界事实上就是“天理流行”的道德世界,只不过这个道德世界具有存有论上的终极性依据,即“天地之大德曰生”的“天道创生原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周敦颐认为“道德有于身”就是“孔颜之乐”,确实体现了宋明理学的一般思维原则。但是周敦颐这一说法的缺憾在于,他将超越性的“道德”与经验性的“贫贱富贵”对立起来,并得出了“一大一小”的结论,这就制造了一种以价值世界压制经验世界、自然世界的紧张格局,“孔颜之乐”的圆融性无疑就会大打折扣。
按照二程的思路,颜回之乐不会源自于价值世界与自然世界的分裂和紧张,相反,价值世界和自然世界原本就是合一的,道德秩序就是宇宙秩序。“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体则谓之易,其用则谓之神,其命于人者则谓之性。”[1]P4只是由于人的情感和私欲的作用,才造成了价值世界和自然世界的分裂,“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适道,大率在于自私而用智”[1]P460。因此,沟通这两个世界的方法就在于“识仁”,当仁体呈露时,自然没有内外之分,自然世界和价值世界合为一体,自然世界的万事万物都沐浴在价值理想的光辉之中,由此而产生内心真正的“至乐”。“此道与物无对,大不足以明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须反身而诚,乃为大乐。若反身未诚,则犹是二物有对,以己合彼,终未有之,又安得乐?”[1]P17“以己合彼”尚有人为斧凿的痕迹,“反身而诚”则泯除内外之分而纯任天然,如晋人陶渊明的诗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在此忘言忘意的天然境界中,尚有何对象可以执持?一切均停停当当,自然天成,“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周易·系辞上》)
依照二程的思路,颜回之乐就是“乐”此自然天成的世界。在此世界中,道德行为是一种自然行为,“风行水上,自然成文”,如同荒野中的民谣俚曲,尽管有天籁之美,但在歌者的心目中只是生命的自我抒发,“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并不自居为音乐或艺术。自然天成的世界中,道德行为也是如此,虽有道德之实,而无道德之名,无形无迹,一过而化。只有在这样的语境中,才可以理解程子所说“若有道可乐,便不是颜子”。
四
总结宋明理学对“孔颜之乐”的认识,我们发现,从周敦颐到二程,对儒家的精神方向始终有一个明确的把握,但又有一个不断深入认识的过程。从汉唐以来,儒学追求外在的训诂章句、外王事功,在精神境界方面日渐低落,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尽管坚持儒家的社会价值观,但在精神修养方面已经走上了佛家、道家的道路。周敦颐指点二程“寻孔颜之乐”,一入手就指出儒家在精神性“内圣”领域的高度成就,这确实是敏锐地把握到了时代的脉搏,为宋明理学开启了新的方向。但周敦颐的解释是初步的,他的生命境界完全体现了“颜子之乐”,而在现存的《通书》中,其解释确实有不够圆融之处。二程所领悟的周子之学,主要是通过“颜子之乐”以窥见儒学精神殿堂之华美,从而进一步构筑了理学“内圣”学的宏伟规模。
让我们再回到颜回。《论语》和《庄子》中的颜回已经远去,我们现在看到的颜回是宋代理学视野中的“颜回”。姑且允许我们将这些文献记录中的颜回暂且“悬置”,从自己的生命体验出发,以哲学解释学“视域相融”的方式,揣测一下究竟“颜子所乐何事”。
颜子是圣哲,也是凡人,他同样要受到经验世界法则的播弄,如同我们一样,在命运的威力面前无能为力。对于平常人来说,世界居高临下俯视着我们,接受命运的安排是人世间的唯一出路,尽管怀抱着“不堪其忧”的愤恨。但是对于颜子这样的圣哲来说,人不但需要仰视世界,同时也可以用微笑的姿态凝视世界。借用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我与你》一书的理论来说,人总是生活在两重世界中,一重是“我与它”的世界,一重是“我与你”的世界。在“我与它”的世界中,人与万物相分离、相对待,“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庄子·齐物论》)在“我与你”的世界中,“我”和世界相遇并建立一种超越是非对待的纯净关系,“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乐府诗集·长歌行》)颜子尽管受到命运的无情播弄而有着凄惨的人生,但他的世界是“我与你”的世界,“一旦‘你’之天穹鉴临,光耀于我颅顶之上,则因果之疾风将俯伏足下,命运之流转将畏缩不前”[5]P24。在“我与你”的世界中,世界脱离了因果之网的限制,呈现为冰清玉洁的琼楼玉宇,一切是非对立、美丑贫富、贵贱高低的差别都烟消云散,存在就是存在,哪怕是卑微、贫贱的存在,也自有其庄严和神圣的价值。因此颜子即使居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也能够“不改其乐”。
颜子的心境是否确实如此,我们无从揣测。但颜子确实在平凡的生活中活出了一个圣哲的姿态。“颜子之乐”是一个圣哲的生命面对无情命运的微笑凝视,在这种微笑凝视下,铁一样的经验世界法则似乎退缩、失效了。这种精神境界使历代儒家人士备受鼓舞,增添了他们在逆境中奋斗的勇气,因而散发出巨大的思想魅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颜子之乐”成了儒学历史上永恒的经典。
[1]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五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4]周敦颐.周敦颐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9.
[5][德]布伯(陈维纲译).我与你[M].北京:三联书店,1986.
——《宋明理学人格美育论》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