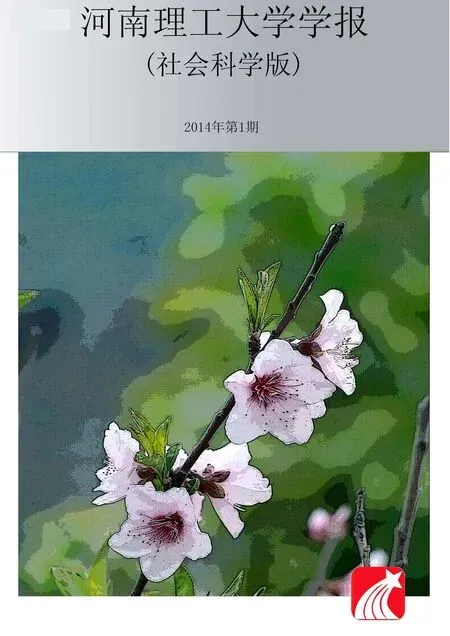论师陀创作的文学史价值及其局限
王 欣
(河南理工大学 文法学院,河南 焦作454000)
论师陀创作的文学史价值及其局限
王 欣
(河南理工大学 文法学院,河南 焦作454000)
师陀是20世纪中国乡土作家的杰出代表和诗化小说的积极探索者与实践者,他对于创作个性的坚守、对于民族文学传统的承继与创新,以及严肃的创作态度与正直的创作品格,给文学史带来了优秀的质素和生动的文学景观,为当代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与书写维度,为一个民族的文学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但他单薄的文化教育背景、不够丰厚的人生阅历和文化积累、农民的思维习惯和情感生活特点影响了他整体创作视野的深度,并在都市小说、乡土小说的创作方面表现出一定的缺憾。
师陀;文学史价值;局限
文学作品“是文学史的核心内容,因为文学创作最终体现为文学作品,没有作品就没有文学,更没有文学史”[1]。作为中国文学史进程中一个独特而坚实的存在,师陀不但书写了一部风格独具且深刻揭示了乡土中国整体结构和内在质相的短篇小说集《果园城记》,而且还以自己丰富而出色的创作实践为文坛贡献了一个由小说、散文、戏剧、电影剧本、诗歌等诸多文学样式共同构建而成的纵横交错、互相勾连的艺术体系。师陀依凭丰富的创作成果,在对乡土中国的深度观照,对诗化小说的成功实践,对社会关怀、审美话语、超越意识和谐一致的追求中,参与并推动着文学史的建构和发展。特别是他对于创作个性的坚守、对于民族文学传统的承继与创新,以及严肃的创作态度与正直的创作品格,给文学史带来了优秀的质素和生动、丰富的文学景观,为一个民族的文学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
一
师陀在现代文坛上特立独行的创作姿态令人瞩目,他不媚俗、不附众,从检视文化与人生审美的双重角度出发,以最适合自己个性气质的诗性方式切入时代与社会,表现出不同流俗的创新勇气和创作追求。他对创作独立品格的坚守和文本创新实践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体现,激发了文学创造的内在活力,推动着时代文学走向开阔、多样、开放。师陀为散文集取名为《黄花苔》,并自诩为默默无闻的黄花苔。他说:“我是从乡下来的人,而黄花苔乃暗暗的开,暗暗的败,然后又暗暗的腐烂,不为世人闻问的花。”(《黄花苔·序》)这样的表述代表着作家的谨严自守、理性低调,但并不代表作家浅陋自负、保守孤僻。师陀的思维活跃开放,从来没有封闭过自己的创作时空。中原、北京、上海是他生命中重要的栖居之地,他接受着不同地域文化的滋养、塑形和锻造,并依凭自身本然的天赋与性情,创造性地选择、吸纳、消融着多方文化的神彩。中原,是他创作的原乡;北平,为他提供了文化的启蒙;上海,点燃了他的创作活力,使他在两种文明的对比中真正把握了乡土文化的实质,完成了《无望村的馆主》、《马兰》、《荒野》、《结婚》等作品的书写。虽然他没有加入左联,但他的许多作品表现出了鲜明的政治情感、忧患意识和社会担当。当京派批评家因欣赏他对田园风物的精细摹写和散文化风致,向他投出橄榄枝时,他却在《行旅》一文中锐利地指出:那些京派作家当作美来颂扬的中国农民的原始、蒙昧、落后正是外国人“不住的把玩着,赞叹着”的“东方情调”,“他们希望中国人最好能够永远在这种没有希望的所谓东方情调中生活,永远不死不活的供他们‘同情’”。这些尖锐的言辞是他为自己和京派作家之间划出的一条明晰的界限。即便当师陀漂泊于上海之时,贫寒的生活急需他将孤独的个体纳入某一团体,因为社团是上海人“日常生活的社会依托”[2],可师陀依然在困窘的生活中保持着个性的独立。正如师陀在《〈马兰〉成书后录》中所谈到的,“在文学上我反对遵从任何流派,我认为一个人如果从事文学工作,他的任务不在能否增长完成一种流派或方法,一种极平常的我相信是任何人都明白的道理,而是利用各种方法完成自己,或者说达成写作目的”[3]。师陀反对把自己纳入任何团体流派,却并不拒绝从一切流派中获取灵感,选择有益于艺术创造的积极因素,来完善和充实自己的艺术世界。他与巴金、丁玲、沙汀、王鲁彦、陈荒煤、唐弢、沈从文、李健吾、卞之琳、姚雪垠、柯灵等不同流派团体的作家都有交好或往来。他以强大而独特的“自我”兼容四方,积极吸纳着异域文化理论和现代写作技法,形成个性鲜明的艺术品格和创作追求,实现了作品的不断创新。通过对师陀创作版图的全景式考量可以看到,他行走于启蒙一途,承继着鲁迅对国民精神和历史文化的理性烛照,同时又将左翼作家直面现实、书写苦难的气魄,京派作家关注人性、坚守诗美的热情和现代派作家质疑命运、探究终极的哲思融入其中,艺术化地呈现出对于人的尊严、和谐的生命境界和永恒价值的追求,实现了生命的自由表达与艺术自由表现的完美对接。师陀以创作表明:“一个民族的健全的丰厚的文学传统,是建立在作家独立精神的持续性和艺术形式的积累的基础上的。”[4]
作为20世纪文学之流中的个体,师陀注重民族文学传统的承继和世界文学优秀质素的吸纳。文学传统支撑和丰实了作家,他又进一步转化、创造,承载起民族文学传统延续、发展、新变的现代化使命,并惠及到当下的创作。虽然对说书艺术和话本小说的爱好,帮助师陀成为一个言说故事的能手,但与这些民间文学传统比起来,属于文人文学传统的抒情文学因子与师陀内在的沉静、诗性气质更相契合。因此,受其熏陶,师陀本质上还是一个抒情诗人。他始终保持着对古典诗词、散文游记、山水画卷的热爱和研习,并创造性地引诗歌、散文、绘画等因素入小说,打破了小说与相邻文学艺术形式之间的壁障,创作出一些具有综合艺术色彩和模糊文体边界的作品,像《果园城记》这样代表着他成熟风格的“师陀式”的文本被评论家赞誉为“小说而兼有诗的品质,散文的风格”[5]。师陀吸纳着抒情文学传统并大胆创造,情调结构、象征隐喻、意境营造、以画入文等手法,浓郁了师陀作品的整体抒情氛围和古典情韵,显示出一个具有思想力度的作家柔性隽永极富个性色彩的一面。西方文学中的阿左林、莱芒托夫、梅里美、哈代、高尔基、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作品也伴随着五四新文学,进入了师陀的视野。在师陀的作品中,不难看到西方文学传统的优秀质素。师陀个性独具的文学世界不仅映照着过去,而且还昭示着未来,潜在地推动或引导着当代作家对文学世界的营构。且不说在抒情小说那一脉中,师陀不求文体界限鲜明、随意赋形的写作方式,以及散文化的小说中体现出的诗的节奏韵味、诗的语言、诗的构思与意境对当代作家的影响;也不说在关于知识分子的文本中,师陀以社会责任为基点,以灵魂的拷问与人性陷落的查究为诉求,以社会的全面改善以及改善的无限性与人存在的有限性之间矛盾的揭示为终极旨归的“自审”与“他审”对当代作家的启发;单就乡土文化小说而言,就可看到当代作家与师陀的一脉相承,或者说师陀为当代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与书写维度。当代寻根小说代表作家贾平凹曾说:“欲以商州这块地方,来体验、研究、分析、解剖中国农村的历史发展,社会变革,生活变化,以一个角度来反映这个大千世界和人对这个大千世界的心声。”[6]这样的表白让人想起40多年前写作《果园城记》的师陀相似的更为凝练传神的表述:“我有意把这小城写成中国一切小城的代表。”(《果园城记·序》)的确,在韩少功、贾平凹、郑义、李杭育、郑万隆等作家为代表的文化寻根小说中,我们能看到师陀式的欲以人的命运折射中国的命运,欲以个体文化人格的剖析探究民族深层文化心理,以为人类的灵魂寻找到稳定的精神栖息地的写作路向的延续,看到师陀式的于乡村与都市、传统与变革、情感与理性之间犹疑和抉择的精神矛盾的呈现。只是,与师陀比起来,某些当代作家的历史使命感和文化批判精神相对薄弱,他们屈服于情感,持城乡二元对立的立场,更愿意退回到知识分子的那个“精神乡土”。当然,如师陀般理性、超越,以思想者和诗人的双重身份投入写作,并在其中表现出越来越鲜明的生态意识的作家也不乏其人,王安忆在谈她写作的小说《归去来兮》时说:“归去来兮?走进白云?走出白云?自然和都市?”虽然她对遥不可及的未来难以把握,但她还是在梦想中高扬理想:“既不要失去与自然协调的纯净、质朴,又不断地去追求和创造最现代的幸福生活。”同样是由写人、由写故乡的地域文化抽象为对整个民族文化的书写,在创作延续中,与师陀相比,一些当代作家丰富了创作技巧,繁荣了主题表现,扩大了借鉴资源,加入了“阅读快感”的设置。但是,却在一定程度上稀薄了地域美学特征、现实责感、人性关怀、哲理意味,软弱了理想精神的张扬,这些都是可以在师陀的文学世界中吸纳到的优长。
师陀是一个极具道德感和责任感的作家,他严肃的创作态度与正直的创作品格彰显出作家的精神境界和人文理想,给予读者和作者以丰厚的精神滋养。师陀不属于才思敏捷、天马行空的天才型作家,然而,他有他自己的优势:沉郁、缜密、勤恳、耐苦。人们的追名逐利没有扰乱他的心灵,他绝不出卖自己的良心和才华。当上海的作家们“迅速的著书,一完稿便急于送出,没有闲暇在抽斗里横一遍竖一遍的修改”[7]时,他却蜗居在那间棺材大小的“饿夫墓”中,“在极大的苦痛中还抱无限耐性,不计岁月的为人物及故事工作过服务过”(《果园城记·序》):《果园城记》耗费了8年长长的岁月、《结婚》酝酿了三四年、《马兰》花了大量的心血,以致作家在完稿搁笔时感叹:“我疲倦了,纵然书中人物的生活让我亲自尝试一遍,我也不会感到像现在劳苦,我尽了我的力了。”(《<马兰>成书后录》)他真正做到了美国作家弗兰克·诺里斯在《小说家的责任》一文中说过的:“作家,不应该像农村集市上机灵的魔术师那样,只想从观众身上捞取富余钱,而应该严肃、斟酌,认识自己的可能和限度,并以极其正直的精神对待自己的任务。”师陀反对文学屈服于金钱,也不赞成文学做政治的奴隶,他张扬写作的个性色彩、审美品格和超越精神。但作为一个有担当的作家,师陀并不无限地膨胀“自我”,他要求作家在坚守自我的时候与时代、国家、民族相通。他的作品集《里门拾记》、《野鸟集》、《上海手札》、《无名氏》、《江湖集》等,洋溢着批判现实、关注政治、关怀民众、检审文化的热情。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年代,师陀不同于那些在创作中片面地追求艺术的“精”与“雅”,疏离政治、有意低徊、顾影自怜的作家,他勇于对历史和社会保持理性认知和批判精神,并尽量淡化为严酷的战争环境铸就的以狭隘的功利主义为特征的情感和思想规范,以风格独具的创作为民族解放与国人灵魂的更新承担起一份责任。这种道义书写的精神力量,既体现了中国文学的原色,也在一定程度上规范并引领着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走向。因为怀抱时代理想,以文学参与着历史的创造,师陀的作品中没有同时代某些作家作品中存在的萎靡和颓废,而是具有历史的品格,成了历史的部分。“时代要求素朴,是浮沫的东西,让人清清楚楚看出了是浮沫。”[8]师陀不为金钱、不为名利,以一种宗教式的热情和献身精神,坚定执著地在新文学的艺苑里默默地劳作。他培育的果实饱满甘醇,是时代浮沫下独特坚实的“这一个”,它们不一定都能取悦于当世,但却属于文学史永恒的时空。
二
作为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师陀的创作也存在着缺陷。单薄的文化教育背景、不够丰厚的人生阅历和文化积累、农民的思维习惯和情感生活特点影响了他整体创作视野的广度。他从“生活样式”这一视角观照民族生存,因为有着源自乡村生命体验的探究和思考,他对于乡土社会“生活样式”的考察获得了成功,他的《果园城记》思想性和笔力都不弱于一位世界性的小说家。然而,面对乡土之外的世界,他的属于自己的对世界的把握和解释有一点力不从心。与张爱玲笔下的上海比起来,师陀对上海的叙述似乎还没抵达这个城市的本质,多重文化的纠结没有演绎得足够充分。与钱钟书比起来,师陀对于都市知识分子人性的剖析,多了想象性的夸张成分,而“幽默”因为没有足够的智慧作支撑,反而成了一种外加的“佐料”,有些刻板、肤浅。因为对能否把握都市的生活不太自信,师陀写得有些拘谨,不像张爱玲或钱钟书运笔时如跳踢踏舞般自由流转。对生命本体持有的悲观主义态度使师陀这位草根出生的农民作家与钱钟书、张爱玲等有着精英文化教育背景或是贵族血统的作家交汇了。他们都书写生命个体在命运的围城中左冲右突,自以为能主宰自己的命运,最后却终难如愿的悲剧。在师陀那些笼罩着朦胧的哀感的作品里,你能感受到他对那些挣扎在命运之网中的人物的感同身受的同情,他看到了他们的局限,也颂扬他们在苦难中的明慧与韧性。然而,师陀对人性的考察和生命本体悲剧的理性洞析不及钱钟书与张爱玲那样鲜明、刻深、毫发毕现,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对现代人生的哲学思考。师陀对西方现代主义创作方法的学习很努力,但有时让人感觉老实、生硬,没有像完全融于颓靡、暧昧的都市之风的刘呐鸥、穆时英等新感觉派来得老练、自如。他的合于规矩的语言、情感和结构,明晰了小说的主题,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小说的生活容量与思想容量。
师陀观照乡土承继的是鲁迅精神并进而升华至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探索的路向,《果园城记》就是体现其哲思、彰显其思想深度的作品。但令人遗憾的是,师陀没能持之以恒地像鲁迅一样站在人类学的高度,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切入国人的生存,进而在哲学的意义上对整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积淀做出持续的全方位的价值判断。虽然他创作出了《谷》、《里门拾记》、《落日光》、《野鸟集》等许多从单个角度看起来很优秀的乡土小说,但却没有创作出更多的像《果园城记》一样有着把握世界整体的浑厚与深刻,包涵着生活的延展和思想的延伸的作品,也没有提炼出像阿Q一样有着高度精神象征性和概括性的形象。
可以说,师陀的作品从文化的角度观照乡土中国,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中国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但从另一方面来看,着力于文化价值判断,有时会使作家过多地徘徊于“自我”的象牙塔中凝于“过往”的沉思,疏忽了时代情绪心理的表现,沈从文似乎给人的表象即是如此。但师陀不一样,他最初是以一个战士的姿态登上文坛,主观上他一直努力使自己与时代相通。或许后来因为政治视野有限,或许对“时代”本质探究用力不足、深度不够,他虽然有很多呼应于时代的优秀作品,但也有不少作品因为意图直露、思想掘进不够深入,未能探寻到社会心理的暗流微波和时代的“力”掩盖下的灵魂搏斗。师陀的确参加过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和不少进步活动,阅读过许多革命书刊,交往过一些共产党朋友。但他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获取也许只能算是零散的、断续的,而不是系统、坚实的占有,囿于知识分子的圈子也使作家对工农革命难以有深入的接触与认识。可踏入文坛不久的师陀有时却急于以无产阶级世界观来正面描写工农阶级和实际斗争,因准备不足火候未到,有时难免显得捉襟见肘。师陀早期创作的这些不足,也是时代文学共同的症候,在特定的情境下是可以理解的。作为一位有着深厚忧患意识和使命感的作家,在逐渐成熟的岁月中,他努力以笔为武器更深地介入现实的黑暗。当追随左翼流行的创作范式写作一些“急就章”后,他很快意识到这种急功近利的标语、口号式写作对艺术规律的背离,进而转入能够融入自己生命体验的发掘国民精神病苦的一途,尝试着在社会现实与人的生命状态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通过拷问国民灵魂,来表现社会人生。
师陀与沈从文一样,都是对中国重大现实问题有独立的思考,并从文化心理层面进行发掘的作家。沈从文以某种“偏执”与激情,表达了构建理想的人性和重造民族文化的愿望,契合了中国思想史的巨大命题。遗憾的是,师陀有批判的深度却没有建构的实践。乡土与都市这两大现实中的生存空间,谁最足以托起人类理想的生活?师陀游走于乡土和都市之间,通过大量文本呈现了对于理想生存的思考。面对乡土,师陀看到了貌似和谐的自然生态下不和谐的精神生态与文化生态。看来,理想的生存不是如有的作家所宣称的“倒退”,“不能退回到那个时期的未受伤害的乡村风貌”[9]。面向都市,物质文明极度丰富下日趋恶化的自然生态与精神生态同样令人触目惊心,既不能以乡土文明来批判都市文明,也不能简单化地以都市文明来取代乡土文明,那么,怎样的生存才最接近人“诗意的栖居”?颇具双重批判眼光的师陀没有言说,他只停留于批判,他在建构的空缺中丧失了一定的精神深度、创造活力以及一定的读者群体。师陀是理性的,但过分强大的理性有时反而窒碍了他的审美感受力,使他缺乏了萧红那种对世界的浑然一体、朴素而亲切的直感,作品也少了些许健旺的活力、恣肆的元气、自然的情致。
然而,瑕不掩瑜,作为20世纪乡土作家的杰出代表和诗化小说的积极探索者与实践者,师陀依然是文学史上不可复制的永恒存在[10]。他通过形象世界对中国乡土文化形态及深层缺陷进行自觉探究,为文坛提供了一幅现代中国“生活样式”的浮世绘,他创制的“果园城”也成了乡土中国的永恒记忆。他既承继传统,又勇于创新;既关注时代,又言说自我,并以哲学的眼光探究终极,他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证明了作家对时代的感念、对人的深度关注以及审美意识是可以和谐统一、互为表里的。他的文学成就,他的文品人品为当代文学的发展,为当代作家精神的再塑提供了有力的借鉴和坚实的依据。“一件艺术品的全部意义,是不能仅仅以其作者和作者的同时代人的看法来界定的。它是一个累积过程的结果,亦即历代的无数读者对此作品批评过程的结果。”[11]对于一个作家亦是如此。师陀的文学史价值与意义依凭作家丰厚的创作成果和独特的创作品格,在百年批评话语的变换之间不断累积与彰显。
[1]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1[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4.
[2] 小浜正子.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M].葛涛,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34.
[3] 芦焚.《马兰》成书后录[J].文艺杂志,1943,2(3):71-112.
[4] 洪子诚.作家的姿态与自我意识[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215.
[5] 师陀.果园城记[M].上海:上海出版公司,1946:5.
[6] 贾平凹. 小月前本·在商州山地(代序)[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7] 苏汶.文人在上海[J].现代,1933,4(2):12-17.
[8] 胡兰成.乱世文谈[J].天地,1944,8(11):20-21.
[9] [德]冈特·绍伊博尔德.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科技[M].宋祖良,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240.
[10] 王欣.师陀的现代婚恋观探析[J].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2):203-207.
[11] [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M].刘象愚,邢培明,陈圣生,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36.
[责任编辑 杨玉东]
The Value of Literature History and Limitations of Shi Tuo’s Writing
WANG Xin
(School of Liberal Arts and Law, Hen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Jiaozuo 454000, Henan, China)
Shi Tuo is an eminent representative of Chinese rural literature writers, an active explorer and practitioner of poetic fiction writ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He upholds creative personality, carries forward national literature tradition and adores a serious attitude and integrity in writing, which not only brings about excellent quality and vivid literary landscape for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rovides rich intellectual resources and a new writing dimension for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creation, which further serves a role mode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literature. However, due to Shi Tuo’s poo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insufficient life experiences, peasant’s thinking manner and emotion, there are some limits in his urban and rural novels.
Shi Tuo; the value of literature history; limitations
2013-10-19
2012年度河南省高校科技创新人才支持计划;河南省社科规划课题(2013CWX029)。
王欣(1974—),女,四川资中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
E-mail:wx1996@hpu.edu.cn
I246.7
:A
:1673-9779(2014)01-00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