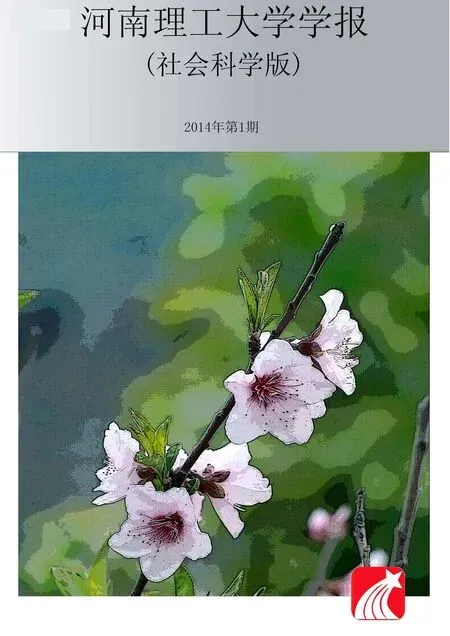时间在空间中流淌
——读贾平凹小说《腊月·正月》
魏华莹
(1.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北京100872;2.河南警察学院,郑州450000)
贾平凹的中篇小说《腊月·正月》发表于《十月》杂志1984年第4期,是其继《小月前本》、《鸡窝洼的人家》之后的又一力作,获得了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也是“商州系列”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部作品中,贾平凹继续抒写了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陕南山区的自然与人文景观,并且着重写出了变革对于传统心理结构的冲击和影响,这部作品对于贾平凹的写作来说意味着何种转变,又贯穿着作者的哪些思考呢?
一、两户人家
在《腊月·正月》之前,贾平凹就已经开始探索改革之于乡村带来的种种变化,包括《小月前本》中小月在不正经务农的小商贩门门和传统农民才才之间的爱情摇摆,也包括《鸡窝洼的人家》禾禾不安心农业生产,作为农民又不想当农民的种种副业尝试。在这些画卷中,贾平凹写得极富生活气息,对于乡土人物平凡生活的淡淡诗意描写,成为一种独特的美学现象。这也是作者创作发生重大改变的系列作品。它起因于1982年陕西的文学评论家 (主要是“笔耕”文学评论组的评论家)对其1981年前后的作品进行的一次大的、全面的评说,这便是《沙地》、《好了歌》、《“厦屋婆”悼文》等等,以及《长城》杂志关于《二月杏》的批评。这些批评意见,使得贾平凹深感震动[1]:
一批又一批作品的发表,我等待着它们的爆炸,等待着社会的赞美,但是,回答我的,却是评论家的批评。批评得多么严厉啊!
我认真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分析自己的优势和劣势,针对自己生活阅历的不足和认识生活的能力不强之短处,我只能到商州去丰富自己,用当时的话说:“再去投胎!”
我开始一个县一个县游走,每到一县,先翻县志,了解历史、地理,然后熟人找熟人,层层找下去,随着这些在下面跑着的人到某某乡、村、人家,有意无意地了解和获得了许许多多的人和事。
城市生活和近几年里读到的现代哲学、文学书籍,使我多少有了点现代意识,而重新到商州,审视商州的历史、文学、传统的和现实的生活,商州给我的印象就相当强烈!
正是1983年开始的商州之行,使得当代文学又增添了新的地理版图“商州”,并和沈从文的湘西、莫言的高密等等绘筑在文学的地图上。早春二月,从省城西安回到商洛山,贾平凹游走白浪街头,挤进人群和乡亲们拉家常,闻知开饭馆的老秦刚和女儿吵了架,将女儿赶出门外了,就搭讪着进了人家屋子,听老人讲出了和女儿的冲突,闹矛盾的根根梢梢,并据此构思了《小月前本》。又跋涉在商洛最偏远的镇安县,访问了养蚕专业户,专程去探访了解村子里队长和一位复转军人换老婆的情况,写出了《鸡窝洼的人家》。而以当年回家过春节的经历书写的《腊月·正月》中,贾平凹则开始更深层面的思考,摆脱了之前较为浓重的故事情节,而是重点写出变革年代对人性、心理的冲击,这主要通过两户人家的冲突展开。
个体户王才和文化站长韩玄子是颇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并非之前写作中安于农业生产和热衷副业发展的传统与现代农民意识冲突,而且进入到文化哲学层面,使得作为乡村秩序既得利益者韩玄子以及新兴暴发户王才之前的种种纠葛、心理暗战得以彰显。韩玄子“一生教了三十四年书,三年前退休,虽谈不上是衣锦还乡,却仍是踌躇满怀。因为他的学生‘桃李满天下’,有当县委书记的,也有任地委部长的;最体面的是,他的长子,叫大贝的,竟是全镇第一个大学生,现又作了记者,在省城也算个了不得的人物!” “他家里,四间堂屋,三间厦房,墙砌一砖到顶,脊雕五禽六兽,俨然庙宇一般坚固。”[2]281相较于韩玄子的农村贵族身份,王才的历史则是卑贱、不上台面的。“王才是他的学生,又瘦又小,家里守一个瞎眼老娘,日子恓惶得是什么模样?冬天里,穿不上袜子,麻杆子细腿,垢甲多厚,又尿床,一条被子总是晒在学校的后墙头上。什么时候能体面地走到人前来呢?”“当了农民,王才个子还是不长。犁地,他不会,撒种,他不会,工分就一直是六分。直到瞎眼娘下世、新媳妇过门,他依旧是什么都没有。就这么个不如人的人,土地承包以后,竟然暴发了!”[2]306按照政治学家的话语,“政治结构的基本单位是个人角色。一个角色就是一种规则化的行为模式……描述一个政治结构也就说明了各种角色之间的联系;每个人各就其位,在这个位置上,人们期望他经常按一定的方式行事”[3]62。在韩玄子的以往经验中,王才是不如人的人,但就是这样的人,但通过办食品加工厂迅速富裕起来,进而严重挑战到他在村子的地位,这无疑引起他的极大不满,并竭力压制王才。
贾平凹善于写矛盾,从《满月儿》时期姐妹俩的性格冲突,到《小月前本》中小月的爱情纠结,再到《鸡窝洼的人家》中两户人家错综复杂的关系,到了《腊月·正月》似乎更为明了,韩玄子的不满打压与王才作为“改革者”的挣脱,进一步印证了反对农村改革的最顽固最有威胁性的阻力并不在普通的农民中,而是在那些由旧秩序获得优越感的人之中。贾平凹说,他是用春秋战国时代新兴地主阶级与奴隶主贵族殊死斗争的那种历史感来写《腊月·正月》的。所以,这部作品能做到时代感与历史感、真实性与倾向性的内在统一。对于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文学来讲,伤痕、改革、寻根此起彼伏,交相呼应;同时,也是与“改革开放”密切同构的,如果在新的意识形态下写出文学的新意,如何在中西合璧、融会交流的文学形态中走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子呢?贾平凹更想着眼于考察和研究这里的地理、风情、历史、习俗,于是他从年前年后这一极富民族学和风俗学的层面着手。
二、年前年后
和贾平凹一同深入商洛山区采风的何丹萌透露出《腊月·正月》的写作痕迹:“那年春节,是我第二次去他家,正月初三我们去逛丹凤县城,因初四即小妹新婚喜日,临走老人叮咛让早点回来。”“正月的公路上,满是穿红戴绿的拜年人,有的提篮,有的背包,有的架单车前儿后女地一路如风,有的三两人相伴着说天谈地。望着来往如梭的行人,我感慨道:‘一年到头地忙,腊月也是忙,难得正月的逍闲,正月的气氛呀……’话没说完,平凹猛睁开眼,望了眼摩肩接踵的人们,深情地说:‘腊月,正月,腊月过去不就是正月吗?’他又眯起双眼,但这回没了睡意,又思索开了……简直预想不到,春节未过完,他的中篇小说《腊月·正月》就脱稿了。读罢手稿,我问:‘一些描写很有些象你们村你们家的事,王才这不是咱一块去山阳那个食品加工专业户的小伙?’他忙笑着制止:‘不敢,不敢这么说……要不,一对入号麻烦事就来了!’《腊月·正月》就是他偶然地想到了腊月过去就是正月,即经过艰辛漫长的改革,必然会有一个新的局面,这是大势,谁也不会留着年那边。”[4]
因为是一气呵成的创作,最容易看出作者在创作上流露出的潜意识。贾平凹曾如是总结,自己“常常一组一组地各组以三篇小说为步伐进行‘步步为营’,我写出了《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这一组。它的写法与三录不同,题材着眼于现实生活。当然,这一组,我的目的并不在要解释农村经济改革是正确还是失败,政策是好是坏,艺术作品不是作为解释的,它是一种创造。所以,这一组小说的内容全不在具体生产上用力,尽在家庭,道德,观念上纠缠,以统一在三录的竖的和横的体系里”[5]。正是在这接二连三的创作中,贾平凹意识到文化的兴衰与人的命运与心理的变化才是小说家重点关注的对象,开始追求用民族特色来表现时代生活、挖掘时代精神。在文本中,韩玄子为打压王才,做出种种挑战,包括阻止其买队里的四间公房,因自家儿子大贝、小贝集体反对,筹不来钱作罢;王才包场电影,他便鼓动巩德胜也包场电影打擂台。而闹社火时有意不让狮子队进王才家门,引起对方内心极大酸楚并进而反击,则是文中浓笔重彩之处。
“鼓儿咚咚,锣儿锵锵,大小三个麻丝做成的狮子,翻,掀,扑,剪,相搏相斗,然后一起面向堂屋,摇头晃脑,领头儿的就在几十个彩灯彩旗下大声说一段吉祥快板。完毕,韩玄子请客入内,送上两瓶好酒、两条好烟,二贝娘便将三尺红绸系在狮子头上,接着有人点响了鞭炮,很是热闹了一番。”[2]373相形之下,“王才很纳闷狮子队怎么没到他家来?让媳妇在门口大场上张望了几次,渐渐听得锣鼓声慢慢向后塬村远去了,知道再不回来。王才媳妇一回到家,就伤心地趴在炕上呜呜哭”。这次的打击也激起了王才的反抗之心,第二天,天未黑,白沟村的狮子队就进了镇,故意张灯结彩,锣鼓喧天,在王才家的院子里耍了一场又一场,整整一个小时不肯停歇。接着,夜里又来了竹马队,又来了魔女队,来了就独独往王才家喝彩,喝彩完再在大场上耍闹一场。
韩玄子在腊月里利用自己的既有威望狠狠整治了王才,但是在正月里,随着狮子队、闹社火这些极具有民俗特色、集体形态的群众性活动中,因王才的金钱后盾而节节败退。正如书中所写,“韩玄子毕竟只是镇街上的韩玄子,他管不了白沟村”,即便在家庭内部,对于儿媳白银穿两个扣的西装上衣、穿拖鞋、烫发等种种“时髦”行为深恶痛绝,但他也同样无能为力。虽然在这部作品中,贾平凹仍是在探索改革时代乡村社会的种种变革,并试图深入到文化心理层面,但他的故事仍是以改革者的全面胜利而告结束,其结尾的清官模式,即县委书记重视王才、全面支持其在雇工18人的规模上继续扩大,而轻韩玄子没有去他家拜年,来宣告二者的胜负不免有图解之嫌。正如有学者指出:“80年代文学”是一个与“改革开放”的国家方案紧密配合并形成的文学时期和文学形态。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中也有如下回顾:“1982年,由于发现有些个体户雇工超过8人,立刻引起了争论。但邓小平说,怕什么,难道这会危害到社会主义?他用了一个朴素的例子来说明自己的态度:如果农民养三只鸭子没有问题,那他又多养了一只鸭子就变成资本家了?给私营主能雇多少人划出界线在当时仍是相当敏感的问题,需要由邓小平和陈云这样的人亲自拍板。邓小平对陈云说,如果公开讨论这个问题,会让人担心允许私营企业的政策有变。因此他建议‘雇工问题,放两年再说’。一些企业害怕树大招风,但也有一些企业在继续发展壮大。这段时间邓小平继续避免公开表态,他的策略是允许私营企业发展,但不使其引起舆论上的反对。”[6]437
可以说,贾平凹在《腊月·正月》中政策对于乡村生活的改变可以从改革的认知装置中寻求依据,正如当时研究者所概括的,这三部中篇小说的一个共同特点,都是着意于描绘农村新的生活和新的人物,“通过新的人物的改革业绩和改革所引起的道德观念的变化,来反映和赞颂中国农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所发生的历史性转折”[7]89。仅仅对政策的图解,恐怕低估了贾平凹的艺术表现能力,作为一个早已成名的作家,并在《商州初录》、《商州又录》中对商州的地理、风土、人情作了全面诠释和思考的贾平凹,在《腊月·正月》中所表现的内容虽然受到当时改革文学的规训,但他仍有自己的美学追求,正如他所说:“人是活在尘世上的,每个人都顺着潮流往前走。大风来了所有的草都摇晃,但从事创作有时你得感应整个时代,要坚持自己的。”[8]68恐怕在作品中,他更想呈现的是对变革声浪的思索。
三、变革声浪中的思索
在文学史序列中,探讨乡村文化变迁的作品不在少数,许多作家已敏感地意识到社会转型给人的心理结构、乡村文化所带来的巨大冲击。从《长河》开始,沈从文的创作重心就转移到了“处在自在状态的生命形态及其在剧烈社会变动下的演变”[9]235。而在商州游走的贾平凹,也感知到社会转型时期到来所带来的变化,并进而思考“历史的进步是否会带来人们道德标准的下降,浮虚之风的繁衍呢?诚挚的人情是否只适应于闭塞的自然经济环境呢?社会朝现代的推移是否会导致美好的伦理观念的解体或趋尚实利世风的萌发呢?这些问题使我十分苦恼,同时也使我产生了莫大的兴趣”。
不可否认的是,韩玄子这个人物的悲剧性有着时代意义,他是作品中所刻意营造的新旧冲突中作为“旧”的典型代表,相比较青年人王才、二贝,他已六十开外,是老年人,在儿子二贝眼中,“我爹人老了,旧观念多”;在文化结构中,他常翻爱读的仍是古时的《商州方志》,并以古人的标准来自我归省和审视他人。在时代风潮中,他注定沦落为悲剧人物,即便有着很好的出场,却在变革的声浪中步步溃败,正如那腊月和正月的不同,时间的变幻即使对于封闭的空间结构也会带来不同的心理感受。
贾平凹把他创作历程中的三种创作境界归纳为“单纯入世”、“复杂处世”和“冷静观世”[10]。也许韩玄子、王才只是他笔下的表意符号,但在这些符码所代表的青年/老年、新/旧、改革者/墨守成规者之间,却悄悄进行了一种农村权力机制的解体。让韩玄子忿忿不平的是,乡村干部除了计划生育什么都管不了了,他这个文化站长连一年一度的社火也组织不起来了,商品社会的逐利性一再打压着他为之骄傲的人情和脸面。福柯说:“权力无所不在……这不是说它囊括一切,而是指它来自各处。”权力有多种含义,其中一种解释认为:“在社会关系中,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效果的支配能力,它又表现为三种形式:⑴一方强制另一方做某事的能力;⑵某一群体不仅有掌控对其有利的结果并且还有制定游戏规则的能力;⑶一种操纵人们而不会引起不满的能力……”[11]90无论从那种形式来看,韩玄子的控制能力在送女子的宴席上全面崩盘,平日里最爱讲人情的韩玄子家里的客人跑走多半,王书记和张武干、韩玄子平日喝酒总是吆三喝四、猜令划拳的,那日也喝起了哑酒……礼俗作为被神圣化了的传统,本是村落家族文化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却也面临着分崩离析,“第二天,便是正月初三,依照风俗,社火从这一天开始,一直要闹过十六。经过全公社动员、安排,这天上午,川道地的各村就响起锣鼓,十点左右,各路社火芯子抬出来,往镇街上集中。最后在街东大场评比,才算结束”。谁知今年,“韩玄子去催了几次,都借口没有经费,不愿干了”。 “眼看到了正月十二,县上要进行社火比赛,镇子的社火却组织不起来。”最终仍是王才用40元钱加以摆平。正如有社会学者所分析的,“包产到户不仅改变了组织结构,而且使服务于经济发展的利益观念深入人心,利益观念、利益原则成为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的标准,一定程度上动摇了集体互助精神的价值和道德基础”[12]63。
“商州固然是贫困的,但随着时代的前进,社会的推移,它是和全国别的地方一样,进行着它的变革。难能可贵的是,它的变革又不同于别的地方,而带有其浓厚的特点和色彩。我便产生这么一个妄想:以商州作为一个点,详细地去考察它,研究它,从而较深地去感受中国农村的历史演进和社会的变迁以及这个大千世界里人的生活、情绪、心理结构的变化。”[13]422回过头看,贾平凹的创作一直延续着对浮世人生的思索,如《浮躁》对时代情绪的体察、《废都》对于市场经济时代文人的堕落、《秦腔》乡村文化消泯的哀唱、《带灯》对于微弱光亮的捕捉都是如此。对于贾平凹来说,他虽不断转换阵地,却试图以点带面,在封闭的空间中写出流动的时间,正如《腊月·正月》中的商州、《浮躁》中的州河、 《废都》中的西京、 《带灯》中的樱镇,这些小小的空间总是传神地表达着时代的情绪,正如他所宣称的:“作家艺术家生存于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就决定了我们的品种和命运,只有去记录去表达这个时代。以我个人而言,我想,我虽能关注,观察这个身处的社会,我不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我开不了药方,我难以成为英雄,我也写不出史诗,我仅能尽力地以史的笔法去写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自然地使他们在庸常而烦恼的生活中生出梦想的翅膀。”[14]50
[1] 贾平凹.答《文学家》编辑部问 [M] //贾平凹.贾平凹文集:散文杂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
[2] 贾平凹.腊月·正月[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
[3] 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 [M].曹沛霖,郑世平,公婷,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4] 丹萌.贾平凹在商州山地 [J].延河文学,1985(4):63-68.
[5] 贾平凹.我的追求——在中篇近作讨论会上的说明[M] //贾平凹.贾平凹文集:散文杂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
[6] 傅高义.邓小平时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7] 唐先田.充满浓郁诗意和改革精神的农村画卷——评贾平凹的三部中篇小说 [J].江淮论坛,1984(5):92-100.
[8] 贾平凹,谢有顺.贾平凹谢有顺对话录[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
[9] 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 [M].北京:三联书店,1986.
[10] 费秉勋.贾平凹与中国古代文化及美学 [J].文学家,1986(1):45-56.
[11] 王晓路,肖薇,徐沛,等.文化批评关键词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2] 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13] 贾平凹.腊月·正月 (后记)[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
[14] 贾平凹.一种责任与风度[Z].北京:社科院外文所,2013.
——商州实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