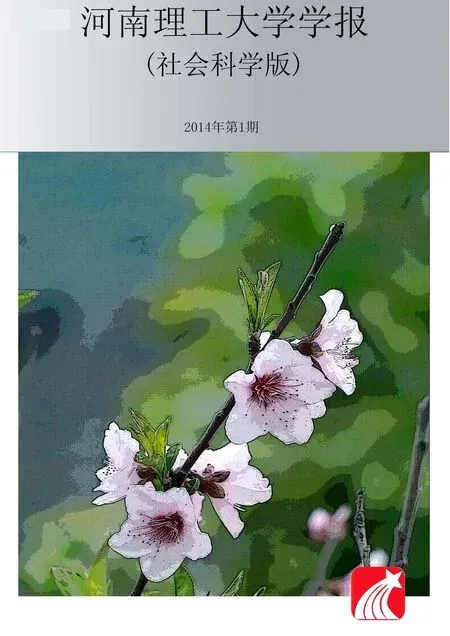全球化背景下加勒比流散文学研究
张建萍
(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天津300300)
谈及加勒比地区可能很多人都比较陌生,但是从这片土地走出了一大批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家。其中最知名的是1992年和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德里克·沃尔科特和V.S.奈保尔,他们使得加勒比文学开始被世界关注并逐渐进入主流文学研究的范围。活跃在世界文坛的加勒比作家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主要在本土进行创作的作家,尼可拉斯·纪廉和阿莱霍·卡彭铁尔是主要代表;第二类是在欧美文坛的加勒比裔作家,有用法语创作的艾米·塞沙勒和爱多尔德·格列森特,还有用英语进行创作的作家,如卡里尔·菲利普斯、克劳德·麦凯、简·里斯、威尔逊·哈里斯、乔治·拉明、爱德华·卡莫·布莱斯维特、弗莱德·达圭尔、大卫·达比狄恩和牙买加·金凯德等,当代新晋作家有奥利弗·斯尼尔、宝林·梅尔维勒和玛琳娜·诺贝斯·菲利普等。
其中,活跃在欧美文坛的加勒比作家非常特殊,一方面他们与加勒比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另一方面,他们又往来穿梭于加勒比、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地,是当代加勒比文学研究专家阿里森·多奈尔所认为的名副其实的“这个世界上最具有世界性的公民”[1]255。因此他们的作品是研究流散文学变迁的绝佳角度,反映了当今世界流散文学的最新动向。
一、加勒比文化背景
加勒比文学之所以与流散研究有着密切关系,这与其独特的文化背景分不开。加勒比位于中美洲,地理位置非常特殊,是近代以来两个世界(西方与东方)、两个大陆 (新大陆和旧大陆)、四个大洲 (欧洲、非洲、亚洲和美洲)和四个殖民地 (英国、法国、西班牙和荷兰)激烈碰撞的地区,也是世界上最早移民地区之一,常年处于不同的种族、语言、宗教、文化传统杂交和融合的十字路口[2]3。不仅如此,加勒比是一个充满差异的地方,它由古巴、多米尼克、多米尼加、海地、圭亚那、牙买加和巴巴多斯等众多小国及岛屿组成,各个岛屿地理特征各不相同,比如圭亚那是个地势低洼、海岸平坦、拥有广阔森林腹地的岛屿国家,巴巴多斯是地形起伏较小的珊瑚岛等,他们还有自己语言并且各自独立成国,每一个岛屿都因受到不同的地理文化的影响而具有特殊性。曾经是殖民地的加勒比各个岛屿上的居民有黑人、白人、欧洲人、美国人、法国人、印度人、中国人、葡萄牙人、犹太人和荷兰人等,而本土人几乎消失殆尽,可以说在文化上是名符其实的“大熔炉”地区,“世界上在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在如此狭小的空间内集中了世界上所有的文化”[3]94。这也是一种以地理、人口、语言、历史差异为基础的文化混杂、混合和抵抗为特征的文化。得益于这种混杂的背景,加勒比走出了许多殖民地作家,因为加勒比曾在很长时间内是英属殖民地,所以这些作家常常用英语来创作,活跃在欧美文坛。但在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随着沃尔科特和奈保尔获得诺贝尔奖,对于加勒比文学才开始关注。
20世纪的50年代之前的加勒比作家主要活跃在加勒比本土,他们并非流散作家,比如维克托·瑞德和米切尔·安东尼,因此不在研究范围之内。如果从流散视阈中审视加勒比文学的特点,其时间应当从大规模的加勒比移民运动开始,即20世纪50年代左右。与此相对应对的第一个阶段是从1950年到1980年左右,是特殊流亡中的前流散时代;第二个阶段从1980年到现在,是全球化背景下的流散时代。但这两个阶段相互重叠,并没有明显的界限。
二、特殊流亡中的前流散时代
对于大多数的流散群族来说,比如犹太人流散群族、亚美尼亚流散群体、非洲流散群体、亚洲流散群体和爱尔兰女性流散群体等,“放逐、流放或者背井离乡”,流亡是他们走向当代流散文化的必经阶段。但是对于加勒比流散群族来说,其走向现代流散的过程中却经历一种特殊的流亡经历。
首先,从流亡的原因来看,在传统意义中,流亡者的人口迁徙行为是一种被迫的行为,主要是因为政治或者宗教原因,通过法律的形式强行将他们驱逐或者放逐,禁止他们再踏上移出国。比如犹太人的流亡,1685年南特敕令被撤消后大批的胡格诺派教徒前往法国的流亡等。从20世纪初期开始,大批的加勒比人离开本土前往欧美国家,但是他们的人口迁徙并非是因为政治或者宗教原因,而是因为经济原因,这可以说是时代背景下流亡的新形势。加勒比移民的主要目标是英国,因为20世纪50年代英国政府规定所有进入英国的移民就可以获得合法的公民身份。但从1962年起,英国移民法的修改限制了加勒比移民进入英国的机会,这影响了加勒比移民的流向,他们纷纷前往美国和加拿大。随着1967年《加拿大移民法》(Canadian Immigration Act)的颁布出现了加勒比人移民加拿大的狂潮。加勒比移民的最初动力是为了寻找更好的教育、技能培训的机会和更好的生活。加勒比地区本身就是一个移民地区,早期在殖民政策下本土居民几乎被灭绝殆尽,为了满足种植园经济所需要的大量劳动力,殖民者将大量的非洲黑人输送到加勒比地区,这样的“奴隶制度定型了加勒比”[4]1。因此,加勒比人们的生活并非十分富裕,同时殖民者往往将其丑化成落后、野蛮和未开化的地区。正如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所写的“加勒比很难被看作是国家……但是更确切的讲,是属于大型社区的边远的农业或者工业不动产。”[5]69相比之下,欧美殖民者则被神化为辉煌、浪漫、充满勇气和伟大的地方,二者之间形成了一种“恋母情节权力方程”,其结果是加勒比人对于殖民者的文化总是充满了向往和崇拜。在殖民者这种对自我文化美化的光晕中,对于加勒比人而言,能够进入欧美社会就意味着获得了巨大的能量,而留在加勒比则意味着灰暗的未来。
对于文学创作而言,流亡促成了大批经典作家的产生。如詹姆士·乔伊斯、艾略特、弗拉迪米尔·纳博科夫、托马斯·曼、贝尔托·布莱希特等的人生大部分时光都处于流亡状态,而流亡中所创作的作品也让他们名声大噪。在一点上,加勒比作家并不例外。比如塞穆尔·塞尔文、乔治·拉明、埃德加·米特赫尔兹、奈保尔、简·卡科瑞、奥斯汀·克拉克、威尔逊·哈里斯、罗瑞娜·古蒂森等都是因流亡而成名。
其次,传统的流亡者往往对移出国充满回归的渴望。这主要是因为流亡者往往在移入国经历了种种歧视、盘剥甚至长时间地受到移入国政策和势力的排斥,为了重塑身份,他们坚持保持着从移入国带来的文化习俗,渴望有朝一日能够重回移出国[6]。即使是他们在新的地方开始了新的生活,也从来没有隔断与移出国心理上的联系。相比他们在移出国积极开拓新生活的野心,他们对于移出国的回归梦想依然是居于首位的,对此,由多尔达·格里桑 (Edouard Glissant)曾写道,“移植人口的首先冲动就是并不是在移入地保持其价值体系的古老的顺序,而是回归”[7]30。但是加勒比流亡群族却是非常特殊的,他们早期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回归渴望。比如奈保尔在他的游记《中途》 (The Middle Passage)中写道:“特立尼达拉岛并不重要……我们的兴趣是外面的世界……。”[8]45拉明离开巴巴多斯的原因与奈保尔的原因几乎相同。对于他而言,加勒比没有太多的文化底蕴,前往文化上生机勃勃的白人世界是最安全的。他在1960年的作品《流亡的乐趣》(The Pleasures of Exile)中曾直白的说:“我们艺术家是不得不离开的。”[9]41而巴哈拉提·穆克尔瑞兹在短篇小说《茉莉花》(Jasmine)中写道:“特立尼达拉岛太小了,但是这却是个大问题。这样小的岛屿怎能够容下下一个充满报复的姑娘?”[10]128同样在 《玫瑰堡的白色女巫》(The White Witch of Rosehall)中,小说中的英国英雄打算回归英国。在海滨,一位送行的老人对他说,“你认为你还会回来新印度群岛吗?”“绝对不会。”他回答[11]。虽然如此,当加勒比群族在移出国很多年后,他们意识到无论在英国、美国或者加拿大等移入国,他们有着所有流亡者所经历的因贫困、种族歧视和压迫所带来的不安全感,因此在移入国生活了几年之后,有许多人重返加勒比。在文化上,在加勒比地区乃至整个黑人世界促生了“黑人意识”运动,具体表现有古巴-波多黎各兴起的“非洲-安德雷斯”运动、海地的“本土主义”运动、流亡欧洲的黑人作家开始为自己的文学创作寻根溯源所兴起的“尼格罗士”运动 (也被称之为黑人文化认同运动)、 “拉斯塔法里”运动等。这些运动以颂扬家园的根源性、神秘性和神圣性为特点。在文学领域,生活在欧美国家的加勒比作家也都无一例外的开始关注回归的问题。许多的加勒比作家前往加勒比寻找他们精神上的家园并进行创作。有的作家甚至将家园定义在非洲,比如卡麦由·布拉斯华特等作家致力于这一方面的工作。
可以说,以回归家园为特点的加勒比流亡文学呈现出了流亡文学的新特点,基于其双重的生活经历,他们往往不自主的通过西方文化的棱镜来审视曾经的家园,而经过西方文化棱镜折射后的加勒比已不同于真正的家园形象,于是当现实中的他们真正回到加勒比后,家园的期望和现实之间产生了巨大的落差,他们因此对于家园采取了摇摆的态度。而这一时期加勒比流亡写作的创新点就是他们开始思索回归的乌托邦性,一反之前将移入国与移出国对立起来的态度,开始积极关注在移入国的生活。萨尔曼·拉什迪在《想象的家园》 (Imaginary Homelands)中以印度为例阐明了这一观点,认为移出国只存在与他们的记忆和幻想中。马丹·萨拉普在其著作《身份,文化和后现代的世界》(Identity,Culture,and the Postmodern World)中也有此类的论述。此外还有塞穆尔·塞尔文的《孤独的伦敦人》(The Lonely Londoners)和《摩西的攀登》(Moses Ascending)、大卫·达比狄恩的《预期》(The Intended)和《消逝》(Disappearance),都在讲述着回归家园的困难。还有一大批关注移入国生活的作品相继出版,比如《霍格斯的黑人:十八世纪英国艺术的黑人形象》(Hogarth’s Blacks:Images of Black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ish Arts)、《黒人作家在英国,1760—1890》 (Black Writers in Britian,1760—1890)等。
可以看出,随着上个世纪中期人口迁徙新特点的出现,在加勒比文学中,家园回归成为精神旗帜,而非实际性的行为,家园的静态定义转变成为动态的变量,其所代表的特征如固定、舒适、回归和团圆一一被颠覆,移入国与移出国之间的二元对立特点正在逐渐的消解,这种特点为全球化背景下流亡文学向着流散文学变化创造了条件。
三、全球化背景下的流散时代
到了20世纪80年代,加勒比流散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与整个世界全球化的背景密不可分,正如范可所指出的,只有在全球化语境和全球化视野的关照下谈论流散研究才有意义[12]。当代美国知名学者弗里德曼指出,流散化本身就是全球化扩散意义的隐喻[13]。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和跨境人口急速流动,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间的交流、碰撞乃至冲突在深度与广度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态势,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流散文化下,流散呈现出反对二元对立的特点。抛去背井离乡所带来的悲惨色彩,流散者往往可以自由穿梭于移出国和移入国之间。虽然流散者的移出国只有一个,移入国却众多,但是他与移入国和移出国之间的距离关系是对等的,因此他们被赋予中间人的身份,同时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动态的,流散者的身份不再是只与“存在”(being)有关,而与“变化的过程”(becoming)有关,流散者永远奔跑在移出国和移入国之间,因此提供了以反二元对立为基础的跨国家的、世界性的、多语言的、混杂性的世界地图。与此相对应,流散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不再是在“此地”或者在“彼地”,因其不断地游走在多种文化之间,因此能够独立的、冷静的、客观的看待各种文化,因此不再如同流亡时期神化移出国的生存方式,也不再将移入国的生活方式与移出国对立起来[14]。
这种流散特征与加勒比文化移民的经历正好不谋而合。到了20世纪80年代,第二代和第三代移民逐渐长大,他们与第一代加勒比移民在国外的经历完全不同,他们大多数因出生、成长在移入国或者很小的时候就移民移入国,而对于加勒比没有太多的实质性接触,他们对于移出国的概念更多的是来自于上一代人的讲述,他们的文化是一种混杂文化,他们既不接受移出国的文化,也不接受移入国的文化,而是产生了一种新的文化特点。
对于崛起的加勒比流散作家的蓬勃潮流,爱德华·萨义德曾评论道“一群耀眼的作家……他们打开了……一扇大门”[15]。与萨义德的话语遥相呼应的是萨尔曼·拉什迪的说法“一种新的小说正在产生……这是一种去中心的、跨国的、跨语际的、同时也是跨文化的小说”[16]。如果为这种去中心的、跨国的、跨语际的、跨文化的流散文学构建特征的话,就是“混杂”。在一定的程度上,是“一种话语和形式的多样性具有高度复杂的合成因素”,对于这种混杂性,米塔·巴内基认为“不仅仅迎合了混杂理论的观念,同时也通过这一个混杂概念来被理解”[17]202。的确,在当代流散文学领域,来自加勒比的作家依然是佼佼者,许多经典的流散文学均出自与加勒比作家笔下。一些流亡的后殖民作家开始通过用移民状态来代替流亡状态来重新确定他们的身份问题。代表作家和作品有卡里尔·菲利普斯的《最后的通道》 (The Final Passage)、汉尼夫·库瑞史的《郊区佛爷》(The Buddha of Suburbia)、査戴·史密斯的《白牙》(White Teeth)、萨尔曼·拉什迪的《羞辱》 (Shame)和《摩尔人最后的叹息》(The Moor’s Last Sigh)、M.G.瓦斯安吉的《英国病人》 (The English Patient)、阿米塔夫·格恩斯的《影子轮廓》 (The Shadow Lines)、巴哈拉提·穆克尔瑞兹的《茉莉花》和奈保尔的《抵达之谜》(The Enigma of Arrival)等。他们不再像往日一样太多的谈及流亡,而是谈论一种混杂的、非静态的、非二元对立的、居于移出国和移入国之间的流散状态。卡里尔·菲利普斯是这一时期的最佳代表。他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加勒比的圣基茨岛,3个月大时同父母一起移民英国北部,同父母一起居住在白人工人阶级居住区,高中毕业后他进入牛津大学求学。1978年菲利普斯前往美国,在早期的英国边缘化经历和后期的美国种族文化对其所带来的文化双重影响之下,卡里尔·菲利普斯正式开始进行文学创作。1980年,他在母亲陪伴下返回圣基兹岛。从90年代起,他开始在美国教书,同时还在英国、印度、瑞士等国家的大学教书任职,因此现在的他常年穿梭往来于世界等地,多变的人生角色和丰富的阅历让他见识甚广,也有着比同龄人更加开阔的视野,因此他被誉为“世界公民”和非裔流散研究的活地图”[18]。他的作品基于自己混杂的经历,他从加勒比移民的角度,也从黑人英国的角度,又从白人的角度来审视流散问题。
除了菲利普斯之外,还有茱莉亚·阿尔瓦瑞兹等作家也堪称加勒比流散文学的代表,她的作品《哟!》(Yo!)中主人公由兰达·佳西亚在移出国人的眼中,她已经美国化了,而美国人依然视她为拉丁女性,她既不属于移出国也不属于移入国。这是流散文学所提倡的身份混杂。流散人群往返于移出国和移入国之间,是永久的移民,对于西方权力而言,他们是少数人群,不会被轻易的同化,因为他们与生俱来的肤色和宗教,而在当前的文化背景之下,他们也不渴望被完全的同化。他们的创作反映了这种经历。
总之,以菲利普斯为代表的加勒比流散作家,致力于一种超越二元对立、无种族的混杂研究路线,提倡流散者的身份既不属于移出国、也不属于移入国,他们从离开移出国之时其便注定永远无法回归,而且流散身份又让其注定永远无法彻底的被同化于移入国,唯一的出路就是如同谢夫描述的状态,即“身在异乡,却如同在家”[19]。目前看来,流散族群的最佳状态是:经过几代移民,他们已经融入而不是被同化于移入国,但又成功地保持了自己的族群特性。他们还强烈抵制将关系简单粗暴的对立,以一种公平博爱的姿态揭示了另外一种真实,让流散群体中所涉及到的所有沉默的“他者”得以发声,而并非将“他者”的范围限定为黑人,“他者”甚至可以是犹太人或者白人流散群族。
[1] DONNELL,ALISON.The Routledge Reader in Caribbean Literature[M].London,New York:Routledge,1996.
[2] 张德明.流散群族的身份建构——当代加勒比英语文学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3] BURNETT,PAULA.Derek Walcott:Politics and Poetics[M].Gainesville: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2000.
[4] CHAMBERLIN,J EDWARD.Come Back to Me My Language:Poetry and the West India[M].Nubana and 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3.
[5] SAID,EDWARD W.Culture and Imperialism [M].London:Vintage,1994.
[6] SAFRAN,WILLIAM.Diasporas in Modern Societies:Myths of Homeland and Return[J].Diaspora,1991(1):301-320.
[7] GLISSANT,EDOUARD.Le discours antillais[M].Seuil,1981.
[8] NAIPAUL,V.S.The Middle Passage:The Caribbean Revisited[M].Harmondsworth:Penguin,1975.
[9] LAMMING,GEORGE.The Pleasures of Exile[M].London:Michael Joseph,1960.
[10] MUKHERJEE,BHARATI.The Middlemen and Other Stories[M].New Delhi:Prentice Hall of India,1989.
[11] RAMCHAND,KENNETH.Decolonization in West Indian Literature[J].Transition,1965(22):48-49.
[12] 范可.移民与“离散”:迁徙的政治 [J].思想战线,2012(01):14-20.
[13] FRIEDMAN,THOMAS L.The World is Flat: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M].London:Penguin Books Ltd,2005.
[14] 郑海霞.美国华裔流散写作中的身份焦虑 [J].河南理工大学:社会科学版,2013(02):200-203.
[15] SAID,EDWARD.Introduction:Criticism and Exile[M] //Edward Said:Reflection on Exile and Other Literay and Cultural Essays.London:Granta Books,2000:xi-xxxv.
[16] RUSHDIE,SALMAN.In Defense of the Novel,Yet A-gain[M] //Step across This Line.Collected Non-Fiction 1992-2002.London:Vintage,2002:54-63.
[17] BANERJEE,MITA.The Chutneyfication of History[A] //Salman Rushdie,Michael Ondaatje,Bharati Mukherjee and the Postcolonial Debate.Heidelberg:Universitatsverlag,2002:194-212.
[18] JAGGI,MAYA.Tracking the African Diaspora[J].Manchester Guardian weekly,1993(30):20-32.
[19] AMERSFOORT,HANS VAN.Gabriel Sheffer and the Diaspora Experience[J].Diaspora: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Studies,2004(13):359-3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