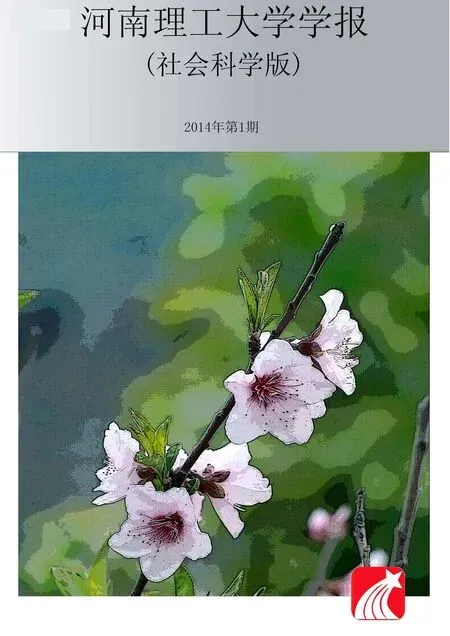焦虑·怨恨·惩罚
——刘庆邦长篇小说《红煤》的精神诉求
史修永
(1.中国矿业大学文学与法政学院,江苏徐州221116;2.中国煤矿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江苏徐州221116)
伴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市场经济的全面崛起,矿区成为社会转型期特殊而微妙的空间地带,它包孕着城市与农村之间各种形式的冲突和矛盾,在不同层面展现着社会底层个体生存复杂多变的人性张力。当代著名煤矿作家刘庆邦,在2006年推出的长篇力作《红煤》,紧紧抓住处在城市与农村夹缝地带的矿区,通过叙述一个农民轮换工宋长玉为了改变农民身份成为一个城市人不择手段向上爬的故事,着力揭示在煤矿这个舞台上,轮换工身份的焦虑所引发的为获得认同而进行的斗争;在城乡二元对立和冲突的体制内,农村青年人由于遭到城里人的排斥而滋生的出怨恨情绪;在成功之后恣意放纵欲望,遭到自然的报复和惩罚,进而沦落为漂泊的异乡人。在故事情节的不断转换中,人性的变异、扭曲和底层个体的生存状态得以彰显,因此,刘庆邦自评到:“《红煤》写的是农村青年进城打工的心灵史。”[1]换句话说,《红煤》为我们深入了解转型期中国社会农村青年进城打工的生存状态和深层的情感心理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一、矿工身份的焦虑与认同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提速,必然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来满足城市空间的建设和发展。在这样的社会情形下,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他们怀揣着发财梦,离开农村,去感受城里人的生活。但是,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之后,不可避免地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如何为生存而斗争?也就是为了更好地生存,必须获取更多的物质财富;二是如何为承认而斗争?即要改变自己的身份并且得到别人的认同,以此在精神上获得满足。《红煤》在描写宋长玉为生存而不懈努力的同时,在更大程度上,不惜笔墨来展示宋长玉为争取成为城里人而进行的争斗。在乔集煤矿,宋长玉只是一个“农民轮换工”,“农门轮换工和国家正式工的一个本质性的区别在于,农民轮换工不往矿上迁户口,不改变原来的户籍关系,干满五年或十年,从哪里来还要回到哪里去。也就是说,矿方利用的是农民工的青春和力量”[2]10-11。农民轮换工的称谓和属性意味着宋长玉的身份处在一个非常尴尬和忧虑的境地,离开农村和土地来到矿上当工人,但是又不具备城里人的身份,更让宋长玉担忧和焦虑的是,当青春和力量消耗殆尽之时,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被退回到农村。为矿区的建设和发展付出了如此巨大的身体和生命的代价,却没有得到相应的福利救济和身份认可,在某种意义上应有的尊严和尊重也没有体现出来。由此可以看出,《红煤》不仅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农民轮换工艰难的生存困境,也深刻地表现出作家对农民轮换工身份焦虑和认同问题的思考。
与孟东辉那些农民轮换工不同,宋长玉能够自觉意识到这种身份的尴尬和焦虑,担心自己将来的命运与矿区规章制度所设定的农民轮换工的退路相一致。同时这种身份的焦虑激发了宋长玉对城里人身份的渴求,他渴望与城市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保持一致,从而获得一种被尊重的生命体验。“如同所有的欲求一样,对身份的欲求有其效用:能激励我们竭力发挥自己的才能,促进卓越者,使我们远离社会中有不良癖好的人及固执的人从而归属于一般的价值体系”[3]。在观念和行为方式上,宋长玉都表现出积极向上的心态。他是高中毕业生,“是有一定文化水准的人,也是胸中怀有大目标的人,自然应当与普通矿工有所区别,并与普通矿工的行为适当拉开一点儿距离”[2]4。他从不抽烟,也不往澡池里撒尿,就连洗澡也非常的仔细。小说中详细描写了宋长玉洗澡的全过程:第一步先洗手和脚;第二步要洗鼻孔、鼻窝、耳郭、耳后、眼睑等容易藏污纳垢的重点部位;第三步就是洗头,宋长玉不用肥皂,而是洗头膏,这在当时是相当时尚和文明的,可以看出,每个洗澡环节都充分体现出他是按照城市文明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虽然他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城里人,只是置身煤城之中,但是在观念和行动上努力向城市文明的身份标识靠近,以便在实践和想象中获得一种满足。这样一来,宋长玉远离与自己设定的身份地位有一定距离的人,避免走向平庸和低级,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完成自我身份的改造和认同。
我们知道,接受高等教育是农村青年走出土地,走向城市的一条途径。只有凭借专业知识和技能,才能在城市里生活的更好。宋长玉虽然高考落榜,但毕竟具备了一定的知识和技能。在二百多位轮换工中,持有高中毕业证书的只有两三个,他就是其中的一个。作为准大学生,他对自己的文化水平和写作能力比较自信,可以说,这是他换取身份和地位的文化资本。于是,宋长玉利用这种文化资本当上了矿区的通讯员,让好多矿工羡慕和嫉妒。以写信的方式向矿长的女儿唐丽华表达爱意,在信中试图通过把自己摆在弱者和落难的地位,让自己的身份充分的情感化和戏剧化,想方设法得到唐丽华同情,与她建立恋爱关系,以此改变自己轮换工的身份。他深信:“他将彻底告别农村、农民、农身,摇身一变,变成一个和现在的宋长玉完全不一样的新的宋长玉。从这个意义上讲,唐丽华将是他老家西北方向的福星,将是给他的命运带来转折的贵人。”[2]16从逻辑推理上讲,宋长玉赢得她的芳心也就意味着赢得了矿长,也就轻而易举地改变自己的身份,扎根城市,过上体面和有依靠的生活。对于宋长玉尴尬的身份而言,虽然在动机上有些不纯,但是为改变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而努力,为获得承认而斗争,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不幸的是,矿长唐洪涛得知宋长玉和唐丽华之间的关系后,借井下的小事故,故意开除宋长玉,使得宋长玉转成国家正式工的梦想破灭。唐洪涛身上表现出的对农村和农民的偏见,让宋长玉认识到自我内心深处的渺小,身上所有的优点形同虚有,自己的存在被偏见和势利观念淹没。这种对身份的歧视和伤害,在宋长玉心里埋下了怨恨和报复的种子。
在小说的后半部分,离开乔集煤矿的宋长玉投奔红煤厂,在岳父明守福的帮助下成为红煤厂的矿长,他依然没有放弃对城市身份的渴求。他不允许矿工称呼他为“窑主”,而称他为“矿长”。回到家乡,通过向乡亲递“名片”来表明自己是城里人身份。阳正县打算实施搬迁和重建,“不管你是什么人,不管你户口在哪里,只要你愿意拿出五千块钱,可以立即转成城市户口,并在新城落户”[2]230。宋长玉一听到这个消息,毫不犹豫地出钱买下了城市户口,借此机会,宋长玉买了一套房子,让一家人铁定成了城里人。耐人寻味的是,宋长玉有房有车,有家庭有事业,过上比城里人还富足的生活,但是,外在物质的拥有和满足,并没有真正改变宋长玉农村人的身份,他对唐丽华说:“和你相比,我还是一个乡下人。”这是宋长玉潜意识的自卑和尴尬。小说通过宋长玉对自我身份的焦虑和身份认同的建构的叙述,一方面表现出对轮换工、弱势群体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发出呼吁,农民工应该得到社会的尊重;另一方面在向读者昭示弱势群体对身份的虚假认同或认同的错位,必然导致人性的变异、精神贫乏和空虚。这是必须予以深刻剖析和冷静批判的。我以为,这是小说的的深刻之处。
二、城乡冲突与怨恨心态
刘庆邦在《红煤·后记》中写道:“城市代表着权力、金钱、美女、高楼、汽车和一切繁华与享乐。而一提农村呢,就意味着偏僻、贫穷、落后、饥饿和被压制与被剥夺。”[2]371我们可以把这段描述看成是作家进行小说创作的大前提和大背景,也是进一步深入理解《红煤》小说创作内涵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因为,这段表述中蕴含着关于现代与传统、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的价值判断。这种价值判断无形中规定了城里人的优越性和城市发展的优先性,而乡村则是在城市强势形象遮蔽之下的否定性存在,先验性地被放置在低劣的位置,这种等级性的存在格局使得农村青年想改变自己的命运、想出人头地,就必须离开农村到城市里去施展自己的才华。小说中写道宋长玉被唐洪涛开除之后,有一段精彩的心理描写: “他早就知道了,除了有农村,还有城市,城市在高处,农村在低处。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他要想混出个人样儿,要想有点儿出息,就必须到城市里去。不能去大城市,去小城市也行。不能去小城市,当工人也行。只要当上工人,靠工资生活,也算半个身子进了城市。待在农村,土里刨食,再埋到土里,一点儿出息都没有。”[2]137-138可以看出,在城乡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中,这种强烈的比较意识成为宋长玉这样的农村青年人向城市发展的强大动力。在现实的发展中,他们充分意识到,面对日益开放、充满诱惑力的城市世界,田园牧歌式的农耕文明已经不可能为他们提供个人发展的资源和机会,也不能承载他们的所有梦想,逃离土地,去城市谋求发展成为当代青年农民的生存选择,他们渴望用城市意识置换自己的农民意识,从而成为一个立足城市的崭新主体。
对于一个单纯、善良和质朴的农村年轻人来讲,自己只有具备一定的心理准备和价值评判标准,才能适应到处充斥着惟利是图、人性冷漠、自由开放和物质富足的城市文明。宋长玉在实现自己向上爬的过程中,一味地用城市的价值标准来衡量自己的价值,忽视了属于自身的心理优势和道德价值标准,这样一来,容易把自己推向了自卑和自怜的边缘,导致心理世界的单一性和精神价值标准的外在化,最终陷入精神迷失的境地。一旦遇到强者的阻挠、排斥和伤害的时候,内心就出现不规则和反常的情感律动,无法用一种成熟和理性的心态来面对城市的强势剥夺,必然产生一种怨恨的心态。当然这种怨恨,“不是简单的自怜,也不只是一种对自身不幸的意识,而是包含着一种谴责和个人愤慨,一种向外投射的,一种不可遏制的不公平感”[4],小说中写道,宋长玉到宣传科假装要给局里《矿工报》写稿子,想要矿上的稿纸和信封,这样可以给家里写信和给唐丽华写情书,反而遭到宣传科长的反复审问,紧张的满头是汉,两腿发硬,结果稿纸和信封没拿到手。对于这件事,宋长玉立刻有一种反应性情感和愤慨的行为。“他再次意识到作为一个农民轮换工的临时性身份,并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地位是那么的卑微。……受到打击的宋长玉,自尊心有所反弹,有所抵抗,他心里说,你不就是一个科长嘛,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什么话都不愿再跟科长说,也没说礼貌性的告辞话,脸一扭就走了”[2]21。当得知被唐洪涛开除之后,宋长玉越想越恨,怎么都咽不下这口气。“他肚子里的疙瘩鼓到一定程度,就通过血液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这种转移类似癌症的转移,转移不会使毒瘤消失,只会使仇恨的毒瘤越生越多,越长越疯狂,似乎连他每个手指头肚上都布满仇恨”[2]133。作为城里人和强势群体的代表,唐洪涛手中“合法的伤害权”构了宋长玉最大的伤害源。相应的,唐洪涛给矿工雨中送伞;为矿工举行集体婚礼,希望有情有义姑娘嫁到矿上;到井下为矿工送肉包子,这些一系列体现唐洪涛开明、亲民和平等的事件,与唐洪涛坚决反对宋长玉与女儿交往,借机开除宋长玉形成鲜明的对比,小说成功揭示了唐洪涛的伪善和虚假的丑恶嘴脸。这也让宋长玉看清楚了,所谓的公正和平等并不是承认他人相应权利上的平等,而是一种口惠性的平等,实质上就是不允许别人超过自己,不允许别人危害到自己的利益和权力。这种强烈的反差使得渴望平等和尊严的宋长玉内心不可避免地受到伤害,自然怨恨情绪随之而来。
对于一切的不公平和个人的自尊受到伤害,宋长玉无法直接作出相应的反击,只能隐忍暂时的无能感和软弱感。这样一来,怨恨的心态和报复感势必强抑在宋长玉的内心深处。当遇到合适倾泻的机会,这种怨恨的心态和报复感必然以邪恶的力量释放出来。当上矿长的宋长玉采用复仇的方式对唐洪涛进行打击。一是向组织部和上级部门写信揭发唐洪涛贪污受贿和对矿难隐瞒不报,二是通过占有其女儿唐丽华进行报复,完成农村人对城里人的征服,彻底释放自己压抑性的怨恨心态。从道德的层面上,宋长玉的做法是卑鄙的,是泯灭良知的,应该受到谴责。但重要的是,放在城乡二元冲突和社会转型的特定背景下,小说真实而生动地还原和展示了城市化进城中农村青年人在实现自身价值的过程中所生成的生存性情感,即作为弱者所表现出的怨恨心态。正如刘小枫所言:这种现代怨恨涉及到生存性的伤害,生存行的隐忍和生存性的无能感,在本质上是一种生存性的伦理情绪[5]。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使得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心理结构充分彰显出来,体现出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
三、放纵欲望与惩罚
按照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康的理解,欲望是人的本质,欲望主体渴望“在看自己的时候是以他者的眼睛来看自己,因为如果没有作为他者的形象,他不能看到自己”[6]。也就是说,欲望主体喜欢用他者的目光打量自己,渴望被他者所尊重,所羡慕,以填补自己的原始缺失。宋长玉试图以婚姻为跳板,加上自我奋斗,获取城里人的身份。这种欲望逻辑,是建立在对城里人身份的想象性理解基础之上的。作为心目中的他者形象,城里人是宋长玉所认同的理想自我,是为了化解自我生存中无法逃脱的匮乏和不完美性所作出的努力。换句话说,宋长玉幻想自己能像城里人一样生活,只有这样,他才能感受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因此,宋长玉受这种欲望的驱使,决定走自己的生活道路,渴望将欲望对象拥为己有,表现出很强的进取性、攻击性和占有欲,促使自己不断奋斗和努力。
城里人身份在表述上是空洞的、笼统的,甚至是想象性的。而金钱、财富、权力是现代城市生活品质和精神方式的重要表征,每时每刻都在彰显现代城里人的身份特征。由于长期的贫困造成宋长玉开始他的追求时,就把对金钱作为欲望对象,用金钱缔造自己的价值和表征自己的身份。一开始宋长玉想通过婚姻的形式来摆脱自己在经济上的弱势地位,失败之后落难红煤厂,宋长玉越来越意识到金钱在生活中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他兴办旅游业,从中提取利润,向游客出售假的红煤厂大蒜来获取差价,继而以廉价的价格承包红煤厂的小煤窑,短时间就发了财。有了经济资本之后,他才敢和矿长唐洪涛叫板,才能感觉“现在有资格与书记和乡长对话”,才能扳倒在精神上压迫了他全家几十年的村支书宋海林。在征服唐丽华的过程中,金钱同样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与唐丽华的几次约会中,宋长玉都出手比较大方,送二千元给她女儿买礼物,在温馨典雅的咖啡屋请唐丽华喝高档鸡尾酒。而对于唐丽华来说,咖啡屋从来没来过,鸡尾酒也从来没喝过,这让作为城里人的唐丽华感到羡慕,甚至让她感觉自己在宋长玉面前都成了“土老帽”。在这个意义上,宋长玉感觉到被唐丽华所喜欢、所羡慕,在将唐丽华的身体压在下面时,认同理想自我的欲望得到暂时的满足。同时,他也坚定自己的金钱观,“钱是什么?钱是钥匙,是打开女人的钥匙。有了这把万能的钥匙,女人是不难打开的。不管什么样的女人,都有可能被打开”[2]257。的确,金钱成为宋长玉在编制社会关系中的润滑剂,为扩展交往和生存空间提供了便利。当万种风情的金钱和凌驾于芸芸众生之上的权力相遇的时候,人的欲望就会日益膨胀,容易达到彻底放纵的境地。人生的理想、人性的光辉和伦理关怀将被利益熏心的人们弃之一旁。宋长玉利用当权者卖官,有钱者买官的游戏规则,拉拢乡党委书记和乡长,让自己的弟弟当上了村支书;他贿赂阳正市煤管局局长王利民,为省煤管局官员出嫖资,和当权者达成一片,好让自己无证经营的煤矿正常运营;为了提高生产和获得更多利润,他以包工头的形式欺压矿上的农民工;他讨好岳父,最终加入中国共产党,获得了为今后继续发展的政治资本。宋长玉心里明白,只有牢牢地掌握了权力,才能有可能获得更多的金钱,才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权力的掌控也意味着他自己被压抑的力比多和最疯狂的梦想得到相当程度的满足。但是,他丝毫没有意识到,人的情感一旦寄托在无动于衷的中介物上,将金钱和权力攀升至目的的高度,生命的感觉注定要随之萎缩,变得越来越枯萎和无聊。整天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架子端的高高的宋长玉,在报社通讯员商小亮身上获得了轻而易举的满足,到煤管局经营的洗浴中心嫖妓,回到家还和妻子温存一番,愧疚和良知被日益放纵的欲望肢解得支离破碎,人性美好的一面荡然无存。
如果对欲望不加以干预、约束和驯服,必然导致人性的堕落,罪恶和惩罚将随时降临到欲望主体身上。正如刘庆邦所言:“社会从物质匮乏到全面物质化,人的身体成了欲望的盛筵,人对金钱的索取也到了疯狂的程度。频发的矿难是物欲横流结出的一个恶果。”[7]在小说的后半部分中写道,由于煤管局的玩忽职守,纵容了宋长玉对煤矿的疯狂滥采,红煤厂水资源枯竭,水位下降,最终导致井下透水事故,17人遇难。对于这么大的矿难和罪恶,宋长玉本该接受法律制裁,但是,作者却安排他上了南下的火车。显然,对宋长玉的惩罚偏离了基本的道德观念和法治观念。作者也并没有设置像路遥《人生》中德顺老汉那样的道德模范对这种违背基本道德观念的人物和事件进行训斥和说教,而是在小说中将对放纵欲望的宋长玉的惩罚和叙事话语紧密结合在起来,也就是将小说多处叙述的美好的自然景色和后来恶化的生态形成鲜明的对比来营造具体的道德意识和生态伦理诉求。小说中借杨师傅的口中这样叙述道:“红煤厂村前有一条小河,河边有柳树,河里是常流水。水里有鱼有虾,还有螃蟹。村后是一座青山,半山腰有一座古寺院的遗址,半截儿砖塔还矗立在那里。”[2]52宋长玉和唐丽华谈恋爱时还专门到过红煤厂,曾被那里原生态的山水风光所震撼。宋长玉落难到红煤厂,借助那里的自然风光搞旅游开发,但是,宋长玉滥采煤矿之后,红煤厂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因为缺水,山上的树木几乎死了一半。“已经死了的,枝干发枯,发黑。没有死的,树叶也发干发毛,一片燥色。山林间没有了水汽,也就没有了灵气,路边的野花没有了,鸟鸣也听不到了。偶尔有风吹来,都是干风,灼得人心起躁。那座古塔的情况更糟了,由于地基下沉,使古塔的塔身裂开了一道缝。”[2]350不难看出,宋长玉等人是自然生态的破坏者,他们竭泽而渔式的毁灭性开采,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破坏和资源枯竭,而生态恶化势必也反过来无情地惩罚和报复宋长玉,让其成为亡命天涯的罪犯,沦落为漂泊无根的异乡人。作者跳出了利用传统道德观念进行批判的写作思路,不再担当传统道德观念和价值体系的说教者和宣扬者,而将批判现实的精神自然镶嵌在简单而深刻的叙事话语中,透射出一种非常微妙和生动的叙事伦理。正如刘小枫所言:“叙事伦理讲述个人经历的生命故事,通过个人经历的叙事提出关于生命感觉的问题,营建具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8]《红煤》虽然讲述了宋长玉个人奋斗的故事,但是这种人生的经历复原了充满质感和律动的生命感觉。如果说,美好的自然象征着宋长玉原本质朴、善良的一面,那么,恶化的生态则预示着宋长玉真实生命感觉的枯萎和凋零,进一步讲,宋长玉的本真性需要却被异化自我的欲望取代,生命终究会被不加节制的欲望所吞噬,人生的悲剧与自然生态的变化紧密结合起来,互为因果,相辅相成。因此,我以为,与其说这种惩罚宋长玉的方式表达出作者对宋长玉命运的同情、理解和呵护,不如说这样更能体现出作者的人性关怀,他把读者引向了对人类生存和自然生态问题的忧思,足以彰显出小说独特的伦理韵味。
四、结 语
人性是一座富矿。刘庆邦用掘进巷道的扎实方法,不断向人性深处掘进。《红煤》立足于社会转型期农村青年逃离土地进入城市之后生存状态的变迁,紧紧抓住身份的转换、怨恨心态、欲望的满足和放纵等人生的心理事实,在处理这些能够体现人性深度的心理事实上,作家不矫揉造作,不盲目跟随写作时尚,不将人性绝对超越历史和文化,不将人性变成“神性”或“兽性”,而是真实地还原生存变迁中人性的善恶、美丑和是非,在诚实和质朴的叙事风格中让人们明朗自己的道德困境和生存信念,启示人们重新找回生命的感觉,重新拾回被人性中的丑恶所抹去的自我,进而彻底释放出人性这座富矿的高效能量。这就是《红煤》独特的审美精神诉求。
[1] 刘庆邦,萧符.写作是人生的一种修行 [J].上海文学,2010(1):98.
[2] 刘庆邦.红煤[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
[3] 阿兰·德波顿.身份的焦虑 [M].陈广兴,南治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7.
[4] 成伯清.怨恨与承认——一种社会学的探索 [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5):64.
[5]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 [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362.
[6] 拉康.拉康选集 [M].褚孝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408.
[7] 夏榆.刘庆邦眼中的矿区生活 [N].南方周末,2004-12-30(06).
[8]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 [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