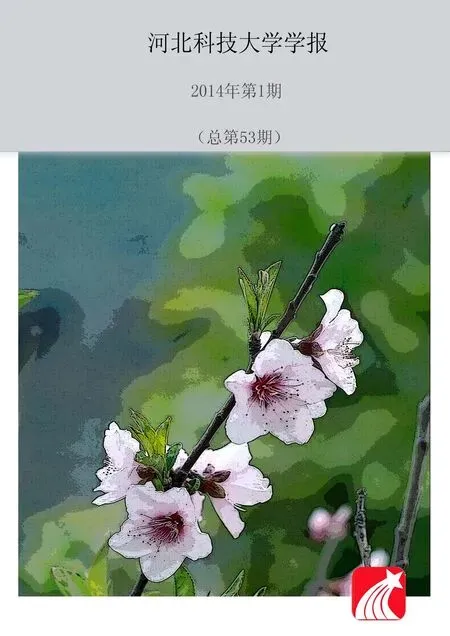浪漫传奇中的真实
——《奥兰多: 一部传记》中的历史观
于 佳 慧
(山东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济南 250199 )
出版于1928年的《奥兰多: 一部传记》(以下简称《奥兰多》)被认为是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作品中最富于浪漫传奇色彩的一部小说,被誉为世界上最长最优美的情书。这部小说表面看似是一部人物传记,实际却是嬉戏般的浪漫传奇。作者通过主人公奥兰多穿越时间、跨越性别的传奇经历,以独特的视角审视历史、重构历史,在嬉戏中对历史的真实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一、传记掩盖下的浪漫嬉戏
《奥兰多》讲述了伊丽莎白时代年轻贵族奥兰多的故事。叙述开始于伊丽莎白时代末期,结束于伍尔夫创作这部小说的“现世”,历时四百年,而此时奥兰多只有36岁。在16世纪,年轻的奥兰多成为伊丽莎白女王的情人,初入宫廷。大霜冻期间, 奥兰多和一位俄罗斯公主展开一段短暂而激烈的感情,不能自拔,结果却失恋亦失宠,隐居乡间祖宅。热爱文学与诗歌的奥兰多相识并资助颇有名气的诗人格林,却受到戏弄。后来,他因不堪忍受女大公无休止的骚扰,逃离祖宅,并被查尔斯二世委派出使土耳其。在君士坦丁堡的一场动乱中的大火之后,奥兰多变为女子,离开官场,与一群吉普赛人为伍。而后她返回英国,进入安妮女王时代的英国上流社会。作为名媛淑女,她结识了蒲伯、艾迪生等当时著名文人。在注重家庭和传统的维多利亚时期,奥兰多被迫向时代潮流妥协,结婚生子。后来,她赢了旷日持久的继承权官司,夺回了祖屋,并最终完成了她创作了近四百年的长诗。
从表面看,《奥兰多》似乎是一部传统的人物传记。首先,小说的副标题即为“一部传记”;其次,这部小说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特点,即作者故意在正文前后加上了“序言”和“索引”两部分,并在正文中使用脚注、插图。这都使这部小说看起来像一部严肃的人物传记,甚至颇有学术研究论文的气息。再者,伍尔夫的日记和信件显示薇塔·萨克维尔·韦斯特(Vita Sackville-West)是小说主人公奥兰多的原型。薇塔是英国作家、诗人,1927年和1933年连续两届获得霍桑登奖(Hawthornden)。她出身贵族,因其多彩而奢华的上等社会生活而闻名。她是一名双性恋者,具有明显的双性倾向,曾热情而大胆地卷入一系列风流韵事中,其中以与伍尔芙本人的情事尤为出名。由于她的女性身份,薇塔曾经在一场诉讼中失去了家族产业。从薇塔的生平中可以看出,她与小说人物奥兰多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然而,尽管“披着”人物传记的“外衣”,但是这部小说为读者讲述了一系列令人惊异的事件。奥兰多穿越时间、跨越性别的事迹在实际的世界中似乎永远无法实现。伍尔夫叙述的人物生平实际上是人物传记掩盖下浪漫传奇的嬉戏。
首先,《奥兰多》中的人物与现实中的人物相比,具有明显的多维性。伍尔夫认为,人的自我是多维度的,一个人往往在特定时刻呈现不同的自我,包括男女这两种性别属性等因素。“传记只需叙述六七个自我,就可以认为是完整的了,而一个人完全可能有上千个自我”。[1](P182)人物的诸多自我“好似侍者手中一摞盘子”,有着不同的秉性和喜好,“因此一个只肯下雨时来,一个要房间里有绿窗帘才来……”。[1](P182)读者可以看到,小说中奥兰多的人生远远比其原型的现实生活丰富多彩,性格也更加多变。小说中的叙述者说奥兰多也有许多迥异的自我,而小说的篇幅无法一一描述。正如Fleishman所说,从伊丽莎白时代到维多利亚时代,时移势迁,奥兰多的性格特点也从“英勇而慷慨的男子”和“时时陷入冥想的隐士”变为“男文豪的女崇拜者”和“爱脸红、易晕倒的穿着衬裙的女人”。[2](P238~239)小说中其他人物的自我也体现出明显的多维性,如女大公哈里特/大公哈利。当奥兰多是一位年轻的贵族男子时,她以女性的身份出现,无休止地追求他。当奥兰多变为女性时,他又以男性的形象出现,继续纠缠奥兰多。
《奥兰多》的传奇性还体现在其作者对时间概念嬉戏般的处理上。时间的概念在伍尔夫小说中常常占有重要的地位。伍尔夫擅长把多种时间序列混合交错在一起,以形成多维度的时间概念,起到主题或叙述方面的作用。正如小说中的人物个性一样,《奥兰多》中的时间也具有明显的多维性。主人公奥兰多在经历了四百年的风风雨雨后,年龄只有36岁,是超自然的。瞿世镜认为,《奥兰多》中时间的多维性体现在宇宙时间、钟表时间和心理时间这三种时间序列的交错融合。[3](P145)笔者认为《奥兰多》中不只存在这三种时间序列,还存在历史时间与这三者的交融。历史时间是人们寻求社会价值或历史意义的框架[4](P65),在男权社会往往体现在“建功立业”上,或是对现世社会产生影响,或是在历史上“永垂不朽”。奥兰多见证了英国四百年的风云变幻,期间的伟人和他们的丰功伟绩不可计数。然而,与漫长的钟表时间和历史时间相比较,心理时间和宇宙时间却仅有短短的几十年。无论一位伟人在历史时间的范畴内如何永垂不朽,其影响从宇宙时间序列看也只是白驹过隙。身为女子的奥兰多在埋葬着先祖的墓地间思考“不过三四百年前,这些骷髅的主人,如同现代的所有新贵,正在这个世界上奔走钻营,……建大宅,谋高官,最终显赫一时”[1](P99)。因此,那些遗骨“也多少失去了它们的神圣意义”[1](P99)。由此,伍尔夫通过奥兰多的沉思揭示出“建功立业”这一男权社会中衡量历史时间的标准的虚伪性。在这种融合中,人物的主观意识可以任意控制有限的钟表时间,使其超越历史时间,在无限的宇宙时间中自由活动。由于人的主观意识的作用,钟表时间可以拉长或者缩短:一个小时“甚至可能超出其时钟长度的五十或一百倍”,但是也有可能“由一秒钟来精确表示。”[1](P53)因此,奥兰多的年岁可能在一上午增加二十岁,而在有的星期则只增加了三秒钟。通过表现人物的主观心理时间, 伍尔夫不仅表达了她独特的时间观、历史观,还使奥兰多跨越四百年的传奇故事能够得到延续和统一。
伍尔夫本人曾说这部小说“只是儿童的嬉戏”,“在为其他严肃、诗意而又实验性的作品的形式殚精竭虑后”的一次“离经叛道”。[5](P84,131)而在这部嬉戏似的作品中,伍尔夫通过多维度的人物自我和时间概念,展现出其独特的世界观、时间观和历史观,表达了严肃的主题。
二、嬉戏中隐藏的历史重构
虽然《奥兰多》是一部充满了嬉戏色彩的浪漫传奇,但是伍尔夫通过奥兰多四百年的奇幻经历,折射出了英国历史的风云变幻,并对之进行了重构。
《奥兰多》反映了萨克维尔家族的历史。伍尔夫在1927年10月10日给薇塔的信中问:“[如果这部小说]是关于你以及你肉体的欲望和思想的诱惑,你是否介意?”[6](P181~203)由此可见, “奥兰多是薇塔的人生延续了三个多世纪的魔术幻景。”[6](P181~203)首先,除前文已经提及的几点外,还有一些地方体现出这部小说与萨克维尔家族及薇塔本人的密切联系。小说中的许多人物在薇塔的现实生活中可以找到原型:萨沙和女大公哈里特、大公哈利的原型都曾是她的恋人,谢尔默丁的原型是她的丈夫英国外交官兼作家尼尔逊爵士。小说中对奥兰多家族的描述也恰如其分地展示了萨克维尔家族的地位。甚至小说中的插图也都基于萨克维尔家族和薇塔本人的肖像。[7](VII)再者,尽管这部小说的情节似乎奇异而令人难以置信,一些学者还是意识到了其中的现实主义因素。Susan Dick认为《奥兰多》中叙述了许多真实的历史事件,人物的生活都基于现实情况,奥兰多遇到的人和物都以现实主义的手法详细地展现出来。[8](P50~70)这部小说可以被看作是萨克维尔家族四百年历史的缩影。
薇塔认为一代代萨克维尔家族的成员成为了其时代的典型,这是萨克维尔家族的重要性之所在。[2](P238~239)因此,这部小说也可以说是四百年英国历史的一个缩影。伍尔夫将奥兰多置于英国近四百年的风云变幻中,通过其社会身份和性别的变化,从不同的角度审视英国历史。詹姆士王统治时期,奥兰多作为一位年轻贵族见证了大霜冻期间贫苦的百姓冻饿致死,而国王和他的朝臣们日夜寻欢作乐的场景。随后,奥兰多体验了各个时代的特点:安妮女王时期的社交圈子枯燥而令人厌烦;18世纪贵族子弟们所谓的才学浪得虚名;维多利亚时期出现了帝国的概念;爱德华时代的科技带来了便利却侵蚀了自然,家庭规模也变小了。
由于奥兰多曾经是男性,因此在性别转换后,她更能够体会到社会强加给女性的诸多限制和种种不公正待遇。当已经变为女性的奥兰多乘坐“痴情女郎”号返回英国时,她开始对今后的生活十分担忧。她意识到自己一旦踏上英格兰的土地,就不能再像身为男子时随心所欲,“唯一能做的就是给老爷端茶倒水,察言观色。要放糖吗?要放奶油吗?”[1](P89)她开始反思女性的处境之根源和男权社会的虚伪。她回忆自己作为男子时的心理,发现自己当时想当然地认为“女性必须顺从、贞洁,浑身散发香气、衣着优雅。”然而,通过亲身体会,她发现女性并非天生如此,“她们只能通过最单调乏味的磨练,才能获得这些魅力,而没有这些魅力,她们就无法享受生活的乐趣。”[1](P88)男性认为“女人不过是群大孩子……聪明男人只是陪她们玩玩儿,奉承她们,哄她们开心”。而作为女人,奥兰多自己也很清楚尽管男人称赞、奉承她,却从来不尊重她的意见,从不真心实意地欣赏她的见解。她发觉“自己现在是多么看不起另一性别,即所谓的男子气概”[1](P89),因为她亲身看到身边的男性“只因看到女子的脚踝……就从桅杆上跌下来;穿着如盖伊·福克斯,招摇过市,只为得到女人的赞扬;拒绝让女人受教育,惟恐她会嘲笑你;明明拜倒在穿衬裙的黄毛丫头脚下,却俨然装出创世主的模样……”。[1](P89)进入维多利亚时期,女性的处境并没有任何改善,正如奥兰多看到的那样,婚姻、生儿育女和相夫教子成为普通女性的唯一归宿。直到1928年,英国女性才获得了同男性一样的财产权,奥兰多才得以收回祖宅。曾经身为男性的奥兰多在性别转换后,她更能够感同身受女性的诸多困境。通过奥兰多独特的视角,伍尔夫巧妙地展现出英国女性的处境,并反思女性的处境根源和男权社会的虚伪。
小说中,通过展现奥兰多的人生经历,作者还表达了其对文学正史质疑的态度。纵览奥兰多的一生,读者可以发现许多文人墨客给人留下的印象与其在文学正史中的形象大相径庭。当奥兰多还是身怀文学抱负的青年贵族男子时,当时颇有名气的诗人格林就颠覆了他对英国文学史上几位大文豪的印象。对于莎士比亚,格林评论说:“莎士比亚是写过一些还算不错的剧目;但他主要是抄袭马洛。”[1](P47)“如今,所有的年轻作家都受雇于书商,大量生产能卖钱的垃圾。莎士比亚就是这类生产的罪魁祸首,而且莎士比亚已经在付罚金了。”[1](P48)格林还评论了其他几位文豪:“马洛是个可爱的家伙,但对一个活了不到三十岁的小伙子,你能说些什么呢?至于布朗,他赞成以散文入诗,而人们很快就会厌烦这类别出心裁的玩意儿。多恩是个江湖骗子,用艰涩的词语来掩盖意义的贫乏。”[1](P47)通过格林的评论,伍尔夫提供了对英国文学史上这些文豪的另类解读。在她的笔下,这些文学大师的神圣光环被驱散,他们作为普通人的一面(如酗酒、拈花惹草、惧内等)被展示给读者。他们“说起话来,只管俏皮,不问信仰,做出事来,连廷臣们的胡作非为也相形见绌。”[1](P49)格林后来写文章嘲讽资助他的奥兰多。这种不磊落的做法,似乎也印证了他自己对文人的评价。在十八世纪,此时的奥兰多已变为年轻淑女,看待事物的视角发生了变化,她发现了令人崇拜的文豪身上的不尽人意之处:“蒲伯先生的讥讽嘲骂、艾迪生先生的居高临下、切斯菲尔德爵士的世事洞明。”[1](P126)而这些都让奥兰多对文人圈“倒了胃口”,十分失望。到了维多利亚时期,尽管身为女性的奥兰多亲身体会到女性作家在男性占绝对主导的社会中的弱势地位,但是她继续创作她的长诗《大橡树》,这暗示了越来越多女性在这个时期开始写作并开始得到重视。奥兰多最终于1928年出版了她的作品,这“隐喻了女作家的逐步崛起。”[9](P115)伍尔夫意欲重构英国文学史,使被压抑、被忽视的女性声音得以展露,并受到重视。
总之,伍尔夫通过奥兰多一生看似荒诞的传奇经历,反映了萨克维尔家族的历史;通过其社会身份和性别的变化,从不同的角度对英国历史进行审视。伍尔夫巧妙地将女性因被压抑而没有诉说出的“历史”展现出来,并反思男权社会的虚伪。作者还表达了其对文学正史质疑的态度,重新发掘了因受压抑而被忽视的女性声音。
三、关于历史真实性的反思
前文已经提及《奥兰多》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一部充满学术气息的人物传记,实则是人物传记掩盖下浪漫传奇的嬉戏。伍尔夫在嬉戏中通过奥兰多一生看似荒诞的传奇经历,对英国历史进行审视,重构了英国文学史。在这个过程中,伍尔夫对传统的人物传记和历史著作进行了质疑。她反思了传统历史著作的可信性,认为历史没有唯一的真相,只有相对接近于事实的多种可能。由于历史事实发生的物证和一手文字资料常常由于各种原因而轶散,因此后世对历史的了解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历史学家的推断。正如《奥兰多》中的叙述者所说,“载有可信记录的所有文件”被大火损毁之后,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只能尽力“根据虽已烧得支离破碎却留存至今的文件,一点点拼凑出一个梗概,却常常还得去推想、猜测,甚至要凭空虚构”。[1](P66)同样由于这一点,当传记作者们掌握的资料十分匮乏时,他们借助“一些无根据的流言蜚语、传说和轶闻”[1](P69)构建出奥兰多在君士坦丁堡的生活。
再者,即便是在历史物证和一手文字资料完整的情况下,由于历史著作是文字的再创造,因此无法避免作者的主观性干扰。因此,伍尔夫认为用传统手法描述历史无法展现事实,而文学的虚构也许更加可信:“做这件事,惟有信任那些不需要事实,或不尊重事实的人,即诗人和小说家,因为这是一个不存在事实的领域”[1](P110)。在描述奥兰多被封为公爵的庆典时,伍尔夫特意提供了三种迥异的叙述,使读者从不同的角度了解这个事件。小说的叙述者引用了一位英国海军军官的日记、将军之女的信件和当时的一篇新闻报道。海军军官的日记内容充满了当时典型的民族优越感,将军女儿的关注点在庆典上的佳肴华服、俊男美女,而新闻报道则相对客观。这样,通过并置这三种第一手“文献”,伍尔夫揭示出由于不同叙述者的关注点、叙述方式和叙述动机有所不同,他们对同一事件的描述会大相径庭。
伍尔夫还在小说中暗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使是同一类叙述者(甚至是同一位),对同样的对象也会产生不同看法。诗人格林第一次遇见奥兰多时,他对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文学评论道:“文学的伟大时代已经过去,……如今,所有的年轻作家都受雇于书商,大量生产能卖钱的垃圾,……当代的特征是十足的造作和疯狂的猎奇,而古希腊人片刻都不能容忍这两条中的任何一条。”[1](P48)然而,当他在维多利亚时期第二次遇见奥兰多时,他对伊丽莎白时期文学的评价却截然相反:“马洛、莎士比亚、本·琼生,这些人是巨人,……他们现在都不在了,……我们所有的青年作家,如今都被书商雇了来生产卖得出去的垃圾,赚钱付账给裁缝……这个时代的标志就是十足的造作和疯狂的猎奇。对所有这些,伊丽莎白时代的人一刻都不能容忍”[1](P163~164)。由上述两段引文可见,同一位评论者在不同时间对同一事物的观点截然相反,对两个现世的评价却惊人的类似,这再次印证了历史著作中存在固有的主观性。
伍尔夫认为,维多利亚时期的传统传记存在诸多不足,即虽然强调以事实为依据,讲求准确性,但是存在对人物进行美化的现象,以掩盖不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部分。“传记对象的一生更像是维多利亚式美德的反映,而不是一个真实的人的真实故事。”[10](P89)这使后世更加难以探究历史的真相。小说中奥兰多第二次昏睡的情节可以体现出伍尔夫对传统传记重道德而轻事实的批判。当传记作家对这含糊不清的情况不知如何处理,想要结篇了事的时候,“事实、坦率和诚实这三位守在传记作者墨水瓶旁的神祇,厉声喊道‘不行’!”[1](P74)并呼唤“真相”。这时,“纯洁”、“贞操”、“谦恭”三位小姐进入房间,她们齐唱:“真相你勿要跑出可怕的洞穴。藏得更隐蔽吧,可怕的真相。你在光天化日之下,炫耀最好未知和未做的事情:你揭示耻辱,让真相大白。”[1](P75~76)伍尔夫还通过这个情节批判了当时社会广泛存在的这种倾向。“纯洁”、“贞操”、“谦恭”三位小姐齐声唱道:“那些禁止别人、拒绝别人的人,那些无缘无故敬畏、莫名其妙赞美的人……那些宁愿视而不见、孤陋寡闻的人,喜爱阴暗的人,毫无由来仍然崇拜我们的人”仍然欢迎我们,“因为我们给了他们财富、成功、舒适和悠闲”。[1](P76)
伍尔夫在质疑传统历史著作和人物传记的可信性的同时,进行了创新性的尝试。海德格尔认为艺术是真相发生的场所,这是艺术作品和艺术家所依存的艺术的本质。[11](P197)这恰当地印证了伍尔夫对真相的看法。她认为,虽然事实是真相存在的基础,但是现世的事实无法准确地显露出隐含其中的真相。由于生活的真相是看不见摸不到的,因此获得真相的唯一途径就是在艺术作品中构建一个真相可以发生的虚构的世界。伍尔夫将虚构元素引入具有传记性质的作品《奥兰多》,将事实与虚构结合,试图将本应该讲求事实的传记和以虚构性为特点的小说相结合,以达到传递人物真实生活的目的。通过艺术的虚构,她真实地再现了薇塔和其家族以及整个英国历史。
四、结语
与伍尔夫其他的小说相比,《奥兰多》有着明显的特征。在创作时,伍尔夫没有采用其常用的意识流写法,而是在看似严谨的学术下隐藏着浪漫嬉戏,通过奥兰多穿越时间、跨越性别的传奇经历,以主人公独特的视角审视历史、重构历史,并对历史的真实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她认为历史没有唯一的真相,而有相对接近于事实的多种可能,而接近真相的唯一方法就是在艺术作品中构建一个真相可以发生的虚构的世界。通过虚构,她真实地再现了历史。
伍尔夫的历史观具有很强的前瞻性。随着女性主义和新历史主义批评理论的兴起,她对历史的反思得到了继续。女性主义批评家努力挖掘被压抑、忽视的女性作家及其作品,并重构了文学正史。而新历史主义批评家则提出历史是一种叙述。海登·怀特将历史编纂界定为一种文学与修辞的建构。他认为历史事实是在研究文献的基础上虚构出来的。[12](P24)伍尔夫对历史的态度和写作手法还影响了后来许多作家,如约翰·班维尔(John Banville)和约翰·福尔斯(John Fowls)等。因此,通过艺术与历史的结合,《奥兰多》实现了在虚构的浪漫传奇中构建世界,寻找真实。
参考文献:
[1][英]弗吉尼亚·伍尔夫.林 燕,译.奥兰多[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2]Fleishman,Avrom.The English Historical Novel: From Walter Scott to Virginia Woolf[M].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1971.
[3]瞿世镜.意识流小说家伍尔夫[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
[4]申富英.《达洛卫夫人》的叙事联接方式和时间序列[J].外国文学评论, 2005, (3).
[5]Woolf, Virginia.The Diary of Virginia Woolf(Volume III)[M].New York:Harcourt Brac Jovanovich, 1977.
[6]Glendnning, Victoria. Vita: A Biography of Vita Sackville-West[M].New York: Quill, 1983.
[7]Pawlowski, Merry M..Introduction[A].Virginia Woolf.Orlando:A Biography[M].Hertfordshire:Wordsworth, 2003.
[8]Dick, Susan. Literary Realism inMrsDalloway,TotheLighthouse,OrlandoandTheWaves[A].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Virginia Woolf[C].Shanghai: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9]吴庆宏.《奥兰多》中的文学与历史叙事[J].外国文学评论, 2010,(4).
[10]隋晓荻.弗吉尼亚·伍尔夫小说和传记中的事实与虚构[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0.
[11]Heidegger, Martin.Basic Writings: From Being and Time (1927) to the Task of Thinking(1964) [M].NY:HarperCollins, 1993.
[12][美]海登·怀特.旧事重提: 历史编纂是艺术还是科学?[A].陈启能,倪为国.书写历史(第一辑) [C]. 上海:三联书店,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