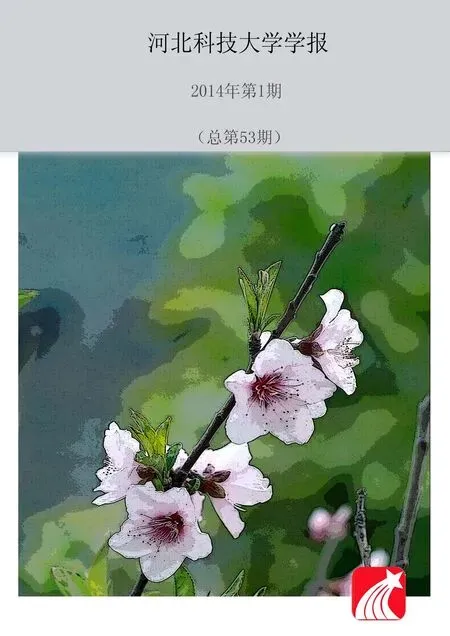试析《梅雨之夕》中的欲望法则
陈 泉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
在前弗洛伊德时代,关于疯狂的小说情节,为热心于叙述心理冲突的写作者提供了丰富的范式。而在20世纪前后,伴随着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动荡,人的焦虑、欲望的压抑、自我认同的危机,作为人类经验第一次由弗洛伊德医生结构为一个系统的知识体系。此后,对人类心理的深入探究开始了另一个方向,从日常生活显在的常态里面阅读隐含或扭曲的东西,在合理化秩序化的人群中寻找“正常”主体的症候。而作为“重写”弗洛伊德的拉康理论,在主体存在的社会网络层面,尤其于主体与语言的关系层面,激活了精神分析学的魅力。作为一个有着文本实验自觉的写作者,施蛰存的小说《梅雨之夕》于弱化情节的淡然之中,叙述了一个绮丽的街头幻景,这个幻景是由清丽素雅的男女邂逅构成表象的。本文尝试用精神分析的方法观照这篇小说的潜在结构以及无意识涌动深层的欲望法则。
一、同一条能指链上的两环:“雨”和“伞”的隐喻
(一)“雨”—“伞”,意识与无意识的冲突
雨,并且是梅雨时节黄昏时候,绵绵不绝,阴暗,潮湿,延伸至黑暗深处。文本一开始就为我们描画了一幅无意识涌动弥散的画面,或者说直接打开了一扇通向无意识世界的门。“至于人……用嫌恶的眼神望着这奈何不得的雨”,不可琢磨,无法把握,内心深沉的不安,这都来源于无意识世界欲望的释放。
“我”游走于街头,有所期待的正是内心欲望的满足。但是主体在此时又并非是不设防的,“我”手中的“伞”正是阻挡这种欲望的“盾牌”,行使着理性的功能,也即弗洛伊德意义上的拯救主体的工具。及至欲望对象的必然出现,主体历经了无意识欲望不断变幻面目的冲击,初恋女友、日本画中的古典少女,无意识为欲望的满足生产着合理化的幻象。但是在理性意识“伞”的规避下,这些幻象一一遭到了破坏,“……倒是我妻的嘴唇却与画里的少女的嘴唇有些仿佛的”,“……她是另一个不相干的少女”,通过颠覆欲望对象的形象,欲望最终被压抑。
在这场由无意识编织的欲望场景中,“伞”始终作为主体间理性交往的契机,规训和压抑着欲望的满足。“我”和姑娘同享了由“伞”所表征的理性秩序,在“伞”的保护下才能够进行交谈,才能够躲避路人的窥视。在文本的最后部分,“雨”的停止,欲望对象的丧失之后,主体依然紧握着手中的这把“伞”,这场欲望的冲突最后在“伞底下伴送着走的少女的声音”变成了“我”妻子的声音而引退离席。
(二)“雨”—“伞”,都市意识形态对都市主体的召唤
故事的背景是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这个时空线索在文本内外都能觅其踪迹。在近代中国,真正意义上的都市非上海莫属。在文本中,“公司”、“电车”这样的词汇,乘客中的俄罗斯人、日本妇人,都表征着这座城市的工业化与国际化。“我”的雨中漫步的娱乐,也是以“安逸的心境去看看都市的雨景”。在这个细节中,雨和都市景观被联系在一起,雨的能指为都市的能指所吸附。笼罩于整个文本的“雨”,成为都市意识形态的表征,这种意识形态又是由都市的所指生产出来的。同时,“意识形态将个体作为招呼或质询”[1],阿尔杜塞受拉康的启发做出这一阐释,在此文本中,个体被“招呼”(或译成“召唤”)成为主体的象征性转变的符号,正是“伞”在文本中承担的功能。也就是说“雨”与“伞”的对应性表现在被都市意识形态(以“雨”作为表征)成功召唤为都市主体的个体是以携带“伞”或与“伞”构成同一性关系作为标志的。
于是在文本中,我们可以发现三类主体,而前两种主体正是与上面所说的标志所捆绑存在的。第一类是以“我”为代表的久居都市惯于在雨中持伞的行人。第二类是久居都市但忘却带伞的行人。第三类在文本中设定为一名从外围进入都市的没有带伞的苏州姑娘。考察文本中的细节,可以发现后两者之间重要的区别,前者表现为无奈,而后者表现为焦虑。这个从苏州来的姑娘,带着他者的意识形态——古典和传统,这些在文本中不仅通过人物描画进行表征,并且由一个附加的小文本、一幅日本的古典画作作为辅助的修辞。
而“我”作为一名都市主体,发现了他者的焦虑,与他者共享“伞”的行为可以被视为都市意识形态发出的指令。意识形态的强大力量表现在它试图将所有卷入其中的个体全部召唤成主体。但是苏州姑娘乃是另外一种意识形态所召唤成功的主体。于是我们可以发现,在伞下发生的对话乃至心理的互相寻探,正是两种意识形态冲突的隐喻。但是意识形态总是把它的对象作为个体对待。尽管苏州姑娘始终保持着排拒,及至最后她脱离了“我”的伞(依据文本的交代,她的遁走是不知去向的),但是她永远都会受到这种都市意识形态的召唤。而后一种意识形态的召唤是相对微弱的,至少在文本的范围内还不足于证明对“我”的召唤将会是成功的,“我”在经过心里的涟漪之后,又回归到都市的家中。
(三)能指的运动与欲望的释放
在文本中,“雨”和“伞”的能指在不断地滑动,正是这样一条能指链作为文本结构的核心功能。“这个可能是没有尽头的从一个能指向另一个能指的运动就是拉康用欲望所指的东西”。[2]文本所指涉的欲望通过考察“雨”和“伞”这一对能指,它们不断地改变自身,从弗洛伊德式的主体内在无意识欲望以及冲突,到拉康式的外在社会关系这一欲望主体间的冲突,能指无法在欲望丛林中找寻它的所指。无论是作为功能或是作为生产的场域,真正的所指是不存在的。也正是在能指的运动场域之中,文本中潜在的性本能的冲突以及主体意识形态的召唤特性,此欲望法则之一端才得以释放。
二、欲望的二元结构:凝视的快感与规训
(一)作为观察者的“我”与欲望对象的客体化
在文本中的“我”是作为一个观察者存在的,甚至于整个文本都是由“我”的视觉网络所联结。通过“我”的视觉来一一呈现欲望元素,可以说在文本一开始,凝视的动力学已经开始运作。在欲望的法则之下,视网膜经验中筛选的对象都是通过欲望的认可来得到实现。从景观到行人,乃至有生命与无生命他者的细节,都被置于凝视的控制之中,从而建立起一个无遮蔽的欲望场域。而欲望主体的建构以及他对此场域的掌控也在同一时间完成。而假设被作为叙事文本的支撑点的一组叙事结构,就是欲望主体对欲望对象的凝视,或者也可以理解成在凝视的过程中欲望主体和欲望对象得到了实现。这一组凝视的动力学是通过三个步骤展开的。
第一步是性本能主导的情色窥视。“我”在接近欲望对象的过程是由无意识渐渐引导的,在文本中,“我”的“转弯”、“止步”都不是意识发出指令的结果,这一系列动作以及接下来的“移动”都可以转喻成无意识捕捉欲望收获快感的隐在语言。“我”开始了消费一个美丽的形象,从女性的“风仪”及至联想到“衣裳贴了肉”,采用了透视法般的窥视完成对女性身体的想象。这种隐秘的性快感缝合在文本的细节之中,主体间的无意识网络已经笼罩上了情色的意味。欲望主体享用了这种情色,并且完成了凝视的第一层快感。
第二步是附带淫虐意识的窥视。欲望主体在消费欲望对象的情色形象之过程中,又带有施虐的心理。对象在遭遇雨中的困境,呈现“窘急”的样态,而“我”“有一个残忍的好奇心”,以“怜悯和旁观”的心态细细观察和品味。“怜悯”是试图触及和占有对象多面体般的复杂形象,也是翻转这一多面体的柔软地带准备欲望的染指。“旁观”又是带有施虐性快感。主体在凝视的过程中充分享用着这层快感,也为进一步的凝视和对对象的全面控制做出了准备。
第三步是凝视动力学的最后一个环节,将欲望对象客体化。一旦欲望对象保持着她的主体性,欲望主体对对象的控制和占有就存在不可测的不稳定性,欲望的实现就会时常溢出强烈的不安。通过凝视将对象客体化是全面控制的最终途径,其表征为对象的静止和定格。固定化和平面化的仪式之后,丧失任何能动性的对象最终能作为一个欲望的客体被完全享用。但是这一层面的达成经过了两次努力,也经过了两次失败。第一次是试图将对象幻化为初恋女友,但是这种记忆中的形象已经不很完整,在与对象进行拼接的过程中,一再出现一些阻碍,两个真实性的个体很难完全重叠在一起。第二次是将对象与日本古典画中的少女形象进行了拼接,与之前的努力一样,欲望都达成了瞬间的成功,但是最后总还是有不和谐的元素从此间溢出,没有办法得到持续的静止和固定。文本的细节透露在这两次尝试的文字中都夹带了“我”的妻子的形象。显然,欲望主体对他建构的场域存在严重的误认,这类对快感进行规训的元素伴随着文本的展开自始至终地在行使着它的功能。
(二)三重规训:他者的凝视
拉康可能会赞同,被凝视的他者并非是消极被动的,它也在回头凝视它的观察者。欲望主体建构的欲望场域并非真实的无遮蔽的。萨特也认为,“一个个体的凝视,不可避免地要被纳入一个主体间的感觉网络中”[3]。他者的凝视同样带着欲望,但是在与欲望主体凝视的交锋中,于欲望主体划定的欲望场域内,行使着对欲望主体的凝视快感进行规训的功能。在文本中,他者的凝视有三重。
第一重是欲望对象对欲望主体的凝视。从“忧闷的眼光”到“惊异地看着我”,到“她凝视着半微笑着”,对象的主体性在困惑和审查着欲望主体的凝视,个体始终在保持着自我的情感反应来摆脱欲望主体对其控制。这种凝视自然也带着控制的意味,它表征着对欲望主体的侵入性有着完全的认识和把握。及至在与欲望主体共享着理性符号的“伞”,对象通过凝视的方式分析了与欲望主体之间的权力关系,从而将自我安置在一个安全的位置。同时,在欲望对象的凝视之中还夹杂着另一层控制,即由对象的欲望本身驱动的自我转变成欲望主体的冲动,比较明显的是这一层凝视的动机始终是被压制的,这种压力既来自欲望主体的凝视也来自自我理性意识的作用。及至到了分别的场景,“她微微地侧面向我说着”,对象放弃了凝视,而采取了逃离欲望场域的方式,一是因为规训的功能已没有必要,二是为了压制在凝视中自我成为欲望主体的危险。
第二重是他人对欲望主体(连带欲望对象)的凝视。这里的“他人”是指文本中的“店铺里有许多人”,他们是由欲望主体划定的欲望场域之外的意义上的他者,但是这些他者在文本中又渗入了这个场域之内。“他们歇下工作对我,或是我们,看着”,这些他者表征着社会网络对个体行为的监控,在他们的凝视中,欲望主体乃至欲望对象都还原为个体。欲望被裸露出来,这一层强有力的规训是足以使欲望主体感到沮丧的。在这一组权力关系中,他者的凝视连带控制着欲望对象,从而在另一层意义上钳制着欲望主体的满足。“伞”作为欲望场域中的理性“盾牌”,此时不仅压抑着这个场域的欲望游走,同时也成为向那些他者解释和澄清的符号,这也是文本中欲望法则的吊诡之处。
第三重是“妻”对欲望主体的凝视。“妻”在这里也是作为一个符号行使其功能。“妻”不仅表征着强大的社会秩序和权威,而且是以合法的欲望对象作为身份来呈现的。她“用着忧郁的眼光”,这一层凝视之中生产着三种意义,其一是对欲望主体的控制和惩戒;其二是对欲望对象的驱逐和争夺;其三是对欲望主体的说服和召唤。“忧郁”蕴含着这三种意义,对场域中的欲望进行了强有力的冲击。在文本的结尾处,“妻”不是作为符号,而是作为主体正式登场,这正是表征着这一层凝视的最终胜利以及她对自己身份的确认。
三、欲望的生产机制
(一)漫游及回忆的功能
梅雨的潮湿沉闷正如欲望的无处排解。“我”在雨中的行路成为了一次漫游,此时“家”这个目的地首先暧昧化了。“从江西路南口走到四川路桥,竟走了差不多半点钟光景。”时间的延迟与其说是暗示了主体无意识地在等待一场相遇,毋宁说是在找寻。正如在戴望舒的《雨巷》中这句“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两个作品之间的互文性关系。“希望逢着”成为漫游的目的,这是此一空间中欲望的起源,尽管是以无意识的形式。“我在上海住得很久,我懂得走路的规则。我为什么不在这个可以穿过去的时候走到对街去呢?我没知道”。这里受欲望激发的无意识成为引导主体行动的动力,并且是预言式的、宿命般的,这也是赋予小说神秘性与浪漫性的修辞术,同时也营造了一种诗意的氛围,如梦境一般(无意识的世界)。漫游是为了发现,“我”成为这个空间的观察者。与匆匆低头赶路的人们不同,“我”的视界遍布整个街道,“店铺”、“行人”、“有雨衣”和“无雨衣”的,及至“我”发现了停下的电车和下车的乘客。
“我”开始数头等车下来的乘客。为什么是头等车?“我”立刻做了解释,宛如是一份辩词,是对那个危险的预言的掩饰。“我”看到了五位乘客,前四位乘客立刻被捕捉为是一个俄罗斯人、一个日本妇人及两个像是宁波人的商人。“我”哪里是百无聊赖地探头张望呢,真切的是细细地观察。最重要的细节是,这四个人中间有三个人穿雨衣,另一个人带雨伞,只有第五个人手里没有伞身上也没有雨衣。而这个人恰好(是恰好吗?)是一位“丁香一样的姑娘”。没有任何雨具使这个姑娘暂时地构成一个缺失的主体,在来自另一主体欲望无意识的视界中,这一缺失就构成了对欲望主体的召唤。这难道不正是“我”在街道漫游所要找寻的对象吗?
在经历了一系列犹豫、纠结和唐突之后,“我”和姑娘终于相聚在同一把伞之下。但是这令“我”惶恐不安,这种不安源自欲望释放的危险将由主体来承担。欲望的生产引发主体内部极大的冲突,这表现为两个面向:一是“我开始诧异我的奇遇”,这是除“和我的妻之外不曾有的经历”,在欲望生产的间隙,意识主体开始对抗被欲望主导的无意识。二是“我心里吃惊了,这里有着我认识的人吗?或是有着认识他的人吗?”与肆无忌惮的无意识不同,意识生产着对禁忌的强烈警醒。需要一个媒介来克服这种冲突和危机,这个媒介就是回忆。“我”对初恋对象的回忆与身边的姑娘重叠起来,一旦被处理为是昨日恋人,这场故人相遇就既理所当然又自然而然。对“往事的回忆”在这里成为一种治疗和解放的手段,解除了不安与压抑的危机。[4]当然,这种假想是欲望对意识主体的安抚。
(二)作为欲望(无意识)结构的语言
语言是主体间性的媒介,在精神分析的场域中,语言也是对病症最直接的表达。被压制的欲望在一定程度上也显现为一种病理特征,语言的自反性充当了治疗与解放的手段。在《梅雨之夕》这个文本中,作为主体行动的语言由穿插交错的“实语和虚语”(拉康意义上的)构成。在这里实语指对话,虚语则指内心独白。但是文本中“我”的独白同样也具有对话特征。在“我”对姑娘说出第一句话之前的独白表现为无意识内部的辩驳和诘问。从“但我何以不即穿过去,走上了归家的路呢?”到“你有伞,但你不走,你愿意分一半伞给我,但还在等待什么更适当的时候呢?”,一共出现了16个问句。在这16个问句中,12个是“我”对自己的质问,另外4个是想象性的来自姑娘的问询。在这里“我”同时担任了发话者、听话者和分析者的三重角色,构成了欲望(无意识)的三重结构。这三重结构是欲望借助辩证法自我展开的过程,释放(正题)、压抑(反题)、来自欲望对象的同意(合题)。在这整个过程中,无意识在最后自我充当了分析者,通过分析得到治愈,成功使欲望的生产得以延续。“终归是我移近了这少女,将我的伞分一半遮蔽她”。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一行动的迈出立刻伴随着语言,即“我”对少女说出了第一句话(实语)。
在这场相遇中,“我”和少女的对话(实语)一共有六组,每一组实语对话中间又夹杂着若干虚语对白(内心独白)。少女在参与六组实语对话中,前三组是被动的,回应“我”的问题,而后三组则是主动的,谢绝“我”继续相送的行动。这些对话始终是单向度的,在前三组中少女只有回答没有提问,事实上使对话无法展开,而后三组的拒绝性语言只能使“我”以沉默作答。正是少女的语言溢出了这个欲望弥散的空间,使欲望不断遭受挫折。而中间的虚语,则是欲望为克服创伤构建出的幻象。尤其是在第二组对话之后,“刘吗?一定是假的。”“我”的无意识将少女的淡漠解释为欺骗。这样欲望的挫败就来源于外在的伤害,从而保持了自我(意识与无意识)内部的同一性。只要保持了这样的同一性,欲望仍然能够得到想象性的满足,而不是由内部高度紧张而导致的(精神)分裂。这就是文本中那幅日本画所扮演的补偿功能。在姑娘离开之后,“我”用“一个醒觉之后就要忘记了的梦”来总结这一次相遇,当然这是欲望的白日梦,梦醒了,欲望就退场。作为文本的结束,还有两个细节值得注意。其一是小说中最后出现的一句话(实语)“谁?”说话者是“我”的妻子,这是规训的语言,也是回归家庭的预言,最后也是梦彻底终结的声音,“从我妻的脸色上再也找不出那个女子的幻影”。另一个是“我”说了谎话。谎话成为欲望冒险的证据,实际上又暗示了欲望深陷于道德命题之中,这也是为什么弗洛伊德要把“升华”视为狂乱的力比多自身内在的要求。
四、结语
通过对《梅雨之夕》的阅读,可以发现作者有意识地借助了精神分析的方法。或者说这是一篇可以归入为心理分析范畴的小说。但是文本自身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它的开放性决定了事实上无法用一种方法来还原其本体。作为假设存在的本体分裂、散落在文本的细节之中,从而构成了可以不断去阅读和发现的潜在结构。任何一种阐释都决定了对另一种或多种阐释的可能性的遮蔽,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多样性的阅读和批评也许才有其价值。本文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尝试了对此文本进行一种还原的可能,考察了其中欲望的产生及其结构。这也是本文对《梅雨之夕》的一种阐释和一种读法,一种尽量去接近此文本的路径和企图。
[1][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德]泰奥德·阿尔多诺,等.方 杰,译.图绘意识形态[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125.
[2][英]特雷·伊格尔顿.伍晓明,译.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67.
[3][英]丹尼·卡拉拉罗.张卫东,张 生,赵顺宏,译.文化理论关键词[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43.
[4][美]赫伯特·马尔库塞.黄 勇,薛 民,译.爱欲与文明——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哲学探讨[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8.
——从学科规训视角出发